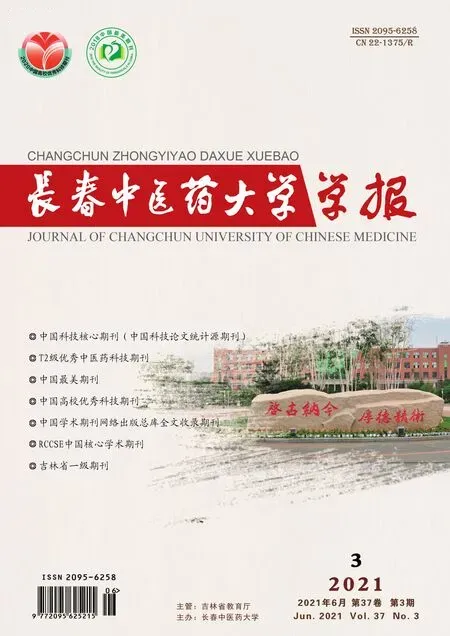中医运气学理论与疫病发病学研究
沈娟娟,张文风,马 丹,魏 岩,胡亚男,聂金娜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中医运气学理论以宇宙时空整体恒动观为理论依据,阐述自然环境及气候变化对人体生命规律的影响,运气学理论来源于《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大论。《黄帝内经》认识到天地、四时、阴阳的气化运转化生了世间万物,是天地万物化生的基础。阐明古人的生命观,即万物生息皆因天地阴阳感召化和,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天地阴阳的消长盈亏,影响物候及万物生命规律的变化[1]。正常的运气变化是宇宙万物生息的基础,同时异常的运气变化则会导致气候物候异常变化,导致人体发生疾病。运用运气理论推演值年的运气格局,判断气候变化、疾病性质、流行趋势,指导疫病预防、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1 运气学与疫病发病学研究
《黄帝内经》是最早记载疫病的著作,从中医运气学角度对疫病的发病进行深入剖析。《素问·刺法论》云:“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如此三年,变大疫也。”《素问·本病论》云:“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认为不同年分、不同节令的气候物候变化均会对人体产生影响易发民病,阐明了五运六气变化与瘟疫的关系。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阐明人秉承天地阴阳之气而生,人体脏腑阴阳与天地四时五行阴阳其象相通。天地气运异常、四时阴阳失衡则会影响人体脏腑气血失和、气机紊乱,大风苛毒伺机侵袭,易发生时行民病或疫病。《素问·刺法论》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疠大至,民善暴死。”《周礼》云:“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说明瘟疫是传染性强,病情传变迅速、凶险的流行性疾病。季节性、地域性是瘟疫发生的重要因素。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大论阐明不迁正,不退位年份易发生疫疠。不迁正为司天、在泉之气轮升不及,不退位为前一年的司天、在泉之气滞留不降,升降不前,在泉的右间气不能按时上升、司天的右间气不能按时下降,亦为“刚柔失守”,导致暴烈的郁气,轻则使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失常,重则发生疫疠[2]。岁运太过之年,气候变化剧烈,可三年后化生疫病。“岁运不及”“正气虚”“人神失守”此为三虚,三虚致疫是三年化疫的根本原因,伏邪郁藏而待发[3]。病机是刚柔失守,上刚干失其位,下柔干不能独主,则中运不能执法,天地不和,天运失序,三年后变疫[4]。
《黄帝内经》论述了60甲子总运行规律中,随着岁运递迁、客主加临、变异、胜负、郁发,出现德化政令之变、气候常异、万物荣枯,形成疫病流行的时空环境[5]。所以,运用运气学理论推演重大疫情可能出现的年分,研究疫病发病规律,分析病因病机指导临床治疗,对疫病防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运气学与疫病医家的学术及治方思想研究
历代名医继承《内经》运气理论,本于天人之理,从多角度进行挖掘,分析气候、藏象、病症变化规律,进一步推演五运六气格局,分析疫病致病机理。例如清代医家陆懋修梳理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发现,不同的流派医家的主要学术观点与所处的时代气候及环境变化因素密切相关,符合相应运气大司天时代气候特征[6]。
2.1 东汉时期——萌芽阶段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频发疫病,疫情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据考察,自建宁四年至建安二年间,发生五次大疫,其中四次疫病都发生在寒湿流行的时代背景下。此时期正值第48甲子(公元124-183年),大司天为太阳寒水,大在泉为太阴湿土。《伤寒杂病论·序》云:“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时期正处于寒疫流行时期,民病多见外感风寒证,仲景认为,外感寒邪伤人最甚,治疗当以辛温解表、温阳散寒为主,所创立的治疫经典名方如:桂枝汤、麻黄汤、四逆汤等均能体现运气理论思路。可见《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寒疫诊疗的基础。
2.2 两晋时期——拓展阶段
两晋时期战乱不断,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因此在一些医学著作中可看到内服、外敷、鼻吸、烧熏等相关防疫措施。魏晋时期医家王叔和提出:“非时之气为病”的观点,认为“时行之气”可导致传染性疾病发生。东晋时期医家葛洪著《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时行、瘟疫……源本小异。”并记载“天花”的临床特征。医家葛洪所处于第51甲子(公元304-364年),大司天为太阴湿土,大在泉为太阳寒水,整处于太阴湿土为病期间。观《肘后备急方》治疗以利湿清热解肌发表为主,例如:治疗时行伤寒用苦参煮酒以除湿;治疗时行疫疠一二日,头痛壮热烦躁,用麻黄解肌汤以发散解肌,利湿升脾,其用药规律均符合太阴湿土为病的大时代背景。
2.3 宋金元时期——详实阶段
宋末元初,战事频发,劳役繁重,疫病的变化趋于复杂。宋代政府成立医疗机构,大力宣传防疫措施,研制防疫方药,将预防疫病药方传印成册颁布全国,自宋代后对于疫病的认识已有长足的发展,形成较为系统的防疫机制。北宋时期医家刘完素一生经历2个大司天,第64甲子(公元1084-1143年),大司天为少阳相火,大在泉为厥阴风木;第65甲子(公元1144-1203年),大司天为阳明燥金,大在泉为少阴君火。两个甲子气运都以风火燥热为主,说明当时大环境应该多温多燥,民病多见热性传染性疾病,提出“六气皆能化火”的火热论观点,认为六经病症传变,从浅至深,多为热证,故用药多以寒凉为主。可见与仲景学术思想及用药规律有较大不同,说明刘完素所处时期气候寒温背景已有较大变化。
金元医家李东垣一生经历2个大司天,第65甲子(公元1144-1203年),大司天为阳明燥金,大在泉少阴君火。气运主要以燥火为主,泰和二年,发生了大头瘟,李东垣创立了普济消毒饮以清热解毒消肿。第66甲子(公元1204-1263年),大司天为太阳寒水,大在泉太阴湿土,气候背景以寒湿为主,湿寒为阴邪,易伤正气困脾胃,故李东垣认为,用药当以扶助阳气、补益脾胃为主,创立补中益气汤等代表方剂,后世医家尊其“补土派”。
元代医家朱丹溪一生经历2个大司天,第67甲子(公元1264-1323年),大司天为厥阴风木、大在泉为少阳相火;第68甲子(公元1324-1383年),大司天为少阴君火、大在泉为阳明燥金。两个甲子气运均主要以风火燥热为主,民病多以外感热症为主,燥热之邪最易伤阴,故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治疗主张用滋阴降火之法,为“滋阴派”代表医家。
2.4 明清时期——成熟阶段
明清时期是疫病爆发的顶峰时期,这段时期已形成较为成熟中医疫病学体系,并涌现出许多治疫名家。明末清初医家吴又可,42岁正值第73甲子(公元1624-1683年),大司天为厥阴风木,大在泉少阳相火,处于风火当令大气候背景时期。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中原地区温疫流行,吴又可著《瘟疫论》提出:“疠气”之说,认为“邪伏膜原”邪在少阳半表半里,创立了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
清代医家叶天士一生经历2个大司天,第73甲子(公元1642-1683年),大司天为厥阴风木、大在泉为少阳相火;第74甲子(公元1684-1743年),大司天为阳明燥金、大在泉为少阴君火。两个甲子气运主要以风火燥热为主,叶天士著《温热论》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观点以及“卫气营血”的辨证思路,其用药以轻灵著称,为温病学派代表医家。
清代医家吴鞠通,46岁正值第76甲子(公元1804-1963年),大司天为少阳相火、大在泉为厥阴风木,风火当令。吴鞠通著《温病条辨》,提出三焦辨证,将温病分为9类,创立“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犀角地黄汤”等著名方剂沿用至今。
3 运气学理论指导下的运气制方研究
运气七篇大论中对于五运六气理论的解释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主要论述了宇宙整体恒动观、运气的推演、临证治疗原则及制方之法等。《内经》阐明五运六气的气化异常,如六气不正与太过皆能化生疫病,故临证分析时应结合相应时间、空间因素对病症的影响。运气七篇大论提出了具有运气理论指导的临证治疗原则,是运气制方理论的萌芽与初步形成的阶段,没有具体的运气方。后世医家以此为本,结合临床经验,衍生出各具特点的运气方药,指导临床治疗。
3.1 运气方概念
运气方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运气方是在运气理论指导下分析病机,按照运气理论思路分析病症,制定治疗原则,组方用药均以运气理论为指导。狭义的运气方是指具体的运气方,例如:陈无择所创的运气方16方[7]。
3.2 运气制方依据
运气制方依据:1)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推演具体年代气候特征,分析流行民病的病症特点,酌情择药配伍形成特定的方剂,例如陈无择所创五运方和六气方;宋代《太医局诸科程文格》记载的六气组方。2)根据五运六气理论,选择现有的成方,例如伤寒方,温病方,四时感冒方的选用。张仲景将运气理论结合病症脉象运用于临床治疗中,可见《伤寒论》中诸多经方都能体现运气的理论思路。3)在通常辨证论治选方或经验通治方的基础上,根据病人的运气特点,结合药食适症加减[8]。
4 应用现代疫病临证实例的运气制方理论解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初发于武汉,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衔接长江、汉江,水域分布广阔。回顾2019全年武汉气候变化情况,上半年平均气温较往年偏高,入秋后以温燥气候特点为主,温燥之邪伏于肺。同年12月起武汉地区出现寒潮,并见多次降雨,阴雨连绵,气温骤降,气候特点以寒湿为主[9]。寒湿利于戾气滋生,寒湿裹挟戾气,或从口鼻而入,或从表而入,或直中于里,此为外敌;寒湿之邪易伤脾阳,受本年运气影响,木郁乘脾,脾阳本弱,其民易脾胃正气不足,脾虚运化无权,湿浊内生,此为内患;外敌内患相交,导致寒热错杂、寒湿疫毒闭肺困脾之时令疫病。究其病因,虽为寒湿,然疫病伤人,传变最速,且人有禀赋、年龄、体质之别,故寒湿疫气伤人,也可见化热、变燥、伤阴、致瘀、闭脱之变[10]。
新冠肺炎病因为寒湿,病位在肺与脾,病机核心为疫毒湿寒与伏燥搏结,损伤正气,疫毒闭肺困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认为,可将新冠肺炎分为初期寒湿郁肺、中期疫毒闭肺、重症期内闭外脱和恢复期肺脾气虚[11]。仝小林院士等专家,针对发病初期患者,症见乏力,周身酸痛,发热、恶寒、咳嗽、咽痛、纳呆、恶心呕吐、腹泻,舌质淡胖,齿痕,舌苔白厚腻、或腐腻,脉沉滑或濡等,提出运用“武汉抗疫方”治疗[12]。方药组成为麻黄、石膏、苦杏仁、羌活、葶苈子、贯众、地龙、徐长卿、藿香、佩兰、苍术、茯苓、白术、焦三仙、厚朴、焦槟榔、煨草果、生姜。本方为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藿朴夏苓汤、神术散、达原饮等化裁而成,以开通肺气、祛湿化浊、解毒通络。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凡此厥阴司天之政,……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新冠肺炎发生在己亥年终之气,己亥年岁运为土运不及之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为天刑年,全年气候变化剧烈。气运特点为土运不及,本运衰,所不胜者乘之,厥阴风木亢胜。本年终之气少阳相火加临太阳寒水,火热在内郁藏,寒气束表,伏邪郁藏。《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民病飱泄霍乱,体重腹痛……民食少失味。”己亥年土运不及,厥阴风木司天,木郁横逆脾土。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制定五运方为白术厚朴汤,治以益脾资胃,扶土抑肝[13]。可见,对于新冠肺炎初期病程阶段,治疗应以宣通肺气为主,并且注重恢复脾胃运化之职,及时截断疾病进一步传化,逐渐恢复体内正气。
5 结语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无失气宜。”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运气理论取法于自然,以天地阴阳转化、五行生克之理为本,观测自然气候,候查人体五脏,提出了内外气化环境交感互通的发病观。在辨证论治时,关注运气因素对人体疾病规律的影响,有利于确定更加恰当的治法方药,医因时识宜,圆通化裁。故以运气理论为依据,深化病症研究,可为预防疫病提供前瞻性信息,完善中医疫病诊疗体系,守正创新,传承中医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