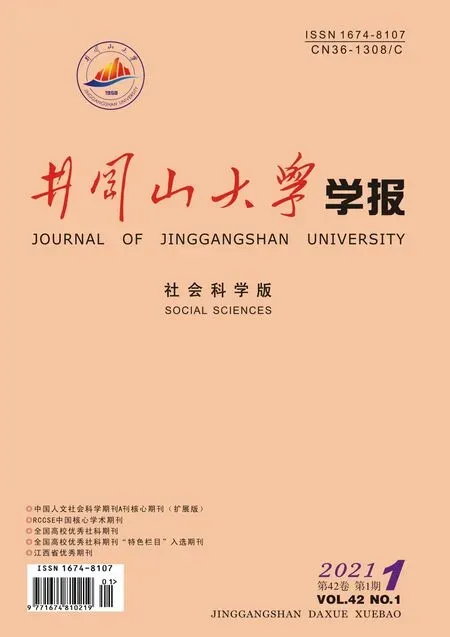谭其骧与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潘 晟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谭其骧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贡献, 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的重要研究对象, 也是近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对象。 除谭先生自述外①夏泉、曾金莲:《探寻谭其骧先生早年的学术足迹——以暨南大学为中心的考察》,《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3 期,第92-96 页。 第92 页脚注1、2、3 对谭先生自传与回忆性文字有较详细的回顾,提到了应《晋阳学刊》之邀大约1980 年由葛剑雄执笔的《谭其骧自传》,该自传收入《晋阳学刊》编辑部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2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361-373 页),稍经整理,又收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丛书第4 辑(第325-340 页);该文又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收入《世纪学人自述》丛书第4卷,标题改为《谭其骧自述》(2000 年,第101-114 页)。 另1981 年写成的《锲而不舍,终身以许之》,原载《浙江日报》1981 年5 月22 日第4版,收入百花文艺社2000 年出版社的《求索时空》(第241-251 页);1990 年后写成的《我与暨南》初刊于《暨南大学报》1990 年11 月25 日和12 月10 日两期上,后收入《求索时空》(第252-256 页)。 按:《谭其骧自传》还见于《文献》1982 年第1 期,第163-178 页。 另外还有《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文献》1982 年第4 期,第243-247 页)、《长水集》的《自序》(写于1984 年1 月3 日)和《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等。,最具代表性的是葛剑雄先生撰写的 《悠悠长水——谭其骧传》②葛剑雄所撰传记,初为《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继为《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014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葛剑雄文集》时,汇为《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版)。。 关于谭先生的学术贡献,正式的表述是葛剑雄《悼念谭其骧先生》,在列举《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之后,概括地指出谭先生在“中国历史政区和疆域、人口迁徙、民族分布、地名学、方志学、地理学史、地图学史研究和地理古籍整理等方面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③葛剑雄:《悼念谭其骧先生》,发表于《地理学报》1993 年第1 期,第97 页。 这是谭先生去世后,向学术界发布的正式悼念文字。大多数关于谭其骧学术贡献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大项目大成果,对于他在地理古籍整理,或者更宽一点讲, 历史地理文献方面的工作还缺乏关注,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图谈谈他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
一、 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绩概述
谭其骧先生极为重视历史文献学, 曾特别指出“扎实的历史文献学基础”是复旦史地所的学术风格与特色。[1]谭先生所讲的扎实的历史文献学自然不限于古代地理文献, 但古代地理文献应该是其中的核心, 他与历史文献有关的工作也主要表现在古代地理文献方面。古代地理文献,是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核心对象, 梳理谭先生在这方面的成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他亲自做的或者主持参与的工作,一是他呼吁或支持的工作。
(一)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绩
历史文献工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搜集、编目、整理、复制出版、注释、文献源流研究等。其中搜集,包括从各类公私机构发现、发掘新文献,并公诸于世。编目,包括古籍编目和现代研究论著编目。整理,主要是通过版本校勘的工作,恢复古书原貌,得到便于使用与流通的善本,具体表现就是今天通称的点校本。 复制出版,其形式多样,从传统的影钞,经由各种照相影印,到现在的扫描电子版, 宽泛一点也可以看作是文献整理的范畴, 但是严格一点讲这属于文献出版传播工作。 注释,可以有传统的解经训诂,古今注解汇聚的集解,也可以是白话今译,以及各种对字词、制度、典故、史事的考订与解释。 文献源流研究,则包括文献作者生平、成书经过、版本流传、作品价值等各种探究。谭其骧先生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方志编目。谭其骧第一份正式的学术工作是1932 年初——1934 年底在当时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馆员,在此期间他接受馆方安排,在原有基础上编纂了馆藏方志目录,即《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初编)。该馆藏方志目录,以1932 年底以前入藏为限,共5200 余部,除去复本共计3800余种,毛边铅印4 册。1933 年5 月起边编边印,陆续到1934 年下半年完成。
该目录的编纂,除了统一体例、改正疏谬或不恰当处之外, 谭其骧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创新是凡例第七条:
凡省志、府志、直隶州志及领有属县之直隶厅志用黑字排印,散州及厅县用普通字排印。志有名为直隶州而实际但志本州一邑者, 亦用普通字排印,有不标直隶之名而所志兼及全郡者,亦用黑字排印。
即通过不同的字体区别各地方志书地域等级与范围,使读者一目了然。谭其骧先生对这一创新极为重视,“我所看到过的其他任何方志目录都没有采用与此相同或类似的办法”。
同时,谭先生也对该目录的不足作了说明,他认为该目第十二条凡例标出各志金石类, 并不妥当,因为金石目录并非方志中最重要内容,不应予以特殊待遇。 但因旧目编者已付出劳动, 不便删除。 又,该目乡土志、乡镇志不入正目,别为附录,以及不采丛书中的方志,也是沿用旧例,认为不见得恰当。①详细情况,参见谭其骧:《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文献》1982 年第4 期,第243-247 页。 另部分细节校改,参见文榕生:《从图书馆员到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院士的启迪》,《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 年第1 期,第79-81 页。
(2)古地理文献校补与注释。谭先生很早就做了古地理文献校补与注释方面的工作,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的《〈辽史·地理志〉补正》(《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4 年3 月),《〈清史稿·地理志〉校正(一、直隶)》(《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 年4 月1 日),《〈清史稿·地理志〉 校正(二、 奉天)》(《禹贡半月刊》 第一卷第九期,1934年7 月1 日),《〈宋州郡志校勘记〉校补》(《禹贡半月刊》第6 卷第7 期,1936 年11 月),《〈补陈疆域志〉 校补》(《禹贡半月刊》 第5 卷第6、7 期,1936年6 月)等(上述诸文,都收入《长水集》)。
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二类, 第一类,《〈辽史·地理志〉补正》《〈清史稿·地理志〉校正》《〈补陈疆域志〉校补》主要是校正讹误,补充新说;第二类,《〈宋州郡志校勘记〉校补》则是整理前辈工作,并补正其说。 下文引用《〈补陈疆域志〉校补》以见谭先生古地理文献校补工作之一斑。
《〈补陈疆域志〉校补》前有一段序言,详细讨论了写作的缘起,以及对臧励和《补陈疆域志》得失的评价,寥寥几百字,直击要害:
《补陈疆域志》四卷,武进臧励和撰;旧无刻本,上海开明书店据稿本采入《二十五史补编》。其骧因王伯祥先生之介,得于排印时睹其校样焉。研读一过,深服作者用力至勤,体思至密,全书排列得宜,考定详审;洵足与其乡先辈洪氏父子之《补三国》、《补梁》等作,后先辉映,入著作之林矣。 惟是作史之难,不在有功,而在无过;补志尤然。 《补三国疆域志》纰缪甚多,故谢钟英为之补注,吴增仅别有《郡县表》之作,皆所以匡其不逮;而吴表仍有未尽处, 杨守敬复作为补校。 《东晋》《十六国》《补梁》诸志虽后无续辑,然以之与徐文范之《东晋南北朝舆地表》相校,则漏略立见,有不胜枚举者矣。臧氏此志,实亦未能例外。其骧前尝读《陈书》、《南史》,积有札记,以考证地理者居多,今即据以核臧著,凡可得资校补者百余条,因录以充《禹贡》篇幅,并就正于臧先生及世之大雅君子。[2](P104)
其具体条目做法大致如下。
卷一“扬州州治”条:
扬州州治,《陈书·程季文传》“世祖嗣位,除宣惠始兴王府, 限内中直兵参军, 是时王为扬州刺史,镇冶城。 ”
[补]废帝时高宗为刺史,太建末始兴王叔陵为刺史,治并在东府城。《世祖沈皇后传》:“刘师知矫敕谓高宗曰:‘今四方无事, 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叔陵传》:“太建九年除扬州刺史,十一年至都,治在东府。 ”[2](P104)
卷二“南江”条:
南江,陈于新吴立。 《陈书·周敷传》:“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 私署令长, 不受召, 唯敷独先入朝。 ”
[校]“南江”统指赣水所经诸郡,时属江州。犹言“南州”、“南川”、“南中”耳,非县名。 《敷传》原文,“琳平,授豫章太守,是时南江酋帅”云云。文义甚明。 此志不特误以为县,且以为长沙郡之属县,诚匪夷所思。 《华皎传》:“天嘉初,知江州事,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 不遵朝宪, 文帝令皎以法驭之”。正可为《敷传》此段作注解。《熊昙郎传》:“王琳东下,世祖征南川兵。 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奭毛欲沿流应赴。昙郎据新淦县应琳,带江为城,列舰断遏迪等,迪与法奭毛因帅南中兵筑城围之”。按其时江州分置高州,此所谓“南川”、“南中”者,统指江高二州而言也。《志》谓南江县陈于新吴立;按梁末曾于新吴置南江州,作者岂因是二致误欤?[2](P125)
统观全文,虽广征博引地志等书,但是诚谭先生在该文序言中所说,此文以其平日所积《陈书》《南史》札记为基础,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以本书纪传为基础进行校正。
谭其骧先生古地理文献注释的代表作, 则是《〈汉书·地理志〉选释》。[3]该文是1957 年应侯仁之先生之邀,为《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而作,住在青岛疗养所一个多月里做的注释。 虽然仅选注了《汉志》103 个郡国中的6 个,但是“它不折不扣地就是一篇历史地理典籍的研读法、 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论”。①张伟然:《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学问的敬意与温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1-13 页,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 年第3 期。
(3)古代地理文献影印、汇编、汇释。 《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影印出版。谭先生在古代地理文献影印方面的代表工作是将日本复制回国的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影印出版。 1986 年秋,谭其骧先生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赴日交流, 请斯波义信教授代为向东洋文库提出摄制一份《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照片的请求,得允,复制件携回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得知后有意影印出版, 并请谭先生撰写出版前言,因无明刻本比对,谭先生将复制件送交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曹婉如先生,请曹先生撰写前言。出版延宕,至1989 年年底正式发行,影印本前有谭其骧先生《序言》,曹宛如先生《前言》,都是对该书内容、作者、时代、版本等方面的讨论。此书的影印出版曾引起小风波,但是它推动了关于我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 在古籍影印出版方面有重要地位。
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 古代地理文献的汇编方面的代表性工作则是《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7 册)(1986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全书7 册,分为总论(论说、序跋)、总志(考释、序跋)、方志(考释:古地理、地方沿革、民族、杂说;序跋,按省区分门别类,并附修志义例)、河渠水利(考释、记叙、策议、杂说、序跋)、山川(考释、杂说、序跋)、游记(山、水、其他、序跋)、古迹名胜(考释、杂记、序跋)、外纪·边防(考释、序跋)九个部分,附录为所收文集目录,所收文集著者姓氏索引,全书300 万字。
谭先生主编该书, 是依据王重民20 世纪30年代编的《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进行的,当时他协助王重民编排了地理类的篇目, 深深感到这对于了解、利用清人的学术成果很便利,而80 年代的时候要利用清人文集还很不方便, 遂在复旦史地所同仁的协助下于1983 年开始编纂,1984年7 月份完成收集、标点的工作。参加该项标点的有“王妙发、王颋、王福兴、王翠兰、朱荣琴、朱毅、贡久谅、佟佩琴、陈家麟、杨正泰、周云鹤、周源和、胡菊兴、祝培坤、钱林书、葛剑雄。”编辑工作由“葛剑雄、杨正泰负责,全书由葛剑雄校定”。①谭其骧:《前言》,《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 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5 页。 《前言》后的落款时间是1984 年7 月23日。
《历代地理志汇释》是谭先生主持的另一项大工程。 由于《历代地理志汇释》的《丛刊前言》没有落款, 故公开发布的材料中未见该工程明确启动时间的记载。 谭先生之后,由其学生接续,陆续推进正史十六部地理志的汇释。 所见安徽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的有张修桂、 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2001 年),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2002年),郭黎安《宋史地理志汇释》(2003 年),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2006 年),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2006 年),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2007 年),孟刚、邹逸麟《晋书地理志汇释》(2018年),华林甫、赖青寿、薛亚玲《隋书地理志汇释》(2019 年)等。
(4)古代地理文献校点。古代地理文献校点方面的代表性工作是主持《肇域志》的整理点校。《肇域志》的点校整理,是“文革”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第一件事,相关领导及学界极为关注,影响很大,压力也就很大。从1982 年10 月谭其骧在昆明主持首次工作会议,到200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用去了20 多年时间。
由于《肇域志》并非定稿,只是资料汇集的草本, 离成书的程度还较远, 而传世钞本又都不理想,整理难度极大。 “文革”前吴杰做过《肇域志》的整理工作,当时是打散稿本顺序,按《大明一统志》的系统来编排,学术界意见很大,认为面目完全变了。 因此最初谭先生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认为完全不动,编一个目录说明,又有人认为不妥,应调整,等等。还有顾炎武《肇域志》中的引文是否都核对,是否核对方志,整理凡例的详细程度,政区的标识方法,校记的写法等,谭其骧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②朱惠荣:《谭其骧先生谈〈肇域志〉整理》,《西南古籍研究》2008 年辑,第28-31 页。正文关于谭其骧与《肇域志》工作的文字,皆依据此文。
虽然谭先生说答应两年完成, 不能拖太长时间, 但是该书的点校整理工作最后正式出版却依然是跌宕到了2004 年。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权页可知,参加点校的学者有“王天良、王文楚、王颋、朱惠荣、李自强、李孝友、李东平、周振鹤、胡菊兴、葛剑雄、杨正泰、郑宝恒”12 人。
(5)地理文献编纂。谭先生还有撰写地理志书的宏愿,虽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是仍然留下了一篇代表作,即《清代东三省疆理志》(《长水集》第159-184 页,原载《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1940年)。
据正文之前的“序言”,谭先生撰写该志的缘起是,《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是乾隆时期之作,《吉林通志》则光绪中叶之作,都不足以尽一代之制。而当时新出的《清史稿·地理志》及《黑龙江志》稿、《奉天通志》在谭先生看来有“草率成编,脱略刺谬”之嫌,因此他准备撰写一部东北地区的通志以为一代之备。 其最初的设想是“参稽群籍,荟萃众说,首述经制沿革,次志境界所至,并及城治、户口、邮驿、卡伦、界牌、鄂博、铁道、电报、矿局诸端,凡属政令之设施,靡所或遗。 征信阙疑,力求详而不诬,简而不阙,庶几勘备一代之掌焉。”但是实际并未达到, 谭先生在该志刊出时指出:“此编初拟规模颇备,旋以薄于事役,匆匆整装南行,致未及将全文杀青。 兹所刊布者,仅限于吉林、黑龙江二省之沿革、疆域两部分,与序文所述内容,广狭迥不相伦,惟阅者谅焉。 ”③谭其骧:《清代东三省疆理志》,《长水集》第159 页脚注。
(6) 古地图文献研究。 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应接触过大量古旧地图,但是写成文字的古地图研究文章并不多, 专门讨论古地图文献的主要就是《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第2 期,第43-48 页),④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 年第2 期,第43-48 页。 另一篇《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5 年第6 期(后收入《古地图论文集》,修改后收入湖南人出版社1981 年的《马王堆汉墓研究》,收入《长水集》),以及《鄂君启节铭文释地》,《〈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等主要是历史地理问题的讨论,故不论。以及为曹婉如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写的《序》,《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影印出版的《序言》。
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一文中,谭先生详细考察了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 从图例、注记、山脉、水道绘制方法、比例等方面,进行古今对比, 充分肯定了该地图在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重新评价了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史。
而《中国古代地图集序》则在倡导整理古旧地图资料的时候, 对古代地图流传较少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1)“图的摹绘比书的传写要难得多”;(2)“古代的制图技术还不大可能在等大的缣帛或纸张上, 用多种不同比例尺来画出面积大小不同、内容多少不一的地图来,图幅的宽度长度一般都得跟着所画地域范围的大小和内容的多寡或大或小或长或方”,由于图形和大小形状差异很大,而难以装订成册,以单幅形式收藏,保存不易;(3)地图几乎全部都是官府收藏,历经劫难不易幸存;(4)地图因难以摹绘、大小不一而难以被汇集入书。[4]谭先生对古代地图难以流传的原因的概括, 对于进一步推动地图学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二)谭其骧先生对历史地理文献工作的呼与鼓
呼吁鼓励搜集、整理、汇编古文献。 1982 年《文献》第1 期发表了一组《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的文章,谭其骧写的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大量翻印古籍》,谭先生有感于当时市面上古籍奇缺的现状,认为要大量翻印古籍,既可以保护古籍,也有利于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 只有大量翻印古籍才有可能大规模开展古籍整理,培养从事标点、校勘、注释和今译工作的人才。因此谭先生大声呼吁大规模翻印古籍, 并认为最好是影印, 排印也可以,而且品种要多,“一年印它一二千部”,边印边整理。[5]该笔谈中,谭先生对于古籍翻印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扑面都是。
他为曹婉如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撰写《序言》;为《天一阁方志选刊续编》(1990 年上海书店精装72 册)的出版撰写《前言》;撰写《王国维水经注旧本集校书前题记》 等。 谭先生积极鼓励、呼吁并推动古代地理文献的搜集、整理、汇编,以及翻印出版。 他自己还曾希望利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水经注》和编制《水经注图》”[1]
谭其骧还很重视近代历史地理研究论著目录的编纂工作。 他为杜瑜、朱玲玲编纂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撰写了《序》,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当前迫切需要的有意义的工作。”认为,当时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重视资料检索工作,如果资料检索工作做好了,专家学者不用去做无效劳动, 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以思考、分析,那就肯定能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同时谭先生还指出,“从资料检索的要求来说,编辑论文目录索引还是初步的工作, 还应该进一步编辑文献资料内容的各种索引、提要,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6]
二、 谭其骧先生对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理论思考
谭其骧先生从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工作,并不局限于具体的考订,而是很擅长于理论总结。
(一)地理志编纂与校释中史料的利用问题
他在《〈补陈疆域志〉校补》一文中对臧励和工作的评论, 可以看做是关于地理志编纂中史料使用的理论思考。他指出,臧励和《补陈疆域志》体制上不足之处7 条:
一引证史文,未能择其最切当最关紧要者。如建康有宫城,又名台城,下引南康嗣王《方泰传》,“方泰所部将士离散,乃弃船走;及台城陷,与后主俱入关”。 应以改用《任忠传》“祯明三年,降隋,引韩擒虎军共入南掖门,台城陷”为当。
二引用史料,时或舍原料而用次料。如建康有陶家后渚,下引《南史》,应改用《陈书·高祖纪》。南豫州州治下引《通鉴》,应改用《陈书·后主纪》。 巴陵郡巴丘下引《方舆纪要》, 应改用《陈书·世祖纪》。宜都有荆门城,下引《通典》,应改用《陈书·叔慎传》。 此病最繁,不胜枚举。
三同一性质之史事, 其记载方式, 及引用史料,未能一律。如封建侯王,或纪年或不纪年,或用纪或用传。 私意凡有年月可考者,皆当详载;凡纪传并见者,当用纪。
四凡作志引证史事,或全录,或选录。 若选录则必须有例,或用首见,或用末一次见。 此志如石头城下引祯明二年九月一条,则是用后见者。但太极前殿下引永定元年事,则又系用最先见者。是无一定之例也。 且有非首见,亦非最后见者。 如白下下引太建十一年一条,按《宣帝纪》,太建五年,北讨都督吴明彻统众十万发自白下, 在十一年前;《方泰传》,祯明三年,领水军于白下往来,断遏水路,在太建十一年后。
五引证史事,遇同书纪传或二传以上并载者,未能审度情宜,择其最相当者。 如北掖门下引《袁宪传》一条,应改用《后主纪》“祯明三年,贺若弼进攻宫城,烧北掖门”。临海郡下引《宣帝纪》一条,应改用《废帝纪》“光大二年,太后特降帝为临海王”。
六《志》以陈为名,故凡两国交兵,事互见于齐、周、隋《书》者,自应以引用《陈书》为合理,殊不必好奇立异,采录他史。 而此志则时犯是病。 如京口下引《隋书》开皇九年贺若弼济江一条,按事迹具见于《陈书·宣帝纪》及《萧摩诃传》,则不应采及《隋书》也。
七陈初受梁禅,境宇弥蹇:江北入于高齐;郢湘诸州则或为王琳所有,或为北周所据。 天嘉、光大以来,中流渐复。太建北伐,始克定淮南。凡此既非开国时旧土,自宜详记其隶入版图之岁月。此志于太建所得淮南地皆能一一记注,甚合史法,然于中流诸州则概不及一字, 遂使读志者几疑永定中即有郢、湘、巴、荆,岂非惑乎!?[2](P131-132)
谭先生上述归纳,总结起来,即在撰写或校释古地理文献时, 其史料的引用应以最切当最关紧要的记载为先;要以原始记载为主,尽量避免次生史料; 同一性质史事, 写法的体例应尽量保持一致;引证材料应有相对统一的体例;引证史料要考辨,择其最切当者;纂修(或校释)应以写作对象为主体来运用材料与立场;涉及王朝疆域,应注明各地隶入版图的时间等。这些归纳,对于我们今天历史地理研究,特别是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来说,依然是原则性的指导方法。
(二)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区别,以及旧志史料利用的问题
谭其骧在1981 年7 月15 日太原举行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做的报告《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材料不可轻信》,是关于该问题迄今为止仍然有参考价值的论述。
谭先生首先指出清人章学诚所谓“志” 就是“史”,方志就是一方之史,并不可取,地方史和地方志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 然后从文献学上概略梳理了一下两类书的性质,指出《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不是地方志,而是地方史。然后从《华阳国志·巴志》所引《巴郡图经》开始扼要梳理了地方志的发展过程。
谭其骧认为地方志与地方史不同之处有三点:(1)地方史主要是记叙一个地区的过去,志主要记载现状, 虽然有时要追溯过去, 但以现状为主。(2)史主要是记述一个地方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活动,而志则不然,至少应该自然与社会双方并重;史以大事为主要线索,体裁接近纪事本末体,志则是分门别类记述。 (3)史以记载过去为主,以记载社会发展为主,所以主要依靠史料。修史工作主要是搜集史料;而地方志以现状为主,主要依靠调查。
谭先生特别指出,采用旧方志资料,要经过审核,不可轻信。 如(1)地方沿革,或遗迹,方志不见得比《水经注》等总志靠得住;(2)方志中讲的具体的,不见得可信;(3)方志有个通病,往往把历史上的名人拉作本地人,也不可轻信;(4)地方志中还有关于灾异的记载,如地震、水灾、旱灾,有些补正史之不足,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但也有些是靠不住的,不经过认真核对,决不能全部照抄。(5)方志中有“艺文类”,辑录许多前人诗文,最可宝贵。①谭其骧:《关于编修地方史志的意见》,《贵州文史丛刊》1981 年第3 期,第67-70 页。 因一时手头找不到其他文献,遂采此《贵州文史丛刊》所发报告。 按:该文为谭其骧在1981 年7.15 太原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材料不可轻信》的修改版,未经谭其骧先生审阅过。 据葛剑雄,当时只有《江海学刊》1982 年第1 期上《浅谈地方史和地方志》是经过谭先生审阅的,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集。 同年《红旗》杂志社征稿但最后未用,1992 年来新夏与日本独协大学齐藤博教授合编《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论文集》索要此文,经葛剑雄整理后寄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年出版。 (详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224-225 页;《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520-521 页)
(三) 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的思考
1982 年谭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一文中,针对当时忽视文献资料的倾向, 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对待历史文献的方法。 他将历史资料分为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两类,阐释了这两类资料的特点,特别提出三个原则性的意见:(1)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2)不要把传说当做真实史料。(3)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7]
(四)方志编目与古籍点校的思考
谭先生在编纂 《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初编)的时候,对方志目录的编纂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方法, 即通过不同的字体区别各地方志书地域等级与范围,使读者一目了然。他为这一创新方法, 在编目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劳动, 在晚年回忆时,特别强调,那样做是值得的,因为给读者带来了便利。 另外,他对于当时沿用旧体例,乡土志和乡镇志不入正目,别为附录,以及不采录丛书中的方志,进行了反思,认为这两条是不妥当的。[8]
在古籍整理方面,谭先生主持《肇域志》的点校工作,在他的讲话中,对古籍整理中的原本属于未定稿的整理方法、校勘问题等,从实际工作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古籍整理, 如果是定稿本或刻本, 相对好处理,用不同的版本,通过多种校勘方法,恢复文本原貌,写出校勘记说明各版本情况,做到最大程度地恢复原本是整理的标准方法。
如果古籍本来就是未定稿,没有最终成书,未有刻本,只有稿本和各家抄本,这种情况如何进行整理工作?《肇域志》的整理就面对这种情况。据朱惠荣先生整理,谭先生认为:即使文句通顺的地方也需要一定的他校;但是他校要做一定的规定;反对用方志来核对;凡例要尽量详细,每条举例一个太少,最好每条举两个例子;校记文风、笔法差别不能太大,以从简为原则,但要交代清楚;政区标识办法等。[9]
谭其骧先生关于历史地理文献的理论思考虽然并没有系统汇集成专题,相对零散,但是就其所思考的问题而言, 都是文献研究与具体历史地理工作中最为常见的基本问题, 是在实践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具有原则意义的指导性结论。
三、余论
(一)谭其骧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取得成绩的学术渊源
谭其骧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重视, 在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方面的工作, 对中国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绩, 除了他所处的地位能够进行高屋建瓴的思考, 并作出高瞻远瞩的决定外, 与他早年曾经在图书馆从事过实际的编目工作,系统地翻阅过各种地方志与其他古籍,以及受到当时工作过程中图书馆专家的熏陶有莫大的关系。
他自己在回忆文章中说,“向达(觉明)、贺昌群(藏云)、刘节(子植)、王庸(以中)、谢国桢(刚主)、赵万里(斐云)、孙楷第(子书)、王重民(有三)等一批中年学者在馆从事与图书整理有关的研究工作……这几位先生年龄都要比我大十岁左右,早就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以一个后辈的身份和他们亦师亦友地相与游处, 关系远比在大学里的同事密切, 因此我得到这几位前辈再加上同年辈的萧璋(仲圭)张秀民(涤澹)等同事的熏陶切磋之益, 也有过于后来单纯在大学里教书的年代”[5],并非虚语。 这样的经历, 为他在版面目录学和古代文献的理解方面奠定了极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认知。 这一点在他写的《王国维水经注旧本集校书前题记》, 以及日本学术交流期间携回《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的准备方面即可见一斑。
(二)谭其骧先生对历史地理文献工作的重视对史地所的影响
谭先生除了其自己积极进行历史地理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工作之外, 他培养了一批擅长且重视历史地理文献工作的学生。
谭先生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的工作, 不少是由学生帮助或接续完成的,如《肇域志》的校点,《历代地理志汇释》等。 而其学生辈或专注或兼顾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如王文楚、魏嵩山校点《元丰九域志》(附《新定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 年),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8 年)。 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编纂《中国历史地理要籍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明实录水利资料汇编》(一)《治河工程分册》、(二)《水害分册》、(三)《农田水利、交通运输、河道管理》(史地所1983 年),杨正泰在《明代驿站考》1994 年初版附录 《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两种,2006 年出版增订本,附录增加了《寰宇通衢》。邹逸麟整理的《禹贡锥指》(上海古籍,1996 年) 影印 《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1993 年),《五岳游草·广志绎》(中华书局,1990、2006 年,上海人民2019 年新校本)。 傅林祥点校《通鉴地理通释》(中华书局,2016 年)。 李晓杰主持的《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等等。 在一个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 有如此众多的同仁从事历史地理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这在全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这其中可以看到谭先生的影响。
(三)谭其骧先生关于历史地理文献工作的思考在当下的意义
当前史学研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数字化趋势日益凸显[10],大数据、可视化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但是无论理论与方法如何日新月异, 历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仍然是读懂史料,恰如其分地运用史料进行论证, 是且将永远是最为基础的第一步工作。如果做不到这第一步,那么无论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如何炫酷, 其研究从本质上就已经失去了可靠性。
就历史地理学而言, 在研究过去的各种地理学问题时,是以可资利用的史料为基础的,如果读不懂史料,特别是读不懂历史时期的地理史料,那么所建立的各种数据库的可信度就会打折扣,大数据就会出现系统性失真。
怎么样才能读懂史料, 特别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史料, 谭其骧先生的相关思考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尺。如果在历史地理的实践工作中,注意到了谭其骧先生所谈到的问题, 那么就基本合格了; 如果没有注意到就很可能在史料的使用方面出了差错,由此而进行的数据库建设,大数据研究,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工作都有加剧偏离历史地理真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