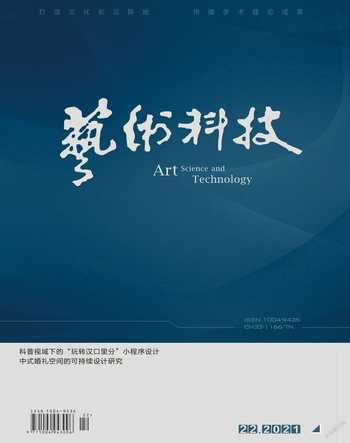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视域下脱口秀节目的现状及其问题研究
毛云秋 陈逊
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脱口秀节目受到了追捧,在网络视频节目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类节目因语言诙谐、互动性强、主持人个性鲜明等特点备受当代青年群体的关注。《吐槽大会》是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收视率较高,但同时也存在缺乏创新、形式单一、商业化明显等问题。文章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视角切入,分析网络脱口秀节目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文化工业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2-0-0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压力。《吐槽大会》作为一档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通过吐槽释放情绪,从而缓解个体心理压力[1],使处于高压环境下的年轻人实现一定的精神满足,因此备受关注。这一备受关注的脱口秀节目背后隐藏着一种文化工业[2]。
1 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的定位、特点
中国的喜剧节目有其独特的生存路径,随着网络的发展,新兴网络综艺节目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其中以《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为代表的年轻态喜剧综艺节目创造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喜剧文化。
1.1 受众群体多层覆盖
《吐槽大会》的节目风格是“吐槽”,受众主要以碎片化、游戏化的方式参与,从而提高话题的热度。吐槽不仅能够缓解当代年轻人的压力,还能传达大众的声音。年轻的受众群体往往面临着生活與工作的压力,对娱乐的追求也是他们表达自我的一个渠道。《吐槽大会》这档脱口秀节目精准捕捉到了受众群体的需求,以年轻人能感受到的笑点创造段子或者故事,将吐槽与脱口秀完美融合。节目开播后,观众可以通过视频上的弹幕交流,从而达到双方共同商榷节目话题的目的。
1.2 内容定位幽默诙谐
《吐槽大会》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自带热度的主要嘉宾,除此之外,还会邀请这位主要嘉宾的朋友以及其他嘉宾相互吐槽,最后在这些人中选出表现最好的并颁发奖杯。后现代主义者福柯认为,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人们的社会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脱口秀演员虽然在搞笑,但他们也吐露了心声,为吐槽披上了华丽的外衣。
《吐槽大会》每一季吐槽的力度都会比前一季大许多,大部分嘉宾会把吐槽的重点放在自己身上,放低姿态从而赢得观众的好感。例如,卡姆在后台见到甄子丹时会说:“老师,您好您好。”在台上卡姆便转换腔调说:“甄子丹垃圾!”此时此刻,观看节目的观众会对卡姆的表现感到十分惊讶,而卡姆随后也解释说,这是角色塑造的要求,并非他的真实想法。
1.3 传递年轻沟通方式
《吐槽大会》是笑果文化为打造年轻态喜剧的一次成功尝试。在第三季中,以“吐槽是一种年轻生活方式”为主题,传递了一些生活正能量,让吐槽成为人们放松的方式[3]。《吐槽大会》第三季的LOGO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将表达的翅膀安插在了年轻态喜剧上,吸收、接纳了更广泛的人群,让年轻态喜剧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这样一种喜剧样态的背后是对个性和自我的追求,传播快速,能够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吐槽文化”不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影响着人们,有时也会改变人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其蕴含着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中国“吐槽文化”的发展显示了受众群体的需求,吐槽也创造出了新的话语空间,蕴含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和一种高尚的生活哲学。
2 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视域下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存在的问题
2.1 文化工业产品的标准化
2.1.1 脱口秀节目内容标准化
所谓标准化就是风格单一[4],缺乏创新,按照一定的标准机械化、批量化生产[5]。
《吐槽大会》作为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的典型代表,节目嘉宾编写的搞笑段子和故事的灵感大多源于日常生活或工作经历。但随着《吐槽大会》收视率的不断提升和一些生面孔的出现,节目中出现的段子也逐渐大同小异,吐槽语言的表达以及内容的呈现方式如出一辙。从《吐槽大会》的嘉宾选择来看,以名人为主,包括体育界、演艺界人士等,这些名人通过《吐槽大会》暴露自己在日常工作或生活中的“槽点”,《吐槽大会》也成为他们“洗白”自己的平台。除此之外,《吐槽大会》每一期的嘉宾不同,但吐槽的内容频频出现雷同现象,如李诞深夜买醉、何云伟离开郭德纲团队等事件屡次被嘉宾拿来凑数。这一现象不仅展现了录制脱口秀节目需要一定的门槛,还印证了想要在这一行业立足,需要不断学习理论方法,而非运用相同套路创作。
由此可见,在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中,一些搞笑的段子与故事往往遵循同一种模式创作[6],程序化的创作过程使如今的脱口秀节目呈现为一种标准化生产的文化工业[7]。
2.1.2 脱口秀节目宣传标准化
人们一说到脱口秀,通常第一印象就是李诞的笑果文化。笑果文化的努力付出激活了脱口秀行业的需求端[8]。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一些演员的离职等,笑果文化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一环境下,笑果文化靠《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3》的爆火逆风翻盘,这一现象离不开笑果文化的标准化宣传。
首先,抓住年轻态喜剧受众群体的特征[9]。《吐槽大会》的受众以年轻群体为主,这个群体不仅年轻上进,收入较高,而且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收看综艺类节目,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短视频软件都是这个群体闲暇之余的最爱,他们的心态、心理很容易受到这些平台的影响。
其次,资本能够获利归根到底是标准化的推动[10]。笑果文化以媒体为主,通过制作电视节目使脱口秀获得了成功,每一期节目在此基础上借助互联网进行话题推广。例如,在《吐槽大会》体育专场,范志毅曾因“被运动耽误的脱口秀演员”屡次登上微博热搜榜。《吐槽大会》自播出后贡献了近百个的微博热搜。由此可见,标准化的宣传是笑果文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2.2 脱口秀节目的伪个性化
2.2.1 伪个性化含义
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化是指文化产品的创作是受标准化模式控制的虚假个性化,文化产品的创作只是为了迎合大众需求,是一种无限复制和格式化的生产模式。个性本身变成了一种模式,呈现的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随着脱口秀节目热度的高涨,一些新人演员也加入其中,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整个脱口秀行业也认识到了个性创新的重要作用。
2.2.2 伪个性化表现
阿多诺指出,标准化是伪个性化的特征。在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中,改变表面才能使观众对脱口秀节目热情不减。例如,邀请不同类型的脱口秀演员、固定的节目嘉宾以及运用“爆梗”等达到保持新鲜感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脱口秀节目一反常态,那么受众群体对节目内容便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样一来,标准化的实质被伪个性化掩盖,而受众群体依然在熟悉、安全的环境中享受脱口秀节目带来的愉悦感。
2.3 大众与脱口秀文化相互作用
2.3.1 脱口秀节目为了迎合大众需求而改变
消费者往往受文化工业的操纵,这一操纵往往具有潜伏性,并不具有目的性和控制性[11]。在这一环境下,个人会受到文化工业的影响,转变为消费者,然而消费者随之接收到的也是一些流于表面的事物,这一现象在综艺节目中极为常见[12]。一档节目获得高收视率的背后是受众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就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而言,人们追捧与热爱它的原因之一便是精神需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精神娱乐消费造就了脱口秀节目的爆火。由此可见,脱口秀节目的成功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与热爱,而只有迎合消费者,才能刺激消费者持续消费[13]。在阿多诺看来,文化不再拥有其本身的批评功能。随着脱口秀节目在中国的爆火,脱口秀文化开始刻意迎合消费者,没有了对问题的思考与分析,最后演变成只能娱乐大众的产品。
2.3.2 脫口秀文化中“异化”现象的出现
脱口秀文化为适应市场环境不断改变,不断创新,从而为大众服务[14]。例如,在一些网络公司,员工会收到一些脱口秀节目的门票,时不时去看一场脱口秀节目,如此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精神上也会得到满足。脱口秀文化成为人们日常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5]。与此同时,观众在观看脱口秀节目之前,有时可以预料到脱口秀节目发展的整体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受众群体被脱口秀文化异化了。例如,在《吐槽大会》中,一些观众虽然不知道演员的段子与故事内容,但对演员呈现的状态和最后结果会有预判,在此过程中,受众群体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这一现象也意味着观众没有思考、认识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对脱口秀节目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对于其背后意义的探究不感兴趣,不再具有批判性。
从《吐槽大会》这档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中可以发现,观众成为不断再生产的对象,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被带入程序化的模式中。如《吐槽大会》中曾多次出现“谐音梗”,即用相同字音强行建立某种联系,最终达到搞笑的目的。这一现象实质上是创作者在偷懒,但这一模式被许多脱口秀演员使用。
3 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视域下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的影响
3.1 对脱口秀节目受众群体的影响
脱口秀节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固定的,观众没有意识到脱口秀节目本身在愉悦大众的同时还会带来的一些问题。例如,忽视一些段子或搞笑故事背后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对一些言语上的冒犯与调侃习以为常,不再抵触。阿多诺认为人们没有办法远离文化工业,这样一来,脱口秀演员有时也会引发焦点话题的讨论,对观众来说,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3.2 参加脱口秀节目或将成为身份符号
在文化工业的影响下,人们不再深入思考与分析现象背后的根源,受众群体只关注一些不重要的东西,看问题浮于表面,看不到问题的关键。在市场的推动下,一些线下脱口秀节目门票价格成倍上涨,甚至人气高的演员演出时,“黄牛”还会倒卖门票,进而导致门票价格上涨为原本票价的十几倍。对于一些喜爱追星、爱攀比的年轻受众来说,这张门票已不具有可以观看节目的意味,反而象征着特定身份,他们以此炫耀。这些受众不再关注整场脱口秀演出想要展现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坐在座位上拍照、炫耀,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4 结语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文化工业理论在每一时代所处的特定环境不同,但其中的一些经验是共通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阿多诺认为,今天的人们对比过去而言,可以无拘无束地思考,但人们不会或不愿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因为自身的想法会被限制,他们会认为自己只能或应该想什么。而在这一环境下,人们却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并没有发现自己丧失了关键能力。这一现象会出现,背后既有新媒体等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带来的影响,也与人们自身的选择有关。
参考文献:
[1] 徐伟悦.新媒体视阈下大学生网络社交焦虑研究[J].大众文艺,2018(12):194-195.
[2] 韩望.弗洛姆异化消费理论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1(28):4-6.
[3] 左丽丽.发挥抖音短视频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J].汉字文化,2020(4):134-135.
[4] 梁苗.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启示[J].学理论,2019(4):62-64.
[5] 梁苗.启蒙理性退化与文化沉沦[J].文化学刊,2018(11):85-90.
[6] 严雪珂.马尔库塞解构视域下“单向度性”理论的批判[J].戏剧之家,2019(26):225,227.
[7] 张亦冉.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的结合: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传播价值与创新路径[J].汉字文化,2020(15):179-181.
[8] 张雪婷.浅谈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思想[J].青年文学家,2018(24):170-171.
[9] 吴宁子,乔永平.在困境中成长:读《守望——中国环保HGO媒体调查》[J].经济研究导刊,2018(33):188-189.
[10] 魏晓宇,魏嘉敏.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影视文化表达现状与问题[J].汉字文化,2020(11):60-62.
[11] 翟梦璠.新媒体时代群体心理对网络舆论的影响[J].汉字文化,2019(14):154-155.
[12] 张亦冉.浅析文化类节目的语言艺术之美:以《朗读者》为例[J].汉字文化,2021(15):24-25.
[13] 左丽丽.中国神话中的语言和文化:以《女娲补天》为例[J].汉字文化,2021(8):126-127.
[14] 叶朗.《伊利亚特》中英雄的典型人物形象分析[J].戏剧之家,2019(32):228-229.
[15] 何如意.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审视[J].戏剧之家,2019(19):222,224.
作者简介:毛云秋(1998—),女,江苏扬州人,硕士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陈逊(1998—),男,江苏无锡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336350190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