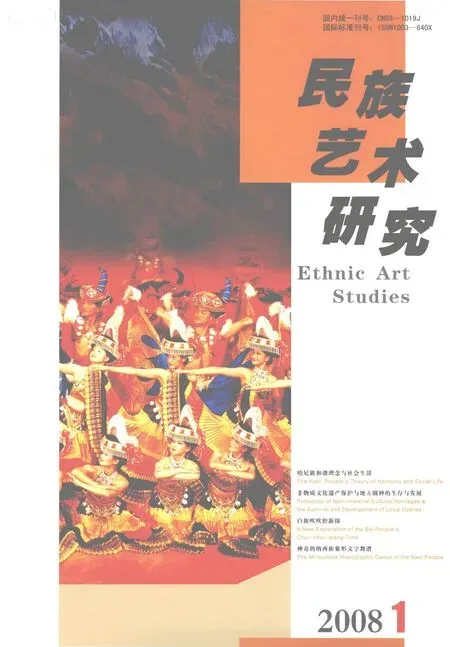现代戏曲:“文体”再辨
——兼评吕效平“现代戏曲”研究
孙红侠
文体,是文学研究中的概念,指“文学体裁或者文学类型……指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方式”①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文体学,源于古希腊修辞学,20世纪后,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开始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此后在西方理论界又进化出形式主义文体学、功能主义文体学、批评主义文体学等等。其中,运用文体学方法分析与阐释文本的做法,为文学文体学②候维瑞:《文学文体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文学文体学是语言学、修辞学的新兴学科之一,又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当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存在时,文本的文体特征对文学批评与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用文体学方法,对作品进行阐释和描述是文体学所能提供的批评路径。这种“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与美学价值为目的的为文体学派”③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7页。。文体学是西方学术研究范式,但同时也是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从《文心雕龙》到王国维,都有传统文学研究中的文体意识,因而有学者认为,“文体学是中国传统文学话语的基础”“是新世纪以来古代文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④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第208—209页。。
从文体学视角出发的戏剧研究,虽不算戏剧戏曲学领域的显学,但也并不缺乏相关积累,主要体现为戏剧文体学研究⑤俞东明:《戏剧文体与戏剧文体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100页。、戏剧文体的重要性论述①陆炜:《试论戏剧文体》,《文艺理论与研究》2001年第6期,第30—38页。、中西戏剧文体特征的比较研究②郭英德:《中西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戏剧文学》1993年第8期,第37页。,以及运用文体学对戏剧文本的关注和解读③谢谦:《文学文体学与诗体戏剧中语言变异的翻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9页。、语言变革与戏剧文体关系研究④王佳琴:《文学语言变革与戏剧文体的现代转型》,《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117页。、王国维戏曲文体观研究⑤朱维:《王国维戏曲文体观嬗变》,《文化与诗学》2018年第2期,第60—71页。、戏曲文体特征与创作关系研究⑥朱忠元:《体贴人情物理——认识戏曲文体特征的创作论视野》,《文化艺术研究》2015年第3期,第56—59页。、古代戏曲文体特征研究⑦王瑜瑜:《中国古代藏书目录对古代戏曲文体特征的独特呈现》,《戏曲研究》第84辑,第304页。等等。中国戏曲,和大范围概念之下的戏剧一样,有存在于舞台的生命,有存在于文学的生命。无论中国戏曲的特点被如何强化为“以表演为中心”,当任何一个时候需要直面文本,我们讨论以剧本方式存在的戏曲时,它都是文学之一种——戏剧文学是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种形式之外的“第三种类型的文学”⑧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凡独立文本,皆有样式。因为模式之别,文体的概念由此而生,狭义的“文体”通常被简单化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体裁之别,而广义的“戏剧文体”探讨范围则为“戏剧文体实涉及戏剧文学的话语模式、语言特性、叙事结构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又与戏剧观念、演出形式有关”⑨陆炜:《试论戏剧文体》,《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第30—38页。,所以,对戏剧或者戏曲文体的探讨,本质上都是形式范畴的概念探讨。
正是这些从文体学角度进行的戏剧研究和探索,为“现代戏曲”的“文体”论述做了铺垫与积累。
一
在“现代戏曲”的学术框架之下,首先提出“现代戏曲文体”概念的是南京大学吕效平教授,他在《论“现代戏曲”》10吕效平:《论“现代戏曲”》,《戏剧艺术》2004年第1期,第38—48页。《再论“现代戏曲”》11吕效平:《再论“现代戏曲”》,《戏剧艺术》2005年第1期,第4—16页。《论现代戏曲的戏曲性》12吕效平:《论现代戏曲的戏曲性》,《戏剧艺术》2008年第1期,第13—24页。系列研究中不但率先提出现代戏曲的文体概念,还以此为出发点对“现代戏曲”概念相关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文体视角下“现代戏曲”具有的“戏曲性”做了全面论述。吕效平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其一,提出“现代戏曲”的“文体”概念。
将现代戏曲定义为当代戏曲创作的主流样式。认为当代戏曲创作所采用的文体,是一种不同于以古典京剧为代表的古典地方戏的新文体,根据它的“现代性”特征,用“现代戏曲”命名。并以“现代戏曲”的概念将其与包括元杂剧、明清传奇和古典地方戏三个阶段的古典戏曲区分开来。
其二,论述了“现代戏曲”的文体样式。
认为现代戏曲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古典地方戏有着本质的区别,认为其恢复了古典地方戏丢失的文学传统,又以情节艺术的特征区别于元杂剧,以剧场情节艺术的特征区别于明清传奇的非剧场情节艺术。同时,戏曲新文体的原则从表面上看,是中国本土戏剧向西方戏剧学习得来的,而实际上却是摆脱了封建政治、社会与精神奴役的中国人的现代寻求在戏曲中被表现的结果。
其三,论述了“现代戏曲”的现代精神。
从现代文体和现代精神两个方面描述了现代戏曲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戏曲的文体原则是解放了的“现代人”的精神表现,在于表现出在古典地方戏中丢失了的个人自由创造的艺术精神。现代戏曲作家的精神须自由解放,现代戏曲作品中的人物也须精神自由,超越有形与无形的脸谱。而现代性,就是人的解放,是人从自然界的束缚和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奴役下的解放。
其四,在“现代戏曲”文体概念的基础上论述了现代戏曲所具有的“戏曲性”。
从文本形式、“虚拟性”和“程式”的本质、剧本中的戏曲性三个方面论述现代戏曲的“戏曲性”。这一部分的核心观点是:现代戏曲的戏曲性与古典戏曲的戏曲性一脉相承,现代戏曲是戏剧文学和剧场表演并重的戏剧文体。
吕效平教授对现代戏曲的系列研究,奠定了吕效平在现代戏曲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其贡献有三:
其一,从“文体”的角度进入现代戏曲研究领域,提出“现代戏曲”的“文体”概念。在现代戏曲的研究领域引入“文体”概念,使用的是文学文体学的批评方法,如前所述,这是对西方研究范式的借鉴与为我所用,同时也延续了传统文学研究中文体研究的传统,还把文学文体学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引入戏曲研究,这不仅开辟了戏曲研究的新思路,更是为观察当代戏曲创作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路径,提供了文体学研究的思路和范式,具有新的阐释能力。但是并不是单纯提出概念,更远非停留于概念的描述与论述中,而是将现代戏曲的概念从理论领域延展到了实践领域,也就是对于现代戏曲的戏曲性的论述。
其二,在现代戏曲“文体”概念论述的基础上进入了现代戏曲“现代性”的讨论,从现代文体与现代精神两个方面论述现代戏曲的现代性,在注重对现代戏曲戏剧精神与价值追求的出发点上,论述了现代戏曲的文体原则。这种批评视角跳出了对作品的阐释,进入到戏剧戏曲学学科基础理论探讨的范围——现代戏曲有现代文体,更有现代的戏剧精神。在文体论述的基础上,对现代戏曲具有的戏曲性的论述,则基于舞台特性,也着力于价值内涵,现代戏曲的文体特征在这些论述中面目逐渐清晰。吕效平这样的理论视角体现了从陈白尘到董健所确立的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体现了对其业师董健学术思想的继承与传承。
其三,吕效平力图将“现代戏曲”作为一种戏曲文体样式而存在的观照视角,为进一步论述现代戏曲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打下了学术思考的基础,也为学术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推进的思路、路径。他对于“现代戏曲的文本是莎士比亚式的?还是梅兰芳式的?”的提问,对于“曹杨是现代戏曲文本的理想样式,左边是郭启宏更个人、更文学的文本,右边是余笑予创作群体更集体、更个人的作品”①吕效平:《论现代戏曲的戏曲性》,《戏剧艺术》2008年第1期,第17页。的描述方式,对于中国戏曲第四种主流文体样式,作为稳定新文体形成于《十五贯》《团圆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 《曹操与杨修》等问题的提出与关注,都在他的主要观点和理论贡献以外引发了新的提问、新的思考。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的是如何看待中国戏曲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些问题,有些则是创作与演出实践中最核心的问题,也许在尝试着找寻答案的过程中,不仅“现代戏曲”会以更清晰的面目呈现,中国戏曲在21世纪,甚至是更远的将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会得到长足的思考。
二
对现代戏曲的系列研究成果做全面综述,厘清文体学研究背景和方法在戏曲研究中的背景和路径,对这种批评与研究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话语,还是西方学术范式的属性做考察,并在文体学研究的理论背景上对吕效平的研究做出定位与评价,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一。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戏曲”的“现代文体”做推进性的、补充性的论述,是为“再辨”,这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二。
那么,现代戏曲是否有了一种新的“现代文体”?如果没有,提供阐释的文本和传统戏曲的文本是否一样?如果有了文体的更替,那么新文体的标志是什么?有哪些变化使其不同以往?是现代精神催生了现代文体?还是文体变化才适应了现代戏剧精神的表达?
如果我们认可“现代戏曲”的确可以因文本的嬗变而成就一种新文体的话,那这种文体的文本,与传统文本,或者说文体的最大区别并不是价值追求的不同,虽然文本表现的内容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文本的形式。
叙事模式的变化,是文体生成和变化的一个重要指征。就戏曲而言,就是剧本体制、语言风格、抒情方式的变化。南京大学陆炜教授的研究认为戏剧文体涉及戏剧文学的“话语模式、语言特征、叙事结构”①陆炜:《试论戏剧文体》,《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第31页。三个方面。
在传统戏曲现代转化的进程中,戏曲文本的改变是很大的,这主要表现为剧本的形制变化,也可以说是剧本写作手法、语言风格、抒情方式、表现形式的全方位变化。如果这些文本都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转化过程中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那我们才能有理由认为,不同于传统戏曲文体的现代戏曲新文体随之生成。
回到现代戏曲的概念②孙红侠:《现代戏曲:概念源流与再辨》,《戏曲研究》2020年总第112辑。上,现代戏曲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是一种固定的形态。作为传统戏曲现代转化的目的,也是其结果,现代戏曲承载着从“旧剧现代化”到“戏曲现代化”的文艺生产逻辑。在这样一个贯穿20世纪的转化过程中,戏曲“文体”更替的首要标志——文本,发生着不同于传统的显著变化。
(一)“场”的变化
“场”是传统戏曲舞台演出中根据剧情发展而形成的基本段落。传统戏曲和西方戏剧在这种演出段落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戏剧的“段落”是依据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情节”而形成的,其情节是基于“行动”而形成的,所以西方戏剧的“幕”的原文为“act”——就是行动。基于情节与行动而形成的戏剧段落与传统戏曲的“折”“出”“场”的含义和概念完全不同。西方戏剧按照结构与规模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多幕剧,无论有几幕,总是依据“开端—高潮—结局”的基本走向而设置,高潮的部分是一种转变。而传统戏曲的“场”与此完全不同,演员一上台,为“入场”,为“逢场作戏”,跑上一圈为一个“圆场”,器乐演奏要分“文武场”,表演者在“上场门”和“下场门”之间一上一下、一进一出形成“上下场”。阿甲所言“无穷物化时空过,不断人流上下场”就是在描述基于一上一下就可以完成一个演出段落的戏曲时空观念的自由与超脱。这些关于“场”的表演理论总结与戏曲表演自由的形式当然是舞台观念的产物,但其实也是受限于舞台形制从而寻求时空表达的结果,是舞台物理空间和表演之间的相互限制和相互成就。戏曲的分场形态是传统戏剧独特的舞台结构,这些特点带着民族的美学原则与时空观,形成于数百年之间,在明清时期的演出实践中趋于成熟定型。这的确是一种“自由”,但也因为自由,“场”的毫无限制形成了动辄数十场数十出的鸿篇巨制的戏剧文本形制。
这样宏大、庞杂、不受限制的戏剧文本形态在世界戏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甚至不必去以民间连演数日的宗教祭祀戏剧或者宫廷戏楼常见的连台本戏为例,随意翻检任何明清传奇,其文本的“出”与实际表演中的场次都至少在数十之巨。《牡丹亭》五十五出,《长生殿》五十出,《桃花扇》四十出……这些文人士大夫的案头之作,从来以直抒胸臆、酒杯块垒为最高艺术追求,他们几乎从来不会考虑演出的效果和观看的感受,加之明清家班的体制和厅堂氍毹的演出形式,都可以为他们的文本提供私人化的一切便利的观演场所。因此,文本的体制庞大成为传统戏曲在地方戏时代来临之前的特点之一,是“词山曲海”时代的共同特征。这些以曲牌联套为音乐形制的作品,登场的角色几乎都会开口演唱,曲调与文辞确实都典雅优美,但剧情结构却拖沓冗长,因此才有了凝聚表演精华的场次被单独挑出来演出,这也就是“折子戏”的出现。折子戏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戏剧特有的戏剧现象。这种把精华部分抽出来演的做法,叫作“摘锦”,这个词完全可以望文生义,就是选取精华的意思。折子戏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戏剧与生俱来的音乐性。“折”,在元杂剧时期,专指“四折一楔子”这种起承转合的戏剧结构,但也并不是仅指戏剧矛盾的安排,而更多是适应音乐结构。一折就是一段音乐,划分的依据和基础是曲,也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音乐单元。后世的折子戏的“折”当然不完全是依据音乐划分的,但其对音乐性的重视并没有消失。也正因此,折子戏往往集中的是全本戏中最精华的音乐段落,也就是后来我们经常说的“核心唱段”。至于表演形式,也受到中国戏曲一直以来就具有的清唱与家乐戏班的氍毹演出传统的影响。折子戏凝聚的表演技术精华是当之无愧和毫无疑问的,是传统戏剧表演技术的典范,但在文本上是残缺的,在文学构成上是畸形的,是碎片化的戏剧。此外,传统戏剧具有一种独特的文本——连台本戏,无论是民间演出还是宫廷演出,这种能够连续演出很久的戏剧形式因为残留着祭祀戏剧的胎记而始终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宫廷演出也概莫能外。这种仪式性大于娱乐性的戏剧很难拥有太高的欣赏价值,因此,在其世俗化的过程中也大量地被“折子”化。
无论是庞杂的文本,还是“折子”,这些传统戏曲的文本特点,在走向和进入“现代”之时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花雅之争”之后,京剧等“花部”的演出长度已经缩减到一个晚上之内;四大名旦时期,新编戏的演出长度再次根据观众的要求而缩减。地方剧种也因短小精炼的创作方式而成为从乡村进入城市演出的重要因素,成兆才的时事剧创作就是其中鲜明的一例。
真正使“场”的数目发生改变的时期是“戏改”以及之后的数十年。1956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昆曲《十五贯》只有精炼的八场戏,完全不同于清代朱素臣时期的原貌。1961年,孟超为北方昆曲剧院创作的《李慧娘》只有“豪门”“游湖”“杀妾”“幽恨”“救裴”“鬼辨”六场,而周朝俊的原著《红梅记》足有上下两卷三十四出。田汉的《西厢记》只有六场,而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五本二十一折五楔子。这种简化的背后是20世纪传统戏曲的“经典化”过程,这体现为传统戏曲要在“不断的经典化努力中保持艺术精髓”①施旭升:《现代化与经典化:20世纪中国戏曲的文化选择》,《戏剧艺术》2004年第3期,第34页。。因为如果保持原貌,则不适应要求,也不适应观赏的需要。这种变化足以说明戏曲在其转化过程中存在危机,需要自保。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看不到连台本戏,更不会出现在现代剧场中一个剧目连续数日的演出。样板戏的场次更为“现代”,《红灯记》十一场,《杜鹃山》九场。场次的削减只是文本形制的一个显性的变化,无论这些削减是否可以算作形成了一种新文体,这些场次的精炼更便捷地为剧目所表现的内容而服务,也通过“样板”确立了新的文本体制。这种创作传统和文本的改变,就是现代戏曲的生成与渐进过程。
(二)“冲突”的出现与凸显
戏剧要有由行动和人物意志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表现人物行动和冲突的文体是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②郭英德:《中西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戏剧文学》1993年第8期,第37页。,这在现代的剧场艺术范畴里并不是一件让观众多难理解的事情。从古希腊到尤金·奥尼尔都推崇戏剧的行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中心”。但对于以抒情言志、曲为本体,以剧诗性为文体特征的传统戏曲而言,“冲突”这两个字,不是说在传统戏曲表现中完全没有,但形式和理解都是完全不同的,与西方戏剧“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的原则相去甚远。《文昭关》的冲突并不在过关一刻的紧张,而在之前的“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当锏卖马》的冲突也不在卖或者不买之间,而在于“店主东带过黄镖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中那份由抒情产生的共情。中国戏曲,意志和行动并不居于主要地位,酒杯块垒才是创作者和观众共同想要的。
“冲突”是在现代戏曲转化与形成的进程中进入戏曲文本的,得到创作者越来越多的重视的,这种对冲突的重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现代进程中的标志性时期。当时的戏曲创作实践,表现为二,一是“西剧中演”,二是本土创作的自然生发。
“西剧中演”并不是简单地移植一个故事,而是在戏剧结构、精神等方面给本土戏曲施加影响。1987年上海昆剧院排演的《血手记》,由郑拾风改编、黄佐临任艺术指导,使莎士比亚笔下充满意志冲突和欲望的人性第一次在轻歌曼舞的昆曲舞台上出现;1989年,由姬君超改编、罗锦鳞导演的河北梆子《美狄亚》,随着古希腊式的舞台和歌队在中国舞台出现的还有西方女性那种因意志和行动产生的冲突;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先后被徐棻和孟华以川剧和河南曲剧的形式移植改编。这些剧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戏曲给予观众的叙事印象,也挑战了传统的文化伦理观念,但这些剧中人物的意志和行动,这些故事的呈现方式,也将西方戏剧意义上的冲突带入了中国观众和本土创作者的视野中。罗怀臻编剧、郭小男导演的淮剧《金龙与蜉蝣》是这一时期作品中最具有冲突意味和代表意义的作品,这部以历史虚构表达历史追问的作品,带着浓烈而鲜明的现代意识。无所不在的意志与欲望构成了强烈的冲突,完全不同于传统戏曲作品风格,舞台的形式也完全突破,大面积象征欲望、毁灭的鲜血一般的颜色触目惊心。正是因为冲突的进入,人物心理在戏曲舞台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和延展,传统舞台物理空间之外几乎不存在的心理空间随导演中心而逐渐得到重视。李紫贵在《长生殿》里的一条从天而降的巨大白绫,郭小男在《金龙与蜉蝣》中铺天盖地的红色,都是形式追随内容而进行的改变。这一时期,对设置戏剧冲突的运用受到创作者全体的重视,其剧作法和文本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这是戏曲在表现新思想和新价值时的自我转型。但这绝非对西方戏剧的简单模仿、重复,而是其特殊的形态更替。
(三)“曲”到“剧”的变革
“曲”到“剧”的变革是现代戏曲文体的最终变革。传统戏曲当然是综合艺术,但“曲”的重要性占据重要位置,《曲论》 《曲藻》《曲品》《曲律》都是戏曲理论著作,但都是从“曲”的角度出发来观照的。词为诗余,曲为词余,李渔所言“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他是在说他的戏曲创作,而不是真的在说“填词。”在这样的创作传统之下,传统戏曲形成了曲词为主、宾白为辅、以韵文为传统戏曲文体,以诗意戏剧情境营造为目的,以对仗、押韵为唱词写作要求,以声腔,也就是声律和旋律的结合来演唱的戏剧样式。
从“曲”到“剧”的变化过程,是戏曲艺术由形式美转向描摹现实、反映生活、注重社会功能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戏曲转化为现代戏曲的过程。戏曲仍然是戏曲,可以在更大的概念范围中从属于又不同于戏剧,但“曲”的转化为“剧”仍然不同于“戏曲”变成“戏剧”。我无意在此介入戏曲本体的宏大讨论,只是用由“曲”而“剧”的转化过程来说明戏曲文本的复杂化变化。这种“复杂化”与场次的削减成正比。传统戏曲习惯于在繁复冗长的场次中去讲一个又一个剧情看似复杂,而其实并不复杂,且又基本情节千篇一律的雷同故事;而现代戏曲则与之相反,在简洁精炼的场次结构中去给予观众一个意蕴深厚、有人文价值的故事,后者才是文本真正的复杂化。在传统戏曲到现代戏曲的转化过程中,曲的重要性渐渐让位于剧,依字行腔的演唱不再居于剧作和舞台的核心,虽然有时也仍然以核心唱段的形式存在,但“天女散花”的时代过去了,不关心剧情,只关心演唱;不关心演唱内容,只在乎演唱风格和谁在表演的时代渐行渐远。这样的形式更替也许也构成了吕效平讲的文体变化的一个方面,但我想补充的是谢瑶环文学与表演的此消彼长并不是发生于或者说集中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进程中,《曹操与杨修》是一部代表性的作品,但显然不是开端性或者在现代的进程中的一部具有发展意义的作品,因为现代戏曲文学的彰显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初露端倪。“戏改”的“改戏”,表面上去掉的是传统戏曲中由色情表演、宗教祭祀元素而形成的“带彩戏”等,这些对舞台形式的净化其实并不是“戏改”真正的内容,用现代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来重新书写戏曲故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的语境里用到“现代”这个话语并不是无知和张冠李戴,因为如果从作品分析出发和入手,你不能否认田汉的剧作实践不是现代的。田汉所着力的正是让传统戏曲的文本呈现出现代的样态。在田汉笔下的《白蛇传》里的白素贞第一次脱离了民国时期《金山寺》里单纯的女妖形象,有志怪色彩的、色情意味的人妖恋被田汉变成了“虽然是异类我待你情非浅”的动人爱情故事,流传千年的白蛇故事有了形象,有了人情。《谢瑶环》更是如此,剥离政治的隐喻和寄托,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因性情而可叹的人。从田汉开始,戏曲的唱词有了服务于形象塑造的功能,而不再是服务于情绪。田汉和田汉们引领的创作,在文本领域开始了不同“传统”的“现代”更替。这种更替的转型发轫于延安,经历了戏改到样板戏的积累渐进的过程,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里喷薄而出。这些文本形态的更替,足以证明现代戏曲文体在进行嬗变与更新。
三
虽然现代戏曲的文本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形式变化,但就创作者而言,对古典情味的追求却少有改变。从孟超的《李慧娘》到郭启宏的 《南唐遗事》,再到有“古典诗人”之誉的王仁杰等,他们都毕生致力于继承和延续古典的雅致蕴藉,以对传统的心怀敬畏,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带着自己充满古典韵味的作品进入了现代范畴。因为在他们身后的时代里,现代戏曲已经经随了“戏改”以及此后通过“三并举”政策确立的经典化进程,经由20世纪80年代积累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资源与成果,进入了由“传统”转型至“现代”的过程。
现代戏曲现代转型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但这并不体现为现代戏的转型,而是体现为新编古装戏和新编历史剧的现代转型,郭启宏的《南唐遗事》、郑怀兴的《新亭泪》、刘和平的 《甲申三百年祭》、盛和煜的《山鬼》等作品都是在刷新传统戏认知的基础上前进的。思想与意识的现代必然带来形态的变化,带来舞台美学风貌和美学原则的改变,梅兰芳所言的“思想改革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并不存在,思想改革最终就是技术改革,内容决定形式。现代戏曲在“文体”更新的同时,进入了形态的更新与建构。探讨形态,才能真正解决现代戏曲的核心问题,而非永远浮在探讨价值追求的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