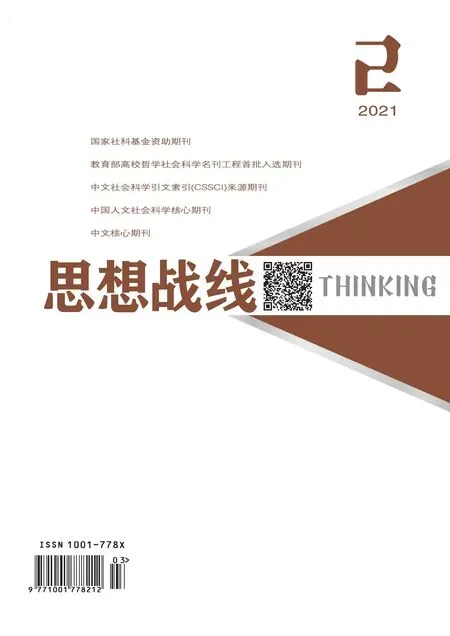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不可靠叙述
王 浩
不可靠叙述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自韦恩·布思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叙事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现象的关注和研究热力不减,但迄今为止,不可靠叙述研究基本以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对第三人称叙事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很少。塔玛尔·雅各比在分析叙述者可靠性的可变与可逆时认为,不可靠叙述不仅来自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可能来自第三人称叙述者。(1)See Tamar Yacobi,“Package Deals in Fictional Narrative:The Case of the Narrator’s(Un)Reliability”,Narrative,vol.9,no.2,2001.申丹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第三人称叙述可以将人物的不可靠眼光提升到叙述层,形成不可靠叙述。(2)参见申 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提尔曼·科佩和汤姆·金德提出了“模仿性不可靠叙述”的概念,认为不论文本中是否存在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都可能存在不可靠叙述。(3)See Tilmann Köppe and Tom Kindt,“Unreliable Narration With a Narrator and Without”,JLTonline(18.04.2011),Link: http://nbn-resolving.de/urn:nbn:de:0222-001628.实际上,很多研究者在对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加以分析的同时,并不否认第三人称叙事文本中存在不可靠叙述现象,但并没有就此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本文试图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视野从第一人称叙事向第三人称叙事拓展,以期增进我们对这一文本现象的认识。
一
对于叙事学研究而言,不可靠叙述的经典界定仍然以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所作的描述为基本出发点,即“当叙述者为作品的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代言或是在行动上与之保持一致,我将其称为可靠的,反之,则称为不可靠的”。(4)Wayne C.Booth,Rhetoric of Fiction(Second Edition),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pp.158~159.依据这一描述,叙述者是否与隐含作者思想规范保持一致,是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基本标准。近一二十年来,无论是以詹姆斯·费伦为主要代表的“修辞派”,还是以安斯加·纽宁为代表的“认知派”,他们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研究都建立在布思奠定的研究基础之上。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雅各比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试图从“生成原则”“存在原则”“文类原则”“功能原则”和“视角原则”(5)See Tamar Yacobi,“Fictional Reliability as a Communication Problem”,Poetics Today,vol.2,no.2,1981.这五个方面拓展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范围,但理论界反响不大。总体而言,“修辞派”和“认知派”可以说是当前不可靠叙述研究中最为活跃的学派。这两者的主要差别,概而论之,可以说前者研究的重点在于作者的写作行为如何使不可靠叙述得以发生,后者关注的焦点则是读者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对不可靠叙述加以阐释。
“修辞派”和“认知派”都采纳了布思对不可靠叙述的判别标准,而且,费伦仍然沿用了隐含作者的概念,但纽宁试图用“结构性总体”(the structural whole)的概念来取代隐含作者,(6)See Ansgar Nünning,“Deconstructing and Reconceptualizing the Implied Author”,Organ des Verbandes Deutscher Anglisten,1997,(8):pp.95~116.因为从“认知派”的理论视角出发,文本中的思想规范不可能恒定不变,而是会因为读者群体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就此申丹认为,隐含作者的概念实际上“既涉及作者的编码又涉及读者的解码”,并用“作者(编码)—文本(产品)—读者(解码)”(7)申 丹:《何为“隐含作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这一简约的图示来说明这个双向过程。这也告诉我们,对于隐含作者的生成,作者的编码与读者的解码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考虑到从“认知派”角度对不可靠叙述进行分析和阐释存在诸多变量,例如真实读者的反应,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不确定因素等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从作者编码的角度来考察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不可靠叙述。
从其发展历程上说,不可靠叙述研究从诞生之时起就与第一人称叙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前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研究和文本分析中,大都以来自第一人称叙事文本的案例为支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用以佐证不可靠叙述的例子很多,但似乎来自第一人称叙事的案例最为直观,最易理解。例如就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而言,布思指出:“叙述者自称生性邪恶,而作者却在背后无声地赞扬他的美德。”(8)Wayne C.Booth,Rhetoric of Fiction(Second Edition),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p.159.这类例子的典型性非常有利于我们将其作为试金石,通过类比,在其他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找到相似的案例。虽然布思也研究了来自第三人称叙事的案例,且富有洞见,但却远不够清晰,而且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其二,戏剧化、人格化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往往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其不可靠性易于识别。在不可靠叙述研究兴起的早期,威廉·里甘就在其专著《流浪汉、疯子、孩子、小丑: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中列举了九种不可靠的叙述者。虽然里甘的这项研究缺乏抽象的理论归纳,但却表明,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存在很多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些丰富的例子足以支撑费伦这样的叙事学者归纳出不可靠叙述的“事实/事件”“知识/感知”“价值/判断”三条轴线、六种不可靠叙述类型,以及“疏离型不可靠”和“契约型不可靠”等概念和框架。其三,第三人称叙事中的叙述主体基本都是非戏剧化、非人格化的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人物不存在利害冲突。虽然其全知性可以由作者任意调节,但其是否存在不可靠性,却很不易判断。任何研究都要以典型案例来支撑其理论阐述,与第一人称叙事相比,第三人称叙事似乎缺乏足够且易于分析的不可靠叙述案例,因此,相关研究很少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将不可靠叙述研究向第三人称叙事拓展,首先面临的问题在于:第一、第三人称叙事的二分对于这项研究而言是否合理。鉴于文本的叙事角度与叙述效果之间的复杂关系,叙事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叙述的角度、姿态,而非人称。布思指出:“滥用最严重的,恐怕非人称的划分莫属。说某个故事是通过第一或第三人称来讲述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我们能够更为精准地展开研究,把握叙述者的特征与叙述效果之间的关联。”(9)Wayne C.Booth,Rhetoric of Fiction(Second Edition),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p.150.热奈特也不赞成所谓第一或第三人称叙事的说法,他认为,小说作者是在两种叙述姿态(narrative posture)之间做出选择,而人称则是这种选择自然导致的结果,因此他用“同故事”和“异故事”来对叙述者加以区分。(10)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pp.244~245.布思和热奈特的观点表明,对叙述和叙述者的分析而言,人称的划分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然而,面对不可靠叙述研究大多聚焦于第一人称叙事的现实情况,大量存在的第三人称叙事游离于这一研究之外,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在文学批评中,将第一、第三人称叙事用于标示文本差异的做法比较普遍,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对“模仿”和“讲述”的区分。他在《理想国》第四卷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叙述者难道不是通过纯叙事、模仿叙事和这两者的混合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吗?”(11)Plato,Republic,trans.Robin Waterfie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92d.加拿大学者安德烈·戈德罗依据苏格拉底和阿德曼托斯的这段对话总结出了一个叙事分类图(见图1):(12)[加]安德里·戈德罗:《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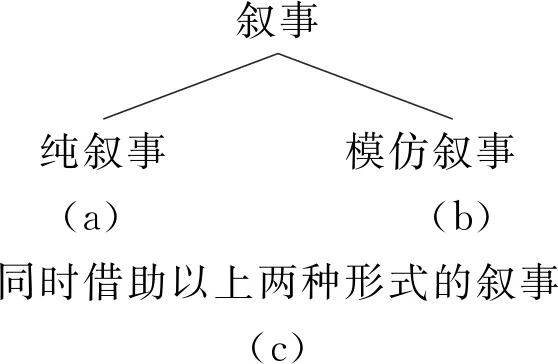
叙事纯叙事 模仿叙事(a) (b)同时借助以上两种形式的叙事(c)
图1:叙事分类图
柏拉图认为,模仿叙事“贯穿于几乎所有他(荷马)对发生在特洛伊和伊萨卡的事件的叙述之中,以及《奥德赛》的总体叙述之中”,(13)Plato,Republic,trans.Robin Waterfie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93b.为了说明何为纯叙事,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将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模仿鲁塞斯的口吻说出的话(即模仿叙事)“改写”为叙述者的纯叙事。(14)Plato,Republic,trans.Robin Waterfie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94a.这段“改写”而来的纯叙事属于典型的第三人称叙事,相比之下,《奥德赛》中的模仿叙事内嵌于一个第三人称叙事的框架之中,但是其篇幅之长,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足的第一人称叙事。从这个角度看,模仿叙事与纯叙事的不同,也可以视为第一、第三人称叙事之间的差别。柏拉图的描述和戈德罗的图示表明,在纯叙事与模仿叙事之间还存在融合此二者的叙事类型。在小说研究中,如果把文学史上的所有小说作品视为一个集合,我们不难发现,在纯粹的第一、第三人称叙事之间,还存在无数融合两者的文本类型,例如,第一人称叙事逐步让位第三人称叙事的情况,或者第三人称叙事中出现第一人称叙事的情况。(15)本文不讨论“第二人称叙事”“集体第一人称叙事”和“无人称叙事”的特例。在麦尔维尔的《白鲸》中,第一人称人物叙述者以实马利从第45章之后已然隐退,直至踪迹全无。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托妮·莫里森的《宠儿》都以第三人称叙事为主,但小说中却出现了较长篇幅的第一人称人物自述。
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把第一、第三人称叙事归为两个集合,而把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的第三人称叙事分离出来,同时把第三人称叙事文本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分离出来,然后分别加以探讨。但从实践层面上看,这种截然的二元划分既难实现也无必要。如果从左到右,按照从第一到第三人称叙事的顺序把所有小说文本排列成一条直线,我们看到的实际状况是,截至目前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几乎都偏向这条直线的左边,而右边则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将不可靠叙述研究向第三人称叙事拓展,就是希望在这些空白之处找到不可靠叙述研究得以生根的地方。
本文需要廓清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可靠叙述的主体是谁?这个问题不免会进一步引发对叙述者的本体论追问,但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在相关的讨论和分类中,有两类叙述者十分常见,此二者将构成了本文的术语基础。第一类叙述者是叙述层面上的话语主体,其特点是处于故事之外,并对整个故事世界的生成负责。在其理论框架中确认这一叙述者存在的学者包括C.布雷蒙、米克·巴尔、塔玛尔·雅各比等人。戈德罗也认为,无论在柏拉图所说的纯叙事还是模仿叙事之中,都应该假设一种暗隐的“讲述机制”的存在:“必须将一个叙事的全部内容归因于我们从此以后称为‘基本叙述者’的这一暗隐机制……一切叙事都处于这第一级机制的管辖之下,即使叙事中出现明显的代理叙述者也不例外。”(16)[加]安德里·戈德罗:《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4页。他所说的“基本叙述者”就是这一类叙述者。第二类是在故事层面上从事叙述行为的人物,也称为“人物叙述者”或“人物—叙述者”,热奈特、布思、费伦在他们的理论阐述中所说的“叙述者”往往就是这类叙述者。为简便起见,下文把第一类叙述者称为“叙述者”,把第二类叙述者称为“人物叙述者”。
叙述者往往就是作者的代言人,这有时会导致叙述者和作者难以分辨,但在叙事学理论体系中,这两者轩轾分明。其实,不论在第一或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都具有明确的存在,因为任何叙述都对应一个叙述主体,但在第一人称叙事中,由于人物叙述者“我”处于“台前”,这往往使“幕后”的叙述者不像在第三人称叙事中那么易于感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既然叙述者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创造了故事世界,那么就很难说叙述者会与作者的“第二自我”(即隐含作者)产生龃龉。从理论上说,叙述者的叙述既是作者对隐含作者进行编码的手段,也是读者借以对隐含作者进行解码的途径,因此,叙述者偏离、背离隐含作者思想规范的情况都是难以想象的。叙事学研究把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区分开来,但在普通读者眼中,这三者是同一个主体,都是“作者”。严肃作品常常因崇高的思想境界与高尚的道德内涵令人心生敬意,虽然日常生活中的作者本人未必以作品中的道德标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虽然书中的人物时常受到读者的褒贬臧否,但读者恐怕不会质疑作者的用心,或者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作品中的叙述者往往都能获得读者的认可。至于经典之外的平庸之作,乃至等而下之的叙事读物,如果因违反常识、道德和人伦而引起读者不满,则不在当前的研究范围之内,并且,这类叙事文中的叙述者也在知识、思想、道德水平上与各自的隐含作者保持一致。
相比之下,人物叙述者是芸芸众生在作品中的投影,因此必然带有人性的种种优点和缺点,而通过人物叙述者的叙述行为来展现其优点,暴露其缺点,进而揭示社会、人生的复杂性,这往往是作者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可以说,人物叙述者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背离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这样的作品就可能缺乏应有的深度,对人物的塑造也会显得机械、呆板,缺乏生动性。从实践上说,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对象迄今为止都以人物叙述者为主,而所谓不可靠叙述也基本是故事层面上人物叙述者的叙述。
三
虽说针对第三人称叙事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很少,但实际上布思已经做过相关分析,只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未能得到继承和发扬。布思在《小说修辞学》第十二章中专门探讨了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不可靠叙述,例如他对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撒谎者》所作的分析。这个故事讲的是:画家里昂(Lyon)到大卫男爵(Sir David)府上为其绘制肖像,巧遇已为人妻的前女友卡巴多斯太太(Mrs.Capadose)。里昂在交谈中发现她的丈夫卡巴多斯上校(Colonel Capadose)满口谎言,于是主动提出为卡巴多斯画像,并竭力将其不诚实的品性表现出来,希望借此让卡巴多斯太太识破丈夫的本质,但最终未能如愿。布思敏锐地发现有多位批评家误读了里昂这个人物,他们认为里昂不论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男人,“都受到真理缪斯的鼓舞”,(17)Wayne C.Booth,Rhetoric of Fiction(Second Edition),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350.而布思精当地指出:“如果把里昂解读为一位为了抵制庸俗文化而谋求真理的高尚艺术家,那么这部作品就未免太浅薄了,书中精辟的妙语和辛辣的嘲讽十之八九都会失去意义。”(18)Wayne C.Booth,Rhetoric of Fiction(Second Edition),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353.布思的观点十分中肯,但是他的论述却令人难以完全信服。例如,他认为里昂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但里昂只是一个人物而非人物叙述者,因此从逻辑上说里昂不可能从事不可靠叙述。
令人不解的是,通过文本细读,读者也会像布思一样从小说中听到一种不可靠的“声音”。里昂提出给卡巴多斯上校画像,他的理由是:“他是个难得的模特,一个如此令人好奇的题材。他有一张表情丰富的脸,它将教会我无穷无尽的事物。”里昂的这番说辞显然是在误导卡巴多斯太太,从费伦提出的“事实/事件”轴线来看,这句话后面隐藏着里昂的不良动机。此刻里昂只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非人物叙述者,但这句话却与我们所熟悉的不可靠叙述非常相似。如果以其他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人物叙述者为参照,例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等,我们就会发现里昂说的这句话很不可靠,而且,这种不可靠与第一人称叙事中的人物叙述者的不可靠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共性:其一,人物偏离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其二,作者和读者能够背着人物达成某种“秘密交流”(secret communion),对于人物的不可靠性产生的反讽效果,读者能够心领神会。此处的第一种共性是不可靠叙述的基本判断标准,第二种共性是不可靠叙述的重要修辞效果。
上文中里昂所说的话属于直接引语,这使他的不可靠性得到了较为直接的体现。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某种间接的方式去感知他的不可靠性。里昂想要知道卡巴多斯夫妇对未完成的肖像画会作何评价,于是躲在暗处窥视。当看到卡巴多斯夫人声泪俱下,并目睹卡巴多斯上校用匕首将画像毁坏,里昂满以为自己的目标已经实现,此时文中出现了一句描述他心理活动的自由间接引语:“他的老朋友为自己的丈夫感到羞愧,而且是他让她经历这种感受,他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虽然这幅画已经沦为一块破布。”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卡巴多斯太太的真实感受,里昂显然对她的心理状态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前文中的直接引语一样,这句引语也体现了人物对隐含作者思想规范的背离,读者也能与隐含作者达成“秘密交流”。
申丹已经注意到自由间接引语中暗含的不可靠叙述。她研究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唱歌课》中的潜文本,发现自由间接引语可以“将人物不可靠的‘眼光’提升至叙述层”,形成一种隐蔽的不可靠叙述。(19)申 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小说中人物话语的表现方式是文体学、叙事学共同关注的话题,英国文体学家利奇和肖特将引语的表现形式分为五类: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言语行为的叙述体。英国学者罗伊·帕斯卡尔在对19世纪欧洲小说的研究中发现,自由间接文体(即利奇和肖特所说的自由间接引语)“通过词汇、句子结构和语气巧妙地把人物和叙述者的声音融合起来”。(20)Roy Pascal,The Dual Voice:Free Indirect Speech and Its Functioning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Novel,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21.在叙事学研究中,自由间接引语也称为“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间接自由形式”(indirect free form)等等。热奈特发现,自由间接文体会导致人物话语与叙述者话语的混淆,(21)Gé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Manchester: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172.而查特曼则认为,间接自由形式“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虽然含混在所难免,但由于少了附加语,它听起来更像是人物在说话或者思考,而不是叙述者的报道”。(22)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p.201.以上学者对自由间接引语的效果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撒谎者》的这个例子中,可以说是叙述者运用自由间接引语来模仿里昂不可靠的声音,由此形成不可靠叙述。
《撒谎者》通过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把里昂表现为一个不可靠的人物,这是叙述者模仿人物的话语和心理活动取得的效果。《撒谎者》的总体框架是第三人称叙事,(23)《撒谎者》1888年首次出版的时候,其中出现了一个以“我”自指的叙述者。在之后的一个修改版中,詹姆斯删除了三个“我”字,使整个文本的第三人称叙事框架变得更加纯粹。并且文本中混合了纯叙事与模仿叙事。在纯叙事部分,叙述者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其叙述是可靠的;在模仿叙事部分,叙述者成为了人物的代言人,其叙述既有可靠的成分,也有不可靠的成分。换言之,在模仿叙事中,当叙述者用不同的引语方式来转述人物的语言或思想的时候,人物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得到了揭示。其实在任何第三人称叙事文本中,只要出现模仿叙事,读者就能够感知到人物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以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为例,叙述者在第四章后半部分用大量的间接引语来进行模仿叙事,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对事件的错误认识和对彼此心理的错误判断,从而揭示出二人婚姻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聊斋志异》可以提供相反的极端案例。书中有若干篇短小精悍的小说,例如《象》《义犬》《大鼠》等,其中并不存在模仿人物语言的叙事,文中的叙述没有任何不可靠的迹象。因此,无论从理论推导还是文本案例来看,不论在第一或是第三人称叙事中,只要出现模仿叙事,就可能存在不可靠叙述。
四
以上分析表明,模仿叙事是不可靠叙述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叙述者通过模仿叙事来展现人物的不可靠性,一方面可以使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生动,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反讽,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在比较纯粹的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模仿叙事占据主导地位,故事世界的呈现受到人物眼光的过滤,因此故事中的现实可能是扭曲的,人物的思想可能是错误的,人物的品性可能是卑劣的。在较为纯粹的第三人称叙事中,纯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叙述者需要代替作者陈述事件、表达观点,以构建故事虚拟世界中基本的事实框架和道德立场,其可靠的叙述使叙事文本具有一种基本的稳定性。模仿叙事与纯叙事的这一差别可以进一步从根源上说明,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往往聚焦于第一人称叙事。
需要指出的是,在较为纯粹的第一人称叙事中,即便出现大量的不可靠叙述,退居“幕后”的叙述者仍然是很可靠的,不可靠叙述是叙述者的模仿叙事造成的结果。叙述者不仅要模仿人物发声,还要通过这种模仿让隐含作者与读者达成“秘密交流”。当我们把第三人称叙事纳入研究视野,并确定模仿叙事是不可靠叙述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时,就会发现不可靠叙述是一种“模仿叙述”。叙述者在纯叙事中的叙述是可靠的,我们可称之为“本色叙述”;叙述者在模仿叙事中的叙述或许可靠,或许不可靠,可称为“模仿叙述”;在混合了两种叙事的文本中,叙述者交替使用两种叙述手段。在模仿叙事中,人物可以在故事层面发挥叙述功能,成为人物叙述者,并可以在叙述中表现出不可靠性;人物也可以不发挥叙述功能(例如与卡巴多斯太太对话的里昂),其可靠性或不可靠性由叙述者通过模仿叙事来体现。我们由此发现,在第一、第三人称叙事中都可能存在不可靠叙述,但二者的重要不同在于,第一人称叙事中既有不可靠叙述,也有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而第三人称叙事中虽然有不可靠叙述,却没有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因此在将不可靠叙述研究向第三人称叙事拓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不可靠叙述者”这个术语。
细究起来,“不可靠叙述者”这个术语本身就不够严谨。谭君强发现,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的可逆性变化,(24)谭君强:《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115页。如果人物在一条轴线上不可靠,但是在另一条轴线上显示出可靠性,读者就会感受到不可靠叙述者向可靠叙述者的转变,反之亦然。里昂在“事实/事件”和“价值/判断”轴上都有过不可靠的表现,他先是误导卡巴多斯太太,后来又错误地推测她的心理活动,但是他对卡巴多斯上校病态的撒谎癖却具有极为正确的感知和认识。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在同一条轴线上的不可靠性也会发生变化,鲁迅笔下患病期间的狂人因精神分裂而无法以正常的感知去报道事件,但他却在隐喻层面上对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极为痛恨;病愈后的狂人应当能够以常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看待周遭世界,但他“赴某地候补”的行为却很可能是出于对封建体制的屈从。再者,“不可靠”含有贬义,用于指称言语不实、动机不良的人物十分恰当,但是,某些人物的“不可靠”却闪现出人性的光辉。例如,哈克贝里·芬在“文明”社会中接受的训导使他对自己匿藏吉姆的行为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但这一错误判断却表现出他天真可爱的一面和淳朴善良的本性,因此他的“不可靠”只在反讽的意义上成立。
以上分析可以从“不可靠”本身来说明“不可靠叙述者”这一表述的不恰当性,但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不可靠叙述现象可以从根源上否定这个术语的适用性。既然人物的叙述在本质上是叙述者的“模仿叙述”,那么人物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只是一种表象,因此更准确地说,所谓“不可靠叙述者”应该是“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但即便如此,“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也会造成理论分析上的困难。前文指出,第一人称叙事中可能存在不可靠的叙述者,但第三人称叙事中却没有。如果“不可靠叙述者”(或是“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这个术语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失去用武之地,那么其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从根源上说,叙述者可以决定是否模仿人物进行不可靠叙述,而且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只是在表现、揭示人物的不可靠性而已,因此在第一、第三人称叙事中,我们都可以把不可靠性归于人物,而叙述——不论其可靠与否——只能归属于叙述者。由于布思将里昂视为不可靠的叙述者,他就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不可靠叙述所作的分析难免存在理论上的混淆,其理论价值难免遭到削弱。
将第三人称叙事全面纳入不可靠叙述研究,有望打通一条理论路径,让我们从不可靠叙述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人称叙事文本。鲁迅的《肥皂》是一篇意味深长的小说,研究者可以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来阐释其丰富的内涵。在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视野中,仅就四铭这个主要人物而言,叙述者通过模仿叙事,在“知识/感知”和“价值/判断”轴线上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很不可靠的人物。对于西学和西方文化,四铭的心态是既向往又憎恨。之所以向往,是因为西方科技给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甚至令他的病态心理得到某种满足;之所以憎恨,是因为他对新学的无知使他茫然失措、落为笑柄。他对西学的贬斥虽然有些言不由衷,但反对女学的九公公和驯顺的儿子学程就像是给封建礼教增重的砝码,使他获得慰藉,进而坚定了他向“恶社会宣战”的决心。然而,重新返回封建道德制高点上的四铭,心中仍不断回响着光棍调笑女乞丐的恶俗话语。这一系列反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叙述者的模仿叙事,虽然事件的发展和其他人物的映衬也对四铭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模仿叙事使四铭的不可靠性得到了非常生动的展现,读者能够通过与隐含作者的“秘密交流”得到极大的阅读快感。
对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不可靠叙述保持敏感,还有助于我们从不同乃至相反的方向来解读文本,例如布思通过对里昂不可靠性的分析,对《撒谎者》做出了迥异于其他批评家的阐释。王阳认为《项链》的中译本剥离了西方传统和“女吉诃德”的小说传统,造成了这篇小说在中国的文化误读。(25)王 阳:《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239页。从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理解为译者将本国文化传统代入了对隐含作者的解码过程,同时又在翻译过程中构建出一个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高度一致的隐含作者形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误读。如果将“女吉诃德”传统还原到中译本之中,那么我们会发现,隐含作者并不否定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对美的追求,她并不是一个受资产阶级价值观毒害的女性。当玛蒂尔德为了偿清债务而辛劳时,叙述者转述了她的内心话语:“一定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她一定会把它还清。”此时我们也不能纯粹从道德层面出发,简单地将她的坚韧和笃定肯定为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叙述者只是借此来突出她身上的“女吉诃德”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是一致的。因此玛蒂尔德并不是一个不可靠的人物。在故事结尾的情节逆转中,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对资产阶级虚荣心的讽刺,而是对玛蒂尔德悲剧命运的嗟叹。
不可靠叙述研究一直未能有效地把第三人称叙事纳入研究视野,这可以归结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原因应该追溯到这一理论本身对“不可靠叙述者”这个术语不甚严谨的描述和使用。第三人称叙事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虽然不如第一人称叙事文本中那么明显,有时候甚至不易于察觉,但其客观存在却不容忽视。如果从根源上厘清一些理论混淆,从模仿叙事出发,把不可靠叙述归结为叙述者的“模仿叙述”,那么,第三人称叙事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现象就会变得易于识别和分析。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文本内涵的把握,甚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更新我们对某些作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