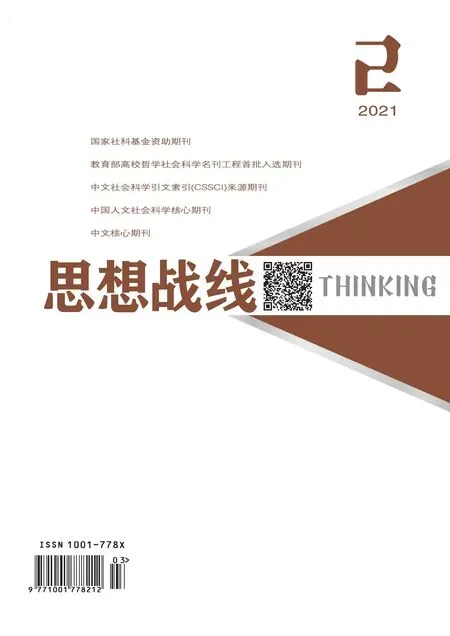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乡村减贫行动研究
——以湖南少数民族D村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张和清
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扶贫模式主要是以增加贫困人群收入为目标的福利救济,以及市场化、产业化的扶贫模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乡村贫困问题除了直接体现在经济收入不足之外,还间接表现在社会文化资产贫乏、生态致贫、乡村自治难以落实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受阻方面,因此,反贫困策略也逐渐从单纯的“收入+消费”扶贫模式转向发展型扶贫。(1)李 欢,周永康:《发展取向的资产建设: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扶贫实践研究——以P村“三区计划”项目为例》,《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如何从单纯着眼于经济减贫,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乡村减贫与乡村社区发展的有机结合,成为了社会工作介入乡村反贫困时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依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中国反贫困社会工作必须探索社区经济、社区社会文化资产、社区生态资产建设,以及社区自治等多维度的专业实务方法和减贫策略,以协助党和政府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建设,实现“五位一体”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图1)。
这其中,社区文化资产建设是中国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方法和策略的重要环节。依据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文化振兴是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五位一体”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重要维度。以此出发,本文运用资产建设理论和行动研究方法,(2)本文是历时4年行动过程的研究成果。行动研究提出研究即实践,研究者即行动者,行动为研究和理论反思提供了对象和依据,其核心在于理论和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即在行动中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再进行理论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用于指导行动。笔者自始至今参与了D村项目的“目标—计划—过程—反思”这一循环往复的行动。具体方法包括田野日志、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行动反思报告、一线社会工作者工作日志、项目规划及评估总结报告等。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下称绿耕)(3)关于该中心的介绍可见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lvgeng.org/about/。在湖南D村的减贫项目为例,研究运用社区文化资产建设行动策略重塑乡村文化主体性、推动乡村社区减贫的实践经验,探索基于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工作乡村社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实务模式。

图1:社区减贫框架图
(一)乡村社区文化问题与乡村贫困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乡村文化的边缘化及衰落,无不与发展主义取向的发展模式有关。发展主义将经济增长作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信念”,(4)参见许宝强《前言:发展、知识、权力》,载许宝强,汪 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单一向度的发展,本质上体现的是资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而且建构了一套“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和话语(Discourse)体系,(5)Arturo Escobar,Encountering Development:The Market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United Kingdo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p.9~10.从而保证其绝对控制的地位。在全球文化互动的张力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话语实践建构出了诸如“现代”与“传统”、“发达”与“欠发达”等二元对立的话语和文化分类体系,将现代文化视为正确的、主流的文化,(6)参见[澳]苏珊·谢区,珍·哈吉斯《文化与发展:批判性导论》,沈台讯译,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6页。并且不断用现代科技的知识系统取代其他知识系统,确保以西方工业城市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的同质性发展。这套发展话语对中国传统乡村的影响表现为:乡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逐步被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或工业化农业)所取代,(7)参见[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乡村被贴上了“贫穷落后”的标签,乡村需要通过发展科技、工业等手段进行“脱贫”。而文化上的二元论述则使乡村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陷入边缘化境地。(8)参见张和清《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8页。一方面,将乡村建构为贫穷落后的“他者”,并不断强化“中心—边缘”的意识,(9)See Arturo Escobar,Encountering Development:The Market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United Kingdo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p.49~52.相应地,将农民型塑为等待资本主义发展的对象,(10)参见张和清《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9页。并被客体化为“文盲”“等待发展的他者”,导致乡村文化主体地位丧落,(11)参见张和清《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9页;[美]埃斯科巴《权力与能见性: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发明与管理》,载许宝强,汪 晖《发展的幻象》,卢思骋译、张彩云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84~107页。进而加剧了乡村贫困。另一方面,重新建构了“知识”,将知识完全等同于学识(即专家的专业知识),排斥和贬低乡村的传统知识,视传统农耕文化为“廉价的”,致使农民缺乏对乡村文化资产的完整认知,逐渐丧失了对乡村文化的传承能力和归属动力,更无法利用文化资产获得平等的社会资源和公平发展的机会,最终导致传统文化价值意识淡漠且文化传承意识缺乏。(12)参见彭华民《福利三角中的社会排斥——对中国城市新贫穷社群的一个实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1页;[美]埃斯科巴《权力与能见性: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发明与管理》,载许宝强,汪 晖《发展的幻象》,卢思骋译,张彩云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84~107页。总之,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建构了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不断边缘化乡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致使乡村日益陷入结构性贫困的境地,同时,乡村文化被推向更加边缘的位置,面临文化主体缺失和文化传承意识淡薄的困境。
具体到少数民族乡村,令人感到尴尬的现实是,一方面乡村保留着独特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遗产,另一方面又面临民族文化不被认同以及自我否定的矛盾状态。少数民族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特定群体经过日常生活实践而形成的一套具有共享规范、价值、象征符号的内容。(13)[英]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罗世宏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第234页。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遗产有有形和无形文化两种形式,均反映了少数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维系着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遗产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族群的主体性和文化认同上,而以资本强权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了少数民族的“他者”身份,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主体的缺失和文化认同意识淡漠,最终加剧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脆弱性和边缘化,(14)张和清:《扎根社区推动脱贫攻坚》,《人民论坛》2018年第10期。更加深了少数民族乡村的贫困程度。
(二)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反贫困社会工作
社区资产建设最早由美国西北大学的John Kretzmann和John Mcknight运用到社区社会工作中,从而开创了社区资产建设社会工作新的实务理论和方法。社区资产建设相信社区民众(尤其是穷人、边缘群体等)有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强调实现社区长远发展终归要依靠社区内部力量。社区资产建设的目的就是动员、组织和发展社区的内生动力,核心是通过社会赋权提高社区民众的能力。在社区资产建设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挖掘和利用那些常常被忽略和遗忘的资产,(15)See Templeman,S.B.,“Building Assets in Rural Communities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in Ginsberg,L.H.,ed.,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Alexandria,VA:CSWE Press,2005.恢复社区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从而增强人们的主体性。(16)参见张和清,杨锡聪等《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0~41页、第68页。因此,社区资产建设的发展模式不是依靠外部力量,也不单纯以物质增长、收入增加来衡量发展,而是强调社区合作,激发社区内生力量,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重建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文化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文化遗产,(17)参见丁惠芳《四川省灾后资产建设与生计重建》,载邓 锁,[美]迈克尔·谢若登等《资产建设——亚洲的策略与创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3~276页。是社区资产建设中重要的资产资源。迈克尔·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在《资产与穷人》一书中将“资产”看做是任何想象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抽象的和实体的,如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等。(18)参见[美]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3~125页。学者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基于文化表现出来的有形或者无形财富的积累,进一步将文化资产划分为有形文化资产和无形文化资产,前者是指物质文化遗产和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包括油画、雕塑、工艺品、建筑等,后者则指民众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等。(19)[澳大利亚]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潘 飞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有形文化资产是可以被触摸到的、可视化的内容,而无形文化资产则强调文化内在共享的规范、价值和态度等内容,二者是互相承载、互相维系的,有形文化资产是无形文化资产的载体,无形文化资产是有形文化的灵魂,只有二者共同作用,才能塑造文化的主体性。(20)参见[美]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3~125页、第177~228页。
二、社会工作社区文化资产建设的社区减贫实践
2016年2月至今,绿耕深入少数民族村落D村开展农村反贫困工作探索。驻村社会工作者运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模式”,与村干部、村民,尤其是“三留守”人群共同行动,逐步探索中国乡村文化传承、生计发展、社会互助、生态保育和社区自治的“五位一体”社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D村概况与贫困表现
D村地处通道侗族自治县,该县是典型的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D村有1 800余人,其中10个村民组共计1 200余人集中居住在D村古寨,侗族比例占99%以上。人口结构方面,该村是典型的“三留守”村落,在已入户探访的77户中,留守家庭为50户,占总数的65%,其家庭的中青壮年均外出务工。(25)陈敏芳等:《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16年,第27页。同时,D村保留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产,包括有形文化资产如侗寨建筑,以及存在于侗族日常生活中的无形文化资产如侗族“萨坛”(祭祀老祖母)、“侃”(围在一起聊天),以及各种多姿多彩节日习俗。
D村的贫困使人印象深刻。首先,从生计方面来看,D村地处山区,山地比例大,耕地少,共有山地11 000多亩,而人均耕地不足7分,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下,村民仍能维持基本生计。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传统农业逐渐被纳入农业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难以抵御市场风险,面临“越种越穷”“生计困难”的窘境,而微薄的收入又难以满足高昂的现代消费开支。以栗某家为例,祖孙三代六口人,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4岁,按照一年的收入和支出计算:通过种植水稻、茶油、生姜、辣椒、玉米、棉花、钩藤、茶叶等农副产品,总收入约为7 700元;而年支出学费、农业生产成本、电费、伙食费、医疗费(无大病且不住院的情况下)、交通费、人情随礼等,在不购买衣物、添置家具家电和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年日常开支已接近10 000元,收不抵支。(26)陈敏芳等:《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16年,第26页。栗某一家三代同堂,夫妻二人年富力强,子女未到适龄入学阶段,一家正常年景尚且收不抵支,其他贫困户、民政对象的生计则更加困难。其次,从文化方面看,D村的贫困还表现在文化认同和传承意识淡漠,以及文化主体性的衰落。尽管还有掌握民族文化技艺(染布、织布、制作侗锦和头巾、木工等技艺,且擅长侗歌、侗戏等传统表演)的老人,但年轻人已逐渐放弃了对侗族文化技艺的学习,尤其是大量中青年人外出务工,使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相对于文明先进的现代化,D村被认为是落后贫穷的地方,村民也用外来的眼光看待自己,将自己视为“文盲农民”,导致D村的文化认同淡漠,不断丧失文化的主体性。
D村的贫困问题与经济全球化及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首先,随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的农业、农民无论是在产业分工,还是在市场竞争中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剧烈的价格波动使传统的小农难以适应,农民“越种越穷”的现象日益凸显。(27)张慧鹏:《集体经济与精准扶贫:兼论塘约道路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在D村,无论是农产品的销售,还是获取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都要通过市场来实现,但是,村民难以预测市场需求,更无法控制种子、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成本及农作物市场的价格,尽管不断努力提高农产品产量,但往往都是增产不增收,致使许多小农难以维持生计而陷入贫困,越来越多的中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留在乡村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儿童及边缘弱势群体,村庄陷入空心化的状态。同时,消费主义意识在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在D村,村民不断通过快速消费满足欲望,“短缺感”替代了“容易满足”。除了日益增加的生产消费和日常消费以外,尤为严重的是,以手机、衣物和汽车等物品为导向的享受型消费潜移默化地侵入村民的日常生活,这些“巨额”开支是大多数村民无力承担的,这更加剧了D村的贫困。可见,资本主导的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及消费主义都是导致乡村贫困的根源。(28)参见张和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8期;古学斌《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24页。其次,发展主义建构的二元对立的话语实践,造成D村文化主体丧落和文化认同意识淡薄。村里大部分青壮年进城务工,他们不仅想要增加经济收入,而且希望摆脱“农民”的身份和“贫穷落后”的文化标签。这既反映了村民对发展主义话语下的文明、富裕现代化的向往,又说明村民接受了西方“发达—欠发达”“先进—落后”等话语体系,从而内化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贫乏、生产方式原始、生活方式落后等标签。村民用“别人(西方)的眼光”来衡量和评价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以至于认同本民族传统的耕作方式落后,造成文化认同和文化主体性的丧落,失去了发展的自主性。
在解决中国农村,尤其是“三区”即“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农村的贫困问题时,大多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为目标,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产业化的途径发展市场化、规模化农业,增加农民务农收入;(29)陈文胜:《论乡村振兴与产业扶贫》,《农村经济》2019年第9期。二是鼓励农民进城打工,补贴家庭生计开支;(30)贺雪峰:《论农民收入断裂带》,《学术研究》2019年第1期。三是推动农村城镇化或工业化,通过“减少农民”解决农村贫困问题。(31)邢成举:《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陕省证据》,《改革》2016年第11期。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是鼓励和引导小农参与市场分工和竞争。然而,以“原子化”状态进入市场的农民既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无法摆脱被资本盘剥的弱势地位,许多人因此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同时,追求经济单向度的发展,以“收入+消费”增长衡量减贫成效,更是造成了农民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主义话语实践和现代化发展路径的依赖,从而失去发展的主体性。
迄今为止,只有经过严格选择的患者才能在生物制剂治疗中获益,因此,在疾病早期能够全面评估患者对疾病的易感性、临床特征、生物学标记、遗传学特征及疗效影响因素,进一步精准地进行CRSwNP内在型细化分型能有助于提出个性化的特异性治疗措施、最优化疗效,减少反复手术几率及有效预防下呼吸道炎症的进展[10]。另外,在治疗某一种特定发病机制的CRSwNP内在型时,是仅生物制剂就足矣还是需要联合应用其他的治疗手段,业界专家有必要共同探讨并达成相关共识[20]。
农村社会工作坚守弱势优先、公平正义的专业价值观,不可能复制资本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置“原子化”状态的农民遭受不公对待于不顾。相反,社会工作者要帮助农民争取劳动权益,就必须与劳动者共同探索自主发展的道路。
(二)乡村减贫的社区文化资产建设
绿耕的乡村减贫策略之一是社区文化资产建设,具体做法是推动村民重新认识社区文化资产,形成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社区自主发展。2016年至今,绿耕利用D村丰富多彩的侗族文化资产优势开展了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以此推动社区减贫。
1.挖掘、整理D村优势文化资产
以优势视角挖掘社区文化资产是社区资产建设的重要环节。社会工作者动员D村村民共同找寻社区文化资产,挖掘资产背后的故事和意义。首先,社会工作者与村民一起“用脚画地图”。通过重新走访社区,以欣赏性的眼光找寻各种显性的“有形文化资产”,并绘制成社区资产地图,尤其是对D村的鼓楼、戏台、寨门、礼堂、风雨桥等特色建筑资产做了挖掘整理后,发现这些有形文化资产依然发挥着维系村寨人际关系、宗族关系并提供公共活动场所的作用。(32)陈敏芳等:《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内部资料),2016年,第7~9页。
其次,与村民共同挖掘社区文化资产背后的内涵和价值。在社区走访和绘制社区地图的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培训并动员村里的青少年以深度访谈等方式访谈村里的长者,并将这些访谈整理、记录下来,作为社区教育的素材。一是有关侗寨建筑的,比如,作为侗族标志性建筑的鼓楼,曾经发挥集体议事、告知村规民约、迎送宾客、节日庆祝等政治、文化的多重功能,同时,也体现族群关系——一般是一寨一座鼓楼,并位于村寨的中心位置,(33)龚 敏:《侗族鼓楼建筑艺术的美学认知》,《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有重要的文化内涵。二是有关侗寨传统习俗和节日的,比如,侗族“萨坛”“侃”和“款文化”等民族文化及其治理习俗,以及村寨每年五月十三和六月初一的全村大聚餐等节日。三是有关传统民族技艺和文艺活动的,比如,侗歌、侗戏及制作芦笙的工艺,D村有一支村民自发组织的芦笙队,遇到逢年过节和重大活动时,芦笙队会免费为村民和客人们表演,大家随着芦笙音乐围圈跳起芦笙舞。(34)陈敏芳等:《怀化市社会工作“三区计划”通道侗族自治县洞雷项目点调研报告及项目计划书》(内部资料),2016年,第30页。
需要强调的是,运用优势视角挖掘社区优势文化资产贯穿于整个社区资产建设过程,因此,D村的社区文化资产挖掘工作是不断循环往复、持续深入的过程。
2.参与式打造文化博物馆
D村的社区文化资产优势非常突出,因此,以社区文化资产建设来推动社区减贫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参与式打造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考虑到老年人协会仍然是维系村庄宗族关系的重要组织,部分成员还掌握许多侗族的传统技艺,而且对打造博物馆一事积极性很高,因此,博物馆的筹建组织工作主要由老年人协会承担,社会工作者从中协助,村委会、妇女小组、文艺队和村民代表也参与其中。
第一阶段,老物件捐赠与故事整理。动员大会后,老年人协会和村民代表在村里广泛宣传博物馆计划并动员村民捐赠老物件,社会工作者制作了海报配合宣传和说明。很快,老年人协会成员主动捐赠出了自家的一些老物件,就连平时不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老年妇女也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进来,不仅捐赠旧物,还逐一上门游说动员邻居积极捐赠。慢慢地,几乎全村都参与到了博物馆建设的过程中。之后,社会工作者与青少年一起将口述故事整理、编写为记录册(《老物件故事书》),以书面文字的形式呈现给村民,共享本民族的记忆。
第二阶段,捐木料和制作展架。村委会召集村党员会议,讨论捐木料的具体工作,并向村民发出倡议,动员群众捐木料。社会工作者与老年人协会、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相关细节并作了分工,明确由村民积极分子负责和喊寨人沟通,确定喊寨时间和喊寨内容,以喊寨的方式同时进行动员;由老年人协会负责登记捐赠情况及出榜公布等事宜。最终,共计有58人捐赠50根木材、20余块木板。在展架的加工制作过程中,老年人协会骨干只负责搬运木料,社会工作者发动和邀请村里的木工手艺人与设计师共同制作展架,村内擅长电工的村民帮忙为博物馆安装电灯。
第三阶段,老物件摆放。社会工作者与村民一起,根据老物件的年代、历史、类别和外形大小,确定摆放方案;根据摆放方案将老物件逐一整理,摆放到相应位置。青少年则将有寓意的老物件文化卡片放在相应的物件旁边,以供阅读理解。
第四阶段,博物馆开张。在老年人协会的组织下,村民们策划了博物馆开张仪式。村民集资购买“合拢宴”(侗族聚餐)食材,妇女小组和其他村民负责做饭和安排聚餐,老年人协会和芦笙队负责迎宾表演,每一位老物件捐赠人负责在博物馆讲述老物件背后的故事,社会工作者担任协调者角色,负责协助村民做好开张的工作。博物馆的开张仪式不是由村委会和社工站主导,而是完全交由老年人协会和村民们自己去做,村委和社会工作者只是起到协助的作用,老年人协会和村民的组织能力、文化认同和主人翁精神在活动中都得以体现。
3.生态种植互助组
与以往依靠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及新种植方式,排斥老品种种植和传统农耕技艺,进而造成农民越来越依附市场的产业化扶贫模式的做法不同,绿耕尊重传统农耕方式和技艺,将之看做是小农参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祖辈传承下来的农耕方式和技艺,不应该成为农民在发展中被歧视、被标签化的包袱,而应成为实现自力更生内源性发展的源泉。绿耕利用D村红糯米种植的传统和文化优势,成立采取传统农耕方式的生态种植小组,不使用农药、化肥,减少中间商的差价;小组采用志愿合作的方式,集体经营、民主管理、按劳分配,改善小组成员的生计;小组收益5%~10%留作社区公益金,用于修建村庄公共设施、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开展社区救助等事项,以此推动村庄内部形成凝聚力,提升村庄的自主发展意识和积极性,以此进一步推进村庄朝着“五位一体”经济社会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一,推动成立妇女生态种植小组。绿耕社会工作者在留守村庄的妇女中进行沟通,并在贫困户中培育了11名妇女骨干。为了引导妇女小组深入理解生态种植的理念,拓展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工作者邀请贵州黎平县流芳村生态种植协会会员来分享生态种植经验,(35)D村与贵州黎平县流芳村交流时,两村都是侗族村,都从事生态种植。激发了妇女骨干对“什么是生态种植”“生态种植的可行性”“如何参与生态种植”等议题的兴趣,开始讨论生态种植红糯米改善生计的方案。社会工作者还组织妇女骨干前往广州市从化仙娘溪村参访,实地了解生态种植基地并体验生态旅舍,最终促成了妇女生态种植小组的成立。(36)陈敏芳等:《绿耕湖南D村项目的工作简报》(内部资料),2017年。
第二,增强自信心、完善管理。为推动生态种植小组建立严格的规则,确保种植的全过程是环保健康的,社会工作者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链接城乡互助网络资源。通过参加“农村网络建设与生态农业培训活动”和“地方品种登记及选育种经验交流会”,参观生态农场、了解生态农副产品的手作过程,共同学习生态旅社、合作社的运作经验等,开阔了D村生态种植小组的眼界,开始有意识地用优势视角认识本村的资产和特色文化。而通过参加广州“城乡汇”丰年庆活动,D村的15名村民吹响芦笙,集体表演庆祝丰收的芦笙舞,吸引了许多城市消费者的围观和赞扬,也极大地振奋了村民生态种植的自信心。在学习、借鉴外部经验的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引导生态种植小组成员不断制定和完善生态互助小组的规章制度,以集体民主协商的形式明确内部平等参与、互惠互利的权利、义务规定,以及分工、财务、分配等管理规则。
第三,搭建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平台。尊重劳动,赋予劳动者劳动的价值,是实现劳动者自主发展的前提。因此,首先要对生态种植小组生产的红糯米有合理定价。社会工作者和妇女小组一起核算成本:从育种到收割所需的人工成本,再加上种子、农家肥、保温薄膜等生产资料成本,1亩红糯米的总成本为5 000元,按平均亩产500斤算,每斤红糯米的成本约为10元。其次是要让消费者接受尊重劳动的定价。社会工作者通过链接城市消费者资源,搭建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交易平台,同时,组织城市消费者体验红糯米生态种植活动,让城市消费者参与播种、插秧、除草、收割、脱粒等劳动环节,从中认识传统农耕劳动的知识和技术,体会农耕的劳作的辛苦,进而理解并认同劳动价值及公平贸易的定价原则。
生态种植不仅增强了D村的互动与联结,而且拓展了其生计发展的渠道。红糯米生态种植改善了小组成员的生计,社会工作者适时推动村民发展生态民宿,充分利用D村丰富的文化资产优势,吸引外来消费者体验农村生活,品尝侗族传统美食,了解村寨的历史、传统建筑特色和侗族文艺活动等,增加了村民的生计收入。
总之,挖掘社区文化资产、打造文化博物馆与生态种植互助组间不是分割的,而是层层递进并互相促进的。挖掘社区文化资产的过程使村民意识到民族文化(侗寨建筑、红糯米等)是社区发展的重要资产,开始重视并理解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参与式打造文化博物馆能使村民内化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增强认同和文化自信心,同时,文化博物馆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发挥着凝聚并巩固社区内部联系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生态种植互助组进一步增加村民尤其是妇女之间、个体与社区之间的互动与联结。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文化博物馆和生态种植的乡村生态体验游有别于大众商业化文化旅游,它将民族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融合起来,加深了城市居民与民族文化的联结,使他们意识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种发展方式也为乡村生计发展拓展了新的渠道,并将社区减贫从文化层面拓展到经济、社会关系、生态等层面,进一步推动“五位一体”的社区减贫实践。
三、文化主体性建设与乡村社区减贫实务模式反思
基于D村的减贫实践,本文尝试反思基于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乡村社区减贫实务模式。第一,社会工作者打破资本的“客体化(物化)”逻辑,肯定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重建乡村主体性。社会工作者扎根乡村社区,以“局内人”身份理解社区民众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并引导其反思宏观社会变迁对微观日常生活的作用与影响,同时,社会工作者引导社区民众将“三留守”“原子化”“传统文化式微”和“生计贫困”等问题外化,从优势视角和资产为本出发,发掘被忽略、被边缘的社区文化资产,以整合社会工作的视角推动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建立社区互助组织,在互动合作的过程中,促使长者、妇女等群体在文化行动中找回自己角色、位置和主体性,(37)参见古学斌《云南省少数民族村的文化资产建设》,载邓 锁,[美]迈克尔·谢若登莉等《资产建设——亚洲的策略与创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4~252页。重新掌握社会文化关系的主导权。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使民众重新认识到了文化资产背后的内在价值,从而激发起整村弘扬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促进社区内源性发展。
第二,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赋权策略与方法,提升民众文化意识,重建乡村文化主体性认同。社会工作者立足于社区和民众文化资产,从“台前”走到“幕后”,将社区民众看作“参与者”而非“参加者”,关注和促进“人”的成长。基于被外化的问题(文化边缘化)和社区资产(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社会工作者打破“中心—边缘”的话语体系,将民众看作有能力的人,而非等待救助的对象,即坚持以社区和村民为主体,赋予民众平等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广泛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引导和启发村民以平等自由的对话方式共商合议、以团结协作的方式解决问题,使村民意识到个体的能动性及集体力量的重要性,在多次互动交流的过程中,社区民众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我”而是团结的“我们”,从而确立其主人翁地位,促进乡村文化主体性复兴。
第三,社会工作者构建社会资源网络,保障乡村文化主体性建设,有效推进社区减贫。社会工作者搭建社会资源网络的核心在于,摆脱资本控制的经济社会关系(即市场逻辑下的生产和非生产过程),重新定义和理解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和位置。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分别位于资源体系的两端,即二者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然而,资源体系存在资源不平衡、资源错位等诸多问题。(38)参见罗秀华,沈曜逸等《类汤恩比馆的实践取向:社工社群在草根社区的服务学习与推进》,台北:松慧有限公司,2012年,第170页。基于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视角,社会工作者通过盘点分析社区资源和小农户生产的低风险性,(39)参见[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小农与农业艺术:恰亚诺夫主义宣言》,潘 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5页。重整资源的配置,坚持以互惠互利“生产—消费”关系的公平贸易理念(40)曲如晓,赵方荣:《公平贸易运动:全球化背景下更具社会经济责任的贸易潮流》,《观察家札记》2009年第1期。推动资源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合作,构建“城乡合作,公平贸易”资源网络。在该网络的互动过程中,村民不再是被扶贫的对象,而是农业生产者、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市民也不再是扶贫者,而是民族文化的学习者、体验者,市民以公平贸易的价格购买村民的生态农副产品,不再是“上帝”,而是自我健康生活的践行者。这种互惠互利的“城乡合作、公平贸易”是城乡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尝试,能够提升社区的自主与自治精神,有效推进社区减贫。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文化资产建设是乡村“五位一体”社区减贫模式的重要维度,它发挥着促进民众意识提升(摆脱“物化”控制)、激发社区内生动力(重塑民众主体性、活化社会文化关系)的重要作用。D村的文化减贫实践表明,发展主义背后蕴含和隐藏着深层的资本运作逻辑,只有通过文化资产建设和社会赋权,才能破除隐藏于民族文化和民众意识中“他者化”的逻辑,并以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来推动文化资产建设行动,从而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自治的社区减贫,重建社区文化自信心。
致 谢:本项目得以落地实施,要感谢湖南省民政厅、怀化市民政局、通道县民政局相关领导及乡村干部的鼎力支持,尤其感谢所有驻村社会工作者长年累月的艰辛付出及村民参与!本文的完成得到了博士生陈曦的帮助和支持,特此谢忱!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