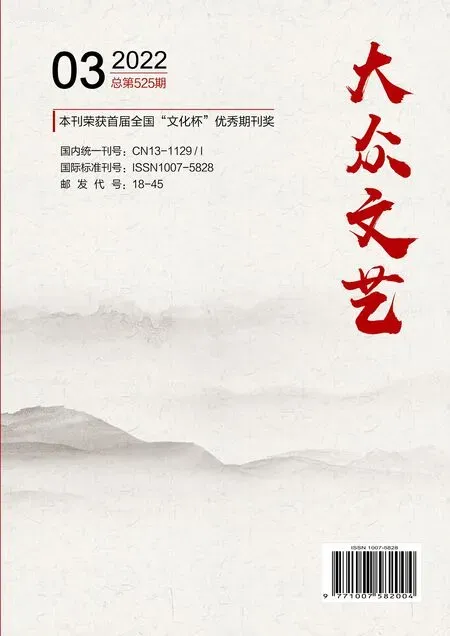“诗化的语言”*
——列维纳斯哲学语言研究
张炜炜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00)
列维纳斯力求建立“他者”哲学,保留他者的独立性、他异性。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列维纳斯在把和“他者”的关系认作语言、意义、差异之源而与“同一”无关时,他必须在哲学话语上强调打破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只能用一种“同一”的语言来诉说“他者”问题。
一、试图脱离存在论的语言
列维纳斯谈论《总体与无限》的缺点时说:“我谈论存在,用一种存在论的术语,自那以后我试图逃脱那种语言。”
列维纳斯《别样于存在》一书最后一部分的标题为In Other Words(换而言之),可见他试图在这本书中为换一种说法做出努力,《别样于存在》是列维纳斯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总体和无限》的深化。但在此书中他对存在论的语言更为警惕,他的术语一直都在变化,虽然常常取自日常生活,却没有严格定义,只是提供相近的、类似的词,希望能够建立一套新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固定化都有实体化的嫌疑,都会陷入存在论的陷阱,而这正是他要反对的,所以避免严格的定义就可以避免这种困境。
二、作为伦理关系的语言
列维纳斯认为语言不属于存在论而是从属于伦理学,语言代表了一种伦理关系,没有语言,伦理形而上学无法建构起来。他认为语言并不通过命题呈现世界,呈现存在,语言也不会是自我呈现的实体。语言是由“他人”带来的,一直处于一种“到来”的状态,语言的工作就是进入到一种和他人共处的关系中,即使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也能发现到,我们说出的话总是指向他人,而听到的话又是来自他人的,语言、话语、对话构成一种他异性的关系,这是主体之外的,缺少他人就不可能存在的世界。通过语言,主体和他人组成的关系就构成了伦理关系,语言呈现出一种“被表达的存在总体”,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语言呈现的对象,但是他人却不包含在这个“存在总体”中,因为他人不是对象,而是使对象得以可能的条件。
“脸”是他人身上最具有表达功能的地方,所以“脸”甚至直接可以用“言谈”(discourse)来代替,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脸”与语言是一致的。“脸”本质上是一个对话者,“脸”是一种在主体之外的意义的源头,由此成为要求对“他者”负责的话语的源头。列维纳斯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一种质询(interpellation),我与他者相互质询。[语言表明了在主体自身中不能被发现的,而且超出了经验的意义,“脸”提供了“我”和“他者”之间互相交流的可能性。但是这种交流也会有讲“他者”对象化、主题化的可能,所以“面对面”就是必然的了。“面对面”构成了主体和外在性的关系,使语言创建的东西得以可能。因为列维纳斯是在现象学经验的领域内说明“脸”的,脸是可见的,而与他人的相遇才因此可能,变成一种“面对面”的相遇。言谈意味着“回应”(response),在他人的“脸”的表达中,我“回应”他[列维纳斯在其著作中经常把“回应”和“责任”(responsibitilty)看作一回事]“你的脸的反应就是一种回应,不仅仅是回应,而且是一种责任,这两个词密切相关。”所以通过语言才能接近到和“他者”相关的外在性中,语言并未归入“他者”,语言不属于“他者”,只是从盯着“我”的他人那里而来。这个他质问我,命令我,而面对“脸”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肩负起了“责任”,语言由此构建出“我”和“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使用伦理标志出“存在的世界”。
“脸”在《总体和无限》中对理解列维纳斯的思想有重要作用。因为列维纳斯把主体和他人的“脸”的相遇放置在主体世界之外,“脸”代表了“他者”的异他性,这种异他性和外在性证明了存在不是终极和唯一的,在存在之外还有伦理甚至上帝。德里达对列维纳斯作为言语和注视的“脸”的评价是:“因为它打开和超出了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标识了一切权力、一切暴力的边界,标识了伦理的起源。”
三、言说和所说
列维纳斯“言说”(the saying)和“所说”(the said)的划分是他后期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他认为传统哲学只重视“所说”的内容,因为在日常的生活中,正是由于“所说”,词语才起到符号的作用,呈现出各种存在物,世界、存在等都是所说的内容,所说是主体之间的交流可以顺利进行的语言命题化系统,“存在论的诞生地就在所说之中”,“进入存在和真理就是进入所说”。因为所说(主要是内容)在日常生活和传统哲学中的优先地位,“超越”的向度就往往被忽略了,“超越”会将自己主题化,重新置于存在之中,始终被存在束缚。可见,列维纳斯想要达到超越、逃避存在的目的就不能按照传统的惯性规定“所说”,而是要回到“所说”中的“言说”去。
“言说”完全游离在“所说”的系统之外,“躲避理解、打断存在论,是同者向他者运动的真正体现”,揭示的是那些在语言的存在论方面发现不了的东西。尽管它必须依赖“所说”,但是它却指向语言中前源性的(preoriginal)、非主题化(unthematized)的伦理关系。所说总是主题化的,连贯的,也是有文法、逻辑的,“言说”却先于制约“所说”的所有的语法现象,它先于我们所说的语言,它来自人和他人之间的“亲近”(proximity),也就是面向他人。
但是“所说”和“言说”之间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或者可以被概括的辩证关系。虽然“言说”必须服从于“所说”,离不开“所说”规定的内容,但是“言说”并非“所说”的一个部分。相反,“所说”的主题化,也就是在“所说”的语言中,“言说”只剩下了印迹,列维纳斯说“每一种翻译都是一种背叛”,这就是指“所说”对“言说”的背叛,在“言说”中的东西在“所说”中被遗忘了,这个被遗忘的东西就是超越于存在的那个“别样于存在”。
四、诗化的语言
究竟哪种文字才能展示从“所说”到“言说”的还原,并且能够表达出“言说”中的“不可说”呢?《别样于存在》一书就是在做这种努力,他努力尝试许多新的名词,在互相呼应、互相关联中引申出意义,摆脱存在论,证明“超越”和“别于存在”的“不可说”。这种情况下,诗歌的语言形式激发了列维纳斯对自己哲学任务的新认识,尽管他对艺术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仍然承认自己后期的写作使用了诗歌的文体。诗歌,是“别于存在的形式”。
列维纳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对诗歌的研究中发现,诗歌的语言方式是历时性的,但是通过历时性却表明了一种不能被集合成整体的同时性的意义。他在诗歌的“所说”中发现了“不可说”的意义,他说这些“不可说”在诗歌中“比任何存在都离我们更近,没到场的东西在诗歌中得以重现。这就是诗歌中的诗意。诗意预示着维持它的东西在诗歌中的复活:不是在文字中,而是在每一次讲述文字的过程中。”
可是列维纳斯早期并没有意识到艺术的作用,反而对艺术一直秉持批判的态度。在1948年他的《现实与阴影》中,他就指出艺术不受制于道德,审美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一种不道德的无为,道德不是建立在感觉或者感觉机制上的行为。艺术并不能比存在更能表现真理性的东西,在《整体和无限》以及他的其他一些早期著作中,列维纳斯认为诗歌或者其他艺术形式最重要的功能是使人入迷,而不是别的,他始终心怀对诗歌使人陶醉力量的不信任。
一直到《整体和无限》之后,列维纳斯的思想才有了重大改变,他关于艺术的功用、地位,尤其对诗歌开始报以慷慨宽容的态度和理解,并且逐渐意识到“诗歌”语言作为一种“不可说”的“所说”形式对表述“超越存在”的重要性,在《别样于存在》中,他甚至自己用诗化的语言证明了从“所说”向“言说”还原的可能性,将诗作为一种“别于存在的形式”。在他看来诗人们有能力用诗歌描绘出一种不可言喻的东西超越人的具体感知,而且不知何故,诗总是可以表达远远超越了概念和普通语言本质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列维纳斯提起了康德和浪漫主义的美学传统。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发现的作为人类特殊的心理机能的“反思判断力”是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的统一,也就是说,康德认为在审美的反思判断中,反思判断力提供了一条从经验通往先验领域的道路,而在目的论的反思判断中,反思判断提供了一条从经验过渡到道德信仰的道路。正是反思判断力和理性之间的结合才能使它成为沟通自然和自由的中介,而美学就是呼吁人们利用天生的反思判断力超越概念的认识,通向在实践或理论经验中遗失的真理,列维纳斯认为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似乎比哲学更能接近真理。
“无法言说的正是哲学的任务”,列维纳斯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所说”的不可言说性,打破本质的概念结构,提取出“别样于存在”。他的《别样于存在》这本书解读起来相当困难,原因在于本书中那些模棱两可的陈述,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含糊其词的写作其实是列维纳斯表述清楚的唯一方法,因为这样的陈述不仅是对意义的再现,还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呈现,或者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命令或者要求,也正因如此列维纳斯的语言被当作伦理意义的使用,是一种伦理语言。通过这种诗化的伦理语言,列维纳斯希望走到通向“他者”的道路上来,他说“伦理的语言,是现象学诉诸为了纪念自身的中断,而不是来自一个展开了描述的伦理干预,这是接近的意义,和认识形成对比。”这样一种“诗化”的语言,正是列维纳斯寻求和展示的“超越存在”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