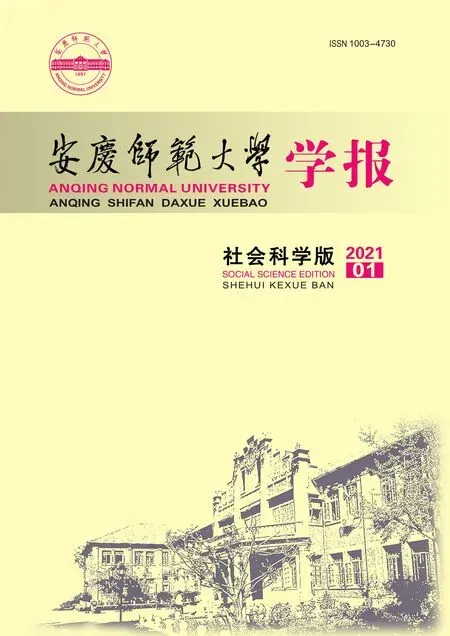论先秦两汉解经文体的萌生与确立
——以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为中心
王 静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相马经》文本凡3段5 200余字,根据其文本特点和语言风格,学界多认为是编定于战国时期楚人的抄本。颇值得注意的是,该《相马经》文本形态呈现出前后章节间对应、重叠的特殊现象。对此,赵逵夫先生曾敏锐指出,该帛书结构大体由“经”“传”“故训”三部分组成。其中,“故训”是对“经”的训释,而“传”则是对经文的深度阐发和引申[1]48-51。这一文体分类说颇有创见卓识,但目前相关研究仍显单薄。
历来人们对于“故训”“传”的性质定位,多认为其是伴随着汉代经学而蔚兴的解经文体,或仅将其内容限定于儒家六艺的范畴。这一方面是受到根深蒂固的古代经学思维影响,另一方面囿于先秦时期相关文献语焉不详,甚至付诸阙如。20世纪以来相继出土的简帛文献,极大拓展了这一问题的探讨空间,但遗憾的是始终缺乏一个完整确定文本。帛书《相马经》的面世,无疑为进一步探索解经之体的发生与嬗递提供了新证据、新思路。其“经”“传”“故训”的体例,证明了该文体在先秦经典传播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的形态,而且其在相关技术行当的经典文本记录中就已流行,是早期传播经典的通用文体样式。因此可以说,作为古代解经文体史上的一块活化石,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对于我们审视古代解经文体发展的学理路径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经典传授与古代解经文体的生成
古代解经文体,大抵是伴随着对古籍经典的讲授、传播而发展起来的。早在先秦经典之学的形成、传授过程中,业已孕育出了以“故训”“传”为代表的后世诸多解经文体。据史料记载,“经”早在春秋前已诞生。《庄子·天运》记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2]389此话似有依托之嫌,但孔子时就存“六经”自是不争的事实。春秋时期,“六经”已经成为贵族君子的教育文本,是当时的基本教材和普遍知识。《国语·楚语上》记载了楚国申叔时教育太子,其内容除了“春秋”“故志”“训典”等典制法令之学外,还有“诗”“礼”“乐”传统六艺之教,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3]由此观之,在“学在官府”的古代教育体系下,教学知识除了来自传统史官系统的累积,还应有源于师氏系统的传承。因此,无论是最初的教科书编订,还是师生教授活动,均当有简单的字句训诂和义理疏通,此概为后世经典解析之源头。这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六经”的传习论述发挥了关键作用。
孔子治经,强调“述而不作”。所谓“述”,即指其遵循古制,从事古籍整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4]1935-1936。
与此同时,孔子亦致力于对经典的广泛传播教学活动。文献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1938。孔子既没,弟子子思、子夏之徒相继传其学,共同奠定了传统经典文化深厚根基。《史记·儒林列传》曰: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4]3116。
可见,在师门前后相继的授受活动中,儒家已然形成了某种规范性的经典体系和师承源流。然而,以早期文化传播特点论,此时师生教学仍以口授为主,弟子将其中的言谈高见、口头传说等知识大意记录下来,此概为后世文体之渊薮。究其功用而言,由于文化早期人们离经未远,经典的诠释旨在帮助理解记诵、阐明学说以及发扬主张。因而,其文本通常不追求逐字逐句的疏解,转而以疏通大义为主要阐释方式。由此我们依稀能发见《毛传》“传”体博通杂论式释经涵义的源头。
历来人们对于《毛传》书题“故训传”的体例渊源多有探究。学者们多认为,《毛传》之所以摒弃今文经学“三家诗”各自独立的讲经模式,而集“故训”“传”注解体例于一书,原因可能与古文经学遵从古制,沿用先秦以来一脉相承的经典解说传统相关。如学者洪湛侯、吴万钟就明确指出《毛传》有着先秦以来古老的训诂、传来源①相关著作可参见洪湛侯:《诗经学史》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吴万钟:《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中华书局,2001年版。。在此基础上,徐建委《〈诗〉的编次与〈毛诗〉的形成》一文,通过具体诗文内容的对比溯源,大胆提出战国时代的《诗》,已有与今本《毛传》极相类之训诂的猜想[5]。对此,20世纪以来的出土《诗》学简帛文献可资以旁证。如阜阳汉简《诗经》、上博简《诗论》以及郭店楚简中涉《诗》材料等,编定时间就多集中于战国中晚期。这些出土材料对《诗经》词义阐释、题旨评判,与今《毛传》《诗序》已多有互见,从侧面证明了先秦时期《诗》学阐释的丰富形态,以及其与《毛传》的不解之缘[6]。
由此推想,在汉代经学形成之前,早期经典不断阐释、注疏和研习过程或已蕴含着多种文体因素的产生。如汉代解经之“章句”体,最初实源于古人读书授学中所施加的符号。汉代经学增益,辗转相授,故而发展成为“辨章析句”的章句之学。今考诸文献,先秦时并无“章句”之称,但根据其文体溯源可推测其早期大略形态。冯友兰认为:
章句是从汉朝以来的一种注解的名称。先秦的书是一连串写下来的,既不分章,又无断句。分章断句,都需要老师的口授。在分章断句之中,也表现了老师对于书的理解,因此,章句也成为一种注解的名称[7]。
可见,先秦时期由于文字载体的特殊性,“章句”或已成为早期解释经典的一种最基本方式,多表现为口授中以类似句读、符号功能而呈现的文本理解。因此,后代在追溯“章句”体来源时,亦往往上及先秦。据《后汉书·徐防传》记载:
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8]1500。
该引文将章句发明之功归于子夏,此说或因其寄托着汉儒稽古求道的主观愿望而未可尽信,但至少说明汉儒认为子夏之学已开章句注经的先河。对此,李贤注引《史记》曰:
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8]1501。
李贤注释透露出子夏授学传经活动与“章句”之隐约关系。“子夏传经”的史实于文献中多有记载,或为其“章句注经”说提供了可能性支撑。司马贞《史记索隐》亦曰:
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9]。
作为孔门“四科十哲”之一,子夏曾亲受圣人之道,谙熟“六经”训解与运用。孔子之后,其居于西河专门教授经典之学,对儒学的创立、传播自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推之,“章句”作为一种基本的文本训释方法和义例,出现在其经典传授活动中并不为过。
诚然,这种在经典传播过程中产生解经文体的方式,不唯儒家官学六经所独有,而实乃百家通用的解经之法。战国时期私家著述兴起,诸子百家立经而著说,在各自师门的传习中自当出现各式各样的解经文体。据今所见诸子著作,“解”“说”就是当时颇为流行的释经体。如《墨子》书就有《经》和《经说》,法家之《韩非子·内外储说》《韩非子·解老》《管子解》等。这两种肇始于先秦时期的解经文体,在汉代仍多有承传。简言之,至战国中晚期,诸子百家学派对经典的传授活动中应有一套基本稳定的文本阐释方式和话语体系,包括校定文字、考辨文义、经典运用等。当这些具体的释经方法诉诸文本形成记录时,性质大抵如老师的“教案”,或者教学实况记录。同时,该诠释体系亦凭借其特殊形式发挥着早期文体的功能,进而成为后世诸多文体的滥觞。以“故训”“传”“章句”等为代表的解经文体,最早或正是萌芽于其中。可惜的是,由于早期文化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这些知识多零散留之于口头而湮没不彰,因而缺乏一个完整确定的文本。而帛书《相马经》的面世,正给我们提供了一篇先秦时期解经文体的样板作品。
二、帛书《相马经》“故训”“传”的文体形态与特征
《相马经》文本呈现出前后章节间对应、重叠的特殊现象,尤其是“在第一行至二十八行里,大部分的描述好似显得更为玄抄莫测,但在第四十四行起到七十七行的叙述,大多是第一至第二十二行所述的重复,而在此作了必要的解释和补充”[10]。为此,赵逵夫先生撰文明确指出,该帛书从第1行至22行为“经”,篇名应为《大光破章》;从第44至77行为“故训”,是对第一部分“经”的解释、训诂。夹在“经”“故训”中间的为“传”,是对“经”“故训”部分的深入总结提炼[1]48-51。赵氏以汉代经学背景下的注疏文体为基本参照,分析《相马经》“经”“传”“故训”文体形态的合理性,其说颇多可采之处,故学界咸以为是。然而,从宏观的文体发展规律来看,各个时期文体功能差异决定了其文体内涵的不同,而仅仅以《相马经》文本内容而论,其“故训”“传”亦呈现出迥异于汉代经学之下的文体特征。
其一,“故训”释“经”的“取义”原则。《相马经》“经”“故训”对读互用,共同呈现文本内涵。综观《相马经》“经”部,其内容释文几乎全见于“故训”。从表现方式而言,“故训”对经文的解释即有整句、整段大意的串讲,如:
经:有月出其上,半矣而未明。上有君台,下有逢芳,旁有積緛,急其帷剛。
故训:有月出其上,半矣而未明者,欲目上环如半〔月;上〕有君台者,欲目上如四荣之盖。下有逢芳者,欲阴上〔者良目〕久。旁有積緛者,欲□□□□□□□□□□〔急〕其帷刚者,欲睫本之急,急坚久①本文所引帛书《相马经》文本均出自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后文不再出注。。
可见,“故训”整体以“经文+释文”相对应的方法,几乎对“经”文每一句都进行了释读。这种释义方式看似详尽繁琐,但其实质乃是建立在关键语义基础上的综合解说,上文如“月”“君台”“逢芳”“帷刚”等。同时,对于这些词语的解释,“故训”通常采用的是一种言语修辞的描述性分析,而非词源语义的探讨。如“月”在经文中是形容马的眼睛形态,“故训”训为“欲目上环如半〔月〕”;又如经文中“帷刚”指马的眼睫毛,“故训”以“欲睫本之急,急坚久”,直陈睫毛形态与马之材质的关系。
另,也有仅仅只是针对重点语词的阐释,如:
经:吾请言其解?夫徹肉散筋,而颈领弥高。泽光弥强,而筋骨难劳。
故训:吾请言其解?此夫徹肉者,肉毋傰,毋傰善踊躣。散筋者,欲诸筋尽细,细多利。泽光者,欲目旁之泽毋毛,毋毛多气。
显然,整段“故训”只是集中对经文中“徹肉”“散筋”“泽光”三词而作的训解,其余经文内容则略而不谈。如“徹肉”,当为马眼周围某一部位的紧缩肌肉。帛书整理小组亦以为:“徹,紧缩。《释名·释宫室》:‘柵,蹟也。以木为之,上平蹟然也。又谓之徹,徹,紧也,诜诜然紧也。’……凡物紧密则似缩敛,故名为徹而释以紧。”[11]“故训”直接译为,徹肉要大而紧致,不能松散,则马善走。他如“散筋”“泽光”,训为马眼旁边的筋脉要细小,则马多力。马眼要明亮有光泽,周围毫毛不宜多,则马气血足,能胜任长时间的负重。
综观以上两种“故训“方式可知,《相马经》“故训”不以传统的名物词义训诂为务,转而关注的是字词本身语义基础上的意义构写与功能描摹。简言之,“故训”主要目的在于挖掘语词背后所蕴含的实用知识,及其与相马之间的意义关联。这一点在“故训”未及阐释的经文中亦可见其端倪。如:
时风出本,行马以襄。昭乎冥乎,骏□□强。
伯乐所相,君子之马:阴阳受绳,曲直中矩。长颐短颊,乃中参伍。
信能知一,百节尽开。知一之解,虽多不烦。尺也成,利乃生,气乃并。
用之不倦,据□□见。其故何也?不唯一节正乎?
以上是为数不多未见于“故训”的4句经文。这些经文的共同特点是性质多为带有相马方法论意义的总结性论断。这种总结或是承接其上文而言,如1、3、4三句,显然是对前文所论的相马知识的总括、评价;或是对时人所共知的相马知识的强调,如句2引用相马家伯乐相马法,此法或为当时通用相法,与《庄子》记载徐无鬼相马法如出一辙,曰:“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2]626正鉴于此,经文大意已甚明晰,因而以“取义”为重心的“故训”直接忽略不予录入阐释。
之所以形成这种文体内涵的差异,概与《相马经》之形法数术性质紧密相关。相马隶属于“相六畜”,是中国古代形法数术中的重要类型。所谓“形法”,《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曰: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李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12]1775。
形法,即依据客观对象的形表来占断吉凶的方法数术,因此“形”与“法”为该类知识的一体两翼。古代“形”的本义包含“名”的辨析,亦称“形名”。然而,在相法技术行当里,“名”有时就是指行业内部约定俗成的专业术语或谚语,其意义通常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换言之,作为古代相马技术行当的经典,《相马经》文中的草木鸟兽、穴位筋骨在相马行家眼里,自然就对应着马体的高棱大眼、长毛厚吻等器官部位及形态特征,其意义已不言自明[13]。因此,《相马经》之“故训”通过揭示名物背后的“形法”意义,进而发挥其对经文的助读、评点等多种功能。
其二,“传”依附于“经”的互补性。从内容上看,《相马经》“传”部前半部分主要介绍马眼眶角部分的构造及其相法。文段开篇曰:“角欲长欲约,欲细欲危,阴欲䘏毋肉,欲廉……凡眶角所以相材久及肢能下节徐疾及徵表也”。然后进一步解说眶角周围徹肉、尺肉、游肉、微肉的结构及特征。可见,“传”文乃基于眶角为观察马体性能重要表征的出发点,而对其相法标准的补述。如其中介绍“徹肉”一节,显然是对经文“夫徹肉散筋,而颈领弥高。泽光弥强,而筋骨难劳”的阐发:
徹肉欲长欲深,欲薄欲泽,欲有焦,欲高前。故长贤短,深〔贤〕浅,薄贤厚,泽贤不泽,又(有)焦贤无焦,高前贤庳(卑)前。徹肉薄泽,薄骨而毋肉者,名曰骨荐,国马也。徹肉有三画会于前者,命(名)曰□□;杀兽能擒其前者,杀上兽。徹肉又(有)画二以兑(锐),会于前者……徹肉之驽四:□□者,一驽也;□而□者,二驽也;不能开阖者,三驽也;毋泽,四驽也。
“传”文先总说徹肉标准,然后再分论徹肉形态优劣、良马徹肉特征以及驽马徹肉特征。其后“尺肉”“游肉”“微肉”亦循此叙述之道,只不过此三者内容与“经”文无涉,“传”文阐释则是对“徹肉”的触类引申,但仍未脱离“经”马眼相法的主题。
后半段则分别由两段长篇“法曰”引文构成,其中一则曰:
法曰:良(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是恤(溢)而暴者也。不恤(溢)不暴而不走者,何也?前不能大抒,良(眼)不能后傅者也。大抒〔后傅〕而不走者,何也?是光泽不善,而动摇(摇)稗(迥)者也。有光泽动摇(摇)疾而不走者,何也?是(眼不〕能及徨,时见睫本者也。能及夜,时见睫本,而不能走者,何也?
根据前文“伯乐所相,君子之马”“吾请言其解”的措辞推测,“传”文所引“法曰”当指伯乐相马法内容。就其行文来看,引文主要聚焦于马的奔跑能力与眼之大小、光泽、睫毛、筋脉之间关系的论述。这些内容在“经”部皆有论及,但多造语玄奥,一笔带过。如经文“大光破章”,即《齐民要术》“目睛欲得黄,目欲大而光”,意为马眼大而亮;又如“急其帷刚”,是指马眼睫毛要紧固、坚挺而持久。对比之下,此处“传”文显然在直接的连续问答形式中铺叙了更多细节,甚至包括马的饮食、起居对于其善跑的影响等。由此推知,“传”文试图通过引用伯乐相法中的相关论述,对“经”作进一步通俗讲解和说明,“经”“传”相互补益,从而完整的传达相法意义。
总之,作为一部编定于战国时期的作品,《相马经》“传”体似反映了该阐述方式的最初功能和意义。赵逵夫先生亦认为,其“就其中的某几点加以发挥,既有对《经》文的总结,也有对‘经’的阐发”“深入透彻地就一些关键的问题作了论述,但却是自成章法,自有重点……这同西汉时代所谓‘传’的体例是一致的”[1]50。其实,赵氏所论的“一致性”,主要是就其文体内涵与释经方式的承传相通而论。然而,较之与“经”的关系,《相马经》“传”文无疑更加紧密。这主要是缘于早期文体发展尚不成熟,各种文体质素处于原生文体的裹挟、依附之中,尚未完全独立出来。故而,此时的“传”通常以传达经文作者意志为上,正如王充《论衡》所言:“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14]因此,《相马经》中的“传”看似独立于“经”“故训”之外,其实彼此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亲密关系,代表了早期经典“传”文的基本范式。
颇值得注意的是,《相马经》“经”“传”“故训”体例普遍采用三四七言的韵诵体句式结构全篇,富有极强的节奏感和文学性,从而显示出与传统儒家经典不一样的体例和解经风貌。如单论“经”文,曰:
大光破章。有月出其上,半矣而未明。上有君台,下有逢芳,旁有积緛,急其帷刚。兰筋既骛,狄筋冥爽,攸攸时动,半盖其明。周草既匿,莫见于旁,时风出本,行马以襄。昭乎冥乎,骏□□强。阳前阴后,瘛乎若处。而比离之似簧,若合相复。
《相马经》“经”部主要以四言为主,间杂以六言过渡,语句多骈文韵语。其中几乎每一句用韵,如“章”“上”“芳”“刚”“爽”“旁”“襄”“强”“簧”等前后相谐同韵。初读此文,如若不看“故训”,俨然一首体例严谨的描写诗。
另外,“传”“故训”句法上则往往骈散相间,以散句为主,与传统“五经”“六艺”之文“教案”式的解经形式大相径庭。如“故训”曰:
兰筋骛者,欲其如鸡目中絬,絬者善走。〔狄〕筋冥爽者,欲眼中白者粉,细而赤,赤多气……阳前阴后者,前后之夬也。前夬欲上,而后夬欲下,〔上者〕多气,下者善走。
“故训”语言则时而押韵时而不押韵,多杂言散句。除去并无实义的“者”“也”语助词,部分章节亦隐约呈现出三四七言组合的句法结构,具有明显的口诵、通俗的文体特征。
这种文本体制上的差异,或与《相马经》实用文的文本性质有莫大关联。中国古代实用文属于俗文学,其产生通常与社会生活、人生日用密切相关。据考察,先秦以来许多实用之文常使用韵诵体体式,其中一些就以三四七言为显著标识。这种句法结构亦以其顺口成腔的语言节奏,成为当时民间街头巷陌广泛传播和运用的体式。加之,古代社会早期,书写不易,许多专业知识依靠口耳相传。因此,为了便于记忆或诵读需要,人们常辅之以韵语形成音节韵律的流畅之美。《相马经》作为古代知识技术领域中的实用文,无疑强调其在行业口传心授中的上口、易记的文体特性。故而在造文作经过程中,自然采用“或歌或诵”的韵文体来增强文章可读性和认同感。
要之,帛书《相马经》“故训”“传”体例,反映了先秦时期解经之体循经立文、依经取义,与“经”相辅而行的亲密关系。与此同时,帛书文本鲜明的韵诵体式,亦使得“故训”“传”呈现出通俗、活泼的文体风貌。这些文体形态与特征,对于考察古代解经文体在先秦至汉代的发展递变,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三、“故训”“传”文体意义的确立与汉代阐释
作为一种独立而成熟的解读文献、训释经典的文体义例,“故训”“传”盛兴于汉代经学背景之下。中国古代的经学形成于汉代,内容上特指对儒家典籍的阐发、注释、议论之学。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有诸多以“故训”“传”为名的古书,其中仅“六艺略”诗家就有如《鲁故》《齐后氏故》《韩外传》《韩内传》《毛诗故训传》等。可见,“故”“训”“传”是汉代常用的三种经学注疏文体,有时亦合称为“故训”“故训传”。对于这几种文体的区别,前人多有探讨①可参见王博玄:《唐代以前经籍注解体裁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13年7月;冯浩菲:《〈毛诗故训传〉名义解及其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6期。。
首先,“诂”,亦作“故”“古”,或与“训”连称“古训”“故训”“诂训”。《说文》“言”部释曰:“训故言也。从言古声。《诗》曰诂训。”段注曰:“故言者,旧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谓诂。分之则如《尔雅》析故訓言为三,三而实一也。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15]92-93《诗经·大雅·烝民》亦载:“古训是式。”毛《传》云:“古,故。训,道。”郑《笺》曰:“古训,先王之遗典也。”[16]可见,其实在汉代之前,“诂”“故”“训”三者含义自有分别,西汉以后则合体兼用,并谓以今言释旧语,用通言训方言。据《汉书·儒林传》载:“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无传,疑者则阙弗传。”[12]3608《汉书·艺文志》独载“《鲁故》二十五卷”。此处的“训诂”当即指下文之“故”而言,意为鲁公释《诗》只解释词义、训诂旧文,而无阐发经旨义理,凡有疑惑处,便阙存待知,不强为之解。由此观之,至少在西汉经学发展时期,或单称“故”“训”,或并言“故训”“训诂”,彼此已互为训释,均强调对名物、制典的词义解释,此即阅读文本、疏通文字障碍的第一步。
其次,所谓“传”,本义为传述、传达。《说文》“人”部,段注曰:“‘遽,传也。’与此为互訓。此二篆之本义也。《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又文书亦谓之传。……引伸传遽之义。则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而传注、流传皆是也。”[15]377按段氏之说,凡传达、引申皆可谓之“传”,由此暗示出其与“经”的紧密关系。《文心雕龙·史传》对此亦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翻,记籍之冠冕也。”[17]283可见,作为经学的常备注疏文体,“传”之主要功能在于阐述经文微言大义,使其得以传示、流布于后。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12]1708。汉初传《诗》众家,尤以齐鲁韩毛四家为盛。三家今文经学中,齐、韩为《诗》作《传》,《汉书·艺文志》载《齐孙氏传》《韩内传》即是。汉代“传”体,内容“或取春秋,采杂说”,因此其阐发既可以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补充叙事,也可博引文献来进行议论。可以看出,这种博论、自由的解经方式本质上沿袭了先秦一贯的阐释传统。而在汉代经学功能逐步扩张的文化氛围之下,“传”体所论常常“咸非其本义”,尤其是今文经学“一经说至百余万言”[12]3620。“传”俨然成为一种服膺于现实政治教化的艺术手段。由此,其文体内部亦衍生出诸多体例划分,诸如“大传”“小传”“内传”“外传”等,某种程度反映了当时“传”体与经文关系的支解疏离。最典型的如《韩诗外传》中,其几乎每条引《诗经》作结,以支持政事或论辩的观点,显示出以传资政的为文用心。
同时,随着汉代古今文经学的盛衰,“传”体内涵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据学者考察,西汉时期的“传”多为泛论大意、通论杂说式,东汉“传”之义则更近于训诂,常表现为词义解释[18]。如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晚年著有《易传》《书传》《诗传》《礼传》。诸经传今已不传,但后人多有辑佚,其中《尚书马氏传》有四卷,其文“厥民隩,鸟兽氄毛”释为“隩,煖也;氄,温柔貌”[19]395,“竄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中训“三苗,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三危,西裔也;殛,诛也;羽山在东裔也。祖,始也”[19]398等。文中类似这种字词释文多不胜举,可见马氏解经完全是以“传”之名而行训诂之实。另一位荀爽,著《易传》《礼传》,其“传”亦为训诂式的体裁。古代文体的发展嬗递通常是多种因素促成,除了文体内部规律的调整完善外,同时也受到创作主体身份、文化心态的制约。据文献记载,东汉中晚期之际,古今文经学渐兴融合之势,古文经学迎来全盛时期。以马融、郑玄、贾逵等为代表的古文经师遍注群经,对经文注释时兼采各家之长,进一步促进各种经学体裁的交叉互渗。当时,古文学家提倡“古文科斗近于为实”“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教之始”[15]763,文字训诂再次回到人们视野得以重视。因此,东汉之际“传”体融入训诂的表现方式,改变其传统强调经学大义与价值的写作路径,无疑为“传”体注入了“为实”的经学内涵。
可见,从单纯解“经”的文体层面来看,“故训”“传”可能是有所区别的。然而,这种微妙的文体界限在汉代经学阐释背景之下,亦可形成某种微妙的文本创作张力。西汉毛公《毛诗故训传》(亦称《故训传》《毛传》)即为该方面释经之作的典型代表。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毛传》乃毛亨所作,赵人毛苌传其学。作为古文《诗》学的代表作,该书书题“故训”“传”的解经文体涵义,历来引起诸多讨论,其中尤以清代马瑞辰之辨析最详。其论“诗故训传名义考”条曰:
……盖故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故训”“传”之别也……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言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则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毛公传《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三体,故名其书曰《诂训传》……训诂不可以该传,而传可以统训话,故标其总目为《话训传》而分篇则但言《传》而已[20]4-5。按马氏言下之意,故、训虽分列二体,却兼有训释字义基础上的循经释文原则,因此可合而观之。而“传”常言经文之未言,更强调对文本内容补充与经义的引申阐发。具体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曰:
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21]59。
《毛传》首标“兴”体,然后再依次对字词名物解释、文意串讲。马瑞辰分析该诗体例,曰:“‘窈窕,幽闲也。椒,善;述,匹也’之类,诂之体也。‘关关,和声也’之类,训之体也。若‘夫妇有别,则父子。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传之体也。”[20]5此诗中,“传”即是取经典之义来申明学说。
又有以“传”事来解经者,如《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传》曰:
二子,伋、寿也。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泛泛然迅疾而不碍也[21]73。
《毛传》认为,《二子乘舟》乃为伋、寿而作。因此引卫宣公二子赴死就义之事来解诗意,所记情节亦与《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相类。此即《毛传》取“合之经传”事以解经之法。
总之,汉代经典之学凭借其地位和权威,势必得到广泛的传习、解说,由此亦建构出与解经文体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以“故训”“传”为代表的经籍注解之体,正是伴随着经学发展轨迹而形成文体意义的确立和嬗变,并最终走向成熟。
综上,中国古代解经文体的萌生与确立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一直以来,古代文体溯源虽有“宗经”的文化传统,但关于早期解经文体发生方式的探讨,多数情况下仍不免成为文体研究的“注脚”。《相马经》的出现,证实了先秦时期,至迟于战国中晚期,以故训、传为代表的解经文体并不拘泥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阐释,同时其在一些技术行业经典文本记录中亦已广泛流行,并形成较为稳定的文本形态。据此推定,该文体在先秦或已得到大量实战性训练,甚至以程式化方式加以成熟运用,因而是一种早期传播经典的通用文体模型。迄至汉代,经学大昌,经典所蕴涵的文体意义被挖掘出来,各种经典解说名目大量生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相关解经文体亦随之确立和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