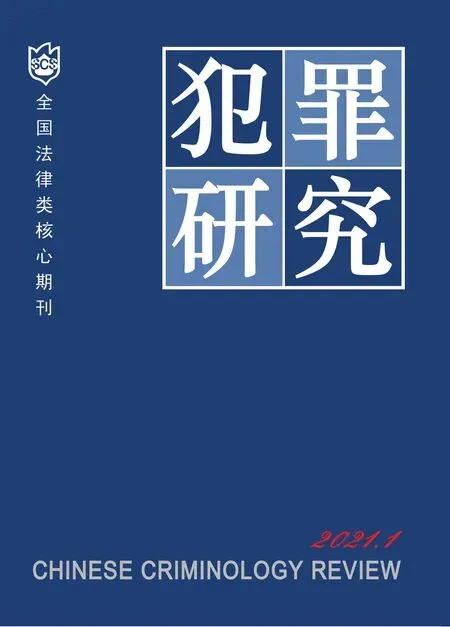新自由主义对美英国家刑事法制的影响及反思
时延安
一、引言
如何看待犯罪与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并非刑事法学所关心的问题。不过,从比较法研究的视域来看,如果结合其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会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对一国法律制度予以理解与分析。自21世纪以来,我国刑事法学界引入大量域外刑事法学理论,并对一些法治先行国家的法律实践进行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老一辈刑事法学家所积累的、基于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法社会学对刑事法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几乎被遗忘了,因而极少将域外刑事法学理论置于其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去研究,这或许是受一段时间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去苏俄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以及基于分析实证主义思想的法教义学研究范式在刑事法学界大行其道使然。然而,即便带有深刻分析实证主义烙印的刑法学,也不可能完全剔除政治观念的影子。〔1〕主要体现在违法性理论中,参见时延安:《大陆与台湾违法论之比较研究——以违法性的本质为中心》,载《刑法论丛》2013年第1 期,第497 页。当然,将一国刑事法制置于其政治经济体制之中予以分析研究,似乎不是法教义学的“特长”,不过,我们确实需要以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一个国家或地区刑事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轨迹,从而为我国刑事法制建设提供更为准确的设计方案,尤其是在尝试移植某些所谓“先进”法律理论或制度的时候。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英国家刑事法制有很大的转向,就是在刑事法制放弃或者大大贬低改善(rehabilitation)观念的积极意义,而在刑事法制中更加强调“应报(desert)”的思想,这集中体现在通过推动警察改革、量刑改革、监狱改革、预防性措施来强化刑事法制在社会中的治理效用。同时,通过在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中大量使用辩诉交易、对犯罪企业适用强制性合规、在刑事法制中大量引入私营企业的力量,通过购买服务来解决治安和刑事执行问题,进而在刑事法制中明显表现出经济考量(简单地说,就是“成本——产出”)的色彩。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两个倾向都在持续前行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美英国家的刑事法制。这两个倾向背后所支撑的思潮是什么?为何发生于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如何解释美英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监禁率急遽上升?为何美国刑事法制要将“改善”观念打入“冷宫”?西方一些左翼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影响美英国家刑事法制这些变化的思潮就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理解所遵循的路径,就是将刑事法制变迁置于更为广阔的分析框架之中,由此来发现刑事法制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脉络轨迹。
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角度对犯罪和刑事法制问题展开分析,在西方犯罪学研究也独占一席。例如,左派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绝对贫穷不引起犯罪,一些最贫穷的人是较少犯罪的,导致对政治结构不满的,是极端的收入差异;应当尽可能改善工人阶级的地位,包括减少街头犯罪率,同时也始终赞同采取措施减少法人犯罪和白领犯罪。〔2〕亚历克斯· 皮盖惹主编:《犯罪学理论手册》,吴宗宪主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12—413 页。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理解犯罪问题,也是西方左翼犯罪学的理论贡献之一。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分支受到冷落。例如,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曾说过:“在20世纪80年代,左派……逐渐相信犯罪原因完全是结构性的……从这种论述中,我们排除了个人的责任。”〔3〕[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 页。对1981年7月发生在伦敦的城市暴乱,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承认“暴乱事件”与收入、住房和失业等问题相关,而是出于“显然的”贪婪。〔4〕彼得·韦勒、赛思·密顿思:《英国的城市暴乱》,朱州译,载《世界知识》1981年第16 期,第6 页。这些执政者的看法,显然对从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分析犯罪的观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犯罪是个人行为,因而应强化对犯罪人的谴责和惩罚。作为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撒切尔、布莱尔的看法并不稀奇。可以说,有什么样经济思想的人,相应地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就会对犯罪与惩罚问题有着相应的主张。
本文引入的一个分析视角就是在美英国家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国内政治学、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比较深入,由此展开的批判也比较透彻,而这一思潮对刑事法制的影响,却很少为国内刑事法学界和犯罪学界所关注。对于这一思潮对刑事法制的影响,欧美一些左翼犯罪学家则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批判性研究。本文所运用的资料主要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犯罪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路径进行介绍,进而阐述美英左翼犯罪学家对新自由主义对刑事法制影响的批判;其次描述新自由主义对美英国家刑事法制的影响并进行评价;最后结合本土视角讨论这一问题及由此给出的警示。
二、美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刑事法制变化的影响
犯罪问题,既有社会生成的层面,也有权力构建的层面。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1)前者表现在,有些犯罪(即所谓自然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没有关联,可谓自古以来就有的犯罪;后者表现在,一些犯罪(包括但不限于法定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具有一定关联,是权力政治的产物。(2)国家权力将何种行为纳入犯罪,有着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考虑,也不排除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换个角度讲,一定行为被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侵害法益)本身就有价值选择的性质和过程。而被认为有社会危害性(或者侵害法益)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也是经过权力运作机制进行判断、选择的过程。因而,观察犯罪问题,必然要同时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而对一个特定社会的犯罪问题及刑事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更应关注权力构建的层面,如此可以一方面更为深入地理解其制度的来源和背后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由此可以更好地观察这一制度所存在的权力运作机制。所以,当我们将眼光转向美英等国家〔5〕本文所称之“美英国家”,主要指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不包括加拿大等其他英美法国家;本文所引用文献批判对象,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少数文献指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共同之处是,在晚近一段时间里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并在经济、社会、政治上付诸实施。过去半个世纪犯罪问题及刑事法制变迁时,就应当多视角看问题。而从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对于深入了解其刑罚权的运作机制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和路径。
(一)观察美英刑事法制的一个新视角
尽管我国刑法立法在经济犯罪、恐怖犯罪、腐败犯罪等方面大量借鉴了美英立法例,但在刑法理论上直接借鉴美英国家的内容并不多,其中引人关注的主要是犯罪化、预防性司法、量刑、社区矫正等理论和实践。在我们对美英国家刑事法制进行整体性观察时,会发现若干值得思考的现象:一是犯罪圈的庞大,而且规制犯(regulatory offense)的数量仍在不断膨胀;二是监狱人口自1980年代以来的快速膨胀;〔6〕Carey L.Biron,U.S.Prison Population Seeing “Unprecedented Increase”, IPS(Feb.4, 2013), http://www.ipsnews.net/2013/02/u-s-prison-population-seeing-unprecedented-increase.三是“向下刑法”的出现,即刑法及其适用更加指向贫穷人口,尤其在美国,监狱中黑人(同时也是穷人)在押犯比重畸高;四是监狱等刑罚机构的私营化;五是政府在刑事司法中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大;六是刑事追诉权的可交易化,最为典型的就是大行其道的辩诉交易制度;七是将刑事追诉作为维护本国经济优势、企业利益的手段。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明显看出刑事法制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联,要么作为统治在社会、经济竞争中“失败者”的工具,要么将刑事法制本身经济化了。
这些观察与很多人对美英刑事法制的感觉是有些落差的,因为从这些观察可以看出,这样的刑事司法体系具有三个倾向:一是歧视,即呈现出“向下刑法”的趋势;二是刑法被赋予更多规制功能,即以刑罚的“恐吓”达到社会控制的目标;三是以刑罚实施来保障安全,即将大量“危险人群”羁押于监禁机构,以期换取社会治安的优化。刑事法制如果具有这样的倾向,显然令人深感不安,因为如果刑事法制本身即具有这些“病症”,即便有着良好的“正当程序”保障,也终究不能解决实质正义问题,就像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前也经历了一个“像样的”审判程序。而对这些症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析,对我们的启示可能更为重要,这就要延伸到刑事法制的背景部分,尤其是所依赖的主流政治观念。
如果从主流政治观念思考刑事法制的变化,无疑要冒一些风险,一则具有上述倾向的刑事法制中所有制定法和判例都会表示不受政治观念的影响;二则在美英国家的各种政治理论和思潮色彩驳杂,从中提炼出影响刑事法制发展的主导型政治理论并不容易;三是已经习惯于纯粹法学研究的刑事法学界几乎不再从政治理论层面去讨论刑事法问题,而将刑事法研究与政治理论相结合,无疑会引起一些研究者的不适感。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一视角引入,恐怕根本看不清楚,美英刑事法制发展背后的动力和方向,也无法准确理解其遵循的真实法理,仅仅是以功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来理解,充其量是一种描述性的,而不是解构式的。这里所运用的视角,就是在美英国家乃至全世界喧嚣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对一些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
(二)过去半个世纪美英国家刑事法制的变化
美英国家犯罪种类的快速增加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其中大量罪名属于规制犯,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为防范社会风险、加强社会控制而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威吓和惩罚。当然,犯罪罪名及种类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刑事法制更为严厉,不能反映刑事法制实践的重心,也不能直接反映刑事法制存在的问题。结合本文主题,以下选取三个切入点来分析美英刑事法制的变化,为澄清导致这一变化的思潮提供事实基础。
1.监狱人口规模的激增
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狱是刑事法制的“末端”,但也是分析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刑事法制状况最好的切入点之一。从这个切入点,可以直接看到,某一特定刑事法制在惩罚犯罪方面投入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其运用刑罚手段管控社会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刑罚是不得已的“恶”,而“不得已”却是一个很主观的表述,就是对谁而言“不得已”,而基于不同价值理念和政策考虑,就刑法对社会和个人的干涉程度会形成不同认识,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得已”,而在另外一群人看来还没有达到“不得已”的程度。对监狱人口规模的观察,可以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了防卫社会,监狱是否应当关押这么多人?
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监狱人口飞速上升。1980年,美国监狱人口仅有503586 人,而到2017年则达到2234563 人,是1980年的4.44 倍。人数变化及趋势参见图一。〔7〕1980—2004年数据来自http://www.prisonstudies.org/country/united-states-america;其他数据来自美国司法数据局网站,2019年6月5日访问。美国监狱人口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一。〔8〕Roy Walmsley, World Prison Population List, WPB(Nov.6, 2018)https://www.prisonstudie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downloads/wppl_12.pdf.

图1 美国监狱人口总数
从图1 可以看出,美国自1980年以来监狱人口规模的飞速增长,在其他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存在同样的趋势。例如,英国1980年监狱人口为50550 人,而2019年5月监狱人口已经达到92406 人,是1980年的1.83 倍。〔9〕1950—2018年数据来自http://www.prisonstudies.org/country;2019年数据来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prison-population-figures-2019,2019年6月5日访问。新西兰1980年监狱人口为2625 人,而到了2019年5月监狱人口则达到10053 人,是1980年的3.83 倍。〔10〕1950—2016年数据来自http://www.prisonstudies.org/country/new-zealand,2019年数据来自“Prison Facts and Statistics-March 2019”,https://www.corrections.govt.nz/resources/research_and_statistics/quarterly_prison_statistics/prison_stats_march_2019.html, 2019年6月5日访问。监狱人口规模增大,能够明显看出,一国或地区的政府对监狱功能的重视,对刑罚的报应和隔离功能给予更多期待。
2.刑事法制财政支出的变化
刑事法制财政支出的增长,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惩罚犯罪而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治安,在政府财力充裕的情况下加大刑事法制资源投入,本无可厚非;而如果一方面消减社会公共福利,另一方面却加大刑事法制资源投入,那么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美国联邦用于司法部的预算过去19年增加了2.2 倍,2019年预算规模已达到299 亿美元,具体情况详见图2。〔11〕以上数据,来自美国联邦司法部网站,www.doj.gov,2019年6月5日访问。英国司法部预算在过去30年里也有显著变化,增长了近6 倍,其中2009年比1988年增长了近10 倍,〔12〕“Budget 2018”,载英国政府官网https://www.gov.uk/),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2019年6月5日访问。其中主要部分用于刑事法制。

图2 美国刑事司法预算
如果从绝对数目来讲,在美国和英国,刑事法制所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很高。例如,在2016年财政预算中,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的预算只占到0.7%,但教育部的预算也只占到2%。〔13〕美国驻华大使馆博客:《美国联邦部门预算一览》,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f297b00102xni7.html,2019年10月15日访问。2017年,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此后10年削减3.6 万亿美元联邦政府支出,其中针对美国穷人的医保、食品救助等支出将被大幅削减,〔14〕《特朗普“瘦身预算计划”新鲜出炉 穷人福利被大幅削减》,载今日看点网站,http://www.todayfocus.cn/p/12954.html,2020年1月10日访问。而用于刑事法制支出的费用并未明显减少。
3.刑罚处遇中的种族差异
种族歧视问题是美国社会的老问题。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应当说,黑人赢得了相对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其经济地位时至今日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纽约等大都市区黑人失业、贫困状况也比较严重。因而,当刑事法制转向严厉之后,黑人监禁人口显著上升。目前,美国人口约3.3 亿(截至2019年12月),其中非拉美裔白人约占62.1%;拉美裔约占16.9%,非洲裔约占13.4%,亚裔约占5.9%,混血约占2.7% 。〔15〕参见《美国国家概况》,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1206x0_680530/,2020年3月31日访问。而在2017年,刑期1年以上的罪犯为1439808 人,其中黑人占比为33.1%,白人占比30.3%,拉丁裔占比为23.7%。〔16〕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Prisoners in 2017, April 2019。从美国缓刑和假释的情况也能看出端倪,2016年底,大约有4537100 名成年人处于缓刑或假释当中,其中被处缓刑的人群中白人占55%,黑人为28%,拉丁裔占14%,被处假释的人群中白人占45%,黑人占38%,拉丁裔占15%。〔17〕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Probation and Paro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6, April 2018.
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的适用方面也存在明显的歧视问题。自1976年以来,美国共执行死刑人数为1499 人,其中34.2%是黑人,55.8%是白人,拉丁裔占8.5%;截至2020年1月1日,美国在押死刑犯有2620 人,其中42%是黑人,42%为白人,13%为拉丁裔。〔18〕Facts about the Death Penalty,https://files.deathpenaltyinfo.org/documents/pdf/FactSheet.f1585003454.pdf/[2020-6-1].在具体犯罪处理上,种族问题也被隐含地嵌入到刑事司法当中。以毒品犯罪为例,美国立法采取计量定罪的模式,即不考虑毒品纯度。由于毒品价格上的差异,黑人族群的“瘾君子”们使用一种叫“快克(crack)”的毒品,这种毒品纯度低但产生兴奋感快,价格低;白人“瘾君子”更喜欢纯度高但价格贵的海洛因。美国反毒机构在“反毒战争”中即聚焦于前者,因而从1985 至1986年,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年轻人因毒品犯罪被拘禁的比例上升71%;年轻黑人男性一度因毒品犯罪而被判处监禁的达到联邦监狱人口的57.7%。〔19〕Norman Abrams、Sara Sun Beals,Federal Criminal Law and Its Enforcement, Thomson and West, 2006, 359.
美国“反毒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歧视问题,不仅是种族歧视问题,更是经济地位问题,因为被定罪监禁的黑人也多是无业或失业人群,其本身即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底端。所以说,美国等国家的刑事法制更“青睐”少数族裔,兼有种族和政治经济地位差异两方面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一因素可能作用更大。没有证据能够说明,处于政治经济地位底端的人群更倾向于犯罪,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刑事法制对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端人群越轨行为的态度,就是观察这一刑事法制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有意忽视导致这一人群越轨行为的社会经济原因而更多强调个人的责任,那么,这种观念就已经具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因此,如果不关注一个人犯罪的社会背景而一味对个人进行谴责,那么刑罚的积极一般预防功能就会被削弱,这样的社会环境仍可能促成新的犯罪发生。
三、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刑事法制的批判
英国左翼犯罪学家罗伯特·莱纳教授在《法律与秩序:一个诚实公民的犯罪与控制指南》一书中指出:“过去数十年犯罪的大幅增长,以及对‘法律与秩序’的趋向,其共同的原因在于,自19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取得统治地位。”〔20〕Robert Reiner, Law and Order:An Honest Citizen’s Guide to Crime and Control, London: Polity, 2008, p.1.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林林总总。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的界定,新自由主义是指在继续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21〕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 页。这一定义基本上是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层面进行界定的。在新自由主义看来,自由市场可以将效率和财富最大化、将消费者需求传递给生产者,将资源分配最优化,并为企业家和工人提供动力。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光谱从经济领域必然延伸到社会和文化领域。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不仅是提升经济效率,而且还要提升政治和个人价值。在新自由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主张者哈耶克的论述中,即将新自由主义观念与法治、道德乃至国际关系问题紧密起来。〔22〕[英]弗雷德里希· 奥古斯特·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多个章节讨论了这些问题。莱纳教授也认为:“超出经济学之外,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下时代的主流话语,并深深植根于文化的各个角落,甚至成为公共政策讨论中想当然的正统观念。”“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自由市场与民主、自由和伦理相关。而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者宣称,有许多道德灾难:它们削弱了个人责任,迎合了公共部门的部门性利益,而非公共服务本身。”〔23〕Robert Reiner, Law and Order:An Honest Citizen’s Guide to Crime and Control, London: Polity, 2008, p.2.
法国学者艾玛·贝尔(Emma Bell)就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政策、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归纳:〔24〕Emma Bell, Criminal Justice And Neoliberalism, Palgrave and Macmillan, 2011, p.147-161.在社会政策方面,以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例,“故意地寻求‘不平等的策略’,进而形成社会分化为‘伤痕’的社会”。对此,英国学者艾伦·沃克(Alan Walker)也尖锐地指出:“与将不平等视为对社会肌体潜在危害的看法相反,撒切尔政府将其看作是事业的引擎。”〔25〕Alan Walker,‘Introduction: The Strategy of Inequality’ in A.Walker and C.Walker.(eds), Britain Divided:The Growth of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1997, p.5.按照新自由主义保守派的观点,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将贫穷视为理性选择,贫穷的威胁被用来充当鼓励发展企业精神的工具。为弥合由经济地位造成的社会裂痕,新自由主义政府试图将不同“行列”的团结建立在宗教和道德或者古老的政治形式如民族主义之上。在新自由主义文化方面,撒切尔政府试图促进文化转变,即背离社会民主主义并拥抱“企业文化”。正如撒切尔所说:“经济是办法;目标是改造心灵。”如此也形成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提供参与“大众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的机会,另一方面惩罚那些继续信奉“依赖文化”的人。以上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出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政策和文化的影响,而新自由主义对刑事法制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犯罪学者对本国刑事法制批判性文献比较多,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点明美国刑事法制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但揭示出的问题及其根源却直指美国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乔纳森·西蒙(Jonathan Simon)教授将美国刑事法制称为“通过犯罪进行治理(governance through crime)”,并将之作为专著的书名。〔26〕Jonathan Simon,Governing Through Crime:How the War on Transformed American Democracy and Created a Culture of Fe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虽然他自己承认,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他认为如此可以对当代美国法律和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策略问题。政客们努力在犯罪议题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二是,通过有效地运用犯罪议题将干预合法化藉以实现其他目标,例如将袭击孕妇导致胎儿死亡操作成堕胎权话题。三是,关于犯罪和刑事司法的话语、技术在各种制度中更加引入注目,由此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为治理提供新的机会。“通过犯罪进行治理”的后果就是,大量财政和行政资源被投入到刑事司法当中,如此导致一个从“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到“惩罚国家(penal state)”的转变;监禁人口比例急速上升,是20世纪80年代监禁人口的五倍,而3%的美国成年人处于矫正机构的某种控制(如缓刑、假释或社区监督)之下。然而,通过刑事司法体系管控这类人群并没有促使向城市内部增加更多投入来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却进一步使已被贫穷所困扰的社区被污名化了。在这一背景之下,穷人要忍受这种命运,同样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也在发生改变,但并非犯罪本身,而是“对犯罪的恐惧”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詹姆士·怀德曼(James Q.Whiteman)教授批评美国刑事法制是“严苛的司法(Harsh Justice)”。〔27〕James Q.Whiteman, Harsh Justice:Criminal Punishment and the Widening Divide between America and Europ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杜尔凯姆曾预见,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在社会的刑罚会变得宽缓。前现代社会倾向报应式的严苛,这种观念根植于人类复仇的本性,有助于社会创造和加强社会凝聚力。杜尔凯姆的预见只对了一半,就是欧洲大陆多数国家的刑罚确实变得宽缓了,但美国的刑罚却相反。实际上,自1975年以来,报应主义的强力复苏,不仅表现是在法律理论上,同样也表现在惩罚实践上,其中还不乏类似于前现代的羞辱实践,以及故意地开始复兴前现代的“枷锁”文化。报应主义的回归,其中也伴随着民粹主义司法和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情绪。
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洛伊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比上述两位学者对美国刑事司法的批判更为强烈,他在《惩罚穷人——对社会不安全的新自由主义治理》〔28〕Loïc Wacquant,Punishing the Poor:The Neoliberal Governance of Social Insecurity,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书对过去半个世纪主要政治转变进行了分析,即“福利国家的危机”和“惩罚国家的侵入”,而这一转变与新自由主义的勃兴具有紧密关系。在美国,在放弃“社会学的自负”的同时,犯罪学被认为已经显示出,犯罪的原因是犯罪人个人的不负责任和不道德,而对各种“粗鲁”和各式各样低水平脱序行为予以无情的惩罚,是抵御严重犯罪的最为可靠的手段;在美国大都市,警察被认为有能力“扭转犯罪传染病”,其方式就是,要么采取“零容忍”的手段,要么与失去产业的邻里“共同创造”安全;而监狱则被作为驯服“暴力掠夺者”和其他“习惯犯罪人”的明智选择。从被改造过的福利制度和惩罚政策之间存在的关联,即“工作福利制”与“监狱制(prisonfare)”之间,可以看出美国惩罚范围和强度上的快速增长。在社会最底层,监禁成为安置工人阶级中无固定工作人群的手段,尤其是那些被污名化的、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针对犯罪的战争(War on Crime)”的做法,事实上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第一世界”的样板,如此就导致这些国家的犯罪规模有所上升。华康德教授鲜明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美国刑事法制的影响,也指出,这一做法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法国和北欧的一些国家。
英国学者罗伯特·莱纳教授的研究将政治经济学与犯罪学相结合,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犯罪问题。而对美英刑事法制最近几十年变化的批判,他也是将其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在不平等的快速增长中,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解释为富人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倾向的政府的影响,资本运作曾被限制在安全、稳定和社会正义的范围内,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限制或多或少被解除了。对于刑事法制在遏制方面的功效,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充满了“毫无用处(nothing works)”的悲观看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经变形为寻找在治安、惩罚、缓刑和预防方面“什么能够发生作用(what works)”的思路,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刑事司法加强了打击力度,在美国一些大城市街头犯罪率下降,在美国乃至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刑事司法精英中聚合了一种“能够做到”的乐观主义精神。新右翼现实主义对妥当的刑事政策发挥有效的犯罪控制作用充满信心。詹姆士·威尔森(James Q.Wilson)即认为,控制犯罪的关键,是按照惩罚的可能性与强度,提供针对潜在犯罪的成本。“监狱有用(prison works)”的观念被这些人所推崇。“监狱有用”的共识基础,就是被监禁的人不能危害他人;不断增加的监禁人口受到欢迎,是因为如此会导致犯罪下降。但是,这种看法令人质疑,因为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美国监禁利率上升相比,加拿大和苏格兰,虽未提高监禁率,但犯罪率同样下降。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严重犯罪的高发率,比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更为严重,同时带有更具惩罚性和非人道的犯罪控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西方左翼犯罪学家对美英国家刑事司法进行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刑事法制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表现在:报应观念的回归,对刑罚惩罚的高度依赖,刑罚惩罚力度的加强,监禁人口快速增长以及对犯罪人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而更为深刻的影响则是,将刑事法制的重点集中在穷人和社会底层人群上,并通过营造对“犯罪的恐惧”来影响中产阶级人群。这一分析和本文第二部分的数据变化,是非常吻合的。更为准确地说,上述分析是对这些数据变化的分析和总结。
四、对新自由主义刑事法制的反思
毫无疑问,刑事法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经济思潮的影响,无论为刑事法制赋予何种神圣的光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就是,它不能不为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服务,也不可能不受特定意识形态的指引。在美英国家,新自由主义对刑事法制的影响,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在这些国家的刑事法制中,不会开宗明义地予以阐明,相反,其会通过相应的理论修饰来进行。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犯罪学界开始批评刑事矫正制度中的“复归(rehabilitation)”的观念,随之“罪有应得(just desert)”的观念(实际上就是报应主义)直接影响到刑事立法,最为典型的就是1984年的《量刑改革法》,之后美国联邦及各州开始推行量刑指南,大规模监禁的时代拉开序幕。从这一理论变化中,是无法直接看出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看待当时的历史背景,并不难理解,这一思潮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动因。
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及其他美英国家民权运动之后,出现了犯罪高企的现象,在批判犯罪学者眼里,这种现象应归结于社会、经济变动上的原因。而对犯罪高发的态势,美英国家右翼政治家的选择却是加大惩罚力度,在理论上否认犯罪的社会原因,转而强调犯罪是犯罪人的选择,与贫穷毫无关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具有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那里,自我主义的伦理与更多的惩罚、较少福利和更为暴力的犯罪联系在一起,而社会民主主义则奉行互惠的个人主义,当然,两种思潮的共同子集仍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在犯罪议题上能够压倒社会民主主义等其他思潮,实践上也是权力的推动,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在英国以撒切尔政府为代表、在美国以里根政府为代表)大力推动的结果。对此,英国牛津大学伊恩·路德(Ian Loader)教授论述到,首先“无论是自由派精英主义还是刑罚福利主义(penal-welfarism)都不能在过去40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中完好无损地存活下来。这有很多原因,既有地方性的、偶然性的原因,也有更为宽泛的、更为一般性的外来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派精英主义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情感——这一群体或许是一个阶层的某个部分,或者如布迪厄所说的、某种特定‘文化品位’的拥趸——这种情感保留在由他们共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非正式的关系中,或许常常是注定的。………随之而来的是,因‘复归理念’的衰落,而促使这一自信丧失;其次,更具争议且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清晰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并作为1979年撒切尔第一届政府选举主张的核心部分”。〔29〕Ian Loader and Richard Sparks, Public Crimin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71.
对“刑罚福利主义”的放弃,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刑罚的教育改造功能,进而使刑罚变成一个单纯维护治安、维护统治的工具。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研究,都强调社会、家庭对犯罪人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当然有个人原因,但也有相当程度的外在环境影响,尤其是经济地位上的原因。贫穷不是一个人犯罪的理由,但贫穷却是解释犯罪原因的根据之一。在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上,贫穷也不是减轻或者免除罪责的理由,但在犯罪预防上,必然考虑贫穷对诱发犯罪的影响。同时,在刑事处遇上,无论追究刑事责任还是刑罚执行,也不能因个人的经济及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变化对刑事法制的挑战,就是“试图割裂犯罪与不平等的联系,进而切断减少犯罪与一般社会条件改善的关系,以及采取理性选择的观点,而这与撒切尔、里根以及新右翼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30〕同上。
新自由主义刑事法制的观念,显然是将对贫穷问题的关注排除于刑事法制之外,而且将刑罚的对象集中于贫困人群,不仅在犯罪原因(及动因)上否定贫穷以及其他导致社会排斥因素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类人群在道德上予以贬低,其手段就是营造“对犯罪的恐惧”心理。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必然演化为对高危险人群的恐惧,如此对这类人群采取过度的刑罚性措施,无论是开放性还是监禁性的,自然会得到公众的支持。例如,美国联邦于1996年开始“梅根法”要求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所住各州执法机关登记,并将其资料公诸于众;如果州政府没有达到联邦“梅根法”的要求,联邦政府将停止向各州发放打击犯罪的联邦拨款。〔31〕“梅根法”的做法,在我国国内也得到很多支持。例如,史洪举:《呼唤中国版“梅根法案”》,载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12/id/3101970.shtml,2019年5月1日访问。不能否认这种做法有利于预防针对幼童的性侵案件,但其创造的问题就是,会造成对这类犯罪人过度的社会排斥,甚至“逼迫”这类犯罪人完全沦落犯罪深渊。
对犯罪人群的“固化”方式,在刑事司法中也表现出来。英国官方就曾宣称,一小撮持久的犯罪人是主要问题。托尼·布莱尔在2004年发起的惯犯和要犯对策(Prolific and Priority Offenders Strategy)即指出其将目标锁定于“多次犯罪人的最重要部分——只有5千人”,而这些人为10%的犯罪负责。内政大臣大卫·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声称:10 万罪犯实施了全部犯罪的一半。〔32〕Robert Reiner, Law and Order:An Honest Citizen’s Guide to Crime and Control, London: Polity, 2008, p11.这看起来有严格的实证调查根据,但却忽视了犯罪类型和犯罪人类型,以及警察执法和刑事司法本身的“偏好”。警察执法本身的偏好就是街头犯罪、毒品犯罪等下层人群实施的犯罪,而白领犯罪并非重点领域,刑事司法也同样如此。如此,在一种存在明显倾向的刑事追诉机制中,将追诉对象集中在一定人群就显得这些人对犯罪率“贡献”比较大。而一旦将这一人群“固化”后,对他们施以严惩并采取较为严厉的预防措施,自然就容易得到舆论和公众的支持,殊不知那些被警察执法、刑事司法有意无意忽视的犯罪类型及犯罪人群,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害会更大。
综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英国家刑事司法的趋重趋严转向,其根本的动因是,其主导阶级力量政治经济变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刑事法制未必是其着力的重点,但刑事法制肯定会受到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柯里即提出:“公众所讨论的美国社会中的犯罪已被主导意识形态所控制,该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遮掩居高不下的暴力犯罪和囚禁的社会和政治本质,并且试图证明我们所继续扩张的处罚制度是正确的,它使得任何事情在其他工业世界中或者在我们自身的历史中都是不那么重要了。”〔33〕[美]埃利奥特·柯里:《美国的犯罪与惩罚:神话,现实与可能性》,载戴维·凯瑞斯编:《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 页。显然,新自由主义刑事法制,成为西方一些左翼犯罪学者以及社会学家笔诛口伐的对象,那么,对于我们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警示就更加重要了。
五、结论
对于自1975年以来,由美英国家所引发的国际刑事政策变化,德国学者罗可辛(Roxin)指出:“抛弃过去占统治地位的重新社会化的思想,而要求回归报应理论和一般预防的趋势。这种处置性刑法(Behandlungsstrafrecht)的思潮被称为‘新古典主义’,〔34〕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紧密关系,再加上常引发混淆的“自由主义”一词,一些人主张应该将新自由主义改称为“新古典主义哲学”。用语所指思潮具有同一性。这种思潮在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赢得了特别大的影响。”〔35〕[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 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0 页。可以说,这一思潮对其他国家刑事法制的冲击也是存在的,这一思潮对我国刑事法制是否存在影响则需要考量。
从目前看,这一思潮对我国刑事法制的影响有限,几个基本观测点可以说明这一判断:(1)我国刑法、监狱法仍坚持教育和改造相结合的观念,从来没有放弃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的理念;(2)我国刑事法制始终强调平等原则,在司法实务当中也不存在针对贫困人群歧视性对待的情况;(3)刑事追诉权没有交易空间,认罪认罚制度的思想虽源于美国,但以一种相对合理的方式被立法机关所采纳;(4)刑罚配置和适用并没有表现出严厉的趋势,刑罚整体适用的规模呈现下降趋势;〔36〕最主要的指标就是5年有期徒刑以上宣告刑适用情况在下降。(5)监狱人口规模虽然有一定增加,但增加趋势并不明显。不过,刑事法制中的不平等问题仍令人警醒。例如,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即带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动因。即便微观层面的问题也值得反思和纠正,例如企业内部盗窃和职务侵占入罪“门槛”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现象或者问题,与新自由主义思潮似乎关联不大,但同样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更应当在理论界进行。坦白地说,目前刑事法学界对西方刑事法理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批判能力。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很容易被源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包装的刑法“统治术”〔37〕统治术(governmentility)的提法,源自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所迷惑,如风险刑法、预防性刑法、安全刑法、民生刑法等提法及相应理论无不是为刑罚权的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如果这些理论成为现实,那么,刑法作为“惩罚法”的角色,要更大幅度地向“刑事规制法”的角色转变,刑罚权的调整范围势必要大幅扩张。这些理论或者提法的缘起,或多或少都是源自西方国家,如果不加甄别,难免会在刑事法制效果上与这些新自由主义刑事法制的做法相类似。需要强调的是,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在刑事法制建设领域掀起意识形态之争,但要对美国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对其刑事法制的影响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加以甄别。对西方刑事法制采取批判式的借鉴态度是可取的,盲目地亦步亦趋甚至落入失语状态则是可怕的。
从本文第二部分图表,能够看出美国监狱人口在过去几年的降低,这出现在奥巴马当政时期。出身于社区工作者的奥巴马对美国刑事法制中存在的不平等给予极大关注和批评,在其任内进行了较大的调整。〔38〕Barack Obama, Commentary: The President’s Role in Advancing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Harvard Law Review 2017, January.应该看到这一纠偏过程的积极意义,然而,美国政治经济中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没有改变,也没有消退。也就是说,影响刑事法制的不平等因素和歧视政策不会有根本改变,因而这种自我纠偏的功效也不会发挥太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