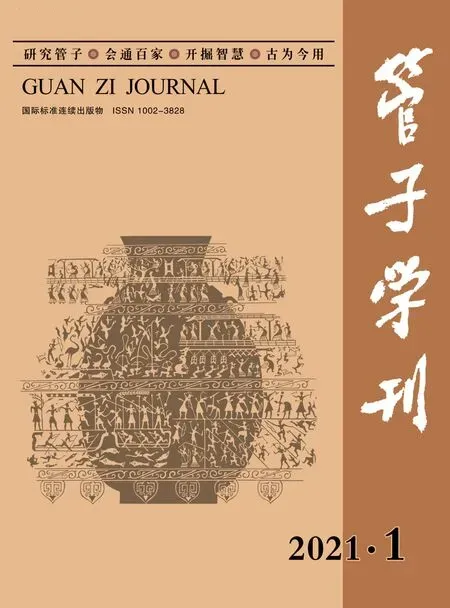《商君书》各篇的作者、创作时间及其成书考
黄 效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一、关于《商君书》复杂多样的争议
对于《商君书》的作者,学界历来充满争议。《汉书·艺文志》法家类:“《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1)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这是最早明确将《商君》的作者归于商鞅的著录。在唐代之前,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到了宋代以后,各种观点逐渐增多:一是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黄震谓:
《商子》者……其文烦碎不可以句,至今开卷于千载之下,犹为心目紊乱,况当时身被其祸者乎!……或疑鞅亦法吏有才者,其书不应烦乱至此,真伪殆未可知。(2)黄震:《黄氏日抄》,纪昀等:《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6页。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对《商君书》的作者进行怀疑的说法。但是黄震所说,顶多算是一种怀疑,尚未对它的真伪性作出判断,文辞的烦碎也未必能作为伪出的确凿证据,也可能是流传的原因。至周端朝则谓:“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拟取他辞,非本所论著也。”(3)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7页。周端朝的观点后来被马端临(4)马端临:《文献通考》,第247页。、姚际恒(5)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上海:世界书局,1967年版,第19页。、马国翰(6)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1页。等人引用,但其说法已被陈启天驳斥(7)陈启天:《商鞅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2页。。后来纪昀等人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亦称引周端朝的说法,但谓其“据文臆断,未能确证其非”,故其列举了新的证据:
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48页。
然《提要》所称的谥号,实仅见于《更法》和《定分》两篇,其他篇中并未提及孝公的谥号,所以即使这两篇为伪作,也不能得出其他篇就是伪作的结论。民国时期,胡适举《徕民》篇说及魏襄、秦王和长平三事来证明“今世所传《商君书》二十四篇,乃是商鞅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商君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没有法理学的书。”(9)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但胡适和纪昀等人一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即使《徕民》篇不是商鞅所作,也不能证明《商君书》中没有商鞅的作品。
胡适之后,容肇祖将书中各篇分为11组,并详细考证每组篇章的成书及产生时间,其最终结论认为:“《商君书》的著成,除首末二篇为后来加入外,(其他各篇)大体约成于秦昭王晚年之时。”(10)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但容肇祖的考证方法似乎存在极大的缺陷,因为他只是简单地依据各篇有一定相似的地方,便开始将其认定为同一时期的作品,但文中相似的地方至多说明各篇之间存在一定的借鉴和传承,并不必然说明其产生的年代是否相同。蒋伯潜认为《商君书》乃商鞅后学拾掇而成,至于是拾掇商鞅的遗著,还是拾掇只言片语,还是拾掇了一些思想,则没有明确说明(11)蒋伯潜:《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94页。。罗根泽则对其真伪及成书年代都作了探究和推断,推定此书非商鞅所作,且其成书应在商鞅死后百年左右的战国末年,其作者应该是一群秦国人或一些为秦谋的客卿,其思想的来源应该是商鞅(12)罗根泽:《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0-510页。。但罗根泽的证据实只涉及《更法》《定分》《徕民》《境内》数篇而已,对于以外的篇章则没有详细的探讨,故其实际上也是以偏概全。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没有论证和分析便认为今本《商君书》“内容乖舛极多,显为后人伪托”(1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62页。,比较武断。类似的还有蒙文通在《古学甄微》中直接将《商君书》称为伪书(14)蒙文通:《蒙文通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85页。等。
二是有学者退回到了唐代以前,认为《商君书》全是商鞅所作,但这种观点非常少见。清孙星衍在问经堂本《商子校本序》中谓:“《商子》书中屡称‘臣窃以为’‘臣之所谓’云云,盖此二十九篇是见秦孝公所上书,故后魏《刑法志》称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设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所称《法经》,似即此书,非李悝《法经》也。后人以其前有《更法》一篇,疑为编次者袭《史记》之文,谓其非先秦书。……盖由商子既死,为其学者哀其师而次其文,纪其遇合始末于卷端,如今世之序录者,不得以此疑其非古书也。”(15)方勇主编:《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524-525页。孙星衍的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认为《商君书》中的部分文章是陈上之文,把《更法》篇看成是序文。但他认为《商君书》完全是商鞅所作的说法实是一种倒退,因为早在孙星衍之前,学界已经在《商君书》中找到了多处后出的证据。类似的还有今人张觉,他认为:“前人对《商君书》各篇的怀疑大多不能成立。我的结论是:《商君书》大部分是商鞅的遗著,但其中也被编入了少许他人之作。”(16)张觉:《商君书校疏》,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页。
三是认为《商君书》中含有商鞅的遗著,但同时也承认它包含着法家者流的作品。李茹更谓:
《商子》文甚沉奥,定是战国文字。黄氏谓烦碎不可句,盖由讹舛多尔。至谓真伪不可知,大抵真伪无常,期于有合。商子以后为法家言者非一人,或润色为之耳。故《商子》之书,不必尽出商子;即不尽出于商子,亦不害为《商子》也。(17)方勇:《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第1册),第136页。
其意谓虽然《商君书》的行文似乎不可句读,但:一,《商君书》是战国文字;二,商鞅的作品可能被他的后学“润色”过;三,虽然《商君书》不一定全部出自商鞅,但一定是商鞅思想的体现。显然,在李茹更眼里,《商君书》包含着商鞅和商鞅后学的著作。类似观点如刘咸炘认为,《更法》《定分》为后人所记,《墾令》《境内》或为商鞅条上之文,《去强》以下有门人溢入的部分,不得谓全书是商鞅所作,也不得谓无商鞅所作(18)方勇:《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第8册),第291页。。惜其和李茹更一样,缺乏具体分析,只是直观的感觉。郭沫若认为,“现存《商君书》除《境内》篇殆系当时功令,然亦残夺不全者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并怀疑是韩非的门人伪作此书(19)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但也只分析了《徕民》《弱民》两篇,而对于为什么说《境内》篇是商鞅所作则没有分析。陈启天则认为《墾令》《说民》《开塞》《战法》《立本》《兵守》《境内》《慎法》等篇为商鞅所作或可视为商鞅所作,余为战国末期法家者流或汉人所作(20)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71-188页。。张舜徽先生认为商鞅“其初本有遗文传世,至六国时,又有人拾掇余论以补充之”(21)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第160页。,也只是推测之词,没有证据和论证。
高亨也认为《商君书》中有一部分是商鞅所著,如《墾令》《靳令》《外内》篇;《开塞》《农战》篇疑为商鞅所著;《更法》《错法》《徕民》《弱民》《定分》五篇是商鞅死后的作品;其他篇章已不可考(22)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5页。。郑良树则认为《墾令》《境内》这两篇应为商鞅自撰,《战法》《立本》两篇疑是商鞅自撰或其学派所写,余应为商鞅后学所著(23)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156页。。李存山则认为,商鞅自撰的篇目有《境内》《墾令》两篇,疑自撰的有《战法》《立本》《兵守》《外内》《修权》五篇,余十七篇为商鞅后学所作(24)李存山:《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9页。。刘泽华认为,《商君书》的大部分篇章非出自商鞅之手,其全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如《墾令》《外内》《开塞》《耕战》等是出自商鞅之手;第二类如《更法》篇是记载商鞅的言论;第三类是由商鞅后学写成的。可惜只有观点,没有论证(25)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5页。。张林祥则认为,《更法》《定分》篇是商鞅言行的追记;《墾令》《境内》篇是商鞅遗著;《开塞》《农战》《靳令》《战法》《立本》《兵守》六篇疑为商鞅所著;《画策》《修权》是战国晚期商鞅后学的政论文;《算地》《徕民》《错法》《赏刑》《君臣》《慎法》《禁使》是商鞅后学献给国君之书(26)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105页。。仝卫敏认为除《画策》《错法》《徕民》《赏刑》《慎法》是出自商鞅的再传弟子、《定分》一篇是拾掇商鞅余论的法家者流的作品外,其余应都是商鞅自著或亲闻商鞅之教的徒属和门客所为(27)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以上这些观点虽然承认《商君书》中有商鞅遗著,但对于具体哪些篇章是商鞅所作,则又莫衷一是。
四是一些人只是承认它是战国文字,但对于它是否为商鞅所作,又不置可否。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谓:“《管子》及《商君书》皆先秦作品,非后人伪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战国时事的资料。……《商君书》亦战国时的法家杂著。”(2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卷十七),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6页。只是指出了它属春秋战国时的资料,至于它是不是商鞅所作,则没有说。同样,吕思勉则谓:“今《商君书》精义虽不逮《管》《韩》之多,然要为古书,非伪撰,全书宗旨,尽于一民于农战一语。其中可考古制,及社会情形者颇多,亦可贵也。”(29)吕思勉:《吕思勉讲历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也只是肯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由上可知,对于《商君书》的作者及各篇的成书时间问题,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虽然在《商君书》是否有商鞅遗著这个问题上观点相似,但具体到哪些篇章应该是商鞅所作的问题,分歧巨大。所以,对于《商君书》各篇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
二、《商君书》各篇的作者及创作时间问题
(一)商鞅所作或疑似商鞅所作的作品
目前学界意见比较统一的是,《商君书》中《墾令》《境内》两篇应该是商鞅所作。笔者对此没有异议。《农战》一篇尽管遭到陈启天、容肇祖和郑良树的质疑(30)陈启天认为此篇是“商鞅死后战国时人推衍商鞅的主张而成”,见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24页。容肇祖认为此篇和《开塞》篇同出一手,见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郑良树虽然认为此篇非鞅亲撰,但应去其不远,说见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25-29、145页。,但也应如司马迁、张觉、张林祥、仝卫敏等人所言(31)司马迁曾谓:“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说见《史记·商君列传》。张觉说见其著《商君书校疏》,第38-39页。张林祥说见其著《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第77-81页。仝卫敏说见其著《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98页。,极有可能是商鞅的作品。因前人已有详细的辩驳,此不再重复。《战法》《立本》《兵守》《立法》篇学界也多怀疑是商鞅所作,笔者对此也认可。除此之外,《开塞》《君臣》篇也有可能是商鞅所作。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开塞》。对于此篇作者,刘安、司马迁、陈启天、高亨、仝卫敏、张觉等人明确为商君所作(32)刘安说见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24页。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18页。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27页。高亨:《商君书译注》,第11页。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37页。张觉:《商君书校疏》,第107页。,但是容肇祖(33)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郑良树(34)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59-60、153页。根据文中出现的“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与《去强》篇倡导的“重罚轻赏”“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相似;此篇还敌视“仁”“义”等,断定此篇当非商鞅所作。张林祥则认为肯定与否定的理由都不充足,故疑为商鞅所作(35)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第81-82页。。对于“多”“少”与“重”“轻”的区别,张觉认为一个是强调“量”,而另一个是强调“度”,两者不能等同(36)张觉:《商君书校疏》,第107页。。笔者认为张林祥所辨在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开塞》篇并没有《去强》篇中强国刑赏观的论述,其削国的刑赏观与《去强》篇也并不一致。在后文,我们将论证《去强》篇是商鞅后学对商鞅著作的摘录或感悟,同时还可能混入有后学的思想。照此看来,《去强》篇的作者可能也见过《开塞》篇,并误把刑赏中多与少的关系发展为重与轻的关系。此外,《开塞》篇谓“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其所描述的正是战国时期的景象。而文中倡导的告奸、刑名等观念也和商鞅本人的观念契合,故此篇还是极有可能是商鞅所作。
2.《君臣》。对于此篇的作者问题,学界分歧较大。陈启天认为:“本篇是一篇奏疏……主旨在‘缘法而治,按功而赏’,使民不得游食谈说而去农战,可说与商鞅的思想完全相合。然行文清畅,究为商鞅所作,抑为战国末期‘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未能断定,只可视为商鞅所作。”(37)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33页。容肇祖则认为本篇和《慎法》《农战》两篇是同出一人之手。但其依据依然只是文中有些地方重复互见(38)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郑良树则认为儒家的思想重点是分阶段性的,“到孟子时代,才把思想重点放在‘义’字上,而‘诚’字的宣扬却要到《中庸》的成书时代,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因此《商君书》对儒家的批判也是分层次的,本篇只言“义”不及“仁”,因此可能与《徕民》与《修权》篇相似(39)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21-123、155页。。仝卫敏则从本篇的思想特色出发,认为本篇的思想符合商鞅的思想特点,故应是商鞅所作(40)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206页。。
笔者认为,此篇也极有可能是商鞅所作。因为:一,郑良树对儒家思想发展重点的理解可能未必准确,事实上“义”的观念从孔子时代开始,在儒家中就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即使到了孟子时,也不会超过“仁”,否则孟子就应该提倡“义政”而非“仁政”。二,郑良树认为,《中庸》篇的成书似乎应该在孟子之后,但事实上《中庸》的成书一直争议较大,学界多认为是子思的作品,对此笔者已有文章考证(41)黄效:《再论〈中庸〉的成书及作者问题》,高华平:《先秦诸子研究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180页。。三,事实上当时的各国都面临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王权的任务,秦国也不例外。在孝公之前,秦国的公室其实十分混乱,贵族之间经常争权夺利,以致王权的交接也经常出现波折,孝公父亲献公废立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商鞅作为孝公朝的变革者,其上书提醒孝公注意“依法行政”,以革除前朝弊端,似乎也应该是“变法”的题中之义。故综合考虑篇中的思想特色和篇外的现实需要,《君臣》篇也极有可能是商鞅所作。
(二)商鞅死后至秦昭王时期的作品
除了上述篇章可能是商鞅自著的作品之外,《商君书》中还应存在一类不是商鞅自著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应该是商鞅的后学或战国时期受商鞅影响的法家者流所作。这部分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商鞅死后至秦昭王时期的作品;另一类是秦昭王后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作品。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前一类。
其中,《更法》篇虽然从《四库全书》开始便被质疑非商鞅所作,但其所记载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对此仝卫敏已有详论,笔者同意其认为本篇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史官所作的说法(42)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211页。,但认为应该是孝公死后的追记。《赏刑》篇虽然学界多认为非商鞅所作,但对于其是否受《韩非子》的影响,郑良树、张林祥、仝卫敏等人有不同的意见。其中郑良树认为此篇中的无赏、无刑、无教等思想可能受《韩非子》影响(43)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66、109-113页。,张、仝则不以为然,认为郑良树所说的思想在《商君书》其他篇章早已出现,如“以刑去刑”“以战去战”“以言去言”等。而且他们都注意到了,与《墾令》《农战》等篇中将赏罚归于农、战不同,《赏刑》篇只重视“战”,故他们结合《画策》等内容将其判定为秦昭王时期的作品(44)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第97-98页。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79-183页。。笔者认为他们的判断较为合理。其他各篇的具体分析如下:
1.《去强》《说民》《弱民》。关于《去强》篇的作者问题,陈启天认为是战国末年和汉初“法家者流”研究商韩的读书杂志(45)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25页。。容肇祖认为它和《说民》《弱民》篇可能是出自同一作者,成于秦昭王时期(46)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而郑良树认为其因袭了《农战》篇许多观点,故其成书要比《农战》晚,又因其文中主张“重刑轻赏”,故把它推定为商鞅后学中持异议者所作(47)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25-30、35-40页。。张林祥则注意到它不仅因袭了《农战》篇中的观点,也与《开塞》《靳令》《错法》中的观点有重叠,并认为“重刑轻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最后将它判定为杂录(48)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第101页。。仝卫敏则力排众说,将它视为商鞅所作,并认为它虽然成书比《墾令》篇晚,但应该在商鞅变法期间,张觉的观点与之类似(49)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09-119页。。仝和张还对前面众人的观点都有所批驳,但略显牵强。
笔者认为,《去强》篇是商鞅著作杂录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一,从其行文的特点看,《去强》篇整体上是无序的状态,像是摘录或片段式的感悟。二,从其和《农战》一文的关系看,两篇类似的地方很多。但在这两篇谁因袭谁的问题上,很可能像郑良树所说的,是《去强》篇因袭了《农战》篇,而非《农战》篇因袭了《去强》篇。因为《农战》一文逻辑连贯,文风混融,应该是成于一人一时之手,我们前文已经说明,它应该是商鞅所作,而《去强》篇逻辑杂乱,故更像是后学从多处著作中摘录而来。那么,《去强》篇既然与《农战》篇有部分重叠,这是否就说明它全篇的内容都成书较早呢?这个可能未必。据蒙季甫先生的研究,《说民》《弱民》篇应该是《去强》篇的传(50)蒙季甫:《商君书说民弱民篇为解说去强篇刊正记》,《图书集刊》1942年第一辑,第55-61页。,这种说法获得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同时,学者们注意到了《弱民》篇提到了商鞅逝世六十年后秦国攻破楚国鄢、郢之事。故《弱民》篇不可能为商鞅所作,《说民》篇也应类似。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两篇传的特点就会发现,虽然它们同为《去强》篇的传,但其解说的范围却没有重叠,《弱民》篇对应的是《去强》篇前面的部分;《说民》篇对应的是《去强》篇后面的部分,这两部分极有可能成于不同人之手,但其风格体制相差不大,故或在成书时间上相差不远。而从《弱民》篇提到商鞅死后之事看,《去强》篇与之对应的部分应该成书较早,或出自商鞅所作的各篇作品,《说民》篇对应的部分可能比之稍晚,但也不会太迟,也有可能是同时期的作品。故《去强》篇这两个部分的成书应该整体上比较早。但是,《去强》篇末尾“举民众口数”“粟死而金生”“强国知十三数”等部分,并未见于《说民》《弱民》篇。对此,郑良树认为这些都是后人附益的部分,应该是秦始皇即位以前加入的,“编撰者既将前后两篇误合为一,又杂抄另四段文字于篇末,才形成今天《去强篇》的样子了”(51)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48页。。笔者认为此说不无道理。三、就像郑良树所注意到的那样,《韩非子·定法》篇说商鞅主张“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史记》也记载了他变法之初曾重赏徙木者,但此文却主张“重罚轻赏”,与《史记》所载精神不符。虽然张林祥、仝卫敏、张觉等人对此多有辨析,但笔者认为“厚”与“轻”应该是不同的,故《去强》篇或许包含着商鞅后学发挥的部分。四、摘录式的文章在先秦并非没有先例,《郭店楚简》中的几篇《语丛》就是各家学说的杂录,故《去强》是杂录也并非不可能。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篇杂录,而且这篇杂录的形成具有历时性。至于《说民》《弱民》两篇的成书时间,因为它们都是《去强》篇的传,体例又大致相同,故应该相差不远或同一时期,由于《弱民》篇提到商鞅死后六十年发生的事,我们大概可以将它们视为秦昭王时期的作品。
2.《徕民》。关于此篇的作者,虽然学界历来都认为它不是商鞅所作,但它的作者究竟是谁,众说纷纭。明代袁了九谓:“此篇(《徕民》)似《管子》,又似魏公子无忌之文。”(52)方勇:《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第5册),第288页。同时代的王维祯也怀疑此篇“酷似无忌谏魏王书”(53)方勇:《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第5册),第291页。,但他们只是感觉和猜测。清代沈钦韩谓:“第十五《徕民篇》云:‘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胜,攻城必拔。’又云:‘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又第二十《弱民篇》云:‘秦师至鄢郢……’皆秦昭王时事,非商君本书也。”(54)蒋伯潜:《诸子通考》,第493页。清汪中:“《商子·来民》篇称其君曰王。”“案:孝公子惠文王即位十四年始更元年,其称王实在此时。”(55)汪中:《旧学蓄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681页。刘汝霖大致同意沈钦韩的说法,并进一步根据篇中所载“周军之胜”而将其推断为前255—前251年间所作(56)刘汝霖:《周秦诸子考》,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版,第286-287页。。陈启天认为“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虽然都是秦昭王时期的事,但其“通篇针对时事讲话,不像伪作”,故认为此篇“疑是秦孝文王或庄襄王时的大臣或客卿,如吕不韦等所作,而为后人误编入《商君书》中,未必是后人假托商君所作”(57)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30-131页。。徐勇则认为《徕民》篇“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中的“四世”,应该指的是魏襄王至景湣王这四代国君,故将此篇推定为尉缭所作,并列了十条理由(58)徐勇:《〈商君书·徕民〉篇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蠡测》,《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50-55页。。仝卫敏注意到了刘汝霖、陈启天和徐勇的说法,但并不同意徐勇有关“四世”的解读,认为仍指秦孝公开始到秦昭王,其最后根据《徕民》篇的思想特点、秦昭王时期的形势等将其判断为商鞅后学所作(59)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73-178页。。
那么,此篇的作者到底是谁呢?首先,从文中“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这两句话的语气来看,此篇陈述的对象应该不是魏王。另外,魏无忌是魏安釐王时期人,虽然在时间上有可能作此文,但他是魏国的公子,曾两次击败秦军,是东方六国对抗秦国的主要人物,故其不可能向秦王献计来削弱三晋。故明人袁了九、王维祯的说法不太能经得起推敲。
其次,对于“四世”的具体所指问题,笔者认为这“四世”应该还是指秦国方面。无独有偶,《荀子·强国》篇记载荀子见秦昭王时谓:“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60)王先谦撰,王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页。故在秦昭王时期,秦国的“四世”之胜可能是当时社会的共识。那么既然这里的“四世”是指秦国方面,为什么后文中又出现了一个“三世”呢?对于这里的“三世”,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它应该也是指秦国方面。那么文中的“四世”和“三世”是否存在矛盾呢?笔者认为可能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详细体会“三世”所出现的语境就会发现,此处“三世”强调的是“天下不服”,而作者可能要上书的正是“四世”中的第四世秦昭王。前面三世,天下不服,是历史事实,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故可以下定论,但现在正处于秦昭王第四世,其能不能使天下服,还不知道。正因为如此,作者上书献计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服。综合考虑上面前人所指出的史实和此处所暗示的时间线索,此篇应该是秦昭王时期的作品。
再次,从文章的论述内容看,它也符合秦昭王时期的社会特点。当时的三晋地区应该还有一定的实力,所以要使用计谋来作长远打算,如果双方的实力悬殊,强大一方直接将弱方吞并即可,何必弯弯曲曲玩计谋?综合考虑,还是最可能出现在秦昭王时期,至迟不会到秦始皇时期。因为秦始皇时期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不需要这种来回迂曲之道。至于它是何人所作,从内容看,作者无非也是主张农战,与商鞅农战思想不同的是,商鞅的农战思想只注重对国内人力和农业资源的开发,此文的作者却注重对他国资源的利用,但其归根结底是为了农战,两者在主要思想上有一致性。从这点看,说此文的作者是商鞅的后学也不为过。
3.《外内》。关于此篇的作者问题,向来争议较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韩非子·南面》曾谓:“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61)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0页。罗根泽谓:“商君之《内外》者,即《商君书·外内》篇也。”韩非所谓“铁殳重盾而豫戒”是说使民持殳操盾准备战争(62)罗根泽:《诸子考索》,第506页。。容肇祖亦同意罗根泽的说法,并谓:“这《外内》篇以为外事轻法不可以使,内事轻治不可以使,与《南面》所说‘严必行之’相合。”故断定《外内》篇为最早《商君书》所有(63)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仝卫敏同意这种说法(64)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200页。。但是,陈奇猷等人却认为,此处的“内外”应作“出入”解,不能作为《商君书》的篇名。因为他看到《史记·商君列传》载赵良对商君曰:“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阘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这种情况指的就是“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65)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郑良树对此也进行了辨别,并认为是《徕民》之后的作品(66)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15-120页。。张林祥同意陈启天的说法(67)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第104-105页。,张觉虽然仍然认为《外内》篇为商鞅所作,但其不同意罗根泽、容肇祖等人的说法,而是同意陈奇猷的说法(68)张觉:《商君书校疏》,第252-253页。。
那么,《韩非子·南面》中的“内外”应作何解呢?笔者认为这首先需要从《韩非子》本身的情况出发,其次才是求证于《韩非子》之外,而且不能用外在的联想推理来否定其内在的逻辑。具体到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内容值得注意:一是这句话的上下文关系。主张“内外”属篇名的人大多只注意到了前文中出现了“严必行之”这句话,认为这和《商君书·外内》中的不可“轻法”“轻治”的思想相似。事实上,这句话的后面一句同样重要,其谓“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69)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120页。。所谓“故”者,其表承接之意非常明显,其后面也非常明确地说文公之官卒、桓公之武车,是为了“戒民”,而不是为了准备战争,故罗根泽的战争说或有待商榷。而这里作“戒民”也是非常符合文意的,因为前文说“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必立其治”。其意谓,只要能治国安邦,即使违背民心也一定要实行。故这里的“铁殳”“重盾”“官卒”“武车”是为了防止内部民怨,其意甚明。
二,“说在……之……”的句型在《韩非子》中多见,计有15条,其大多表示某人某事:

《韩非子》中所见“说在……之……”句型表
从这15条文献材料可知,虽然这种句型都是说明来源,但其更多是指某人某事或说过某话,而非文章之出处。而且此处的“内外”与篇名的“外内”,语序也不同。故《南面》中的“内外”,据此恐也不能指篇名。
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商鞅所作呢?认为“内外”指篇名的一派基本都认为这篇文章应该是商鞅所作,其主要理由除了《韩非子·南面》中提到了这个篇名外,还有就是这篇文章的思想也符合商鞅的特色。而否定“内外”是篇名一派,除张觉外,基本都认为它不是商鞅所作。陈启天认为文中提到“边利”,应该是汉代晁错的作品。但后来许多学者也指出“边利”的思想不是汉代才有,而是早已有之。除陈启天外,他们并不否定这篇文章的思想符合商鞅的思想特色,但认为这篇文章的行文思路逻辑严谨,文章清畅,不似商鞅所作。
而在事实上,其思想也未必符合商鞅的思想特点。拿劝农的思想来说,似乎只把市利与劝农联系起来,但在《墾令》篇,粮食是禁止买卖的,正所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是也,不是让利那么简单,而且《墾令》篇与劝农相关的有20多个方面,这里却只有一个方面。内容也不仅仅涉及到劝农,也涉及到乐战的问题,但其文中却没有提及。所以,本质上它把商鞅的思想简单化了,也淡化了。它之所以那么重视市场对农业的调节,则可能与商鞅之后,秦国的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日益发展有关。郑良树认为其将外内的利益划分得十分清楚,和《徕民》篇的思维相似又较之深刻,故将其判为在《徕民》篇之后。笔者认为,其深刻未必有过《徕民》篇,但注重调节内外资源的思维相似,故成书也应在同一时段。
4.《慎法》。对于此篇的作者情况,陈启天谓这是一篇奏疏,或即是商鞅上孝公的书。其首节和次节重在破胜党人,节去言谈,任法而治;末节重在说明耕战为国力之本,须“劫以刑,驱以赏”,使务耕战。末节与前两节不相属,或是两篇合成一篇。本篇的议论与商鞅思想相合(70)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34页。。容肇祖则认为此篇与《农战》《君臣》应该出自同一人(71)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郑良树则根据篇中对“义”的仇视和它不提“抟力”“杀力”的观念,认为此篇应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是秦始皇元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作品(72)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26-127、154页。。张林祥则认为这篇的成书线索不明显,但根据其行文特点,应该比较晚出(73)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第99页。。仝卫敏则反对陈启天的末节与前两节不相属说,也反对郑良树的说法,其根据文中出现的反对“尚贤”的观念,认为这与《开塞》篇类似,又根据“忠臣孝子”的独特观点,认为其应该成书在墨子之后、孟韩之前,故应该是商鞅所作(74)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213-216页。。
笔者认为,判断此篇的成书,不能单单求之于思想的论证。郑良树的说法,仝卫敏等人已有所批驳,但是仝卫敏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就“尚贤”这种观念而言,不单是《开塞》篇反对,《商君书》其他篇章也反对。“忠臣”这个词最早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很难考究,因为先秦文献大部分已经缺佚,其参考的语料相对于整个先秦的语言生态而言,实只鳞片爪,故此篇的作者问题还有待探索。笔者注意到了此篇中有“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韩非子·定法》谓:
公孙鞅之治秦也……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75)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398页。
《韩非子·定法》中的张仪、甘茂、穰侯、应侯等人,可能就是“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的真实写照,故《慎法》篇应该不似仝卫敏所说的是商鞅所作。那么它又应该出于何人何时之手呢?我们前文已经论证《君臣》篇可能是商鞅所作,在《君臣》篇中,作者希望通过法制来明君臣之义,鼓励农战,以达到兵强主尊的效果。而《慎法》篇同样提倡法和农战,只不过其更多针对“党人”而非一般的“君臣之义”。故从思想上看,此篇的作者应该是商鞅后学。笔者注意到,此文中出现了“耕战”一词,而在整部《商君书》中也只有《说民》和《慎法》两篇出现了此词,其他篇章都作“农战”,故从文章的用语习惯看,两篇可能作于同一时期。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证,《说民》篇应该是昭王时期的作品,《慎法》篇大概也在这时期。
(三)秦昭王后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作品
前文我们讨论了《商君书》里商鞅死后至秦昭王时期的作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秦昭王后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作品。其中,《定分》篇则当如郑良树所言,是《商君书》中成书最晚的作品(76)郑良树:《商鞅评传》,第248页。。其他篇章的情况如下:
1.《算地》。陈启天认为,论其主张,如“为国之数,务在墾草;用兵之道,务在一赏”等,极像商鞅的说法。但再三谈到“数者臣主之术”“法术之患”“失术”“立术”等道理,又像申不害的说法。故其断定此篇是申商后战国“法家者流”衍述申商的说法(77)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26页。。容肇祖认为此篇与《徕民》应该同出一人,大约成书在秦昭王晚年,其主要依据在《算地》篇首段“先王之正律”的文字与《徕民》篇“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一段相似(78)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这种逻辑缺陷是明显的,因为单凭相似不足判为同出,其也可能有相互借鉴的关系,或这段话是当时的热点,谁都可以引用。郑良树则认为此篇大概和《农战》同时或稍后,不会太晚,是商鞅的后学所作。因为他发现此篇和《农战》相似,同时篇中强调了“术”的思想,保存了“君子”“小人”的原始意义(79)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44-145页。。笔者认为,就像上面指出容肇祖的逻辑缺点一样,郑良树这里也是如此,相似并不一定就能证它们同时。张林祥大致同意郑良树的说法(80)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第94-95页。。仝卫敏对以上诸家都有所批驳,并认为即使商鞅也讲“势”“术”,此篇还是视为商鞅的思想比较切合,故应该是商鞅所作(81)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24-131页。。
笔者认为,此篇应该成书在韩非前后。因为,前文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韩非子》谓“无术以知奸”是商鞅之法较为明显的缺陷。今观《算地》一文,其有“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云云,已关注到了用术来知奸的方面,而且它对于申不害政令多出的缺点也有所纠正,主张“操权一正以立术”,故其观点更像是综合了申、商、韩三家,但以商学为主的作品,故其成书或在韩非前后。
2.《错法》。有关此篇的作者,目前学界有多种说法:一是容肇祖的说法。他认为此篇的作者和成书与《弱民》篇应该相同(82)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其中的逻辑缺陷,前文已有辩驳,此不再重复。二是陈启天的说法。他认为此篇应该是战国末期的“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编”。其主要依据是本篇文字行文明畅,又曾提及乌获,故决非商鞅所作(83)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28页。。乌获是秦武王时力士,去商鞅死时有二十九年,商鞅实不及见乌获。三是郑良树的说法。郑良树认为此篇应作于秦始皇元年到天下统一期间。其主要理由是此篇出现了“德明教行”“教流成”的字眼,主张教化百姓,与《墾令》的反智思想不同,故应该在“百姓可智可愚”的《壹言》篇之后(84)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69-74、151-153页。。四是仝卫敏的说法。仝卫敏认为此篇应该是秦武王时期的商鞅后学所作,其主要依据是文中出现了乌获此人,此篇的思想也和商鞅的思想相似(85)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43-146页。。
笔者认为,此篇可能是战国末年秦国的法家者流所作,未必是商鞅的后学。理由如下:一,此篇中出现了秦武王时期的人物乌获,由此可知其不可能是商鞅所作,只能是秦武王时期或以后的人所作。二,商鞅的思想,虽然也重视法、爵,但一般会归结到农战上,赏与刑也会并重,甚至刑重过赏。但此篇重视的是法和爵,虽然仍然强调强兵,但重农和刑罚的思想基本没有了。所以它可能是法家者流的作品,但未必会是商鞅后学的作品。三,“德明教行”中的“德”和“教”不是指儒家类的仁义,但其思维和秦始皇石刻中的思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会稽石刻中的“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等(86)司马迁:《史记》,第333页。,这些都应该是“德明教行”的体现。故此文极有可能是成于战国末年的法家者流之手。
3.《壹言》。关于此篇作者,陈启天认为“大约是战国末期‘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编’,也足以发挥商鞅的思想”。同时又认为它“论旨多与他篇相同,而行文又极明畅,是否出于鞅手,未能断定”(87)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27页。。可见,虽认为它不是商鞅所作,但事实上拿不出什么实在的证据,只能根据文章风格作些猜测。容肇祖则认为此篇与《农战》篇相似,故应该是商鞅所作(88)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郑良树则根据“壹”字意义的流变,将其判为成书于战争开始频繁或正在频繁的时期(89)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61-65、73-74、150页。。仝卫敏对郑良树的说法有所批驳,并认为其成书应该较早,是亲炙商鞅的门客或弟子所为(90)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40-143页。。
笔者认为,《壹言》篇确可能如陈启天所说的,是战国末年的作品。首先,文中一开始便将“制度”“治法”“国务”“事本”这四种事务分别开来,但通过观察《更法》篇可知,商鞅与孝公对话之时,礼与法其实就包括了这四个方面内容,甚至礼与法在那时还常常混合应用,其行文将“变法”与“更礼”对着讲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故假如《壹言》篇将这四种事务区分开来,就有后出的嫌疑。其次,《壹言》谓:“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91)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63页。不仅强调要宜于时,而且强调要“因世”和“度俗”。我们知道,在《更法》篇商鞅是强调了不法古,不修今,但并没有强调“因世”“度俗”。《更法》篇甘龙在反对商鞅变法时说:“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公孙鞅反驳道:“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9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3-4页。第一句话便充满了对“世俗”的蔑视,而且商鞅变法本身就革除了许多俗习。可见,“因世”“度俗”无疑与甘龙的主张更为接近。笔者据此推断此篇应该是后学所作。至于为什么说它可能是战国末年的作品,一,本文开篇即谓“凡将立国”云云,证明其可能针对的是即将新生的政权;二,文章强调“壹”和“制度”,可能是为大统一局面即将到来所作的理论探索。故综合以上种种,笔者认为此篇应该成书于秦统一的前夕。
4.《靳令》。由于此篇在很大篇幅上与《韩非·饬令》重复,故历来学界有关此篇的争议比较大。首先,朱师辙、罗根泽、陈奇猷、高亨、周勋初、郑良树等人认为是《韩非子》抄录了商学派的文章(93)郑良树:《商鞅评传》,第238页。。郑良树从文句、用字、文章的连贯程度及其与《商君书》其他各篇的关系等方面辨之甚详。其次,陈启天等人认为是《靳令》抄录了《饬令》。此篇乃“汉人杂凑充数之文,决非鞅作,也非纯粹的‘法家者流’推衍商鞅议论而成。其一部分全袭《韩非子·饬令》篇;又一部分用本书他篇语穿插其间,致不能成章;更有一部分为杂凑者所妄加,致与商鞅思想根本冲突。简书于此篇袭取《韩非子》,考证甚详”。“我想本篇既剿袭又杂乱的原故,大概由于汉时征书,应征者杂取充数,以求多得赏金;既收藏于秘阁后,校书者未加细审,又以一并编入耳。”(94)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29页。据笔者分析,《靳令》一文其实整体上语气还算连贯,说其为杂凑,或太过。最后,值得关注的还有容肇祖的说法。容肇祖认为《靳令》“本是一种法家者流的余论,其较完全者,掇入于《商君书》;其较删节者,掇入于《韩非子》,而实在则不知为何人所作,大约既非商君所为,又非韩非所著的呵”(95)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事实上,尽管先秦许多重复的篇章难以确定孰先孰后,它们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共同话语,但要是具体到《靳令》与《饬令》等篇,笔者还是认为郑良树等人的分析比较合理。那么《靳令》又大概成书于何时呢?
笔者认为,虽然可能是《饬令》抄录了《靳令》,但两者的成书时间应该相差不大。《靳令》谓:“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96)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80页。一些学者注意到,“非兵”“羞战”等观念是墨家学派的思想主张,此处“六虱”,说明学派间的思想交锋味道很浓。而《去强》篇谓:“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97)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28页。其所针对的,大多是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和习惯。我们前文已经论证,《去强》篇大部分应该是商鞅作品的摘录,这部分的成书也应该较早,而商鞅变法之时,其主要针对的也应该是秦国当时某些陈旧落后的观念,而非学派观点。故《去强》篇“六虱”的观念应该较为接近商鞅的观念,而《靳令》篇的“六虱”,应该是战国末年各学派思想发展成熟后的观念。其次,《靳令》篇最后一段非常强调“赏罚以壹”与“仁义”的结合,并涉及到了“心”与“力”、“德”与“力”的关系。据笔者观察,此种思路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石刻文思路较为接近。琅琊石刻文谓: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功,劝劳本事。……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匡饬异俗……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莫不受德,各安其宇。(98)司马迁:《史记》,第314-315页。
刻文中将宣扬秦始皇的仁义道德与劝农、抟心揖志、匡饬异俗、诛乱除害等相结合,这与《靳令》篇最后一段有相似之处,《靳令》篇可能为此先声,故《靳令》篇应成书在战国末年。
5.《修权》。有关此篇的作者问题,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将其视为商鞅所作。陈启天认为此篇所说观点和商鞅的思想非常相似(99)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29-130页。,因此可视为商鞅所作,容肇祖、郑良树、仝卫敏、张觉等人都对此认同。容肇祖认为此篇中的“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是法治的极端主张,符合商鞅的思想特色。此外,他还将此篇中肯定禅让的思想和《战国策》中记载孝公临死前欲让位于商鞅一事联系起来,证明其或出商鞅之手(100)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郑良树多承其意,并且把《修权》里的“权”字都解读为“权衡”的意思,认为其用法和《墾令》《农战》《算地》中的用法不同(101)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05-107页。。仝卫敏、张觉两人虽然不同意郑良树对“权”字的解读,但其仍然认为这篇当如容肇祖所说,是商鞅所作(102)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63-168页。张觉:《商君书校疏》,第164页。。
二是认为此篇应该不是商鞅所作。张林祥即持此种说法,其主要依据是《修权》篇主题过于集中,还肯定了先王,肯定了“论贤举能而传”这种公天下的观念等,这些都不是商鞅的思想特色,因此,他推定此篇应该是战国末年比较同情儒、墨思想的法家所写(103)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第91-94页。。笔者认为商鞅作为改革家,其所主张的应该一切都以是否合时、便事、富国强兵和维护王权为目的,而不会考虑先王的做法,也不会致力于破坏王权的家族传承,故张祥林于此处应该辨析得较为合理。但其进而否定禅让思潮在战国的存在则可能不尽正确,只是这不在《商君书》的考证范围,故笔者对此不作细辨。
6.《画策》。对于此篇的作者,历来存在多种说法:一,笼统地指出非商鞅所作。陈启天认为,这是一篇论著,它不是商鞅所作,而是“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其主要依据是文中有“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的话,似非极端任法的商鞅所说。又有“所谓义者,为人臣忠……此乃有法之常也”的话,是以法释义,与《开塞》篇刑义完全相反的论调不同,且本篇文义在全书中最为流畅(104)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31页。。二,当在秦昭王晚年时完成。容肇祖认为《画策》和《算地》《去强》《靳令》《说民》《徕民》《弱民》《墾令》篇都有关系,故应当是出于同一作者,同时成书于秦昭王晚年。而细考其所谓“关系”者,无非是两者在某些内容片段上有相似性(105)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三,成于秦始皇元年到天下一统期间。郑良树认为此篇内容与《赏刑》篇相似:“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这段“无为而治”的思想应受《韩非子》影响;本篇的上古帝系与《更法》篇有差异;末段连用几个“必”字的语气也和其他篇不同,故非商鞅所作。又篇中不仅敌视“仁”也敌视“义”,故此篇应该是秦始皇元年至大统一时的作品(106)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13-115、152页。。仝卫敏对以上观点作了逐一辨析,认为此篇的“贤”也可指法律和农战方面的贤人;容肇祖的论证是用局部来代替整体;本篇只是不贵义,并非仇义等,大致合理。其又根据此篇“在具体内容上有很多观点与全书中成书较早的篇章极为相似”,故将此篇断为下限在秦惠文王时期,“作者是一位非常熟悉商鞅学说的人物”(107)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185-190页。。
笔者认为,此篇还是有可能如郑良树所说,是秦始皇元年至大一统时期的作品。首先,从思想内容上看,这篇应该是商鞅后学的作品,故其对商鞅学说有所继承是非常自然的事,并不能因此断定其成书时代。故仝卫敏的说法未必准确。其次,郑良树的部分怀疑是正确的,如指出它的上古帝系与《更法》篇不同,但其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也显而易见,有些仝卫敏已有所辨析。此外,所谓的“无为而治”或“垂拱而治”的思想,其实《论语》《老子》等儒道经典中都存在,其不必然受《韩非子》的影响,也可能是《韩非子》受其影响,或当时的共同思潮如此。再次,从思想上看,此篇最推崇的是明主和极端的法治。其最后一段实际上是把“法”和“法治”极端理想化了,认为这是“必然之理”,并且一连用了几个“必”。这种极端的法治思想其实和《修权》篇所提倡的“公天下”的极端法治有相似性。最后,其末段以“圣人”相期、“以法释义”的思维方式和后来秦始皇石刻中的思维十分相似,如“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108)司马迁:《史记》,第319页。。此篇可能是石刻思维的先声,故其成书还是非常可能在秦始皇元年至天下一统前的。
7.《禁使》。有关此篇的作者及成书时间,学界历来也是众说纷纭。陈启天谓:
本篇是一种奏疏……文中所谓“势数”“持其势”“托其势”和“贵势”等语,好像与慎子所谓“势”相近。然仔细一考,则“别其势,使其难匿”以便“稽验”,又与申子所谓“术”相近。商鞅曾为秦相,对于察吏的方法,当有所考究,此篇究为何人所作,虽难断定,而就其主旨说,也可视为商鞅所作,或“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109)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33-134页。
由上述材料可知,陈启天对此篇应是何人所作的问题没有明确的判断。郑良树则认为本篇中提到的丞、监的官职可能要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设置,故此篇也应作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而其篇中的比喻甚多,有的甚至和《荀子·劝学》篇相似,故可能作于荀卿之后(110)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23-126页。。仝卫敏承认此篇中的“势”论与慎到的“势”论是一致的,也承认此篇中的“术”论与申不害的“术”论是一致的,但她认为商鞅距申、慎不远,或许对“势”“术”早有认识。此外,她还论证了“御史”这类的监察官在战国早已有之,不必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此篇中论功察罪应谨慎的观点也与《算地》篇相似等,故其将此篇断为商鞅所作(111)仝卫敏:《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第208-211页。。
笔者认为,首先,商鞅的思想一般以农战和法作为主体,即使对察吏的方法有所感悟,也应该首先重“法”,而不会通篇不提“法”,只提“势”“术”,如《君臣》篇。前文中我们也曾提到过《韩非子·定法》篇谓商鞅之法的最大缺点是“无术以知奸”,故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商鞅已经深悟“势”“术”的思想,否则仝卫敏此处的猜测很难服人。其次,所谓的比喻甚多虽可作为怀疑此篇非商鞅所作的依据,但不能作为其出于荀卿之后的依据。因为用寓言和形象思维来说理是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一个普遍特点,像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儒道法的思想家们都有这个传统,因此不能用其来确定作文的时间,加之战国时期本有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其在话题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不能说明谁先谁后,故郑良树的出于荀卿之后的说法是非常勉强的。再次,就像陈启天、仝卫敏两人所注意到的,本篇应该至少包含了申不害、慎到和商鞅三人的思想,故非常有可能是成于法、势、术三家逐渐开始融合之时,而韩非子向来被学界视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故其成书应该在韩非前后。
三、《商君书》的成书时间和编者
前文中我们大致梳理了《商君书》各篇的成书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先秦古书大多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往往是先有篇,后有书。从前文对《商君书》中各篇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的考证情况来看,《商君书》也应该如此。那么,《商君书》大概在什么时候成书呢?它又是由谁辑录成书的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刘汝霖认为应该成书于公元前260年至前251年之间(112)刘汝霖:《周秦诸子考》,第286-289页。。其主要依据是《徕民》篇明确提到了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这是目前从《商君书》中发现的最为直接和有力的时间线索,假设其他晚出的篇章判断错误,此篇也不可能出错,故它的成书最早也不能早于此,这也是成书的上限。容肇祖认为《商君书》“除首末二篇为后来加入外,大体约成于秦昭王晚年之时”(113)容肇祖:《商君书考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一期,第61-118页。。罗根泽认为应该成书于公元前260年至公元前233年(114)罗根泽:《诸子考索》,第500-510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死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子·五蠹》中谓:“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罗根泽将这里的“管、商之法”理解为管、商之书,故将其断定为成书的下限。另外,刘汝霖、容肇祖、郑良树还根据《定分》篇言及丞相、御史、时等官职和名词,将其推断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作品(115)刘汝霖说见《周秦诸子考》,第286-287页。容肇祖说见《商君书考证》,第61-118页。郑良树说见《商鞅评传》,第248页。,黄云眉、陈启天等还认为《商君书》中混入了汉人的成分(116)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1页。陈启天:《商鞅评传》,第171-188页。。法国汉学家H. Maspero认为《商君书》可能成书于三世纪,但后来《商君书》的原本缺佚了,现在的《商君书》可能是六朝人编造(117)H.Maspero,La Chine antique(1927),pp.520-521.。荷兰汉学家J.J.-L.Duyvendak对此表示认同(118)J.J.-L.Duyvendak:The Book of Lord Shang(1928),pp.86-87.。冯树勋认为:“《商君书》在汉代初年有不少单篇的行本在学界中流行,但不一定在西汉初年已形成如今本之巨型结集;因为西汉学者群对‘农战’和‘耕战’两词的特定用法,与东汉初年的班固作对比,可以推测《商君书》的编成,当在东汉初年。”(119)冯树勋:《从商君书辑定年代看古籍整理的几项要素》,《书目季刊》2004年第38卷第3期,第69-90页。故其下限实在众说纷纭,现在学界观点比较一致的是,至迟到刘向校书时,《商君书》应该已经有了定本。
而对于《商君书》应该是何人所编的问题,学界也争议颇多。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它是商鞅所著,如《汉志》,但这种观点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1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848页。。清人钱熙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商子》二十四篇,词多重复,疑后人割裂以充篇数”(121)方勇:《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第3册),第127页。。这种观点未必正确,因为《商君书》中虽然有些句子重出,但绝大部分文风比较圆融,所以“割裂以充篇数”的说法恐不能成立。俄国汉学家A.Ivanov认为《商君书》完好无损,没有重要的重复和溢入(122)A.Ivanov:Materialy po kitajskoj,filosofii,vvedenie škola fa(1912),p.XV.。德国汉学家Dr.A.Forke则认为《商君书》并非商鞅所作,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是他的言论,带有“臣”字的篇章可能是他的条上之文,另外一些则是后人的溢入。它可能是商鞅的忠实信徒们在他死后搜集而成的(123)Dr.A.Forke:Geschichte der alt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1927),p.454.。陈启天则认为此书乃刘向所编。蒋伯潜则谓:“《商君书》,亦犹《管子》《晏子》,为后人所辑集,非鞅自著。”(124)蒋伯潜:《诸子通考》,第494页。高亨、郑良树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125)高亨:《商君书注译》,第20-25页。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39-156页。。郭沫若怀疑是韩非的门人伪作此书(126)郭沫若:《十批判书》,第339页。。张舜徽认为《商君书》“其初本有遗文传世,至六国时,又有人拾掇余论以补充之”(127)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第160页。。张觉则认为刘向并未留下校《商君书》的叙录,故《商君书》可能在刘向之前即保存完好,无需刘向校订。但是刘向的叙录并未完整流传下来,我们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商君书》的叙录,故此点不足为据。接着,张觉又注意到了古代弟子编自己老师的书时,往往改其师为“子”,而现传本《更法》《定分》篇都将其称为“公孙鞅”,故此书不可能是商鞅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们所编。他认为,此书当为秦国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所编,所以才会把档案性质的《更法》排在第一篇(128)张觉:《〈商君书〉杂考纠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5期,第12-14页。。张林祥对张觉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档案应该是实录,《更法》篇不似实录,故不能认为是御史所编,而且商鞅的“弟子”,不能和儒家的弟子相提并论,故《商君书》依然可能是商鞅的后学所编。其在战国时期即有本子在流行,到刘向时方有定本(129)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命名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第1-3页。。
由上可知,目前学界对这两个问题所能达成的共识是,《商君书》不是商鞅自著,是后人所编。但对于是何人所编的问题,则有韩非门人、法家者流、商鞅后学、秦国御史这四种说法;而对于是何时所编的问题,则有战国、秦朝、东汉和六朝这四种说法。那么,到底是何人何时所编的呢?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时官方主导下所编。
第一,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论述商鞅变法时谓“其事在商君语中”(130)司马迁:《史记》,第275页。,这里的“商君”二字固然有可能指商鞅本人而非指书,但通观全文,指人的用法与《秦本纪》的行文风格不符。《秦本纪》在论述商鞅变法时“商君”二字只使用了两次,除在这里用了一次外,后面介绍他的封号时又用了一次,说他“号商君”,其余提到商鞅时一律作“卫鞅”或“鞅”。结合后来《汉志》谓“《商君》二十九篇”,可知西汉时《商君书》被称为“商君”,《本纪》中的“商君”应是指书无疑。故可以推定的是,司马迁之前,《商君》一书已经存在,东汉、六朝的说法不成立。又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他曾读《开塞》《耕战》书,考之今本《商君书》,即有《农战》《开塞》两篇,但“耕战”与“农战”虽然词意相近,用字却有别。故司马迁所见,未必就是后来的《商君书》,《商君书》此时可能尚未有固定的版本。而对《商君书》完整著录最早见于《汉志》,《汉志》是在刘向等人所编《别录》的基础上删补而来的,刘向等人曾对当时的书籍进行过大规模的整理,现传书籍的许多篇章目录都是由他们删订增补而来的,故《商君书》可能直到刘向时才有较为固定的版本。但拥有定本也不意味着其文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不发生变化,而是依然有增删缺佚,只是其变化的程度可能要小得多而已(131)对于其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的变化,详情参考黄效:《〈商君书〉源流考》,《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5-26页。。
第二,由前文对全书各篇的考证可知,《商君书》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去强》篇和《说民》《弱民》篇存在的经传关系清楚表明此书形成过程的历时性。那么,为什么只有《去强》篇有传,而其他篇章没有呢?难道是因为《去强》篇的思想特别深奥和特别精辟吗?可能并非如此,很大可能是由于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一直在单篇流传,其所见者独有此篇,故对其作传。而且郑良树已经指出,目前《去强》篇不见于《说民》《弱民》的部分,很可能是在秦始皇时期溢入的,故其文本可能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当然,这只是就单篇的情况而言。除此之外,《商君书》中的许多篇章被认为成书较晚,像《算地》《徕民》《定分》等篇,应该成书比《说民》《弱民》篇更晚。这就说明在时间上,《商君书》也具有多层次性。最原始的应该是商鞅的作品,其次是《去强》中有传的部分等,再到《说民》《弱民》等,再到《算地》《徕民》等,最后到《定分》。到《定分》篇,应该已经到了秦始皇时期。这个过程中,有些作品或许会受到法家者流的关注和收集,但谁有这个能力将其编定为一个持各种观点的商鞅后学们都愿意接受的版本呢?战国时期,各家学说彼此攻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即使学派的内部,也是分歧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像《论语》那样,只收与开宗立派者有关的言论,后学者如子思、孟子、荀子等自立门户,各自著述,否则很难让人们信服和将其奉为教材。故其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第三,至于是何人编成的问题,笔者认为高华平先生在论述《老子》成书时的一段话颇具启发性,其谓:“到《韩非子》引《老子》时代为止……《老子》文本似一直处于一个不断被添加的过程之中。这也说明,在文献的‘抄写时代’,以任何个人之力都是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老子》‘定本’的。要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老子》‘定本’,必须借助国家意志,以法定的形式来推行。”(132)高华平:《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中州学刊》2019年第10期,第107-118页。纵观《商君书》的成书情况,也应该和《老子》类似。而且张觉已经指出,《商君书》中并没有将商鞅称为“商子”,故《商君书》的编定,不似是商鞅后学所为。而商鞅后学之外其他的法家学派,似乎也没有这个必须去编一本和自己师承无关的《商君书》。故《商君书》的编定很可能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官方所为。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颁布法令来推动全国实现“书同文,车同轨”,而且当时的秦朝,十分推崇法家思想,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别白黑而定一尊”,对其他学说大为贬斥。有学者认为,秦朝建立后曾一度尝试构建新的历史叙事模式,这在秦始皇石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133)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2页。。以上这些都需要有引以为据的思想资源,而商鞅作为法家学说的重要开创者和实践者,使秦国变得日益强大,最后统一了全国。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功臣,他的学说和思想很容易进入秦朝当局的视野。而且,《商君》而非《商子》,用具有行政性的官爵而非学术性的“子”作为书名,或也说明它应该是官修之书。故综上所述,秦朝的官方最有可能编定了《商君》一书。
结语
可见,《商君书》的成书情况十分复杂,争议较多,它应该不是一时一人之作,而是历时性的产物。具体而言,《商君书》中的《墾令》《境内》《农战》《战法》《立本》《兵守》《开塞》《君臣》《立法》这九篇都应该是商鞅所作,《更法》《去强》《说民》《弱民》《赏刑》《徕民》《慎法》《外内》这八篇大约成书在商鞅死后到秦昭王之间,为商鞅后学或当时崇尚商鞅学说的法家者流所作。其中《去强》篇可能经过长期的累积而成,《说民》《弱民》篇与《去强》篇有清晰的经传关系。《算地》《错法》《壹言》《靳令》《修权》《画策》《禁使》《定分》这八篇应该是战国末期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的作品,其中《定分》篇可能是《商君书》中最晚的作品。究竟何人将它结集成书,可以看出,它不会是商鞅自著,而最有可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时,由官方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