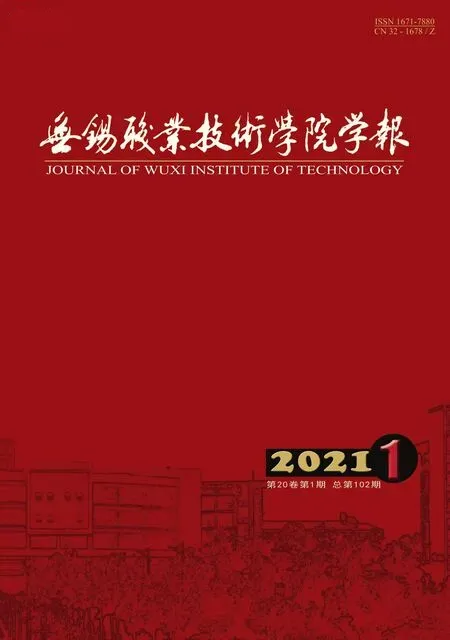认知生态批评下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路径研究
——以英德工业及教堂建筑遗产为例
操 磊 张虞昕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与旅游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1)
物质文化遗产,也称之为“有形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经过历史锤炼,沉淀而生的宝贵资产和有形财富。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公共实物,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得益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对其保护和传承也得到了学术界及社会各层人士的高度认同和普遍重视。由于欧洲物质文明发展进程较快,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也萌生较早。伴随着欧美国家文物古迹保护运动的兴起,欧洲社会各界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与保护也存在众多理论及观点。例如:勒·杜克的风格性修复理论、约翰·罗斯金的反修复理论、威廉·莫里斯的保守性修复理论、卡米罗·博伊托的文献性修复理论、卢卡·贝尔特拉米的历史性修复理论以及古斯塔沃·乔万诺尼的科学性修复理论。各种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为欧洲以及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存续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价值。
1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中,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多关注了遗产本身的修复或重塑,却忽略了遗产周围环境以及人作为认知及保护主体的情绪、态度、愿景等诉求,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保护及有效推广。
认知生态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顾名思义,该学科旨在将生物学、环保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有机整合,形成关于人、自然与社会的集大成式研究,以实现三者的稳定、和谐、持续发展。认知生态学虽然起源于心理学,但又区别于心理学,其主要贡献是将人类的认知过程定义为一种生物行为,而非简单的逻辑行为和机械表现。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对人类生态属性的自然回归,更是对自然生态的人性解放。基于认知生态视角,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迎来新的契机。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会或自然的一部分,需要与认知的主体——人,进行良性的生态互动。
2 工业建筑遗产的活态保护路径
19世纪60年代左右,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大地悄然问世。与之相伴的是大批优秀工业建筑的诞生,其中以英国和德国为甚。英国作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也最先遭遇工业城市衰退的问题,尤其在二战期间,许多富有价值的工业厂区遭到战争破坏,沦为废墟。此后,英国政府也将保护工业遗产提上日程,并设立“城乡规划署”来专门负责工业城市的修复和改造工作[1]。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德国,尽管前期德国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由于二战后内乏外困,经济开始衰退,逆工业化趋势日益突出。工人失业,工厂倒闭或外迁,留下大量的空置工业建筑及设施,成为见证德国工业社会发展的优秀文化遗产。工业遗产保护国际委员会(TICCIH)对工业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ists of the remains of industrial culture which are of historical, technological, social, architectural or scientific value. These remains consist of buildings and machinery, workshops, mills and factories, mines and sites for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warehouses and stores, places where energy is generated, transmitted and used, transport and all its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places used for soc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industry such as housing, religious worship or education.
不难发现,工业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科技、社会以及建筑等多重人文价值,是人类记忆和习俗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对其的保护也应当在关注人类认知需求的基础之上实现人与物的生态整合与共生。
2.1 风格共存的活态保护方式
工业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孤岛保护效应”,将工业遗产与周围人文社区分裂和隔离,形成二元对立的尴尬局面。工业遗产沦为单一的展示场所,缺乏整体性统一。认知生态学研究者杜卡斯认为:人类所做的任何决策都不是既定的、单一的,而是基于所在的生态语境衍生而来的[2]272。Edwin Hutchins也强调“Cognitive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cognitive phenomena in context. In particular, it points to the web of mutual dependence among the elements of a cognitive ecosystem.”[3]因此,在对工业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也要深入工业遗产所处的地缘人文语境,不能“一刀切,随大流”。要充分考虑工业遗产的生态特殊性以及认知个体性,实现工业遗产与当地物质人文语境的风格统一,从而彰显城市的文化底蕴与人文风格。以德国波兰工业核心区之一的克罗伊茨贝格区为例,该区是著名的工商业及住宅混住区域,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为了全面保护古工业历史建筑,拆除了大量的现代中小企业工厂,试图将工业建筑与居民住宅分割。这遭到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他们要求保留现有的工业区并维护现代的住宅,商业、教育、交通等资源设施与现存的工业历史建筑相辅相成。这样既能较好保护工业建筑遗产,又能维护当地居民的已有生活工作习惯,形成工业建筑遗产与居民生活生态风格共存的良性局面。
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对工业建筑遗产的一系列改造始终围绕着工业建筑与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对工业建筑遗产的改造或保护政策需要同时兼顾城市的生态功能和人居的社会功能,融入现有的社会习俗和认知诉求,让二者共存、共生、共长。
2.2 功能置换的活态保护方式
与德国相似,英国作为世界老牌的工业帝国,工业文明发达程度举世无双,但伴随着全球化产业格局的调整,大批工业面临关停并转的严峻局面,导致大量工业厂址的空置以及废弃。如何有效保护及利用工业遗址成为国民关注的重大议题之一。Reuven Dukas在CognitiveEcologyII著作中提到:cognitive traits are subjected to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2]1。也就是说人类的认知随着自然选择与社会发展也必将发生改变。因此,在对某一工业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也要考虑认知的主体——周围环境中人的认知趋向。众所周知,欧美国家普遍实行的是自下而上的工业遗产保护路径,公众的参与保护占据主要地位,获取当地公众的认同及主动也至关重要。如果只是一味恢复其原始的工业加工功能或工业展览功能,很难满足公众的认知诉求,也与当下新的经济产业生态格格不入。考虑到这一关键因子,基于公众对工业遗产的认知改变和生态需求,势必需要对某些工业遗产的功能进行转变。
以英国诺丁汉的蕾丝市场(lace market)为例,该市场是18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最繁华的蕾丝生产、加工及销售集散地。相应的生产作坊和工厂建筑颇具雍容华美的时代特色,它们普遍高大坚固,细腻雄伟。当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建筑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典型代表。后来由于蕾丝经济衰退,大部分蕾丝工厂关停。1969年,该地被批准为工业遗产保护区。1979年,英国政府试图重振该地的蕾丝产业经济,不料未能成功。到了80年代,诺丁汉市政府改变策略,在保护蕾丝工业建筑遗产的同时,将蕾丝市场发展为城市休闲文化中心。有了新的发展定位,市政府改造蕾丝市场的工业历史建筑,建成了两大博物馆:Framework Knitters’ Museum 以及National Justice Museum,保留并还原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劳作以及法庭审判现场旧物人文场景,吸引了大批海内外游客前来观赏。后期又引入了现代化的商店,咖啡店等休闲场地。得益于蕾丝市场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上千家文娱以及艺术企业也相继落户于此。市政府通过工业遗产的功能置换有效保证了蕾丝市场的生命延续。
3 教堂建筑遗产的活态保护路径
如果说工业建筑遗产是欧洲文明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教堂建筑遗产则是欧洲文明得以延续的精神支柱。对于教堂建筑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英国著名建筑史比尔·里斯贝罗早有论述,他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政治史就是一部教堂发展史。宗教信仰促进了国家种族认同感的形成和巩固,教堂被认为是精神力量的源泉和政治力量的象征[4]6。古往今来,这些教堂依然是欧洲人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对教堂建筑遗产的保护格外重要。
3.1 文化衍生的活态保护方式
德国对教堂文化遗产的保护可追溯至18世纪中后期的浪漫主义时期,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折服于斯特拉斯堡哥特式大教堂的绚烂魅力,惊叹之余在其艺术文集《德国建筑艺术》(DieDeutscheBaukunst)一书中讴歌了天才建筑师 Erwin Von Steinbach举世无双的工业建筑技艺和工业匠人精神。文化认知作为生态认知研究的一个理论维度,强调生态环境对人心智活动的映射和互动,尤其强调客体信息结构对人心理认知过程的重要影响,这里的信息结构不同于简单的环境刺激。刺激会激发消极被动的认知结果,而协调有效的信息结构则催生出积极主动的认知建构。基于认知生态学的文化属性,对教堂这一文化意义深厚的建筑实体保护则更应侧重其文化认知层面的拓展。
以德国著名教堂文化遗产科隆大教堂为例,该教堂位于德国科隆市,作为世界闻名的天主教堂之一,因其磅礴而又细腻的建筑风格堪称哥特式教堂建筑的绝世佳作。不幸的是,在二战期间,部分建筑结构遭受损坏,此后德国政府一直在对教堂进行精心修复和大力保护。然而,德国政府对科隆大教堂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物理修复层面,更是颇为用心地为其拍摄了一部名为“DerKölnerDom”的纪录片,追溯了科隆大教堂的前世今生,再现了科隆大教堂的恢宏壮丽。从文化认知角度来看,纪录片作为文化传播的形式,是教堂建筑的信息缩影,这一缩影跨越时空限制抵达欧洲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大脑中,生成世界范围内的公众认知以及保护认知,这就是基于教堂建筑的文化衍生保护。
本质上而言,文化衍生的活态保护就是利用生态——认知的图式框架,来实现信息映射和重构。从生态认知的角度来说,关于科隆大教堂的这部纪录片在片中并未反复呼吁公众去保护科隆大教堂,影片只是陈列了庞杂的历史发展以及构造探究信息。这种历史的与具体的场景结合生成的信息映射到公众对科隆大教堂历史重要性和结构精美性的认知图式框架,进而生成文化生态保护认知。
3.2 第二历史的活态保护方式
第二历史是基于第一历史的相生概念,建筑遗产的第一历史通常指的是该建筑最初建立时的相关信息,包括时间、建筑师、建筑风格、建筑功能等[5]。而第二历史是指该建筑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后或被改变或被损坏而形成的新风貌。较之于原始风貌,这种新风貌蕴含了新的历史内涵和时代变迁,从而赋予建筑遗产独特的文物价值。以中国的圆明园建筑遗址为例,186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并恣意破坏,烧毁圆明园。经历了这样一场空前的历史劫难,残垣断壁的圆明园留给中华后人的不仅是那段屈辱不堪的历史,更是警示中国要发展强大的座右铭。残缺而破败的圆明园所书写的第二历史彰显了比原始奢华糜贵的圆明园更深厚的时代印记和精神传承,因此也更具有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从认知生态角度而言,对建筑遗产第二历史的保护是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可与把握:人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并非局限于理想的实验化环境,而更多的是受到周围复杂的,意外的生态环境影响。提起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修复性保护,即尽可能将残缺受损的部分恢复到原样,这样才能激起在人心中的历史、艺术、审美价值。然而,这只是理想化的认知模型导向,事实上认知客体的不完美会引发更大的悲剧性审美欲望和艺术价值。因此,在对建筑遗产的保护中也可适当遵循这一原则。
以英国圣安德鲁斯大教堂为例,该教堂坐落于苏格兰著名的圣安德鲁斯市,始建于1160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大教堂之一。到了1559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登上王位,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圣安德鲁斯教堂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摧毁,沦为废墟。圣安德鲁斯大教堂失去了原先的模样和朝拜中心地位,然而荒凉破败却赋予它一种别样的庄严肃穆和悲壮崇高。这种认知审美有别于华丽感、完美感带来的审美感受,更具时空沧桑感和穿越感。在实验化的环境中往往只有完美华丽的客体才能引起人的个体保护认知和审美趣味。但是,从认知生态学来说,人的认知往往更多是由自然生态环境中更加复杂和意外的环境影响生成的结果。因此,在对教堂建筑遗产进行保护时,亦可考虑基于认知生态的第二历史的活态保护。
4 结语
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就是要让文化遗产成为大众物质生活及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活态文化”保护就是在鲜活的自然生存生态链条中,人们主动对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传承并发扬光大,使其生命延续的保护方式[6]。 “活态保护”基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流变性特点,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历史及文化空间的保护。就我国而言,工业建筑以及教堂建筑遗产在数量以及历史跨度方面略逊于欧美国家,对其保护也起步较晚。欧美国家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许多策略和经验也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尤其是在当下“互联网+”以及“一带一路”新的国家经济格局和发展战略形势下,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更要迎合时代需求和代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