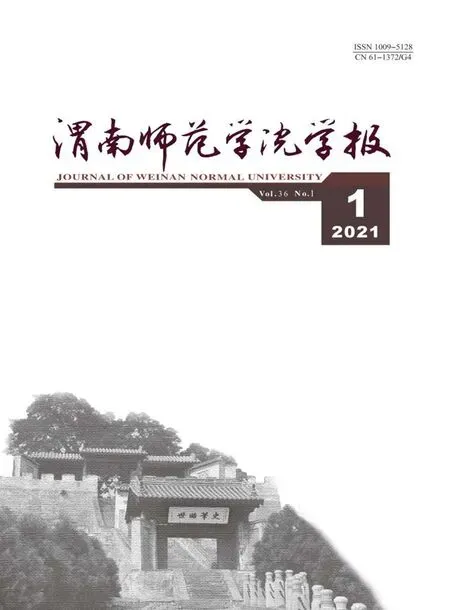孙德谦对《史记》之“义”的阐说
刘 骏 勃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史记》自成书后历代注解研究汗牛充栋,晚清学者孙德谦却认为仍有严重的不足。他说,历代“为之学者,整辑排比,参互搜讨,是特史纂史考之所为,于迁之垂为义法、足为史家作之准者,皆未有以窥其真也”[1]74,这一缺憾遂成为孙德谦撰《太史公书义法》的缘由。
一、孙氏对“义法”的界说
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又字寿芝,号益葊,晚号隘堪居士,室号四益宧,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孙氏生当同治、光绪之际,辛亥后心系前朝,立场保守,但博通四部,治学以章学诚“文史校雠”之旨为依归,深契流略之学,著《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等,又“以章氏治史之法治诸子”[2]30,著《诸子通考》《诸子要略》等,复以余力工骈文,著《六朝丽指》。孙氏学兼四部,尤以子学为长。近年来学界已逐渐重视其诸子学方面的成就,对其校雠学和骈文理论也有相当的研究。相比之下,对其史学方面的成就目前关注尚少,尤其对《太史公书义法》这部孙氏暮年心血之作的研究尚不充分,目前仅见两篇论文[3-4],故仍有很大推进空间。
《太史公书义法》写定于1924年,是孙德谦平生最后一部成书的著作,1927年始正式刊行。知交张尔田称孙氏《义法》“尤为一生精力之所萃焉”[1]5。《太史公书义法》卷上由《衷圣》至《辨谤》共26篇,卷下由《通古》至《引旨》共24篇,合计共50篇。末篇《引旨》仿《史记·太史公自序》体例,自述其著书缘由及治学经历等,其余49篇即孙氏所总结的49条义法。孙氏自言这一篇数是模仿了《文心雕龙》的安排,所谓“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1]75。其书名所以不称《史记义法》者,也是孙氏有意使用《太史公书》的原名[1]75。
至于孙氏特别强调并见于书名的“义法”二字,原是司马迁赞述孔子作《春秋》时所特别揭出者。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谓:“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5]509可见在司马迁心目中《春秋》最重要的价值即在于“制义法”。然“义法”二字何解?自裴骃以下历代注家均无阐释。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称:“‘义法’二字始见乎此。自方苞揭出此二字,近时作古文者奉为圭臬。”[6]717方苞对“义法”的阐释见其《又书〈货殖传〉后》,其中谓:“《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7]58方苞向以古文知名,因此刘咸炘谓方苞虽然对于《史记》“说义例较多于他人”,但目的却是“藉以明其所谓古文义法”[8]92,故泷川资言云方苞的解说被“近时作古文者奉为圭臬”。不过虽然方苞主要目的在于讲古文义法,但其将“义法”分开解释的思路仍颇有参考的价值。内藤湖南对方苞的解说极为赞赏,他说:“‘言有物’是说所写作的内容要充实,‘言有序’是对内容的组织构建。这是自古以来对司马迁评论中最有见地的观点。”[9]92大约与内藤此语同时,孙德谦也注意到所谓“义法”的问题,但他没有提起方苞的说法,而是引用了杜预的一段话作为阐释。孙氏云:
所谓“义法”者,杜预注《左传》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是也。[1]74
其中,“因鲁史”云云指明《春秋》的史料来源,考真伪与志其典礼点出记述之原则(孔疏云“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10]10),遵周公之制与明将来之法是撰作宗旨,“刊而正之”云云是对史料的利用之法,以达到“示劝戒”的宗旨。可知孙德谦认为司马迁所谓《春秋》的“义法”,包含《春秋》一书的撰作宗旨、记述原则、史料来源、史料利用等若干方面。如结合方苞、内藤的阐说来看,撰作宗旨与记述原则与“言有物”的“义”颇可相通,而史料来源与利用亦与“言有序”的“法”十分接近。
孙德谦紧接着指出,既然司马迁特别赞述《春秋》的义法,那么作为“绍明世”“继《春秋》”而成一家言的《史记》“亦岂无义法昭著哉?”然而历代注家中“能寻绎其义法者,概未有闻”[1]74,因此孙氏特别揭出此二字,撰成《太史公书义法》一书,从“义法”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也即是说,其书的内容不在于对《史记》所记史实的排比考证,而在于从宏观上对《史记》的撰作宗旨、记述原则、史料来源、史料利用等若干方面加以总结与阐发。
二、孙氏论《史记》的撰作宗旨
孙氏《义法》中除去《引旨》外的49篇正文实际上就是孙氏总结出的49则义法,孙氏胪列各篇,但次第之间亦约略可见其脉络。在“义法”的几个方面中,居于最紧要地位的无疑是撰作宗旨、记述原则等偏重于“义”的部分,因此《义法》一书起首的数篇即是对《史记》撰作宗旨的揭示与阐发。
《史记》为继《春秋》而作,这是明见于《太史公自序》的,因此孙德谦认为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精神。在《义法》首篇《衷圣》里孙氏开宗明义地指出:“孔子之圣,万世师表……司马迁之作《史记》也,立言一本孔子。”[1]8司马迁宗旨于孔子,首先表现在对《史记》中对孔子的特别重视,孙氏谓,第一,“本纪、世家之中,于孔子之卒必特笔书之”[1]8;第二,“十二诸侯年表又以其和孔子相为终始”[1]8,是司马迁“直以素王尊之”[1]8;第三,孔子为布衣而司马迁“置之世家之列,足征其意在尊圣矣”[1]8。更重要的是,《史记》评价人事时“无不折衷于圣人也”[1]8。对此孙德谦举出孔子论夏时、论殷路车等例子,尤其显著的则是孔子对吴太伯和伯夷的赞誉,孙氏进而认为:“窥子长之意,一若言世家之首太伯、列传之首伯夷,先圣早有定论,其折衷为至当也。”[1]8凡此种种,都表明司马迁宗旨于孔子,因而孙氏谓:“乃班固讥其‘是非颇缪于圣人’,岂不异哉?”[1]8对班固的这一看法表示了明确的反对。
尊孔则必尊儒,故孙德谦在第二篇《尊儒》中从显、隐两方面论述司马迁的尊儒态度。明显的表现如立孔子于世家,为孔门弟子立列传,又立《儒林传》等,这是人人皆知的。亦有不太明显的,如孙氏指出,儒家尚仁义,而《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称“要之以仁义为本”[1]9,《高祖功臣侯年表》称“岂非笃于仁义”[1]9,《惠景间侯者年表》称“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1]9,可见司马迁以儒家仁义的观念为评论之标准。此外,儒家尊六经,孙氏指出《史记》亦宗经,在《宗经》篇他从“宗经之体”“宗经之文”“宗经之说”“宗经之意”四个方面论述《史记》的“宗经”。第一,六经皆史也,《易》为殷周之际史,《诗》为西周史,《春秋》为东周史,而《尚书》则为通史,《史记》取法《尚书》,故为“宗经之体”;第二,《尧本纪》引《尚书》文、《舜本纪》引《左传》文,这是“宗经之文”;第三,据《礼》批评秦国郊祀不合礼法,此为“宗经之说”;第四,将吴太伯和伯夷分别置于世家和列传之首,乃本《春秋》首隐公之意,是为“宗经之意”。总之,《史记》“用其体、袭其文、采其说、师其意,且一以经为宗”[1]10-11。
孙德谦还指出司马迁尊孔尊儒的另两项具体表现,一是特重表彰贤者。在《彰贤》篇孙氏指出,孔子盛赞伯夷、叔齐这样的岩穴之士,司马迁本孔子之意,对布衣贤者“故为表彰之”,使其不至于湮灭无闻。刘知几曾对司马迁不为皋陶、傅说这样功业昭彰的古人立传表示遗憾,孙德谦指出这是刘知几未曾领会司马迁特重表彰贤者之意。对于《史记索隐》称应当补子产、叔向等传,孙氏认为其中有些已见于世家等相关篇章,而有些应当表彰的则由于文献不足无法立传,这也正是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赞里对贤者磨灭无闻太息痛恨的原因。[1]29-30在《崇学》篇中,孙德谦指出司马迁尊儒的另一具体表现是重学术源流的记载。儒家所重在于学,《史记》传人物时“于人之有学及所从学之人,无不详哉言之”[1]34-35,即便所记不是儒家学者,也原原本本述其源流,几如一篇艺文志,如此不仅是尊儒的表现,也体现了史家的眼光。
孙德谦用宏观的《衷圣》《尊儒》《宗经》等篇和具体的《彰贤》《崇学》等篇,从不同方面反驳班固“是非颇缪于圣人”的说法,证明了《史记》尊孔的撰作宗旨。然而,孙氏自己也发现了一个危疑之处,即《太史公自序》中有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5]3296《易传》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太史公父子意欲正之,岂不是和尊孔有所冲突?面对这一疑难,孙氏特作《正易》篇加以解释,他说,伏羲始画八卦,故《易传》溯源伏羲;而黄帝首置史官,故《史记》断自黄帝。这是《史记》和《易传》的不同之处,“《易》学出于庖牺,史学出于黄帝”,“史与《易》既各有所宗,斯其正之之义也”[1]11-12。孙德谦把“正之”的意思同廓清源头联系起来,以弥合“正易”和尊孔之间的不合之处,虽颇显勉强,却也维护了他所相信的司马迁尊孔的初衷。
同时,孙德谦还用这种廓清源头的做法来反驳班固认为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批评。在《原史》篇中,孙氏指出,史职创立于黄帝,老子也曾为史职,且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道家出于史官,故“论大道而先黄老,为史家所当然耳。何也?以史学导原于黄老耳”。司马迁并非有意崇黄老而抑六经,“特其所撰百三十篇乃史也,为史学而究其原,六经宜在其后,不得不取黄老为先矣”[1]15-16。孙氏将班固语中的“黄老”与“六经”放入历史发展中,指出司马迁先黄老是为史学“究其源”,而非宗旨之取舍,前提既已取消,则班固所言在孙氏这里便不攻自破了。
三、孙氏论《史记》的记述原则
孔子曾赞美董狐云:“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直言不讳,书法不隐,历来是史家所应坚守的记述原则,司马迁更是如此。即使班固对司马迁颇有不满,也不得不承认《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1]2738。孙德谦在书中亦立《直言》一篇加以申论。他指出,司马迁不仅坚持了直言的原则,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是由于司马迁直言景帝、武帝之短,才触怒了武帝,他之所以受蚕室之刑,表面是由于李陵之事,实则“武帝之怒,特怒其直言耳”,“不过借此以洩其怒,而蚕室之罪,实因直言所致也”。孙氏还指出,正因为司马迁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导致此后“孟坚而下,良直之风不行”[1]28-29,凸显出司马迁坚守原则的可贵之处。
在《行权》篇,孙德谦引用唐代韦安石之语云:“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1]26这里的“权”是一种独立于甚至抗衡于相权(以及君权)的“史权”,其实,与其说是“权力”,不如看作史官所应肩负的崇高使命与责任。这样的权力与使命一方面只有真正坚持直言等记述原则的史官才有资格行使,另一方面,行使这种“史权”时也很难避免王权的干预。孙德谦指出:“迁之得罪,武帝特恶其史权之重。”[1]26司马迁行使史权,直言景帝、武帝之短,以此触怒武帝,是以武帝借口李陵之事来泄其怒,但始终无法公开从史权角度指责和处罚司马迁,显示出史官天然地具有独立于君王的地位并且必须坚守这种独立性原则。
作为良史,除了“直言”的原则外,在记述上还应做到识大体、知变化。在《识大》篇,孙德谦引用章学诚论司马迁“略于名物器数,惟期得其大体”的一大段言论,认为这是作史的原则,然后略加发挥,指出“史之当识大体,与经之当通大义,其道同也”,并由此出发,对当时“专务琐屑考订”的经学家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昧于大义”[1]25-26。与此类似,在《知变》篇孙德谦指出,史官之可贵,正在于能“通古今之变”,以资考鉴,而当时一些治史者则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说:
其治史也,又详于古而略于今。于是见商周鼎彝,释其文字,得一碑志,喜其古也,且谓可以征史,而史之所藉以为今人鉴戒之具者则懵然而无知也。尤其甚者,高谈皇古,欲求之地下,而期乎发掘之有所得,谓庶几史材之凭证焉。呜呼!史学岂若是哉?[1]27-28
这段批评显示出孙氏对考古发掘、文字考证等取向的不满,认为这类工作厚古薄今,在“今人之借鉴”方面缺少价值。这一方面出于他对传统的微观考证路径的不赞同,另一方面或亦与当时的新旧之别有关。孙德谦以遗老自居,学术上也甚保守,认为新学不利于世道人心,对民国时兴起的重视出土材料、追求所谓科学的新风尚难免有所排斥,故这里从强调通古今之变转而去批评当时的考古发掘,看似略显突兀,实则是其立场与思想的自然体现,同时客观上也对沉溺考据缺乏致用的弊端有所警示。
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是书法无隐的表率,但汉代以来却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作《史记》是为“发愤”,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对这一观点孙氏在卷上最后一篇《辨谤》中专门作了反驳。孙氏梳理了“谤书”说的诸观点,首先“汉王允有云,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自此说出,迁史遂受谤书之诮矣”,后人便引《太史公自序》中“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一句为佐证,认为《史记》之作出于发其愤恨,此后“如葛洪辈见伯夷居列传之首,则谓善而无报;项羽之入本纪,又谓居高位者非关有德,疑迁命意在此”,“章怀之注《后汉》也……曰……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缗、榷酤之类是也。又引《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对于此类言论,孙氏一一加以辩驳。第一,孙氏指出,王允之言是有所为而发,当董卓死后,蔡邕颇为叹息,故王允收其下狱,蔡邕乞免死以继成汉史,王允遂有是言。孙德谦认为,在王允看来,蔡邕党附董卓,“苟使之继成汉史,必不能得《春秋》诛乱贼之意,允故借迁以甚其辞,遂有此谤书之称,岂知迁书遂蒙不白乎?”第二,关于《太史公自序》中的“发愤”之语,孙氏引《论语》“发愤忘食”一语,谓“发愤者岂必谓愤恨哉?”第三,对于葛洪所言,孙氏指出冠伯夷于列传之首是“以前贤旧传唯是为先”,且有孔子之赞,而项羽入本纪是因为“羽当秦汉之际,政权所归”,“几践天子之位矣”,与所谓善而无报或高位无德并无关系。第四,对于章怀太子之语,孙氏指出,一方面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缗、榷酤之类汉家不善之事均是事实,记之合理,“安得斥为毁谤乎”?另一方面,司马迁并非只记汉家不善之事,他对汉室亦不掩其善,如《高祖本纪》赞中云“得天统矣”,《秦楚之际月表》序云“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都是赞誉之词。第五,对于章怀所引的《班固集》中之语(据《文选》卷四八《典引》,此实为汉明帝诏书中语),孙氏从时间上指出,司马迁自称“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表明《史记》之撰写早在受刑以前就已开始,故身罹刑狱之后而微文刺讥是不足为据的。总之,司马迁绝非故作谤书,而是善恶兼著,坚持了秉笔直书的原则,“诚无愧乎良史”。最后,孙氏总结称:“倘误以微文为史家之能事,而引迁为口实,则是悖理蔑义者转得诿过于迁,谓其撰史之法所重在兹,史学何自而明乎?”[1]38-40郑重指出谤书说不仅会影响对司马迁的正确评价,更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引为口实,对史学造成严重的危害。
四、孙氏对《史记》一些疑难问题的看法
《史记》中除了宏观的撰作宗旨、原则等偏于“义”的部分外,孙德谦还对《史记》中一些历来聚讼不己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被记作“《太史公》百三十篇”[11]714,对于何以称“公”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孙氏在《称公》篇首先列举了前人对此的解释:如张守节《正义》认为“书之称公,迁乃尊父并以自显耳”;《索隐》认为是东方朔所加之名;钱大昕认为书成一家言,当云《太史公春秋》,而谦虚不敢称“春秋”,故云《太史公书》,以官名之,承父志也。对于这些说法,孙德谦都不同意,他认为司马迁不愿其书与诸子同列,故称公“意欲高过诸子也”。这里孙氏附带讨论了司马氏父子的官名是“太史令”还是“太史公”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其官为太史令,或以位在丞相之上,并因尊天之道,故亦可称为太史公。在迁与父谈居官时则有公之名,迁卒而定名为令,自是而不复称公矣”[1]67-68。对于太史公和太史令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有所讨论[12],孙氏所言可作一家参考。
关于司马迁作史的时间,孙氏在《考年》篇认为:“自太初元年至太始二年,终始凡十年而其书则成也。”[1]68按《太史公自序》云“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于是论次其文”,是司马迁作史始于太初元年,这一时间自来都无异说。至于成书时间,孙氏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中的“至于麟止”一语,《汉书·司马迁传》中亦引此语,其下服虔注云:“武帝得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作《史记》止于此也。”[11]2722故孙氏据此称:
《汉书》武帝太始二年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则是年诏有获麟之语,故知其书成为二年也。初以获麟在元狩元年,诏又言“往者郊见”,疑非此二年事。然服虔、张晏于“麟止”下作注,皆云“铸金作麟足形”,今诏有“更黄金为麟褭蹄以协瑞焉”之文,则正就此年言也。迁故不曰“止于获麟”而曰“至于麟止”,可知其为太始二年矣。盖“止”与“趾”古字通,服氏为“铸金作麟足形”下有“故云麟止”说,是彼固以麟足解麟趾也。[1]68-69
可见孙氏是根据服虔、张晏注“麟止”时所谓“铸金作麟足形”之语,将“至于麟止”解为“至于作麟足(麟趾)事件”,铸金作麟足形之事在太始二年(前95),故孙氏将《史记》成书系于此年。
关于《史记》的性质是国史还是私史,孙氏坚定地认为应当为国史。在《纂职》篇他指出,首先,“未有居史官之职而其书乃可名之为私史者”,司马迁父子均为史官,所著之书自然属于国史;其次,书中多次自称“臣迁”,也可证其书为奏进的性质;最后,班彪等对《史记》作的续补是属于国史的,“后传既为国史,而史公所作其为国史也益可信”。对于一些反面意见,如有人认为遭李陵之祸后司马迁已改任中书令,不居史职,孙氏称《报任安书》开篇自称太史公牛马走,可见征和时“必以中书而犹兼史职也”。对于班固所言司马迁“私作本纪”,孙氏称班固所谓“私”并非指私史,而是出于二者修史体例上的不同。孙氏认为在班固看来,以汉朝断代为史是当王为贵,而以通古体修史,将汉家帝王“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出于司马迁一己之私,因此班固特别称司马迁“私作本纪”,而不及列传等[1]65-67。
此外还有若干小的问题,孙氏放在《杂志》篇一并讨论,包括“辟天数”“辨兵谋”“引成说”“编次之乱难考”“窜加之迹易知”“书经删补”“书早流传”“书有单行之篇”“书有续入之辞”“史文之难读”“史文之宜法”共11个小题目[1]70-73。在“辟天数”中,孙氏反对将本纪等五体的篇数都和十二月等天象之数配合起来的说法,他指出:
《正义》之论史例也,曰:“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此盖言纪传之为数,皆合于天也。余未敢信其为然,张氏殆以意揣测耳。[1]70
孙氏指出,《太史公自序》中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说法只是司马迁的“譬况之词,未必本纪诸体篇数胥皆欲合天数也”[1]70-71。孙德谦对《史记》无疑是极为赞赏与尊崇的,但他在篇数问题上反对部分人将《史记》神秘化的做法,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分析研究,故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余“编次之乱难考”“窜加之迹易知”“书经删补”“书早流传”“书有单行之篇”“书有续入之辞”诸条聚焦《史记》最初的文本及流传中的问题,虽然篇幅简短,但对《史记》文献学角度的研究亦不乏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关于“正《易传》”与《史记》成书时间的讨论
孙德谦在《太史公书义法》自序中借答客问的形式说:“使后世推为功臣,以比师古之于班氏,岂非快事!”[1]4自许为司马迁之功臣,可见对该书是颇为自负的。《义法》一书确有许多可称道之处。例如孙氏如实揭示出《史记》继承孔子的宗旨与精神,反驳了班固等对《史记》的不当评价,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史记》的主旨。直言、行权、识大、知变等篇的论述不仅适用于《史记》,对整体认识和从事史学工作也有理论上的价值。又如孙氏对《史记》尊崇但却不神化,反对将诸体篇数和天象之数相配,表现出一个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
1.2 输卵管病变 在继发性不孕症中,输卵管性不孕为首要原因。输卵管的主要作用是拾卵、提供精卵结合场所、将受精卵运送到子宫。输卵管通畅、平滑肌正常蠕动以及输卵管黏膜上皮纤毛摆动是输卵管发挥功能的前提,所有可引起输卵管结构或功能异常的原因均可影响妊娠。
但孙氏有些观点亦可堪商榷,尤其是其对“正《易传》”颇为自负的解释和对成书下限的考定,在这两个问题上孙氏的论证都颇为牵强。
1925年孙氏曾致信同以遗老自居的旧派学者曹元弼,其中云:
弟去秋八月后当乱离之际,又成《太史公书义法》都二卷,共五十篇。龙门自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书固不敢以知意自矜,然略去考据而推阐其撰述之意,知古人著书自有苦心,且恐来学不晓,作为序、赞以发明其意。即如《自序》“正《易传》”一语,在彼所以见《系辞》之说首溯伏羲,此《易》道当然;而史学始于黄帝,故本纪以之书首。而人皆疏忽不甚经意,不知正言其断自黄帝,与《易传》不同也。[13]122
孙氏向曹元弼谈及《义法》一书时,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即对“正《易传》”的解释,可见其对此解之自矜。“正《易传》”一语确实是向来学者“皆疏忽不甚经意”之处,孙氏特别加以考察,是颇具眼光的。他以易学溯源伏羲,史学始于黄帝,故司马迁以黄帝首本纪,以显示“与《易传》不同”,是为“正《易传》”之意。不过当时曹氏尚未见到书稿具体内容,故没有特别回应。1927年《义法》刻成,孙氏倩人持赠曹氏,曹氏于覆书中针对“正《易传》”表达了不同意见,书云:
《正易》篇言本纪托始黄帝之故,卓识崇论,发前贤所未发,惜不能令张平子见之。窃谓经始于伏羲,史始于黄帝,《易大传》皆有明文……太史谈受《易》于杨何,子长传家学作史,首纪黄帝,固本《大戴礼·五帝德》,抑亦《易》之微言与?曰“正《易传》”者,当时《易》家多阴阳、占侯、灾异之说,皆谓之《易传》,厥后《京氏易传》正其类。《史记》贯彻天人,所据《易传》皆孔子《十翼》,如引“同归殊涂,一致百虑”及《坤·文言》之等,皆夫子《大传》之文。其义光明正大,如日月之中天,非禨祥家所得而混淆。《史记》称《易》之例明而《易传》正矣,所谓“言六艺折衷于夫子”,此其一端。区区之见,因大论而引伸之,不知有当否邪?[13]126
曹元弼不同意孙氏的解释,在曹氏看来,“正《易传》”是指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摒除当时禨祥家说《易》之言论,而继承孔子说《易》之途辙,此为“正”字之义。然而孙氏颇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回信中反驳曹说云:
然窃有疑焉,敢请训诲。经学之盛,莫若两汉,惟在武帝时不过创兴伊始。《汉书·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今只丁宽尚有辑佚本可考遗说。据本传,从周王孙受古义,训诂举大义而已,并无阴阳灾异。至《高相传》云:“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称为“自言”,则是高相假托,而宽之说《易》不主阴阳灾异也。《史记·儒林传》中且无丁宽姓名,可见王同诸家《易传》决不重阴阳灾异者,子长父子何容取而正之?《易》家之阴阳灾异,班氏惟于《孟喜传》言之,传云“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直书之曰“诈言”、曰“独传”,亦足证阴阳灾异为孟喜之学,而非传自田氏者也。汉初言《易》则为田何,其时阴阳灾异犹独未行于世,必谓史公之正《易传》在彼诸家,殆不然与。[13]127
此外,曹元弼在提出对“正《易传》”之不同意见的信中,也同时提到了另一处不同观点:“尝谓子长识至高、学至正、叙事理至善,惜其书为未成之书,孟坚所谓疏略抵牾者,皆其长编未定之稿耳。”[13]126曹氏认为《史记》没有最终完成,这与孙德谦也相反。故孙德谦在回信中一并反驳云:“又史公作《史》年岁,弟考定创始于太初元年,成于太始二年,《义法》中有《考年篇》,私谓鄙说无可刊易。观《序》于篇目总数以及全书凡若干字,而‘故作《黄帝本纪第一》’‘故作《夏本纪第二》’之类,断非未成之书。”[13]127孙德谦不仅认为《史记》确已完成,而且考定了具体的写作时间,并且自负地认为“私谓鄙说无可刊易”,然而其关于《史记》完成时间考定实际上却存在两层失误。
首先,关于《史记》完成时间孙氏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中的“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语,然而,此语分明是司马迁自序其书中所载内容的断限时间,如将“麟止”理解为写作完成时间,显然无法与“陶唐以来”呼应,是故几乎从无学者如此理解“麟止”一语(仅见裘新江认同孙说,谓“麟止”为定稿时间[14]),此为第一层失误。其次,就“麟止”事件本身来说,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其定在武帝元狩元年(前122),这是因为据《汉书》所载武帝获麟仅此一次。孙氏一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后来却改变了意见,他说:“初以获麟在元狩元年,诏又言‘往者郊见’,疑非此二年事。然服虔、张晏于‘麟止’下作注,皆云‘铸金作麟足形’,今诏有‘更黄金为麟褭蹄以协瑞焉’之文,则正就此年言也。迁故不曰‘止于获麟’而曰‘至于麟止’,可知其为太始二年矣。”[1]68其中所谓诏书指太始二年三月之诏,全文云:“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褭蹄以协瑞焉。”[11]206按渥洼水出天马在元鼎四年(前113),诏书叙获麟在渥洼水出天马之前,故知诏书中所叙获麟确在元狩元年(前122),太始二年(前95)不曾获麟,因此孙氏最初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孙氏看到诏书中的“更黄金为麟褭蹄”,又看到服虔注中的“铸金作麟足形”(张晏注无此说),反而产生了误解,认为服以“麟足”解“麟止”,是将“至于麟止”理解为“到作麟足事件”,故孙氏把麟止的年份下移到“铸金作麟足形”的太始二年(前95)。按,服虔注云:“武帝得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作《史记》止于此也。”[11]2722其文确实易产生误解。实际上,所谓“而铸金作麟足形”仅为顺带提及获麟一事之后续,并非以“麟足”解“麟止”,因后文明确出现了“止于”的本字,故其云“作《史记》止于此”,仍谓止于获麟之元狩元年(前122),而非铸金之太始二年(前95)。孙氏误牵合二者,又求之过深,故将“至于麟止”误系在太始二年,这是第二层失误。
孙氏在向曹元弼介绍《义法》时称此书是“略去考据而推阐其撰述之意”[13]122,然而“正《易传》”和《史记》作成年岁两个问题均脱不开考据之工夫,也许恰由于孙氏于考据措意略少,故在这两个问题上未免疏漏。不过,即使有此瑕疵,从总体上看,读书当先观其大,《义法》一书论《史记》宗旨、原则等确能有所启发,值得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