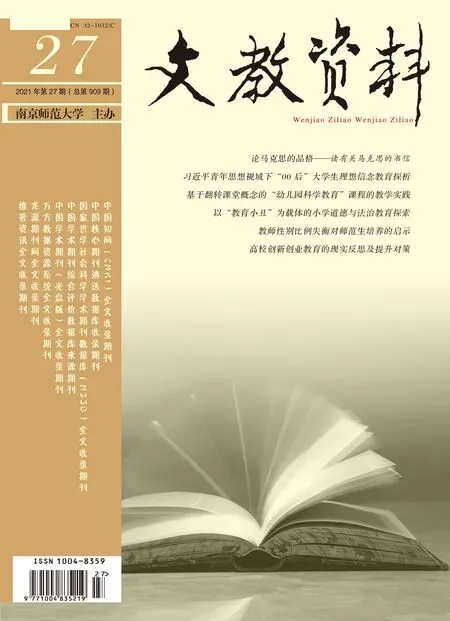“尺一牍”“钱十一当一布”和“六百六十钱”
——试论秦汉时期历法数字“十一”的应用
赵 龙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00)
在日常生活中,数字的应用是很平常的事情,一般情形下以便利性为第一考虑要素。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都偏好使用能够被整除的数字,其中以带五和带十的数字为先,最不济也是偶数。特别是对于数学运算还不发达、还没有阿拉伯数字、运算工具还很落后的古人来说,自然越便利越好。这种偏好传承至今,仍左右着人们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尺一牍”“钱十一当一布”及秦律汉律中的“六百六十钱”“二百二十钱”,不免令人费解。这样的官方规定,在日常生活中殊不便利,那究竟为何推行?
一、“尺一牍”与“尺一诏书”
(一)简牍的尺寸
简牍常见长度有六寸、八寸、一尺、尺二、二尺四、三尺等。尽管学界一致认为就目前的发现而言,秦和西汉甚至东汉的简牍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简牍形制方面的规范,但不妨碍我们回顾人们对这些尺寸进行过一些解释的尝试。国内在这方面最早的解释是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一文中提到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八册),由胡平生整理成的“分数”“倍数”论。[1]
古策长短皆为二尺四寸之分数。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周末以降,经书(六经)之策皆用二尺四寸,礼制法令之书亦然。其次一尺二寸。《孝经》长一尺二寸,汉以后官府尺籍、郡国户口黄籍皆一尺二寸。其次八寸,《论语》策长八寸。其次六寸,汉符长六寸。
牍之长短皆为五之倍数。最长为椠,长三尺;其次为檄,长二尺;其次为乘驿之传,长一尺五寸;其次为牍,长一尺。天子诏书一尺一寸。又其次为门关之传,长五寸。
在这里可以注意到两点:其一,王国维认为古策长短和二尺四寸有关,牍之尺寸与五有关。亦即,简牍的长度可能有数字性规律。其二,天子诏书一尺一寸与五并不成倍数关系。后来的学者,对王国维的看法或肯定,或否定,但都没能解释为何天子诏书长尺一。
(二)“尺一牍”形制的形成
在有关秦汉时期的传世文献中,关于长度为尺一的木牍并不少见,或记为“尺一牍”,或记为“尺一木”,或记为“尺一诏”。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2]
辛未诏曰:(李贤注)《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3]
(李贤注)蔡质《汉仪》曰:“延熹中……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对诘……”[4]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李贤注)尺一之板谓诏策也。[5]
答诏问灾异八事。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诏书尺一,召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华、蔡邕、太史令单扬……受诏书各一通,尺一木版草书。[6]
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7]
而灵帝曾不克己复礼,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驺骑电激,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内嬖鸿都,并受封爵。[8]
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尺一出升。政由是显名。[9]
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李贤注)尺一谓板长尺一,以写诏书也。[10]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长度为尺一的木牍,一般用作诏书。诏书木牍的长短,必然是制定之后,有别于其他形制的尺寸。所以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而不是尺一寸,自然有其中的缘由。毕竟,那时是一个阐发义理、开创制度的有其用意的时代。众所周知的秦“数以六为纪”[11]就是一例。
一般学者认为简牍形制没有固定,这是因为其中有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假设有固定的形制要求,这一要求如何实现?必然是有一定的规制。一种情况是官方定制,在大量空简空牍的制作之中,按照一定规制形成,自然可以做到。前文提到的王国维所总结的“汉以后官府尺籍、郡国户口黄籍皆一尺二寸”即为一例。另一种情况是制作有专门用途的简牍,会依照统一的形制。前文提到的,王国维所提出的“经书(六经)之策皆用二尺四寸……《孝经》长一尺二寸……最长为椠,长三尺;其次为檄,长二尺;其次为乘驿之传,长一尺五寸”即例证。
一般而言,这两种情况有时一起出现,有时单独出现。但无论如何,正因如此,简牍才会出现特定的形制。“尺一牍”因为是诏书,所以尺寸异于其他简牍,那么,为何是“尺一”,而不是其他尺寸?
二、“钱十一当一布”
不仅是传世文献中,秦汉时期有这种关于数字“十一”的可疑之处,出土文献中例子也有一些,其中最主要的有政府规制的钱布交易兑换比和罚金数额两类。此处先讨论钱布交易中的例子。
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睡虎地M11《秦律十八种》金布六七)[12]
乍一看,并无奇怪之处,政府制定金和布的兑换比而已。但这样的规定实际在生活中却很麻烦,远没有钱十当一布方便,甚至没有钱十二当一布方便。因为这样的兑换比,简文中出现大量的数字呈现出十一的倍数。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出土的法律文献中“多十一的倍数”[13]。于豪亮认为这和律文中钱布交换的规定有关:“律文规定一疋布折合十一个钱。”[14]“而《效律》中关于物资的计算,总是以布为单位,折合成钱计算……廿二钱是两匹布,六百六十钱是六十疋布。”[15]这样的解释本身没有问题,但仍然没有回应为何是“十一”,而不是其他数字;为何不使用便利的数字这一问题。
可以确定不是出于经济学的考虑而如此设定。同时,数字“十一”显然与数字“六”没有关联,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数以六为纪”。那是什么原因呢?
三、秦律、汉律中的“十一”
秦律、汉律中与“十一”相关的数字比较常见,主要体现在犯罪金额上。犯罪金额是数字运用的一种,其使用与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偏好一致。例如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罚金数额基本是带五或者带十的数字。秦和西汉的律法当中,罚金数额却与数字“十一”相关。
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睡虎地M11秦简《法律答问》)[16]
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不盈百一十钱到廿二钱,罚金四两。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17](张家山M247汉简《二年律令·盗律》J55-5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认为:秦至汉初律文钱数常采用十一的倍数,系因“钱十一当一布”[18]。如果用钱十一当一布理解,就等于用布匹衡量所盗物品的价值。乍一看没有问题,但稍一想就能想到一点,在已经有货币的秦汉时期,盗贼所盗物品是卖掉换成赃款,还是换成布匹?恐怕不是以物易物换成布匹,而是换成钱币。衡量盗贼所盗物品的价值,大概根据其售卖非法所得物品的所得算。在这种情况下犯罪金额与十一捆绑,虽然有金布兑换比的原因,但亦存在其他原因的可能。
四、历法中的“十一”
在同一时期的历法中也出现十一这个数字。古代的历法大多围绕如何解决阴阳合历下日月周期耦合的问题展开。几经更新后,古人摸索出来十九年七闰的方法解决日月两个周期不合的问题。十九年七闰的分布方式,根据历法研究者对《汉书·律法志》中朔闰分布的考究得知,确实是按“3-3-3-2-3-3-2”这样的规律分布的,即秦至汉初的闰年分布设置。这样的分布方式正好是前十一后八的排列。秦制昼漏正好是十一刻,正是秦人对于这一发现的应用。
五、字的联系
数字被赋予独特意义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运用这种被赋予了意义的数字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在秦统一之后,尚“六”即一例。将历法中独特的数字“十一”与简牍长度、金布兑换比、秦汉律中犯罪金额等联系起来,乃是受辛德勇先生将历法中一章之数十九与《古诗十九首》联系在一起的启发。翻阅史料,有以下两条证据可备参考。
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史记正义》)[19]
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20]
《别录》与《洪范五行传论》都是西汉刘向所整理撰写的。刘向是博学之士,作为史家的他熟悉天文历法,将历法中的一个成数应用在其他事物上是存在这个可能的。秦汉继承了战国时期学者对于天文历法的知识探索,制定了各种规章名物制度,正好是掌握此等学识的人,可能是博士官、法家、阴阳家,但毫无疑问,这些人将其学说与其他学说融合后,贯穿在秦汉的制度之中。
在此基础上,官府借助国家力量把少数人认可的一些数字应用推行在专有的领域,如官方简牍(诏书)的长度、法律规定的犯罪金额区间、市场上金布兑换的比例等。数字的发明起初是为了方便使用,但后来经过人为的建构,赋予它们独特的意义,然后推行这种具有独特意义的数字,使之处处可见,正是人为建构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