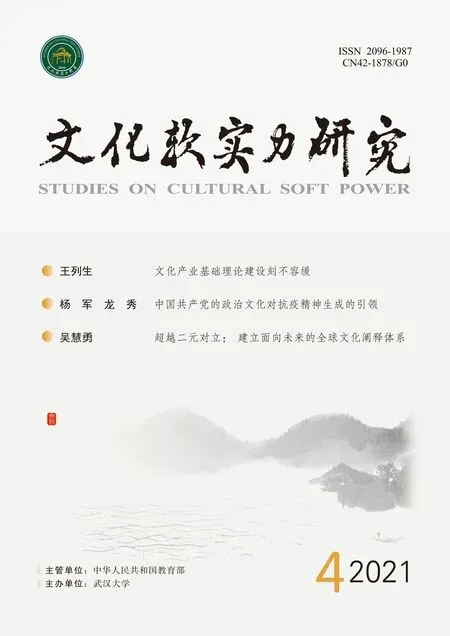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建设刻不容缓
王列生
无论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是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进而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高度统一的协调推进,从而确保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助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得成效显著双赢成果。毫无疑问,这一战略导向,价值定位精确,逻辑起点坚实,目标预期也非常理性,政府、社会、市场和亿万参与的人民群众,无不对此给予厚望。
不无遗憾的是,尽管已经获得的实际进展不容小觑,然而不仅进展与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即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的绩效增量溢出效应并未大范围呈现,而且还在资本无序扩张中,因片面而激进的非边际效应优先性与无条件产业膨胀,不期而至地带来诸多明显预期不足的负向量问题,有些甚至已经演绎为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抑或发展瓶颈问题。对于“天价片酬”“流量至上”“饭圈文化”“网游沉迷”以及从业明星丧失道德底线等,中央出重拳进行系统性而且全方位的监管、整顿、处罚乃至追究法律责任,足以说明事态的严重性、负面社会后果的广泛性甚至危及正能量价值坚守的深刻性。随着整顿强度和监管力度不断增强并且能够可持续深入,相信被动局面一定会有实质性扭转,诸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现场的乱象,会在强力干预之下一段时期内退场或者消失。尤其会迅速见诸效果的是,企业自律、平台自律、从业者自律,会较大程度地从被动状态转为主动状态,而这显然是大整顿和强监管的理想治理目标。作为专业文化政策研究者,对所有这一切不仅拥护而且信心满满。
那么,事态发展就会如此清晰地呈现为我们意欲呈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吗?或者换句话说,复杂的必然性与繁多的偶然性,会不会一些矛盾解决了而又代之以另外一些矛盾?一些乱象退场消失,换了马甲之后又会显形为新的乱象?忧虑的根源在于,整顿和监管的功能有效性,应该来源于对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进行有效治理的制度理性、制度安排和制度功能工具匹配,而且尤其应该来源于既具中国事态现场问题针对性,同时更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揽子“治理方案”,而不能仅仅某些社会表象集中爆发,就以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随机方式应急处置。社会问题出现以后,针对任何表象的应急处置,不仅必要而且还需及时。但问题在于,止于单纯应急处置就将在自变量极强的社会表象事件中疲于奔命,治理效果会因轻本重末而效能大打折扣,更何况作为社会表象的任何文化事件,其隐存内置与复杂因果关系,远非那些交通事故、骗保骗贷事件抑或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事态等所可比拟,尽管后者也都是非常棘手的解困对象之所在。
所以问题的逻辑递进更在于,不仅要在知其然中致力于应急处置效率最大化,而且还要在知其所以然中努力获取能够统辖有效应急处置的问题发生机理的最大清晰度,由此才可以在确保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力避处置盲目、处置盲动抑或处置盲评。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在随机位置寻求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均值平衡,就必须使所在问题域治理效能凸显的“中国方案”,从一开始并且可持续地使其获得学理赋能与机理驱动的支撑杠杆,而这也就意味着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建设刻不容缓,因为没有基础理论不断完善和深化所带来的完整知识地图、清晰知识路线和精准知识解读,就一定难以产生对特殊产业形态的文化产业存在属性、发展规律、目标定位乃至风险评估等诸多总体性、基础性、前置性问题的科学认识与理论把握,进而也就有可能导致一系列技术知识层面的衍生性纠缠,以不同负向量方式延滞或者阻碍这一特殊产业形态的健康发展,亦如我们所正面遭遇的种种社会乱象以及企业困局。
以此为逻辑起点,焦点所在就由是否需要迅速推进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建设,转换为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基于中国事态背景、中国知识立场和中国实践进程,建构起具有基础理论强大支撑力的完整功能框架,不仅以知识学姿态,来实现本体论、存在论和生存论,在阐释界面获得纯粹理性认识升华,而且以实践性导向,在具证维度上,实现核心问题、基本问题和关键性问题的实践理性行动张力。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亦如没有实践的理论无疑乃空洞的理论,所以具有中国学派特征的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及其知识框架,将一定是理论与实践互驱发展并且互为条件的开放性知识系统,并且这一系统不是单一学科架构而是学科交叉且合力解困的综合知识聚集,尽管某些涉身者会更加执着于“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化思维定势。无论不同阐释界面还是不同具证维度,对于迫切需要建设的文化产业基础理论,我们现在所具有的内置义项编序与框架性知识生成逻辑的可及性还非常有限,一切还有待知识界、文化产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跟进努力,但某些前置性基本原则可以先行言明并成为此后跟进建设的鲜明导向。
首先在于切实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所议知识域精准而全面价值嵌位,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科学与研究动能互驱,力求中国问题靶向意识与世界经验知识参照的开放性学理推进,从而在中国学派与中国话语体系积极建构的大背景下,促使中国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少走弯路,昂首正路,探索前路,并沿着这样的发展轨迹最大限度地完成文化产业有效治理的知识体系建构,进而因这种知识体系建构而获得文化产业良性扩容以及发展方式充分激活。
其次在于切实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及其在产业形态中的诸多价值理性原则。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现实,同时也是个体、民族和社会赖以存身的内在价值维系。既有其复杂价值分层,又有其丰富形态分类,其日常栖居满足与精神家园庇护异质生存论界面,包蕴着同质存在论指向的高度价值叠合。绝对多数文化意义和价值都与文化产业无涉,文化产业只是在边际条件与叠合状态下,具有现代日常文化消费语境中的存身不可或缺,因而也就意味着非条件性文化产业论、文化市场论和文化消费论等,极容易去条件化地意义遮蔽而不自觉地离开民族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宏大事态、基本规律和价值理性。鲍德里亚在其“残留物”与“符号象征交换”中,都已意识到无条件将会导致娱乐化、欲望化乃至亚文化泛滥的负面后果,我们在“意识形态”“精神家园”“文化理性”等关键词统辖下,就更没有理由以一种冲动姿态,沉溺于价格利益而懵懵于价值精神。作为宏大事态的文化发展远远超越于局部事态的文化产业发展,甚至所谓“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法,也只是社会文化治理过程中的粗放型行为模式与行政性言说方式,如果我们浅表态止于这样的行为模式与言说方式,那就会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功能覆盖与价值实现的理论真空与实践盲目,当然也就与民族与人类的文化理性升华抑或精神家园建构,还有更为遥远的距离。所有涉身者在此需要切记的是,文化产业扩容增量,并不必然导致现实社会的文化发展,某些条件下还会因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等适得其反。所以这里亟待理论解困的一系列隐存问题在于,在文化产业合法性不容置疑的现代生存背景下,如何有效给定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发展价值链中的清晰价值定位,进而寻求基于这种定位而与整个文化价值建构事态的功能链接和力点支撑所在,追求彼此恰配性的同时充分显现其存身不可或缺与合法利益最大值。没有诸如此类的全方位理论解困,仍然止步于隐存问题遮蔽的盲动再生产,将不仅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难以在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康庄大道行稳致远,而且还会不经意间随机遭遇畸形无序扩张所导致的种种负向量后果,近期一系列网游事件就是产业初衷与实际后果的悖离具证。
再次在于切实遵循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在推进文化产业中的一系列产业发展内在条件。离开这些规律和条件,只盯住高附加值资本介入投机后果,迟早会在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的铁律合击下输得血本无归,而这无论对于投资个体还是对于我国的文化产业,都是应该着力加以规避的“雷区”和“陷阱”。要想对“雷区”和“陷阱”有效规避,当务之急,当然是为这种规避提供系统而坚实的理论支撑,因为一旦支撑有效,至少不会出现文化产业领域系统性、断崖式或者畸形化的整体风险。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支撑有效的基础理论建设当以如下方面最为迫切:
(一)对象定位。所谓文化产业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其所存在的逻辑起点、价值目标、社会功能、要素构成、价格机制、绩效模式、产业链配套、投资渠道、生产方式、产品形态等等,都必须在边际条件给定的前置条件下予以清晰化和规范化,从而以理论建设成果为所有涉身者打开一幅完整把握产业进入的可识别地图。
(二)制度完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在基本经济制度和具体产业制度支撑下才有发展的可能,而文化产业制度究竟包括哪些具有中国利益立场的运行制度、保障制度、激励制度、监管制度乃至更加微观精细的技术化制度配套安排,则是文化产业基础理论需要给予完整精准回答之所在,同时也是由此牵引政策联动效应的知识使命。文化产业制度与其他产业制度既有同质性亦有异质性,因而锁定异质性及其同质性的可兼容机理,同样是制度完型的重要构件。没有完善而强有力的文化产业制度安排,任何文化产业行为都程度不同地具有盲动特征,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三)工具匹配。与时下往往以“小数据”或“个案”为支撑,无的放矢于“路径”“模式”“吸引投资”“扩大消费”等五花八门非边际“朝天开枪”的建言方式不同,文化产业基础理论需要在产业发展不同领域、不同生产分工位置、不同产业要素配置方式和不同投资效率测值模型等诸多关键环节,形成学理性而且机理性均相对成熟的技术化理论预设和实践可操作方案,并且尽可能使所有这些方案成为行动具证与绩效测值的匹配工具。功能性的知识工具抑或操作工具,乃是文化产业制度对文化产业运行有效的规范化且稳定性的技术支撑条件,因为唯有这些支撑条件,才能确保其作为特定产业形态的增量与拓值。
(四)问题编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核心问题、基本问题以及关联问题,有些问题会在总体边际条件下普遍存在,亦如另外一些问题只在某些具体边际条件下偶然发生,但无论“核心”“基本”“关联”,还是“普遍存在”与“偶然发生”,它们都具有逻辑必然的问题存在属性,因而也就必然会在正负向量两端,与文化产业运行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关系。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尽可能找出这些问题,并且基于问题预期及其更为具体的轻重程度、存在界面和测值维度等,予以问题编序及编序后的知识澄明与揭蔽,从而以理论自觉和产业理论先在优势,抢占问题预期与问题解困的可持续行动优势,由此最大限度地促使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场事态朝正向量发生端递进延伸,而不是相反,尤其不能是盲人摸象的随机事态与无序状态。一个明显的教训就是,由于对投资风险、效益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缺乏风险预期与管控的问题意识,导致相关负面后果在不同范围内频频发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产业理论缺乏的被动后果。
毫无疑问,所议绝非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建设的全称覆盖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良性发展,必然会有更为复杂同时更为深刻的实践解困诉求与知识建构挑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我们矢志不渝地责任担当于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一定能在理论建设与知识进展中啃下那些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因为在现实诉求面前理论无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