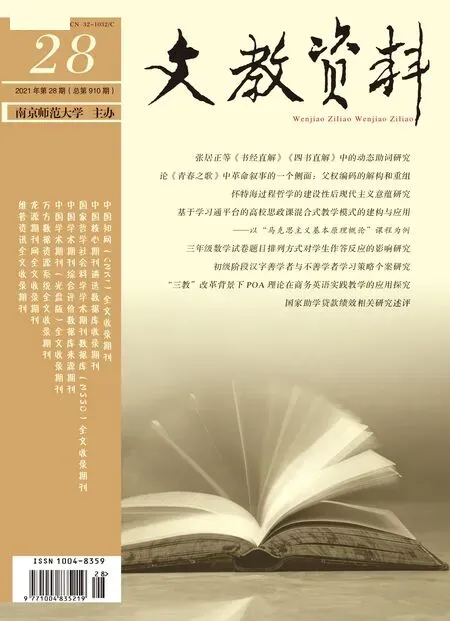论《仁慈的关系》的叙事空间
——兼及与“传统-现代”模式的生成
符 晓 孙 雪
(长春理工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ászló Krаsznаhоrkаi,以下称“拉斯洛”),是匈牙利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当代作家之一。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某次访谈中称他为“当代最富哲学性的小说家”,“能与果戈理和梅尔维尔相提并论的匈牙利启示录大师”[1]。拉斯洛于1954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久洛,《仁慈的关系》(Kegyelmi viszonyok)是拉斯洛1980年代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包括《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理发师的手》《荷曼·猎场看守》《手艺的终结》《茹兹的陷阱》《火》《调台旋钮》以及《最后一条船》。
《仁慈的关系》描绘了中东欧国家人的生活的多个剖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包括但不限于罪犯、理发师、猎人、军官、办公室职员、餐馆女服务生以及公务员等。同时,拉斯洛还以其个性化的语言从不同的主题出发,描绘了许多具有空间意义的文本画面,从中可以看到,在历史性逐渐衰弱、信息破碎的现代社会,时间感在文学作品中渐趋隐匿,以并置为主要特征的空间感的逐渐增强。龙迪勇教授在《空间叙事学》中曾指出:“叙事学研究中必将出现‘空间转向’,这既是叙事理论本身完整性的要求,也是为了适应创作实践的需要。”[2]沿此逻辑,《仁慈的关系》最值得关注的恰是拉斯洛构建的空间,其重要者包括酒馆、交通工具以及家宅等。以空间叙事学的理论为切入点,厘清拉斯洛试图在文本中构建的独特叙事空间及其背后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可以透视出拉斯洛短篇小说更加复杂而隐秘的思想逻辑。
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并置及其叙事学意义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认为“公共领域为公共交往的现代形式铺垫了历史背景”,将公共领域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领域中区别开来。[3]按照这种标准,可以将《仁慈的关系》中的叙事空间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为了解小说的叙事空间设置是如何为人物描写服务的提供了可能,又可以衍生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个概念。私人空间,即小说中人物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而公共空间则是小说中众多人物聚集的公共领域。在《仁慈的关系》中,公共空间包括交通工具和酒馆;而私人空间主要体现为家宅及其变形,即临时避难所。
交通工具是一个作为媒介的公共空间,是《仁慈的关系》中最常出现的空间。一方面,它是一个物理性质上人物行动的媒介,将人物的肉体从一处场所运输到另一处场所。例如《理发师的手》中,汽车只载走了西蒙想要逃离的肉体,并没有载走他的灵魂,乔卡的死在静谧和谐的乡村仍然敲打着他的良知,在这个意义上,汽车是一个物理媒介。另一方面,交通工具作为媒介式的公共空间,也代表着抽象意义上人物心理的趋向。例如,在《茹兹的陷阱》中三人连环跟踪,汽车和火车是形成这个跟踪链的重要组成节点,也是这几个人的肉体跳脱出规则,灵魂追逐过程的重要载体。“我”是一个生活枯燥的办公室职员,某天早晨上班途中在郊区火车站台遇到了的科沃勒斯基。同样,科沃勒斯基乘汽车来到这个火车站台跟踪萨博,火车是他进行自己的“朝圣”之旅的心理媒介。而萨博则沉迷于观察昆虫,为了解开昆虫的叫声中隐藏的自然“信息密码”反复乘火车往返乡村。于是,火车就成为帮助萨博探寻真理之路的指路明灯。
需要说明是,拉斯洛小说中惯用的象征和隐喻手法也常常与他的叙事空间相结合,呈现出更为深厚的哲学意义。比如,《最后一条船》中,那艘“破旧的中型多瑙河游轮”载着战乱后的幸存者,在“夏娃特别行动队”的指挥下离开匈牙利,俨然是基督教末日寓言里的挪亚方舟(Noah’s ark)。根据《圣经》,诺亚方舟并非抽象物,而有具体尺寸,而一艘中型游轮大约三万吨,长度在170米左右,宽度在25米以上,与圣经中记载的挪亚方舟尺寸极其相似。[4]“破烂的木船”作为神赐避难所的象征,带着他们离开战乱后一片废墟的匈牙利,去寻找和平的“橄榄枝”。此外,《荷曼,猎场看守》中荷曼所骑的自行车是整部《仁慈的关系》中唯一一辆为所乘坐的人物所驾驭的交通工具,颇似神化身的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施行救赎骑的驴,其中卑微的感觉也与《圣经》如出一辙,这种象征手法在《撒旦探戈》中也常常出现,成为拉斯洛的艺术特征之一。
《仁慈的关系》中另一类不容忽视的公共空间是酒馆。酒馆是拉斯洛小说中惯用的空间之一,《撒旦探戈》中村民时常聚集的村庄酒馆,《最后的狼》中“我”对酒保倾吐故事的德国街头酒吧,都是重要的空间场域。拉斯洛的酒馆是绝对理性和绝对秩序的破坏者,是人类精神堕落、肉体享乐的场所。例如,在《仁慈的关系》中,《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是一场通宵狂欢后的宿醉游荡;《理发师的手》的大鼓酒馆催生西蒙内心的恶念。酒馆成为一个现代人逃避生活逃避人生的欢乐乡,是表达具有抽象意义的非理性和去秩序的具体场域。酒馆作为空间的另一种特征是作为人与自身关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掩体”,酒馆通过其自身的号召性聚集人群;酒保站在吧台内向人们提供酒精的麻醉并窥探酒馆中人们的隐私。《茹兹的陷阱》中,酒精发挥着作用,使得女厨师变成窥探人类隐私的魔鬼。这说明酒馆已经具有非常深刻的公共空间意义。
与公共空间相对应的私人空间,是市民日常生活的私密场所。私人空间在《仁慈的关系》中传统空间在《仁慈的关系》里主要体现为家宅,其重要的功能是庇护所。《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中,“我”在宿醉后几经周折甩掉了埃勒·博格达诺维奇,心中只想回家,家宅成为逃避城市的混乱,安慰心灵的场所。加斯东·巴什拉认为,“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6]作为庇护所,家宅具有“地窖-阁楼”的双重性,在幸福幻想之外,还具有给人以恐惧感的特质。《手艺的终结》中,家宅被比作“母亲”, 玛丽埃塔的母亲在那“汇聚她的出生和即将到来的解脱的纹路”家宅中的死亡,象征着玛丽埃塔作为“性倒错的尝试”青年中的一员,出生的庇护所以及道德伦理感的消失。基于“家宅具备人体的生理和道德能量”。[5]这种安全感和母亲形象,使得家宅成为人们同外界危险做斗争的保护神。
可以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是拉斯洛小说空间的功能性划分,通过对不同空间的公共或私人属性特征的描写,拉斯洛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并且为他们的活动以及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具体场所。而在这些具体的空间表征之外,更大的社会空间单位以其本身具备的特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相应的空间模式。
二、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及“乡村-城市”模式的形成
作为公共空间的交通工具、酒馆,与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宅和避难所具备的私人或公共属性塑造了拉斯洛早期短篇小说的叙事空间样态。由此推及,可以发现《仁慈的关系》深处所蕴含的更加深广的叙事空间,即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实际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背后隐藏着的是地理区域,这些地理区域以人居住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划分,可分为大城市、小城市、郊区、小镇、村子以及森林。其空间设置不是拉斯洛的终点而是一个基点,他将这些空间设置在更广维的可以被称为“乡村-城市”模式的空间之内。“乡村”包括文本中的小镇、村子、森林,“城市”包括大城市、小城市以及郊区,交通工具起到连接乡村和城市的功能,人们依靠交通工具来进行乡村和城市间的转换游移。这也解释前述交通工具成为重要叙事空间的原因,
从具体文本中可以看出小说中乡村和城市空间的差异。第一,小说中乡村空间人们少量聚居,而城市空间则密集拥挤。例如《茹兹的陷阱》中萨博居住的是二层小楼,其所在的街区具有“明显解脱感的空旷”,而大都市的人们则大多生活在公寓中,如《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中“我”的公寓,以及《理发师的手》中乔卡在小城中的公寓。乡村空间中,人们由于密度低,因此大多住在自己的独栋房屋内,在土地上呈扁平分布。而城市空间中,人口密度变大,居住地成了竖直的公寓楼。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大都市中的家宅对私人空间进行了相应的压缩。在愈繁华的都市,人们愈加失去自己的小天地,陷于高楼大厦的“盒子”当中。[6]这种“盒子”便是现代城市对于人肉体的挤压。
第二,小说中乡村空间的人与人的距离更近,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稳定;而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之间则充满着冷漠和审视,节奏快速狂乱。例如《理发师的手》中主动与西蒙进行对话的酒馆老板娘和理发师,他们并没有因为西蒙的蓬头垢面去避开他,而是主动询问西蒙的状况。而城市中的大鼓酒馆,则充满着“目光短浅、视若无睹的人群”。又如,《理发师的手》中所描绘的村子是“安静、睡意沉沉”的,而《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中大都市则充满着车流、人群以及酒吧的“午夜狂欢”。在拉斯洛看来,现代城市中人们的工作占据了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它那狂乱的节奏把人们卷入漩涡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放松,压抑之下变得冷漠。同时,城市中人们的私人空间无时无刻都在被压缩、侵占,这就导致了冷漠视线的溢出,即对他人的审视。
第三,乡村空间的人性是原始的,城市空间的人性是扭曲的。例如《调台旋钮》中那些脸上泛着“羔羊”般红晕的热情学生,对着冷漠内向的老师依旧热情洋溢。乡村空间人性情感的表达,方式是直接的,内容是赤诚的。而城市空间则不同,在消弭的私人空间的挤压下,人性是变形扭曲的,情感是堕落赤裸的。《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中因为“令人生厌的午夜狂欢”而宿醉街头的二人,在林立的高楼下游荡,仿佛被剥夺了灵魂,如同行尸走肉。城市的居民已经是被现代社会异化的最无序的狂欢人群,他们的肉体空间在现代城市被无限压缩,导致精神上的扭曲变异,被裹挟到现代城市的迷狂荒诞之中。《手艺的终结》中的青年军官们靠酒精、毒品、滥交来麻痹自己无法面对混乱现实的神经,用私人的混乱来将自己与现代社会公共的混乱所隔离开来,以逃避来面对颠覆。
综上,城市空间以资本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改造,和转瞬即逝的震撼来体现其割裂的外在表征,带来的是一种“超验的无家可归感”。而乡村空间则充满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文化之间的原始联系。二者之间的不同,被乘坐交通工具联系这两类空间的人物活动赋予了张力,从而形成“乡村-城市”的模式。这一模式是人类找寻灵魂安居之所的行动表征,超脱了物理意义上的移动和地域空间,承载着城市中的人们试图逃离城市空间的愿望,使人们去往乡村寻找寄托灵魂的归处。
三、空间诗学与拉斯洛的“传统-现代”二元观念
通过对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呈现,拉斯洛建构了“乡村-城市”模式,之所以要建构这种模式,是因为“乡村-城市”模式背后隐藏着作者需要表达的诸多问题。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将家宅放置在乡村和城市之中加以讨论,这二者之间的社会张力给予了具体空间以独特的意义。[7]在拉斯洛1980年代的小说中,几乎都存在着这种乡村和城市关系模式,也成为拉斯洛的文学创作标签。如果深入探讨拉斯洛早期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会发现乡村是古典的象征,而城市则是现代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乡村-城市”模式甚至可以成为“古典-现代”的具象投影。
首先,《仁慈的关系》的城市都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现代属性。这种现代属性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都市”体验层面,本雅明认为,对城市空间最大的现代性体验来自于人从都市生活的多重意象中获得的异化。[8]在《仁慈的关系》中,异化体现为肉体和精神的麻木,如《茹兹的陷阱》中,办公室职员“我”的眼里,首都是拥挤的列车、枯燥的办公室工作、以及令人恐惧的领导。“我”每天的行程准确到分钟,只为了走上那个有着集中营标语的火车站台,开始重复性的工作,“相信反抗已毫无意义”[9],这些人物形象就像是波德莱尔描写的在巴黎拱廊街厮混的“浪荡子”形象。拉斯洛在文中将多个空间并置,制造出一种大城市独有的瞬间和片刻体验,城市发展中技术爆炸性对人的刺激,使得城市中的人们迷失在交错的行人、街道、车流之中,体会到一种超验的无家可归感,成为城市中的游荡者或永远的“奥德修斯”。拉斯洛所描述的城市体验和波德莱尔一样,都强调都市中的游荡者,实际上暴露了西方现代性危机,其本质是一种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这也恰恰迎合了尼采关于现代性的主张:虚无主义是启蒙现代性本质的界定,它是对存在的遗忘。都市中的游荡者终其一生都是在追问人的存在意义,而在这种追寻最高存在的过程中,遗忘了存在的本身。[10]
其次,与城市相对,拉斯洛笔下的乡村则具有某种古典属性。所谓“古典”,并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也不是17世纪法国文学艺术的“古典主义”,而是某种具有朴素意义的“往昔”。[11]拉斯洛笔下乡村的人们似乎更接近于人类幼儿的状态,在慢节奏的日常生活中掌握了稚拙和赤诚的情感,也在和自然亲密接触的劳作中获得了生活的真实感。因此,拉斯洛笔下的乡村是古典的象征。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访谈中,拉斯洛曾表示,当他时隔多年回到他出生的那个久洛小村的时候,他关于这个古典村庄的一切记忆都被现代性抹消了。拉斯洛说,从这样的久洛身上,他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失落感。[12]因此,他在创作之中刻意去描绘乡村,寻找失落的记忆。
归结起来,这种二元模式的生成是匈牙利文学传统和拉斯洛本人情结共同塑造的结果。一方面,拉斯洛的这种“装置”设计顺应了匈牙利文学的传统。20世纪匈牙利文学中存在很多关于乡村的文学叙述和文学史叙事,沙布·德若、多保耶·伊姆雷、沙尔柯蒂·伊姆雷和瑟尔伯·昂托等人的小说都集中讨论乡村问题,并且在乡村叙事中呈现出如拉斯洛一样的古典属性。民粹派代表作家沙布·德若赋予建立在宗法制之上的匈牙利农村以正面意义;多保耶·伊姆雷的《春天的风》题材都取自农村书写乡村的朴实生活。此外,匈牙利很多作家也存在“厚古薄今”的倾向,如在《月光下的旅人》中,“匈牙利是现代的象征,意大利是传统的象征”[13],所以主人公向往以意大利为中心的西欧,也就是对古典的某种礼赞。另一方面,拉斯洛本人对乡村有一种深刻的情结。拉斯洛本人长期居住在匈牙利北部一个名为乔班考的村庄中,常居一间古老的石头房子,并在这里获得了《撒旦探戈》的创作灵感[14],在《撒旦探戈》中,城市的美好仅存在于村民的美好幻想中,而现实中的城市却常常与爆炸、废墟与冷酷联系到一起。可以说,在个人情感上,拉斯洛是偏向乡村的,而这种情感的表达,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现代性批判意识。
因此,拉斯洛的审美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复古倾向的批判现代性。《仁慈的关系》把重心放在乡村和城市、古典和现代的关系的探讨上,通过描写被现代性异化的人们从回归乡土获得精神救赎的过程,来表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典型问题,乡村在拉斯洛的笔下无异于真理的启示,现实的寓言。人们在乡村的朴实自然中获得了城市的光鲜亮丽所不能给予的,灵魂真正存在的感受。有学者认为审美现代性具有世俗的救赎功能,即艺术将人们从日常的千篇一律中拯救出来的救赎。 从回归中得到救赎是拉斯洛小说中重要的一点,他看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危机导致人们产生的虚无主义倾向,并认为对于自然乡村的回归是治愈这种现代社会存在主义病症的主要解药。《仁慈的关系》通过叙事空间的设置,描写人类的生存状态,从而揭露并探讨了东欧人普遍的精神困境。这种探讨长久以来存在于匈牙利文学传统之中,但拉斯洛的价值是在继承民族遗传的同时,用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和文本架构,对这种精神困境进行了一次存在主义意味上的现实解剖。
——《日用家当》中“家宅”的心理几何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