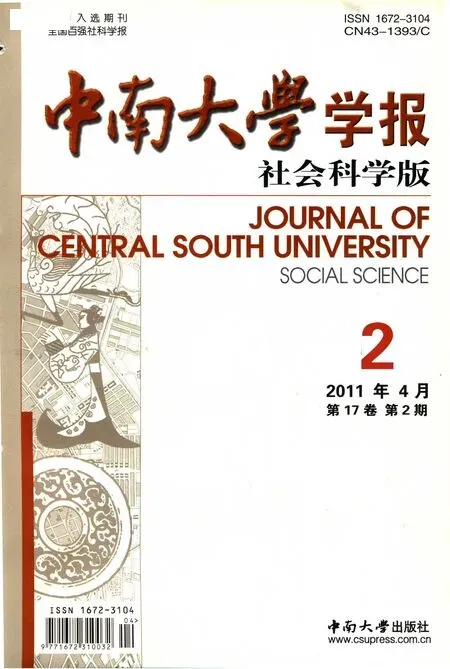空间格义背后的举意与旁观
——《日用家当》中“家宅”的心理几何图解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空间格义背后的举意与旁观
——《日用家当》中“家宅”的心理几何图解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在爱丽丝·沃克的短篇小说《日用家当》中,家宅被赋予了一定的格义属性,这可以被视为19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语境中的心理现象学介入。家宅格义背后的心理图解划清了个体“生存空间”的原型与流变,洋溢着深切的心理几何假设内涵。作者借助不同人物对于家宅的写实性解读,提供了一个富有曲面内涵的边缘记忆空间,揭示了主体的物我元一思想已然深植于家宅意象当中,并以拓扑图腾的同胚形式得以彰显。家宅的心理几何图解立体地刻画了个体在生存空间日渐缩限时的困顿与挣扎,更是直指个体守护本我世界时的一种精神重估,而这正是该部文学作品所隐含的原生代性旨归所在。
空间格义;《日用家当》;家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心理现象学
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 是一位近年来在美国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黑人女作家,可以同托尼*莫里森齐名比肩。从大学时代开始,沃克就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当中,这一志向直到她毕业之后仍旧丝毫未变。沃克曾是黑人妇女运动的喉舌《女士》杂志的编辑,她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种族平等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作为美国当代黑人文学的领军人物,她的作品题材广泛,主题深刻,并且以描写黑人妇女的命运见长。在小说创作中,沃克善于把深受白人社会和黑人社会男性双重压迫的黑人妇女作为女主人公,在表达对她们的同情的同时,也传达出她愤世嫉俗的战斗精神。她的作品除了代表作《紫色》之外,收录在《爱情与困惑:黑人妇女的故事》(1973)中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日用家当》同样深受评论家的关注。该短篇小说以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风起云涌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为背景。在《日用家当》中,作者宏观上以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与冲突为大背景,微观上却关注美国普通黑人家庭内部女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
国内外的学者长期以来对于该部小说的文学主题认识趋于一致:赞扬母亲和麦姬是黑人文化传统和种族身份的守护神,谴责迪伊是本族文化传统的叛逆者[1](11)。十分有趣的是,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小说中“被子”的文学意蕴,“两床祖传的被子凝聚着美国黑人的集体智慧,是黑人传统文化遗产的象征,也是黑人美学价值观的具体体现”[2](56)。但是细致揣摩小说文本,发现“家宅”这个意象同样值得深究。从小说建构来看,家宅是《日用家当》中的核心意象之一——它出现在小说的所有关键部分,并且颇具高频性。从主题烘托来看,家宅也是母亲和麦姬对抗迪伊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侵蚀与反噬的掩体。可以说,家宅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黑人世界存在的历史坚实性与抗同化性品格。因此,如果说《日用家当》是一部富含象征意义的小说的话,家宅的象征内涵发掘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然而,这一点却被莫名地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心理现象学视角入手分析个体与家宅之间的几何与超几何关系,并进一步介入家宅空间格义背后的立体投影,展示个体在家宅曲面内涵当中所包孕的边缘记忆,从而准确刻画家宅的拓扑图腾背后被悬置的物我元一图景。
一、空间格义:家宅的立体投影介入
《日用家当》中的家宅从一开始就被置于空间格义范式当中,并且这一点可以回溯到家宅的历史变迁本身当中。小说开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所由房子和小院子组成的家宅。这是在一场大火之后全家人“倾其所有”而建造的另一处居所,除了房顶是用铁皮敲成的之外,其他地方与被烧毁的旧房子并无分别。家宅所进行的结构改造不但体现出自我本身的不断占有与被占有;同时由于新增的铁皮,新建的家宅又是对旧式家宅自我本身的变幻式远离。借助家宅建构的原型相似性与几何格义性[3](22),新建的家宅完成与旧式家宅的全息式互现与表征。在小说当中,新建的家宅之上可以看到旧式家宅的投影,因为家宅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过去投影的世界。更为有趣的是,旧时的回忆在那时比在此时还要古老许多,因为对于新生代的黑人来说,家宅的底片价值已经流失殆尽。例如,在迪伊的眼中,家宅代表的是腐朽与没落;在母亲和麦姬的眼中,家宅却是温馨与归属的代名词。同一个物件在不同人的眼里变幻出的是不同的特点,就如同投影随着视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幻一样,这一点也不稀奇。但让人赞叹的是,黑人母女“越来越窄小,但却历久弥新”的悖论式生存境遇以及其间掺杂的纠结与超脱却在家宅背景中得以完美体现,而这显然离不开家宅在个体心理空间中的投影差异。随着迪伊位移速度和频率的加快,以封闭、内敛、缓慢、寂静为特征的乡村生活整体性断裂了[4](125),在迪伊看来,母亲和妹妹所珍视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而对于母女而言,未曾离开半步的家宅却是值得坚守的故土与精神家园。此时,家宅与外面新世界的对抗中是否会获得自己的胜利这一假设命题的证明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家宅与个体的固守共同体中,在传统家宅和新鲜事物的对峙中,唯有跳出单纯几何形式的牵绊,转而切入格义所激活的立体投影空间,才能准确地描摹个体的胜利。
家宅的空间格义属性直接旨归主人公生活的现实性,因为那里有主人公出生、存在与生活过的痕迹。与此同时,家宅的空间格式属性又间接地激活了家宅的非现实性,具体表现为灵性个体不应该也不可能囿于家宅的物理属性当中,否则个体将沦落为失去社会文化传统的动物。通过引入非现实性元素,家宅的立体投影旨在将物理学家于普通的生理活动中所发现的行为矛盾封闭——家宅所象征的传统在时空面前可以跳出衰老与破败的轮回,而是走向历久弥新的般若之境。正是在家宅的这种现实与非现实的错杂投影当中,主人公游走于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变迁当中。这正好验证了“人的生存是在空间中的生存,所以人对于空间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4](134)这句话。由此,通过详细考察家宅中个体的自我生命节奏,就可以建立基于家宅空间格义基础之上的个体分析。当我们从紧缩而又压抑的家宅转移到膨胀而又宽释的家宅,从而对节奏的分析敏感的时候[4],这种呼声就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回荡起来。
家宅的空间格义特性还体现在它的超现实性当中。借助于格义的边界效应[5](17),古老的家宅成为传统印象的栖身之所,这比外面的花花世界更为安全静谐。空间格义当中,家宅的传统价值显示出充分的人性底蕴,特别是在空间格义的框定下,这一价值冲突变得异常猛烈。此时,家宅的立体投影关指的不再仅是一个关于“存在”抑或“存活”的问题,而是关于维系自我存在能量的思考以及关于反对自我存在的能量的对抗的问题[4](136),这就是家宅的超现实性所在。确切地说,外化式的场所格义可以通过规定家宅的对象性来细化其内涵的投射效果,因此家宅不再是一个静态的箱子,而演化为一个“芥子纳须弥”的神奇魔方,在那里居住的空间范畴超越了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值域。尤为重要的是,这里新旧事物之间存在的矛盾与斗争结果最终将取决于家宅的空间格义价值的投影。也正是在家宅的格义化投影当中,我们看到家宅演化为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交界处的敏感标识,它能够准确地考量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抑或抵触程度。也正是在这样的考量当中,黑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黑人性”(Blackness)——才能得以充分显映。空间几何元素分析对于文学作品批评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从空间格义的角度出发,通过审视家宅与主人公生存空间的关联,不但扩充了小说主题载体的现象学内涵,同时也揭示了“家宅”与“日用家当”之间上下义关联背后的心理学用意。这一点在家宅的曲面内涵与边缘记忆的关系上体现得更为明晰。
二、边缘记忆:家宅的曲面内涵萃取
小说中的家宅里面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外面的风是永远吹不到里面去的。小小的院子是唯一让家人感到舒适的地方,母亲幽默地说打扫干净以后就像“向外延伸的客厅”。这是小说对于家宅的延展性最为直白的交代。换言之,家宅具备随着个体心识的扩张而表现出弹性伸缩的能力。个体若要安“心”于家宅之内,就需要一个“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破”的禅境思维。心识之力使得家宅在空间中如花绽放,因此其空间显现出无尽的延展。这里的家宅就是世界,它与自然浑然一体并超越了几何学意义上的人工雕琢与浮泛划界。借助心识之力,非现实性内涵却被赋予很强的现实性形象,这就使得我们进入了小说的心理学现象学发掘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家宅的几何性并非棱角分明,它隐藏着些许曲面,而曲面背后的内涵阐释则是小说美学发掘的重中之重,毕竟文学作品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距离控制而显得言未尽意[6](23)。表面上看,主人公似乎在家宅的曲面里治疗幽闭症,这在笨拙的麦姬身上似乎体现得最为直观。然而,对于这种有关自我存在空间的思考来说,这种类似自欺欺人的“嫁接”却是极其重要的——它建构了本体对立的生存标记,释放了小说中个体内心久被封印的边缘记忆。在读者自己很可能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这些对立使得一些重要的原型活动起来:现实与虚拟、平面与曲面、思想与梦想、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种种强烈矛盾将读者从单一概念的迷梦中惊醒,并将读者从实用性的几何学中解放出来,从而更为切身地去体会小说主人公被边缘化的社会境遇——家宅是黑人女性在残酷的劣势文化环境下精心营造的家园,是她们痛苦生活的见证,是她们情感的寄托,是庇护她们的精神归宿,也是沿袭守护遍体伤痕的黑人传统文化的阵地。可以说,家宅在小说中经历了格义化处理,并被赋予了丰富的边缘性记忆内涵。
当母亲和麦姬幸福地生活在当下家宅中时,尘封的记忆便已然开始获得了活生生的存在可能性。这是因为主人公的记忆当中塞满了“他者”视野之下的体验事实,并渗透于家宅新旧模样的无形比对当中。如果她们在记忆中剔除了幻想而以边缘回忆的准确收集为目的,那么消失在时间的立体投影里的家宅就会从曲面中一点一点地得以复现。并且,这种记忆根本无需人为地将其重新组合,因为它缘起于个体的内心空间[4](137),并在个体生活的温馨体验中完成浴火涅槃。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一种空间的融合感,过去与现在的印象对比是那么深刻。对于新生代黑人女性而言,家宅已经沦为不现实的乌托梦影,她们至多偶而沉浸于一段被剥脱了具体日期的过去当中,出生家宅的清晰印象在其内心已经悄然失色。于是,家宅的曲面内涵因为她们的“识时务”而被变相湮没,转而出现的是阿Q精神胜利法般的自我暗示——家宅已不再是根之所在。而对于固守自我传统的黑人女性来说,回忆的现实性却显得那么伸手可及。与新生代同伴对比的增多使得家宅的曲面内涵价值都生动起来。家宅的中心性体验是叛离者与守护者之间分野的标尺,就像处女的守宫砂一样清晰。这就决定了现实与幻想的复合体从来得不到确定的化解,因此迪伊的出走并非偶然。同样,母亲和麦姬固守内心空间的温柔质料进而重新找回家宅的归属感也就可以理解,因为家宅即使在它开始以人性的方式生活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失去其“对象性”。由此,就可以描绘出这些旧日的家宅,从而呈现出一个具有所有实物复制品特征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宅刻下了一部传奇,尽管它掩映在自我的曲面阴影里。
到了小说的结尾,迪伊走了,剩下了母亲和小女儿麦姬。迪伊还要走自己的路;母亲和麦姬也会和往常一样坐在院子里,和着微风慢慢地品尝着草莓酱直到天黑,小院还是她们守护传统的依靠,那里包孕的是自我身份认同的最佳时空节点。但是,在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雨之后,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萦绕不去——家宅曲面内涵中的边缘记忆还能像这样持续多久?如果说家宅的各种不同特征之间的辩证法可能会打破家宅原型感知的同一性,那么还是让原型之间的分歧掩盖在家宅的曲面当中较好。毕竟,边缘记忆所附带的自我撕裂疼痛压合于无形当中才是最为隐匿、最为体面的,尽管这样可能更疼。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隐性启发动力,读者可以走得更远,思辨得更深,进而去解读家宅的高度如何被折叠在固定的再现当中[4](141)。当读者将其展开、予以延展性解读时,家宅就从纯粹的现象学角度呈现本体,而这正是家宅的曲面内涵所在。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一切意向性的对象化、主体间性和想象力的自由变更,无不是以这种自我极的能动性作为前提才得以可能的”[7](9)。
三、物我元一:家宅的拓扑图腾同胚
诚如弥撒经中的一句箴言所说“花儿总在种子里”,家宅就可以被看作是简化了的庇护所在内心空间的紧密压缩[4](142)。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宅可以被看作是拓扑变换的本体与载体。据此,家宅的简化感知就可以看作是寄居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函数,前者因个体境遇不同而发生变异性投射。家宅的心理现实性是基于具有现实基础的准事实构成的,并有其自身的虚拟结构与边界。因此,家宅完全有资格担当物我元一的拓扑图腾。在家宅的心理几何分析当中,只需要确定拓扑变换下的同胚变形(homeomorphism)[8](11),找到转换中“恒量”得以继承的轨迹,我们就能在特定时刻标明个体的一切可能有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所有路径,而这恰好是深陷“白人文化”与“男权主义”双重囹圄中的黑人女性当下处境的准确刻画。在单纯的心理学范畴之内,家宅强化了居住的幸福感;在复杂的心理学范畴当中,家宅却蜕变为“自由是束缚”。但不管怎样,家宅的拓扑分析都可以锁定寄居个体的一种灵魂状态。确切地说,即使家宅的外表被改造,它还是表达着内心的空间——小说中的房子虽然历经修复,但在母女看来依然光鲜。在她们眼里的家宅是活生生,具有灵动性的拓扑图腾。
细微差别并不是起着补充性的表面角色。没有居住经验的人只会刻画出家宅的现实,却没有真正体验过它的原初性,虽然这种原初性属于每个居住者,只要他愿意固守自己的根。然而,深谙世事的辩证法早已剥脱了家宅在新生代眼中的原初价值,个体与自我传统的关系在异化一代的生活里是如此的疏离,以至于她们(小说中的迪伊)不再感受到自己对于家宅的原初依恋。她们迫不及待地逃离扎根于“世界一角”的厄运。对于那些固守者来说,家宅的居住价值在于它是一个保护着自我的非我。这里将看到心识用无形的阴影建造起墙壁,用受保护的形变来自我安慰(小说中的母亲),或则相反,在厚厚的墙壁背后颤抖,不信赖最坚固的壁垒(小说中的麦姬)。在同胚变形求索当中,我们就可以触摸到家宅的全部拓扑弹性——家宅减少了个体遭遇危险的概率;家宅减少了不幸经历后的负性连锁反应,提供一个有所慰藉的港湾;家宅重新培育提高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家宅为个体指出正面的机会,这能帮助他们产生希望和获取成功的资源。也正是因为如此,家宅在许多无处怀疑的深处感动着我们。显然,这里的家宅具有了“去社会化”的特点,特别是在自我蜕变将到临界点时,这里的思考巧妙地推举出家宅空间中的拓扑哲学。正是在衡量这些细微之处当中,我们验证了家宅的心理学假设,因为细节往往是魔鬼的栖身之所。
新生代居住的家宅已经让家宅平常化了,其原初价值已经降格。因此在迪伊历经流浪后回到老宅,眼睛不再能够捕捉到原初的细微,最初的动作不会突然鲜活起来,取而代之的却是攻击与蔑视。家宅价值的主题变奏喧宾夺主地取代了简易而走向浮华。家宅被复杂化处理成一个失语的存在,传统的神圣光晕在斑驳的装饰中显得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家宅被想象成一个破败的存在,它不再唤起新生代的图腾意识,尽管新生代的潜意识还保留了对于家宅认同的一点点心理羡余。例如,迪伊拍照的时候总是想把屋子扩进去,但她对此浑然不觉。其背后的原因可以看作是原代生性使然的结果。黑尔德认为,原代生性是一个起点,通过它才可能进入到陌生世界之中。因此,原生代性成为个体之间相互认同的第一性图腾。然而,小说中的迪伊和麦姬在这一理据上已然出现彼此偏离。至于哪一方最终会完成物我元一的修炼,其答案不言而喻——失去了根的个体很快就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又何谈知晓去往何方?家宅的拓扑图腾分析表明,物我元一境界的出现往往需要个体顺利地带进自己的心理假设。诚如佛语所云,“一相三昧,一心专志,既至彼国”。小说中最后母亲和麦姬的惬意就是物我元一的表现,此间的心理假设就是一心专志、不离不弃。
四、结语
《日用家当》这部小说的主题载体可能并不唯一,以往大多数研究将视点聚焦于“百纳被”上就是一例,这与小说本身的副文本性[9](408)不无关联。但是,小说的美学阐释要求更为开阔的分析向度,因为关注视点的同质化倾向都会导致简单化的错误,进而剥夺文学作品的立体美感与充实内涵。因此,小说的具体研究需要仔细甄别基础上的主题分析视点的转换。本文从现象学视阈阐释了《日用家当》中家宅意象的心理几何内涵,发现家宅在经历了空间格义之后,其立体投影中掩映着个体的物理困境与纠结之路。同时,家宅作为个体生存空间的曲面,其内涵在于揭示个体的思想性顿悟与超脱,这又与家宅的拓扑图腾属性密切相关,并直接关指个体存在的“物我元一”诉求。《日用家当》作为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还有很多深层的东西值得进一步玩味与剖析。最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读者,这是小说价值大小的直观写照,同时也是家宅意象的心理几何属性剖析的现实必要性写照。诚如M·扎贝尔所说,“从根本说来,伟大小说的目的并不是批评的、思辨的、辩证的,或专注于细微的鉴别,而在于其抓住并体现出心灵的价值、本能和直觉的共鸣的价值……”[10](97)。小说《日用家当》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称之为经典绝对当之无愧。
[1] 张瑛. 艾丽丝·沃克<日用家当>中的人物解读[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 (5): 11−14.
[2] 赵艺红. <日用家当>的多维度象征意义探析[J]. 东疆学刊,2009, (1): 55−59.
[3] 倪梁康. 交互文化理解中的“格义”现象——一个交互文化史的和现象学的分析[J]. 浙江学刊, 1998, (2): 22−28.
[4]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5] 白欲晓. “格义”与中国哲学的“致曲”之路——研究者的“自觉”与“选择”[J]. 福建论坛, 2010, (2): 17−19.
[6] W. C. 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华明, 胡苏晓, 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7] 邓晓芒. 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1): 5−12.
[8] 库尔特·勒温. 拓扑心理学原理[M]. 竺培梁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9]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holders of Interpretation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08.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R·雷德·哈代的长篇小说的形式[C]//陈焘宇. 哈代创作论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61.
Abstract:House has been assigned with a certain Ko-yi characteristics in Everyday Use by Alice Walker, which can be deemed as a psychological and phenomenological intrusion into feminist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 psychological diagram behind Ko-yi of house delineates a clear cut between prototype and variants of the individual’s living space, where lies a hypothesis of psychological geometry.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house present a periphralized memory space with curving connotation, which means the nature-and-nurture dilemma is a part of house in the form of homeomorphism.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house geometry ends up with a vivid picture of complexes and struggles of the individual suffering from narrowing down of living space, pointing at a spiritual re-evaluation of ego at risk, which is the hard core of Urgenerativitat in the novel.
Key Words:spatial Ko-yi; Everyday Use; house; psychological geometrical diagram; feministic criticism; psycholphenomenology
Vowing and watching behind spatial Ko-yi: On the psychological geometrical diagram of the “House” in Everyday Use
MAO Yanshe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I106.4
A
1672-3104(2011)02−0142−05
2010−09−01;
2011−01−24
201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00481032)
毛延生(1980−),男,黑龙江大庆人,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副教授,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文学语用学.
[编辑: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