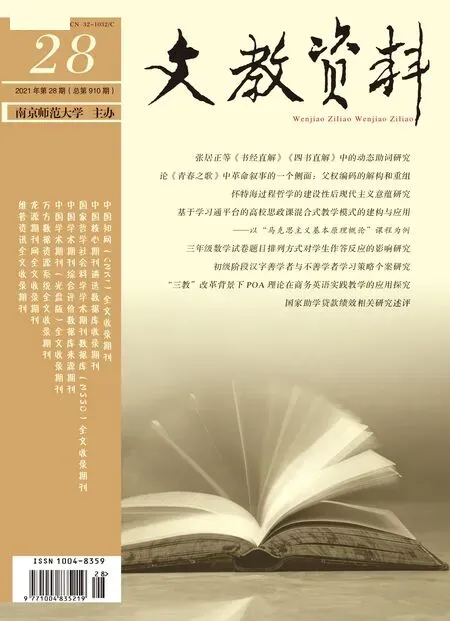语言文化视角下李白《静夜思》中“床”义辨析及文本解读
顾劲松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江苏 淮安 223003)
李白的《静夜思》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千百年来备受世人称颂。全诗仅短短4句20字,却以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之笔,平实地描述了月华如霜的静夜之景,巧妙地传达了远游之客的浓浓月下乡愁。
时过境迁,如何精准地理解、把握这首诗的文本内容,历来人们莫衷一是。特别是其中的“床”究竟指何物,可谓众说纷纭。缘于时下“床”的常见形制和基本功能,一般多认为这里的“床”是一种卧具。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人提出新看法。学界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① 卧具说,颜春峰、汪少华(1998)[1],陆业龙(2001)[2]等人持此观点;② 坐具说,持本说法的主要有刘国成(1984)[3]、蔺瑞生(2017)[4]等人;③ 坐卧具说,赞同这一说法的,主要有乔松(1985)[5]、范慧琴(2009)[6]等人;④ 井栏说,朱鉴珉(1985)[7]、王晓祥(1986)[8]等人认可此说。
然而,这几种观点都有可争议之处。鉴于此,我们从读者集中的困惑和普遍的质疑出发,厘清本诗中“床”的本来面目,侧重从语言文化视角,结合作者写作背景,以期对这首诗进行相对合理的解读。
一、读者的共同困惑
(一)主人公的空间位置
《静夜思》文本中“床”为卧具,这是比较传统的看法,向来赞成者甚多。根据这首诗本身意境,既然“床”是卧具,那么当为供人躺卧、休息和睡眠之用,理应放在室内,所以主人公也应在室内。不过这样就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假如是在室内,很难“床前明月光”。室内见到月光,按理说要么是屋子无顶,月光不受遮挡,直接照进来,显然不可能。要么就是窗户大,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并洒落床前,这一说也难以立足,因为唐代普通房屋窗户皆不大,月光照进屋内概率很小。第二,假如是初升之月或将落之月,月光确有可能勉强照进来,却又与“举头望明月”产生矛盾。月亮在低空,月光近乎平射,根本无须“举”头望月。第三,就算主人公是在室内,且月光确实洒落床前,但霜露正常应当不会降在室内,故主人公“疑是地上霜”很牵强。“按生活常理,只有在可能下霜的地方,人才会联想到霜。”[9]
如此推理,主人公空间位置不是室内。就这一点,“床”的坐具说、井栏说则较好地解决了相关问题。坐具说认为“床”乃安坐之具,则不排除是在室外;井栏说因为井栏本身就在室外,故主人公不会在室内。
(二)主人公身姿体态
诗中对“床”的理解不同,主人公身姿、体态自然不同。这样难免引起众人思考:主人公究竟是躺卧于床,安坐于床,还是站立或行走于床前?
若赞同“床”的卧具说,则主人公躺卧于床;若认可“床”的坐卧具说,主人公可能阶段性地躺卧于床,那么总体上应该是头部平放、仰面直视屋顶之态势。这样一来主人公调整视角就极为不便,只能勉强左右转头,“举头望月”和“低头思乡”都会异常困难。据此,主人公不该是躺卧在床,更可能是坐立或站立。
若支持“床”的坐具说,则主人公是安坐于床;若坚持“床”的坐卧具说,则主人公可能阶段性地坐立;若坚持“床”的井栏说,则主人公是站立或行走于床前,主人公确实容易抬头、平视、低头。然而,主人公“举头望月”依然困难,因为“举”本来就是将某物由低处转移到高处,位置上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而从本诗来看,无论是坐在“床”上,还是站在“床”边,主人公都没有由低到高的起立动作,“举头望月”不合情理。
二、问题破解思路
基于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主人公是在室外,故“床”的卧具说不成立;第二,主人公并非躺卧,这进一步否定了“床”的卧具说,也不是安坐或站立,而是有一个起立过程,故“床”的坐具说、坐卧具说、井栏说皆难以立足。那么,“床”究竟应该如何解读?
(一)“床”的本义及方言义
“床”本是“牀”的俗体,“牀”才是正体。《说文解字》:“牀,从木,爿(chuáng)声。”[10]从造字法看,剖木为两半,左为“爿”,右为“片”。“爿”本为几,其横向字形很像“几”之外形,本义为“几”形器具,原为“牀”的初文,为象形字。商代后期,汉字竖向直行排列法确立,很多字改变了字形方向。“爿”字写法由横向改成竖向,“几”的字形与实物“几”的外形差距拉大,其本义也有一定磨损,于是人们就在“几”的基础上加注义符“木”,强化“几”的质地本为木,故写成“牀”,从此变成了形声字。《说文解字》中“爿”字失收,不过在士部“壮”、羊部“牂”、啬部“墙”、犬部“状”、戈部“戕”、斤部“斨”、酉部“酱”及木部“牀”等字下皆云“爿声”,女部“妆”下云“牀省声”,其实,诸字均为从“爿(牀)声”。今“爿(pán)”乃“片”字的反写,与“爿(chuáng)”字同形字,义音皆不同。后来,“牀”俗书改“爿”为“广(yǎn)”,写作“床”,又由从木爿声的形声字变成从广从木的会意字。《玉篇》:“床,俗牀字。”[11]到现代汉语阶段,汉字规范化以后,“牀”作为异体字并入了“床”字。
普通话中卧具是“床”的基本义。在方言中,卧具义也是“床”相对常见义。“床”的坐具义在晋语中有所体现,忻州话谓板凳为“床子”[12],万荣话特指木制低矮的小凳子为“床床”[13]。平遥话、文水话、祁县话称普通小凳子为“床床”,清徐话、武乡话称小板凳为“床床”,运城话称小板凳为“板床”,盂县称小板凳为“床子”。[14]晋语区恰恰是汉魏之际北方“胡床”传入中原的前哨,故较多保留“床”的坐具义。“床”字原初的“几”形器具义较多保留在闽语当中,比如广东汕头、潮州、揭阳、海康、中山隆都,福建莆田、仙游等地就称“桌子”“台子”为“床”。[15]在雷州和海口闽语中,“床”既可指卧具,也可指桌子。雷州话需根据上下文判断是睡床还是桌子,海口话多将“床”写为训读字“桌”。[16]相对其他方言,闽语保留上古汉语词汇特征较多,这是学界基本共识。
据此,我们认为,诗中的“床”是“几”类器具,搁置物品是其基本功能之一。虽然汉魏时坐具胡床已传入中原,但直到唐代,“几”类器具“床”尚未被胡床完全取代,它依然活跃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二)主人公真实“坐”法
《说文解字》:“坐,止也。从土,从畱省。”[17]“坐”后引申为席地而坐。甲骨文“坐”本像人在席上跪跽的形状。再从我国古代坐姿演变史看,古人开始皆席地而坐,并非高坐,坐姿本为跪坐。具体坐法为:双膝跪下着地,臀部下沉靠在脚后跟上。一开始跪坐于普通地面,后来渐渐变成草垫、席垫之类。“胡床”传入中原后,“胡坐”法随之传入,并逐渐为中原人接受,即坐在高处,垂足而坐。“从南朝开始,我国史书上就有了‘胡坐’法的记载。但直到唐末五代,人们还有盘坐或跪坐的习惯。”[18]
主人公不是躺卧,亦非站立,而是坐,但不是在床上“胡坐”,而是在床边跪坐或盘坐。这一坐法回答了前述第二个问题:一方面,跪坐或盘坐时间长了,主人公变得疲乏,需要临时借助外物支撑来缓解,而身边的“床”除搁置物品,还能借以倚靠,待体力恢复后继续跪坐或盘坐。另一方面,当有特殊需要时,跪坐或盘坐的主人公也可以起身、站立甚至走动,这样身体重心就会由低处转移到高处,头部上“举”,“举头望月”;站立后也可以下蹲、落地、坐下,从而“低头思乡”。
三、诗歌文本释读
(一)诗歌创作背景
《静夜思》真实的写作背景对于准确理解本诗的内容影响很大,当然也会波及其中“床”字的合理解释和稳妥把握。
李白一生漫游天下,年少饱览蜀地名山大川,阅历渐趋丰富。开元十二年(724),24岁的李白告别家乡,辞亲远游,东下渝州(今重庆市)。开元十三年(725),李白离开蜀地,正式出川,远赴吴越,欲遍游东南。开元十四年(726)春天,26岁的李白来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在越地游览半年之后,于同年秋天北上扬州。因长途跋涉,舟车劳顿,李白刚到扬州就突然病倒,只得暂时滞留以调理休养。
盛唐时扬州是我国东南重镇,其繁华不亚于京城长安。李白本应过得怡然自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他的处境颇为尴尬。其一,李白并非富家子弟,离家长期远游,没有条件携带丰厚盘缠,只能“穷游”。到达扬州之时,李白已离家两年,盘缠无法得到补充。就算是养病,他也只能寄身于简陋的小旅馆。其二,此次远游是李白初次远距离出川,离别家乡和亲人,当时的交通条件使得他根本无法随时返乡。他远离亲人和旧友日久,“独在异乡为异客”,对家乡和亲友的思念与日俱增,却无法及时得以排解。其三,初到扬州即病倒,得不到亲人照顾和亲情抚慰,对于年轻的李白来说,形单影只、孤独落寞既是他的真实处境,也是他的心境。其四,李白并非“烟花三月下扬州”,而是秋意渐浓时赴扬州。作为普通文人,李白像常人一样,“自古逢秋悲寂寥”,感怀伤情在所难免。
可以说,初到扬州的李白陷入思亲却无法见亲、思乡而无从归乡的无奈和矛盾中。心性敏感、阅历尚浅,初次客居遥远异乡,长期见不到家乡亲友,李白的乡思之苦、思亲之切远超一般人。他只能寄情诗酒,去化解浓浓乡愁。
(二)诗歌现实场景
思念家乡、亲人、旧友是李白初到扬州时的真实状况,尤其是无奈地卧病休养于客舍,恰逢明月当空照、夜静无可依之景,这种深沉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浓烈。此时此刻,李白无法向亲人、友人倾诉衷肠,加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只好“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推测成诗时的场景:明月当空,思乡难耐、孤独难眠的李白将一张“床(几案)”从小旅馆的室内搬出,安放在室外地上,接着将酒壶和酒杯摆放在“床”上,自己独“坐”床边,借着月光,开始自斟独饮、借酒浇愁,慰藉挥之不去的苦涩乡思。半醉半醒时分,李白已酒劲上头,醉眼朦胧,明朗的月光洒落于“床”前的空地上。不经意中,李白看到“床”前白茫茫的一片。而此时正值秋季,他不禁有些怀疑是不是秋霜降落。于是他起身站立,踮起双脚,抬起头来,可他并未发现有下霜迹象,反而看到一轮明月高悬空中。李白顿悟,其实这一轮扬州明月也正是自己家乡的明月,而自己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唯有这一轮明月如此熟悉、可亲。思虑至此,本来已经消解殆尽的乡愁一下子又完全涌上心头,他沮丧地低下头,极度失落地趴在“床”边,一下子又陷入离愁别绪当中,许久才抬起头来。故乡、亲人、旧友皆远隔千山万水,可以遥相思念,却无法相见。李白唯有再次斟满酒,举起酒杯,仰起头一饮而尽。就着这月光,李白挥笔写下了这一首千古名诗。后来,他还写就了与《静夜思》时间地点几乎完全相同的续篇《秋夕旅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漂泊异乡、浪迹天涯的游子的思乡怀故之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实际上是有着几案一类家具外形的物件,是一种兼有搁置物品和临时借以倚靠的双重功能的置靠具。我们还认为,李白写就本诗之时应该是在异地他乡扬州的一个小旅馆的室外;推测当时的场景应该是备受浓浓乡愁煎熬的李白在月明之夜,孤独地席地而“坐”,倚靠在“床”前,无奈而伤感地对月当空,举杯邀月,解忧消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