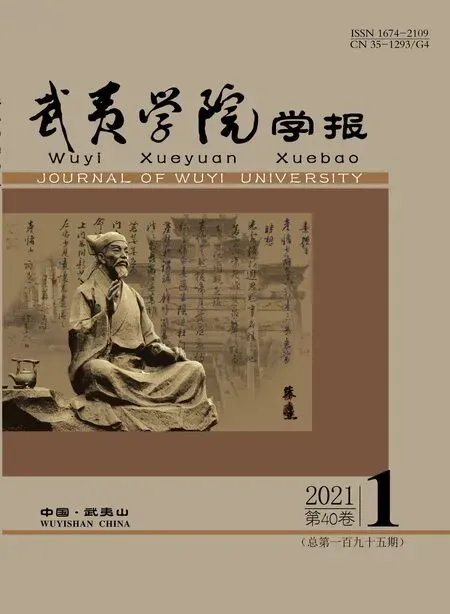略论李锐《无风之树》的复调叙事艺术
邓春霞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复调本指以单调相对的、由两段或多段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组成的音乐。复调艺术本是以巴赫作品为代表的一种音乐技术。在192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提出了享誉中外的复调小说理论。他认为,如果过去的小说是一种受到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独白小说,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小说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全面对话”的小说,即复调小说。[1]至此,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蓬勃发展。而创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山西作家李锐的《无风之树》正是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当代中国化尝试。
一、复调的叙事视角
如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钱中文教授在中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前言中所言:“复调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开展情节、人物命运、人物性格,而在于展现那些有着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1]复调作品中主人公们独立完整的思想以及爱思考、爱探索的意识在复调理论中都尤为重要。而在李锐的《无风之树》中,为了表现那些各自独立而又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他运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两种叙事视角进行叙述。
第一人称叙述虽然使得叙述者的叙事视角受到了其角色身份的限制,但能够更着重地描写出角色本身的主观心理,因而复调小说创作大都以第一人称“我”的有限视角进行。小说《无风之树》也运用了大量的不同的“我”通过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来向读者展示主人公们各自平等而又各自独立的自我意识。《无风之树》中有十二个,甚至十三个“我”,“我”们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受作者的统一意识支配,“我”们的存在向读者们呈现出了“我”们对于自己周围现实的所思所想。自我意识成为了小说主人公们自身反射的客体。如小说中,富农分子曹永福(瘤拐拐老五)之死,通过对矮人坪中不同的人对此事的不同反映描写,每个人都成为了小说的主人公。小说中,“我”——大狗(矮人坪生产队队长曹天柱的大儿子)是最先发现拐爷不对劲的,因为我与弟弟二狗去偷拐爷家的豆子时,发现拐爷立在炕上,头上有根绳子,喊他也不说话。对此年幼的“我”与二狗都是懵懂的,“我们俩”都十分害怕,二狗都吓哭了,“我们”不知道拐爷为什么要站在炕上不动也不说话。随后,小说又针对这一事件从“我”——曹永福(死者)的立场进行了叙述,“我”“千小心万小心就怕吓着别人,到底还是吓着那两个孩子啦”[2]。因而“我”(拐老五)的内心是内疚的,同时“我”也为自己的将死感到伤感,始终惦记着二黑(“我”养了大半辈子的爱驴)。之后是“我”——刘长胜(公社刘主任)的独白,“我”一边骂他“曹永福,……还嫌矮人坪阶级斗争不复杂?”,[2]一边抡起斧头把他解下来。当曹永福倒在我的怀里的时候,“我”(刘长胜)联想到了抗战时期王政委之死,他当时也是倒在我的怀里的。但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心境也变了,现在的“我”更多的是从当前的立场考虑,因而对于曹永福的死,“我”是不屑的,甚至觉得拐老五是畏罪自杀,使得矮人坪的阶级斗争复杂化。
此外,小说中还有众多的“我”——丑娃爸(村民)、暖玉(寡妇,与矮人坪所有男人关系复杂)、曹天柱(生产队长)、丑娃(村民)、糊米(村民,天柱的对头)、李传灯(做棺材的)、二牛(传灯爷徒弟)甚至是曹永福的鬼魂等。“我们”都分别因为曹永福之死前后出现并且站在各自的视角上对此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1]复调小说强调的是小说主人公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最终看法,因而在《无风之树》中,拥有众多个“我”,并且对于每一个“我”的性格以及背景,小说都并未做半点介绍,它需要读者自行推理,揭开每一个“我”的谜底。为“我”发声,展现“我”的自我意识,复调小说的这一特征在《无风之树》中得到了极大的呈现。
为了更好地表现出主人公们各自独立甚至对立的价值观,除第一人称叙事外,《无风之树》中第三人称视角也偶有运用。“现代的第三人称叙述作品有一类不同于‘全知全能’式叙述的变体,作者放弃了第三人称可以无所不在的自由,实际上退缩到了一个固定的焦点上。”[3]创作于当代的《无风之树》中的第三人称叙述并不是传统的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其叙述的焦点始终是落在烈士子弟苦根儿(赵卫国)的身上的。除了苦根儿的所见、所为和所说之外,小说主要着重描写的是他的心理活动,包括苦根儿下乡前与县委陈书记的谈话、他成为烈士遗孤的原因以及他留在矮人坪挖沟的内心独白等,其他人物都是作为同苦根儿有关的环境中的人物出现的。《无风之树》中,作者对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进行了融合,使得作品更加全面地呈现出了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
二、复调的结构布局
小说的结构布局是存在于文本之间的故事情节、人物行动以及人物关系的根本描述单位。虽然复调小说不重在展现故事情节,但作为小说的主要元素,它始终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文论《关于结构艺术的对话》中所言:“小说中的对位的必要条件是:第一,各个不同的‘线索’平等;第二、整体的不可分割。……复调在小说中与其说是技巧性的,不如说是富有诗意的。”[4]复调小说在结构上呈现出了更多的不同的声音,它们被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却又保持着各自的相对独立性。
小说《无风之树》的文本内部同样存在着众多不同但又平等的“线索”,它们共同组成了文本内部的复调。《无风之树》中有多少个“我”,就有多少条“线索”,这些“线索”既相互平行又共同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小说的第一条“线索”是苦根儿,前后出现了5次,依次在第一、十、十六、三十四和四十七章,由“我”目送刘主任下沟、看刘主任配眼镜、煤油灯下看毛主席像、与丑娃对话以及深夜给拐叔守灵等共同书写了赵卫国成为烈士孤儿前后的故事。赵卫国的世界是向毛主席、向党、向革命事业以及他笔下的英雄人物赵英杰看齐的,他是活在日记中的英雄。第二条“线索”是关于拐老五的,文中共叙述了7次,分别出现在小说的第二、八、十三、十七、二十、二十三、四十六章,由刘主任找“我”谈话、喂大黑二黑们、窑洞给刘主任倒水、开完会后坐夜路回家、被苦根儿逼问与暖玉的关系、上吊前的所思所想以及成为鬼魂后与二黑的独白等共同刻画出了曹永福虽然身为瘤拐却为人善良的形象,他的内心世界是柔和的、温悯的,以爱驴二黑为主的。小说的第三条“线索”是暖玉,文中也叙述了7次,分别出现在小说中的第三、五、七、十一、二十七、四十八和六十一章,由二弟吃面撑死、女儿小翠的死、刘主任嘿嘿的笑、矮人坪的男人们都骨碌骨碌的看“我”以及给逝去的拐叔做衣裳等,它们共同描绘出了秦暖玉成了寡妇后以及成为矮人坪共妻后的生活。不管是当初留在矮人坪还是拐叔去世后她的离开,暖玉始终是有着自己的自我意识的,一切皆有着其独特的人生价值,皆是其世界观的折射。除了与苦根儿、拐叔和秦暖玉有关的三条“线索”外,《无风之树》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线索”。如刘主任、大狗、天柱、糊米、传灯爷、二牛等,文中分别描写了六次、九次、九次、四次、两次和三次,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出发,孕育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声音,蕴藏着一种又一种不同的思想。
这些各自独立的“线索”“保持着远近不同的距离”[5],却又互相穿插,他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无风之树》这个“多声部小说”的集体。的确,尽管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不相同的“线索”,但“眼前的‘阶级斗争’的残杀,过去的战争屠杀,贫困,劳苦,死亡,人的麻木、隔膜、无法沟通,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剥夺,善与恶的相互纠缠”等[2],始终充斥其中,他们共同构成了《无风之树》这个六十三章的故事,这个由作家李锐的短篇小说《送葬》改编而成的故事,它们共同汇聚成了“矮人坪的矮人们无法逃避的苦难”。[2]
“文本外部或文本之间的复调效果,又被视为一种‘互文性’的表现,它是指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引用、融入、指涉。”[6]互文性也是复调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些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构成了小说的多声部性和复调性。在《无风之树》中,这一特征同样得到了体现。如小说三十九章,“我”——刘主任,回公社前与苦根儿的对话,“我”(刘主任)把空白的介绍信递给他(苦根儿)对应的正是小说的第一章,“我”——烈士子弟赵卫国(苦根儿),目送刘主任下沟十五里,想着刘主任得摸黑赶路了,紧紧地捏住了刘主任离开前给“我”的那几张叠起来的纸(介绍信)并且回想起了刘主任离开时的言语。又如小说四十九章,“我”——曹天柱,在暖玉家喝兰子(奶羊)的奶时,梦见“我”七岁时暖玉和兰子在一块儿,随之回忆起“我”(天柱)七岁那年日本人来村里时的场景,这对应的正是小说的第十二章,“我”——天柱,因为天气炎热,渴了,回忆起了“我”七岁时的那年也是因为渴了,所以拉过奶羊来,那年矮人坪的女人们都被糟蹋了的事情。
此外,小说中还存在着众多的互文,如第二章与第十三章,“我”(曹永福)成为富农分子是因为“我”留下来帮哥哥一家守地;第五章与第四十八章,小翠死后,“我”(暖玉)给二弟、小翠送了三天饭,拐叔一直守护着“我”;第七章与第十章,苦根儿因为暖玉的调戏脸红;……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时间与空间的对立与统一,复调的《无风之树》由此而生。
三、复调的叙述语言
“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7]文学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常规层面,小说语言的运用也存在着无限的表达方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其运用的语言类型是对话,因而对话成为了巴赫金创设的复调理论中语言世界的中心,并且它被分为了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
大型对话是指小说整体之间潜在的对话性,它主要表现为“人类生活和人类思想本身的对话关系”[8]。因而在《无风之树》中,它主要通过主人公们同别人、同第三者说话来渗透其自我价值。《无风之树》中,其大型对话是遍布全文的,有些是用的间接引语,有的是用的直接引语。直接引语的部分较少,主要集中在小说第十、十六、三十四和第四十七章,都是围绕苦根儿的“线索”进行的,包括苦根儿与矮人坪矮人们的对话、与刘主任的对话、与寡妇暖玉的对话以及读毛泽东语录产生的对话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作者给苦根儿塑造的形象,作者对于苦根儿式的人物是不满的,深冷透骨的悲凉渗透在苦根儿的故事中。至于间接引语的大型对话,《无风之树》则有着太多太多。如以生产队队长曹天柱为主体的,包括天柱与大狗、与拐叔、与暖玉、与刘主任、与苦根儿、与糊米、与铁成(矮人坪村民)、与二黑等的对话;以天柱儿子大狗为主体的,包括大狗与大弟弟二狗、与自己的傻哑母亲、与父亲天柱、与死去的拐爷、与传灯爷、与小卖部老板大黄牙等的对话;以暖玉为主体的,包括暖玉与自己爹娘、与二弟虎牛儿、与短命鬼丈夫、与死去的女儿翠儿、与拐叔、与天柱、与刘主任、与苦根儿、与丑娃家的等的对话;……无数的话语共同构成了《无风之树》中大型对话。
微型对话是主人公们内心的对话。尽管《无风之树》对大型对话进行了大量的运用,但诚如小说的作者李锐在《无风之树》的结语中所言,小说的写作是借鉴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的。福克纳是美国意识流小说代表人物,因而李锐的《无风之树》不管是第一人称叙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不管是文中的哪个“我”,都是带有明显意识流倾向的,外界的所见、所为,所有都成为了塑造主人公们内心世界的绝对动因,从而使得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心理描写,微型对话才是《无风之树》对话的重心。如小说第一章,目送刘主任下沟从而使苦根儿的意识跳跃到了刘主任离开前的对话,跳跃到了暖玉,跳跃到了头顶的他看了六年的乌鸦,跳跃到了他当年上小学、上中学的地方、父亲去世的地方,跳跃到了他笔下的赵英杰等。
“对话体有助于层层剥笋式地展示精微深奥的思想,展示这些思想的诸多方面,……富于引导性启发性,帮助读者养成辩证地思维的习惯。”[9]《无风之树》中的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共同引导着读者进行辩证思考。因此,在小说中,每一个发声者的名字、他(她)的人物性格、他(她)的人物背景以及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读者对前后文的理解以及对小说的理解融会中推理得出。如小说第一章,一开始并不知道文章开头的“他”究竟是谁。但通过下文“他”回忆起与刘主任的对话以及他内心的独白我们得知:“他”就是这一章中的“我”,就是苦根儿,就是党的儿子,就是烈士的孤儿,就是赵卫国。但在这一章中,作者始终给我们埋下了众多的伏笔,刘主任是谁?他为什么要给我几张空白的介绍信?“我”——苦根儿为什么叫苦根儿?为什么成为了烈士的孤儿?暖玉又是谁?“我”为什么不愿意娶她?刘主任与暖玉是什么复杂关系?“我”在那碰见的那位作家是谁?为什么“才下定了决心?”……这些问题,作者都未作丁点解答。
小说对话在段落与段落之间、章节与章节之间环环相扣,它们使得读者层层深入,去伪存真。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共同构成了《无风之树》中的复调语言艺术。
四、结语
“我的不满是看见我们的‘先锋’们,很快的把形式和方法的变化技术化了,甚至到最后只剩下技术化的实弄和操作。”[2]尽管我们可以从复调理论艺术的多个角度对李锐的《无风之树》进行解读,但他的《无风之树》始终都不是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简单复制。“每一代人都得重新翻译和重新解释外国名著,以自己的方式再现它们原有的自然面貌。”[10]诚然,作家李锐的视野是向国际化的,他的《无风之树》是披着复调外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