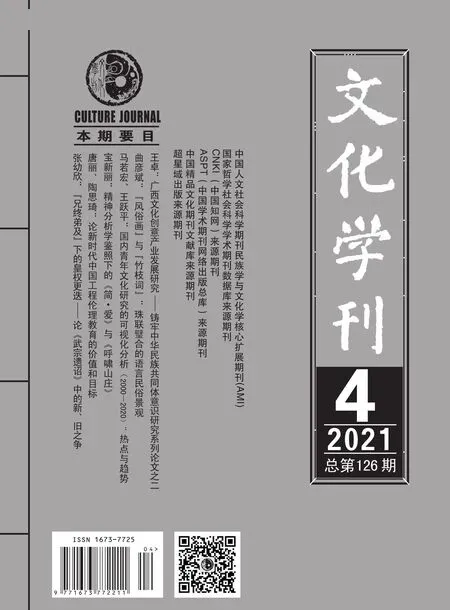精神分析学鉴照下的《简·爱》与《呼啸山庄》
宝新丽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盛行现实主义文学,其中勃朗特姐妹的文学成就影响深远。她们的代表作《简·爱》与《呼啸山庄》分别在讲述不同社会阶层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但相同的题材却不能使两部作品在文学评论的长廊中并驾齐驱,而是褒贬不一。《简·爱》一经出版立即获得成功,夏洛蒂·勃朗特也得到了相应的社会认可;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出版后却遭到了冷落和批评,甚至还受到了其姐姐夏洛蒂的指责。但是,在一百多年后《呼啸山庄》重新获得了世人的赏识,人们对这部小说赞誉有加,相比之下,对于夏洛蒂的《简·爱》则出现了一些微词。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艾米莉的成就要大于夏洛蒂”,因为她是个诗人,而夏洛蒂是一个主观主义作家[1]。
这种后来者居上的文坛现象引起学界的注意,在我国也不乏相关的评论,力图研究为何出现后来者居上的原因。这类文章认为虽然两部作品都有女性为维护自身尊严而反抗男权社会歧视的思想,但《简·爱》最终出现了二律背反的现象,女主人公并没有彻底突破当时社会女性依附男权和财产的窠臼,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男女主人公精神上是合为一体,从而包含着男女平等的思想内涵。该评论主要聚焦小说本身,不乏新颖,却忽略了文本之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进化和发展。本文试将两部小说置于其问世年代和之后的西方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寻找这种文学现象背后的动因。
一、相同题材与不同表现
在处理不同社会阶层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婚姻问题上,夏洛蒂基本上秉承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讲述地位低下的简·爱外出谋职,巧遇心上人,发生婚变,最后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成年相遇,罗切斯特作为庄园主,雇佣简·爱作为家庭教师,他们一开始就对各自的社会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简·爱对自己的地位和人格是这样表述的:“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2]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男女主人公的来历和经历更加清晰,读者对于他们的心路历程也有了清楚的认知。简·爱展露出了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对抗精神,不受任何人奴役和摆布,在自我独立和强烈反抗意识的基础上赢得了爱情,这也是夏洛蒂现实生活的写照。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与婚姻的障碍主要是来自外部的社会原因,而最终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两人之间的客观条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相互抵消而趋同所造成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
在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名望和财富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女性被排除在传统工业之外,不可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独立,所能从事的职业也是有限的,大多被限制在家庭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由于贫困的家境,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丽·勃朗特只能去当家庭教师和寄宿学校的老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处于附属地位,男权文化压抑着女性的意志和自由。不同于现实的是,小说是从社会大环境着眼,塑造了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其结果是在不破坏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前提下维护女性的独立人格,并成为把所爱之人从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天使。这样的女性虽然突破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普遍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的道德期待。
反之,不同于简·爱的爱情故事,凯瑟琳与希斯克厉夫的爱情除了社会原因即社会等级外,最大的困惑出自凯瑟琳的心理原因。《呼啸山庄》里的男女主人公在儿时就已经相见,希斯克厉夫是厄恩肖先生从外面带回来的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男孩子,厄恩肖待他如自己的儿女,因此,厄恩肖家中的三个孩子的社会地位意识是模糊的,天性漫不经心,似乎不知感恩的希斯克厉夫与活泼、任性而又淘气的凯瑟琳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前者对后者言听计从完全是出于天性,而她哥哥对希斯克厉夫的排斥是出于某种直觉,并没有突出表现为社会地位的歧视。直到三人长大,其社会地位的意识才凸显出来,随之希斯克厉夫突然失踪,几年后带着财富回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地位的鸿沟,却难以找回儿时的爱情,于是他在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展开了报复。女主人公凯瑟琳则在情人希斯克厉夫和丈夫林顿之间撕扯分裂,最后香消玉殒。单纯从外部社会原因寻求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爱情的困惑和悲剧产生的原因,并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更多的应是探求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对于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并没有像简·爱那样直接通过主人公的对话或独白等手法进行明确交代,而是完全置身事外的叙事,大多数情况下根据管家的交代将故事记叙下来,而管家的叙事也往往是根据男女主人公的某些行为或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进行猜测和表达,其不确定性使得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些手法在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文学中显得十分另类。《呼啸山庄》超越了传统宗教和道德观的束缚,展现出了狂野性。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的爱情不同于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纯粹是精神之恋,他们因情而生,因情而死,同时,《呼啸山庄》里男主人公希斯克厉夫的疯狂报复行为,和女主人公凯瑟琳婚后情感的混乱也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因此,《呼啸山庄》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是必然的。
二、社会发展与“我”的认知
西方社会意识形态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成为主流,学者对人本身的研究不断深化,进入20世纪以来这个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理论,开启了精神分析学的新纪元,由弗洛伊德创立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按照弗洛伊德1923年出版的《自我与伊德》中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构成。本我是原始的自己,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泉,本我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行动,唯一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从而求得个体的舒适和生存,它是无意识的,是不被个体所察觉的。自我是为本我服务的,它遵循“现实原则”,寻求满足“本我”冲动,同时又保护整个集体不受伤害。而超我遵循的是“道德原则”,代表着理想,追求完美,要求自我按照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的。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弗洛伊德的学说不断地被修正和发展。后人认为人的本性不但被性欲所支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格的形成和教养也都起着作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学领域对勃朗特姐妹作品评论的褒贬起伏,恰恰发生在弗氏学说愈发产生影响的年代。因而,用精神分析学鉴照《简·爱》与《呼啸山庄》,能够进一步说明发生在这两姐妹代表作品上的社会认知现象。
在《简·爱》中女主人公一出场就已经是一位成年女子,她明白自己在桑菲尔德府中地位低下,不同于男主人公社交圈里的所谓淑女,再加上自己相貌平平的外表,与高大英俊的罗切斯特似乎相差甚远。开始她并未想过男主人公会对她产生爱恋之情,而是选择在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做一个本分的家庭教师。罗切斯特一开始对这个家庭教师也是不在意的,只是以一种绅士的态度对待下属。当他对上层社会所谓淑女的虚伪和浮夸感到厌烦时,出于郁闷与简·爱交谈,开始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逐渐被简·爱的人格魅力所吸引。用弗氏的人格理论来解释,小说《简·爱》起始建立在“自我”的层面上,男女主人公都意识到了自己和对方的社会地位和客观条件,并自然地扮演着符合各自身份的角色。随着故事的发展,罗切斯特作为上流阶层所遭遇的不幸和简·爱坚强而独立的个性使二者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但处在不同社会阶层,他们爱情遇到困惑和障碍,外加罗切斯特已婚的事实,这些外界因素使得二者刚迈出结婚的第一步时,女主人公就不得不选择出逃。按照弗氏精神分析学,这一切都发生在自我意识和社会现实原则的层面上,超我发挥着监督自我和本我的作用,使自我不能满足本我的意愿快乐行事,因此男女主人公只能忍痛割爱。但故事到最后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桑菲尔德府和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梅森在大火中消逝了,罗切斯特不再是原来的模样,成为盲人,往日高高在上的形象一扫而光,而此时简·爱却得到了一笔遗产,他们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逆转,简·爱则选择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这个行为已经超越了自我的范畴,简·爱在清醒理智的基础上遵循了爱情忠贞不渝的道德原则,她的思想上升到了超我的境界。
弗洛伊德有一个关于白日梦的说法:“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的实现,并且使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好转。”[3]艾米莉笔下的凯瑟琳就是抛开了本我和超我,遵从自我,而后又被超我惩罚的典型人物。《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在懵懂的儿时相见,他们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呼啸山庄里,凯瑟琳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这个无亲无故的男孩子在家中与自己的身份有什么不同,她不但接受了这个不速之客,还对他表现出极大兴趣,她全然不在乎社会对一个女孩子的行为要求,完全按照自身快乐原则行事,当老厄恩肖要求他做一个好女孩时,她扬起脸来向他大笑着反唇相讥对父亲说“你为什么不能永远作一个好男人呢,父亲?”[4]41希斯克厉夫来到厄恩肖家中,没有寄人篱下的怯懦,甚至对厄恩肖也没有表现出感恩之情,他对家中的事务均显得漫不经心,只是对凯瑟琳表现出绝对顺从。二者天性趋同,都带着与生俱来的野蛮、顽强、自由,这使他们在无意识中互生情愫。这是一种“本我”层面上的相互吸引,他们从中获得了快乐,并一直度过了童年。然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主要表现为凯瑟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位相当、家境优渥的林顿为配偶,其理由是“他会发财,我要做这一带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将有这样一个丈夫而骄傲”[4]75,而希斯克厉夫明白自己没能得到凯瑟琳的原因是金钱作祟,他在愤怒中离开了呼啸山庄,几年后他带着财富回到故地。成年后男女主人公的这些行为受到了社会影响,从“本我”上升到“自我”的层面。凯瑟琳是按照“现实原则”对自己的婚姻作出的选择。对于希斯克厉夫来讲,面对现实,他离开呼啸山庄是他唯一的选择。
当希斯克厉夫带着财富回到呼啸山庄时,与简·爱重回故地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心爱之人已为他人之妻,并过着优裕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遵循“自我”的现实主义原则,男女双方应自我约制,好自为之。但在艾米丽笔下,这对男女的爱情之火不但重燃,而且更加炽烈,凯瑟琳叫道:“我并不愿意你受的苦比我受的还大,希斯克厉夫。我只愿我们永远不分离”[4]154,“啊,我心里像火烧一样!但愿我在外面!但愿我重新是个女孩子,野蛮、顽强、自由,任何伤害只会使我大笑,不会压得我发疯!”[4]239显然温情脉脉的画眉山庄压抑了她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却给现实中一般女子提供了理想家园。正是这种本性与现实的冲突,或者说“本我”与“自我”的争斗,将她撕裂,导致其英年早逝。凯瑟琳去世对于希斯克厉夫来说就等同失去了灵魂,他冷眼看世界,处处皆是恨。这是一种由爱转化成的恨,他发生在“本我”层面上,具有不可遏制的破坏性冲动,表现为毁灭性的复仇。他将仇恨弥漫在夫妻、父子、公媳、表兄妹之间,呼啸山庄已成为人性的荒野。对他来说现实中渴求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就等同“本我”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破灭,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本我”剩下的还有冲动,它按“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对希斯克厉夫来说已无快乐可言,他无法避免痛苦,转向报复可谓是“快乐原则”的变异,它是无意识的,但具有破坏性,而且强大不可遏制。希斯克厉夫不择手段地成为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主人,暴虐地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最后他向自身施暴,绝食而死。他的死是“本我”与现实较量的结果,是“本我”的终极释放,让人叹息!呼啸山庄中男女主人的爱情悲剧一直游荡在“本我”与“自我”之间,他们脱离不了现实,因而具有“自我”意识,但“本我”的强大又使他们的行为显得异常且疯狂。
三、认识深化与价值评价
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现实主义文学往往是从自我层面上描写人在社会中的活动,揭示人与社会的关系,虽不乏人物的心理描写,但是这种描写以理性为主导,感性是次要的。“现实原则”,操纵着人物的行为和思维,并制约着本能冲动。《简·爱》作为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揭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和受制于男权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渴望尊严和独立。在现实与意识的碰撞中作者采用了能够被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元素,通过“自我”到“超我”的升华成就了在世人眼里皆大欢喜的结局。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伍尔夫称之为“主观主义作家”。然而,现实主义作家的确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社会的面貌和女性受压迫的实质,并通过写作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引起社会女性地位的关注。小说《简·爱》的历史认识价值和社会进步意义不可否认。
毋庸置疑的是,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深化了对人类本性的认识,这对于文学批评和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分析表明,《呼啸山庄》不但手法上突破了现实主义,其人物塑造的出发点是在“本我”的层面上,而这个层面是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以医学和理论的形式首次揭示出来,虽然该理论受到某种质疑和修正,但它从根本上将人性探讨引向深入,进入20世纪中叶,它已经能够深入人心。伴随着社会认识的进步,人们对《呼啸山庄》刮目相看是一种自然现象。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爱,歇斯底里的恨,不择手段的报复,不再被看作是道德上的诟病,而是人性的真实写照。这一切似乎违背了社会常理,却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性中隐秘和被压抑的部分,具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作者艾米莉超越自己的时代,用自己的人物形象诠释了半个多世纪后才问世的有关人性的理论,这种超前性奠定了这部小说的潜在价值,而该小说百年之后被重新认识,正是其潜在价值的释放。
综上所述,本文借助精神分析学,论证了《简·爱》主人公意识从“自我”升华到“超我”,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从社会现实出发,再现了那个历史年代的下层社会女性的处境和期待;也论证《呼啸山庄》从人性出发,表现男女爱情中“本我”的产生和冲动,和在现实中“本我”与“自我”的博弈。正如在西方文学史长卷中,现实主义文学页面的光辉不会被现代主义文学所遮蔽,《简·爱》与《呼啸山庄》都是文学宝库中的亮点,各有千秋,其价值无优劣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