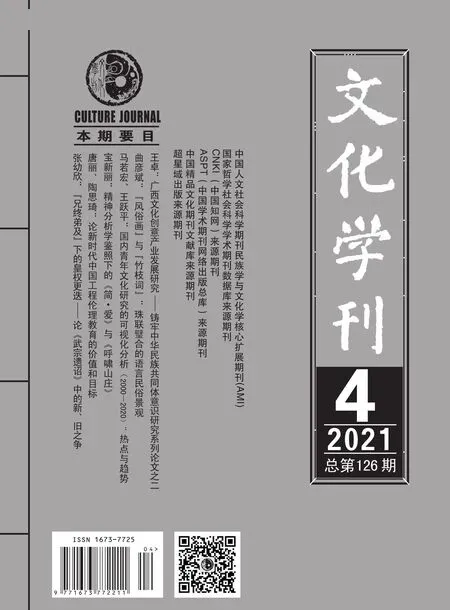论《庄子·天下》中对墨家学派的看法
杨浩宇
一、《天下》篇对墨家学派评论的具体内容分析
《庄子·天下》对墨家学派进行总述性评论,肯定其坚持了“古之道术”的某一方面,即“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但“为之大过,已之大循”。具体评述“非乐”“节用”“自苦”“后世弟子倍谲不同”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评论墨家的“非乐”主张。在《天下》中道家质疑“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的主张,认为这是有悖于人伦常情、对自己的情感抑制太过、刻意为之的追求。其实音乐本就是人的情感宣泄的产物,“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音乐是一种表达情感的工具,而情感的流露也是极为自然的状态,那么墨家主张“非乐”实则是否定了这个情感表达的工具。《非乐》中大谈音乐的各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危害,但没有指出其他的可供替代的情感表达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天下》中对“非乐”的批评与质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其次,评论墨家的“节用”主张。这一主张本是符合“道”之“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的,但“为之大过”,以至于“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天下》认为丧礼本就有贵贱礼仪的区别,若过于要求严苛的节葬主张会导致礼制的崩溃。墨家主张“节用”的初心与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天下苍生能在节俭中免于困顿,但对此提出的具体要求严苛得难以做到,不能顺应人性、顺应自然。
再次,评论墨家的“自苦”主张。《天下》中直引了墨子说的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可以说墨子是将禹的形象和行为作为墨家的榜样与规范,宣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因此后世的墨家之徒也是如此以自苦为幸,以穿着朴素为正统。《天下》中认为墨家“自苦”太过,虽然“自苦”是为了救济天下苍生,是为了苦苦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由于太刻意追求,所以在行动中就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偏移自己的初心。《墨子·公输》中提到墨子听闻公孙盘为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后“起于鲁,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2],墨子不畏艰辛,即刻出发,走十天十夜赶往郢地,就是为了阻止这场楚国攻打宋国的战争,这是典型的“自苦”,也是做到“腓无胈,胫无毛”的具体行为。
最后,评点墨家后世弟子的对峙与学说的内部分裂,不同派系的墨家弟子“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其实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不能据此说明该学说存在矛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后世弟子在理解上存在差异而导致较大争议与矛盾实属正常。不过,墨家后世弟子的争辩已经达到了“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的程度,这有违墨子的初衷。
在分条评论后,《天下》对墨家学派进行总结性评价,提出“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乱之上也,治之下也”。成玄英先生认为墨翟、禽滑厘等“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俭太过,所以非也”[3]610,意在说明墨家的主张用意是对的,但落实到行动上由于太“过”就有所偏离了,导致乱天下有余而治天下不足。那为何行动上“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会导致“乱之上也,治之下也”的结果呢?郭象先生认为原因是“乱莫大于逆物而伤性也”[3]610。所谓“逆物伤性”就是违逆自然、违逆人性。
二、《天下》篇中对墨家的明褒暗贬与惋惜之意
《天下》中对墨子个人的评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似乎显得态度暧昧,是在否定了墨子不可为的主张要求后,又从人性角度肯定了墨子的坚持和不舍,其中存在“明褒暗贬”的意味。《庄子·人间世》提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4]51《庄子》中有对“才之美”的阐述,因此有学者认为《天下》中的“才士”即“才之美者”,意思是说墨子才美而未得道。“才士”若是解释为“才之美者”,那么即是首先肯定了墨子的理想具备一定的正统性,是继承了“道”的某一方面的;其次是墨子拥有坚持不懈、枯槁不舍的毅力与韧劲,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但显得过于严苛,其“才”也无法得到充分展现。这最后的“才士”评语的背后是对美好品质终无所用、穷尽一生劳碌无所得、枯槁不舍的追求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固执的慨叹。 除了这些总述性评价,《天下》中还有一处对墨子的评价——“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但其存在不同的解释。“好学而博,不异”和“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似乎存在矛盾,那么“不异”是指什么呢?王先谦先生在《庄子集解》中引郭象注:“既自以为是,则欲令万物皆同乎己。”[5]这种解释应该是在否定墨子的“不异”,认为墨子的“不异”是要求自然万物与自己一致,自身成为自然参照的对象,这与道家的随顺自然、尊重自然、对话自然的主张截然相反。曹础基先生的《庄子浅注》注“不异”为“不立异。墨子主张‘尚同’”[4]390,这种解释又牵涉墨子的另一主张“尚同”,而且这种解释与前文的“好学而博”的关联不够紧密,“尚同”学说的范畴很广,下文对墨家的评点中也没有再提到“尚同”。再者,“尚同”与后文的“不与先王同”的关联也不大,所以解释为“尚同”似乎会使这一“不立异”的主张孤立出现,显得费解和突兀。再回顾郭象先生的注,若认为“不异”是自以为是地要求自然万物与自己一致,那么“好学而博”就会成为这“不异”的原因,《天下》的用意则会是否定墨子因“好学而博”而自喜自大,认为自己博古通今,强迫自然与自己一致而不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而其后的“非乐”“节用”“自苦”等主张都“为之大过”,是一心想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没有以自然为法度,造成了对“道”的偏离,这或许可以成为墨家学派“为之大过,已之大循”的深层原因。
三、《天下》篇对墨家主张的评论角度及其价值
总体来看,《天下》中对于墨家学派的评论是以“道”为参照的,即是以道家的原初性理念为依据,得“道”才能算是至境,自然就会主张顺应自然、遵从本心、无所凭借、顺“道”而为,所以最后才会认为墨子“才士”也,对他的“才”因不得道而无法施展感到惋惜。可以说,这两家学说的比较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较量,墨家即便为之大过、过于严苛,但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那种即刻行动的精神、自苦坚持的韧劲、为民请命的侠义都是美好的,是弥足珍贵的;道家追求“道”,要顺应自然,是形而上的哲学考量,要在流变的万事万物中把握最为本质的“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家没有现实的考量,形而上的“道”,落到实处,作用于人世间,老子称之为“德”,“德”便是百家本源“道”的现实观照。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评论与比较显然不够全面,墨家形而下的自苦济世因执之太过而离“道”愈来愈远,但道家形而上的“道”也会遇到现实困境,因动态变化难以言说只能靠自身领悟而难以落实“道”的要求,这或许也是“道”在传承过程中出现分裂与偏离的原因。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天下》是客观的具有学术史意义的论著可能有待商榷,它的确有细致考察各家的学说与主张,但全文始终保持着“道”的参照点,且就评点墨家学说而言也并非对其学说进行全面性评价,其依据仍是墨家学说中与“道”的偏离之处和“其意则是,其行则非”的具体表现,所以所谓客观化的学术研究是仅就现代化的研究视角而言的,绝非当时写作者的主观意愿。
重新审视《天下》对墨家的评论时,除了要注意与道家学说的比较和找寻当时写作者的语境外,还应注意当时的写作背景。目前学界对《天下》的作者及成文年代有较大争议,但尚存较多共识的是成文于战国中期或晚期,彼时久经战乱的人民渴望和平、安乐,墨家却主张自苦济世、到处奔波、对自己要求苛刻,这是不符合民心的。当时因战争影响许多百姓都忍饥挨饿、流离失所、漂泊无依,哪里还能做到抑制自己的情感,在各方面都做到省俭克制,去忍受“腓无胈,胫无毛”的自苦生活呢?所以墨家学说和主张的确为之大过,落实到行动上便会偏离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