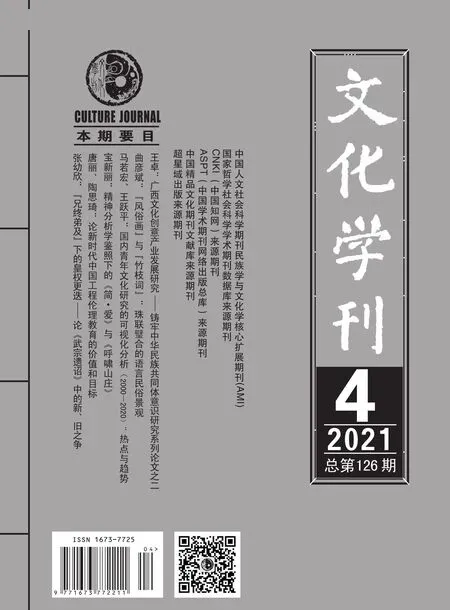论哈耶克法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因子
韩惠名
单就世俗性眼光来看,哈耶克最大的成就是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放大了哈耶克身上经济学家的标签,但是纯粹的经济学研究似乎不能解决他关于市场效用之根源的疑惑,于是他将聚焦于经济学的目光转向了哲学、法学等领域,并最终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哈耶克活跃于20世纪,而这个年代恰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涌现的年代。虽然哈耶克从未明确表明自己与后现代存在着关联,但是从其观点来看,他确实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诸多相似性。
一、哈耶克法哲学渊源中的后现代成分
哈耶克的法哲学在其逻辑顺序中并不处于靠前的位置,它的成立条件必须从哈耶克的哲学及方法论中寻找。哈耶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是在其学派、友人等组成的整体氛围中渐进形成的。这种整体氛围的各个要素中,早已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具备后现代特征的某种成分。
(一)非理性主义的浪潮
1.苏格兰启蒙运动
在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大争论中,苏格兰启蒙选择了前者。苏格兰哲学家通常承认心灵的复杂性,认为理性只是心灵众多官能之一,并对那些非意识性、来源于人之惯性的力量给予高度重视。因此,他们认为知识并不总是来源于理性,大量感知汇聚成的经验才是人类大部分知识的主要形态。哈耶克深受苏格兰学派的影响,他将启蒙运动分为“以德法为中心的启蒙”和“苏格兰式启蒙”两大脉络,并认为通过后者自生自发式的社会历史认识路径得以保留。作为哈耶克重要思想渊源的苏格兰启蒙,内在地蕴含着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要义。培根的“归纳法”奠定了苏格兰哲学的经验主义基调,为这种哲学埋下了一个非理性主义的种子。我们不能说苏格兰启蒙就是后现代的,但是毫无疑问,苏格兰哲学对激情、同情、经验等非理性因素的深切认同,使得它借由非理性的前哨为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来临吹响了号角。
2.波普尔
波普尔与哈耶克是非常要好的友人。哈耶克在1936年以前主要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着,他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这一领域。波普尔对与知识相关研究的归纳,尤其是他在《研究的逻辑》一书提出的可证伪性理论,促使哈耶克经济学研究的知识论转向。可证伪性理论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批判理性主义”,“无法证伪的都是伪科学”是批判理性主义最精练的概括。批判理性主义蕴含着一种根源性思想:因为一切声称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无不是从对具体事物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性总结或在有限的观测下取得的推断,这些归纳、推测中必然掺杂部分主体的臆断,所以我们必须对任何宣称绝对确定的知识保持警惕。波普尔对普遍知识不可揭示性的说明具有一种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意味,虽然我们在波普尔这里找不到明确以“后现代”为主题的论述,但批判理性主义中所展示的思维方式足以让他成为后现代哲学的先驱式人物。
(二)基于理性观的自由观
1.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在反思英国古典经济学客观价值主义的基础上,发起了以主观主义价值学说为特色的“边际革命”[1],但他们对于古典经济学并非全盘推翻,古典经济学对市场和个体自由的推崇被奥地利学派继承下来,使得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成为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方法论。作为奥地利学派第四代中坚力量,哈耶克整套的理论中随处可见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子。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后现代哲学最内在的精神气质。因为从后现代的诉求来看,对主体的解构、反对宏大叙事话语、重述知识等一切行动的目的,最终都要回归到对人之内在性的吁求,以及树立每个人尊严的愿望。
2.波兰尼
知识的默会性是后现代知识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最早提出默会知识的人是英国的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波兰尼从其科研经历中发现,科学知识并不是人们对其固有印象那样,是从精密的演算和严格的推导中产生的;相反,科学知识蕴含着一些只能由科学家凭借直觉才能够把握的东西。直觉是在整体性、情境性感知的统帅下,通过感官、既有经验、瞬时启发等刺激产生的认知形式。直觉的介入使得任何看似客观无误的知识都实际包含着主体无意识的思维前设,从这些前设性认知中,波兰尼提出了默会知识与言述知识的分类。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对于哈耶克的影响是直接的。哈耶克在《感觉的秩序》中所说的通过复杂脑神经元活动而获得的情感化知识大部分属于“默会知识”,而这类知识在哈耶克看来“更具效用”[2]。正如邓正来先生的精辟总结,在波兰尼的影响下,哈耶克才初步提出“默会知识”和“知道如何”的观点[3];并在此基础上,哈耶克才能将“无知”这一核心概念引入其后期的知识观。
二、哈耶克法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理性观上的交叠
后现代主义通常以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反理性主义是后现代哲学最基本的特征。从哈耶克的理性进化主义的基本立场来看,虽然他并没有对理性进行全盘否定,但一定程度上他仍旧是“理性主义的反叛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后现代主义达成了一致。
(一)反对理性主义的共同立场
1.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古典时期的理性之光被中世纪的黑暗所压制。直到17世纪,在法国,一场名为启蒙的运动重新扛起了被天主教压制了近千年的理性主义大旗,哲学世界重树了理性的权威,现代哲学也由此发端。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随着理性逐渐被视作评判一切事物合法性的标杆,现代哲学将理性重新捧上了神坛,继上帝、圣子之后成为新的神祇;于是,启蒙理性也就具有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一切弊病,逐渐走向了启蒙的反面。哈耶克同样是启蒙理性的批判者。哈耶克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并不是统而概之的,而是将启蒙区分为法式和苏格兰式的。依照法式启蒙的观点,只要人们充分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就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确实,自启蒙之后,欧洲文明似乎取得了比其他文明更长足的进步,这是由自由赋予主体的创造力和爆发力的加持下的成果。但是,法式启蒙刻意强调理性的力量,于是人们将这一切的成就记在了理性的功劳簿上,法式启蒙最终将导致“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的诞生。
2.对理性权威的破除
启蒙所奠定的现代哲学通常秉持理性中心主义或者理性本质论的立场。理性的反对者被在理性的话语下被视作反派,理性成为一种用于压迫被其判定为异端的权力,正如利奥塔所说,“理性与权力是一个东西,是同一的”[4],因此,在后现代者的视角中,理性的话语包含着一种自视甚高的自负,这种自负使得最初作为神话终结者的理性自立为新的权威。哈耶克与后现代在批判理性权威性上的共同性是显而易见的。哈耶克在讨论政治语言的混淆时指出,构建论的唯理主义用“意志”代替了“意见”,而意志意味着依照理性的决断有目地的行动[5],意志这一字眼的频繁使用,似乎使得意志连带着理性成为政治哲学中最神圣的字眼。哈耶克极其反感由法式启蒙传统延续下来的构建论唯理主义,这种理论赋予理性极高话语权,这实际上使得理性成为一种低效的工具。
3.对非理性因素的强调
依照后现代哲学的观点,理性不能被断定为意志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人既有理性、受冷静头脑控制的一面,又有兽性、不自觉、动物本能的一面。理性与无意识、直觉、冲动等同样都只是内发于人的内在的某种成分,甚至有时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远远超过理性。非理性是人性中固有的部分,是生命的内驱动力。后现代理性观所强调的非理性因素,在哈耶克的理论体系中是贯穿全局的隐含线索,这条线索要返回他的心智论中去找寻根源。哈耶克在《感觉的秩序》中强调,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只是在于它们各自发挥的分类机制的细致程度有所不同,相比意识、潜意识等非理性形态,意识并不是某种更加高级的心智形态。相反,就意识的范围而言,它是极其狭窄的,无意识、潜意识等非理性形态与意识共同在场,成为意识深不可见的根基。
(二)基于理性观的自由观
现代哲学的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将理性作为自由的前提条件,人的自由来源于理性把握必然之后获得的无限性,当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摆脱了非理性意识的干扰,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1.有限理性的自由
现代哲学的自由观是建立在人的本质理性,或者说无限理性之上的。而后现代自由观则认为自由之根基并非理性,而是行为和思想上的实质性自由,即主体是否能够跳脱社会、文化、环境、权力的框架作出真正源于自身的选择。同时,自由也应当包括非理性的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应当重视人的欲望和本能,包容疯狂、感性、惊恐、异想天开等一切异常的合理存在,关怀、聆听他者的声音。可以说,后现代的自由观建立在有限理性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同后现代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自由的个人维度上,哈耶克将自由定义为消极自由,即免除强制的自由。这里的隐含逻辑是:对某人而言的最优选择或最适当的行动是建立他对自身所处情景性以及选择偏好的判断之上,而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外在意志对于这些信息的获取是力所不能及的,因此任何外在意志都应当被排除在个人行动所遵循的规则之外。
2.个人主义的自由
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福柯在晚期著作中对个人的自由有不少的探讨。在他看来,自由应是主体摆脱固定思维方式、外在权力压制的最终结果。自由来自欲望和本能,与人的生命欲求相关。因此,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应当是个人的内在生命力被充分释放出来的社会,只有这样来自私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被充分激发。可以说,后现代保持了对人之非理性的忠诚因而达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区分了真、伪个人主义。伪个人主义以“笛卡尔式的唯理论”为基础,它将会导致极端的集体主义。哈耶克在最后一部系统性著作中提到,文明进步在当下很大程度上被意指一种趋向于既定目标的发展,而“进步,依其性质,是不可能被计划的”[6]。因为进步是一个自发又缓慢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关进步的知识首先将在少数几个人中自由地流动,如果这一知识确实是有效用的,这些知识才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必须予以明确的是,这一进程必须以广泛的个人自由为前提。
三、哈耶克法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知识论上的共通性
(一)知识论的共同性
依据现代哲学,知识仅指那些能够形成普遍共识的真理性知识,这种知识以科学知识为主要构成,还包括部分经过严格理论化、体系化检验的社科知识。但在哈耶克以及后现代学者看来,知识是十分广泛的范畴,由于主观性的根本性质,在现代知识论的知识范围之外,知识应当还包含着情境性知识以及那些无法通过语言明确表达的知识。
1.知识的主观性
从知识的内在存在方式,即知识与主体的关系来看,后现代哲学认为知识并非普遍的而是主观的。现代哲学所认为的知识的纯粹中立性,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过是“科学”和“真理”的谎言。知识的存在场域是每个人的大脑,这使得知识必然带有主体兴趣、情感、态度、意志的烙印。哈耶克一以贯之地延续着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在哈耶克看来,通过物理现象的刺激而在大脑中产生的一切知识,必须有赖于精神的中介,知识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人的精神世界自身。哈耶克的观点类似康德的“物自体”理论,就哲学主客观的一致性问题,他无疑是属于唯心主义阵营。
2.知识的情境性
在后现代哲学的解读中,知识是作为主体的对认客体的性质、特征、要素等的猜测和假设,因此必然会带有个体的经验、背景、情感性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历史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不存在脱离特定的境域的认识主体和认识行为,也不存在脱离特定境遇的知识。因此,从知识的外在存在方式,即知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知识具有情境性。在《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提出了“科学理论知识”和“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的分类[7]。对情境如何判断有赖于私人的经历、知识水平、判断能力,因此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只能停留在个人的大脑中而无法像科学知识一样取得统摄性概观的形式。哈耶克看来,科学理论知识远没有覆及人类知识范围的全部,因此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的存在是广泛且极其重要的,而这类知识却在当代遭受了极大的忽视。
3.知识的默会性
后现代主义者和哈耶克对知识给出了类似的定义,即知识并不局限于共识性的真理或科学定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这些能被称之为普遍、客观的知识之外,还存在海量默会的知识。默会知识的成立以对默会能力的承认为前提,默会能力是心智的不甚积极的方面,更多的与无意识、潜意识、准意识等相关。这类知识隐晦、模糊的形成路径使得它成为理性无法介入的领域。在构建论唯理主义那里,所有不经由理性的合法性检测,不能从因果关系、逻辑推理和语言陈述上加以呈现的,都不能称之为知识。但哈耶克认为,那些被视作知识唯一来源的显性的、规范的、系统化的知识,事实上只占人类知识总量中很小的比重。而被构建论者排除在知识王国以外的“默会知识”,才是知识的主要形态,它构成了理论知识大厦的基石。
(二)基于知识论的正义观
现代哲学的视角下,知识论是一门有关真理的学问,无关话语,也无关权力,更无关正义,真理以其单纯无价值性得到认可和广泛传播,成为纷繁的世界中唯一可以信任的东西。但是当信任成为信仰,真理成为权威时,真理必然与权力结合,而与作为政治伦理的正义相关联。
1.对元叙事的否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是“元叙事”的时代,元叙事指向单一的叙事模式、一极的话语体系及同一性的语言游戏,现代性的合法性就来自这种一元哲学。在元叙事的合法性下,真理与作为政治伦理的正义享有同一逻辑,正义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政治性共识之上。然而,后现代主义承认语言、话语中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普遍存在的差异性语言结构导致共识难以形成,既然共识无法达成,这就使得正义失去了统一判断标准,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说,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错误的。依哈耶克的知识论,以分散的形态存储于个体大脑中的知识具有私人化的内容和个体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具备建立判断知识真理性统一体系的条件。哈耶克的这种个人主义立场,间接表达了对一元话语体系的排斥,也即对元话语、宏大叙事的否弃。哈耶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正义观也并不是共识性的正义观,而是有关个人主义的正义观。因为在哈耶克看来,正义是个人行为的正义,正义的标准是个人行为的正当性准则,所谓的社会正义只是一种幻想和被毒化的语言。
2.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现代性标榜理性的普遍有效性,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正因为对真理的垄断,现代理性孕育着极权主义的顽疾。正如利奥塔说:“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8]一元叙事的知识模式将把全部知识类型纳入总体性、普遍性的社会理想的框架之内,对其所处位置、发挥功能作出确切的安排,或对人类的前程作出理想的预判。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哈耶克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他的知识观得到阐发。哈耶克认为,原子化的个体通过与一般社会规则的互动形成的内部秩序相较于那些通过刻意规划而形成的“组织”秩序而言是更可行的。哈耶克的这一主张正是对知识和真理问题深刻洞见的结果。因为既然任何的人或群体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的真理,那么所有号称根据它们所做的制度安排都将成为不可靠的存在。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曾掀起了研究哈耶克的热潮,其学术成果经过创造性转化获得了惊人的生命力。但是,在21世纪的最近10年里,哈耶克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热潮似乎已经褪去,似乎他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已经被挖掘完毕。但是,在与作为前卫文化的后现代理论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哈耶克思想的生命仍在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