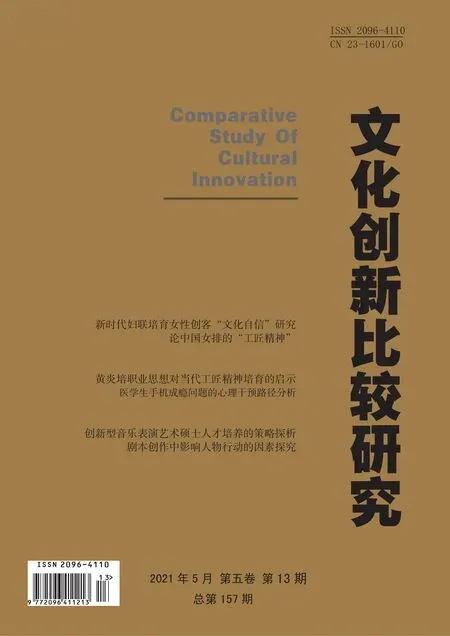从《摩罗诗力说》探究鲁迅对儒家诗学观念的继承与反叛
和之缘子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00)
《摩罗诗力说》于1908年发表于《河南》杂志,彼时正值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大论战时期,鲁迅以革命派的立场撰写了《摩罗诗力说》。这篇文论向来被看作“破旧立新”之先声,但从中可以窥见鲁迅的文学观实际上是对儒家诗学观念的继承与反叛[1]。
1 “诗言志”“诗缘情”
关于儒家诗学观念中对“情”“志”的理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阐释。孔子所处的先秦时期“礼崩乐坏”,人心浮动,在各类典籍的记载中,“志”作为“意”这样偏向“功利化”的解释明显居多(如《礼记·檀弓上第三》有“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这里的“志”郑玄注为“意”;《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训方氏》中有“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郑玄注为“志,谓志虑”),但还是有“情志一体”的例子。如在《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中有“贯乎心,藏乎志”的说法,此处卢辩注为“志者,心之府也。”除此之外《鬼谷子·阴符·养志法灵龟》中直言“志者,欲之使也。”……虽然“诗缘情”的说法是魏晋时代才提出的,但“情”和“志”都发于“心”,“志”也同“情”一样是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二者在诗歌创作的发端可以合而为一[2]。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论述;《礼记·乐记》中记载着“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毛诗序》中也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都是儒家所认同的关于诗歌源起的说法。而《毛诗序》中的“志”与“情”是统一的,指向创作者内心的意志和思想感情,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这里,诗是创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感性化的表达,产生于非功利化的需要[3]。
关于这一点,鲁迅《摩罗诗力说》中诗人的价值和诗歌产生的论述可以与之相和。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之为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起手,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和平,以之将破。”
鲁迅认为“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只是诗人用文辞将其表达出来罢了。而诗人作诗如同拨弦奏乐一般,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尽数抒发。此之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了。
鲁迅继承了儒家“诗言志”“诗缘情”的思想观念,在《摩罗诗力说》中也盛赞了拜伦诗歌中雄伟、豪迈的气魄和敢于抒发自己情志“言人所不能言”的创作方式,由此可见鲁迅的诗学观念中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性特质。他对“摩罗诗派”敢于说真话的大力赞扬恰好反映了其对儒家传统诗学中“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坚守,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对儒家建构在情感之上的教育观念的认同[4]。
但需要区别的是,鲁迅所赞扬的诗歌的抒情特质源于对诗歌立意“反抗”和“动作”的追求,需要让读者产生“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的感叹,由此“撄人心”,将人的本知唤醒,好让“铁屋子”里的人自觉醒来。而儒家倡导的诗歌“无用之用”,即使最初是为了陶冶人的性情,但本质上是为教化服务的,其抒情性是在迎合人的自然欲求基础上进行教化的工具,与鲁迅所倡导的诗歌的抒情性仍存在差别。在中国新诗发端时代,有很多大家认识到了中国传统诗歌“抒情性”特征存在的弊端而大力提倡西方诗歌的“叙事性”特征,如王国维在比较中西诗歌时就以拜伦为例,贬斥抒情诗人,进而反思中国抒情性文学的传统“以士大夫化的情感与趣味为主体,更多出于‘伦理’‘政治’冲动而以‘感物言志’面貌出现的传统中国诗歌,并不足以代表民族全体之情感与趣味,并不能表征民族全体之精神”。
2 诗的教化功能
《周易》有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这里,“化”与“教”都是对人施加影响使其达到一定目的的意思。这是“以文化人”的源起,是儒家诗教观中“教化”思想的依据之一。
《毛诗序》中对诗歌的教化功能是这样阐释的:“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说明在传统的儒家诗学观念中诗歌要有“讽刺”的作用,有教化的功能。但儒家诗教观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情感是其德育的基础,起码在孔子时代就有了这样的观念:“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认为要以诗歌所蕴含的最原始的情感引起人的共鸣,这首先表现的是诗歌的审美功用;进而在共鸣的基础上传达良好的价值观,改变人的思想,使人有良好的行为举止。类似的观点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也有阐述:
“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此他丽于文章能事者,犹有特殊之用一。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门必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门必机,即人生之诚理是也。”
鲁迅认为,文章的职能是“涵养人之神思”,而他以道覃的“游泳说”说明了文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学对人的陶冶如同游泳一般,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人的道德修养、培育人的理想,不仅呼应了前文“诗人之为语,则握住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起手,如睹晓日”,也与孔子所倡导的“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吻合的,好的诗歌可以使人的心思纯正。除此之外,鲁迅特别提出了文学不同于科学的启迪人生的功用,认为文章为人们提供了“人生之诚理”。此处的“人生之诚理”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事实法则”,那便是人生在世应当遵循的守则和为人处世的智慧,只要这样的道理一出现,人们就可以自觉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从这一点出发,鲁迅文学观念中关于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儒家早期的诗学观念是一致的。
但鲁迅对儒家诗学观念中的“教化”思想并没有全盘继承。《毛诗序》中将诗歌的教化功能进一步阐发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这里,诗的教化功能为统治者特有,是统治者推行“王道”的手段,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掌权者需要他的子民遵守一定的社会秩序,于是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即“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但对于鲁迅而言,诗一方面要启迪人生,更重要的是使人发现自己,倾听自己的“心声”:“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
鲁迅认为,诗歌应该有指导生活、指导人生之用。鲁迅以荷马的诗举例,说明诗歌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是有教化作用、“斯益人生”的,并且文学的教育可以调动人内心深处“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
“故人若读鄂谟(Homeros)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凡苓落颓唐之邦,无不以不耳此教示始。”
同时,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强调要发掘人心之“内曜”才可“挽狂澜于既倒”:“以是之故,则思虑动作,咸离万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谓之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可也。”
彼时的鲁迅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对现代物质文明持怀疑态度,认为人只有返归到自己的内心才可以找到真正的信仰,从而指导人在嘈杂寂寞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真正的安宁,看清楚前进的方向。鲁迅认为文学启迪人的心声是使人由内向外发掘自我、与世界相连通的过程,需要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毕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人能说出来被人们接受的都是人们本心所有的。这样的文学观念在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也有所体现。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源于其“熏”“浸”“刺”“提”四种“力”,前三种属于“自外而灌之使入”,最后一种属于“自内而脱之使出”,且“实佛法之上乘也”。这样的文学观一方面感受到了文学的“教化”作用,但又实在与儒家提倡的教化功能大相径庭[5]。
儒家所倡导的诗的教化功能是从外部对人进行约束,使之符合社会规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些都是儒家认为诗的教化功能应该达到的成果,但无一不是强调人应该形成的“认知”,而非人从心底油然而生的“直觉”。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而言,他们并不需要人民的觉醒,只需要于蒙昧中听从指令即可,“铁屋子”里的人是永远不必醒的。
3 对“思无邪”的反叛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看出鲁迅在“诗言志”“诗缘情”和诗的教化功能方面与儒家的诗学观念是存在相似之处的。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痛斥了孔子对于诗所作的“思无邪”的论断,认为“强以无邪,即非人志”——“无邪”是统治者为了保持暂时的平和、打压有识之士而对其文学创作进行的束缚,这种要求泯灭了人的志愿情感,压抑人的本性,是非常可恶的:“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
对于鲁迅而言,“撄人心”是诗人的天职,诗人要说他人所不敢说,将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挖掘出来,进而对人进行“启蒙”,为的就是“美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想”,使人的天性得到释放。但“思无邪”就像是给思想上了牢笼,让诗歌创造失去了自主性,因此他才“别求新声于异邦”。在鲁迅看来,“思无邪”就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走“单行道”,必须符合统治阶级规定的路线,不能损害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愚民”政策的变相说法[6]。
但对于儒家诗教观而言,孔子所说的“思无邪”非常具有权威性。《毛诗序》中有言“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对“思无邪”的进一步阐释。对于儒家以情感为基础构建的诗教观,不能任由通过人的本能形成的原始情感肆意放纵,需要用“礼义”进行约束,使之得到适当的抒发,最终使人的思想“纯正”,达到“思无邪”的境界。然而孔子所说“思无邪”的政治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厚,关于“温柔敦厚”的说法,孔子认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他认为学习《诗》是为了使人的思想符合“仁”“礼”等人伦观念而不至于愚昧,是从人本身出发的,是人立身之本,是追求精神独立的前提条件。但在汉代之后,“思无邪”被统治者采用之后就指向了符合“王道”,因为“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的诗教,在政治方面是由最高统治者主导,要求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使之“江山永固”。这就是鲁迅反对“思无邪”的理由,他实际反抗的不是孔子的“思无邪”,是后世成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中的“思无邪”[7]。
4 对“美刺”的质疑
在文章第一部分,鲁迅就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
接着鲁迅说以拜伦为首的一派诗人:“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与其反对“思无邪”相呼应的,是鲁迅对儒家诗教中“美刺”说的不屑一顾。
《毛诗序》中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说法,其中“谲谏”就是“美刺”,“上以风化下”自是直言也可,但“下以风刺上”需要臣子不直言君王之过,以婉转优美的言辞进言,使其改正错误,维护封建统治。
“谲谏”需要优美的文辞,即在诗中用赋、比、兴、风、雅、颂组织语言。“美刺”之说来源于孔颖达,他认为“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也、诗也;兴云见今之美,嫌于媚谄,取善事以劝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从儒家诗教观念出发,“诗”除了教化功用,就是要反映现实生活,进而指导现实生活,便需要诗有“刺”之用;而在这个循环中,儒家学说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即用优美的言辞、婉转的方式道尽其中曲折,就是“美”。这种思想到了后世有了更具体的讲法,“美”的方式就是用“赋”这种铺排的文体,即使“劝百而讽一”,也达到了“美刺”的效果;同时要使用“比”“兴”的手法,将严肃刻板的政治话语变得更富文采、更易于接受。“总而言之,主文谲谏的原则贯彻在文本中,贯彻在用诗的过程中,是儒家诗教观和温柔敦厚的处事原则的表现,也是君权高度集中情况下儒家人士对其限制的一种方法,同时,能够借助君权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
鲁迅对“美刺”的批判本质上是由于这样的方式最终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美刺”不过是统治阶层内部的自我麻痹,以保其“污浊之和平”。这样做压制了很多主流之外的声音,即“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但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撄人心”,才能让国民“上征”。鲁迅认为,诗歌只有唤醒人心才能“斯益人生”,而打动人心的文字需要真诚的品性,大声疾呼是比“谲谏”更为勇猛和有效的手段。
5 结语
《摩罗诗力说》作为鲁迅早期的重要文论,一直以来被视为“破旧立新”之作,但其文学思想不可能不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看到了他在鞭挞旧思想的同时疾呼变革、启蒙民众,但也应该看到他思想中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正是这些看似过时的东西为他的“推陈出新”提供了基本点。在对儒家传统诗学的继承与反叛之中,他才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