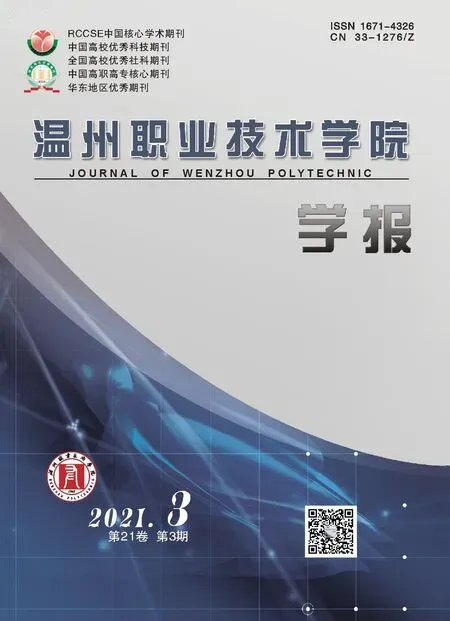儒家伦理观视域下北宋名相富弼的廉政范式
胡正裕,杨海娇,施明业
(1.中共文成县委党校,浙江 文成 325300;2.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浙江 文成 325300)
富弼作为一位“制科”出身的吏干高官,有着独特的廉政范式,其廉是与其德紧密相连的,其大德浑融之中包含了廉。其不贪权财即可视为廉:如“使相”薪俸极高(第一等俸禄),富弼却请辞,诸如此类的辞官辞赏在富弼的为官生涯中相当之多;又如“拎着乌纱帽干事”之为廉,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富弼知青州,恰逢“河朔大水”,富弼毅然私自行赈灾之法,“活民五十余万人”,并且将它作为平生最得意之作,称之为“大胜如二十四考在中书也”,事实上其伟大德行早已超越了廉洁之范畴;再如,不以公权谋私利即为廉,众所周知,王安石是位理财高手,客观上说,青苗法确实颇能理财,但后来因为很多官吏借此大行贪腐之事,对比以青苗法谋利者,富弼不行青苗法,不忍“与民争利”,其德其廉自明。
一、北宋初期士大夫精神对于富弼为官范式的形塑作用
1.北宋士风的提振
中国的士大夫主要来自儒家。儒家在传统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官吏阶层的儒家化之后。儒学在汉代开始被制度化,而后,儒生成了与权力最接近的一个群体。然而儒学并非一成不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隋唐之后的“进士制”使儒学攀上了它的巅峰期。大唐之后的五代,是个大乱世,它几乎彻底消解了唐朝的贵族社会。如果说五代有什么意义的话,除了得到了新发展的五代词之外,客观上破除了唐朝的贵族政治或许算得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即由兵变从后周夺得帝位,因而他对武人政治之害体会极深。在“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之后,宋太祖又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大政方针,其崇文抑武、重用儒者的程度为历朝历代之最。宋朝的科举制度远较隋唐更为成熟和完善,另外,相对于元明清,宋代科举在官僚政治中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宋朝绝不可能出现《儒林外史》之类的讽刺性巨著,因为大体上宋代文人的精神面貌是相当出色的,尤其是宋初在范仲淹等人影响下的庆历士风更是有极多可圈可点之处。
宋代可谓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这有其时代与文化的大背景,主要是皇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逐渐固化为“祖宗家法”,而此外的宗室、后妃、外戚和宦官这四种势力皆受抑制,所以君王与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有宋一代,总的来说是士大夫集团一枝独秀,与此相应,在士大夫集团的内部,激发出了一种百家争鸣式的思想文化,具体表现为学派林立。宋代儒学的复兴,不仅是儒学本身的复兴,更重要的当是士风的提振,即道德人格风范的树立。尤其是“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居多”(《朱子类语》)。
科举与书院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宋代书院之大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宋代教育的平民化。宋代的四大书院之称有好几个版本,其中睢阳、白鹿洞和岳麓三大书院是公认的,差别主要在嵩阳与石鼓,但在宋初,其他书院的影响远不及睢阳。学者罗义俊指出:“睢阳书院是宋初贡献最巨的一个重要的儒学复兴发源地,睢阳学统亦是庆历学统四起之前的第一学统,范仲淹尝就学与掌教睢阳书院,正是上承睢阳学统下启庆历学统四起的中心性的关键人物。”[1]在社会阶层流动方面,科举之上行渠道的完善,加上庶民读书人数的激增,势必会产生许多出自平民阶层的进士,这样一来,宋代士人队伍的扩充就极为迅速,因而出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宋代是传统社会中的“多士之时代”。
2.富弼与“高平学派”的密切关系
(1)高平学派在宋代“新儒学”中的地位。程朱理学之前,北宋新学有影响力巨大的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荆公新学”,而在此之前,还有以大政治家范仲淹为核心的“高平学派”。关于宋明理学,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范仲淹的宋学开创之功。钱穆先生指出:“王安石之于希文,亦推为一世之师。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濂溪为宋学开山,乃或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2]事实上濂、洛、关学这三大学系都与范仲淹有密切的关系:周敦颐(濂溪)为“高平讲友”,受过范仲淹的影响;“二程”从游过濂溪,后又为“安定门人”,所以范仲淹通过胡瑗(安定)下启了洛学;至于张载,其青年时期想去西北参军报国时,范仲淹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3]12723,并送他一部《中庸》,正是在范仲淹的引导下,张载后来开创了“关学”,范仲淹确实是“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此外,范仲淹还曾授“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以《春秋》,所以濂学、洛学与关学之兴,应该首推范仲淹识拔启导之功。高平学派是以士风领袖范仲淹为核心的学派,该学派精神中的“先忧后乐”,本质上是把宗教精神转化为对社会的责任,高平学派之高,首先高在经世的精神。余英时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视为宋代学术的中程,程朱理学则是政治变革再次失败后士风内转的结果。漆侠先生也认为宋代学术最精彩的是经世致用的范仲淹和王安石,高度评价范仲淹与王安石的气格,而将理学视为“荆公新学”的对手,事实上也是对理学的内转提出了批评。显而易见,在理学内转之前,北宋新学是更富于生气的。但由于两次政治改革皆以失败告终,至朱熹的南宋,政治改革转向了教化,彻底完成了宋代新儒学的内转。
(2)高平学派领袖范仲淹对富弼的深刻影响。范仲淹的确伟大,确实堪称“三不朽”,这早已成定论,如王十朋《范文正公祠堂诗》中称他“先忧后乐不为身,上与夔卨相等论”;朱熹赞范仲淹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高启《范魏公手书〈伯夷颂〉为其裔孙天章题》中的“有宋名臣谁第一?公为国家真辅翼。丰功茂烈何煌煌?信与日月争辉赫”等等。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写道:“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4]据此,可推知以下两点:一是在罗大经的时代,对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的评价尚有争议;二是从罗大经的语气上可以琢磨出在当时基本认为富、韩在范文正之上,但罗大经不那么认为,所以他要强调突出范仲淹,以便扭转众评。富弼在南宋仍有那么高的评价并不难理解,因为富弼在北宋当世即被誉为仁宗“嘉祐四真”之一的真宰相。所以大体上,范仲淹与富弼二人,皆数一数二之大贤,不相伯仲。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庆历圣德诗》中称他们为“一夔一契”,又如苏辙《西掖告词·富弼赠太师》所记:“庆历之盛,朝多伟人。维范与富,才业名位,实相先后。海内称诵,见于声诗,比之夔契。”范仲淹本人对富弼也是赞誉有加,如《依韵答青州富资政见寄》一诗:“枢府当年日辇襄,隐然一柱在明堂。亲逢英主开前席,力与皇家正旧章。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欲助清光。龚黄政事追千载,齐鲁风谣及万箱。伟望能令中国重,奇谋曾压北方强。故人待看调元后,乞取优游老洛阳。”事实上富弼高寿,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时间比范仲淹更长。富弼的成长与范仲淹关系密切,曾得其重要鼓励,“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5]70当时宋仁宋恢复制科,范对富说:“子当以是进。”这实乃范仲淹对富弼将为治世能臣的预判,“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5]70。范仲淹还是富弼的大媒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九》记载:“时晏元献公为相,求婚于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元献一见公,大爱重之,遂议婚。”[6]其后,范之于富,终身亦师亦友,“师友僚类,殆三十年”。所谓观人观友,以范仲淹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可知富弼之不等闲。
二、富弼所践行的“先忧后乐”
1.庆历新政:对于内忧外患“山雨欲来”的“先忧”与实践
江苏南通石港文山“范文二贤祠”大殿前柱的联语为:“齐韩富欧为名臣,先忧后乐;秉天地人之正气,取义成仁。”联中的“富”即为富弼,该联的语气中透露出在北宋乃至传统中国,“富欧韩范”确为名臣标杆。毫无疑问,与范仲淹关系异常亲密的富弼也深具“先忧后乐”的品格,并且能极好地践行。
北宋政权的取得是通过“黄袍加身”的政变,它倚仗一些大家族,再加上“杯酒释兵权”,又另外增加了一批高官显贵。放任、袒护大封建主,不抑兼并,所以北宋一立国便有暮气,“冗兵”“冗官”“冗费”与日俱增,朝廷“积贫积弱”的格局不可避免,导致国库空虚,财政赤字极为严重。儒家有其独特的仕文化,所谓“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庆历名臣具有强烈的行道思想,这一新型学者群体秉持以道事君之从政心理,做到了“仕宦者须脱小规模”之精义。富弼认为“得其时,则假富贵之位,以所学之道施于当世之民”。
发生于仁宗朝景祐、庆历之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中三次大规模的战役之“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还有“定川寨之战”,宋军皆败,再加上辽国趁火打劫而致的“庆历增币”(辽国称“重熙增币”),内忧外患严重。可以说宋仁宗是在战争情形即不得已的境况下才打算实行庆历新政的,但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则相当具有革新精神,尤其是富弼“更张之意,更胜韩、范”,富弼向仁宗提议编纂《三朝政要》以便配合庆历新政的实施并获准,高举祖宗之法的大旗,从祖宗言行中找出可用的事例加以新的诠释,颇显政治智慧。
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无疑是主帅,但作为副手的富弼其实同样伟大,所以庆历新政的荣光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富弼的。但是由于范仲淹过于特出,富弼的声名在一定程度上被范仲淹掩盖了,如在山东的青州地区,有所谓的“青州三贤”,即北宋时期先后在青州任职的三位曾为宰相或副相的贬官知州富弼、范仲淹和欧阳修。此三人皆有功于青州,三人中富弼最早知青州,而且很明显功绩最大,然而如今富弼在青州的知名度远不如范仲淹,仅由“三贤祠”在“范公亭公园”之中这一事实便可知。在青州的情形都如此,更不用说在庆历新政中的地位了。此外,富弼还是夏竦使婢女仿石介笔迹所伪造的“政变信件”的主角,石介本来写的是“行伊、周之事”,可见富弼在石介心目中的分量。
富弼上的策论也与范仲淹不相上下,他上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普通的策论大同小异,但“安边十三策”是富弼所独擅的。富弼可谓最了解当时的内忧外患,对内政与外交,他都有过人的对策,所以富弼最知晓“先忧”的背景,由于适当的政治机遇,他与范仲淹也最先有了“先忧”的行动。《宋史》记有一细节,即“此朝廷特用,非使辽故也”,这“特用”即是庆历新政之用:“帝锐以太平责成宰辅,数下诏督弼与范仲淹等,又开天章阁,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3]10253
但作为“先忧”的实践,庆历新政失败了,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不过其政治后果需要他们承担,他们的牺牲是被排斥出朝廷,但富弼无怨无悔,依然保有君子之德,这从其后在青州的救灾表现中可以看出。
2.青州救灾:“大胜如二十四考在中书也”之“后乐”
富弼在青州,通过自己的担当与才干,活民五十余万,并将其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作,称之为“大胜如二十四考在中书也”,真乃“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典范:“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3]10253-10254
“中书二十四考”指久居高官,在富弼心里,青州赈灾比久居高官重要得多。“民生”比官职和荣誉更重要,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此外,富弼值得骄傲的还有他的救灾智慧:一是吃住。他动员有钱人捐一些粮食,加上国家粮库的储备,尽量保障供给,避免灾民为食争斗,解决了治安的后患。他腾出十几处公房和私人闲置房,将灾民安置到靠近水源的地方,便于粮食和柴火的供应,给难民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二是选干。他将候补、闲居在城里的官员,按照各自的资历,临时招聘,发给津贴,并重申他们的工作将被记录在案,根据表现择优录用和请功,有效的制度性激励将这些人的工作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他们随即深入到灾民居住的地方,监督与调配粮、柴供应,还兼做灾民的心理疏导。三是关怀。他每隔五日,便派人拿些酒肉去悄悄慰劳这些志愿者,使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救灾的工作中。四是政策。凡是山林河泊里能够维持生计的物资,让灾民按需取用,不加限制。五是防疫。对死亡的灾民,政府统一设置公祭坑(丛冢)予以掩埋,不得分别安葬,避免疫病暴发和传染。六是征兵。由于赈灾得当,不误农时,第二年麦熟季节,将粮食按照路途远近发放给这些返乡灾民。同时设立征兵站,对愿意参军入伍的青年,一律征召。对这样的政府,百姓感恩戴德,愿意为国效力,不多时,便充实了数以万计的兵员。
富弼知青州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严重的极其令人沮丧的政治失意。但富弼就任青州,做到了“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民病如己病”。当时河朔一带洪水泛滥,大批灾民逃到青州。富弼没有驱赶他们,没有禁止他们入境,而是千方百计给他们备粮,不让他们饿死在青州。地方官若能做到“任一州之责者则忧一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富弼所忧远远超过了一州,他忧的是不分籍贯的灾民。他的做法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灾民们奔走相告,更多的灾民向青州涌来。最后,当时只有十几万人的青州竟然聚集了六十万灾民。这时青州官府若稍有不慎,后果便不堪设想。但富弼极有担当,能甘心“拎着乌纱帽办事”。最后的结果是富弼运用他的救灾智慧完美地解决了这场危机,富弼才德兼具,青州救灾可以说是古代救灾的范式,如《宋史》中的评价:“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3]10254
三、作为吏干高官的富弼廉政范式
1.“隐然一柱”:内圣外王的圣贤气象
所谓“弱国无外交”,弱国使者参与的外交必定是高危外交。辽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军事上辽强宋弱,大敌压境,宋廷无人敢去,只有富弼敢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岳飞说若“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富弼不是武官,可以说是“文官不惜死”,比岳飞所说更进了一层,实乃有豪杰气的士大夫。富弼很有辩才,先问辽国皇帝如果开战是否有必胜的把握。后问就算辽国胜利了,是利于辽主还是利于辽臣。他又说不打仗而增加岁币,是真正利于辽主的,而打仗最多只是利于辽臣罢了。此一说,起到了很好的外交效果。
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弼争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至于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弼声色俱厉,契丹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3]10252
富弼临危和辽,“谋动三国”,奠定宋、辽、西夏三国鼎立之格局,为北宋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为开创“仁宗盛世”创立了先决条件。历史上也有一些德高才小之人,有时被讥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富弼和他们相比最突出的是卓越的经世能力。富弼事功能体现他的豪杰气。所以富弼是“士志于道”的典型,或者说简直就是“圣贤兼豪杰”。他无愧于历代帝王庙,也无愧于“隐然一柱”之评。北京历代帝王庙的政治地位与太庙和孔庙相当。入祀者一是帝王,二是配祀名臣。帝王不一定都是精英,但配祀名臣几乎清一色地可称为精英,富弼是这79位之一。最理想的帝王模式是“内圣外王”,而最理想的贤臣模式则是“圣贤兼豪杰”。富弼被誉为“真宰相”,富弼能入选历代帝王庙,雍正“功在社稷,德协股肱”的评价是最好的解释,可以说是对他“圣贤兼豪杰”的认可。作为配祀名臣的富弼实乃不可多得的“间气伟人”,德高才大、勇毅无比。
2.仕以行道:辞官辞赏之为廉
儒家主张“不仕无义”,富弼能于有功绩的情况下拒绝升官。比如他第一次出使辽国乃吕夷简不怀好意的推荐,他却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不仅临危受命,还真正做到了据理力争、舌战契丹君臣,既善辩又强硬,不辱使命,“以一言息南北百万兵”,可谓厥功至伟,仁宗帝多次想给他升官,他的回应却是“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3]10250以及“愿陛下思其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3]10252-10253。又如在青州救灾大获成功之后,“帝闻之,遣使褒劳,拜礼部侍郎。”富弼只有“此守臣职也”这样一句极朴素的答语。这样的政绩之中,其德其才均无以复加,但他却认为是职责所在,从不居功以自重。
在一般人眼里,相位意味着权益。自古相位可谓人臣之极,但富弼并不恋相位,第一次是不同意“起复”,富弼在仁宗朝任相时,逢母丁忧,丁忧之制对于宰相而言有例外,可提前召回,称“起复”。仁宗虚位以待,五次下诏起复,但富弼亦五次上书坚辞,说这是战争时期特殊的制度,不当行之于太平之世,“此金革变礼,不可施于平世”[3]10254。如此不恋权位,真君子也!比之宋神宗时母丧不报、不服母丧的李定(王安石曾重用之)以及南宋宋理宗时丁父忧而起复的权相史嵩之,真有天壤之别。后来在熙宁二年(1069),富弼为正宰相,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相),富弼觉得自己被架空,便上了数十次奏章称病辞相,后宋神宗同意他辞相,不过他们君臣之间的对话颇耐人寻味,《宋史》中是这么记载的:“问曰:‘卿即去,谁可代卿?’弼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
宋英宗即位之初,富弼拒绝了英宗的额外赏赐,他拒赏的目的十分有远见,也十分伟大,正因为拒赏,他为自己保留了劝谏的底气:“富郑公为枢密使,英宗初即位,赐大臣永昭陵遗留器物。已拜赐,又例外独赐公加千。公力辞,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此微物不足辞。虽家人亦以为不害大体,屡辞恐违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赐不辞,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辞不受。”[7]
富弼为官,不当领的傣禄他便设法相辞,如他上书辞使相俸禄:“仆射师长百僚,使相者,文武中并是第一等俸禄,臣因病退,反有此授,固不敢当。真宗以前惜此官禄,未尝轻有除拜。仁宗冲幼即位,不曾检详祖宗故事,兼当时执政者徇私,亦欲自为地,遂开此例。终仁宗一朝,罢相罢枢密使者,皆除使相,其间最为不可者数人,并以不称职及过恶彰露,台谏官互有弹劾,本合得罪黜削,而亦皆除使相,领大藩,人情非常不允。臣其时正在中书,以仁宗暮召学士,次日宣制,无由进说。陛下临御以来,未尝除人,可从今以去,一一谨惜。若此等爵禄泛泛者容易付与,别或有大贤才,或有立功立事之人,陛下更何以爵禄旌赏之。使相以上,只有三师三公,其品秩虽崇,而俸禄甚少,比使相绝然不侔也。愿立法自臣始。”[8]
当然,他这份奏章不仅仅为辞自己一人之俸禄,主要还涉及为朝廷立制。他指出真宗以前惜此官禄,仁宗年幼即位,再加上执政者徇私,多得俸禄。而英宗新君即位以来,“未曾除人,可从今以去”,富弼劝英宗抓住机会,减少朝廷的财政支出,更要谨惜赏赐,对真正的大贤才或有立功立事之人的赏赐留有余地。
王安石变法,很多官吏借青苗法大行贪腐之事,富弼知亳州时不行青苗法,不忍“与民争利”,其德其廉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