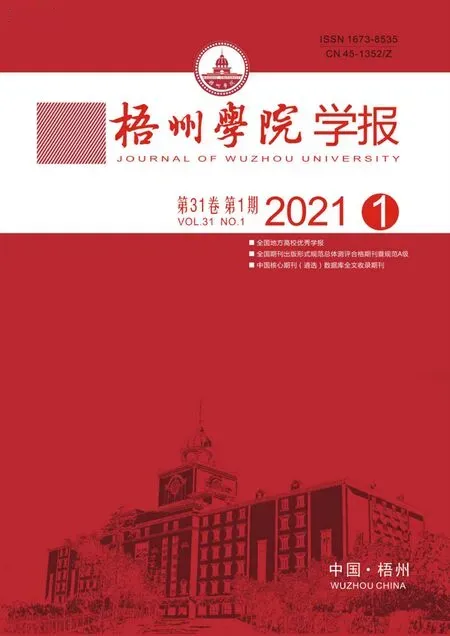组织行为学视域下的近代广西旅游演进规律的历史透视(1912—1949)
蒋勇军
(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旅游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载体,也是整合资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助推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晴雨表”,旅游能生动、形象、立体、客观地展示当时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鲜活地呈现社会演进的历史脉络。鉴于此,从行为文化视角,以1912—1949年为时间节点,以历史演进规律为切入点,以近代广西旅游为考察对象,独辟蹊径,对其进行全面剖析。
演进规律之总结,既是历史研究之要,也是学术研究的应然价值诉求。归纳起来,近代广西旅游演进的历史规律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一、旅游主体:从以官僚士子为主体到以普通百姓和文人学子为主导
在古代,为达到追新猎奇、求乐求知、求健求美等目的,上至贵族官僚等地位显赫的统治阶层,下至凡夫走卒这样的普通布衣百姓,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
近代以来,社会急剧变革、城市迅速崛起,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生活节奏加快,普通民众逐渐成为旅游活动主体,近代旅游呈现出大众化的发展趋向。
(一)普通百姓和文人:近代旅游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普通百姓是近代广西国内旅游活动的核心主体,是构架近代社会安全大厦的牢固基石,也是人数最多、居住地域最广的社会阶层,成为拉动近代旅游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普通民众是岁时节令游的参与主体。在近代这种形式的旅游活动相当普遍。广西各地,“端午划龙船,两岸观者如堵,有上前者,则喝彩鼓掌以助之”[1]。广西南宁“男女儿童平时除到剧场、电影院、儿童运动场外,并于室内天阶、路旁空地、郊外等处,作种种跳飞机、跳舞、滚铁圈、跳绳、打鸡头、打驼螺,捉鸡、乌龟占柱、放风筝等”[2]130。
其次,普通百姓是近代广西游园观光旅游活动的核心主体。1928年夏,河滨公园因“山明水秀,风景幽雅,每届炎夏,游人如织”[3]11。名山奇洞也成为当时普通百姓游览的首选之地,如“梧州茶山,树木扶疏,风景殊胜,上建中山纪念堂,内有图书馆,建筑颇为宏大;山麓右侧有冰泉山馆,山后为自来水池”,“每届夏天,游人络绎不绝”[3]11。
再次,普通民众是宗教旅游活动的参与主体。“月牙山峰,庙宇很多,香烟缭绕,暮鼓晨钟,一般信男善女,敬香求神,非常热闹”[4]76-77。
文人是节日旅游的重要参与力量。“重阳节,秋高气爽,是游山玩水的佳日,诗人画家,接踵而至,或登高歌啸,或饮酒赋诗,往往为之流连忘返。”[4]78
(二)留学生:近代广西旅游活动的主要“引领者”
留学生是近代广西出境旅游活动的积极引领者和有力助推者。近代以来,为救黎民于水火,挽国家于倒悬,广西籍有志青年远涉重洋,寻求革新弊政、强国御侮的“药方”。他们以公费或自费形式,开始了漫长的修学之旅,成为引领近代广西旅游的核心力量。他们或学习西方器物,或考察宪政,或学习思想文化,或研究历史地理,或探讨地方自治,以重启蒙、崇变法、倡民权、启民智、育新民、淳民俗为路径,以陶铸国魂、富国强民、救亡救存为宗旨。毋庸置疑,赴欧美留学之旅为广西培养了不少文化精英、政府智囊,对推动近代广西旅游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马君武、苏希洵、王力、谢康、梁继本等人在海外均获得博士学位”[5]。他们积极倡导“以旅兴国”与“以旅强国”思想,成为广西政坛或教育界的出类拔萃者。
总之,近代广西留学生的海外修学之旅,使其视野开阔、见识广博、改革创新意识浓厚,成为旅游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旅游政策的实际制定者、旅游规划的精心设计者和旅游法规的贯彻实施者。
二、旅游资源开发建设:从盲目“无序”走向规范“有序”
古代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基本上处于自发和盲目开发状态,或官员个人开发,如:唐代宝历元年(825年),“桂州刺史李渤辟隐山”[6]5678,开发南溪山;或民众捐资开发,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当地百姓捐资在富川油沐乡“修回澜风雨桥,方便行人”[6]5876;或士绅捐资开发。
近代是广西旅游资源从盲目自发式开发开始走向有序式开发的重要时期,政府重视绿化工作和市政建设,力求做到整体布局、统一规划,旨在整合优势资源,提升旅游管理绩效。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植树木、掘温泉:提升旅游景区形象吸引力
景区旅游资源开发,以科学布局为重。1932年成立桂林市政处,试图构筑以绿化、美化和亮化为行为导向的旅游景观屏障。采取“培育各种树苗,移植于各马路两旁,及各名胜处,已种有100余万株”[7]13。1933—1934年,广西省政府统筹规划,采取分步实施的景区美化策略,在各县城“共种植苗木205,791,647株”[8]。旨在扩大绿化面积,优化旅游资源空间配置,构建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景观,重塑旅游城市形象。
温泉是重要的旅游资源。经常泡温泉浴,有消除疲劳,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安宁心神,减少疾病和增进身体健康之功效。“治关节之疾,缓四肢麻痹之感,克睡眠之障碍”[9],客观上助推广西温泉旅游资源的开发。据统计,近代广西开发的温泉共计14处,主要有“象州温泉、昭平温泉、贺县温泉、怀集温泉、陆川温泉、上思温泉、博白温泉、桂平温泉、钟山温泉等”[10]。总之,近代广西温泉资源的开发,寓养生于旅游之中,发挥了强身健体的功能。
(二)建公园、修设施:打造旅游景区品牌影响力
发展旅游,要以娱乐设施建设为重,而娱乐设施建设又以公路交通为先。“游览旅行,其关键则系于交通”[11]。1937年桂林市政局统一规划,加修道路,有序推进公园设施建设。“增加电灯,培植树木,添栽花卉,修理亭树,供人坐憩”[7]13,旨在实现公园设施建设的规范化,“供人游览”[7]13。20世纪30年代,广西市政厅统一规划,在“全省共建有公园41所”,“其中,面积以向都公园为最大,以东兰中山公园为最小”[12]。公园设施的改善,有助于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为旅游者提供一个舒适的娱乐休闲环境,是旅游者慕名前往、名副其实的休闲天堂。
发展旅游,以强身健体的娱乐设施建设为基础。国民政府时期,南宁市政府统一规划,于1937年修建了两处游泳场,一处为乐群社游泳场,一处为精武体育会游泳场。“其设备有男女更衣室各1个,跳台、跳板等齐全”[2]132,旨在强体质,健体魄,聚合力,提精神。游戏场为儿童健身之乐园。1930年梧州工务局修建了儿童游戏场。“内设儿童揽架滑板等游戏器具”[13]771。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广西合理布局,陆续修建了一些体育娱乐场所,“共修建了273处”[14]。总之,近代广西各地体育旅游设施的修建,坚持以民众娱乐诉求为前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主动参与为手段,以提升民族素质、提振民族精神为目标,旨在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扩大其影响力,提升其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三)拨经费、修古迹:提升旅游景区整体竞争力
名胜古迹修缮,资金为要。1937年,广西成立修理名胜委员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制定统一调度的财政管理政策,旨在实现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拨3万元为修葺风景之费”[7]13。为了增强名胜古迹修缮的实效性,该局还“供给技术人员,受命办理”[7]13。“将风景区道路开辟完善,使其畅通无阻,可以减少游程与时间”[15]。当时修缮的名胜古迹主要包括:紫金山、风洞山、普陀山、月牙山等处。20世纪30年代,邕宁县亦颇为重视,其修缮与保护的名胜古迹主要有“昆仑台、青山塔、罗山寺、宝林寺、六公祠、王文成公讲学处和王守仁遗像碑碣”[16]。修缮工作井然有序、合理推进。
综上所述,近代广西旅游资源开发,坚持以交通设施修建为“经络”,以名胜古迹开发为“血脉”,以旅游娱乐设施修筑为“皮肉”,以旅游景区建设为“骨架”,旨在增强景区的吸引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旅游组织方式:从注重结伴而行到崇尚集团旅行
在古代社会,旅游者一般采用结伴而行的旅游组织形式,但也不排除个人单独或者带仆人外出旅游的可能。“同游者庆远学博胡君文江,忻城大令莫君向岩,邱子仁甫、徐子治轩、陈子宝田,吴子海树、冯子相山、施子、庞子及献甫共10人”[17]。可见,结伴而行是临时拼凑的一种行为,具有自发性、随意性和偶然性。
从结伴而行到集团旅行是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一种值得倡导的风尚”[18]52,可以“增进友谊”“交换知识”“省钱”“发泄积郁”“裨益身心”和“训练合作精神”[19]。但是,集团旅行也并非十全十美,缺乏自由度,日程安排紧张,旅客较多。
近代时期,集团旅游成为深受旅游者喜爱的一种旅游形式。1932年“五五”旅行团“游览了梧州白云山、中山纪念堂、河滨公园、龙华寺、飞阁庵,参观了南宁中央公园;考察了柳州中山纪念堂、河滨公园,游览了桂林的独秀峰、叠彩山、七星岩和良丰花园”[20]。总之,“五五”旅行团在桂时间较长、考察地域较广、游览景观较多。集团旅行因具有省时方便、价格较便宜、有安全感、享受导游服务等优点,加之具有普遍的适应性,遂成为旅游者极为推崇的一种旅游形式。恽荫棠于1935年6月,“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由汉入湘”,“在桂勾留一个月”[21]。
综上所述,集团旅游是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宗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旅游活动。其出现,推动旅游活动从临时组织、随意拼凑、率性而为特征的结伴旅游向科学规划旅行线路、合理安排食宿、统一组织游览观光为特征的集团旅游嬗变。
四、旅游流向:由国内旅游到国内国际旅游并重
与古代相比,近代广西旅游流向呈现出由近及远、由城市到乡村、由内地到沿海、由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落后地区、由国内向国外延伸。具体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一)国内旅游流向:由近及远、由城市到乡村
近代广西旅游日益普遍化,国内旅游空间不断拓宽,旅游流向呈现由近及远、由城市到乡村的发展趋势。为开展学术研究深入农村游;如“薛暮桥为开展调查研究由江苏流向广西”;为宣传抗战救国而远游,“齐白石由内地湘潭到桂省北海、钦州”[22]。
(二)国际旅游流向:由内而外和由外及内并重
国际旅游是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历史产物,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在近代,广西国际旅游主要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2种情况。
1.入境旅游之流向:以欧美国家为“主体”,以周边国家为“两翼”
入境旅游是衡量近代广西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提高旅游效益、增加旅游收入的有效途径,还是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路径。
从入境旅游的旅客流向来看,西北、正北方向有英国、丹麦、法国、波兰、意大利、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的客流来源;东北方向有美国的客流来源;东南方向有印度、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客流来源,而英美两国则是近代广西入境旅游客流的主体。1932年,“英国入境旅游人数71人,占入境旅游总人数的58.20%;美国入境旅游人数19人,占入境旅游总人数的15.57%”。周边国家在入境旅游客流中占次要地位,“来自印度的入境旅游人数2人,占入境旅游总人数的1.64%;来自马来西亚的入境旅游人数1人,占入境旅游总人数的0.82%”[14]829。可见,近代广西入境旅游,以欧美国家为主,以东南亚国家为辅。
2.出境旅游流向:以周边国家、地区及发达国家为主
首先,广西出入境旅游流向主要以周边国家为主体。1932年桂省民众赴越游历的人数“共计7809人”[13]811,越民赴桂游历的人数“达1337人”[17]。其次,广西出境旅游流向主要以周边地区为主导,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1934年,“从梧州赴香港的出境旅游人数,共计12157人”[13]772-773。可见,秋冬两季出境旅游人数较多,春夏两季出境旅游人数相对减少,季节性差距较为明显。再次,广西出境旅游流向以欧美国家为辅,出境旅游人数总体不多。1934年,“从龙州赴国外的旅客人数,共计93人”[13]772-773。最后,广西海外修学旅游流向主要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以周边国家为辅。“赴日本修学旅游的人数589人,赴俄国修学旅游的人数42人,赴比利时修学旅游的人数7人,赴越南修学旅游人数4人,赴美国修学旅游的人数103人,赴英国修学旅游的人数12人,赴比利时修学旅游的人数7人,赴奥地利修学旅游的人数1人”[23]。总之,近代广西出境旅游,其旅游流向呈现由内而外、由周边国家流向远距离的欧美国家,出游空间向纵深方向拓展延伸。
五、旅游景点布局:由点轴线性态到多元复合态
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古代广西旅游景点的布局,基本上是散点状布局,并沿桂江、西江、柳江不断延伸拓展,形成旅游点——旅游轴的线轴分布态势。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推动近代广西旅游的发展,使近代广西旅游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复合态,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从景点布局的趋向来看,由点轴、线性式分布到集聚、交叉式分布嬗变
广西旅游景点空间布局整体上呈现出南北多、东西少、中部居中的集聚型分布态势。具体言之,呈现出由以水路交通线为主的线性分布向沿公路、铁路、水路交叉分布嬗变。广西桂林旅游景点的空间布局既有沿中正路、中南路、桂东路、中北路、桂西路等公路交通线呈线状分布;也有沿漓江、桂江等水路交通线呈线状分布;还有沿铁路交通线分布。南宁的旅游景点布局主要沿公路交通线呈线状分布。梧州的旅游景点布局主要沿桂江水路交通呈线状分布。柳州的旅游景点既有沿柳江水路交通线呈线状分布,也有沿公路交通线呈线状分布。龙州的旅游景点布局既有沿龙江水路呈线状分布,也有沿公路交通线呈线状分布。
(二)就景点布局的结构而言,由散状分布向差序化格局推进
古代广西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信息闭塞,开发能力有限,景点开发具有随意性和偶发性,决定其景点的空间布局呈散状分布特征。近代以桂林、南宁两个核心节点,凭着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形成一级旅游景区,以梧州、柳州、龙州、百色、玉林、天保、平乐为主要节点形成二级旅游景区,以阳朔、兴安、桂平、北流为次要节点,形成三级旅游景区,以全州、义宁、怀集、融县为末端节点,形成四级旅游景区,其内部吸引力由内而外呈距离衰退规律。总体而言,近代广西初步形成了四维层级结构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性,即形成一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桂林—柳州—南宁—梧州—龙州大体上沿桂江、柳江、浔江、西江等河流分布;形成二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阳朔—玉林—百色—天保—平乐大体上沿主要公路交通线分布;形成三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全州—兴安—灵川—贵县大体沿湘桂铁路分布;形成四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宾阳—宜山—上林—武鸣—融县—怀集—义宁—北流沿公路交通线分布的格局。
(三)从旅客游踪的分布来看,由单一热点型向热点、冷点和温点型并存分布演迁
古代广西旅游景点的空间布局主要呈点状的节点分布趋向,当时广西旅游景点稀少,零散地分布于桂林县、邕宁县和苍梧县,加之文人士子好游,遂成为热点型旅游景点。
近代桂林、南宁等中心城市,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独特优势旅游资源的集聚,逐渐成为核心热点旅游区,“桂林拥有著名旅游景点36处,南宁21处”[3]10-48。柳州、梧州、龙州等城市,或凭借区位交通优势,或依托战略位置优势,逐渐成为次热点旅游区。“梧州拥有著名旅游景点20处,柳州、龙州各13处”[3]10-81。北海、钦州等沿海城市,依托其区位优势,吸引外国游客前来避暑,成为温点旅游区。百色、河池等中等城市,因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加之经济发展落后,遂成为次冷点旅游区。阳朔等县级城市,由于市政建设滞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之,城市整体规模很小,遂成为冷点旅游区。总之,近代广西初步形成了桂林、南宁热点旅游区—梧州、龙州和柳州次热点旅游区—北海、钦州温点旅游区—百色、河池次冷点区—阳朔冷点旅游区的梯度分布格局。
六、旅游交通工具:由传统到传统与现代交织并存
古代人民喜欢游山玩水,寻胜探幽,旨在锻炼身体、刷新精神。其旅行时“水用舟楫,陆用车马,或则徒步往来,但非半年数日,不能达其目的,览其全”[24]13。生动凝练、高度地概括了中国古代游客出行的基本工具,包括筏、舟、马车、轿等,这也是古代广西旅游者外出旅行的重要工具。
而近代以来,则不然,“飞机旅行,身登九宵,刹那千里,回翔数刻,饱览九州,汽车旅行,风驰电掣,游览湖山,千里游程,数日可了”[24]13。寥寥数语,生动地诠释传统旅行交通工具向近代化交通工具嬗变,描绘出一幅纵横交错、流光溢彩、波浪式前进的历史画卷。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工具不断进步,广西旅游工具呈现出由传统走向传统与现代交织并存的发展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7个方面:第一,公共汽车成为近代广西旅游的重要工具。公共汽车作为民众旅行的主要公共载体,具有经济、安全、方便、舒适的优点,颇受民众欢迎。“公共汽车办事处,备有大小车辆,供居民雇用”[2]13。第二,轿子仍是民国时期广西重要的旅行工具,在偏远山区仍得到广泛使用。“惟乡僻县份则仍使用,式样不一,与江浙大同小异”[2]13。第三,洋轿是近代广西新出现的一种旅行工具,广西南宁洋轿,“为数甚多,营业亦旺”[2]13。第四,传统的人力车是近代广西城市旅游的重要代步工具,充斥着街头巷尾。“梧州桂林有2处,其余玉林有3架;柳州乐群社自置有4架,专备接送社中旅客之用”[2]13。第五,自行车日益成为近代广西城市旅游的重要代步工具。广西南宁“有自行车租贷店8间,散布于中山路、民生路一带”[2]13。第六,拖渡是近代广西水路旅行的重要工具。国民政府时期,广西拖渡主要有:“广州—梧州、梧州—三水、梧州—贵县、梧州—柳州四条航线”[25]45。第七,民船是近代广西水路旅游的主要工具。民国时期,“梧州至桂林,尚有可以搭客之民船来往。大者舱底装货舱板搭客;小者则只搭客,不载货,索价较昂,亦较快捷”[25]45-46。
由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及特殊地理条件的制约,决定了近代广西旅游交通工具的嬗变带有双重性,既传承了传统旅游工具,又发展创新了近代新式旅游工具,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并存的格局。“交通器具还相当完全,有公共汽车和黄包车,脚踏车也很普遍,此外还有轿子”[4]78-79。彰显新旧并存、中西合璧的时代特征,实现优势互补,契合不同层次的旅客需要,为其观光游览提供了便捷和快速的服务。
综上所述,近代广西旅游的历史演进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推进的过程。就演进模式来看,既有暴风骤雨式的激进演进模式,也有春风化雨式的渐进演进模式。就演进的社会环境来看,既有先发内源性因素影响,也有后发外生性因素影响。就演进动力来看,既有内生动力,也有外部推力。总体而言,近代广西旅游发展,体现了旅游资源由官僚“独享”向普通民众“共享”转换,旅游开发由盲目无序趋向有序合理,旅游空间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由落后地区趋向发达地区,旅游工具由旧到新、由传统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