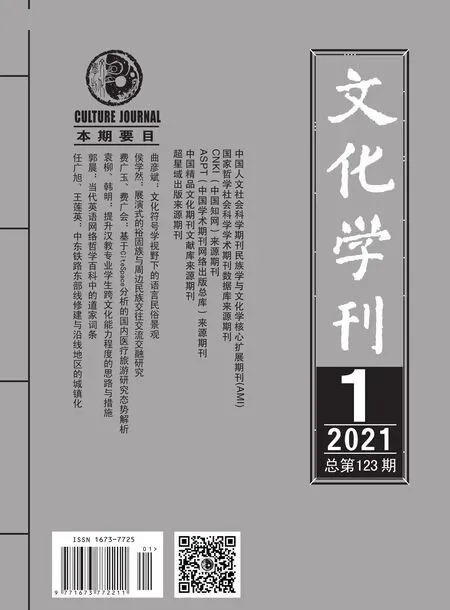从“人格二重性”浅析风格与人格的关系
孔祥睿
一、人格双重内涵的阐释
人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个性,这个概念来自希腊语中的“面具”,类似于中国京剧中的脸谱。那么问题就来了:根据人格这个词的基本含义,人格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而又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可见它是每个人特有的一种人本质的生存状态。既然是一种内在的状态,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外在的面具呢?因为人格可以脱离人本身而存在,外化表现为道德的、审美的、法律的、社会的各方面的要素去展示自身的价值,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人格其实就是人本质的生存状态的外在表现。
这样人格解释为“面具”也就不再难理解,因为在社会中存在的每个人都是渺小而独特的个体,为了能更好地生存,我们不得不给自己戴上“面具”,将一部分真实的自我掩盖起来,以求在社会中更好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生活就好似戏剧舞台,每个人为了能够在舞台上完成出色的表演,不得不扮演着各种角色,也就需要我们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原本这些“面具”并不是人本身的一部分,但是时间久了,这些“面具”似乎变得难以丢弃,逐渐融进每个人的个体存在之中。由此,作为人格就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是“面具”之下的人格,另一种是“面具”所呈现出来的人格。我们将其称为“人格的二重性”:第一重是戴着“面具”的,为的是在生活中能够趋利避害;第二重就是“面具”下真实的自我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面具”更像是一个保护伞,可以使人自身的潜能被无限激发,随意发挥创造力,自然流露真情实感。
关于双重人格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个人与周遭环境(包括他人、自然、社会、阶层)的复杂关系造成的。举例说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到宗法制度的影响,这种通过血缘关系所连接成的看似温情脉脉的政治制度,我们在不否认它进步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缺陷。在这种制度下的文人,既要用宗法制度来规范自己,又要在此基础上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情感,这显然限制了文人人格的丰富和发展,文人在夹缝中求生存,便逐渐形成面具内外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就嵇康来说,作为“竹林七贤”中性情比较豪放刚烈的人之一,在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时候那样愤慨地表达对于仕途的不屑一顾,完全想不到《家戒》也是出自他手。在《家戒》中,我们完全感受不到这是一个有棱角的嵇康,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对于当地的长官表示尊重就可以了,切不可交往过密,因为官场险恶以免招惹是非,陷入困境;不要随意接受邀请去参加聚会,因为参加聚会就避免不了要喝酒,不管你愿不愿意喝都要装模作样地端起杯子,以免人家说你不合群。我们从《家戒》中看到的更像是一个畏首畏尾的嵇康,与之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嵇康判若两人,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这样“面具”内外有双重人格的文人比比皆是。
二、人格与风格的一致性
作家创作为的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抒写自己的理想壮志,阐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最终升华为自己的人生体悟和价值追求。这就明显可以看出作家主观方面的因素对于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有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而在主观因素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格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影响文学风格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在社会中碍于各种现实因素,人们可能不能够完全将自己的人格释放出来,那么在作家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就会将自己藏匿于“面具”之下的人格展开出来,这时候“面具”下的真实人格与创作风格具有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这种一致性仅仅在一种情况下出现:作家真正具有伟大的人格,因此他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带有伟大的风格。换句话讲,就是作家“面具”内外的人格是一致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正如王国维所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文天祥等文人,他们的人格就和他们的文学创作风格是高度一致的。具体以庄子来说,他的散文创作呈现出来的是汪洋自肆、博大精深的创作风格,这与他的伟大人格具有一致性。究其原因,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总是表现出以朴素自然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收放自如的想象空间、心斋坐忘的方式追求自然主义,并希望能够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庄子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人格进行改造、升华和转化,最终形成了专属于他的艺术风格,“面具”之下的真正人格和创作风格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关于风格和人格的一致性问题,有两个非常鲜明的观点:一个是中国古代所提出来的“文如其人”,另一个是布封所提出来的“风格即人”。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理解上的误区,不管是“文如其人”还是“风格即人”,都不能说明风格和人格是简简单单的对等关系。虽说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他们精神面貌的展现,但是我们只能说人格是构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作家创作风格的全部,当人格和审美理想达到一致和统一的时候,作家的人格和创作的风格才会达到一致,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即真正将“面具”之下的真实人格揭开来给人们看。
三、人格与风格的矛盾性
矛盾性更多体现在作家创作时戴着“面具”,将完美的一面示人。换句话讲,作家是戴着“面具”在创作,实际上“面具”下面真实的人格并没有示人,这就造成人格和风格不一致。总结起来,矛盾性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家具有复杂的人格,但是他的作品却具有简单明了的风格;另一种情况是“面具”示人的人格与“面具”下的真实人格有着巨大的差异。
第一种情况即在现实中作家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他们可能会选择佩戴不同样式的“面具”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那都不是他们真实的人格,他们更愿意在创作过程中展现真实的人格。典型的例子如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孙犁,孙犁所面对的现实情况比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要黑暗得多、痛苦得多,但是孙犁却没有因为现实生活影响他的人格和创作风格,在他的心底装着的还是真、善、美,所以他说:“我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去回忆它。”[2]糟糕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改变其内在的风格,是因为这些实际的人生境遇并不能很好地给孙犁带来真正的审美体验以及并不适应他的审美理想,并且达不到他的审美诉求,所以他还是选择保持他的原本。
矛盾性产生的原因不外乎审美理想高于作家现实人格。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活动,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主观性。“只是要作文章,令人观赏而已。”[3]由此可见,作家都期许作品能够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期许在作品中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并由此激发出读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一个作家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和现实中所追求的理想相一致,那么人格和风格就会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如果一个作家追求的审美理想高于现实生活中追求的理想,那么人格和风格就会呈现出矛盾性。具体举例,唐代著名的作家韩愈,后人对于他的散文赞不绝口,但是当提到他的人品的时候不免有些微词。朱熹说,在现实生活中韩愈是一个贪权慕禄、贪财好色的人,这与他文章所彰显的那种大气磅礴、浩然正气的风格相差甚远。我们明显可以看出,韩愈在生活中很少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但是他在行文过程当中却时刻按照儒家的规范来要求自己,他的审美理想和他的真实人格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既势必会导致人格和风格之间相差甚远甚至出现矛盾。
四、结语
如今我们重提风格与人格的关系,不论是探讨人格与风格的一致性还是矛盾性,都是为了摆脱我们已经墨守成规的一些观念,如“文如其人”“风格即人”,认为作家人格与创作风格就是简单的对等关系。事实上,人格和风格的关系是复杂的。同时,探讨人格和风格的关系又是为了明确作家创作的本初目的:以人的精神品质、思想道德为创作的标准,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要戴好“面具”创作,求得更好的生存,而且不要忘记“面具”之下的真实人格,达到真实人格和创作风格高度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