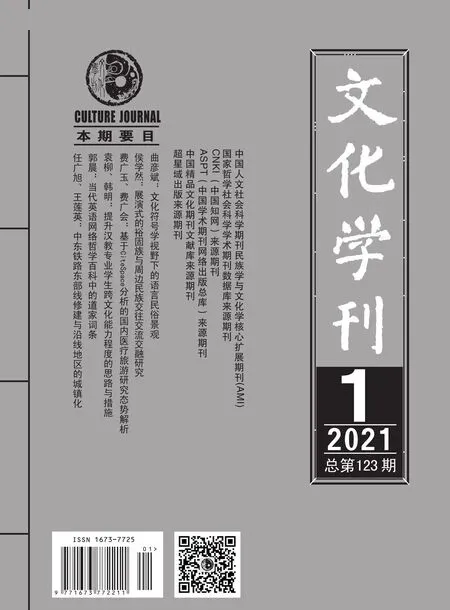少年意象之永恒困境
——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王良娟
《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常读常新的经典作品,原因之一是书中阐释了人类生命体在自然及社会文化语境中存在的永恒困境。这本书20世纪50年代问世,很快引发了责难和赞美两种阅读争议,就如评论家所说,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即便到了现代社会,它还不断地被当代大师学者推荐为必读经典。
一、少年意象
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少年是一名叫霍尔顿的十六岁中学生,少年霍尔顿出身富庶,就读于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流学校的潘西中学。但这所好学校的学生霍尔顿却是着装怪异满口脏话,他抽烟、逃课,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厌憎和嘲弄。当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后,他独自去了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这期间他喝酒,逛夜总会,住小旅店找妓女,不断宣泄着他对身边一切人与事的憎恶。最后,他决定逃到远离现实世界的偏远西部,装聋作哑地去生活,却又舍不得和自己能谈得来的老妹菲苾。当接到消息的老妹赶来要和他一起出走时,霍尔顿的逃离计划就在这场劝阻老妹的过程中泡汤了,最后以轻度精神分裂症被送进医院治疗。
表面看来,少年霍尔顿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小子”:通篇遍布“杂种”等惯用语,极大地挑战着人们对语言的审美接受心理。被社会认可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潘西中学,在他看来却是个阴森可怕的地方。校长是“假模假式”的势利伪君子,只会巴结讨好有钱人。同学“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打篮球的抱成一团,天主教徒抱成一团,那般混账的书呆子抱成一团,打桥牌的抱成一团”[1]172。异性在他眼里也是庸俗让人厌烦的:“姑娘们的问题是,她们要是喜欢什么人,不管他是个多么下流的杂种,她们总要说他有自卑感……连聪明的姑娘也免不了。”[1]178少年霍尔顿厌憎学校的一切,对成人世界中的一些价值取向也充满鄙弃。家人对他“成为成功人士”的期待,在他眼中是虚荣庸俗的打高尔夫球、买汽车、摆臭架子等。他在生活里“痛恨一切”,似乎总想要对抗些什么或破坏些什么。
对于少年霍尔顿的叛逆沉沦,蔡沂岑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了霍尔顿这个卫道者的悲戚和疯癫[2]。屠后红等从小说写作年代美国社会的荒诞特质来分析“霍尔顿”们的救赎主题[3]。还有研究者从生态批评、反成长叙事等角度解读作品,不一而足。笔者以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更多是它对社会、人性的共鸣与思考。所以笔者从人类生命体的少年阶段这个视角入手,通过解析少年霍尔顿的遭遇、心理及行为,明确存在整个少年群体身上那种强烈的迷茫、绝望及寻觅的执着。
二、永恒困境
木心先生说:“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和骚乱。”[4]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恒久魅力,自然也少不了这种永恒困境的呈现。少年的困境在于开始远离童年的天真与单纯,却又无法淡然接受成人社会的复杂污浊和世故。他被时光推出童年之门,内心却强烈地抗拒着即将要进入的成人世界。他被童年排挤,自己又排挤着成人社会。少年阶段,就如一个站在荒野里的游魂,迷茫、孤寂、绝望但又执着地想抓住点什么。当个体生命脱离了备受宠爱的儿童阶段,家庭和社会就会迅速要求青少年的社会化。这种跨越困境就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悬崖”意象:少年站在“悬崖”上,身后是正远去的童年,崖下是充满着未知的成人世界,而“悬崖”就像少年的成长之痛,那份彷徨与痛苦,充满了献祭式的悲壮。
少年霍尔顿外表粗俗怨怒,内心却是柔软善良的。他热爱小说和音乐,还有老妹菲苾脸上的笑容。他给做儿童慈善的修女捐款,他看见老妹菲苾学校的墙上有“×你”两个字,就马上用手擦掉。面对成人世界,他不知如何抗拒,只能用诅咒、出走来表达自己无力的悲哀。他和菲苾谈到自己做一个麦田守望者理想:“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1]229成人世界的虚伪污浊让这个真诚少年徘徊不敢向前,而把生活理想定在回头的守望上,这个温柔又无奈的追求只增重人的伤感。
与少年霍尔顿生活的那个嘈杂混乱的都市比,《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少年维特身上更多体现为自然人性的元素:眼前是青山幽谷、晨光夕照的美丽山村;身边是聪敏单纯,坚毅善良又勤谨娴静的纯真少女绿蒂。但维特的悲剧在于他拒绝将自然美好的人性混同于成人社会体制的腐朽和人性的庸俗。少年维特的成长痛苦以与成人世界彻底决裂为结局,在枪声中自绝性命[5]。少年霍尔顿的焦虑却源自他身上与成人世界有千丝万缕的瓜葛,比如他痛恨电影,自己又百无聊赖地在电影院消磨时间;他讨厌庸俗虚荣的女朋友莎莉,但又迷恋于她的美貌和她搂搂抱抱。他不满“混账的”的成人世界,却又只会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来麻醉自己,所以最后屈从混同于成人社会是必然的结局。与少年维特英雄式的捍卫自己生命天性的决绝战斗力比,霍尔顿的心路历程是或将是更多少年的痛苦选择。这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小说成为经典的恒久魅力所在。
三、当下关怀
生活或文化语境下的困境不外乎两种结局:有解和无解。有解是以强大的思想洞明了某种现象或思维的暗角,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以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隐喻了拉丁美洲孤独自闭求生存的惨淡结局,提示了团结与生存的关系。无解则是困境触及个体生命灵魂最深层的恐慌、孤寂、绝望以及微茫的希望,它无从释怀,常思常悲。比如《红楼梦》中,面对情色名利终成空的无奈,曹雪芹最后让贾宝玉遁入空门,以空化空,不了了之。而设定宝玉原型为无知无欲的石头一块,已是铺垫了无用勿为的悲凉基调。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成为少年困境的一个代名词,真实地呈现出人类在少年阶段的彷徨与焦虑,这也是这部小说被青少年奉为“圣经”的原因之一。
少年是个特殊的群体,虽然少年霍尔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少年困境将是贯串不同时代的永恒存在。当前的文化语境是经济全球化,而文化也正经历转型的阵痛,自由主义、拜物教思想、精致利己主义等诸多呈现。多元文化的冲击,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与交锋,使得传统文化影响呈式微之势。社会的价值观更容易在迷茫困惑的少年身上以极端方式体现,如追名逐利、嘻哈无聊、暴戾凶残等。在当下的现代文化语境中,更好引导少年较为顺利地跨越这种成长困境,也是一种必要。
少年阶段历时短暂,生理和心理的快速变化让他们的言行思维充满矛盾和不安。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的少年霍尔顿,他内心善良,渴望美好,却又带着少年阶段特有的叛逆性,抗拒咒骂着他不愿接受的成人社会。如何让学校、家庭、社会重视少年的成长之痛,怎样让社会价值观更多关注少年的成长需求,用什么样的平等、尊重、信任的原则建立起某种成人与少年的关系,这将是一个恒久的生命研究课题,也是这篇论文想要表达的意思。
四、结语
文学即人学,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经典作品里,作者以一个轻度精神分裂少年的呓语传达了人类生命里一个恒久的需求:关注少年成长。在充满各种复杂规则的成人社会里,如何守护悬崖上的少年,减少他们在成长跨越中的动荡与焦虑,是人文学科的一种社会担当,尤其在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现代性文化的语境下。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结尾,少年霍尔顿看着骑上旋转木马的老妹菲苾一圈圈地转个不停,他心里没缘故地快乐极了[1]280。在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生命成长教育也将是一个不断反思和进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