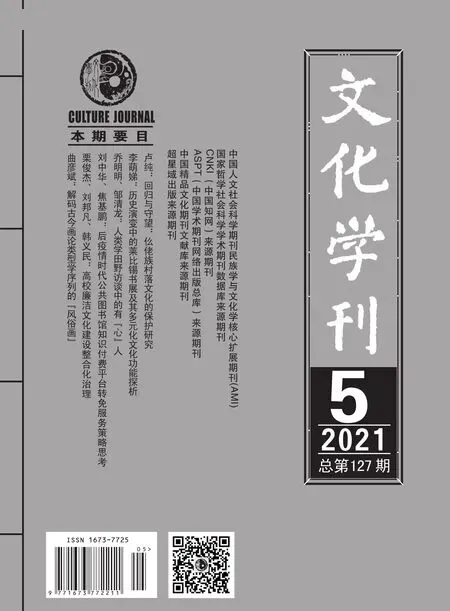浅论清儒关于“乾嘉三大考史名著”优劣的评判
王云燕
一、清儒对“乾嘉三大考史名著”的定位及评价取向
世人常将赵翼《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相提并论,由此产生“乾嘉三大考史名著”一说。有并列就会有比较,比较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梁启超的论点。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1]318与一般清儒的评判相反,张之洞对赵书推崇备至,《劝学篇》中明言:“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缓。”[2]67梁启超亦属意赵书,如他所说:“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其中尤以赵书最值得称赞,“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大昕晚年自号竹汀居士)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称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1]318在钱、赵优劣问题上,张、梁二人的立场一致,与一般清儒尊钱(大昕)抑赵(翼)的取向截然不同。
按梁启超的说法,不免给世人造成一种印象:钱大昕、王鸣盛做的是考据史学,赵翼做的是经世史学;赵书不善考据,故而为乾嘉学者所轻视,但赵书之可贵在于经世致用,此又胜过钱、王二书。事情果真如此?如此分类是否符合历史实相?
将“求真”与“致用”判然两分并不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此为现代大学体制和职业学者出现以后的产物。古代学者并非如此,对于他们而言,“求真”与“致用”未尝分离,“无用”是一句极重的骂人话。是以,说乾嘉学者因为沉迷于“求真”之考据学,所以轻视“致用”之《廿二史札记》,不啻以今概古,很难符合历史实相。事实上,在清人眼里,《札记》从来都是与钱、王二书同列于考据史学。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将三书并为“正史第一”条目下的“总考证”类,与“史评第十四”分属不同条目[3]80。也正因三书同为考据学著作,才有相互比较的可能。
清代考据学相对于义理、词章之学而言,所涉范围很广。考据宗旨或考据对象不同,其方法也可能大异其趣,本就没有一个固定套路。清代学人对《廿二史札记》或有批评,但都局限于质疑其考证结论是否可靠,从没有人将该书排除出考据学的阵营之外。其实梁启超本人也一直将《廿二史札记》算在考据史学之列,而从未将其划入他派。
民国以后,学术分类全然不同于清代,考据学的范围大大窄化,其对应物不再仅仅是义理、词章,而多为历史解释。在此背景下,似乎只有辨误史实才算考据史学。故而周振鹤教授才会说:“《札记》之高并不在其考证的功力,赵翼是不擅长此道的,历来的书目将其归入考证类,并不合适。”[4]实则此处之“考证”已非清儒之“考证”了。
既然在清儒眼里,赵、钱、王三书都是考据书,那么《廿二史札记》与另两书的区别就不在于是否考据,而在于用何种方法考据,考据的宗旨是什么。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三书地位之变化,以及张之洞为何青睐赵书。
二、钱、王、赵三书考据方式之不同
钱大昕在谈及撰写《廿二史考异》的缘由时曾说:
况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著之铅椠,贤于博弈云尔。[5]
在他看来,正史之所以难读,在于义例、舆地、侨置、职官等事项前后变化,名称不一。撰述《廿二史考异》的宗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让世人能够读懂古书所言何事。因此,他采用了一种传注经文的方式解释正史。凡遇疑难之句便详加注释,集合各方材料,从文字训诂到职官舆地无不注解,务求清楚明白。
王鸣盛考据的对象类于钱大昕,但他著书宗旨和考据方式则有所差异。如其所言:
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6]2
相比钱大昕的谦虚谨慎,王鸣盛的作风就显得高调一些,其撰述方式也与钱氏不同。大抵王氏自比顾炎武,遂采用顾亭林《日知录》的方法,将全书分为一个个小论题,引据史料,逐条证明。关于这些小论题的范围,他明确指出:“书生匈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6]1言下之意,他本人不学那些史论家,随便议论褒贬古人,而专事评议史实记载是否准确。
赵翼《廿二史札记》体例与王氏之书颇为相似,皆模仿顾亭林《日知录》。他本人曾自谦地说:“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7]嘴上虽说“不敢”,但内心无疑是以《日知录》为仿效对象。与王鸣盛不同,赵翼考据史学的内容主要不在舆地职官,而在钩稽史实、排比史料。或者说,《廿二史札记》之所长,不在于商榷古书之误,而在于把散落在古书各处的记录按照特定论题集合起来,连缀成文,以见事情的来龙去脉,读罢让人有“纪事本末”之感。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因为考据方法和考据内容有别,难易程度也不相同。杨树达先生曾将“我国学者之治史籍者”分为两派:“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这两派都可以分为两枝,就后者而言:
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洪筠轩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王西庄之所为是也……于是考证派之两枝于乾嘉之际,同时并起,而继其后者,第一枝为盛……综而论之,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丰。要之,非心思缜密,用力勤至者不能为,二者固无异也。[8]
这番话十分精妙地指出,赵翼与钱大昕、王鸣盛的区别是“考证派”内部的区别。钱大昕之“考证史实”与赵翼之“钩稽史实”,其内容、方法不同,难易程度自然有所区别。清儒“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的理由,大抵就是钱书最难,赵书最易。周中孚在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撰写解题时便称:
考史之书,至竹汀此编,诚所谓实事求是,得未曾有者也。同时王西沚(鸣盛)《十七史商榷》,考证舆地典制,颇不减于竹汀,惟其好取事迹加以议论,仍不免蹈前人史论之辙,且于《宋》《辽》《金》《元》四史未及商榷,其书究难与竹汀抗行。至赵云松(翼)《廿二史札记》,类叙事实,毫无发明,又别为一体,尤不可与是编相提并论焉。[9]
周氏之说只可作为杨树达的论据。概而言之,钱、王、赵三书同为“考史之书”;钱、王同为一体,赵书“别为一体”;钱、王重于“考证舆地典制”,赵书则“类叙事实,毫无发明”。“类叙事实”较易,“考证舆地典制”较难,是故赵书尤不可与钱书“相提并论焉”。
换言之,赵书钩稽史实较易,完全可以充当史学考据的入门读物,钱书考证史实较难,却只能供少数专家精研之用。《廿二史札记》的传播范围远较《廿二史考异》广泛,亦与此相关。周振鹤在评价赵书时,有一点睛之笔。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札记》里的每一条实则一篇小论文,有些条目与今天的论文题目简直一模一样……而这种细致的踏实的功夫对于研究史学的人是一项必要的基本的训练,因此《札记》在今天对青年学子依然有它的参考价值。但是《札记》的学术价值也仅在于此,不宜随意拔高。如果说《廿二史考异》足以振聋发聩的话,《廿二史札记》则只是启思开窍,不好同等看待的[4]。
对于史学研究而论,赵书为基本训练,“只是启思开窍”,钱书为专精研究,“足以振聋发聩”,当然前者更有普及价值。需补充说明的是,周振鹤所言“《札记》里的每一条实则一篇小论文”,这里的“小论文”不宜作狭隘理解。它不仅可以指今天撰写的学术论文,更可以指清代朴学教育常用的“课艺文”。张之洞看重《廿二史札记》,就是因为它非常适合做考据学训练的基础读物,尤其适合“课艺文”的体例。
三、张之洞对《廿二史札记》的推广
1873年,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一到四川就发现当地学风败坏,读书人不但终日埋首于时文小楷,而且异常迷信。他在《车酋轩语》中称:“近今风气,年幼方学,五经未毕,即强令为时文。其胸中常无千许字,何论文辞,更何论义理哉。”[10]196又说:“近年川省陋习,扶箕之风大盛。为其术者,将理学、释老、方伎合而为一。”[10]198这些都是当年四川学风的真实写照。
为改革四川学风,张之洞决心引入江浙考据学。他亲自筹建尊经书院,意图以此为阵地推广汉学。他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特别强调:“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10]371又说:“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10]371尊经书院严格采用杭州诂经精舍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模式。比如设立官、师考课制度,每月两次,考课不用帖括时文,而是每课出四题,分别为经解、史论、杂文、诗赋各一题,限四日内交卷。
张之洞极力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认为该书提供了训练学术功底的不二法门。赵翼《廿二史札记》因模仿《日知录》史学条目,而受到张的重视。《书目答问》中特意将《廿二史札记》与《翁注困学纪闻》《日知录集释》一同列入“考订初学各书”,并称“此类各书,约而不陋”[3]254。由此可见,张氏推崇《札记》主要因为它是乾嘉考据学的入门读物。
《廖平年谱》载:“谭宗浚集尊经诸生三年以来课艺及下车观风超等卷,刊为《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钱之教,识者称为江浙派。”[11]《蜀秀集》第四卷收录书院诸生“史论”课艺文,以下摘抄部分目录:
卷四
秦郡县/张祥龄
魏晋南北朝崇尚郑学考/罗长玥
…………
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廖登廷
两汉驭匈奴论/廖登廷
五代疆域论/廖登廷
其中“廖登廷”即廖平。以之对比《廿二史札记》条目,该书之教育功能,一目了然。正是在张之洞、谭宗浚等人的努力下,乾嘉汉学终于在光绪初年泽被蜀中,《廿二史札记》也因此得到四川学界的重视。
《书目答问》问世两年后,唐友耕便开始在四川组织重新刊刻赵翼的全集。此后《瓯北全集》重刊,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成都将军恒训、锦江书院山长伍肇龄等皆为之作序,竭力称赞赵翼史学之成就。《廿二史札记》遂风行蜀地,成为蜀中士子读史必备之参考书。
1898年,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其中再次提到赵翼,称“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此番赵翼的地位竟然越过了钱大昕、王鸣盛,“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缓”[2]67。不过钱、王、赵三书的位置再怎么重新排列,都不足以改变它们的基本功能。
张之洞说得很明确,史学教育首重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也可以选择使用,至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虽然学力深厚,作为专业研究也可,但不适合史学教育的当务之急。乾嘉学者评论三书“赵为下”,因为赵书最易;张之洞评论三书“赵为上”,同样因为赵书最易。前者基于研究的需要,后者基于教育的需要。
与之相匹配,当年7月4日,张之洞、陈宝箴上奏朝廷,提议改革乡试、会试,特别强调第一场要考中国史事,这当然不是让人漫无边际地空发议论,而是必须有本有据,论从史出。张之洞学宗乾嘉,深恨宋明史学游谈无根,如今建议开设“中国史事”考试,自然要屏蔽一些令人炫目的史论性著作,《廿二史札记》的作用就更加凸显。该书以考据学为本,路子纯正,故不会导人以歧途,又浅显易学,适合考官出题和学生作答,十分适合充当考试用书。庚子国变以后,清朝最高统治者下定决心实施新政,张之洞改革科举制的夙愿终成现实。1901年8月29日,清廷正式颁布科举改制诏令,规定:
著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二篇、《五经》义一篇。[12]
为应付“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赵翼《廿二史札记》遂成教辅,行销海内。
综上所言,清儒在钱、赵优劣问题上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取向,这与评论者的治学立场密切相关,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值得注意的是,经由张之洞的推介,《廿二史札记》日益声名鹊起,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逐渐超越钱、王,后来居上。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