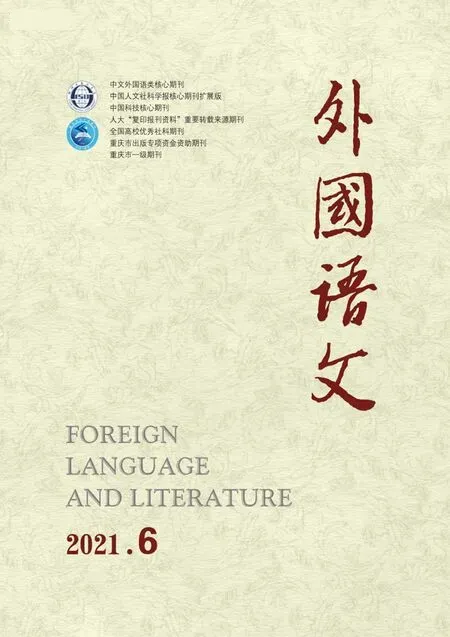《诺桑觉寺》的情感叙事与读者的审美焦虑
熊木清 杜坤
(1.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2.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0 引言
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关注,而“人禀七情”,因而“情”自古便是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情”既是创作的动因也是创作表现的主要对象。亚里士多德的“陶冶”(catharsis,或译“净化”)和柏拉图的“迷狂”指的都是一种情感状态。中国古代文学更注重“情”,汉儒评《诗三百》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一说成为儒家诗学关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以来,情感科学成了一个“发展迅速的领域”(Davidson et al, 2003: xiii),文学研究中的情感叙事学、情感生态批评和情感地理学批评等理论和范式探索应运而生,情感叙事也成为了不少学者关注的话题。根据霍根 (Patrick Colm Hogan)在《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绪结构》(AffectiveNarratology:TheEmotionalStructureofStories)中的观点,情感创造故事,“故事结构从根本上说是为我们的情感系统所塑造和定位的”,“故事在作者和人物身上体现出情感,也通过故事本身的方式在读者或听众那里激发情感”(2011: 1)。情感叙事研究的对象据此可分为三大类:作者在创作尤其是其作品中投射的情感、作品中体现的情感以及读者对作品的情感反应。本文将集中讨论读者的情感反应。
读者的情感反应是一种审美体验。霍根认为,情感体验有四个基本要素:首先,要有诱发条件可以激活情感系统;第二,有表达性的结果,标志着主体正在经历某种情感;第三,对情境的行为反应;第四,现象学基调,它激励我们维持或改变这种情况,让我们体验到满意或厌恶(Hogan, 2011: 3)。在文学阅读中,作品的各种要素及其整体是诱发条件,读者的审美意识契合第二个要素,其审美判断是对情境的反应,最终,读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审美愉悦,即体验到某种满足。读者的情感反应有层次性和阶段性。阅读之初,读者的审美意识可能只是调动了感觉、表象和想象这些心理要素。如果文本有越来越多令人困惑的情节、寓意、情感或人物纠葛等等,读者就会产生审美焦虑,不得不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如思考、意志、情感等。罗恩(Ronen, 2009:13-14)指出:审美领域(Aesthetic domain)涵盖了愉悦和不愉悦(pleasure and displeasure),两者对于艺术经验同样重要,共同作用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焦虑是不愉快的信号,但它也很吸引人,对审美主体充满了潜在的乐趣,是审美判断的先决条件。在审美经验中,“某种焦虑以审美形式表现出来,焦虑本身也被审美化了”(Johnson, 2010: 18)。这里,如同心理学家罗洛·梅所指出的,审美焦虑(aesthetic anxiety)是一种正常的而不是神经性的焦虑,比如“具有诗文想象力的人可能会在某处石岬冥想大海,‘从永恒看瞬间,从沧海见一粟,或更照见自身淹没于无垠陌生空间的景象’”,这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基于浩瀚时空以及个人渺小存在而兴起的诗意感怀”(罗洛·梅, 2010:177),这种“诗性感怀”(poetic feelings)就是审美焦虑的一种释放形式。
事实上,任何文学阅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审美焦虑。奥斯丁的作品看似轻松,其实“在奥斯丁的大多数小说中,在形式、主题和模仿之间存在着强大的、未被发现的张力”(Paris, 1978: 13)。奥斯丁有意设计她的小说来锻炼和挑战读者的反应,特别是在《诺桑觉寺》中,作品“获得的效果几乎完全是通过无情地、肆无忌惮地扭转读者的期望”(Fergus, 1983: 6,19)。汉森(Ellis Hanson)不无夸张地慨叹:“没有比被困在简·奥斯丁的小说里更可怕的噩梦了。”(Spooner, 2007: 174)而文学理论家大卫·洛奇则断言《诺桑觉寺》是“唯一一本适合现代解构阅读的小说,因为它似乎拒绝给读者提供解读和辨识所需的任何确切依据”(Normandin, 2021: xv)。《诺桑觉寺》在主题、人物形象和叙述视角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成为了读者产生审美焦虑的诱发条件,本文将对《诺桑觉寺》中上述三个主要的诱发条件进行讨论,以期生成新的解读。对读者的情感反应或审美焦虑的近期研究聚焦于实证和实验的方法,但也可以综合运用认知科学中涉及情感的理论进行文本分析和评价,如同霍根在《情感叙事学》中的处理,本文将采取这种认知分析方法。
1 模糊的主题蕴涵:婚姻不等于爱情
小说主题是涉及小说类型、题材、作者意图、情感和价值取向、形象塑造等要素综合形成的、贯穿于整个小说的基本思想,是读者审美认知活动关注的焦点,可通俗地概括为:这部小说到底想说什么?说了什么?对于《诺桑觉寺》的主题,国内学者大多认为是爱情,如谭颖沁(2006)认为“《诺桑觉寺》的主要笔墨集中在凯瑟琳·莫兰和亨利·蒂尔尼这一对青年男女一波三折的恋爱故事上”;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诺桑觉寺》的译者金绍禹也认为“《诺桑觉寺》与奥斯丁其他几部长篇一样,故事围绕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的发展而越来越扣人心弦”(奥斯丁,2010:序3)。另一个译本的译者孙致礼、唐慧心更明确指出:“同作者的其他五部作品一样,《诺桑觉寺》是一部爱情小说。”(奥斯丁,1997)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尤其是结合叙事时间(时长)和话语分布的统计进行研究,就不难发现小说的主线是女主人公凯瑟琳的成长以及她与亨利·蒂尔尼的婚姻,而婚姻其实是奥斯丁时代女性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事实上,奥斯丁所有小说的叙事跨度都是从女主人公青春期(大约十岁至十九岁)到她们步入婚姻殿堂。在《诺桑觉寺》中,如同其他几部小说中一样,奥斯丁对爱情并没有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她本身就没有多少恋爱经验,她只写自己熟悉的事件和人物。另一方面,奥斯丁时代的英国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当代作家苏珊·克拉克指出:
19世纪早期作品有它独特之处。故事围绕着女性的未来——是否“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问题展开,而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女主人公选择什么样的丈夫。不论这种观念是否正确,至少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信奉的智慧。很多方面,如女性的收入、社会地位、家庭,或许还有未来的生活内容,都取决于她嫁给了谁。(卡森, 2011:1-2)
卡森(2011:2)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奥斯丁小说中的一些女性在考虑嫁给谁的时候缺少激情,这是有原因的。很多时候,她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丈夫,而且也是未来的身份。”稍加注意,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诺桑觉寺》乃至奥斯丁的全部小说中,很难找到那种温情脉脉、卿卿我我的缠绵场景。奥斯丁时代的年轻女子当然也憧憬甜美的爱情,也有怀春的激情,但基督教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情感尤其对女性情感的抑制,使得奥斯丁时代的年轻女子只能克制自己,很难公开、主动地追求心仪的男子。英国小说家拜厄特评论说:在奥斯丁的作品中,“女人等待男人开口表述爱情,保持沉默对于女人而言是必须的,不管她的感情多么强烈。不要说范妮,就连那些主动的女性,譬如爱玛,当意识到自己爱上某个人时,也不能开口表述。她们只能等待”(卡森, 2011:168)。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奥斯丁小说具有某种情感上的含蓄,因此她的作品中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场面。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文化氛围,使得姑娘们不能自由地追求爱情,只有婚姻才是她们“心中的头等大事”(卡森, 2011:3)。
就《诺桑觉寺》而言,女主人公凯瑟琳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单相思。她总是盼着见到亨利·蒂尔尼,在舞会上总希望他来请自己跳舞(女士是不宜主动邀请男士跳舞的)。第12章中剧场的场景非常细腻传神地描述了凯瑟琳近乎神经质的单恋之苦。她发现亨利和他父亲也在看戏。于是,她的目光转向了亨利。奥斯丁在这里用了一个她惯用的对比手法:“在整整两场演出中,她都这样注视着蒂尔尼先生,然而她一次也没能引起他的注目”;至于亨利,“整整两场戏中,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舞台”(奥斯丁,2010:99)。叙述人这时评论说:“她所流露的并不是女英雄人物的情感,而是自然的情绪”;换言之,她毫无作为女性的矜持,反而认为此前自己有过错,“全都让自己一个人把责任承揽了下来,而且急于寻找机会,要把事情的缘由说个明白”(99)。这是一种单相思的心理自虐。而之后亨利与凯瑟琳的结合,并没有足够的爱情铺垫、孕育与催化,亨利更多的是“感激”凯瑟琳的一往情深。小说的最后一章(第30章)中,奥斯丁不得不再次介入故事,解释读者可能的疑问:“尽管亨利现在真心地爱着她,尽管他感觉到了她性格的贤惠,并为之高兴,同时真心地喜欢与她在一起,然而我必须承认,他的爱是出自于感激,换句话说,因为相信她喜欢自己,他才认真地对她加以考虑。”(268)所以,亨利只是由“了解”到“感激”而生发的“喜欢”,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更没有丝毫花前月下的浪漫,无怪乎苏珊娜·卡森尖刻地指出,“凯瑟琳与亨利之所以能够成为夫妻,这并非因为他们真的般配,而是因为有一位全能的、爱开玩笑的作者将想象强加于真实生活”(卡森,2011:52)。因此,“评论家们认为奥斯丁从不在作品里描绘真正的爱情”,“奥斯丁很清楚,乡绅阶层家的女儿没有能力为爱情付出代价。她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寻找合适的人选,把自己嫁出去”(卡森, 2011:358)。
所以,无论是奥斯丁的创作意图还是文本的组织铺展和话语分布,“爱情”都不是《诺桑觉寺》的真正主题。它只是附着于“婚姻”主题的一件“嫁衣”而已。如何获得亨利的青睐和蒂尔尼上将的首肯,是凯瑟琳“日常生活的焦虑” (Austen, 2007: 169),而如何理解凯瑟琳和亨利的婚恋进而理解小说的主题和奥斯丁的立意,则是读者的审美焦虑。正是出于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读者才会手不释卷。
否定哥特小说不是《诺桑觉寺》的主题,也不是奥斯丁的意图。她只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小说阅读现象有感而发。一方面,她讽刺混淆小说与现实的不良阅读习惯,另一方面,她也讽刺女主人公耽于哥特小说的浪漫幻想和由此产生的哥特式求偶冒险。奥斯丁的良苦用心就是讲述一个有益于姑娘们婚恋大事的有趣故事。她也“并不想完全否定哥特小说——她充分肯定了哥特小说的想象力,只不过要舒缓过度的哥特式情感,有必要控制‘对恐惧的想象’”(Punter, 2004: 80)。当然,为包括哥特小说在内的小说进行辩护,无疑也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之一,但这不是《诺桑觉寺》的关注焦点,而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话题。
2 疑惑的人物形象:女主角的否定性出场
《诺桑觉寺》给读者带来的又一困惑是女主人公的否定性出场。在奥斯丁之前的小说、戏剧乃至当代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都是以贤淑、温婉、美丽的形象出场的,这实际上折射出读者——也是人类普遍的美好向往,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进化的需要和结果,这既反映了一种刻板印象,也是一种文化规范和文学成规。奥斯丁则以否定的形式介绍她的女主人公:
No one who had ever seen Catherine Morland in her infancy would have supposed her born to be a heroine. Her situation in life, the character of her father and mother, her own person and disposition, were all equally against her…and Catherine, for many years of her life, as plain as any. She had a thin awkward figure, a sallow skin without colour, dark lank hair, and strong features — so much for her person; and not less unpropitious for heroism seemed her mind.(Austen,2007:5)
凡是见过凯瑟琳·莫兰孩提时代模样的人,都会觉得她来到这个世界是成不了女主人公的。她所处的生活环境,她父亲、母亲的性格,她自己的相貌和脾气,这一切都不利于她做女主人公……凯瑟琳长到老大了,也还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身材又瘦又难看,蜡黄的皮肤没有血色,一头黑发直挺挺的,五官棱角分明;她的相貌就是如此;说到她的智力,要做女主人公,条件似乎也不见得很有利。(1)
在这个开篇中,奥斯丁通过否定性的语言来描绘凯瑟琳。这是一种叫作“语言否定”(linguistic negation)的手法,具有“显著的文体和修辞潜力”,“有助于小说人物的文本构建”(Chapman, 2014: 111)。语言否定由各种否定词以及包含否定意义的形容词、副词和虚拟条件句等构成,它明确承认某事物或实体显著缺失某种(往往是本质性的)属性和特质。比如凯瑟琳,按惯常的女主人公的标准衡量,她的智力、相貌、家境等都有缺失,当作者使用否定性描述时,凯塞琳的否定性出场会让读者下意识地做出性格推理,因为她与情境不协调。读者固有的关于人物的认知结构和预期无法把凯瑟琳归入“女主人公”类别,就必然需要做出新的认知协调。读者要从否定中推断意义,解释这个否定,找出一个可能存在但未实现的含义,并将其逆转。当然,作者也直接点出了这一点,减轻了读者的认知负担,但却进一步加重读者的好奇心:作者为什么要把女主人公处理成这样?这样的女主人公会出现命运的逆转吗?如此一来,读者的审美焦虑从小说的开篇就被强烈地诱发。这与《傲慢与偏见》那个满含反讽与幽默的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
凯瑟琳的否定性女主人公形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小说的开篇。虽然她“有一颗温柔的心,乐观而开朗,绝不自高自大、装模作样”,外表可爱但只有“高兴的时候样子漂亮”(9),因而至少从容貌来说她远不是一个完美甚或“标准”的女主人公。大约15岁时她进入了青春萌动期,“人变得丰满、红润,五官也显得和谐”,“开始讲究穿着,人变得时髦了”,但整个说来“相貌还是平平常常”(3)。到了17岁,叙述者仍然坦承,这时的“她还够不到当女主人公的标准”(7)。不过,叙述者给她做了安排:“我们的女主人公为运气所青睐”(18),凯瑟琳邂逅亨利。在舞厅里,司仪把她介绍给亨利。“他举止有礼,令凯瑟琳感到很称心”,从此她芳心暗许,踏上了一波三折的求爱之路。但对比之下,凯瑟琳是有不少缺陷的:亨利口若悬河,使她很感兴趣,可是“她一点儿也不懂他表达的意思”(18)。直到小说接近尾声,她仍然缺少一个女主人公应有的自信:“对凯瑟琳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怀疑她自己的意见总比怀疑亨利的意见要容易得多。”(232)
所以,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个人容貌、智识,凯瑟琳似乎都不是一个标准的女主人公。亨利认为凯瑟琳头脑简单,时常拿她逗乐。她与亨利的结合,如前所述,乃是因为亨利感激她的一往情深。因此,有论者认为,亨利和凯瑟琳“并非完美的黄金搭档”,亨利给予凯瑟琳的只是“带有救赎性质的爱情”;作为读者,“我们始终隐约觉得这桩婚姻是个错误——虽然并不严重”(卡森, 2011:49,50)。读者——尤其是现代读者——往往会有不少疑问:感激之情竟然演变成两情相悦的婚姻,可信吗?作为女主人公,凯瑟琳的性格是否足够成熟、足够可信?事实上,奥斯丁似乎也没有把握。她在小说结尾处又一次介入叙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他们借助什么来实现早日完婚的愿望?什么样的可能机缘会对上将这样的性格起一点作用?”(275)尽管最后他们结了婚,“开始他们的美满生活”,但这桩婚姻是否真的合适?亨利和凯瑟琳今后的生活是否真的美满?读者是不可能确信的,广大读者对这些问题也不可能达成共识。其实,这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我们不得不努力探究奥斯丁的艺术特点和创作意图。
事实上,奥斯丁没有想过要塑造完美的女性人物,更不用说男性人物了,因为她对男性远不如对女性那么了解,所以她的作品极少描述男性之间的活动和对话。她关心的是女性,尤其待字闺中的中产阶层年轻女性的生活、教育和婚恋问题。她也主要是为她们写作,因为自18世纪以后,“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越来越悠闲安逸,她们虽然文化水平有限,但普遍都识字”,她们成了小说领域一个“巨大新读者群”(鲁宾斯基,1987:410)。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对小说的那番议论,表明“在上流社会普遍开始阅读小说以后很久,社会风气仍然没有改变。人们还是瞧不起小说,认为小说只适合妇女和小商人阅读”(412)。奥斯丁时代的年轻女性除了一些佼佼者可以通过写小说挣一点英镑外,其他实在没有别的社会性工作可做。所以,奥斯丁很关注自己小说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她常常把自己写的部分稿子念给家人听。
不过,奥斯丁虽然要考虑读者群,但她同样关注妇女问题,更有自己的文学观和艺术追求。所以,她的社会关切是现实主义的;奥斯丁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她是乐观、积极的,因而她的艺术追求是轻松、诙谐的喜剧风格;同时,她创作《诺桑觉寺》时正是哥特小说和浪漫传奇盛行之际,这就使她的作品染上了浪漫主义色彩。这一切,并不表明《诺桑觉寺》是多种风格杂糅的大拼盘,奥斯丁高明地将它们熔铸为一体。她采取了一种低度模仿的(low mimetic)手法。这种叙述模式表明“主人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向作者要求“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找到的同样的概率准则”(Paris, 1978: 14)。所以,她的女主人公就应该是那种平平常常、宛若邻家小妹的姑娘,这样才最大程度地符合现实生活,也契合广大普通女性读者的阅读需要,容易引发她们的共情。如此,凯瑟琳就应该可爱而不必那么漂亮,有几分天真和傻气,但在婚恋大事中又不失精明。她与亨利确实不那么般配,但她乐观向上,敢于追求,在自己执着、诚实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与心仪的男子缔结良缘,这其实是一种弱式的“灰姑娘”故事。但它不正是许许多多平常姑娘的青春梦想吗?奥斯丁要给予自己的读者以希望,于是把生活与艺术中常常冲突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与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尽可能糅合起来。这样,我们有时会觉得故事中的人物似乎滑稽可笑,而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关注的问题却又那么现实而严肃。
3 错综的叙述视点:多种视角的切换
叙述视点(narrative point of view)揭示某故事从谁的角度(perspective)讲述。叙述视点的运用是小说叙事最重要的技巧之一,它可以让读者从某一特定角度来感受故事,创造故事的互动体验,增加读者的认同感,传达(或隐藏)特定角色的已知信息,从而与读者产生联系或制造悬念,或者通过展示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感受和想法来区分不同角色,也可以在文本叙事表层和深层之间提供对比,创造潜台词和隐含意蕴,制造张力和悬念。
奥斯丁在这方面对英国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对奥斯丁倍加赞赏:
简·奥斯汀的小说,为理查逊和菲尔丁只提供了部分答案的两个普遍的叙述问题,找到了最成功的解决方法。她将分别从内部和外部对人物进行刻画的描述的现实主义和评价的现实主义的种种优点结合起来,融汇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之中。(1992:343)
瓦特的结论是:“奥斯汀能在英国小说传统中获得显赫的声名,可能主要也在于她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92:341)在奥斯丁之前,笛福采用自传体作者叙述视角;理查逊采用书信体叙述;菲尔丁则采用作者直接叙述的第一人称手法,但叙述者并不在故事内(即不是故事人物)。这些叙述手法各有局限:自传体和书信体叙述视角都不能进入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直接叙述虽然可以像第三人称那样对自己“无所不知”,但菲尔丁不重视人物的塑造,“拒绝深入他的人物的心灵深处”(瓦特,1992:315)。奥斯丁对自己则不同,她使用了多种叙述视角,用复杂、变幻莫测的视角来呈现叙事,而不是采用那种单一主导的、集中的权威视点。她采用的往往是某种“循环视点”(circulatory point of view)。一般情况下,她使用第三人称视点,但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她的第三人称叙述视点很有特色,丰富多变,有时是全知视角,有时又是有限视角。特别的是,她偶而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让叙述者介入叙述,或者插入作者的议论,而这些不同叙述视点切换自如,这就使得她既能深入人物的心灵深处,描述他们的心理活动,记录他们的情感变化,又可以在必要时留下缺失,制造悬念,适时地掌控读者的阅读情绪进程。
奥斯丁最具特色的叙述方式是大量使用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 FID)和自由间接思维(Free Indirect Thought, FIT)、思维活动叙述(Narrative Report of a Thought Act, NRTA)和作者介入(Author Intrusion, AI)三种叙述视点。
第13章中,好友伊莎贝拉无端指责凯瑟琳,这使凯瑟琳很难过:
凯瑟琳认为这样的指责既奇怪又刻薄。把她的感情暴露给别人看,难道这也算是朋友吗?在她看来,伊莎贝拉心眼太小、太自私了,为了满足自己可以不顾一切。她心里产生了这些痛苦的想法,只是嘴上没有说出来。(106-107)
Catherine thought this reproach equally strange and unkind. Was it the part of a friend thus to expose her feelings to the notice of others? Isabella appeared to her ungenerous and selfish, regardless of everything but her own gratification. These painful ideas crossed her mind, though she said nothing.(Austen,2007:82)
这一段的第一句是凯瑟琳的思维活动叙述,简洁明了,叙事密度大,但客观程度较低,因为它出自叙述者的视点,不是凯瑟琳想法的原始呈现。可是第二句(Was it the part of a friend thus to expose her feelings to the notice of others?)却是自由间接话语,叙述视点由外在的第三人称视角悄然切换到了人物视点,凯瑟琳成了视点人物(Point of View Character, POVC),这句话也就属于凯瑟琳的“原话”,只是动词变成了过去式,这样就完整保留了凯瑟琳思维的内容及细节,但又比直接话语简洁,因为它不需要诸如“她想:‘……’”之类的引述分句和标点,语言形式不着痕迹地镶嵌于思维活动叙述话语中。类似这样自如的叙述视点和叙述人的切换,在《诺桑觉寺》中俯拾皆是。一方面,思维活动叙述可以突出叙述要点,加快叙述速度,而嵌入自由间接话语或自由间接思维能活跃文体,更能增强话语的客观性、人物的情感性和读者的亲历感。另一方面,它迫使读者不时地转换审美注意的焦点,在不同叙述者之间切换,强化了读者的审美焦虑,也使读者于细细品味中获得更多审美愉悦。由于汉语动词没有形态变化,所以,这种视点切换在译文中有时很难察觉。
奥斯丁最具特色的是她的作者介入。和其他人(比如菲尔丁)的作者介入不同,奥斯丁在小说中不是高高在上、冷静理性的监管人,而是蕴涵强烈情感的观察者,很多时候她甚至直接进入故事世界——虽然她始终不是故事内的人物,但她不仅以创造者的身份出现,而且常常表现得如同女主人公的闺蜜,充分表现出叙事的情感指向(emotional orientation)。亨利和他的妹妹蒂尔尼小姐约好出去郊游,到了约定那天,因为下雨未能成行。中午,索普和伊莎贝拉邀凯瑟琳去布莱士城堡游玩,谁知在街上与蒂尔尼兄妹俩的马车擦肩而过,“她不免觉得蒂尔尼兄妹俩待她有些不合情理,这么快就悔了约,也不带个口信来说一声”(91)。她非常痛苦,这时,奥斯丁如同一个慈爱的保护人一般介入叙述:
此刻我可以将我的女主人公打发到睡榻上去辗转反侧了,那才是真正的女主人公的命运;头靠着一个布满了烦恼和浸湿了泪水的枕头。要是在今后的三个月里她还能再睡上一个安稳觉,也许她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了。(96)
And now I may dismiss my heroine to the sleepless couch, which is the true heroine’s portion; to a pillow strewed with thorns and wet with tears. And lucky may she think herself, if she get another good night’s rest in the course of the next three months.(Austen,2007:74)
这一段不仅细腻写出了凯瑟琳的情绪状态,而且“我的女主人公”一语蕴涵浓浓的共情,这种直白的作者介入并不会使读者厌烦,因为它就像老练的闺蜜卫护不谙世事的姊妹那样令人觉得自然、合理并充满温馨,现在时态的使用比冷冰冰的过去式更容易诱发共情。尤其重要的是:奥斯丁不像菲尔丁那样借此机会发表长篇大论,更不会说题外话。小说叙述艺术到奥斯丁这里更为娴熟了。
奥斯丁还借助作者介入的机会提出问题,设置悬念,进一步强化读者的审美焦虑。在第30章中,奥斯丁就凯瑟琳对蒂尔尼上将的怀疑发表议论,但却没有给出非此即彼的断言,而是再次留下了某种“不确定性”:
我打算让读者运用聪明才智去判断,关于所有这一切,亨利可能会向凯瑟琳传达多少?他可能从他父亲那里了解了多少?他自己的猜测可能帮了他多少忙?还有多少必须要留给詹姆斯在来信中说明?我为了读者的方便,把这些情况合在一起说了,请他们为了我的方便,再把它们分开来看吧。无论怎么说,凯瑟琳听到的已经足以让她感到,不管她怀疑上将谋杀妻子还是怀疑他把妻子软禁起来,她根本没有毁坏他的名誉,也没有夸大他的冷酷。(96)
同一章在说到凯瑟琳和亨利婚事的最终结局时,奥斯丁提出了关键问题所在:
他们心中对最终的结局肯定充满了焦虑,所有爱他们的人也必定如此。然而我恐怕这种焦虑不会传到我的读者心里去,因为他们可以从面前压缩得只剩几页的故事猜到,我们正一起急急忙忙地奔向皆大欢喜的结局。可唯一的疑问是,他们借助什么来实现早日完婚的愿望?什么样的可能机缘会对上将这样的性格起一点作用?(275)
奥斯丁的这种作者介入,有时采用复数的第一人称,即“我们”“我们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我们正一起急急忙忙地奔向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种叙述视点兼有作者介入的距离感和灵活度,也就是说,她并不需要成为故事中人物,却可以对故事中的人和事进行点评和控制,不受人物认知的束缚。同时,作者介入又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第一人称单数叙述(I-narration)和第一人称复数叙述(We-narration)的部分功能。一方面,这种手法可以加快叙事进程,给读者提供更多特定人物的信息,增强他们对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另一方面,它把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聚拢在一起,成为“我们”,这样可以创造故事的互动体验,邀请读者参与角色创造,增加读者的认同感和现场感。这是一种认知双重技巧(cognitive “doubling” trick)。事实上,第一人称有其独特优势,有助于营造焦虑、紧张、自然等多种气氛与效果,还能缩小叙事距离(narrative distance),让读者真正深入阅读中的情感和审美体验,“就像有人坐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一样”(Rasley, 2008: 67)。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哥特小说、侦探小说和女性小说中用得较多。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的都是某种“深度视点”(deep POV),将审美注意锁定在当下的场景中。在《诺桑觉寺》中,前者是“伪第一人称”的作者介入,表述的是作者对当下情境的意见和情绪,后者则呈现了人物在当下情境中的感受和思想。无论是作者还是人物,在这种深度视点叙述中,其思想和情感与周围世界没有隔离,而是在生动流畅的节奏中相互依存。
4 结语
奥斯丁的小说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丰富生动的情感和多样复杂的叙事,读者常常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才能在头脑中生成一个较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把握小说意蕴和作者意图。另一方面,奥斯丁要通过她的小说揭示一个严酷的现实:“女子通过婚姻决定命运。”(卡森. 2011:259),所以,“《诺桑觉寺》的大部分篇幅描写一位婚龄小姐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和态度,而不是直接描写婚姻问题”(鲁宾斯基,1987:427),更不是聚焦于爱情,爱情只是婚龄姑娘们在婚姻路上的憧憬。爱情与婚姻之间的不易耦合,造成了奥斯丁时代生活的焦虑,也成了小说中读者审美焦虑的一个诱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