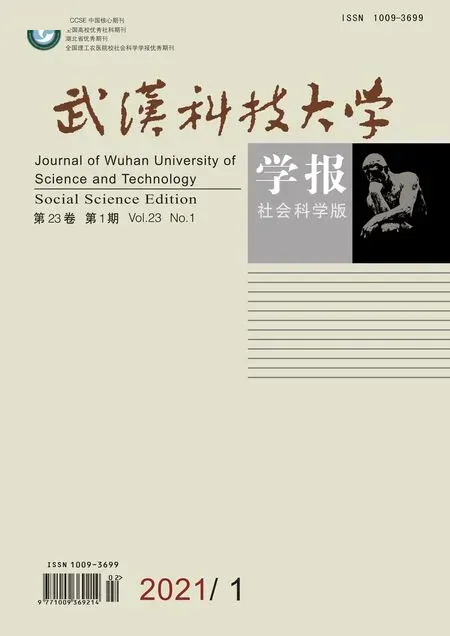刘勰关于语言创制自由的综合判断
李 咏 吟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文学语言的自由决定了文学创作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也决定了文学语言的自由。对于创作者来说,“语言的自由”是创作者最深沉最内在的生命渴望。不过,语言的自由决非简单的事情。应该看到,刘勰的文学语言论或语言自由论,虽然是渗透在《文心雕龙》①中的最基本论题,但是,从有关文献的资料汇编来看,这一问题并未成为龙学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②。不过,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与文体论的具体篇目的详细研究中,王元化等学者已经对刘勰的文学语言论或语言创作自由论进行了深入研究③。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综合刘勰创作论与文体论的相关论述,对刘勰的文学语言自由论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并由此彰显刘勰文艺理论思想的真正价值。
一、文辞根叶,辞令枢机:语言自由的创作显现
刘勰关于文学语言的考察与讨论,对于文学创作奥秘的揭示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代文学理论的“创作法则”。为什么要讨论文学语言?因为文学语言乃文学创造的根本思想动力。语言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没有语言,人的生存就会遭遇困难,语言最大限度地确证了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创造。人如果不会言语,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不可能与他者自由沟通,文学语言是创作者生存表达与审美创造的内在中介。文学语言的自由,就是要通过语言创制让人与人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自由的思想交流与生存交流。文学通过语言表达自我的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最大限度地确证自我的生命本质力量,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生活并想象生命的自由美好,因此,语言的自由对创作者具有决定性影响。
问题在于,语言的自由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语言只有通过学习与创造才可能自由建构。人生活在各种语言氛围中,民族语言或母语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工具,甚至可以说,民族语言之间的交流是主体生存与想象扩展最重要的途径,语言的自由始终在交互作用中形成。鲜活的口头的语言与交际的语言,书面的历史的语言与经典的语言,语言的开放性传统与语言的地方性传统,语言的辞典与语言的记忆库,语言的接受性活动与语言的创造性活动,语言的全部生存记忆与语言的情感体验,这一切构成了语言的海洋。创作者就在这种语言的交互性与语言的共同性中生存,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存在。
按照刘勰的认知,语言的自由有利于“神思”。“神与物游”“心与辞应”,想象与语言有着亲在的联系。刘勰强调,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情感表达,它具体表现在想象与情感体验之中。不过,刘勰强调情感本体,但并没有强调语言本体④,因为语言服务于情感表达,情感的想象决定了语言的自由度,情感越丰富,语言可能越自由。当语言与情感完全一致时,神思的价值就特别值得重视。
语言与情感、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是密切相关的精神活动。刘勰特别强调语言与情感的关系,在语言与情感的探讨中,刘勰隐晦地表达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的生命联系。语言的自由,不是孤立的事件,不是空洞的输出,而是与主体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刘勰发现,“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文心雕龙·神思》,以下简称《神思》),这是从朗诵与阅读意义上讨论文学语言的美感自由,从视觉意义上讨论文学想象的语言图像变化。“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思》),这样,思想、想象与对象之间,就形成了自由的联系,这是无限自由的语言和情感建构方式。与物同在,神与物游,语言的表达是“心证”的外在条件,因此,语言的图像想象并不是空洞的,而是具有内在的丰富性与关联性。
在语言与想象的运作中,刘勰看到,“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神思》)这就是说,“志气”在想象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精神生活的审美意志对于审美想象的关键作用。思想与情感能否得到自由表达,“辞令”显得极其重要。没有自由的语言,就无法实现想象的自由,这说明,“语言的自由”在文学创作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神思》),这其中,语言的自由是关键。只要解决了志气与辞令问题,我们就可以在自由的想象中进行自由的语言表达。如果语言无法与想象和情感获得内在的统一,那么文学创作就会处于堵塞不通的状态。
正是在语言与情感的自由作用下,刘勰看到,“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神思》)从表面上看,这是想象与形象的关系,实际上则是语言自由的状态。想象与形象相关,情感体验与自然事物相联。神思的才能,最终必然落实到语言创制上来,无论多么美丽与自由的想象,没有语言的确证,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想象的无限美妙,全在形象与语言的自由关联之中。想象与形象相关,想象也与语言相联,这种生命感发创造的过程,永远需要语言的自由才能进行充分确证。只有实现了语言的自由,写作才能变成真正的创作,想象本身才能变成“语言的亲证”。
刘勰承认,语言与想象并非完全和谐的,它与创作主体的才能有关。“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神思》)这说明,语言的自由永远无法达到主体期待的最佳效果。创作的未尽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语言的不自由造成的,或者说语言无法实现主体的想象自由,原因就在于想象的美好未必能够通过语言加以实现。这一描述,真正把握了创作想象与语言传达之间的矛盾。“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神思》)这说明,词不达意,语言不自由,表达的效果相差万里,由此显示出思想与语言和想象有着多么复杂的关联。正因为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之间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神思”从根本上说,就是创作形象与创作语言的关系显现,神思的自由就是语言的自由,语言的自由才能保证神思的自由。
刘勰还看到,“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神思》)这是说,语言可能意外地表现出创作者的妙思,语言也可能发挥出人意表的美感作用。“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这个例证说明,语言的自由就在于创作主体的匠心独运。“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神思》)这说明,语言的变化与语言的建构是无限精妙的,充满着无限自由的可能性,永远不会有穷尽和满足。
虽然刘勰在总结神思问题时并没有突出语言的中心性地位,但是他强调,“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神思》)这些认识,无不涉及形象与语言、语言与声律、情感与语言的联系。刘勰的这些论述,深通文学语言的精妙,深刻地体察了文学语言的思想和形象创造价值。对于创作者而言,语言之功极其伟大美妙,刘勰的认知无疑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刘勰为了突出神思与体验的重要地位,有意隐蔽了语言的关键作用,但是,创作自由或神思自由的根本,无不根源于语言的自由合作。
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通过语言自由确证自己的个性,是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那么,到底是语言自由决定了创作个性,还是创作个性决定了语言自由呢?这也极为关键。语言的个性,从根本上说,与创作者的语言价值取向有关;从现代创作学意义上说,人的生命本质力量决定了语言的个性选择与个性风采。
刘勰从相反相对的立场提出了八种语言个性或创作类型。刘勰承认,创作者的语言千差万别,雄浑与秀美相对,流畅与晦涩相对,典雅与通俗相对,简洁与繁复相对。这说明,选择的标准不同,语言的风格就不同。从根本上说,语言的类型并不容易确立,人性有多么复杂,语言就有多么复杂。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重视美感语言或成熟的语言,还有许多不成熟的语言也是创作者的个性显示。不过,刘勰主要从成熟的文学语言出发,确立了八种语言个性类型,强调了它们的美感差异。
必须承认,优秀的创作者往往具有独特的语言天赋。如果创作者能够自由地驾驭语言,就能够彰显出语言的审美风尚与自由个性,但是语言天赋并不是突然生成的,它是创作主体的潜能。语言的天赋与主体的气质有关,这种气质在语言接受与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往往会最大限度地被激活。语言自由与语言确证,显现了创作主体的语言个性。刘勰指出,“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文心雕龙·体性》,以下简称《体性》)总体而言,这八种语言风格,未必能穷尽汉语语言的创作个性,因为这是经验的归纳,并没有普遍的逻辑归类准则,但是这些语言风格按照正反相对的方式进行归纳,已经包括了基本的文学语言风格类型。
刘勰强调,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的形成,与主体的才、气、学、习的修炼密切相关,“才与气”是主体的先天创作特质,“学与习”是主体接受母语并体察母语以及开发自我的过程。他说:“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这说明,辞理与才具相关,语言刚柔与气质相关,语言得失与学识相关,语言风格与主观偏好相关。也就是说,语言风格与语言类型,根源于主体的气质类型与审美内在取向。这种概括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语言个性创造的最高秘密,就在于“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每一创作主体皆能根据自己的特点显现语言的个性。
刘勰通过对大量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行分析,形成了总体的文学语言风格理论:“典雅”的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在于“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远奥”的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在于“馥采曲文,经理玄宗”;“精约”的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在于“核字省句,剖析毫厘”;“显附”的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在于“辞直义畅,切理厌心”;“繁缛”的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在于“博喻酿采,炜烨枝派”;“壮丽”的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在于“高论宏裁,卓烁异采”;“新奇”的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在于“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轻靡”的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在于“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这些归纳,虽然没有严格的定性,但是触摸到了文学语言不同风格类型的基本特质。
其实,创作个性与语言风格的形成,未必真像刘勰所论及的习得途径,但是,“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这些语言风格或创作个性的相反相对,从根本上说与语言的表达效果有关,一切都离不开“文辞根叶”,风格或个性的本质总是源于语言“苑囿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刘勰强调语言风格的力量取决于各种因素的自由综合,它们源自主体的“才力”与“血气”,皆根源于“情性”。在此,刘勰为了突出情感本体论,有意忽略了语言本体论的地位,我们恰恰需要从他的情感本体论读出他的语言本体论。
从创作意义上说,刘勰还强调风骨与语言自由的内在联系。具体说来,语言的形象和意义,表现了文学的道德精神风尚;语言的形式美感,则表现了文学的审美风骨。风骨是文学的精神与灵魂,也是文学创作者的语言品格。刘勰不仅强调语言与个性风格的关系,还特别强调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刘勰看到,“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文心雕龙·风骨》,以下简称《风骨》)这就是说,内容是为了述情,言词是为了立骨,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情感与语言的关系、形象与语言的关系,都可以通过“风”与“骨”来理解。“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骨》)这说明,情与风相关,辞与骨相联,内在的情感需要外在的语言来表达,外在的语言必须呈现主体的精神气质,这就是风骨与语言的内外关系。生命存在的意义呈现为“风”,语言自由的表达呈现为“骨”,风骨隐含在语言的自由表达之中。
为此,刘勰强调,“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骨》)这说明,语言与思想、语言和情感、语言和形象,是相互联通的。“文骨”意味着文学的情感与语言的端直相关,“文风”意味着文学的语言形式与主体的生命意气相通,如果做不到这些,语言和情感都会失去力量。“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这说明,语言与“骨”有着最亲密的联系,情感则与“风”有着最深刻的联系,两者的自由作用才能构成“风骨”。刘勰认为,创作者必须坚守刚健的气质,这就像文学的双翼。“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风骨》)语言与精神、语言与思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足以显现风骨的根本价值。刘勰看到,“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风骨》)如果不能做到这样,文学就不能自由地展示“风骨的力量”。相反,如果注重语言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的统一,那么文学就能实现“风骨的和谐”——通过优美而生动的语言,表达生命的情感正义与德性力量,造就“风骨”的最大和谐。
当然,刘勰也看到了语言与情感、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的分离状态,但在这种状态下,文学很容易失去真正的美感价值。“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风骨》)这说明,风骨的和谐,可以构造文学的美感精神与价值;风骨的背离,则无法达成艺术的美感精神与表达。至于语言美感与风骨的联系,刘勰指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风骨》)这都是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语言与情感不和谐的表现。文学的风骨,取决于创作者的语言习得与语言实践,为此刘勰充分体察了文学语言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风骨的真正形成,是语言与情感、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之间“自由和鸣的结果”。
刘勰认为,“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风骨》)这说明,刘勰对于语言与精神的美感关系有着自己独立而自由的探索。从根本上说,他强调语言与情感的内在统一,即“情与气偕,辞共体并”。语言的自由,与这种生命的本质力量和生命的自由创造有着内在的联系,它昭示着自由的个性、审美的风格、思想与精神的统一。因此,从神思、体性和风骨的意义上说,创作者的语言自由与创作者的情感和思想以及形象创造意图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
二、四言正体,五言流调:语言自由的文体意识
为了深入讨论语言自由问题,刘勰特别考察了文体与语言的关系。文体不同,语言的个性与语言的要求就不一样,相对而言,文体决定了语言的差异。刘勰具体考察了诗歌语言、歌诗(乐府)语言、骚体语言、赋体语言,还考察了其它应用性文体的语言特征,发现这些文体语言既有总体的特性,又有具体的实践。刘勰很重视词语、句子与篇章之间的内在关系。不同的文体形式对于文学语言的句式、句法和韵律要求并不相同,因此,语言的自由必须适应不同文体的内在要求。当语言的自由适应了文体的审美定势之后,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就能获得充分的表达。为此,刘勰不仅强调了语言局部与整体的审美关系,而且为语言的整体构成或细节构成提供了最生动的解释和说明。
按照刘勰的解释,我们必须从“定势”出发理解创作者的语言个性。“风格”,其实就是创作中形成的语言定势,定势一旦形成,创作个性就彰显出来。刘勰认为,“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文心雕龙·定势》,以下简称《定势》)刘勰强调“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这似乎与语言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情感与定势有着直接的联系。“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不过,情与体、体与势,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得到完全的实证。刘勰看到,“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定势》)这说明,文学创作者如果以某种经典为范式,那么创作的语言自由自然会呈现出语言与情感、语言与思想、语言和形象的内在规定性。创作者采纳什么样的美感语言表达方式,直接与文学的定势有关,而文学的定势是思想的定势、情感的定势,最终表现为文学语言的情感定势、色彩定势和力量定势。
刘勰强调自然之势,强调创作个性与语言风格同创作者追摹的风格或经典有关,但是涉及创作的实际效果,他则强调文辞的力量。“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定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辞充分表达了感情,就可以达成形象自由的效果。由于刘勰强调情感本体的地位,所以他主要突出语言与情感的关系,相对隐蔽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的联系。
在刘勰看来,各种语言与各种文体,都与语言的定势有关,不同的文体形式,其语言要求各不相同。“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他认为,“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定势》)他对各种文体的语言特性,都进行了基本规定或界定,这就是说,不同的文体对语言的色彩、意义和方式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要求。这样,文体的本性决定了语言的个性,语言的个性最终造就了文体的风格定势。
刘勰强调,文体之间虽然可以互相贯通,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本体特征的坚守,即“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定势》)。从普遍意义上说,情感优先于语言而存在,语言是对情感的自由表达,因此,“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定势》)。刘勰也强调,情感先于语言,语言是对情感的表达,也是对情感的追摹。文学语言的自由,如果不能表达自由而自然的情感,那么文学的语言确证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如果没有真挚而自由的情感蕴聚,文学语言的文体自由创作也无法获得感人的效果。
刘勰也发现,创作者往往根据时代要求不断进行语言创新。“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定势》)文学语言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表现出“新色”,如果没有“新色”,就无法昭示自由的个性与自由的力量。文学的定势,是语言定势,也是文体的定势,更是情感与思想的定势,只有服从于不同的文体目标,才能将文学语言的自由与情感表达的自由达至“真正的和谐”。
刘勰强调,文学的情感是对事物的感应,由此表达志向与思想,这是文学语言创造中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看到,“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文心雕龙·明诗》,以下简称《明诗》)从汉代文学发展来看,“四言诗”是继承了《诗经》传统的结果,随后发展的“五言诗”,刘勰认为是语言与情感关系的时代变化的产物。从文学语言的历史变化来考察文体语言的变化,从文学文体的发展来观察文学语言的自由形式,这既是对文体的尊重也是对语言的强调。在五言诗的文体创作中,“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明诗》),由此,刘勰特别突出了“五言诗”在魏晋诗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语言与情感、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语言与时代,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由于魏晋诗文与刘勰生活的时代相契,所以他对魏晋诗文的考察极其亲切生动。刘勰看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刘勰发现,“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这就是要充分发挥语言自身的力量。“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明诗》)这是诗人语言风格与创作个性的差异,其审美风格是通过五言诗展现的,诗人的语言与思想对于创作个性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五言诗发生了变化,诗风与诗思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语言所表达的情感内容就有所不同。刘勰对五言诗的重视,与五言诗的语言形式与文体自由有着密切关系。正是五言诗的发展,为中国文学语言的自由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契机。
刘勰还看到了诗歌变化与文体变化以及思想的新发展。在刘勰看来,“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刘勰发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明诗》)这是刘勰对魏晋诗歌的崭新理解。从文体意义上说,五言诗清新流丽、思想自然,显现了语言和思想的真正自由。相对而言,“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明诗》)在此,四言与雅润的关系、五言与清丽的关系,都是文体语言风格的自由体现,也是文体语言自由的内在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对魏晋诗歌语言与情感的自由表达、对魏晋文体语言的自由发展,充满了欣赏与赞佩之情。
刘勰还从“乐府”出发,探讨了文体对语言的特殊规范;从“声律”出发,探讨了语言的音乐效果与美感要求。 他说:“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文心雕龙·乐府》,以下简称《乐府》)诗歌与音律关系密切,而声律本身就是语言的创制特点和审美追求,因此,“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在此,刘勰并未认真讨论诗歌语言的特点,只是讨论诗歌语言与音乐声律的关系。他看到,“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由此可见,声律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了文学语言的美感表达效果。“和乐之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表面上这是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实际上是诗歌文体与语言自由的呈现,语言本身的变化足以比拟音乐的自由力量。因此,“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乐府》)刘勰建立了语言与乐律的关系,并强调可以通过乐律构建语言的精妙美丽,这是对诗歌文体语言的独特把握。“声律”其实也是文学语言的美感体现,尤其是诗歌语言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文体对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文体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的自由,没有语言的自由,根本不能保证文体的自由。
因此,刘勰讨论声律与乐府的关系,其实就是讨论文体语言的音乐性与情感表达的自由关系。语言的自由,不仅是语词意义的自由确证,也是语言的声律、句法和形象的自由。刘勰认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文心雕龙·声律》,以下简称《声律》)诗歌文体的本质在于语言的声律和谐,它追求音乐效果的自由呈现。“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在此,文学语言的表现证明了诗歌文体语言的自由特质,事实上,声律的文体语言价值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讨论。“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声律》)刘勰对外听和内听的区分,确立了声音美感与诗歌意义的内外之别,强调了诗歌意义的特殊价值。语言的自由,就是声律的和谐,就是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语言与情感之间的高度和谐。
刘勰发现,声音与语言的词语关系,对于诗歌文体的美感价值呈现极其重要。“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诗歌的文体特性,要求诗人必须高度关注语言的声律效果与声律和谐感,没有声律的和谐与自由,就没有诗歌文体的真正自由。“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这说明,语言的声律效果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语言美感最重要、最自由的呈现方式,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抓住读者。刘勰看到,“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声律》)文体语言必须最大限度地促进文体的自由,诗歌文体的自由就需要语言的声律与词句变化的自由,这样语言建构与语言韵律就达到了语言的最佳音乐效果,诗歌的美感与意义自然得到了最佳呈现。
刘勰从诗文本身出发,始终以诗文的语言作为基本出发点,强调语言的音乐效果,寻求形象构成与意义呈现之间的联动关系。他认为,“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声律》)这说明,语言的内在和谐与个性特征呈现,决非简单的事情,它取决于创作者的语言自由及对声律的细致把握。
刘勰还从章句入手,探讨语言的自由运动和局部或整体效果的内在生命秩序。刘勰指出,“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文心雕龙·章句》,以下简称《章句》)正是在这种语言的自由经营中,刘勰发现,“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因此,汉语言文学的语言关系,构成了字句章篇的自由互动,它是完整而自由的生命整体,也是和谐而生动的生命个体。他认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这说明,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统一性,当语言的章句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与音律协调性,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由此可见,语言的自由需要创作者匠心独运,调度变化。他还谈到:“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章句》)这说明,文学语言的自由体现在文学语境之中,体现在文学语言的综合评判之上。在此,字、句、章、篇四个要素之间,呈现了语言自由生成的过程。这说明,文体的语言自由,不仅需要在声律上追求字句的和谐,而且需要在章句上追求整体的和谐。
刘勰看到,“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这说明,章句之间的语言有着内在的秩序,必须拼接自由有序。“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章句》)在文体整体建构中,语言与语言的自由关系,必须精心建构,遵循自然声律与章句的审美秩序。刘勰强调,在诗文创作中,章与句构成了语言的自由律动,语言的自由生成,体现在章句的变化与关联中。在诗文中,没有无意义的赘语,语言的章句之间相互紧密联系,构成意义的自由呈现,这说明语言的浑然一体与文体的自由自在非常重要。“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语言的绵密与关联,构成了意义生成的自由秩序。“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在诗文创作中,语序发挥着关键作用,正是由于灵动而自由的语言表达,诗文才构成了生命情感的自由表达。“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章句》)在汉语诗文中,“字”乃最自由的语言单位,除了虚词之外,每一个单字都有实义,“连接词”则可以促成句式的自由变化和语义的自由连接,因此章句之间的统一规定,可以促成音律的节奏变化。同样,章句的字数变化,又可以促成文章的灵活多变与生动有趣。这说明,语言的不和谐、章句的不协调,都可能带来文学语言价值与情感思想形象表达的失误,造成文学文体语言创制的根本缺陷。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语言也具有本体论的位置,只不过刘勰不像强调情感那样特别言明而已。
三、心生文辞,运裁百虑:语言自由的内外修炼
从语言运动与语言呈现上看,文学语言与文体创制和文体定势有关,但是,从生命存在意义上说,文学语言与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有着最深刻的联系。从接受到创造,从创造到超越,文学语言涉及创作主体无限自由的修炼过程。文学语言的自由无边无际,文学语言的修炼必然伴随着生命的终始。刘勰相信,语言的自由决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与创作者的润饰和内心修炼有着极为亲密的联系。其中,刘勰谈到了熔裁、丽辞、夸饰和练字对文学语言创作自由的重要贡献,因为语言的丰裕与贫乏,在不同的创作主体那里表现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语言的自由”通常表现为情感的自由表达、形象的自由创造和思想的丰富性呈现。
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创作主体擅长口头语言的创作,例如讲演与谈话,口若悬河,津津乐道,此时语言的自由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主体的思想与情感;有的创作主体擅长书面语言的表达,例如诗歌与散文创作,语言的自由表现为描述的细致、音节的优美、韵律的和谐以及词义的丰赡。书面语言的自由,不同于口头语言的自由,前者作用于视觉,它需要语言的形式变化与意义生成;后者作用于听觉,它需要语言的简洁明快和语言的节奏韵律和谐,悦耳动听。当然,最自由的文学语言,必定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双重和谐”。
刘勰强调,文学语言可以充分表达情感体验的自由、思想探求的自由与形象建构的自由。为了达成这种内在的自由,他主张创作者必须做到“内外修炼”:从字到句,从句到章,从章到篇,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也可以反向操作,从而使语言实现真正的自由。语言自由的整体与语言自由的局部,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构成了语言自由的“内在和谐”,这说明,语言创作决不是任性而为,而是语言的自由锤炼与长期体察的结果。语言的力量,正是通过语言的自由想象作用与自由情感作用来完成。文学语言并不是天生的,刘勰特别强调语言的内外修炼过程,只有通过语言的内外修炼,创作者才能真正实现语言的自由。文学语言的修炼有许多方法,刘勰突出了熔裁、丽辞、夸饰和练字的特殊地位。
在刘勰看来,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文学语言与思想熔裁的重要作用,这是自由修炼的过程。他发现,“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文心雕龙·熔裁》,以下简称《熔裁》)刘勰强调情理与文采相关,语言与情感、思想、形象,总是交融在一起。“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这是强调刚柔与变通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语言的种种变化,必有内在的宗旨,必须强调语义与语词的审美和谐。刘勰认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熔”与“裁”涉及创作的内心修炼问题,前者是语言的贯通,后者则是语词的修改,都是功夫与本体的统一。为了达成自由的思想建构与情感表达,创作者必须追求语言的整体性,强调语言的简洁性,注重语言的修改。在文学创作中,语言从来不是一蹴而成的。
刘勰特别指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辞采苦杂,这是文学创作语言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刘勰强调,文学创作活动应该遵守三个准则,即“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严格来说,这是创作的三个阶段,显示出文学语言创制是一个漫长的思想修炼与语言修炼的过程。“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熔裁》)这说明,语言的熔裁是语言与情感、思想和形象不断完善的过程。
刘勰认为,“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这说明,诗文语言需要反复锤炼,只有做到语言的精微细密,才能达成真正的完善自由。“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刘勰看到,语言的繁略必须做到恰如其分。在语言的自由表达中,泥沙俱下,我们必须精心选择、精心修改,才能使文学文体语言成为完美与自由的统一体。“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熔裁》)这说明,语言的锤炼是漫长的过程,刘勰强调语言的细节变化与整体变化的统一。
在刘勰看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 这样,善敷和善删,就变成了语言熔裁的两种方式。“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缺,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熔裁》)这说明,语言的“删”与“敷”,都是为了语言的真正美感,最终促成语言的自由表达。从刘勰的文学语言创作论可以看出,语言的熔裁是极其艰难的过程。
刘勰通过诗文的考察发现,“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以下简称《丽辞》)语言与想象紧密相连,这是语言创作的智慧与情感的自由美丽。为此,刘勰特别强调《易传》中“文言篇”“系辞篇”的语言和思想的优美以及情感的深沉。他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刘勰发现,“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丽辞》)由此可见,刘勰对《周易》的思想与语言、语言与情感、语言与形象的理解极其深刻,其中,对语言与思想关系的体察,尤其深邃。刘勰强调,《易传》文辞的优美深邃,在思想表达与形象创造中,可以获得自由和谐,这是语言自由创造的典范。语言的修炼不仅是语言自身的修饰而且是思想的内在超越,只有达成思想的真正自由,才能真正促成语言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语言的自由可能只是形式的和谐,只有思想的内在和谐,才能发挥语言的最大力量。这种语言与思想的修炼,在文学创作中是极为复杂的过程,例如《周易》的语词,简洁而深邃,不仅表现了深刻的思想意义,而且充满了雄强的韵律节奏,其章句往往显现出思想的美丽与意义的卓越,实乃中国文学的奇章。刘勰强调“文言篇”和“系辞篇”的雄文奇辞,不仅肯定了其思想创造的新义,而且确证了其审美句法的创作智慧,这一例证本身,深刻地把握了汉语诗文独特而自由的美感。
刘勰还发现,“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丽辞》)刘勰看到,美丽的语言相对出现,相映成趣,生动美丽。在汉语诗文创造中,对偶是最重要的方法,它不仅构成了诗文的优美句式和韵律节奏,而且显现了语言意义的自由综合变化。“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刘勰看到了“言对与事对”“反对与正对”之间的区别。“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丽辞》)这就是汉语语言的优美与生动的体现,通过语言的自由建构探索生命的和谐,全在这语言的句法变化与语词变化之中。刘勰承认,“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这说明,言对和事对各有不同的美感价值。“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丽辞》)语言本身如果缺乏美感或韵律节奏,那么诗文就显得平淡无趣,更无法获得感动人心的审美效果。因此,刘勰指出,“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丽辞》)当语言的自由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形象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时,诗文本身就会显得生动美丽,语言的自由创造与审美变化可以促成心灵之间的最大和谐与共鸣。刘勰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丽辞”在文学语言创作中的重要美学价值。
刘勰还特别强调语言夸饰的力量,这是语言自由的狂放表达和细腻表达。夸饰本身,可以构造出壮美和优美的双重审美效果。刘勰指出,“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文心雕龙·夸饰》,以下简称《夸饰》)在此,他强调精言和壮辞对于文学形象描写的重要作用。“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刘勰看到,“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夸饰》)这就是说,夸饰可以达到极佳的形象创造效果与情感表达效果。语言的夸饰,是语言创造的真正自由表达,它通过夸张的描写将情感的自由与语言的自由融通为一。
刘勰看到,“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夸饰》)从刘勰的这些论述可见,夸饰可以促成形象与情感的恢弘表达,可以造成巨大的思想气势,显现文学语言的雄伟与壮美。这种夸饰的语言,在诗歌创作与散文创作中,可以达到极其奢华的表达效果,显示出灿烂的才情,因此夸饰在文学语言表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刘勰也强调“练字”在文学语言美感价值呈现中的作用。他认为,“夫文爻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文心雕龙·练字》,以下简称《练字》)刘勰把“语言的体貌”和“文章的宅宇”看作是对自然天地万象和历史生活的记录,与此同时,他强调语言的自然美感和简洁优美的价值。他说,“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这是就魏晋时期的语言特点立论,刘勰强调“简明的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刘勰看来,“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练字》)这说明,语言的自由必须寻求简明的思想情感表达,必须追求“后世同晓”的审美效果,否则艺术就会失去力量。如果说语言是个大概念,那么字则是最具体最生动的语言自身。在汉语中,每一个字都可能表现出语言的力量。“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练字》)可见,言与字有着最亲密的联系。
刘勰看到,“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练字》)这说明,文学语言或诗文用字有着具体的规范,必须避免这里所论及的四种情况。应该承认,刘勰对文学语言的探索涉及许多具体的语言技法,呈现了不自由的语言自身的各种困境。语言的自由,是字词生成与句篇体味的过程,每一个字词,都有自己的生命,创作者通过激情与生命表达,展现出语言的无限力量。文学语言的自由,在于它能张扬情感、扩展情感,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情感、体察自然生命与人类生活的伟大激情,语言自由创作的过程就变成了语言文字锤炼的过程。语言的演奏,如同音乐的演奏,也如同自然的天籁和声,它由许多细节组成,每一个精微处,都可以看到语言的美丽和创作者的“才情闪耀”,每一个自由语句,都是生命与形象的双重力量表达。
刘勰从中国诗文传统中充分体察了汉语语言的自由创造力量,事实上,语言的力量具体表现为文字的力量、句法的力量和篇章的力量。刘勰对《易传》的“文言篇”和“系辞篇”的体察,对魏晋诗歌语言的体察,特别是对楚骚的体察,都达到了语言美感创造的极致,构建了文学语言自由的独特抒情力量。
应该看到,刘勰通过对诗文的具体考察,对文学语言的润饰形成了许多精细入微的看法。他的熔裁、丽辞、夸饰和练字诸论,深入地分析和体察了文学语言修辞的关键作用。这些看法,源于创作,有益于创作,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精微的语言认知和语言修辞对于诗文解释者和诗文学习者来说,具有切实的创作指导意义,但是对于自由的创作者本身而言,语言修辞技巧并没有如此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过度关注语言修饰技巧,甚至可能丧失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对于诗文创作者而言,语言是内在的生命活动,它与创作者自身的天赋和创作者长期的诗文修炼有关。当历来优美诗文的语言自由地进入创作者的心灵,当诗人的思想、情感与形象建构力能够同创作者的内心语言完全契合一致时,语言就变成了自由的思想和优美的形象创造活动。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语言修辞的作用,更应该像刘勰那样强调“情感本体”的作用,当情感本体、语言本体和生命本体高度一致时,语言的自由才能变成真正自由的审美创造力量。
四、自然会妙,润色取美:语言自由的才情嘉会
语言的创制、语言的文体、语言的修炼,都涉及语言的内外关系与语言的自由效果。刘勰在讨论语言自由时,特别强调“才情嘉会”的特殊作用。这就是说,在诗文的自由创造过程中,语言与自然、语言与形象、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更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对生命整体与生命自由的高度重视。只有最大限度地表现出语言与生命的自由关系,才能建构出语言的生命自由力量。语言的自由,最终必然表现为形象的自由、情感的自由与生命的自由。刘勰强调,在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的交互作用中,“自然会妙,润色取美”,这是审美自由创造的典范特征。事实上,形象与意义、自然与情感、知音与生命,无不显现出诗文创造的真正美学秘密。刘勰通过“隐秀”“物色”和“知音”的审美考察,最终确立了语言自由与形象呈现、语言自由与形象建构、语言自由与生命沟通的内在联系。
刘勰极其强调文学语言与意义建构的重要价值,因为文学语言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既可以从创作者意义上进行自由描述,又可以从接受者意义上进行审美认知。“知音”,就是通过文学语言的美感体验自由地言说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按照刘勰的理解,语言离不开自然的体察,自然景致与诗文语言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刘勰强调,诗的形象与意义构成了“隐秀”的表现力量,自然的“物色”构成了情感与形象的表现力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语言作品与形象建构的力量,不仅需要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内在共鸣,而且需要生命主体之间的自由感通,这种主体间的自由沟通,就是“才情嘉会”的过程。
刘勰先强调“隐秀”的形象创造作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共享生命的自由世界,只要表达生命的自然世界,就可以获得强烈的心灵共鸣。“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文心雕龙·隐秀》,以下简称《隐秀》)在此,刘勰提出了文学艺术的美感问题,即隐秀问题,这是生命美感的共同基础。刘勰发现,“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这就是说,“隐”是文学作品的意义呈现与思想建构,“秀”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形象与美感趣味。刘勰强调,“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隐秀》)这说明,隐与秀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但是二者之间又相互关联。
在刘勰看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这说明,“隐”是文学语言之间的意义生成与形象生成,这种形象和意义生成,决不是单调重复或约定俗成的内容,而是“秘响旁通”,可以让人浮想联翩的生命意义世界。“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隐秀》)这是“隐”所体现的情感与形象的力量。相对而言,“秀”则是文学语言自身生成的美感力量,它是可见可感的语词世界,也是语言美感与形象美感的相生相成。刘勰看到,“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这说明,隐与秀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审美交互作用。
刘勰特别强调,自然美感有着共同的生命感通基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在刘勰看来,美丽的情态像远山烟雾,不需要装扮。刘勰还发现,“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穠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馀,而揽之则不足矣。”(《隐秀》)这说明,语言的美感创造,有其纯粹自然的形式和力量,这是语言的本源形式,因此语言的隐与秀所发挥的美感作用,往往显得奇特而生动。
在刘勰的语言认知中,“立意之士”与“工辞之人”,都能把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情感、语言与形象的美感发挥到极致。“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匿思于佳丽之乡。”刘勰认为,“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隐秀》)这说明,创作是艰难思索的过程,也是审美超越的过程,只要我们能够把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形象、语言与情感自由地联结起来,就能创造文学语言的奇迹。语言的形象表现力、语言的生命浩然之气、语言的天地感通力量,都与自然的伟大生命力量相关,隐秀就是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之间自由感通的美感力量与美感形态。
刘勰在古典诗文的考察中发现,“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这说明,自然天成,是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巧夺天工,是语言神匠的才力表现。因此,隐与秀是文学语言或文学创作的美感呈现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离开了隐与秀的原则或隐与秀的和鸣,文学的美感力量就会丧失。刘勰认为,“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语言的隐与语言的秀,是诗文创造的两个方面,离开了任何一面,文学语言的自由就不可能实现。“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隐秀》)在刘勰看来,才思与文辞有着最为自由而美好的关联:没有内在的才华,就没有自由的文辞;没有自由的文辞,才思卓越也就无从体现。
刘勰在具体的语言考察中领悟到:“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这说明,“自然会妙”是生命美感事物的本原创造和呈现,“润色取美”是创作者取之自然并运用自然的审美趣味。“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没有自然的生命感通,就没有自然的美感浸染。“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这是自然生命与文学语言的自由感通,也是形象与语言的才情嘉会。在讨论了隐与秀的美感之后,刘勰认为,“文隐深蔚,馀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隐秀》)这说明,在语言与思想表达、语言与形象创造、语言与情感寄托之间,有着极其深刻而美妙的关系,由此,刘勰将文学语言的各种美妙趣味都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描述。
刘勰还特别关注“物色”的形象表达效果,这是对自然生命美感更加生动的体察。相对而言,物色与语言自由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生命存在关系。刘勰认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以下简称《物色》)岁与物、物与容、情与辞,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语言的精妙与情景的美妙、自然的美丽与生命的快乐,共同形成了文学创作最美妙境界的传达或创造。刘勰承认,“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感物而动,语言就获得了表现世界的动力;联类无穷,就是想象驱动语言自由创造的过程。“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语言的自由,完全被自然的伟大力量所激活,心灵的自由,最大限度地驱动语言的创制。这样,思想与情感、语言与生命、自然与形象,在诗文中变成了浑然一体的自由体验。刘勰的这些伟大发现,充分揭示了文学语言的生命创造与审美交流共感的伟大力量。
刘勰的物色论,主要讨论自然对象与语言传达的关系、自然事物与情感赋丽的关系。自然事物的美妙,可以直接唤醒创作者的生命情感愉悦,自然对象本身的色彩形态与生命形态,直接作用于创作者的五官感觉体验,美妙的情感与美好的事物之间可以形成亲切的审美共鸣。在这种自然情感的体验过程中,创作者必须通过语言来传达这种自然美好的情感。创作者通过语言建构的图像效果与音律效果,必然给接受者带来美妙的生命体验,因此,在物色过程中,情与景相通、情与言合一,生命的美妙与语言的美妙,共同构成自由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深刻地把握了语言与对象世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自由互动关系。
刘勰特别关注自然风景变化与主体情感和语言创制的关系。他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物色》)这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美感境界,窥情与钻貌、吟咏与体物,就在于志与功的力量。因此,刘勰特别强调语言的精妙神奇作用,他认为,“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文学语言的自由与自然表达,可以最生动地表现文学的美感力量。“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物色》)这说明,文学虽然面对的是自然的形态或生活的常态,但是文学语言表现的形式和力量却是无限自由的。文学语言没有确定性规范,它是无限自由的,有限的语言呈现,则是人的生命力量与创造力量的审美显现。只要人能不断超越自我,那么文学语言的力量永远是无限的,因此,在自然与语言创作、心灵与观察、情感与比兴创造之间,永远有着无限美妙的生命存在境界。刘勰强调,“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物色》)在语言创造与自然描绘之间、在语言美感与情感互动之间,语言的自由可以构成最为自由美好的生命创造境界,这就是文学语言的伟大创造力量和表现力量。
刘勰特别强调“知音”或文学接受的语言美感价值体验,强调文学语言的接受与文学语言的认同,这属于文学语言创造自由的最美妙境界。刘勰认为,“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文心雕龙·知音》,以下简称《知音》)可见,人的美感期待不同,则美感体验就不同。“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这说明,语言接受与语言体验之间,可以形成强烈的思想共鸣与情感共鸣。“知音”的形成,就是文学美感期待与作品美感体验的最亲密的联结。
刘勰的知音论,不仅涉及接受者对诗文本身的理解,而且涉及接受者对创作者的心灵体察。“知音”,不仅要求接受者知人论世,而且要求接受者设身处地;“知音”,不仅是对语言与图像的亲在式体验,而且是对创作心理与创作意义的感悟发挥。实际上,“知音”不仅存在于接受者与创作者之间,也存在于创作者与创作者之间,还存在于接受者与接受者之间。“知音”是对文学语言世界和文学价值意义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生命与语言、语言与形象、形象和思想的深度建构。因此,“知音”建立了审美主体之间自由而广大的联系,将文学语言自身的美、文学意义的自由生成和文学形象的生存展示价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思想与形象的联结。
刘勰特别强调,“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这说明,文学语言需要无限自由的理解与体验。“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知音》)“照辞如镜”是极其生动的比喻,这是文学话语接受最重要的法则。“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知音》)刘勰所提到的这六观,既有创作的整体经营,又有语言的细致探讨,但是在这种创作中的整体考虑,离不开语言的自由必须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创作的自由,因为语言的自由就是创作的自由,语言的凝思就是创作的升华。不过,从情感本体论出发,刘勰依然特别强调语言与情感的内在联系。“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在这里,“情动辞发”与“披文入情”,都可以看出语言与情感的内在联系。刘勰认为,情与理、形与意,就是形象与思想、形象与语言、形象与情感的最高生命自由表达。
通过对刘勰有关文学语言自由问题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刘勰的语言自由思想极为细致深刻,他洞察了文学语言创作与文学情感表达、文学语言与文学形象创造、文学语言与思想寄托之间最深沉的联系。刘勰的思想一方面具有极其深刻的古典诗学解释意义,因为这些语言自由理论可以自由有效地解释中国古典诗文经典;另一方面也具有极其生动的现代诗学解释意义,因为它也可以有效地解释现代文学语言的形象生成与意义生成秘密。刘勰的语言自由创制理论,深刻把握了文学创作的生成本质与文学语言的生成本质,在强调情感本体时,他也不自觉地强调了语言的根本价值⑤。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的语言自由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可以由此去开拓用刘勰诗学引领现代文艺理论思想创造的新路。发掘刘勰语言自由创制理论的现代意义,不仅需要通过刘勰的诗学经典文本给予最大限度的还原,而且需要通过文学创作自身确证语言自由的复杂要求。这样,刘勰的文学语言自由创制理论,就不会再被简单地看作是形式化事件或文本策略,而会被看作是生命整体的内在自由活动。
注释:
①参见刘勰:《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牟世金,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
②参见戚良德:《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③参见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④参见李咏吟:《情感本体与刘勰关于文学价值的普遍设定》(载《文史哲》,2014年第2期)。
⑤同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