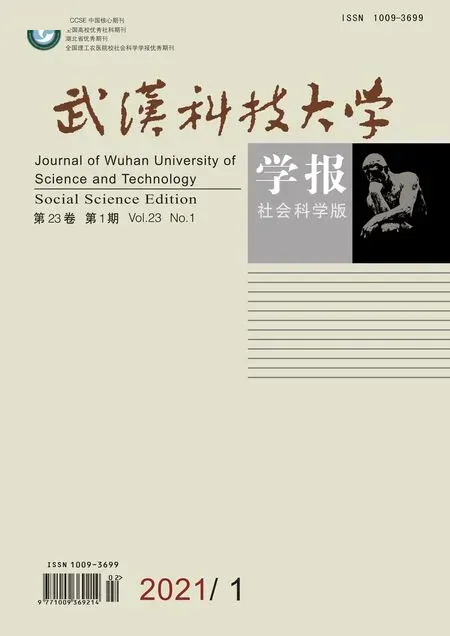金岳霖的分析性心灵哲学建树及其世界意义
高新民 李好笛
(华中师范大学 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心在中国文化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即心的文化。徐复观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多有误解,甚至贬弃。中国文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主要的工作是为人生价值寻找根基或立足点,只要有立足点,人就“有信心,有方向,有归宿”,“否则便会感到漂泊、彷徨,没有方向,没有力量”。中国文化经过自己的摸索和建构,“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是在人的自己的‘心’”[1],因此中国是最重视心同时又作了最多探讨的国度。当然,由其价值取向所决定,经过对心的探讨所成就的心灵哲学主要表现为与西方的求真性心灵哲学大异其趣的价值性或规范性心灵哲学。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而且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一部分熟悉中西文化的哲学家在中西碰撞、融通大背景下仍坚持对价值性心灵哲学的“接着讲”。所谓“接着讲”,是指他们的有关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儒道释价值性心灵哲学的继承,同时由于融合了西方有关思想成果,因此不是简单的“照着讲”,而是在继承、融合的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不过,这里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湖南籍现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的心灵哲学建树。尽管他没有直接接触当时正在兴起的西方分析性心灵哲学,至少从他的有关论述中看不出他读过西方心灵哲学的奠基之作,但由于他受过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良好训练,因此在探讨和谈论心时便表现出了与众不同、非同凡响的特点,甚至可以说,他建构了与西方分析性心灵哲学不谋而合但又有自己特点的中国式分析性心灵哲学。
一、“分析的功夫”与意志、心理因果性、人格同一性
金岳霖(1895~1984),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曾进行过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尝试,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其著作有《论道》《逻辑》《知识论》等。他尽管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贴上语言分析、分析哲学之类的标签,但字里行间浸透的是西方当时正在发展的分析方法和精神,表现出他对“分析的功夫”的驾轻就熟。这功夫尽管本源于哲人的天资,但也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启发,特别是受到了罗素等著名西方分析哲学家的影响。他说:“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他自述是从罗素等人那里明白了这些道理的,并且在自己的研究中一直“注重分析”[2]145。
由于他对西方哲学有深邃研究,且批判地把有关思想融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中,因此他尽管没有注意和专门研究西方20世纪上半叶诞生的分析性心灵哲学这一哲学分支,但由于他把握了英美分析哲学的精神,因此在讨论有关心理现象时,便表现出十足的分析性心灵哲学意趣。在分析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时,他强调:这些概念都有歧义性,因此应先弄清它们的不同用法,再来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他说:“如果我们能用点分析的功夫,我们就觉得自由意志没有绝对的意义。”[3]215由于这个概念不止一种意义,因此它与因果关系是何种关系,就应具体分析。他强调,是否有绝对的自由意志,这要看“自由意志”一词的用法。如果完全在心理学范围之内讨论,那是应该承认有绝对的自由意志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意志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可以不与事实发生关系,因此不会受到限制,例如“我想爱月光,我就爱月光”。如果从与事实的关系的角度看,意志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一种情形是从事物的束缚性看意志。这很复杂,不能绝对说有没有自由,例如中国女子在以前不能与男子社交,在西方人看来不自由,但在中国女子自己看来,并没有不自由的感觉。其他情形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反感的时候,与自由不发生关系,有反感的时候才发生关系”。这里的具体情况有两大类六小类:一类有束缚:①不觉得不自由,也不觉得自由;②觉得自由;③觉得不自由。另一类没有束缚:①不觉得不自由,也不觉得自由;②觉得自由;③觉得不自由。
“意志”有时有“目的”的意义,如果这样看,这里讨论的顺序就应是“从意志(目的)到事物”。它们有两种情况四种关系:一种情况是有阻碍:①能达到目的(自由);②不能达到目的(不自由)。另一种情况是无阻碍:①能达到目的(自由);②不能达到目的(不自由)[3]216-217。
“因果关系”本身也值得具体分析。根据他的梳理,它有旧式因果关系和新式因果关系之别。关于意志与事实的关系,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说它们一定没有关系,但我们可以说,这类的关系在意志与事实间算是极少的了。”“就是有因果关系,意志也不见得因此就自由,也不见得因此就不自由。”[3]214
人格同一性问题是当今心灵哲学和伦理学的热门话题。尽管金先生没有与西方这些领域的直接思想交锋,但所作的讨论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另外,金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人格是否有同一性之类的问题,只是在论述同、等时涉及了它们,因为他是从形而上学上来论一切事物的同、等的质与量,而“由于我们的本身也是一种事物”,因此他对同、等的分析也适用于人这个事。要探讨人格同一性的根源、条件,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同一性?世界上有无同一性?人身上有无同一性?有什么样的同一性?金先生回答的就是这里的形而上学问题。他的提问与分析是很超前的,因为这些问题现在才成了心灵哲学形而上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首先他区分开两种“同”,即①“相同”——多个事物是否相同?②自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空中是否相同?他的看法是:绝对的、完全的相同和自同都没有,只有大致的相同或相似。无论从事实还是从理论上说都是如此,这些看法在当时是很新颖、很超前的,西方心灵哲学只是到现在才有人强调和阐发这类思想[4]305-308。他对“相等”这个概念的分析也是这样,他说:“经验中的相等是差不多的相等,不是完全相等。”[4]313由此所决定,所有的计量都是“差不多”,如说一匹布30尺,这是在“尺”的精度内说的,如果再把精度提高,情况就不是这样[4]315。如果有这样的概念分析作基础,再把它运用于人格同一性这一个案之中,自然会引出极有见地的思想。
二、心物分析与作为“感受性质”典范的知觉
对心与物及其关系问题,金先生也有自己的分析,总的思想倾向带有现象学、中立一元论的性质。在分析印象时,他像休谟一样承认有两种印象,一是由外界引起的或关于外界的印象,如关于苹果之红色的印象,二是关于体内状况的印象,如感觉到身上的痛痒,这些印象是“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他说:“外界的印象不必是‘物’,内体的印象也不必是心。”只要对之作出分析,就会发现,“无论哪种印象都有物,都有心”[5]347。“印象之外,不必有心与物,如果有,我们可以不理它们”。“我所要注意的是,心与物虽然可以成为哲学中心问题,而不必是哲学中心问题”,“不必用终身的精力徘徊于心物之间”[5]377。
金先生对知觉现象的研究有明显的心灵哲学意趣。我们知道,这是心灵哲学产生之初罗素、维特根斯坦等研究得较多的一个课题,在现当代,由于它是新发现的“感受性质”(qualia)或现象学性质的载体,或者说里面充斥着感受性质这样的本质特点,因此成了心灵哲学的前沿热点研究领域。金先生在吸收西方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了有中国特色的解答。像其他分析哲学家一样,他首先对相关概念作了分析,认为知觉(perception)不同于感觉或官觉(sensig),因为有感觉时不一定有知觉,如熟视无睹。其次,他把知觉现象与事实或事件(event)区别开来了,前者是一种心理现象,后者有复杂的构成。例如,知觉事实包含以下因果系统:自然的因果系统(此指由外物到感觉事实)、化学、生理学、心理学范围内的系统(指生物的演化历程)、语言历史的因果系统(文化的历程)、知觉发生时的地点和时间。质言之,“知觉事实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一件的事体,受许多因果系统的影响,外物也不过是群因中的一因”。知觉现象不同于知觉事件,因为它是混合性的、显现性的,因此不是一件东西或一件事件[6]410-411。另外,知觉事件是外物的结果,而知觉现象则不是。知觉现象尽管是知觉事实的部分,但“本身不必属于任何具体的知觉事实的因果系统”[6]411。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些讨论中深入到了知觉的主观与客观问题,而这恰好是当代西方感受性质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当今的研究中,主流的倾向是强调知觉的主观性,而金先生的先见之明在于:既承认知觉有主观性,又强调知觉其实有客观(物观)性、公开性。主观性在于:对同一对象,不同知觉者有不同的知觉经验,“各个人有各个人的知觉现象,而这些知觉现象彼此不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地对于一件东西也有不同的现象”。为什么说知觉现象有客观性、公开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点类似于今日坚持物理主义的人面对感受性质责难所做的工作。反对者由于强调知觉的主观性、私人性、受观点限制等特点,因而“坚决地说知觉现象不是物观的(客观的——引者注)”,而金先生撰《知觉现象》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困难问题”[6]413。他把他化解知觉现象难题的策略称作“观点论”,这类似于当今物理主义迎接感受性质挑战所提出的“现象概念策略”。他说:“观点论的主旨是把人与地点及时点分开,把一部分心理上的不一致的情形变成几何上的不一致的情形。”[6]414这里的“观点”有特定含义,指观察点,而此观察点要用几何学方法来描述,因为知觉者和被知觉的外物都有其位置,两位置的关系是几何关系。他说:“从外物的位置R-欧几里德直线到知觉者的位置,以这直线为半径成圆体形。”因此一圆体就是一观点。这观点表面上是主观的,其实是有客观性的,因为它有客观性,因此由之而起的知觉现象也有客观性。就单个人的知觉来说,由于观点不是点式的、经验内的东西,而是包括外物与知觉者的圆体或系统,因此“外物与观点”就有内存关系。由此所决定,知觉者在不同观点中所得的是性质不同的知觉现象,而在同一观点中,不管位置如何,只要知觉者有同样的感官与知觉,那么他在同一观点中所得的知觉现象就必是相同的知觉现象,因此有客观性。不同的知觉者对同一对象的知觉由于观点相同,因此也必有其客观性。这是因为,知觉者都是人,只要是人在与对象发生同样的位置关系,就会有同样的“观点”,因此“在同一观点中,无论在何位置上,知觉者与外物在知觉事实中发生外在关系,只要知觉者是‘人’,他们所得的现象就是同样的知觉现象”[6]416。
如果说上面对知觉现象的分析是横的分析或空间的分析的话,那么下面则是直的或时间的分析,其结论仍是相同的,即知觉现象具有客观性。他的推论是:“在直觉方面,我们既可以感觉到知觉现象的相同与接续,在经验方面,又能感觉到它的融洽与常一,我们联想到知觉现象所代表的东西,就是外象,是独立地接续地存在的。”[6]421由于知觉现象是客观的,可看作是外物本身,或者说,可由知觉现象推论出外物的性质。他说:“外物与知觉现象相等。”知觉现象尽管有随知觉事实出现而出现的特点,但也可以说它是独立存在的[6]426。
在分析思想时,他指出有两类:一是动的思想,如从上午8点一直想到12点,这种想是一种历程。二是静的思想,它不是历程,而是所思的结构,或思维的结晶[2]142-143。还可从这些方面去分析,一是作为能力,二是作为活动,三是它的样式(可区分为两类,即思议和想象),四是动静,即有动的思想(如“你去想想”)和静的思想(如思路通畅)之别。动的思想有时间过程,而静的思想没有这样的过程,它有关系,但只是结构关系。如果不在这些分析上标上金先生的名字,只看内容,那么由于它与今日心灵哲学的思想研究风格如出一辙,因此可能会以为它出自西人之手。
三、心能、理、道与性情
《知识论》尽管主要是一本认识论著作,但有心灵哲学的意趣,因为它要研究的是知识的“理”,是知识中的“一般”“普遍”的东西,而对此的研究就必然进到对心之理的探讨。例如,知识论必然涉及五种感性认识,即耳闻目见,而要予以研究,就必然要既研究它们的对象,又研究它们的“官”“能”,如视官有视能,等等。他强调:除这些官能之外,还有“心能”[7]19-20。心能不是官能的“所”或对象[7]21,但肯定是可以研究的。“这里所谓心只是能见、能闻的能力而已。它只是‘觉心’,也许它是普通所谓心的一部分而已”[7]22。这些论述无疑触及了心的深层次的结构和本质问题,属于纯正的心灵哲学探讨。
在阐述理-道这类带有形而上学、伦理学、价值性心灵哲学意味的问题的时候,金先生尽管有对传统儒道释思想和方法的承继,但显然也贯穿着他所热衷的分析方法。他认为有两种理:一是潜藏于事物内的由科学、知识论所知的实理,二是纯理,由于它不是根据事实求得的,因此它的特点是“虚”,它不表示事实,也不增加我们的知识。尽管虚,“不见得就是虚无所有的虚”,关于它所形成的逻辑命题“虽不表示事实,然而它不能不有所表示”。相对于事实,纯理是虚,“相对于现实,纯理不虚,不仅不虚,而且表示最普遍的道,最根本的道”。相对于传统的道论而言,金先生的道论有明显的进步,例如他对道作了进一步具体的分析,认为道是式(纯形式)与能(纯材料)的综合[2]154-155。由于道有无穷妙用,因此每种大文化都有它的中坚思想,中坚思想内又有它的最多概念和最基本的原动力。他说:“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它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说:“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就学科性质而言,道学即元学。他认为,“关于道的思想”是“元学的题材”,不是科学知识论的对象[2]156。这种研究有双重意义,即:一是满足理智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要求,二是“求情感的满足”。他说,在做这种研究时,“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的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2]156-157
性、情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焦点问题之一,同样也是他的道论的主题。根据他的分析和界定,性是存于个体中的共相,情是存于个体中的特殊性或具体情况。人的情是普遍的情中的一种。具言之,“是动于中而形于外”的东西。情与用一样是人的认识最初、最容易接触的,是认识体、性的入口。“情求尽性,用求得体,而势有所依归”。自然事物的表现都是尽性,如水往低处流就是“尽性”。人也是这样,情是性的表现,因为“性是情之所依,性表于情,情依于性”[2]323。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即情求尽性而不尽性。
有无至真、至善、至美的总目标?回答是:它没有现实的存在,没有达到,但可思考和言说。这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太极,它真且善、美、如、乐,这种最高、最理想的目标可称作太极。他说:“道无终,无终的极为太极。”“自有意志的个体而言之,太极为综合的绝对的目标。”“目标的现实虽在未来,而目标之所以为目标至少是因为它在现在已经是思考的对象。”“太极为至,就其为至而言之,太极至真、至善、至美、至如。”“如”即佛家所说的不变不动的真如,当然也有自如、自主等理想意义。他说:“在极,情尽性,用得体,万事万物莫不完全自在,完全自如。”他倡导这一理想境界、崇高目标的理由是:“免除好些西方的性情中人对于天堂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太极不是不舒服的境界。它不仅如如,而且至如。”[2]327-329
论道当然不能撇开心。而在讨论心时,他强调,由于心有多种极为不同的用法,因此不是每种用法都与道有关,只有良心与此关系密切。金岳霖先生尽管没有用到“分析性心灵哲学”之类的概念,但由于他精通分析哲学,且将它变成了自己哲学思维的基本框架,因此当他把它用于对心的概念的分析时,自然便有事实上货真价实的分析性心灵哲学。这一心灵哲学的个体发生学其实复演的是英美分析性心灵哲学的发生学。在这一发生学中,心灵哲学恰恰是分析哲学运动的一个必然产物。金先生像著名分析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在《心的概念》中一样,对“心字的各种用法”作了细致的分析。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他认识到:“大部分的哲学上的笔墨官司,是为心字或物字而打的。”他找到的用法很多,如日常生活中可指一个东西、共相,可用于表示意识、意思、意志,等等。另外,心还在生理上运用,如指心脏、大脑。在伦理学上的用法指的是良心[8]494-501。哲学上的用法一是“万物皆有心”,二是“上帝的心”或“帝心”,三是“超心”,四是作为思想之官的心。金先生还从心与思想的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心是思想的能力[8]499-500。他强调,心物及关系问题可予以回避,最好不用“心”“物”这两个字;如果没有,“似乎可以减少许多问题”;“哲学上的心物之战当然用不着讨论”;这“很省事”;“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问题”[8]499。很显然,金先生通过自己的分析,与西方逻辑经验主义可谓殊途同归,最终都有拒斥心身问题这一形而上学问题的倾向。
四、若干思考
与同时代其他哲学相比,金先生的心灵哲学探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其他学者在探讨心时,关注的主要是心体之妙用,这种“心”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其道德哲学、人生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中具有基础性、枢纽性的地位,是由“下落”到“上升”、由“内收”到“外扩”的枢纽和转换器。根据徐复观先生的说法,天命、道、理等下落、内收,便有了中国哲人所要面对和思考的心,通过对它的独特的研究,他们既发现了西方哲学家所发现的那些具有知识论价值的东西,又发现了他们未加注意因而不可能看到的丰富而珍贵的非知识论价值资源,即道德论的、生存论的、修养论的价值资源,一言以蔽之,成圣的价值资源。由此所决定,中国便有十分发达的价值性心灵哲学或如今日西方所说的“规范性心灵科学”。这种特殊的心灵哲学,也可称之为圣性理学或心理哲学。这是“去圣”的“绝学”,至少是其中的枢纽和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致思取向比西方的心灵哲学要广泛,即不仅要追问心灵是什么、是否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与身有何关系之类带有科学和哲学本体论双重性质的问题,而且更为关心的是圣人的心理标志,成圣的心理机理、机制、原理、条件和方法、途径等问题。应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理”不是规律,而是机理、原理、机制,甚至有“纹理”的意思,类似于莱布尼兹所说的大理石之“花纹”。更为重要的是,它关注的心不是一般的心,而是心灵之中的、由自然所授予的“性”或价值资源。中国古代的圣心理哲学就是要以此为条件、根据和基础,用类似于康德的所谓“前进法”,顺推人的善行、德行,人的最美好的人生境界、无漏的幸福生活,人的真诚与美丽是如何可能的,圣人人格之成就是如何可能的,是如何从先天的资源中生发、扩充出来的。因此中国心理哲学的任务是要探寻至圣之道,而直接的对象是心,尤其是其中的先天的禀赋和价值资源,而宗旨是揭示这一资源生成圣人之“理”,即由潜在的性转化为现实的性(圣)之理。这样的探讨在金先生的心灵哲学中极少见,即使在他的道论中有所涉及,但主旨和论述的方式大不相同。
其他学者建构的心灵哲学也可称作“心教”。如钱穆认为,这种心教既以仁为最高境界,又以仁为进入此境界的根本途径。他说:如果说中国的哲学是一种教化的话,那么它可被称作“心教”,儒学就是这样[9]16。他认为,儒家建立心教旨在解决人生两大难题,一是死与生的矛盾问题,二是人与我的矛盾问题。西方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特别强调宗教、法律和道德,中国则不同,如孔教是通过“心教”来解决上述问题的。心教教的是:去凡成圣,或成仁,只要成仁,就没有上述两个矛盾。因为“在仁的境界上,人类一切自私自利之心不复存在,而人我问题亦牵连解决”。“扩充至极,则中国社会可以不要法律,不要宗教,而另有其支撑点。中国社会之支撑点,在内为仁,而在外则为礼”[9]17。
即使是与对西方哲学同样训练有素的贺麟相比,金先生的特点也显而易见。贺先生是我国最早关注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基础问题——心身问题研究的哲学家,而且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其中特别是精通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对于诸心身理论的关系,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当然是可进一步商榷的看法,如他认为,“身心平行论是副象论和心理一元论的前身,副象论是唯物论的一种形式,心理一元论是唯心论的一种形式。因此一谈到身心平行论我们就投入了身和心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而身心关系这个问题又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机械论和目的论、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的焦点”。在总结有关心身学说合理内容、改造身心平行论的基础上,他论证了自己的心身合一论。另外,在分析心的概念时,贺先生也有重语言用法分析的倾向,但整个看,他并未像金先生那样把这一方法贯穿在心灵哲学的所有问题上。最后,就价值取向来说,贺先生关注的仍主要是如何建构价值性心灵哲学这一问题,他倡导的“新心学”足以说明这一点。“新心学”这个词不是贺先生自封的,而是学界鉴于贺先生思想的特点,相对于冯友兰自创的“新理学”而为他的理论安立的一个名称。他自己的命名是把他的有关思想称作“精神哲学”。他说:“故唯心论又尝称为精神哲学,所谓精神哲学,即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哲学。”[10]由于“精神”与“心灵”在西文中可为同义词,因此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也常被译为心灵(mind)哲学,而贺先生所欲建立的精神哲学正是我们要探讨的价值性心灵哲学。贺先生由于精通西方哲学特别是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心灵哲学,因此所创立的新心学自然别具一格,即不同于已有的新理学、新心学,如接受了西方哲学的影响,融合了心灵哲学对心的认识的成果,同时取东方诸家之所长,补心学之短。在吸收西方成果反思中国心身学说时,他又没有妄自菲薄,而持十分辩证的态度,强调中国心身有这样的特点,即超二元论,反对灵肉二分,现象地、一元地而不是截然两分地说心与身。
在西方,分析性心灵哲学是现代心灵哲学最早表现出的形态,后来一直以与现象学心灵哲学分庭抗礼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它敏锐地看到:常识和传统的心灵认识乃至心灵哲学都是错误的堆积,其根源是把心与身并列看待的“范畴错误”。要让心灵哲学摆脱困境,唯一出路就是分析日常心理语言。随着它的分析的推进,一种新的心灵哲学即语言分析的、以逻辑行为主义表现出来的心灵哲学便应运而生了。随着研究的推进,后来还陆续诞生了许多形式的分析性心灵哲学。分析性心灵哲学的有些形式尽管已成为历史,但其历史功绩不可小视。丹尼特说:“最重要的是,这一对于语词的新的分析方法确实摧毁了构筑心灵哲学理论的传统方法。”[11]51它的一些形式的淡出尽管与紧接着出现的自然主义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与它陷入琐碎的分析、充满着严重的错误和混乱有关。丹尼特说:“它的弱点随着它陷入琐碎而日益显露出来。”[11]51尽管如此,它对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的心灵哲学的建立是功不可没的,它倡导的方法、精神、原则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潜移默化于后来的探索之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比较的角度看,金先生强调心灵研究中要重视分析的功夫,无疑也是看到了过去谈论心时陷入的误区,因此在中国倡导和践行分析性心灵哲学对于中国心灵哲学的健康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先生对心的分析又没有西方的“陷入琐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