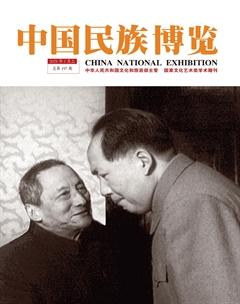文化遗产研究刍议
【摘要】“遗产”之“遗”本义为传续、继承;“产”即“财产”“资产”。“遗产热”“遗产运动”已悄然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就文化而言,人们今天强调“传承”,不过刻意强化那些在现代语境中被凸显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遗产已与生命、生活融为一体。就遗产而言,在遗产实践的过程中,主体性和整体性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只有对文化遗产这门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之后,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遗产;共时;主体性;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1-078-03
【本文著录格式】高玲玲.文化遗产研究刍议[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1):78-80.
遗产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遗产学的任务首先是对“遗产”的概念和范畴进行梳理。由此才能论及:如何建构中国自身的遗产学体系?如何借鉴西方已有的遗产制度?如何对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法规,结合我国的国情,保护、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如何使公民意识与遗产传承有机结合在一起等问题。
一、“遗产”与“文化遗产”释义
“遗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1)死者留下的财产,包括财物、债权等。(2)借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从英文语义来看,‘遗产与‘继承-(inheritance)的概念同源,意义相关。”从广泛意义上说,所有自然存在、历史存续的事物,都可以称为遗产。不同机关与组织由于标准不一,对于遗产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最具权威性,也是被引用最多的当数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性公约,即《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中从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方面对‘文化遗产做了定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遗产的认识以及遗产立法方面也存在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形态上看,遗产可分为物质性的、非物质性的。1982年,“非物质遗产”部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至此出现了“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分类。后来,受到日本遺产保护法的一些概念和分类即“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正式将原来的“物质/非物质”分类名称改为“有形/无形”遗产。“对于‘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和范围,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正式的官方用语和操作概念。”
“从遗产发展的层面来看,当代遗产在概念、定义和分类方面呈现出几个特点。遗产的概念具有流变性,有的原义已经被新义所覆盖和取代。其次,在遗产概念的使用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制定相关遗产保护法规和法令方面起到了先导和主导作用。”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一些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其遗产概念和分类原本有着不同的发生和发展轨迹。再次,“现行的遗产概念和分类还不能将所有的遗产类型都囊括其中,有些观念性的、宗教性的、伦理性等遗产类型,在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所形成和演化的人类智慧、技艺未能包括在内”。现行的遗产概念和分类很可能,或者已经将未被包括的遗产排斥在外。过于详细的遗产分类反而打破了遗产自身的整体性,大部分作为整体的遗产是无法分析、无法拆解的。综上,一方面,在遗产分类中,我们要尽可能做到细化,又要进行整体性认识和保护。
二、遗产研究的理论向度
从遗产的时间角度出发,遗产的历时向度是从知识考古方面梳理,就共时而言,以及相关的践行皆在全球、国家和社区/地方这一三位一体的框架内具体操作,并拓展到相关的领域,如历史、表述、经济、保护等,以求其广,我们称之为遗产的共时认知向度。下文以后者为线索展开讨论。
(一)作为“活态历史”的遗产
文化遗产可以从种类上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通常以口头、表演、器物、仪式、习俗等方式呈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通过人们的身体力行代代延续下去。“因而,遗产又被人们称为‘活态历史,或者‘活的历史。”
在《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中写道:“所有的文化和社会均扎根于由各种各样的历史遗产所构成的、有形或无形的固有表现形式和手法之中,对此应给予充分的尊重。”遗产作为活态历史,将官方与民间、精英与草根、大传统和小传统等多个二元对立的概念有机结合到一起。更重要的是,遗产作为活态历史,揭示出传统本身就是一种鲜活的生命,遗产体现了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状态。活态历史也表明遗产是不断演化和变迁的,这就导致活态历史只能活态传承,活态保护,不能将其凝固化、固态化。简言之,“遗产就是活在当下的历史,今天生活本身就是明天的遗产”。
(二)遗产与经济
遗产能够保存至今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由于其中凝聚了社会的情感因素。尽管遗产与货币相结合出现了市场化的情况,但是在遗产的保护过程中需要经济进行支撑,同时遗产又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但是,遗产与经济又和一般商品不同,遗产本身具有其内在的象征价值,这种价值使遗产成为遗产。
通过利用遗产价值或者创造遗产的附加价值,从而实现生产和再生产,使其商品化带动消费,从而拉动遗产旅游。“在市场机制下,遗产被生产与再生产,形成了“遗产产业”,以遗产本体为核心规则、开发、投资、保护、商品化等活动,都促成了遗产产业的形成。但是,“遗产化”不过是“遗产的第二次生命”,具有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附加值”。“我们今天所面临和认识的“遗产”正是‘过去生产的遗产+现代制造的产物。”
当下大规模的旅游活动开展,也会使遗产和遗产地出现一定的问题,一方面,为了经济目标吸引大量的游客,许多政府机构,商业团体将遗产当做赚钱的工具,对遗产进行装饰,使遗产的寿命大大缩短;另一方面,大量游客的到来使遗产的主体性出现倒置现象,家园遗产的主人处于失语状态。
(三)遗产保护
就遗产的存续来说,遗产保护实践中必须遵循的重要依据和原则是原真性和完整性。原真性概念最初出现在《威尼斯宪章》(1964)。《威尼斯宪章》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这一表述认为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单纯的保护遗产作为“物”本身的状态,更多的是保护遗产这一整体以及经历了时间变迁后遗产留存下来的文化精华。对于遗产原真性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多元文化基本成为一种共识,同时在地方政府、媒体、商业资本、专家学者的合力运作之下,传统的民间文化面临着“遗产化”的洗礼,传统文化的再生产、重构成为趋势。“完整性”,表示尚未受人干扰的原初状态。在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完整性原则首先出现在国际保护联盟对自然遗产提出的标准中,主要体现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包括保护遗产本身,也涵盖与之密切相关的生存环境。完整性还包括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历史、科学、情感、价值等方面的内涵和文化遗产形成的要素。”
除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对于遗产的保护也有相关的遗产法律。“1913年,法国颁布《保护历史古迹法》,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日本。1950年制订、后经多次修订的《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财分为五类,即‘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和‘传统建筑物群落。”
“国内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法规也可根据法律效力的不同分为几个层次,除了保护世界遗产的国际公约外,从宪法到一般性法规、地方法,再到规章制度,形成了一个错落有致的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境内人类遗产保护的有力凭证和保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该条规定了自然资源的产权归属。
三、遗产事业的当代省思
在上述阐释遗产与历史、经济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其中,当下存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遗产与保护的关系。在遗产实践中,遗产的主体性和整体性为至高无上的原则,任何遗产的概念、分类以及对遗产的认知、分析都与遗产主体性、整体性彼此相关联。
(一)遗产主体性的缺失
遗产的可持续性取决于遗产的主体性,而非那些概念变化、术语翻新。至于那些针对遗产的法规法则、行政管理,则必须迁就和服从遗产的主体性和整体性。如果丢失了遗产主体性和其整体性,那么遗产便没有了“遗产”。
“遗产的主体性可以是多样的和复杂的。遗产的主体性表现为个体(部分)一集体(全体)之间的认同关系:遗产一方面属于民族和集体,另一方面又属于个体。”因此,由于遗产主体的特殊性,拥有遗产主权的应该是个体与集体的聚合,换言之,它应该是既代表族群,又可以反映个人意愿的人群共同体。然而,在具体实施层面,由于政治与资本的裹挟,遗产的主体性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然而迫于遗产保护中“完整性”与“原真性”的原则,许多遗产地需要维持原貌,原住民反而丧失了其所在传统社区改造以及发展的权利。伴随着全球化趋势推进,纯粹封闭的传统社区几乎不存在了。当传统与现代发生交汇,原住民自身的文化与观念势必受到冲击。
当然,任何一个人群都应该有追求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权利。但我们可以对其遗产进行整体的收集、记录和存档,比如说有些仪式,如傩戏,里面含有宗教的东西,现在还有些老人表演得较为完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录像,做记录,将整个仪式过程拷贝下来,建立档案,存档,使以后的研究者有资料可查。除此之外,若当地人不愿意维持这一仪式,也不能用强制的手段要求维持。
(二)遗产整体性的破坏
自上而下的遗产管理和旅游经济开发,使遗产所处的地方社会认同和养育根基越来越薄弱。“遗产产生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维护认同”,在“移动性”的旅游情境下,倡导或者说重拾遗产的“地方认同”和“地方拥有感”已经变成各个族群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否则,整个族群的认同纽带将难以持续。如何重拾遗产的地方认同和地方拥有感?用有归属感色彩的“家园遗产”取代生硬、中性的“遗产”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家是个人世界稳定的物质中心,是人们可以放心离开和安全返回的安静所在。”依托于血缘与地缘的纽带,人们形成了对地方性的家园意识。对于“家”与“家园”的意识,不仅涉及遗产的归属主体,也同样涉及到外来者的权利与责任。
作为整体的遗产,其内涵不仅仅是“物”,而是“物”中所凝结的文化,遗产通过这种“物”将记忆与知识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在这些“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先辈创造、重塑这些记忆与知识的能力。人类通过这样一套象征体系从而不断向前发展,遗产不仅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家园遗产强调的是遗产的整体性、遗产的归属性,就是说这个遗产属于这个特殊的人群,特殊的共同体,其内部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的纽带。然而,在遗产与旅游结合的过程中,遗产转换成了景点,家园的主人处于虚置的状态。家园内部的纽带发生了断裂,整体性受到了破坏。
以洪崖洞为例,近年来,重庆依托于其魔幻山地城市的环境特点吸引了巨额的人流量。资本引导下注意到这里的商机的人选择投资开店,很多重庆传统的居住地转换成了商业区。游客旅游时所看到的几乎全是外地人开设的商铺,原住民的离开与外地人的进入导致了景区的“空巢”现象显著。遗产本来应该充满生命力,是“活”的,但在成为遗产地之后,反而加剧了“活文化”的缺失。依托于“遗产”之名的旅游景点反而是对遗产地赤裸裸的讽刺。可以发现,作为网红打卡点的洪崖洞吸引了足够多的游客,然而这种“网红”效应与洪崖洞本体所塑造的文化价值却断裂开来,换言之,洪崖洞没有找到它作为遗产的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民俗风貌区的洪崖洞在建设的过程中,原住民是完全搬离了的。游客所聚集的网红打卡点通常是洪崖洞外景,夜晚很美丽的灯光秀,但是失去了生活气息的洪崖洞更像是一个商业化的空壳。这种空巢现象其实对于家园遗产的纽带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同时,空巢现象在中国遗产运动中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題,值得我们深思。
四、结语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蕴藏并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髓,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遗产之厚重仍待我们细细研究、慢慢体悟。
参考文献:
[1]Howard.P.HeritageManagement.Inter-pretation,Identity. London/New York:Continuum,2006(6).
[2]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世界遗产相关文件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彭兆荣.文化遗产学十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
[5]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6]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衰述与制造[J].文艺研究,2008(2):87-88.
[7]于海广,王巨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8]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9]Harrison.D.Hitch-cock.M.(eds)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Clevedon Buf-falo Toronto: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5(1).
[10]Rapport.N.Dawson.A.(ed.)Migrants of Identity:Perceptions of Home in a World of Movement.Oxford England:Berg,1998(6).
[11]彭兆荣,林雅嫱等.遗产的解释[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作者简介:高玲玲(1993-),女,汉族,四川南充人,艺术学理论硕士,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研究方向: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