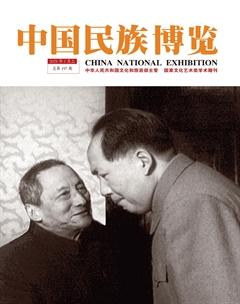袁行霈:学问的气象之论学与散文

「论学两篇」
体志气韵
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馀师录》曰:“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
此所谓“体”“志”“气”“韵”,其含义可意会而难言传。如果要试做一简单的说明,似乎可以这样说:“体”是主体、本体的体,包括体性、体貌、体势、体器等意思,是格局、规模所构成的总体面貌,是诗文的根本。体贵在“正大”,不偏不倚,不局不促,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志”是诗文所饱含的思想内容,贵在“高远”。古人有“诗言志”的说法,志有高下之分、远近之别,高远才是上乘。“气”是作家平时的精神境界(人格、性情、才调)和创作时的心理准备(激情、冲动、勇气)在作品中的表现,气以雄浑为贵。雄浑,是形容气的充盈有力。司空图《诗品》曰:“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有雄浑之气,才能有磅礴之文。“韵”是指韵味、情韵,语言之外令人回味无穷的意蕴,久久荡漾在读者心中的回响。韵当然以隽永为妙,隽永则令人永志不忘,具有长远的艺术效果。
“体”“志”“气”“韵”可以作为我们评价欣赏诗文的标准。文中之佳作,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等,莫非如此。诗中之佳作,如李白《关山月》、杜甫《秋兴》、陆游《书愤》、文天祥《正气歌》亦莫非如此。其实,又何止诗文呢?书画也是如此。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体志气韵四者兼备的作品,每读此帖,辄深感其正大高远雄浑隽永之兼备而且达到了极致。特别是那气韵,体现魏晋士人特有的文化氛围和玄远意味,后人是难以学到的。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他们的书法之所以成为后人的楷模,也由于这四者很好地协调在一起。即以颜真卿而论,他的楷书结体端庄雄秀,天骨开张,用笔浑厚强劲而又饶见筋骨,雄力内含,大气磅礴,具有盛唐气象。他的行草,如《祭侄文稿》,结体沉著,笔划飞扬,其浩然凛然之正气贯穿于始终,读之回肠荡气。画家当中早的如李成、范宽、马远、夏圭,且不必说,即如我喜欢的元代画家高克恭,其《云横秀岭图》设色画云山烟树,溪水茅亭,白云横岭,树木葱茏,气韵之勃郁流润,直欲溢出画面之外。
忽然想到,“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这四句话不是也可以用来评论人物、修养自我吗?正大,遂能有气象;高远,遂能成大事;雄浑,遂能有力量;隽永,遂能得恒久。艺术之道和为人之道,原是可以相通的,艺术的至境和道德的至境也是相近的。从艺术欣赏中可以悟出做人的道理,从修身中也可以得到艺术欣赏的眼光。
江山之助
今冬北京多雪。一天,趁那雪下得正紧的时候,到燕园散步。只见未名湖一带迷迷茫茫,隐现些树木和楼阁,宛如梦境一般,不禁想起前人咏雪的诗句。唐太宗的“无树独飘花”(《望雪》),暗含柳树飘絮的比喻;杜甫的“舟重竟无闻”(《舟中望雪》),暗示雪与雨的不同,都富有意趣,岑参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清新流畅,惊异中透露出对春天的期待,是咏雪的名句。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这两句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一作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人准确地把握并表现了雪后的视觉效果,那雪悄悄地来到眼前,满铺在大地上,给人一个惊喜。至于宋人张元昊的“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见宋俞文豹《清夜录》所引,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引《西清诗话》同。但《苕溪渔隐丛话》所引《西清诗话》作“张元”,诗的字句亦有异。待考),极尽比喻形容之能事,虽然显示了奇特的想象力,毕竟雕琢夸张得有些过分了。
从这些咏雪的诗又想起唐朝宰相郑綮的话,当有人问他:“相国近有新诗否?”他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孙光宪《北梦琐言》)这不太经意的一句话,说出了写诗要到大自然中寻找灵感的道理,很耐人寻味。
关于诗和大自然的关系古人有不少论述。刘勰早在《文心雕龙·物色》就说过:“然屈平所以能够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他把屈原之所以能写出好诗的原因,解释为得到了江山之助,是大自然陶冶了屈原的诗情,赋予他灵感。宋代的王十朋接过这个话题,对白居易和苏东坡有这样的议论:“文章均得江山助,但觉前贤畏后贤。”(《游东坡十一绝》之二)陆游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又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城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其二)这意思杨万里也说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其二)宋周辉的笔记《清波杂志》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易安就是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她到雪中寻诗,也是想求得江山之助吧?清黄宗羲有一段话值得深思:“古人不言诗而有诗,今人多言诗而无诗。其何故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于景,其次求之于古,又其次求之于好尚。”(《金介山诗序》)求之于景,就是求之于江山之助,这是最好的途径;求之于古難免因袭而缺少创新;至于求之于好尚,赶时髦,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书画家也有讲江山之助的。宋董更《书录》记载了黄庭坚的一段话:“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字,似得江山之助。”宋朝的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画家在观赏山水时,要“以林泉之心临之”,“身即山川而取之”,这样画出来的山水画才能把人带到仿佛真实的山水之中。江山之助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江山可以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可以开阔诗人和画家的心胸,激发他们的灵感,培育他们的激情,吕本中所谓:“古人观名山大川,以广其志思而成其德”(见周辉《清波杂志》),就是这个意思。从江山之助我又想起人与大自然的交融合一,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如果能达到这种合一,就有可能进入化境了。明苏伯衡说:“与造物者游,得于心,形于言,灿然在纸而成章,则谓之文;得于心,形于手,灿然在纸而成象,则谓之画。”(《赠金玉贤序》)所谓“与造物者游”包含与大自然合一的愿望。明沈颢在《画麈》中说:“山于春如庆,于夏如竞,于秋如病,于冬如定。”不仅说出了山在四季的不同神态,而且也说出了他自己在看山之际,心与山相交融所得到的不同感受。
江山之助,又何限于文艺创作呢?江山也有助于启迪人的智慧,荡涤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帮助人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真无法想象,离开了江山之助,人的生活将多么贫乏,人的想象力将多么枯涩!
「散记一篇」
读帖
小时候长辈命我临帖,也曾敷衍过一阵子,既是敷衍,当然尝不到什么乐趣,也就没有什么长进。长辈见我不堪造就,便放松了督责,我索性不再临习了。现在想起来颇有点后悔。
然而,毕竟算是摸过帖的人,临不好,读还是乐意的,这读帖的乐趣一直维持到现在。每逢空闲或虽忙而欲“偷闲”的时候,便随意取些帖来,或坐或卧,任意翻阅。《平复》就《平复》,《兰亭》就《兰亭》;《祭侄稿》也行,《寒食诗》也行,拿到什么是什么。有时连文章一起欣赏,王羲之帖中的伤时之情,颜真卿帖中的浩然之气,孙过庭《书谱》的高论,米芾《虹县诗》的遣词,都令我赞叹。有时只看书法,而不顾文章如何。就一个字而言,其提顿转折、间架结构,或严整,或奇险,或潇洒,或庄重,很值得揣摩。就一行字而言,其字距之疏与密,气势之畅与涩,大有可以玩味的地方。就一幅字而言,其布局的巧妙,那种类似音乐旋律的意味,那种徐疾浓淡所形成的节奏感,更是常读常新。有时读到会心处,情不自禁学着用手比划几下,即所谓“书空”。有时并不比划,只是呆呆地读,一边读一边猜测前贤的模样和秉性:王右军也许很瘦,既然“频有哀祸”,又“哀毒益深”,焉得不瘦呢;苏东坡字肥,人大概也胖胖的;张长史嘛,写狂草的人,恐怕有点邋遢;黄山谷呢,笔法开张,为人大概相当豁达。就这样,与千载之上的古人交友,真是无穷的乐趣。
我还有一种习惯,一边读帖一边听音乐,多半是欧洲的古典音乐。眼前是二王,颜柳,苏黄米蔡,耳边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书法与音乐,中国和欧洲,颇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驚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曲终以后,慢慢合上帖,环顾四周,自己多年购置的书籍不太整齐地插在书橱里,心中很充实也很轻松。我不练气功,这就是我的气功。试想,“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这不是气功的境界,又是什么呢?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