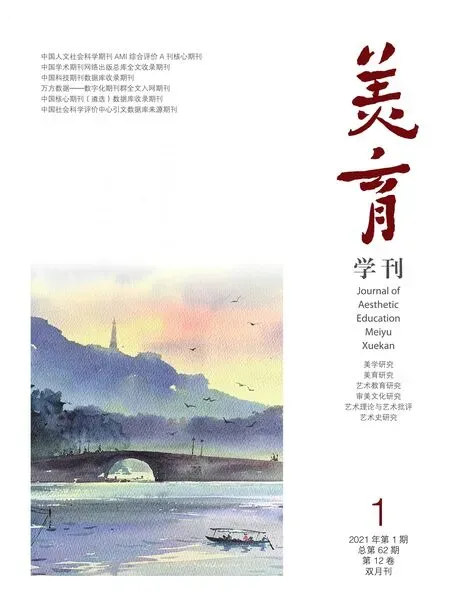魏晋自然审美之竹篇
薛富兴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3)
一、竹审美之前奏
中国竹林面积占世界竹林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利用竹资源历史最悠久的国家。[1]竹很早就被国人认识和喜爱:“竹,冬生草也。”[2]《诗经》提及竹者凡五篇,有径以竹为题者,如其中之《竹竿》,然最著名者当属此篇: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3]
该篇可视为中华竹审美史的开篇之作,体现了先秦时代中华竹审美的最高水平,并大致规范了后世中华竹审美之基本路径。这篇本以“君子”为主题的作品却以竹起兴,且如此者再三,便使竹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本篇诗人用以发兴的写竹之句“绿竹猗猗”“绿竹青青”和“绿竹如箦”本身即可独立,成为一篇关于竹审美的作品,且画意盎然:淇水岸边竹林一片,近察者见其形态,每一棵竹均修长婀娜,如美少女,曰“猗猗”;远观者则见其色,总曰绿,又曰“青青”,再曰“如箦”。盖竹林之色自观者言有浅淡之分,浅者谓绿,深者谓青,最浓郁者则曰“如箦”。“箦”者,积也,言竹林中色彩最为深厚浓烈的部分,如后世之重彩积墨画,似经反复涂抹。此幅竹林图有形有色,有浅有深,有远有近,可谓察之精,写之备。
然而这只是对竹的外在欣赏,一种形式美观照。对作者而言,写竹之言无论再精妙,也不过“兴”而已,“兴者起也,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4]。换言之,“君子”才是本篇主角,竹仅其衬托,君子之隐喻也。因此,本篇的一个重大历史信息是:本篇在欣赏竹的形式美的同时,也开辟了对竹进行“以物比德”“托物言情”式审美欣赏的案例,它根本地规定了国人竹审美的思维路线,特别是对竹进行有深度、有内涵的欣赏。
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来风。[5]
“便娟”者,“猗猗”也。显然,《楚辞》与《诗经》中的竹子拥有同一种美——婀娜旖旎的阴柔之美,《楚辞》进一步强化了《诗经》所塑造的竹形象。两汉是一个以赋称盛的时代,竹子这种世界上长得最高的草,已被“三百篇”吟咏再三的美妙植物,当然不会为辞赋家所遗忘。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华长竿纷实翼。杳筱丛生于水泽,疾风时,纷纷萧飒,削为扇,翣成器,美托御君王。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避暑致清凉。安体定神过消息,百王传之赖功力,寿考康宁累万亿。[6]
本篇所赋者为杖,乃工艺品,本不属自然审美范围,然杖之材为竹,此杖之所以受到辞赋家特别关注,首先因其材,故我们这里先将其视为竹赋,然后再视为竹杖赋。请注意,与《诗经》和《楚辞》不同,本篇作者发现了竹的另一种形象——“兆直”,可谓对中华古代竹审美之新贡献,竹之美的另一副面相。这为后人欣赏竹开拓了新思路,留下新空间。
二、竹审美之四路径
先秦两汉乃中华竹审美之奠基期,魏晋则是拓展期。本时期,欣赏竹成为一种普遍时尚,人们欣赏竹的审美趣味日益细腻、丰富,这使中华竹审美进入一个精致化时代。首先,这是一个追捧竹的时代:
王子猷尝暂居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曰:“暂住何烦耳?”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7]838
本时期人们对竹的普遍喜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以辞赋为例,本时期赋植物者大致有三类:树木、花卉、果蔬,花卉乃辞赋家植物审美之大宗,其花卉类辞赋凡77篇,涉及花卉品种有29种之众。以竹为主题者9篇,其中魏收的《庭竹赋》失文,王鉴的《竹簟赋》现仅存句。本时期还出现了关于竹的谱谍类专书,题为晋戴凯之撰的《竹谱》一卷,记载竹类有70余种,这是本时期竹审美充分自觉,人们对竹的认知专门、深入与系统化的标志。下面我们对本时期以竹为主题的辞赋作品略作分析,以见其竹审美发展的基本情形。

江淹此赋可理解为一幅《竹林图》。作者可谓善状竹形竹态。“绿筠绕岫,翠篁绵岭。参差黛色,陆离绀影”,此竹林之碧色浓郁也。“上谧谧而留闲,下微微而停靖。蒙朱霞之丹气,暧白日之素景”,此竹林之光影也,疏密相间;又曰其“非英非蕊,非香非馥,而珍跨仙草,宝愈灵木”。既可蔽日,又可留风,风动摇曳,百媚生焉。可见,它一方面继承了《诗经》和《楚辞》开辟的竹审美成果,另一方面,它又将这种关于竹的形式美趣味大大地细腻化、丰富化,故而能给人一种对竹之形象驻足流连,细加品味的审美启迪。概言之,本赋代表了本时期竹审美的第一条路径——对竹进行客观、外在的形式美欣赏路径。
灵丘深沈,蔓竹凝阴,神根合拱,桢干百寻。振芳条乎昆岳,敷绿采于高岑。沿淮海而蔚映,带沮漳而萧森。志东南而擅美,在淇卫而流音。方灵寿而均茂,仪菌桂而成林。若乃青春受谢,九野舒荣,绿蘋齐叶,白芷抽萌,干葱葱而特秀,筱擢颖而垂英。霜皦镜于原隰,木衰疏于郊阡。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9]
与前赋相比,此赋对竹的欣赏更为完善,可谓能“上下察也”。首先,作者同时发现了竹根自由地穿梭于地下,其主干却又能直刺云霄的特性。它的分布如此之广,既显身于崇山峻岭,也招摇于平原大川。既受宠于东南,亦传颂于中原。论其寿有千年之竹林,论其生长之速,则迅如菌。它可与夏卉争艳,亦可伴松柏越冬,成竹林影雪之景。如此便将时人为何特别地钟情于竹揭示得较为充分。
有嘉生之美竹,挺纯姿于自然。含虚中以象道,体圆质以仪天。托宗爽垲,列族圃田。缘崇岭带回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凌惊风茂寒乡,藉坚冰负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润本,承清露以擢茎。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10]
江逌此赋可谓将中华竹审美带入一个新阶段,因为它体现出时人对竹性的新认识。首先,竹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植物,无论燥湿,无论山地和平原,人们均可看到竹的身影;其次,虽然竹总体而言喜湿热之地,然它对寒冷气象亦有耐受力,故而人们无论冬夏均可赏其美姿;此外,竹不仅借雨露生长,自身亦可涵液以自存,故而总给以人一种润泽之感。此均言竹之性也。欣赏者既可以竹遮阴,亦可以竹招风:“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此则言竹之功也,即竹对人类物种之诸多功用。概言之,此赋代表了时人竹审美的另一个向度——对竹之生物习性如地理分布,对寒暑气候的适应性、含水性的深入了解,以及对竹功——竹对人类物质利用价值的深入了解。它代表了本时期人们竹审美的第二条路径——客观外向,然又深入地对竹进行审美欣赏的路径。竹性与竹功为核心内涵的竹审美之路是对上述第一条路径——客观外在的形式美欣赏之路的拓展与深化。
然而,本赋对竹的审美欣赏可谓视野复杂,甚至相互矛盾。它开篇即言竹“含虚中以象道,体圆质以仪天”,这是一种在思维方向上与以竹性、竹功为核心内涵的客观外向,然又与深入的竹审美截然相反的审美路径,它忠实地继承了《诗经》所开拓的主观内向式竹审美之路——以竹比德式的审美欣赏。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对竹的自然人化,对自然审美对象的文化化。它先将特定时代、群体审美欣赏者所特别喜爱的某种人文价值观念,比如忠贞、正直、谦逊等附会于竹,然后再以此理由去赞美竹,虽然事实上竹作为一种自然对象根本不可能具备此种人文价值观念。但是,这样的客观事实并不能阻止人们以竹比德实即以德附竹的文化冲动,而且此种主观化,违背竹之自然事实的冲动,却促进了时人对竹的审美欣赏,因为这也许正是时人喜爱竹、不厌其烦地赞美竹的核心理由。究其实,这种以竹比德,或曰以人拟竹、以人德为竹性的思路始于先秦而继承于汉:
礼……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11]
南中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汉章帝三年,子母竹笋生白虎殿前,谓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颂。[12]4272
严格来说,这种主观地对待、观照自然的审美态度并非一种恰当的自然审美方式,却是魏晋人士竹审美之普遍审美倾向。再如:
瞻彼中唐,绿竹猗猗。贞而不介,弱而不亏。[13]
嘉兹奇竹,质劲体直。立比高节,示世矜式。[14]
此乃反映在物赋系列中,以“赞”和“铭”的形式以竹比德之例。
竹生空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耻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15]
此则诗人在韵文中对辞赋家们以竹比德之习的回应,这足以说明:以竹比德式的主观内在欣赏路径实乃本时期人们竹审美之主流方式。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的人们均可喜竹,前者从竹子外在的身材高挑、修长而有节现象中发现其具“兆直”或曰“贞”之德;后者则据竹茎内腔中空之事实认为竹具“虚中”之智。于是,在以物比德思维惯性影响下,竹似已不再是一种普通植物,而成为儒道两家心目中君子——理想人格的象征,因为据说它同时拥有两种难能之美德,一曰坚贞有节,二曰虚空守雌。正因如此,竹便成了这一时期君子集团的处身标配,哪里有高人韵士哪里便有竹;反过来,正人君子们似乎也只愿呆在有竹之地,否则何以彰显其不凡风韵呢?
乐成县民张荐者,隐居颐志,不应辟命。家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屋,恒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荐逃避竹中,不与相见,一郡号为高士。[12]4274
本时期人们的竹审美不仅忠实继承了始于先秦的比德式思维,还将其系统化,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有机性的比德语言: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16]
绿竹影参差,葳蕤带曲池。逄秋叶不落,经寒色讵移。来风韵晚径,集凤动春枝。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17]
在此,比德式竹审美欣赏已然形成一个有机性符号系统,既有高蹈客,亦有传说中的仙鸟——凤凰,当然还有竹。于是理想、完善的竹意象系统形成一个由植物、动物与人构成的三位一体循环互涉系统,这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形象隐喻系统,只要提到其中任何一个,另外两项便会不期然而然地出现在竹欣赏者们的审美潜意识中,且其人文内涵高度稳定。它们均指向一种理想化人格,乃此人格的典型化感性显现。当然,这种以竹比德式的有机性审美符号系统之有效建立是有前提的。首先是人们对竹形竹性的一定了解:
箭竹高者一丈,节间三尺,坚劲中为矢。[12]4273
桃枝(竹,引者注)四寸有节。[12]4273
其次,且更为重要者,乃前代累积的关于竹的神话性传说。
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18]
《韩诗外传》曰:
黄帝时凤凰栖帝梧桐,食帝竹实。[19]
这种传说如此广泛、持久,乃至成为时人对竹的一种信仰:
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凤皇,至是,终为坚贼,入止阿房城焉。[20]
这便是本时期人们以竹比德式竹审美的坚实文化心理基础。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7]800-801
据此,“竹林”已成为魏晋风度的一种必要象征,它隐喻着一种高尚人格、自由的精神状态,庄子逍遥游理念之恰当语境,甚至成为时人精神家园之标志。
以竹比德乃本时期人们竹审美欣赏的第三条路径,亦其主流。它是对先秦时代比类思维传统与以物喻德伦理意识的忠实继承与拓展,奠基了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人对待自然对象的典型态度,自然审美欣赏的主导性审美方式,是中华古代自然审美之大传统。当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传统?始于先秦的中华竹审美中的比德化,或曰人格化现象,已有学者关注,并将这种对“自然物种的人格化”视为环境史上,至少是中国环境史上的一种自然现象。[21]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传统放在当下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理念的环境美学和环境伦理学视野下考察,却暴露出它的严重问题。比德思维的背后乃是主观地对待自然的哲学态度、立场,这种对竹的深度人化,即以人类社会自身所珍视的人文价值观念附会与濡染自然对象的对自然之文化化,将导致两种后果:其一,它不利于培育人们对自然对象进行独立性欣赏,即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特性与价值;其二,它不利于培育人们尊重自然、客观地对待自然的伦理态度。以竹比德式自然审美构成一种悖论:一方面它是人们喜爱、赞美与欣赏竹的强有力证明;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所赞美的有关竹之诸美德并非竹所实有,故而其对竹之称颂可谓言不及义,名不符实,此类欣赏本质上与竹自身无关,而是人类以赏竹为名的自我称颂,在此意义上竹审美可谓有名无实。
以竹言情乃本时期主观内在式竹审美的第四条路径。
风云能变色,松竹且悲吟。[23]
夹池一丛竹,垂翠不惊寒。叶酝宜城酒,皮裁薛县冠。湘川染别泪,衡岭拂仙坛。欲见凌冬质,当为雪中看。[24]
在本时期的抒情诗中,诗人们通过竹意象主要表达两种消极情感,一曰孤独,二曰悲伤,尤以后者为甚。后者有极为久远的动人传说,那便是“斑竹”或曰“湘妃竹”: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挥竹,竹尽斑,今下隽有斑皮竹。[25]
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其文悉斑。[12]4272
自此,竹便与人类的情感世界高度关联,竹与人心又成为一有机性互涉符号系统。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26]
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27]
以竹言孤或以竹言悲成为中国古代抒情诗中又一程式化表达方式。当你孤独或悲伤难耐而又无由表达时,至少可以想到竹,尤其是斑竹。
在以比德为基础的竹审美史上,竹的人格化形象概由两类构成:一曰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男性意象,为内刚外逸人格之隐喻;二曰以“湘妃”为代表的女性意象,乃以相思、孤独为底色的悲剧命运之最佳符号。也许正因如此,曹雪芹才为终日以泪洗面的林黛玉设置了潇湘馆的场景,在曹雪芹看来,大概非竹不足以显悲,不足以彰黛玉之阴柔。
以比德思维为基础的主观化竹审美欣赏一路,其对竹的人格化形成两种审美风格,一曰以“娟”为标识的优美,一曰以“贞”或“节”为代表的壮美。在本时期竹赋的收尾之作中,隋人萧大圆成功地将上述关于竹的两种人格形象、两种审美风格综合起来,融在一幅关于竹审美的景观中,足为本时期竹审美作一种概观。
简言之,魏晋时期竹审美可总结为两个方向,四条路径。两个方向谓客观式欣赏与主观式欣赏。具体地,客观式欣赏包括了如下两条路径:一曰对竹形竹态的外在式形式美欣赏,二曰以竹性和竹功为核心的内在式深度欣赏。主观式欣赏也包括两条路径:一曰以竹比德,二曰以竹言情,其人化自然的内涵具有浑厚的人类中心主义之迹。就当时情形及后来发展趋势看,外在式形式美欣赏与内在式以竹比德、以竹言情三条路径成为中华古代竹审美的主导路径,客观地以竹性、竹功为核心的内在深度欣赏一路则始终未能发扬光大,成为竹审美传统最薄弱的部分。若立足当代环境美学视野则会意识到,其实,最为薄弱的客观而又内在的深度欣赏之路才代表了客观地对待自然、真诚地尊重自然,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实有的正确路线,因为唯此路线才足以确立自然审美欣赏的独立性,使自然审美欣赏实至名归。
三、审美之拓展
作为本时期自然审美之代表性成果,竹审美不仅自身实现了精致化,它同时还获得重要的拓展性成就,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在自然审美领域内,作为本时期人们植物审美系列中之最爱,竹审美与其他同类自然对象审美结为联盟,形成一个具有突出审美优势的特殊植物族群,在古代自然审美与自然艺术史上同时具有显著影响。比如,其时人们已将竹与松、柏、兰等并列:
猗与松竹,独蔚山皋。肃肃修竿,森森长条。[29]
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30]
峭茜青葱间,竹柏得其真。[31]
有趣的是,梅与兰此时亦已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

爰有奇特之草,产于空崖之地。仰鸟路而裁通,视行踪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岂众情之服媚。宁纫结之可求,垂延伫之能洎。稟造化之均育,与卉木而齐致。入坦道而销声,屏山幽而静异。独见识于台,窃逢知于绮季。[33]
据此,则无论是后世所称的“四君子”还是“岁寒三友”,在本时期均已聚齐。一定意义上说,魏晋实乃中华古典树木花卉审美趣味之拓展期,本时期所形成的审美倾向对后世同类题材的自然审美有着持久、稳定的影响。当然,松竹并列之习实始于先秦: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34]
松、竹、梅“岁寒三友”的组合形成于宋元时期,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组合则更晚,形成于明代。然而这些要素在魏晋时已聚齐,故可认为上述组合奠基于魏晋。如何认识在中国古代自然审美史与自然艺术史上具有广泛、持久影响的“四君子”和“岁寒三友”组合的审美与文化意义?从审美上说,一种针对特定自然对象的审美偏好一旦形成,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它均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会形成一种小的审美传统。萌芽于先秦,奠基于魏晋,持续至明清的这种发生于植物审美欣赏领域的持久偏好,正是自然审美趣味转化为自然审美传统的极好证明。此传统如何发生、持续?在自然审美领域内我们恐难获得强有力的阐释,只有当我们将它置于更广泛的古典文化传统,联想到发生于先秦时代的强大类比思维惯性及具体表现形式,早期伦理意识之表达——以物比德的伦理习惯时,这种表现于自然审美领域的特殊爱好——对松、竹、梅、兰的广泛、持久偏爱才能得到更合理解释。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于自然审美领域的这种对“三友”与“四君子”的偏爱,其背后有两个更为强有力的支撑:一是类比思维,二是伦理比德意识,前者为思维形式,后者为伦理意识,此二者结合起来,渗入于自然审美,便塑造出如此自然审美偏好。这说明,审美趣味、审美传统不足以自立,它们会受到其背后更为广泛、深厚的文化传统,包括思维习惯与伦理意识的强有力的影响。
现在再回到自然审美本身,当如何评价这种组合?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松、竹、梅,或梅、兰、竹、菊之所以被组合在一起,无论是审美趣味,还是这些植物自身的生物习性,都不是让它们走在一起的最强有力的理由,这种理由发生在审美之外,自然物性之外,即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类比思维习惯与伦理比德意识。比德现象首先分别地发生于上述四种自然对象自身,发生于对这些单个对象的比德式自然人化或人格化、文化化之中,然后又以同样的理由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使之成为自然审美、植物审美中之“尤物”集团。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将“三友”或“四君子”理解为以竹比德的放大或加强,它们使类比思维传统及以物比德伦理意识在自然审美领域中得到更有力的实现。然而,我们对以竹比德式自然审美欣赏所提出的问题,同样适合于“三友”与“四君子”:这些德性真的属于这些自然对象本身吗?非也,它们是人类欣赏者对自然对象之附会,最多只是一种隐喻,而非自然事实。因此,当我们赞美这些美德时是真的在赞美自然对象吗,亦非也。既如此,我们正在欣赏与赞美的到底是自然对象本身,还是那些人文价值观念?肯定是后者而非前者。我们不得不得出如此结论:尽管“三友”和“四君子”乃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与自然艺术中的强大传统,然而它们并不足以成为恰当的自然审美之典范,而是其反面,因为它们只能让我们离自然对象自身之事实尤其是其生物特性越来越远,如此自然审美只能名不副实。
万千植物对象中,我们若将自己对自然的热爱与赞美始终仅奉献于“三友”与“四君子”,其后果又将如何?我们的自然审美趣味与视野只会越来越狭隘,这种狭隘的审美趣味与视野最终甚至会在无意识中转化为对自然的伦理歧视与傲慢:虽然世上有万千物种,然而值得我们人类物种关注与称颂的甚寥,唯“三友”与“四君子”而已。既如此,我们真的热爱和尊重自然吗?非也,因为其绝大部分对象并不能得到人类的审美垂青。人类若真诚地热爱与尊重自然,应当对万千自然对象给予大致同等的审美关注,应当对它们本质上一视同仁,而不是仅喜欢其中之极小部分,忽视其中之绝大部分,有时甚至会厌恶其中之又一小部分。理想言之,人类应当对自然给予本质上同等的无检择、全范围的审美关注。
魏晋时期竹审美的第二项拓展性成果乃时人的竹审美已然走出自然审美,成功地将它转化为一种艺术趣味,转化为自然艺术,竹已成为本时期绘画中花鸟画科的重要题材之一:
“陈王欢旧,小堂伫轴”,此似可证明其时已有绘竹之习。据说,顾景秀曾绘有《树杂相竹样》,正可佐证。[36]后世的材料证明:竹乃中国古代花鸟画科之大宗,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画谱,比如元人李衎撰《竹谱》十卷便是绘竹之谱,而非育竹之谱。作为自然审美的竹审美首先进入文学领域,从《诗经》到《楚辞》,再到两汉魏晋的辞赋;在本时期,它又进入美术领域,成为花鸟画科中的重要、持久题材。这足以说明国人对竹的喜爱程度,同时也是自然审美对艺术审美前提性影响的重要证明,因为我们不能想象相反的情形:在自然审美领域中,竹并非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却又成为艺术领域的普遍性题材。需要补充的是,本时期乃至后世竹审美的趣味与思维方式在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文学与美术)两大领域高度趋同:外在的欣赏表现为对竹的形式美观照;内在的欣赏则表现为以竹比德与以竹言情。换言之,以竹比德与以竹言情不仅是本时期自然审美中的主导趣味和方式,也是本时期以竹为题材的诗文和绘画的主导趣味和方式。
最后,本时期竹审美的第三项拓展性成果乃竹审美趣味从自然审美向音乐艺术的渗透,一项重要证明便是“丝竹”概念的流行。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37]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31]
竹与音乐之缘可谓尚矣: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明,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风皇之鸣,以别十二律。[38]
据此则竹材很早就被用来制作定律之管,以确定诸乐器的标准音高,对“十二律”的确立作出奠基性贡献。也许正因如此,后世才有了关于竹乐的神话传说:
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乃树之竹,是曰竹林。[39]
概言之,竹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影响盖有三:其一,它是定音之基,中国古代“十二律”乐律体系的出发点;二是以之为材,构成古代管乐的一部分;其三,音乐虽然本质上乃人类文化成果,然而在道家尚自然观念影响下,以竹为材的管乐成为作为人类观念文化成果的音乐中最能体现自然属性与风格的典范,最近于天籁者。
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40]
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沈。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41]
竹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因形而下因素,比如以竹管定基础音,以及以竹为管乐之材,更因一种特殊的形而上观念——崇尚自然。正因如此,竹或丝竹便成为一个关于音乐的特殊文化寓言,它体现了道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音乐的特殊困境、趣味与智慧。一方面,丝竹及其所代言的乐乃人类重要的观念文化成果,儒家甚至要以乐成礼、以乐育德,此乃乐之重要文化属性与功能;然而另一方面,在道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传统中又存在一种对音乐人文属性及其功能的深刻质疑,实际上是对丝竹背后的音乐,乃至音乐背后的人类文化本身的质疑:也许,它们会让人类离自身的天然本性、本然状态越来越远。如果说音乐已然不可彻底放弃,音乐中的人类文化之迹——造作与造作之技无法彻底逃避,那么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在人类文化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引入自然因素,以便对人类文化所固有的缺陷有所反思,有所制约?或者说,能否最低程度地依赖人类文化因素,以便为保留自然智慧留下余地?让我们在陶醉自身文化成就的同时亦不忘怀天地自然。于是,发生于魏晋时代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音乐观念便成为道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式独特音乐趣味、音乐智慧的典型表达,而其时士人间所流传的啸咏之尚正是此观念的绝妙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