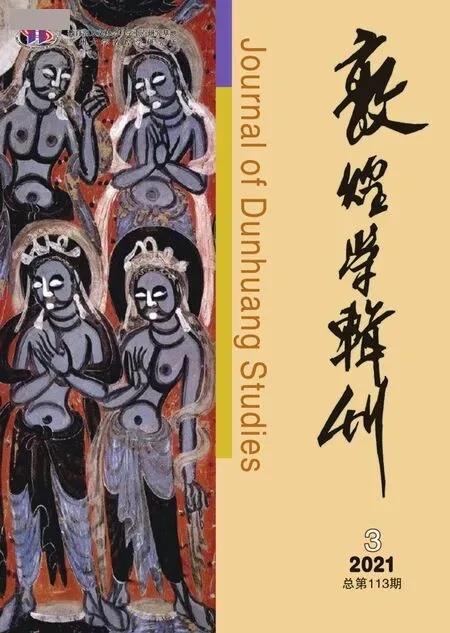武周时代的类书编纂者群体及其影响
——以“珠英学士”为中心
刘全波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唐代是类书编纂、发展的高潮期,虽然多数典籍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唐代的类书编纂却是异常繁荣的。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言:“唐代自开国到玄宗时代,除了中宗、睿宗两个很短的朝代外,累朝都用封建国家的力量编纂了一些大规模的类书。”(1)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新1版,第102页。贾晋华《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言:“从隋炀帝至至唐玄宗开元中,官修类书大量涌现,皇帝、太子、诸王都争先恐后地组织第一流的学者文士编纂类书。”(2)贾晋华《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第127-132页。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亦言:“在初唐时期,知识的合理化组织与分门别类曾风行一时……他还体现在初唐时期编纂的各式各样的‘百科全书’中,这些书籍在720年的秘书省藏书目录中被归为‘类事’,即‘分类事项’。”(3)[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3-74页。诚然,唐初编纂了多部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瑶山玉彩》《累璧》《东殿新书》《策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三教珠英》等。其中,《三教珠英》是有唐一代编纂的卷帙最大的类书,达1300卷,此后几百年也无人能出其右。(4)桂罗敏《〈三教珠英〉考辨》,《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6期,第75-78、52页。桂罗敏认为,作为中国唯一女皇的武则天,之所以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实是她的王朝全面地实现了文治武功。在文治方面,图书典籍的修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而在图书典籍的修撰中,最为出色的是大型类书一千三百卷《三教珠英》的编纂。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总第17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第114-130页。王兰兰亦言,在其(武则天)称帝后期,征天下文士修《三教珠英》,为其时文苑一大盛事。但是,由于《三教珠英》是张昌宗等人领衔,且是在剿袭《文思博要》的基础上成书,故一直不被重视,甚至有些被人看不起,其实,这严重低估了《三教珠英》及其影响,笔者计划在诸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做考索,以加深对《三教珠英》编纂者群体的认知。
一、《三教珠英》的编纂者
《旧唐书》卷47《经籍下》子部“事类”载:“《三教珠英》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张昌宗等撰。”(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7《经籍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46页。《新唐书》卷59《艺文三》子部“类书类”载:“《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张昌宗、李峤、崔湜、阎朝隐、徐彦伯、张说、沈佺期、宋之问、富嘉谟、乔侃、员半千、薛曜等撰。”(6)[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59《艺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63页。此处的“乔侃”当是“乔备”。《珠英学士集(P.3771)》所载亦是“乔备”,《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乔知之传》亦言“乔备”预修《三教珠英》,故“乔侃”当是“乔备”。可见,《旧唐书》对于《三教珠英》编纂者的记载是比较简单的,《新唐书》所记载的作者信息较多,有张昌宗、李峤等12人。
《旧唐书》卷78《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载:“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司仆卿,封邺国公,易之为麟台监,封恒国公,各实封三百户。”(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8《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第2707页。《新唐书》卷104《张行成族子易之昌宗》载:“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8)[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04《张行成族子易之昌宗》,第4014-4015页。《资治通鉴》卷206载:“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9)[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6“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44页,第6546页。两《唐书》皆提及张昌宗、李峤、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富嘉谟,一次提及阎朝隐、崔湜。正史的记载,是我们认知《三教珠英》编纂的基础,甚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在《三教珠英》的编纂之中,上述诸人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资治通鉴》的记载,增加了张易之,且是其他典籍所没有记载的。再一个需要说明的是,三书皆言“二张”“丑声闻于外”,武则天“欲以美事掩其迹”,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不能过分解读,修书之事,与其说是给“二张”美化,不如说是为武则天张目,因为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武则天。(10)刘全波《唐代类书编纂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112页。
《唐会要》卷36《修撰》载:“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哲、富嘉谟、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11)[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6《修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57页。《唐会要》言修《三教珠英》者有“高备”,而王兰兰考证“高备”当是“乔备”。常元旦,无传记资料,新唐书载有“韦元旦”,王兰兰考证此“常元旦”当是“韦元旦”。徐俊认为“乔侃”当是“乔备”,王兰兰认为二人的可能性亦是有的,笔者认为当从本传与《珠英学士集》记载,即只有“乔备”一人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唐会要》对于《三教珠英》编纂者的记载最为详细,其将张昌宗、李峤等26人姓名记载了下来,是我们了解《三教珠英》编纂者最重要的资料。
《太平御览》卷601《文部十七·著书上》载:“又曰天后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备,令麟台监张昌宗与麟台少监李峤,广召文学之士,给事中徐彦伯、水部郎中员半千等二十六人,増损《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于旧书外更加佛教道流及亲属姓氏方域等部,至是毕功,上亲制名曰《三教珠英》,彦伯已下,改官加级赐物。”(12)[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601《文部十七著书上》,《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98册,第530页。《册府元龟》卷607《学校部·撰集》载:“张昌宗为麟台监。圣历中,则天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多未周备,令昌宗与麟台少监李峤,广召文学之士。给事中徐彦伯、水部郎中员半千等二十六人,增损《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于旧书外更加佛教、道教及亲属、姓氏、方域等部,至是毕功,帝亲制名曰《三教珠英》。时左补阙崔湜同修。”(13)[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607《学校部·撰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000页。《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的记载,皆突出了“员半千”,是其他材料所没有的。《册府元龟》的记载还补充了一个重要信息,“时左补阙崔湜同修”,与下文敦煌本《珠英学士集》所载“左补阙清河崔湜”相合,可互证。再者,上述文献多言《三教珠英》编纂者共“二十六人”,其实这应是某一个时期的人数统计,而在真实的修书过程中,会不断的有人加入或退出。
《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传》载:“武后修《三教珠英》书,以李峤、张昌宗为使,取文学士缀集,于是适与王无竞、尹元凯、富嘉谟、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刘允济在选。书成,迁户部员外郎,俄兼修书学士。景龙初,又擢修文馆学士。”(1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传》,第5747页。《新唐书·李适传》提供了不少重要信息,上述诸文献皆未曾记载刘允济参与编纂《三教珠英》之事,故我们可以据此增加一人。
《玉海》卷54载:“无乔侃。《刘禹锡集》云:《珠英》卷后列学士姓名,蒋凤白衣在选。一本吴少微亦预修。”(15)[宋]王应麟撰《玉海》卷5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1029页。《玉海》载事载人,多驳杂,其引用《唐会要》时,小字部分留下了上述文字,乔侃没有参与《三教珠英》的编纂,当是其弟乔备,蒋凤则是白衣入选,而根据此处的记载可知,吴少微应该也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
《新唐书》卷60《艺文四》载:“《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1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60《艺文四》,第1623页。《郡斋读书志》卷20《总集类》载:“《珠英学士集》五卷。右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17)[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20《总集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59页。《文献通考》卷248载:“《珠英学士集》五卷。晁氏曰: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敎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1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8《经籍考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4页。《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皆言,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看来,武三思亦是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领导班子。此外,《珠英学士集》的作者崔融应该也是编纂《三教珠英》的参与者之一。
S.2717《珠英集卷四、卷五》
阙名(李羲仲)(19)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第87-90页。
通事舍人吴兴沈佺期
前通事舍人李适
左补阙清河崔湜
右补阙彭城刘知几(20)余欣《敦煌本〈珠英集〉残卷所见刘知几佚诗三首笺证》,《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94-104页。
右台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琅琊王无竞
卷五
太子文学扶风马吉甫
P.3771《珠英集卷五》
阙名
蒲州安邑县令宋国乔备
太子文学河南元希声
司礼寺博士清河房元阳
洛阳县尉弘农杨齐哲
恭陵丞安定胡皓(21)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48-587页。
《珠英学士集》是唐人编选的时代较早的唐诗选本,敦煌文书中今存残卷二卷(P.3771、S.2717)。崔融《珠英学士集》在701-706年之间的任何时段成书,皆有可能。笔者认为,长安二年(702)成书的可能性更大。其一,长安元年(701)十一月,《三教珠英》编纂完成。其二,由“左补阙清河崔湜” “时左补阙崔湜同修”可知,崔湜的官职,就是修书时或修书刚刚结束时的官职。其三,长安三年正月一日(703),武三思、李峤、朱敬则、徐彦伯、魏知古、崔融、徐坚、刘知几、吴兢等人,又开始了新的撰修工作,即奉武则天敕令编修《唐史》。《唐会要》卷63《史馆上》载:“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22)[唐]王溥《唐会要》卷63《史馆上》,第1094页。一个任务的完成与一个新任务的开启,更应该是次第关系,而不应该是并列关系。

出处参修者人数《旧唐书·经籍下》张昌宗1《新唐书·艺文三》张昌宗、李峤、崔湜、阎朝隐、徐彦伯、张说、沈佺期、宋之问、富嘉谟、乔备、员半千、薛曜12《旧唐书·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张昌宗、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8《新唐书·张行成族子易之昌宗》张昌宗、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6《资治通鉴》张易之、张昌宗、李峤3《唐会要》张昌宗、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乔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韦元旦、杨齐哲、富嘉谟、蒋凤26《太平御览》张昌宗、李峤、徐彦伯、员半千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的《三教珠英》的编纂者,有张昌宗、李峤、徐彦伯、魏知古、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刘允济、王无竞、韦元旦、尹元凯、李适、富嘉谟、员半千、王适、张说、徐坚、刘知几、崔湜、薛曜、乔备、元希声、马吉甫、杨齐哲、胡皓、于季子、李处正、房元阳、蒋凤、吴少微、崔融、武三思、张易之。王素先生认为李羲仲也曾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23)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第87-90页。故目前所能知道的《三教珠英》的编纂者,共计34人。王兰兰认为苏味道、李迥秀、王绍宗、吉顼、田归道、薛稷、房融、崔神庆、杜审言亦有可能参与《三教珠英》的编纂,原因是他们与二张之关系密切,我们暂且持怀疑态度。(24)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第114-130页。
二、“珠英学士”群体及其政治倾向
(一)李峤、徐彦伯、崔融、魏知古
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人并称为“文章四友”,是活跃于初唐后期诗坛的重要文学群体。胡旭、林静《“文章四友”及其政治、文学考论》言:“形成于武周天授元年九月到天授三年正月……主要凭借文学才华,在武周时期仕途大盛,忠于武则天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之事,并因之而与‘二张’、武三思等过从甚密,他们的政治倾向事实上已经背离了李唐政权。”(25)胡旭、林静《“文章四友”及其政治、文学考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5期,第54-64页。其言:“ ‘文章四友’很大程度上属于御用文人,在庙堂文学的创作方面颇有成就,他们主导的宫廷诗风,对近体诗格律的最终形成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李峤、杜审言在这方面的实际作用,甚至超过‘沈宋’。”
《旧唐书》卷94《李峤传》载:“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有文集五十卷。”(2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4《李峤传》,第2993-2995页。《新唐书》卷123《李峤传》载:“十五通《五经》,薛元超称之。二十擢进士第,始调安定尉。举制策甲科,迁长安。时畿尉名文章者,骆宾王、刘光业,峤最少,与等夷……武后时,汜水获瑞石,峤为御史,上《皇符》一篇,为世讥薄。然其仕前与王勃、杨盈川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而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27)[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23《李峤传》,第4367-4371页。从唐高宗时期直至武则天时代,李峤皆有功业,在武则天时代位列宰相,唐中宗时代更是朝廷之谋主,总之,李峤在武则天时代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而此李峤参与到《三教珠英》的编纂中,必然是此编纂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张”之外,李峤应该是最重要的存在,其一李峤的地位高,其二李峤是文章宿老。李峤修《三教珠英》时的年龄,我们以公元700年为基点,(28)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第114-130页。王兰兰认为《三教珠英》的始撰时间是圣历三年(700)改元久视前,撰成时间是长安元年(701)十一月。判断诸编纂者之年龄,李峤的生卒年是645与714年,(29)马茂元《李峤生卒年辨证》,《马茂元说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8页。可见,编纂《三教珠英》之时,李峤的年龄是55岁。
《新唐书》卷114《徐彦伯传》载:“七岁能为文。结庐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抚河北,表其贤,对策高第……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首。”(30)[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14《徐彦伯传》,第4201-4202页。徐彦伯《旧唐书》本传没有记载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之事,《新唐书》本传记载较详,并言选天下文辞之士,徐彦伯与李峤居首,可见,徐彦伯在编纂《三教珠英》时的作用。《白孔六帖》卷73亦载:“撰《三教珠英》。徐彦伯进给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首。”(31)[唐]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白孔六帖》卷7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2册,第207页。另外,我们认为《三教珠英》的编纂,在当时绝对是文坛盛事,并不像后世学者讥讽的那样,浅薄不经,因为除了“二张”兄弟之外,还是有一批文坛高手参与其中。对于徐彦伯编纂《三教珠英》时的年龄,我们也做一个补充。杨玉锋《徐彦伯考》言:“薛元超举荐事在仪凤二年(677),史载徐彦伯七岁能文,以此前推30年作为其生年参照,则可大致判断其生于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徐彦伯官位显要,新旧唐书载其卒年为开元二年(714),当无误。”(32)杨玉锋《徐彦伯考》,《天中学刊》2017年第3期,第127-135页。可见编纂《三教珠英》之时,徐彦伯的年龄是53岁。徐彦伯在部分典籍中,名字位列李峤之前,可见,在编纂《三教珠英》这个事情上,徐彦伯之地位、作用与李峤不相上下。
《旧唐书》卷94《崔融传》载:“中宗在春宫,制融为侍读,兼侍属文,东朝表疏,多成其手。圣历中,则天幸嵩岳,见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圣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内供奉。四年,迁凤阁舍人。久视元年,坐忤张昌宗意,左授婺州长史。顷之,昌宗怒解,又请召为春官郎中,知制诰事。长安二年,再迁凤阁舍人。三年,兼修国史。”“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及易之伏诛,融左授袁州刺史。寻召拜国子司业,兼修国史。神龙二年,以预修《则天实录》成,封清河县子,赐物五百段,玺书褒美。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时年五十四。”(3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4《崔融传》,第2996-3000页。神龙二年(706),崔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时年54岁,而圣历三年(700)之时,即编纂《三教珠英》之时,崔融的年龄是48岁。久视元年,崔融被贬,应是其早期未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原因。
《旧唐书》卷98《魏知古传》载:“长安中,历迁凤阁舍人、卫尉少卿。时睿宗居藩,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黄门侍郎,兼修国史。”(3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8《魏知古传》,第3061页。“开元元年,官名改易,改为黄门监。二年,还京,上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寻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三年卒,时年六十九。”(3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8《魏知古传》,第3064页。《魏知古传》没有记载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之事,开元三年(715)年,魏知古69岁,而圣历三年(700),编纂《三教珠英》时,魏知古的年龄是54岁,算是编纂团队中的年龄较大者。
纵观上述李峤、徐彦伯、崔融、魏知古四人生平事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知,李峤、崔融与武则天、“二张”关系融洽,中宗复位之后,皆坐“二张”窜逐。《旧唐书》卷78《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载:“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3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8《张行成族孙易之昌宗》,第2708页。当然,李峤、崔融后来也都得到起复与重用。此外,李峤、徐彦伯早年都曾得到薛曜之父薛元超的赏识与推荐,而薛曜也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崔融是唐中宗故人,中宗在春宫,融为侍读,兼侍属文。魏知古则是唐睿宗故人,曾任检校相王府司马。总之,四位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老臣,与当时的权力核心联系是较为密切的,且各有渊源,虽不敢由此得出什么结论,但是也可以由此观察《三教珠英》编纂之时的政治生态。
(二)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王无竞、刘允济、韦元旦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沈佺期传》载:“相州内黄人也。进士举。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3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沈佺期传》,第5017页。沈佺期的传记很简单,仍然记载了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事情,可见,编纂《三教珠英》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是有荣耀的“美事”。《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宋之问传》载:“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3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宋之问传》,第5025页。宋之问、沈佺期均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高宗上元二年(675),沈宋同登进士第。武后垂拱元年(685),沈佺期步入仕途。天授元年(691),宋之问开始仕宦生活,以名士身份被武则天征召入宫,为习艺馆学士。圣历三年(700),编纂《三教珠英》之时,二人的年龄皆为44岁。开元四年(716)沈佺期卒,年61岁。先天元年(712),宋之问被赐死,年57岁。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阎朝隐传》载:“累迁给事中,预修《三教珠英》。张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隐及宋之问潜代为之。圣历二年,则天不豫,令朝隐往少室山祈祷。朝隐乃曲申悦媚,以身为牺牲,请代上所苦。及将康复,赐绢彩百匹、金银器十事。俄转麟台少监。易之伏诛,坐徙岭外。寻召还……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3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阎朝隐传》,第5026页。《新唐书》卷202《文艺中·阎朝隐传》载:“中宗为太子,朝隐以舍人幸。性滑稽,属辞奇诡,为武后所赏。”(40)[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2《文艺中·阎朝隐传》,第5751页。阎朝隐年龄不详,亦是当时的文学名士,他与“二张”兄弟关系密切,亦曾做过中宗的舍人,还为武则天所赏识,可见此人的通脱。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王无竞传》载:“时宰相宗楚客、杨再思常离班偶语,无竞前曰:‘朝礼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轻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转无竞为太子舍人。神龙初,坐诃诋权幸,出为苏州司马。及张易之等败,以尝交往,再贬岭外,卒于广州,年五十四。”(4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王无竞传》,第5027页。王无竞在值班时斥责宰相宗楚客、杨再思,可见此人之性格。王无竞与张易之亦有交往,甚至在二张被杀之后,受到牵连,被贬岭外,死于广州。王无竞卒年定为神龙元年(705),54岁,可知圣历三年(700)时,其应是49岁。宋之问曾有《端州驿见杜审言王无竞沈佺期阎朝隐壁有题慨然成咏》一首,可见宋之问与王无竞、沈佺期、阎朝隐诸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刘允济传》载:“博学善属文,与绛州王勃早齐名,特相友善……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长安中,累迁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未几,擢拜凤阁舍人。中兴初,坐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长史,为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4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刘允济传》,第5012-5013页。刘允济早年与王勃齐名,亦是博学之人,后来,为酷吏所构,当死未死,应是武则天暗中保护的结果,从他后来与“二张”关系密切,并因此被贬可知,此刘允济与“二张”乃至武则天的关系是较为紧密的。或许刘允济因为被贬,早期没有参加《三教珠英》的编纂,故《唐会要》不记其名,而由《李适传》可知,其亦是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
《新唐书》卷202《文艺中·韦元旦传》载:“元旦擢进士第,补东阿尉,迁左台监察御史。与张易之有姻属,易之败,贬感义尉。俄召为主客员外郎,迁中书舍人。舅陆颂妻,韦后弟也,故元旦凭以复进云。”(4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2《文艺中·韦元旦传》,第5749页。韦元旦与张易之有姻亲,易之败,贬感义尉。当然,其后来的起复,则是与韦皇后有关。
总之,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王无竞、刘允济、韦元旦六人,皆可视为“二张”一党,编纂《三教珠英》之时,沈佺期、宋之问44岁,王无竞49岁,由此可推知,阎朝隐的年龄亦是差不多。刘允济、韦元旦年龄不详,暂且不论。且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王无竞四人明显是有亲密关系的文人群体,他们与武则天及“二张”的关系更是极其密切,故我们可以认为李峤、崔融之外,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王无竞四人,亦是《三教珠英》编纂中的重要存在,且是极其有影响力的存在,不能因为他们与“二张”关系密切,就怀疑其人品有问题,甚至怀疑他们的学问,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与“二张”关系密切,他们在修书之时,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且他们的才学其实是公认的出众。
(三)尹元凯、李适、富嘉谟、吴少微、员半千、王适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尹元凯传》载:“与张说、卢藏用特相友善,征拜右补阙。”(4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尹元凯传》,第5027页。《新唐书》卷202《文艺中·尹元凯传》亦载:“与张说、卢藏用厚,诏起为右补阙。”(4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2《文艺中·尹元凯传》,第5752页。很可惜,尹元凯本传没有记载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事情。《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阎朝隐传》载:“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4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阎朝隐传》,第5026页。《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传》载:“于是适与王无竞、尹元凯、富嘉谟、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刘允济在选。”(47)[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传》,第5747页。《阎朝隐传》《李适传》明确记载了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事情,并且此尹元凯与张说、卢藏用特相友善。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富嘉谟传》载:“长安中,累转晋阳尉,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后为寿安尉,预修《三教珠英》。中兴初,为左台监察御史,卒。”(4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富嘉谟传》,第5013页。《新唐书》卷202《文艺中·富嘉谟传》载:“豫修《三教珠英》。韦嗣立荐嘉谟、少微并为左台监察御史。已而嘉谟死,少微方病,闻之为恸,亦卒。”(4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2《文艺中·富嘉谟传》,第5752页。富嘉谟本传记载了他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事情,并且,富嘉谟之文章是当时之经典,为时人所钦慕,由此来看,参与编纂《三教珠英》之文士中,亦是有不少真才实学之人。吴少微两《唐书》没有传,《玉海》引《唐会要》小字部分,说吴少微亦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故我们将之附入。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员半千传》载:“长安中,五迁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半千以控鹤之职,古无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轻薄,非朝廷进德之选,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预修《三教珠英》。”(5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员半千传》,第5015页。由员半千上疏请罢控鹤监之事,可见此人之行事,虽然忤旨,其仍然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刘宪传》载:“初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宪与王适、司马锽、梁载言相次判入第二等。”(5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刘宪传》,第5017页。王适本传没有记载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事情,但是《唐会要》记载了他,并且其排名很靠前。
《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传》载:“武后修《三教珠英》书,以李峤、张昌宗为使,取文学士缀集,于是适与王无竞、尹元凯、富嘉谟、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刘允济在选。书成,迁户部员外郎,俄兼修书学士。景龙初,又擢修文馆学士。”(5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传》,第5747页。李适亦是名臣,文辞优美,其于唐睿宗时去世,唐睿宗第二次继位的时间是景云元年至延和元年(710-712),以711年为其卒年,圣历三年(700)其应是38岁左右。
综上,《文苑传》诸人,包括李适,皆是才学之士,但是他们与“二张”的关系没有明显的亲密状态,甚至于员半千上疏请罢控鹤之职,可见诸人之政治倾向,或可称之为中间力量。
(四)张说、徐坚、刘知几、崔湜
《旧唐书》卷97《张说传》载:“弱冠应诏举,对策乙第,授太子校书,累转右补阙,预修《三教珠英》……长安初,修《三教珠英》毕,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擢拜凤阁舍人。”(5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7《张说传》,第3049-3050页。张说后来官至宰相,为大唐名臣,文坛领袖,张说与徐坚等人,后来还编纂有《初学记》,而编纂《三教珠英》的参与人里面亦有此张说,虽然,此时的张说还没有达到政治上的高度,亦是有文名的才俊。对于张说的年龄仕宦履历等,前辈学者多有探究,张说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出生,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病逝,(54)周睿《张说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9-23页。故张说修《三教珠英》时的年龄是33岁左右。
《旧唐书》卷102《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历年未能下笔。坚独与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诸人依坚等规制,俄而书成,迁司封员外郎。”(5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2《徐坚传》,第3175页。《新唐书》卷199《儒学中·徐坚传》载:“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5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99《儒学中·徐坚传》,第5662页。通过《徐坚传》我们得到了新的认知,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编纂《三教珠英》,他们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却历年未能下笔,徐坚与张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汇,由此可见,徐坚与张说是《三教珠英》编纂的核心人物,是体例设定的中心人物,而此时的徐坚与张说皆是中年才俊。徐坚的生卒年为660年至729年,编纂《三教珠英》之时徐坚40岁左右。
很多史料乃至当代学者,皆盛赞“坚独与说构意撰录”,我们对于徐坚、张说的学问还是认可的,但是彼时彼刻,圣历三年(700)前后的时间段里,徐坚与张说之地位还是需要客观评价的,对于《三教珠英》的编纂,他们的贡献不应夸大,由于他们在开元时代的影响大增,会有众善归之、锦上添花之嫌,故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忽视、忽略其他学士的贡献,一味的强调张说、徐坚之功。《初学记》的编纂的确是徐坚之功,《初学记》体例创新的确是举世公认,但是《初学记》之所以如此成功,与《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皆有关系,更与徐坚早年编纂过《三教珠英》极有关系,是《三教珠英》这个大数据库影响、提升了后来的类书,尤其是《初学记》。(57)刘全波《〈初学记〉与〈艺文类聚〉比较研究——以“体例”与“目录”为中心的考察》,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总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136-157页;刘全波《〈初学记〉〈艺文类聚〉比较研究——以“诗文”为中心的考察》,《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76-83页。
《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载:“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5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第3173页。《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载:“子玄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善,尝曰:‘海内知我者数子耳。’”(5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第4520页。可见,刘知几在参与《三教珠英》编纂之时,与徐坚等人的配合是较好的,并且相对于李峤、徐彦伯而言,张说、徐坚、刘知几诸人在当时皆是中青年才俊,而《三教珠英》的真正编纂人员,肯定就是他们无疑,当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绝不仅仅是他们。刘知几的生卒年是661年至721年,可见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之时的年龄为39岁左右。(60)许凌云《刘知几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4、330页。
刘知几《史通》论及同道好友时言:“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61)[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10《自叙第三十六》,上海:上海古出版社,2009年,第268-269页。通过刘知几所言,其同道好友,有徐坚、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而共同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有徐坚、刘允济二人。但是,刘知几的诸位好友中,朱敬则是与二张距离较远的,刘允济却是与二张关系密切的。《新唐书》卷115《朱敬则传》载:“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绘武三思、李峤、苏味道、李迥秀、王绍宗等十八人像以为图,欲引敬则,固辞不与,世洁其为人。”(6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15《朱敬则传》,第4220页。《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刘允济传》载:“中兴初,坐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长史,为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6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刘允济传》,第5013页。所以刘知几的朋友圈,既不是一边倒于“二张”,也不是完全绝缘于“二张”的。
《旧唐书》卷74《崔湜传》载:“湜少以文辞知名,举进士,累转左补阙,预修《三教珠英》,迁殿中侍御史。”(6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4《崔湜传》,第2624页。《新唐书》卷99《崔湜传》载:“玄宗在东宫,数至其第申款密。湜阴附主,时人危之,为寒毛……初,在襄州,与谯王数相问遗。王败,湜当死,赖刘幽求、张说护免。及为宰相,陷幽求岭表,密讽广州都督周利贞杀之,不克。又与太平公主逐张说。”(6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99《崔湜传》,第3921-3922页。崔湜此人出身名门,自比东晋王导、谢安之家,可见其家族之势力,崔湜学问亦佳,后来在唐中宗、唐睿宗时代,崔湜官至宰相,一直处于权力的核心,与武三思、上官婉儿、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以及后来的唐玄宗皆有交集,而他早年亦曾参与过《三教珠英》的编纂,并且由其后来当死之时,刘幽求、张说护免他的事情来看,此人与张说的关系亦是较好,而在参与编纂《三教珠英》之时,张说、徐坚、刘知几、崔湜四人应是关系较为紧密的一个小群体。崔湜的生卒年史书亦有记载,即生于671年,卒于713年,而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时的年龄是29岁左右,是上述四人中最为年轻的。
(五)薛曜、乔备、李羲仲
《旧唐书》卷73《薛元超传》载:“子曜,亦以文学知名,圣历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谏大夫。”(6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3《薛元超传》,第2591页。薛元超早年对李峤、徐彦伯有知遇之恩,薛元超是皇亲国戚,曾参与编纂《东殿新书》,发现、提拔了诸多文学之士,而在编纂《三教珠英》之时,他的儿子薛曜也参与进来了。
《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乔知之传》载:“乔知之,同州冯翊人也。父师望,尚高祖女庐陵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与弟侃、备,并以文词知名……备,预修《三教珠英》,长安中卒于襄阳令。”(6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乔知之传》,第5012页。乔备兄弟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孙,其父乔师望亦是一代名将,作为皇亲国戚,乔备在武则天时代也参与到了《三教珠英》的编纂之中。
李羲仲,王素先生从考实《帝京篇》的性质入手,通过考实作者范围,进而考实作者,认为《帝京篇》系和韵诗,和的应是李百药《帝京篇》的韵,作者应为李百药的曾孙李羲仲。当时武周新立不久,李羲仲作为文学之士,应参加了编修《三教珠英》的盛事,其撰《帝京篇》,和曾祖李百药旧韵,目的是歌颂新朝帝京繁华,矜己家学渊源有自。(68)王素《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第87-90页。
(六)元希声、马吉甫、杨齐哲、胡皓、于季子、李处正、房元阳、蒋凤
元希声、马吉甫、杨齐哲、胡皓、于季子、李处正、房元阳、蒋凤诸人,皆无传记传世,故将他们暂时置于此处,但诸史书对于他们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记载还是可信的,而对他们生平事迹的考察,另文再论。
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言:“从某种程度上说,编修于武周时期的《三教珠英》其实反映了武则天对李唐文化乃至政权的继承与发展。”(69)王兰兰《〈三教珠英〉考补与发微》,第114-130页。纵观诸学士,他们的政治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至少一半以上的政治倾向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他们基本都是依附武则天与“二张”的,在此时,他们与武则天及“二张”的关系是相对融洽的。所以我们说,《三教珠英》的编纂,是武则天及其手下文士的集体杰作。张说撰《故吏部侍郎元公希声神道碑》载:“则天大圣皇后万几之余,属想经籍,思欲撮成群书之要,成一家是美,广集文儒以笔以削目为《三教珠英》,盖一千二百卷。公首膺嘉命,议者荣之,书成克厌帝旨,迁太子文学,主客、考功二员外,赏勤也。”(70)[宋]李昉《文苑英华》卷898《故吏部侍郎元公希声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726页。可见,修书本身就是则天大圣皇后的大手笔,并且是展现武周文治之盛的标志性工程。
三、从“珠英学士”到“修文馆学士”
“珠英学士”完成了《三教珠英》的编纂之后,“珠英学士”群体并没有立即解散,尤其是骨干人员,他们仍然在一起工作,甚至于长安三年(703)正月,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撰修工作。《唐会要》卷63《史馆上》载:“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71)[唐]王溥《唐会要》卷63《史馆上》,第1094页。很显然,修《唐史》是有政治意味的,这是比编纂《三教珠英》更为直接的宣言。
唐中宗复位后,诸学士又开始了《则天皇后实录》《则天皇后文集》的撰修。《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载:“神龙二年,元忠与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7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第2953页。《新唐书》卷58《艺文二》载:“《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7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8《艺文二》,第1471页。《唐会要》卷63《史馆上》亦载:“神龙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骑常侍武三思,中书令魏元忠,礼部尚书祝钦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则天实录》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赐物各有差。”(74)[唐]王溥《唐会要》卷63《史馆上》,第1094页。刘知几在《史通》中,记载了他参与上述修书任务的经历。《史通·自叙第三十六》载:“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75)[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10《自叙第三十六》,第269-270页。
唐中宗景龙二年至四年(708-710),宫廷宴游活动频繁,诗歌唱和之风大盛。在此期间,“修文馆学士”即原来的部分“珠英学士”,创作了大量应制诗,对律诗的定型和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传》载:“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7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2《文艺中·李适传》,第5748页。胡旭、胡倩《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言:“景龙年间的宫廷文学活动,延续了武周时期的繁荣,甚至在频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体现了以唐中宗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对文学的热情。正是他们的积极提倡,才使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崇尚文学创作的风尚,这对于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具有宏观引导的意义。”“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说到底是应酬文学,是游戏文学,真感情不多。喧嚣浮躁的景龙文坛,没有产生经典名作,这是不争之事实。景龙文人诸多集会,相互交流,大量创作,使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提高。”(77)胡旭、胡倩《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文史哲》2017年第6期,第41-49页。
冉旭《唐景龙至开元前期的学士诗人》言:“从武后时期开始,唐代的政局一直处于非常态的环境里……武则天以威权临下,对待朝臣相当的冷酷,甚至是‘诛戮无虚日’。这使得皇权更加专断,朝臣的政治地位下降并相对脆弱。另一方面,由于皇嗣地位的不稳定,围绕着武氏宗戚与嬖幸之臣形成了激烈的朋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宗朝,并更加恶化。”(78)冉旭《唐景龙至开元前期的学士诗人》,《中州学刊》2003年第6期,第120-123页。李淑《唐景龙年间史馆政治分野与刘知几去职之关系》言:“中宗复位后,武三思、太平公主、睿宗等同属这一派力量。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派也发生了分化。武三思被杀后,武氏力量日渐衰落,原本亲近武氏者开始亲近与皇权关系亲密的韦后与安乐公主,使二人权力日渐膨胀;伴随着武氏力量日衰,作为李唐皇室的重要成员,太平公主与睿宗的实力也相对变强。以韦后、安乐公主为代表的一支,与以太平公主、睿宗为代表的一支渐行渐远,终于在中宗去世后决裂。而太平公主、睿宗这一支在后来也分化出李隆基一派,最终战胜了太平公主。”(79)李淑《唐景龙年间史馆政治分野与刘知几去职之关系——刘知几与萧至忠书探微》,《国学学刊》2018年第2期,第40-46页。诚然,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武周、李唐的权力核心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故诸学士,包括前期的“珠英学士”、后期的“修文馆学士”,其实皆是处于激烈的漩涡之中,难免于朋党、派系,故不断有人丧命于其间。
其实,纂修《三教珠英》的学士,多是生于唐朝,长于唐朝的一代人,这一点就明显区别于唐初多部大型类书的编纂者群体,诸如《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虽然武周代唐是一次新的王朝鼎革,但从《三教珠英》的编纂来看,却是第一次完全由“长于唐朝”的文人来负责的文化工程,故可以看作是对初唐以来文化及其秩序的一种总结。武周代唐之后,武则天需要与士人群体合作,以确立其权力地位,大型类书的编纂是士人群体与皇权紧密合作的成果,是皇权维系、彰显的重要形式,粗看“珠英学士”群体的入仕途径,似乎通过科举上升的人占了多数,新的流动方式逐渐生成,他们成为了新的文坛“主角”。而科举这一新的上升方式的形成,又得益于皇权的加强,他们是与皇权合作而不是依赖于原先的门阀或者其他,这似也可为陈寅恪所说武周社会革命做一注脚。
大唐景龙四年(710)岁次庚戌四月壬午朔十五日景申,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卷一载: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修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李峤笔受兼润色
翻经学士通议大夫守吏部侍郎修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上柱国臣崔湜
翻经学士朝议大夫守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修国史上柱国臣张说
翻经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行礼部侍郎修文馆学士修国史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子臣徐坚
翻经学士礼部郎中修文馆直学士轻车都尉河东县开国男臣薜稷
翻经学士正议大夫前蒲州刺史修文馆学士上柱国高平县开国子臣徐彦伯
翻经学士中书舍人修文馆学士上柱国金乡县开国男韦元旦
翻经学士中大夫行中书舍人修文馆学士上柱国臣马怀素
翻经学士朝请大夫守给事中修文馆学士上柱国臣李适
翻经学士朝散大夫行起居郎修文馆直学士上护军臣沈佺期
翻经学士著作佐郎修文馆直学士臣阎朝隐
翻经学士修文馆直学士臣符凤(80)[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大正藏》,第24册,第418-419页。
可见,原来的“珠英学士”,后来的“修文馆”学士,又大量的参与到了义净大师的译场中,这无疑是他们作为群体存在的新证据,虽然他们之间也有种种矛盾,但是他们之间必然是有天然的联系的。张弓先生《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译》言:“唐代许多熟谙传统文化的儒臣,到国家译场中参与译事,这不仅对汉文经藏的形成,而且对古代中印两大文化体系的沟通,对借鉴外域以丰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均作出了重要贡献。”(81)张弓《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48-54页。李小荣先生《唐代译场与文士:参预与影响》言: “最值得一提的是参预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译经之文士,从监译、笔受至翻经学士共三十一人,近三分之一源自武后命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之时的‘珠英学士’,如李峤、徐彦伯、阎朝隐、徐坚、李适、崔湜、张说、沈佺期、符凤、韦元旦。作为类书的《三教珠英》,其编撰原则是‘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三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佛、道加上传统的儒教,当是它得名依据之所在。”(82)李小荣《唐代译场与文士:参预与影响》,《文学遗产》2015年第2期,第94-105页。
总之,我们认为武则天时代的“珠英学士”群体,没有随着《三教珠英》编纂的完成而结束,崔融《珠英学士集》的编纂,《唐史》的撰修,皆是紧随其后的活动,且是武则天长安时代的重要活动。武则天去世后,他们又进行了《则天皇后实录》《则天皇后文集》的撰修。唐中宗时代,随着“修文馆学士”的设置,乃至频繁的宫廷宴游,诸学士多参与其中,则是后续活动的新表现,至景龙四年(710),这群学士中的大部分人,又参与了义净大师的佛经翻译工作。如此来看,从武则天时代到唐中宗时代,这个亲武则天的文人群体,一直很活跃,到了唐玄宗时代,随着大部分人的去世,这个群体就零落了,但是由于张说、徐坚、刘知几诸人的存在,这个群体的“微波”尚在。
王三庆先生《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言:“敦煌本《语对》之编纂上限不得早于高宗永徽元年,唯亦非迟至晚唐之产物,较确切时间约在神龙至景云年间。”(83)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29页。白化文先生、郝春文先生对《语对》的命名皆有保留意见,白先生建议加上引号,郝先生则命名为《失名类书(《语对》)》。白化文《敦煌遗书中的类书简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第57页;郝春文等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 第1卷(修订版)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神龙是唐中宗年号,705年至706年,景云是唐睿宗年号,710年至711年。郑炳林先生《唐李若立〈籯金〉编撰研究》言:“始于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之后, 成书于唐中宗神龙年间, 特别是中宗神龙二年十月移都西京之前。”(84)郑炳林、李强《唐李若立〈籯金〉编撰研究(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22-29页;郑炳林、李强《唐李若立〈籯金〉编撰研究(下)》,《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3-23页。万岁登封元年是公元696年,神龙二年是公元706年。可见,上述二部敦煌类书《语对》《籯金》的编纂时代,与“珠英学士”所处的时代多有重合,目前,我们虽不敢断定三者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测一二,第一,《三教珠英》乃至此前大量官修类书的编纂,带来了私修类书编纂的高潮;第二,“珠英学士”群体及其文学活动,影响到了当时的读书人、士大夫,少室山处士李若立可能即是其中之一。
结语
武周时代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编纂是隋唐时期官修类书编纂潮流的延续,《三教珠英》的编纂者多被称为“珠英学士”,“珠英学士”群体除了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外,更有李峤、徐彦伯、魏知古、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刘允济、王无竞、韦元旦、尹元凯、李适、富嘉谟、员半千、王适、张说、徐坚、刘知几、崔湜、薛曜、乔备、元希声、马吉甫、杨齐哲、胡皓、于季子、李处正、房元阳、蒋凤等人,至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时代,诸学士仍然活跃于政坛、文坛。诸学士在编纂《三教珠英》之余,多编纂有与类书密切相关之典籍,如《李峤杂咏》《燕公事对》,甚至于《初学记》之编纂,亦是受到了《三教珠英》的影响,故《三教珠英》之编纂影响深远,引领了时代风气、学术潮流。此外,敦煌类书《语对》《籯金》的编纂时代,与“珠英学士”所处时代亦有重合,可见《三教珠英》的影响或许更大、更深、更远。对于《三教珠英》的编纂,史书皆言“二张”无才学,盛赞张说、徐坚之功,以今度之,有因人废事、锦上添花之嫌,不应过分夸大张说、徐坚之功,亦不应抹杀李峤、徐彦伯、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王无竞、刘允济等诸人之劳,当然,此中诸人与“二张”之关系,也就是诸人与武则天之关系,皆是太过亲密,故为开元时代的人所不屑,他们的很多业绩自然就被抹杀或者转移。总之,《三教珠英》是武则天时代的杰作,前无古人,就其卷帙而言,几百年间,也未曾被超越,而由其必须超越《文思博要》的编纂目标来看,《三教珠英》必然是拥护武周的一群文人学士的集体成果。“珠英学士”群体的延续时间长达十几年,加之其频繁的文学活动,必然深远的影响了此时此后的文风、学风,更带动了类书的大发展。《隋书·经籍志》中,诸类书是附于杂家之中的,而到了开元时代,政府再次整理图书典籍的时候,尤其是毋煚编纂《古今书录》之时,诸类书已经有了独立的目录学位置,就是后来的“事类”,或称为“类事”,这与唐初近百年的类书大发展、大繁荣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三教珠英》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