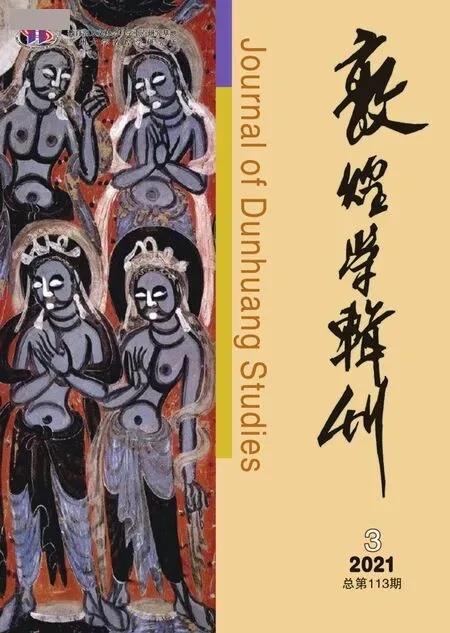再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驮、硕、斗、升
杨 铭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吐蕃统治敦煌从786年起到848年,共有五六十年的时间。期间除了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有较大的变化以外,在敦煌社会的日常经济生产、生活方面也相应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虽然前人已有较多的探讨,但仍然有一些论题至今尚未充分的讨论。其中,有关吐蕃时期度量衡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比如量制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敦煌汉、藏文献中分别出现了“番驮”“汉驮”(rgya khal)“汉硕” (rgya sheg)“蕃升”(bre)等之前不见的计量单位,这些带有“蕃”“番”“汉”的量制,与之前敦煌使用的量制,孰大孰小?是否可以换算?这些都是需要专门探讨的。之前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过相关的问题,以下按究竟是“蕃制”大还是“汉制”大的问题归纳,介绍已有的数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蕃制”比“汉制”大。日本学者武内绍人认为,藏文文书中有rgya sheg/shig一词可译为“石”或“硕”,同期敦煌汉文文献中,一名妇女的身价是二十石小麦,即十驮。(1)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Tokyo, 1995, p.29.武内绍人所转引的关于妇女的身价的文献,实为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遗产分割纠纷》,其载:“大兄嫁女二,一氾家,一张家。妇财麦各得廿石,计卌石,并大兄当房使用。齐周嫁女二,一张家,一曹家。各得麦廿石,并入大家使用。宣子娶妻,妇财麦廿石。羊七口,花毡一领,布一疋,油二斗五升,充妇财。”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85页。言下之意,一驮相当于两石,而一石有十斗。之后,张亚萍等认为吐蕃时期的1驮粟=1石稍过(1.44硕),又说1驮=2石。(2)张亚萍、娜阁《唐五代敦煌的计量单位与价格换算》,《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第38-42页。再其后,高启安撰文讨论吐蕃时期的量器及量制变化,认为在当时的敦煌,汉斗、蕃斗,大驮、小驮,以及“汉石”等曾并行使用了一段时间,而吐蕃的升显然要比汉升大得多,一升相当于十汉升。(3)高启安《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第59-71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蕃制”比“汉制”小。如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敦煌吐蕃文书中的一驮(khal)不足一硕,仅相当于0.87硕,而一硕有10斗,那么一驮仅有8.7斗。(4)[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后来,德国学者童丕在其著作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5)[法]童丕著,余欣、陈建伟译《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3、85页。国内学者杨际平早先研究P.2162《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提出吐蕃时期的一驮等于二石,二石等于二十斗。(6)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兼及其时的税制和户口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第94-100页。宁可、郝春文指出驮有蕃驮与汉驮的区别,此二十斗“是蕃斗而非汉斗”。(7)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第32-40页。所以,杨际平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一番驮等于两番石,又大体相当于一汉石。(8)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1页;杨际平《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第16-21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蕃制”与“汉制”相当,或双方的换算关系不清。比如,王尧、陈践认为藏文文献中的“克”(khal),在敦煌汉文卷子中又作“番豆斗”,与汉斗相等。(9)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3页第32条注释①。而刘忠提出:蕃制,1驮=20克,1克=20升,为20进制,与汉区1石=10斗,1斗=10升,1升=10合的十进制不同。驮和克在藏文中皆为Khal,如何区别难以确定。(10)[英]F.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7页译者注[2]。
看来,有关吐蕃时期敦煌的度量衡制度,尤其是量制的变化,前期虽有文章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有若干不同的观点。故此,笔者不揣浅陋,撰文加以讨论,就教于方家。
一、蕃(番)驮(khal)与汉驮(rgya khal)
如上所述,对在敦煌吐蕃文书中出现的khal一词的翻译,有对应汉文文书译为“驮”的,也有译为“克”或“番斗”的。笔者翻检敦煌吐蕃文书,发现khal一词之前并没有用bod来修饰表示“蕃驮”,而只是发现在出自和田的古藏文文书中有用rgya khal来表示“汉驮”的。换句话讲,在古藏文文书中出现的khal一词,对应的就是汉文文书中的“蕃驮”或“驮”;而拼写成rgya khal的,即在khal之前以rgya“汉”修饰的,对应的是汉文文书中的“汉驮”。
由于古藏文文书记载khal的文书不少,这里就不单独列出,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渐次列出。这里先讨论出自敦煌的汉文文书中的“蕃驮”和“番驮”,目前一共找到有三件,以下分别引出:
S.1475V《卯年(823?)阿骨萨部落百姓马其邻便麦契附僧义英便麦契与便麦记录》后半部分:
(二)
3. 见人僧谈惠
4. 三月十四日记
(三)
1.又便麦两石,分付僧神宝 见人道远
2.又便与僧神宝青[麦]两硕 见人神寂
3. 四月廿七日

“番驮”一词又见于S.6829V《卯年(823?)悉董萨部落百姓张和子预取造芘蓠价麦契》。开头文字为:
1.卯年四月一日悉董萨部落百姓张和和(子)为无种子,
2.今于永康寺常住处取栛篱价麦壹番驮。断
3.造栛篱贰拾扇,长玖尺,阔六尺。其栛篱限四月
4.廿五日已前造了。(以下略)(14)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107页。
又有把“番驮”写成“蕃驮”的,如S.4192v《未年(839?)张国清便麦契》:
1.未年四月五日,张国清遂于 处便麦
2.叁蕃驮。其麦并限至秋八月末还。如不
3.还,其麦请陪(倍),仍掣夺。如中间身不在,
4.一仰保人代还。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
5.平章,书指为记。
6.麦主
7.便麦人张国清年卌三
8.保人罗抱玉年五十五
9.见人李胜
10.见人高子丰
11.见人画允振
12.报恩窖内分付 四月五日记。(15)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150-151页。
有关“汉驮”(rgya khal)的记载,目前不见于敦煌汉文文书,而仅见于一件出自和田的古藏文文书《吐蕃已年(801)秋雇工契》,该文书现藏于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弗根斯博物馆),编号:Hedin3。汉译如下:
1-2、已年秋,质逻(ji la)(16)质逻(ji la),于阗文作Cira,唐代于阗毗沙都督府属下十个州之一,即“六城质逻州”。六城由“质逻”“拔伽”(于阗文Birgamdara,藏文Bergadra)、Pa(于阗文)、skūra(于阗文,藏文Osku)、“潘野”(于阗文Phamya,藏文Phanya)和“杰谢”(Gaysāta)组成,分布在达玛沟河沿岸南北走向的狭长的灌溉区中,地域与今和田地区策勒(Cira)县辖境大致相同。朱丽双《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71-90页。的于阗人萨雄(li bsar gzhong)和卓那墨多(zho nal mor ldogs)〔…〕;
2-3、〔…〕报酬是六汉驮(rgya khal)重的一桶葡萄酒。〔…〕墨多一旦返回,立即支付。
3-5、如果萨雄试图抵赖,〔…〕帕萨莫达(par sha mo dar)将双倍赔偿;
5-7、见人为拉协奴(lha bzhe vdo)和贡朗美东(kong nam myes mthong)、〔…〕春(cung)等人,并盖见证印章,帕萨索达〔…〕盖印。
8a(倒写:)帕萨索达〔指印〕。
8b(两枚私印;一枚吉祥万字符印记和姓名:)阴拉奴(im lha vdo)。(17)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pp.271-274;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6-299页。
此外,记载有“驮”字样、未加“蕃”或“汉”修饰的敦煌汉文书较多,不一一例举。这里只是强调,笔者赞成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没有在“驮”之前标明“蕃”或“汉”字样的,均系“番驮”。(18)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第32-40页。
有关蕃(番)驮(khal)、汉驮(rgya khal)的文书既见于上,按照武内绍人的观点,以上换算关系列成公式便是:
1驮(番、蕃驮)=2汉驮=2汉硕(石)=20斗(汉斗)
用这个标准,再来审视P.2162《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S.5622《杨庆界寅年地子历》中驮与斗的关系。杨际平先是认为,这两件文书中的一驮等于二十斗,这实际上就是武内绍人的上述换算标准,但他后来接受宁可等人的见解,认为此处的“斗”应为蕃斗。但翻检吐蕃统治时期的汉、藏文书,目前均未见“蕃斗”一词,因此,笔者认为这两件文书中的“驮”均是“蕃驮”,前一件文书中的“小驮”相当于“汉驮”(19)高启安认为,P.t.1088《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碨课麦粟历》中的“驮”就是“小驮”,每驮在八斗到一石之间,参见高启安《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第59-71页。,“斗”应为汉斗,一驮等于二十斗。
二、rgya sheg与“汉硕”或“汉石”
上文说过,蕃制的一驮相当于两汉硕,所以本节讨论藏文文书中的rgya sheg/shig “汉硕”,及其与汉文文书中“汉硕”或“汉石”的关系。
藏文文书中的“汉硕”(rgya sheg/shig ),rgya可译为“汉(人)”或“唐(人)”,sheg/shig就是汉文“硕”或“石”的音译。如前所述,武内绍人较早把rgya sheg/shig译为“汉硕”或“汉石”。目前,笔者见到记载有rgya sheg/shig的古藏文文书共三件,引出如下:
第一,P.t.1086《吐蕃亥年(831±)夏王光英购丝棉部落李天昌土地契》:
1-2、亥年夏,丝棉部落(dar pavi sde)李天昌(li thevi tsheng)兄弟二人的房基,与王光英(wang kvang hing)的〔土地〕毗连;
2-3、光英兄弟从天昌兄弟处,以大麦两汉硕和粟米两汉硕,共四汉硕,购得〔土地〕。
3-4、按照原先的约定,已向天昌兄弟全数纳清;
4-6、天昌一方的立契人,以及见人为白顺子(beg shun tshe),梁兴子(lyang zhen tshe),刘英奴(livu hing vdo),宋平奴(song beng vdo)等,在契约上盖印。
6-7、购房之价钱,由幼弟史国乃(shi kog ne)经手,随附国乃的收讫之印。(20)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pp.165-166;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172-174页。
可以看出这是一份契约文书,内容涉及房屋和土地价格支付的协议。然而,文本并没有按照买卖契约的格式来构拟,内容更为简单扼要,清楚表明价款已支付,文书结束处写到“随附国乃的收讫印”,也就是说这是一份收据。
第二,P.t.1115《吐蕃巳年(825±)春悉宁宗部落宋德德与王华子伙耕契》:
1-2、巳年春,悉宁宗部落的宋德德(song tig tig),在康村(kham cung)的籍田一突(dor)半,因无法独自耕种,与王华子(wang hva tshe)合伙共同耕种,各种一半;
2-3、种子由华子租借而来,种子计两汉硕,
3-4、租子共为四汉硕,秋季偿还。其中,两汉硕由宋德德偿还,于秋八月之前如数交付给华子,不能缺少。
5-6、两汉硕的租子在华子手里,如果缺失,将翻倍偿还。
6-7、万一宋德德不在,或手头不济,将由保人薛氏十三娘(ser za shig sam nyang),即借方的妻子负责。
7-8、作为见证,附蔡英(tshevi in)、阴色色(im sevu sevu)等人的印鉴,以及借方和保人的指印。
9(两枚私章.其中一枚印文为:)宋德(song tig)
背面
1、巳年春天,从悉董萨部落的王华子家门口,宋德德先借大麦两汉硕。
2、归还期限,不晚于今年秋八月末之前〔…〕。(21)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pp.208-211;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222-225页。
第三,P.t.1297/1a《吐蕃子年(832±)悉宁宗部落的华折折借麦契》:
1-3、悉宁宗部落(snying tshoms gyi sde)的华折折(hva dze dze),因缺少种子和粮食,确实无法,从永寿寺(weng shivu si)的佛账物中,先借大麦和小麦八汉硕。
3-5、归还时间,为今年秋八月三十日午,送还到永寿寺掌堂师(dge skos)灵贤和尚(ban de leng hyen)所在的寺庙粮库中。
5-8、如不按时偿还,或试图抵赖,将双倍增加,包括本息。折折(dze dze)家中的财物和屋外牛群,以及衣物、用具等,不管何物,按本契约规定,即便抢来,也勿有怨言。
8-10、如果折折(dze dze)不在,其子华科勒(hva khrom legs)应按以上规定负责偿还。
10-12、作为见人,加盖王塔古(wang sta gu)、刘拉勒(livu lha legs) 〔…〕等印鉴,以及折折和担保人的私章和签名。(两枚圆形朱砂章记)。(22)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pp.196-198;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209-211页。
汉文文书中记载的“汉石”目前仅见一例,S.6235《吐蕃子年便麦粟历》:
1子年扌玄领负及官仓如后:昌归边便粟两石,至秋四石。索家仓三驮麦,突田仓
又于面师

至于记载“汉硕”的文书,这里只引出那种写明“汉硕”数量的。另一类明显也是汉硕,但往往在文书中的表达形式是“汉斗”+“多少汉硕”,即在前面用“汉斗”两字说明是汉制,其后才具体提到多少汉硕,“汉斗”在这里只是起到修饰的作用,没有具体的数量。
P.2858V《吐蕃酉年(829?)索海朝租地帖》:
1 索海朝租僧善惠城西阴安渠地两突,每
2 年价麦捌汉硕,仰海朝八月末已前依数
3 填还了。如违不还,及有欠少不充,任将此
4 帖掣夺家资,用充麦直。其每年地子,三分
5 内二分,亦同分付。酉年二月十三日,索海朝立帖。
6 身或东西不在,仰保填还。见人及保弟晟子
7 见人及保兄海如
8 见人□□
9 见人
10 见人
11 见人(24)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319-320页。
引上可见,在吐蕃时期的敦煌,索海朝租僧善惠的地亩年租金的换算关系是:
8汉硕(80斗)÷2突(20亩)=4斗
也就是年租金是每一亩麦四斗。另外也有附加条件,就是索海朝还要替僧善惠交纳“其每年地子,三分内二分亦同分付。”就是要交纳该地块每年的地子税的三分之二。(25)“地子”所交纳的都是粮食,种类有粟、小麦、青麦、豆等,由部落中的某些人专门负责收集,再向官府交纳。“地子”出现于唐朝,最先是唐朝的“义仓税”,按亩计征。《唐六典》记载:“凡王公已下,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亩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仓部郎中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4页。如果把唐朝的标准作为参考,那么,索海朝除了向僧善惠付出年租金“麦捌汉硕”以外,另外还要替后者向官府交纳地子的三分之二,大约是:
20亩×2升(粟)=40升×0.67=2斗7升。
年租四斗的标准,到了归义军时期也还没有多大的变化,由于这一内容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畴,不赘述。(26)根据笔者对S.5927V《唐天复二年(902)慈惠乡百姓刘加兴出租地契(习字)》(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324-325页。)的统计和分析,文书中,樊曹子佃种刘加兴“四畦共十亩”三年的租金计算公式如下:120斗÷(10亩X3年)=4斗。可见,尽管过去了数十年,敦煌地区的地亩租金尚无多少变化,仍然是每一亩4斗。当然,这件文书也有另外的附加条件,就是樊曹子还要另给刘加兴“麦粟五石,布壹疋肆拾尺,又布叁丈。”这与前件文书说,索海朝还要替僧善惠交纳每年的地子税的三分之二性质是相同的,数量也是相近的。
通过以上数件文书的分析以及地亩租金的换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吐蕃时期的所谓“汉硕”或“汉石”,就是该时间段前后唐朝和归义军时期的“硕”或“石”。因为吐蕃时期为了把蕃制的度量衡与唐朝的度量衡相区别,所以官府文书或民间契约均把后者冠上了“汉”,而吐蕃统治之后的量制又恢复了唐时的称呼,即不再冠以“蕃(番)”的修饰。
三、汉斗、汉升(rgya bre)与蕃升(bre)
检索敦煌西域所出的汉、藏文书,暂未发现有“蕃(番)斗”一词。前面说过,“蕃驮”之下就是“蕃升”,那么根据前面讨论的结果,一“蕃驮”等于二十“蕃升”,也就等于二十斗,一蕃升就相当于一斗。所以汉文文书中有“汉斗”,而没有“蕃斗”,藏文文书中也暂时未找到“蕃斗”的对应词,蕃制中一蕃驮直接就等于二十蕃升。王尧只是把吐蕃的驮(khal),有时译作“驮”“蕃驮”或“克”,有时又译为“蕃豆斗”,实际上它们指的是同一种量制单位。(27)关于“蕃斗”,王尧、陈践认为即吐蕃的计量单位,在藏文文献中称为“克”,“克”在敦煌汉文卷子中又作“番豆斗”,与汉斗相对。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第33页第32条注释①。故此,本节只讨论汉文文书中的汉斗和藏文文书中的蕃升(bre)与汉升(rgya bre )。以下先说“汉斗”。S.2228《吐蕃辰年巳年(9世纪前期)麦布酒付历》:
(前缺)

2 断麦五硕五斗,至秋还。其布纳官用。又张老于尼僧边买布一疋卌二尺,
3 至断麦五硕五斗,两家合买,其布纳官用。各半。
4 弔田秀妇平意布三丈三尺,其布于寺家贷。又寺家取布两疋,
5 辰年十月折麦纳官用。又于寺家取布一疋,智远(?)受戒时告裙衫用。
6 巳年四月五日,共曹住送路空设热布一疋,墨两挺,已上合当家送□子一。
7 又于索家贷绯紬一疋,其紬四月廿日却对面分付,惠照上座于车园。
8 五月十四日于索日荣边买小钗子一三斗,其钗子断麦十硕,
9 并汉斗。于阴兴兴边付本身麦三驮,又对僧义(?)岸付麦一石八
10 斗,又对僧道义[付]麦三石,并汉斗,施本身麦六汉斗,云付磑课用。
11 后五月,付宋澄清酒半瓮。廿二日,付王瓢(?)子麦半驮。
12 廿五日,又付宋澄清麦六汉斗,又酒半瓮,付卢(?)朗布□尺,麦三驮,再晟母领。(28)郝春文主编《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编第1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6-367页。
次说“蕃升”(bre)。因为一驮等于二十“蕃升”,又等于二十汉斗,实际上一“蕃升”就等于一“汉斗”或一“斗”,所以在同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中不见“蕃升”(bre),而只见于敦煌吐蕃文书。以下引出两件,足以说明。
IOL Tib J 844 正面《吐蕃亥年春二月阿骨萨部落张嘉佐将纳粮契》:
1-2、阿骨萨部落张嘉藏(cang ka dzo)将的张昆子(cang kun tse),从去年征收的粮食中,通过上年粮官卢毗赞(lo byi brtsan)借小麦一驮半又四升(bre)。
2-3、应在亥年秋季归还,经节儿(rtse rje)同意,改变登记。
3-5、亥年春二月,说堪布土登(mkhan po thub brtan)有一将军(dmag dpon)颁发的公文,要求纳粮官达加玛(dar rgyal ma)和次麦勒(tre mye slebs)等追缴[借出的小麦]。
5-7、将小麦一驮半又四升,在今年春二月十一日,归还给上年粮官卢毗赞。
7、作为毗赞收讫和盖印的见人,
7-8、汜达耒(bam stag slebs)、 曹国珍(dzevu gog tsheng)、张路耒(cang klu legs)等也盖了印。
9a、(倒写:)招来粮官,签定契约。
9b、(五枚私印,其中两枚可能属于毗赞,其余无法辨认)。(29)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pp.257-259.
IOL Tib J 914正面《吐蕃亥年春二月李刚孜借粮契》:
1-2、先是李康子(li kang tse)从上年〔沙州〕粮官卢毗赞(lo byis brtsan)手中借小麦一驮半又四升(bre)。
2-4、亥年春二月十三日,和尚土登(ban de thub brtan)返寺之时,还给毗赞。
4-5、附〔毗赞〕收讫印和纳粮官次麦勒(tre mye slebs)、琼波塔勒(khyung po stag legs)等见人印。
5-6、原来的造册目录在上,再次更新签订。
7a、(倒写:)招来粮官,签定契约。
7b、卢毗赞的私印。(一枚朱砂印记和签名)(30)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pp.282-284;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278-281页。
最后说“汉升”。汉文文书中暂时找不到“汉升”一词,因为“汉升”实际就是汉文文书中的“升”。用在古藏文文书中的“汉升”(rgya bre),就是要与“蕃升”(bre)相区别,因为后者实际上是汉制的一斗。引文如下:
IOL Tib J 0850《吐蕃酉年(829±)春宋三娘借杂物契》:
1-3、酉年春,军士(rgod)令狐林六(ling ho ling lu)之妻宋三娘(song sam nyang),与令狐什比(ling ho shib bir)的一名女佣布显(bevu zhan)联系签约,从什比(shib bir)处借用四个瓷碗、三枚记帐牌,以及用于织布的线团半斤。
3-4、归还期限,不晚于戌年春三月初五日,应送到令孤什比家门口。
4-6、如未按时归还,数量将翻倍,不管其家中的大麦、铜具(zangs spyad),或瓷碗等,即便悉数夺走, 也不得有任何怨言。
6-8、再者,棉布三尺半、大麦四汉升(rgya bre),以门锁及钥匙为抵押,必须在戌年春二月初十日以前赎回。
8、如不按时赎回,门锁和〔钥匙〕将一同被没收。
8-11、作为见人,附张古古 (cang gu gu)、罗来乐(la legs lod)、高张功(khevu bzang gong)〔…〕等人的印鉴,以及宋三娘及其丈夫令狐林六的签字画押,宋三娘的指印。
12a(倒写:)丈夫令孤林六签名。
12b(倒写:)〔高〕张功(见人)签名。
12c(倒写:)宋三娘指印。(31)Tsuguhito Takeuchi,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pp.191-193;杨铭、杨公卫译《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第202-205页。
P.t. 1118《吐蕃申年水磨费等杂据》:
1-2 申年孟夏四月十四日,神殿安国寺水磨,由张龚子、周林林二人看守。
2-4先后向安国寺之张法律交付水磨费,粮数为:仲夏五月初青稞三汉硕(rgya sheg)又两汉升(rgya bre),交张法律。
4-6户差青稞六汉升(rgya bre),交付东归之张师。众比丘在安保沟油房榨油应付费青稞四汉升(rgya bre),比丘们已交,水磨费结清,交付保沟。
6-7夏季六月……日,建成贾公之亭子,举行庆典,小米三驮 (khal),交与张法律。
8-9 ……九日,潘师舅有青稞六汉硕(rgya sheg),交作酥供之顺缘。酥供之……原料、小米二汉升(rgya bre),交与师舅和义娘。
9-11家中用粮,先后……为酥供庆典备办水果葭昆果,用青稞三汉升(rgya bre)。牧羊人蔡巴青稞……二……
(背面)
1 仲夏五月,小米两汉升(rgya bre),交与张法律。之后,潘成玛又交小米五汉升(rgya bre)。
2 大路修毕向沙弥色尔师交占田地费青稞五汉升(rgya bre)。(32)郑炳林、黄维忠主编《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社会经济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63-65页。
综上,本节通过对敦煌汉藏文书的分析,结论就是:一汉斗 = 一蕃升 = 十汉升 。
结语
综上所述,从藏文文书记载的量制词汇出发,结合同期汉文文书的记载,经过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1驮(khal,又称蕃[番]驮)= 2汉驮(rgya khal,又称小驮)= 2汉硕
1汉硕(rgya sheg)= 1硕(石)= 10汉斗
1蕃升(bre)= 1汉斗 = 10汉升(rgya bre)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结论充分考虑了吐蕃统治时期蕃汉双语同时使用的背景。由于统治当局强调吐蕃语为官方使用语言,所以在官府文书中一般不会出现“蕃驮”或“番驮”等用语,而只会出现在民间文书中。同样,在敦煌吐蕃文书中,一般也不会出现用“蕃”(bod)来修饰khal“驮”、bre“升”的情况,只是在某种情形下用rgya (汉)来修饰 khal、bre,以便与蕃制相区别。
如此,我们就能理解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文书为什么会出现“番驮”“蕃驮”与“驮”等不同的写法,原来这是由于上述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书写背景不一致造成的。所以,“番驮”“蕃驮”其与“汉石”或“汉硕”的换算关系,应该放到具体的文书中去分析。换句话讲,如果在某件文书中一驮等于二十斗,这个“驮”就是“蕃驮”,这个斗的就是“汉斗”,而不会是“蕃斗”。到归义军时期,文书中出现的一驮等于一石即十斗,这个驮就已经是汉驮了。

敦煌汉文文书中有关“汉硕(石)”的文献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