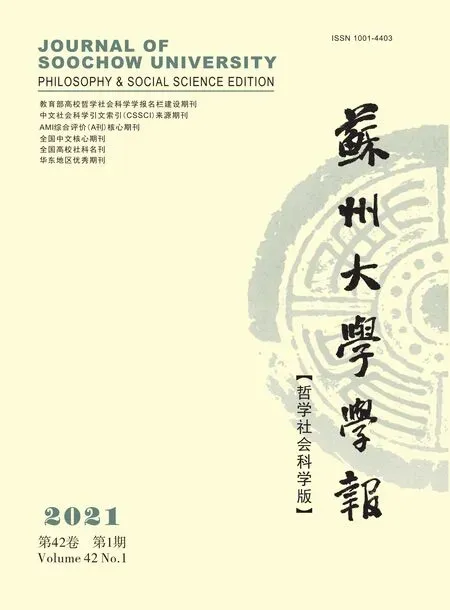陈继儒《建文史待》之编纂及流传索隐
陈广宏
(复旦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 200433)
有关“建文革除”的敦复以及“靖难”遗臣的昭雪、抚恤,在万历间日益成为士林公论的热点,陈继儒《建文史待》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别史类著作。陈氏作为晚明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名士,富于著述,所作往往得以即时刊传,甚至当时或稍后的私人刻书业还有冒托其名的商业出版物不时推出。他名下的众多真伪之作,至今几乎皆有留存,唯独一部重要史纂《建文史待》难觅踪影,这不能不让人颇生疑窦。由此一问题出发,本文拟重新梳理陈氏该著的编纂与流传过程,在试图解答其存佚与否的同时,亦藉以观照这个时代书籍编刊的新动向及建文政治事件的社会化传播。
一
先来看明清重要公私藏书目于《建文史待》的相关著录。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五“别史类”,在著录一系列建文史著中,列“陈继儒《建文史待》”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之后,仅有作者项及书名项,倒是在屠著目下注曰:“万历甲申,叔方为监察御史,尝上疏请祠谥建文仗节诸臣,恤录其子孙,免诸姻党之波及谪戍者。得俞旨。归田后,复辑成是书。首为编年,次为列传,而以传疑、定论附之。是为序。”再下依次为“朱鹭《建文书法儗》四卷(《拥絮迂谈》附)”、“陈仁锡《壬午书》二卷”、“钱士升《逊国逸书》(辑《致身录》《从亡随笔》《拊膝录》,皆伪书)”等(吴校杭钞本)。
万斯同《明史》卷一三四《艺文二》,著录次第及注基本同《千顷堂书目》,唯无“钱士升《逊国逸书》”及“刘琳《拊膝录》”条,其理由可见于该志“史仲彬《致身录》一卷”条下注曰:“钱谦益辨其为伪作,别有程济《从亡随笔》一卷、刘琳《拊膝录》四卷,皆伪书。钱士升辑为《逊国逸书》,不录。”(清钞本)
张廷玉《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著录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朱鹭《建文书法儗》四卷、陈仁锡《壬午书》二卷等,而无陈继儒《建文史待》。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按其体例,将著录书与存目书提要分列,前述《建文朝野汇编》《建文史待》《逊国逸书》《建文书法儗》等均被列入卷五十四史部十“杂史类存目三”,建文史著与其他专题的杂史亦被混编一处。就建文史这一类著述而言,其排列次第显然有所变化,先后为《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建文书法儗》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逊国君记钞》一卷、《臣事钞》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逊国逸书》七卷(内府藏本)、《建文史待》无卷数(内府藏本)、《逊国正气纪》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建文史待》目下叙曰:“明陈继儒撰。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事迹具《明史·隐逸传》。是书乃所辑建文事迹。前列引用书凡一百二十六种。首为逊国编年,次报国列传,次有官职而姓名无考者四人,次有姓名而官职无考者七人,次隐遁十五人,次宫阃十五人。末附以建文传疑,则逊国出亡之说也。”(武英殿本)
嵇璜《续通志》卷一百五十八“艺文略”据《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存目载记,故先后次第全同。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三“经籍考”略有调整,钱士升《南宗书》六十卷、《逊国逸书》七卷著录为一条,而移至《建文书法儗》五卷前,无郑晓《逊国君记钞》一卷、《臣事钞》六卷。

康熙十八年(1679)开馆修《明史》,万斯同主其事,黄虞稷亦入史馆,所分纂《明史·艺文志稿》,即在《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基础上完成。③(3)③可参看张云:《从〈千顷堂书目〉到〈明史艺文志〉》,山东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郑杰文教授。故该本著录及次第自然大抵相同。此处删却“钱士升《逊国逸书》”及“刘琳《拊膝录》”等,是既已知其为伪作或据诸伪作辑录,注明不录,无非循其实而已。至于张廷玉进呈《明史》,《艺文志》部分乃是在王鸿绪删改黄氏《艺文志稿》本的基础上调整成稿,陈继儒《建文史待》被删却,当是如卢文弨所指出的:“史于书不甚著,及无卷数者,俱削之。”[3]卷七
四库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其自家体例,然不可否认,《建文史待》一旦被与《建文朝野汇编》分隔开来,恐遂让人无从体察《千顷堂书目》将屠著与陈著并列著录的用意。朱鹭《建文书法儗》列于《建文史待》之前,无论从“其书作于万历乙未诏复革除年号之时”④(4)④《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四史部十《建文书法儗》条。又,《建文书法儗》卷首钦叔阳序谓:“万历甲午冬,吴诸生臣朱鹭辑《建文书法儗》成,以属臣序,臣未遑也。明年乙未秋九月,上俞言官请复建文年号,中外欢颂明圣,臣更念鹭子言信而志行矣。”(《建文朝野汇编》始纂于万历乙未,详下),还是作者生年,或尚有其理由;然《逊国逸书》“前有崇祯甲申自序”,钱士升年龄又小陈继儒十七岁,何以置于《建文史待》之前,颇令人不明所以。《建文史待》所著录“内府藏本”,应该不是刻本,故无卷数,其被列于钱士升《逊国逸书》之后,或可理解为被归入崇祯年代甚或鼎革之后⑤(5)⑤《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四史部十所著录《建文史待》前、《逊国逸书》后有“《守麋纪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高斗枢撰。该著乃高氏于国亡后遁归故里,追述崇祯辛巳(1641)后守御郧阳两载免于寇难之事。,然是因陈继儒崇祯年间尚在世或其著述如《陈眉公先生全集》编刊于崇祯间,抑或朝廷搜访民间遗书采进《建文史待》稿钞本或抄存之事发生于崇祯甚或鼎革之后,亦已不得而知。
欲印证《建文史待》与《建文朝野汇编》之关系,我们尚可从二书的内容构成来加以比对。上引《千顷堂书目》“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下简注曰:“首为编年,次为列传,而以传疑、定论附之。”《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稍详,曰:“明屠叔方撰。叔方,秀水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书分‘逊国编年’‘报国列传’‘建文传纪’‘建文定论’诸目,盖杂采野史传闻之说,裒合成编。大抵沿袭讹传,不为信史。至摭《典故辑遗》之谬说,谓宣宗为惠帝之子,尤无忌惮矣。”该著明万历二十六年序刊本今存,故可获得更多相关信息。其卷首屠、陈二序后,列《书目》一百三十二种,为所征引朝野撰著建文君臣遗事之史志、笔记、文集及档案资料等。卷一至卷六为《逊国编年》,“凡朝政日系月,月系岁,令次第可考”[4]卷首屠叔方序,细目分别作“建文即位始末”“己卯建文元年正月至七月”“己卯建文元年八月至十二月,革除称洪武三十二年”“庚辰建文二年,革除称洪武三十三年”“辛巳建文三年,革除称洪武三十四年”“壬午建文四年,革除称洪武三十五年”。卷七至卷十八为《报国列传》,所谓“臣义绝者削不书,死与去者则书之,而《宫阃》亦附焉”(卷首屠序),旨在表彰忠义,分别列翰林院七人、国子监一人、吏部一人、礼部三人、兵部三人、刑部四人、户部四人、都察院六人、大理寺五人、太常寺四人、六科四人、十三道九人、中书科五人、行人司一人、宗人府一人、钦天监一人、布政司二人、按察司六人、府十人、州一人、县九人、学官三人、进士二人、举人一人、生员十三人、王府八人、公一人、侯一人、驸马二人、都督七人、都指挥二十人、指挥十二人、卫所九人、内官一人、皂隶一人、有官职而姓名无考四人、有姓名而官职无考七人、隐遁十六人、宫阃十五人。卷十九为《建文传疑》,所谓“闻见相沿而是非真讹复相半者”(卷首屠序),包括“建文君或云自焚,或云出亡,或云出而复归,其所作诗,皆不知真伪,附会传疑;诸臣生死心迹有可疑者,亦附于后”[4]卷一九《建文传疑》。最后一卷为《建文定论》,所谓“列圣之诏旨与诸臣之章疏,业已凿凿见诸施行而事始大著白矣”(卷首屠序),收录与建文君臣相关的诸帝诏令及大臣所上奏疏,包括屠叔方万历十二年之上疏、圣旨批复及礼、兵部覆议等。
《建文史待》虽不获见,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四史部十“杂史类存目三”著录已如前引,所述“前列引用书凡一百二十六种。首为‘逊国编年’,次‘报国列传’,次有官职而姓名无考者四人,次有姓名而官职无考者七人,次隐遁十五人,次宫阃十五人。末附以‘建文传疑’,则逊国出亡之说也”,尚可窥其鳞爪。对照上举《建文朝野汇编》卷七至卷十八《报国列传》详列翰林院以下各官职死与去者人数,此处“次‘报国列传’”与“次有官职而姓名无考者四人”之间,明显文字有所跳脱而未全。按陈继儒《史翰林〈致身录〉序》:“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殉国编年’;曰‘报国列传’;曰‘定论’,如请复庙号,请补《实录》,请宥忠臣子孙还籍是也;曰‘传疑’,如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1]卷四知其所纂原有“定论”部分,所记具体内容“如请复庙号,请补《实录》,请宥忠臣子孙还籍”等皆见于《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建文定论”;而“建文传疑”部分所记显然亦同于《建文朝野汇编》。
依据以上所述板块构成、名目及相关细节,二著颇相印合,应可证其同出一手。至于陈氏自述其《建文史待》时,“定论”先于“传疑”,是否是该本与刊传之《建文朝野汇编》之差异,并不易判定,毕竟该本未分卷数;而四库馆臣述《建文史待》卷前列引用书数与《建文朝野汇编》略有出入,所记“报国列传”中隐遁者人数似亦有一人之差,究竟是统计的问题,还是二本实然的差异,亦难辨清。
二
就陈氏《建文史待》或屠氏《建文朝野汇编》的编纂过程而言,还是有不少材料可供还原的。
据屠叔方万历戊戌(1598)序,述己不惮缀琐、出入史志、检证求理,“如是者三年,而此书始成”,知其编纂当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上举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万历二十四年丙申谱显示的关键信息:“五月,赴馆南湖,纂《建文史待》成。”[1]卷首表明编纂活动在嘉兴,且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已纂成。所赴之馆,《年谱》万历二十三年乙未谱有交代:“嘉禾包学宪瑞溪公延迪鸿逵、鹤龄二孙,同事者如御泠钱公、怀槎沈公、玄海项公、昭自钱公、沈白生昆仲,后先皆巍科上衮,极一时之盛。”知陈继儒是年始乃赴嘉兴名宦包柽芳家坐馆①(6)①包柽芳,字子柳,号瑞溪,嘉兴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刑部主事、贵州提学使、吏部郎中。传见陈继儒撰《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志铭》(《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五)。,时年三十八岁,为包氏孙鸿逵、鹤龄兄弟授业,同时陪读的尚有钱士升、沈道原、项鼎铉、钱士晋及沈孚先、德先兄弟诸名公。①(7)①包鸿逵,字仪甫,号振瑞,浙江秀水籍,华亭人。万历庚戌进士,授湘潭知县,升吏科给事中。传见张弘道《明三元考》卷十四“万历三十七年己酉科解元”(明刻本)。钱士升,字抑之,号御泠,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以殿试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历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传见万斯同《明史》卷三五六(清钞本)、《嘉禾征献录》卷一(清钞本)。沈道原,号淮槎(一作怀槎),嘉善人。万历甲午举人,乙未进士,授乐安令。甲辰司教松江,升国学,寻转工部主事、兵部职方,随改吏部。夙有文名,而尤长于四六。传见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五(明天启刻本)。项鼎铉,字孟璜,号扈虚,秀水人。万历丁酉举人,辛未进士,选庶吉士。著有《实录纪异》《呼桓日记》《学易堂笔记》等。传见《嘉禾征献录》卷五。钱士晋,字康侯,号昭自,士升弟。万历庚子举人,癸丑进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历官至右佥都御史。传见《嘉禾征献录》卷一。沈孚先,字白生,万历丁酉举人,戊戌进士,授应天府教授,升国子助教,转工部主事,改吏部,升验封司郎中。著有《尚白斋诗文稿》等。兄沈德先,字天生,万历己酉顺天中式,上海教谕,国子学录,转桂藩审理,升刑部河南司主事。传见《嘉禾征献录》卷十二。吴郡许重熙为钱士升所编《赐余堂年谱》万历乙未二十三年谱亦有述:“公年二十一,偕弟读书于郡南湖包氏园中,与陈仲醇继儒辈以文章道义相切劘……”其下注曰:“仲醇作《忠所公行状》,有‘往岁乙未,余读书檇李包氏园中,因得与抑之游,又善康侯。’”[5]附录《年谱》万历二十四年冬日别后,包氏卒②(8)②陈继儒翌年作《祭包瑞溪学宪》(《陈眉公先生全集》卷四十六)、《包学宪墓表》(《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七)。,陈氏在嘉兴的坐馆便告结束。如此则时间上恰好吻合。
陈继儒自二十九岁焚弃青衿后,一方面四处坐馆治生,如他此次赴嘉兴任西席,所结交包、钱、项、沈诸氏,皆当地名望不说,授业极富成效,如包鸿逵举万历三十七年顺天乡试解元、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进士,钱士升举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状元,其他如沈道原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项鼎铉中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钱士晋中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沈孚先中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真可谓“极一时之盛”,自然声名大振;另一方面则与私人刻书业合纵连横,开启了操觚编书模式,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短短六七年间,陈氏先后纂辑而成《香牍案》《辟寒部》《太平清话》《虎荟》《逸民史》《元史隐逸补》《读书十六观》《见闻录》《读书镜》等作,当然,其中也包括《建文史待》。万历二十九年,刻《逸民史》于新都吴氏;万历三十一年,刻《品外录》于娄江。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成《宝颜堂秘笈·正集》(其中宋周密《烟云过眼录》署“华亭陈继儒仲醇父订”,明屠隆《娑罗馆逸稿》署“华亭陈继儒仲醇校”),刻成《宝颜堂秘笈·眉公杂著》(收录《太平清话》等共十五种47卷)。而据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万历二十三年乙未谱:“时付《秘笈》于梨枣。”知如《眉公杂著》等,于陈继儒此次赴嘉兴已酝酿付梓,而沈孚先兄弟、姚士粦等众多当地士人皆与其事。
屠叔方,字宗直,嘉兴秀水籍,右春坊右谕德兼侍读屠应埈子。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鄱阳令,官至监察御史。其时屠氏致力于推进建文靖难诸臣的谥祠、抚恤之事。万历十一年(1583),擢广东道御史,次年即上疏,“以建文仗节诸臣请谥请祠,请修治冢墓,请恤录子孙,而交游姻党之波及以世世编戍者,请一体赦宥”[4]卷首屠叔方序。自成祖“革除”建文年号,党禁严迫;仁宗继位,已有松动,如恩宥所谓“奸恶外亲”发各处卫充军者,止留一个在一卫③(9)③“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丁巳,仁宗皇帝即位。十月三十日,兵部官于奉天门奉圣旨:比先奸恶外亲发各处卫分见丁充军的,只留一个壮丁在一卫当军,其余发别卫分当军的都放回去,为民当差,听补军役。钦此。”(《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复谕群臣: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4]卷二〇,然实际执行或为不力。之后,代有要求恢复建文忠臣名誉等呼声。至隆庆六年七月,神宗即位诏曰:“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朕今仰圣祖遗意,褒表忠魂,激励臣节,诏书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诸臣生长乡邑,或特为建祠,或即附本处名贤忠节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尚有存者,厚加恤录。”[4]卷二〇是历来官家最为积极的表态。尽管如此,仍恩不及外亲。故屠叔方万历十二年(1584)上疏,于建文仗节诸臣请谥祠及恤录子孙外,有请推恩赦宥“交游姻党之波及以世世编戍者”。他针对永乐朝左副都御史陈瑛穷治外亲、全家抄解、祸延族党、锻炼成狱之酷,进言称“忠臣既沐建祠,交游至今远戍;苗裔已蒙卹录,姻党犹蔽覆盆”,认为“外亲遗裔犹在戍籍,实为圣世之缺典也”。疏上,奉圣旨下部议覆。而其效颇著,据《明通鉴》所记合计数:“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得免者,凡三千余人。”[6]卷六八“万历十二年二月己酉”
万历十八年(1590),屠氏出任山东兵备副使,致政归。恰在万历二十二年,礼部尚书陈于陛奏请修本朝正史,神宗遂命王锡爵为总裁,陈于陛、沈一贯、冯琦、余继登为副总裁。此亦为建文史的编撰提供了契机,诸臣纷纷以恢复建文年号、改正《实录》为请。如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建言“累朝缺典,究竟难湮,乞圣明及时修举”,“奏建文年号不宜革除,见在修史,乞赐允行”;御史牛应元所奏略同。①(10)①以上并见《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余继登《修史疏二》曰:“臣窃即帝纪而言,……不可不自为一纪者,建文君是已。”[7]卷一焦竑《修史条陈四事议》首条亦以国朝《实录》建文无专纪为当议[8]卷五。结果经神宗折衷斟定,“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9]卷四“让皇帝”十五《靖难事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屠序谓自己“跧伏田野,无所报称,因檃栝建文君臣遗事,以竟初志”。
从屠氏在万历十二年所上奏疏慨叹“奸恶外亲一例,独为陈瑛所蔽,故史传志记略而不书,海内儒生多不及考,抑郁二百年”[4]卷二〇,从《建文朝野汇编》“建文定论”特别著录建文忠臣胡闰外亲见存与死绝之详情,胡闰乃鄱阳人,“叔方宰其邑知之,不胜感怆”[10]卷一八七“屠叔方”,我们大概可以猜测,编纂这样一部建文史著的动议当是屠氏所发,盖与之前任监察御史上疏之事构成某种因果链,陈继儒恰好因坐馆于嘉兴的机会,得以为赋闲家居的屠叔方操觚,其编纂亦可谓基于屠氏的立场,故陈梦莲《年谱》记其父“因屠侍御叔芳题请革除诸公,逊其署名”,所言不虚,着眼的是政治时局上的使命。
于陈继儒而言,如其《建文朝野汇编序》所言:“余少读史,至革除之际,不数行辄涕洟不禁。”[4]卷首陈继儒序有关建文君臣的叙事,早就是士林显示忠义是非的试金石。据说隆庆二年,焦竑于茅山偶得史仲彬《致身录》(见万历己未刻本焦竑序),引发文人士夫搜集纂辑野史逸篇的热忱,陈继儒自己其后亦尝为《致身录》撰序。随之而来的,还有搜寻靖难忠臣遗属之举。方孝孺作为靖难忠臣的一面旗帜,其后人的踪迹尤为人所关注。自郑晓《吾学编·建文逊国臣记》羼入魏泽藏护方氏幼子的叙事,隆庆间便有人自托方氏遗裔,陈继儒周围,如前辈友人王世贞尝为之鼓吹,撰《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姓记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九)等,有关魏泽藏方氏幼子之说及王世贞上文,《建文朝野汇编》卷七皆有引述;万历三十七年,督学杨廷筠嘱松江知府张九德等建表忠书院祀方孝孺及其忠友,为云间一时盛事,董其昌、陈继儒皆尝为撰《求忠书院记》(《容台集》文集卷四,《陈眉公集》卷九)。此段方氏遗裔公案虽至清初史家方始澄清,却毕竟可从一个侧面观照当时士人的心态及舆论走向。
缘于所扮角色,陈氏《建文朝野汇编序》虽仅言“予为参互校订”,然其借屠序之口谓:“凡国家之掌故,郡县之记牒,以及山经地志,崖镌冢刻之属,或检一事而反复他篇,或核一人而流连竟帙,或重复以证其迹之同,或互见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书始成。”表明其搜辑检证建文朝野史料之认真、艰辛,唯所谓“三年而此书始成”,实编纂集中在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上半年,后一年半当就屠氏家族倾注心力在刊印上言。不少书志注意到《建文朝野汇编》明刻本诸卷末多有“嘉善曹承宗写”字样,显示该著在嘉兴地区付梓,该书卷末姚士粦《跋》:“粦与令子昆季分刀削,亦得为此编忠臣。”同样可以为证。②(11)②“姚士粦,字祥叔,海盐人。……与华亭陈继儒、侯官曹学佺、同里胡震亨以奥博相尚,搜讨秦汉以来遗文秘简,撰秘册汇函跋尾,一一考据,具有原委,例补国子生。冯梦祯为南祭酒,校刻二十一史,属士粦校定。年九十余卒。有《蒙吉堂诗集》四卷、《见只编》《后梁春秋》《北魏春秋》《海盐图经》等书。”(盛枫《嘉禾征献录》卷四十六,清钞本)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二十五“山东副使屠宗直叔方”载:“方子五人:泰、观、兑、福征、寿胤,俱有才名。”(明天启刻本)又,盛枫《嘉禾征献录》卷七“屠叔方”传附曰:“少子弘胤,崇祯壬午举人。”
陈继儒本人于《建文史待》一书还颇为看重,在私下的场合面对交游,似并不避言己所编著事。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尝记曰:“(万历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早入城晤陈仲淳,谢生腾蛟来会。仲淳出著述《元隐逸传补》《建文史待》二书,甚有益于世。”③(12)③陈继儒万历戊戌五月初八日撰《元史隐逸补序》:“悉取二十一史之长篇,旁猎孝义、文学、方技之有隐德者,裒为陈氏《逸民史》。既成,二十卷中惟《元史·隐逸传》寥寥若而人,……余以是搜讨传志,不忍笔削其文,悉为网罗,曰《元史隐逸补》。”[11]卷一三
三
从目前能检得的相关材料来看,陈继儒《建文史待》并未获得些许传播,只除了清嘉庆间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著录黄佐《遗事节本》六卷(借月山房汇钞本)时,批评“是书则殊无可取”,“盖明自中叶以后好谈逊国时事”,列举包括《建文朝野汇编》《建文书法儗》《逊国逸史》及《建文史待》等在内一长串书目,谓“其书虽存,等诸自郐以下可也”[12]卷一九史部五。因只是提及《建文史待》,并非收书,或即从书目到书目,亦未可知。倒是《建文朝野汇编》,于万历二十六年梓行,毕竟得以在社会上流通,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关建文史的搜辑、撰著,在万历以来士林中方兴未艾,其势正盛。故其时如朱鹭《建文书法儗》(不分卷,万历乙卯焦竑序刻本),亦志在补国史之缺,仿朱熹《通鉴纲目》,叙纪事之例,其附编录明人相关论述,已将《建文朝野汇编》二序辑为屠叔方《朝野汇编序略》、陈继儒《又序略》收入。郭良翰纂《问奇类林》三十五卷、《续问奇类林》三十卷,是一种类书,所编资料多关乎明代人物轶事、典章制度、学问著述等,其中尝引《建文朝野汇编》载《传信录》所纪宣宗幼时成祖谕牵衣求食一节而加以议论,并谓“由此观之,改正建文年号、补给死事谥典,真今制作首务,尤恶可缓云”[13]卷二一“报应”。至于李乐《续见闻杂纪》中标明采《建文朝野汇编》所载而列“报国诸臣姓名”,“庶使后学一览而易知改革之际豪杰忠贤不约而奋起如此”[14]卷一〇。李乐亦专门关注建文忠臣事,当初举隆庆二年进士,得授江西新淦知县,所著尚有《金川纪事》,当即与练子宁殉难及李梦阳建金川书院祀之事相关。朱荃宰《文通》(明天启刻本)乃汇编类文话,所论皆关著述,卷二十七“大明史材”,列各类明史著述二百六十余种,其中便有《建文汇编》。
仁和卓发之乃江南名士,其族祖卓敬在成祖即位后不屈死,株连三族,其后人遂冒姓宋,凡七世而始复卓姓。①(13)①参详卓发之《卓氏遗书序》,《漉篱集》卷十;《家传一》,《漉篱集》卷十二(明崇祯传经堂刻本)。这样的家族经历令人感慨,王世贞、王世懋兄弟曾分别为其祖父卓贤撰《恩例冠带卓见斋墓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二五)、《见斋卓君传》(《王奉常集》卷十六)。至于他本人,如启、祯之际由南礼部右侍郎升任礼部左侍郎掌翰林院察典的李孙宸,当尝嘱其留心建文史事,故其与书李氏曰:“《建文汇编》已觅得一部,向日命检国史纪年一事,已载是书末简,维庙号祫祭之典、易名录裔之旨,尚未举行,此一代不朽盛事,留待名世大臣起而昌言之,以光耀靑史、润色鸿业耳。”[15]卷二二《与李小湾宗伯》同样能印证《建文朝野汇编》一书的传播与效用。
华亭人王廷宰补嘉兴诸生,以贡任六安教谕,迁沅江知县,他也是《致身录》的热心刊传者,刻有该著泰昌庚申本。其《致身录纂注跋》曰:“友人屠庚朏之先御史冲阳公刻《建文朝野汇编》,意在传疑,迄无删定。庚朏尝欲与宰删其复者而未果,会宰得《致身录》抄本,即语庚朏:当以是为正。因示以纂注,庚朏首肯之,然未敢出也。而谭梁生得是书于史之后亦玄,遂刻行之。史自有刻,陈眉公尝为之序,梁生以宰注为可传,劝宰刻行,因记其颠末如此。时崇祯庚午八月望前一日,廷宰识。”[16]卷下洪熙九年“夏,师与程济适吴江访史仲彬之子晟”条注所叙《致身录》在启、祯间诸刻始末,至少显示嘉兴-华亭这一地域交游圈中,人们关注建文史述的热度未曾稍减。这里提到的屠庚朏,又见于《(崇祯)嘉兴县志》卷五“古迹”录沈思孝(字纯父)《屠庚朏以余诗勒石移置三过堂再叠前韵》诸诗②(14)② 所录依次为沈思孝《春日同诸名胜访三过堂感今念昔怅然有作》、姚士粦《三过堂奉次纯父先生韵》、陈懋仁《和沈司马访东坡三过堂》、项利侯《三过堂和沈司马韵》、屠兑《三过堂次纯父先生韵》,沈思孝《诸名胜见和复此答之叠前韵》、项利侯《沈司马答和什即用前韵再次》、屠兑勒石以记之万历庚戌上巳日题识,沈思孝《屠庚朏以余诗勒石移置三过堂再叠前韵》、项利侯《和纯父先生移诗碣置三过堂之作次韵》(明崇祯十年刻本)。三过堂碑今尚残存,参详《嘉兴历代碑刻集》,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292页。,则屠庚朏当即屠兑,屠叔方第三子,勒石所纪乃万历间嘉兴诸世家名士游三过堂嘉会次韵酬和之作。由此我们还得以见证姚士粦与屠叔方之子的交往。王廷宰谓与屠兑有删定《建文朝野汇编》之想,结果转而从事《致身录》纂注,不管是否真获屠兑首肯,他们之间具有比较近密的关系似可肯定。谭梁生即谭贞默,嘉兴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有意思的是,屠叔方父屠应埈在顾节墩的别业怡园,后即为谭氏所居,更名笈园,亦曰研山书圃。史之后亦玄,当即史兆斗,吴江人,为史仲彬九世孙,《致身录》应为其托名于先祖,述史仲彬以侍书随建文帝出亡事。谭贞默梓《致身录》为崇祯戊辰刻本,而史兆斗自刻为天启刻本,陈继儒《史翰林〈致身录〉序》当为是本所作。史兆斗嗜藏书,又尝为其祖史鉴及圈中不少名士刻集,陈继儒《陈眉公集》十七卷即其万历四十三年所刊。显然,处身于这样一个当事人几乎都在的朋友圈中,王廷宰应可算是知情者,而他对于已刊行的《建文朝野汇编》作者的表述,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随着钱谦益等人力辨《致身录》诸书及建文帝出亡之说为伪①,清初以来,此类著述非信史的看法越来越占上风,参与《明史》修纂、同为吴江人的潘耒,在与徐釚论辩的信中,曾举包括《建文朝野汇编》在内专纪建文逊国事的著述不见有史仲彬为例,反对史氏后裔乞以仲彬入祀乡贤。[18]卷五《再与徐虹亭书》而至四库馆臣,对像《建文朝野汇编》这样的史著亦批其“大抵沿袭讹传,不为信史”[19]卷五四史部十,所举证一例,即其卷十九“建文传疑”中采《传信录》之说,谓宣宗为惠帝之子。此自为谬误无疑,然由是定调,便是对该书乃至该类著述整体的否定性评价,在那个时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鼎革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前朝史事的热衷日益减退,毕竟时过境迁,士林有本朝需关注的新的热点。在这种情形下,《建文朝野汇编》在清代未见重刊,偶有被提到的,亦无非拾四库馆臣之牙慧,如晚清学人蒋超伯在其《南漘楛语》中讥评明人“横议最多,略无忌讳”[20]卷六“横议”,便重提宣宗为惠帝之子旧例,顺手戳了《建文朝野汇编》一枪。至清末民初,士林重新关注明史,如刘承幹《明史例案》考练子宁事迹,还会提及“《建文汇编》引《革朝遗忠录》与《金声玉振集》《表忠录》《备遗集》《逊国记》《群忠事略》等书,只言‘不屈,族诛’”[21]卷三。
以上费不小之篇幅,梳理了陈继儒《建文史待》及与之相关的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的编纂、流传情形,讨论的重点,看似常落在屠氏《建文朝野汇编》一侧,却并非有意要偏离主题。因为政治大局之需要,陈继儒在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间为屠叔方编纂了这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建文史著,而又逊让署名权,结果该书以屠氏《建文朝野汇编》之名于万历二十六年在嘉兴刊行,成为传世之定本被人阅读,陈氏自己则将这部书稿命名为《建文史待》而藏于家,并未付梓。《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建文史待》有内府藏本,应为朝廷搜访民间遗书采进的稿钞本或抄存之物,是作为一个被保存的文本,当非刊本,故无卷数。据现存资料比勘可知,无论已刊之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与陈继儒《建文史待》原稿之间是否有调整,两者应可看作二而一的关系。既然该著以屠氏《建文朝野汇编》之名义流通,传播及影响的一鳞半爪之记录自然便皆在其名下。
①参详钱谦益撰《致身录考》《书致身录考后》,《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