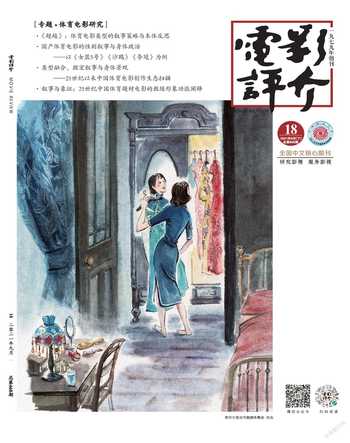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教育多维考索
孙玥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以电影表演教育为主的学校。由于正规教育体系还没有把电影表演教育纳入其中,所以这一时期的电影表演教育多为民间自觉自发行为。按资本构成可以分为三类:民族资本创办的电影表演教育学校、中外合作创办的电影表演教育学校、外国资本创办的电影表演教育学校。虽然这些学校纷纷崛起又纷纷落幕,带有很大程度的投机性、功利性、短视性,但其目的性、针对性、实用性是值得借鉴的。
一、“极多”与“极少”: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教育的两种悖反现象
一方面各影戏学校发布招生广告后,报名投考的人非常踊跃。如民新影戏专门学校登报招生后“来函索章程或报名者日必数十起”[1],大中华影戏学校三日内去函或面索章程者500余起,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函索章程者2000余份,新人演员训练所投考者1500余人,香港中华影戏学校应考者1500人,大陆影戏学校投考者1900余人,中华电影学校欲招收150人,报名投考的人数超过4000。这些现象说明当时社会青年对电影事业的热衷和对电影银幕的向往。这些青年之所以如此狂热,一是由于摩登上海相对开放的风气感染,二是由于电影演员丰厚报酬的吸引。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刚过十余年,中国封建思想仍在,社会风气并未完全开化。大部分舞台演出仍不准男女同班,观众也必须男女分座。彼时影戏仍被看作下等玩意儿受到抵制。1922年3月周剑云在《申报》连载一篇《影戏杂谈》,介绍了反对影戏的人的观点“反对者则谓物质文明与人类道德适成反比例,自有影戏出现而盗风淫风愈益弥漫,盖因影戏取材不外荡检逾闲、打家劫舍,本此原质遂酿成诲盗诲淫之罪恶,要望社会安宁风俗朴厚当自铲除影戏始。”[2]一些封建家庭仍视影戏演员为“戏子”,反对儿女投身影戏事业,尤其女性受到鄙视更甚。民新影片公司成立之初招请演员的广告登了多天,报名的女孩子一个没有。所以初期影戏学校招生时很多学校女生不足,男女比例差距甚大,即使有些女性进入银幕也会受到家庭阻挠或担心自己年老色衰,在演艺的高峰时期嫁人息影。为减少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这一时期影戏学校大多实行男女分班授课,如明星影戏学校“日班专教女学生、夜班专教男学生……女学生下午四点到六点,男学生夜间八点到十点。”[3]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对于女生特兴通融办法,由本校供给膳宿”[4]。
二、宏观与微观: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教育的宗旨与目的
从宏观层面而言,20世纪20年代各电影学校招生简章上,对办学宗旨大多陈义高尚,如大陆影戏学校“以发展中国影戏事业……造就完全无缺之演员,为中国影戏界争人格”[5],民新影戏学校为“提高银幕的艺术,养成国产影戏专门人才”[6]“为中国电影界切实的做一番事业”[7]。这些影戏学校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用振兴民族影业,为民族影业争光相号召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从实际的微观层面而言,这些影戏学校其实都是为了为公司物色漂亮的女演员,选拔配角与训练群众演员,供给本公司或其它公司实际拍片需要的。表面的高尚陈义不过是“以强壮中国影戏事业,以满足有志于影戏事业的青年人梦想的大旗遮盖对学员赤裸裸的盘剥”[8]。
1924年7月26日陈拙民在《申报》发表文章指出“影戏学校影片公司往往因资本不足,欲顾目前之利益起见,故设一影戏学校,名为养成影戏人才,实为彼等利用,公司中不费一文,而能得许多演员。”[9]程步高说“凡电影公司新成立,筹拍新片,要新演员,于是开办学校,以应急需。”[10]尤其到了1927-1928年间,古装武侠神怪片的拍摄需要大量群众演员。1927年2月14日明星影片公司在《申报》刊登广告“本公司筹备多时之古装剧《仪亭》及由大成影片公司委托本公司代理摄制之《王昭君和番》《费宫人刺虎》《狸猫换太子》等剧现已开拍。本公司对于摄制影片向极谨慎。此次古装剧更不愿付流俗,草率将就,故不惜精神财力创一演员养成所,专为古装剧造就相当人才。”[11]其它电影表演教育学校也承担着这样的功能。黎民伟在广州筹拍《胭脂》时创办民新演员养成所,关文清记述“立即开办‘演员养成所’。因为除了主要角色外还需要很多‘特约’和临时演员。”[12]但是临时演员出演电影是有问题的,1927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车迟国唐僧斗法》,需要大量群众演员,但“所拉到的所谓文武百官的演扮者,都是那些失业流氓,或者拉拉黄包车,皮匠,小工,业小贩的杂色人物。用此这般人才来饰演雍容华贵的大人们,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哉。在摄影场中,他们穿起了黄袍,龙袍,戴上了黑纱帽,大摇大摆的一点也不像官儿。”[13]
为了挑选汇聚足够的群众演员,这些学校的招生规模往往很大,如光华影戏专修学校学额一百名,大陆影戏学校定额一百名,中华电影学校额数一百五十名,菩萨电影学校额数二百名……学生边学习边实践,这种造星与使用同时进行的方式,既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有了实践机会,又使电影公司免去了雇佣群众演员的费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各个公司对于群众演员的需要。诚如陈大悲在《演员训练自己的方法》中所说“即使有某一影片公司开办传习所或训练班一类的东西,至多也不过是替影片公司节省雇佣临时演员的一宗开支而已。决没有一个影片公司肯耗费了许多教练费为他家影片公司造就人才的。”[14]
除有演员可用外,各影戏学校还可以收取学费借此赚钱。1924年剑虹在《电影学校的教材问题》一文中说“开设电影学校之人,大半报的是赚钱主义。”[15]明星公司1937年停止运营后张石川为了重振“明星”曾重映《火烧红莲寺》,用《火烧红莲寺》重映赚来的收入筹办演员训练所,筹拍新片。当时报名费每人一元,因为明星公司曾捧出众多红透中国、东南亚的电影明星,因而报名者络绎不绝。明星公司称报名费“取与不取概不发还”,这笔不菲的报名收入招致社会收取“不义之财”的批判,张石川不得已,声明不取者退回报名费。其它一些电影学校也收取学费,如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坤范女子电影学校、新月电影学校、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贝兰电影传习所——美华电影传习所,费用从3元到5元不等。还有些狡猾的牟利者,專门开设电影学校投机骗钱。这显示出20世纪20年代电影表演教育组织者、从业者并不是将电影表演教育事业看作一种社会公利事业,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实行的是商业化的组织运作。
三、招生标准与学生来源
从各学校招生广告的要求来看,准入门槛并不高,一般对考生的年龄、学历、职业、出身均无限制,有些学校如民新影戏专门学校、新月电影学校只要求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历,南洋电影学校要求国文略有根底,有些学校对学生的道德略有要求,如明星影戏学校要求“没有高尚的志愿不必来,不知道(男性)也该守贞操的不必来,不尊重女子人格的不必来,有浮荡底恶习的不必来,曾经有污秽历史,不能忠实的反悔的不必来。”[16]招生标准之所以如此之低的原因如下:一是当时社会普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二是电影被视为低级玩意儿,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大多不愿意屈尊降贵来做电影表演的学员,招生标准提高,生源必然减少;三是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从业者大多也不认为银幕上的演员需要太高的学历。
在表演专业素质方面最初几乎各影戏学校均没有要求,学生都是零基础的,直到1924年中华电影学校招生考试时才开始有对于这方面能力的测验。胡蝶回忆“面试时让我自选动作,在几位主考面前来回走了几次不同的步子表示不同的内心活动。”[17]这样的题目看似随意,但使我们看到了初期电影表演教育创办者已经注重从电影表演的专业角度“内心”挖掘考生的表现力与创造力,同时注重了表演的层次性和丰富性。从考生角度而言,这样的题目并不是“单凭死记硬背就能应付得了的,而非得要有对表演的比较真切的认识和体会才行。”[18]1926年民新影戏专门学校考试新生时涉及了电影表演方面的测试,“徐公美试国文,侯曜试姿态,芳信主试表情。”[19]同年,明星影戏学校入学考试试卷题目也涉及了表演“1.眼睛、嘴、手、脚和身体,你认为何者于演剧为最重要?2.眼睛的表演共有几种?请详细将种数及动作与所表及何种情感一一述出。3.在表演中什么叫单调?什么叫过火?4.述你对于电影事业之态度。”[20]从这些题目的演变来看,有越来越专业化、深入化的倾向,这反映了20年代中期电影表演教育招生考试的选拔标准、对考生专业素质的要求在逐渐提高,考题也越来越具有适应电影表演的针对性。
从地域看,20世紀20年代的电影学校多集中在当时中国电影的重镇上海,虽然北京、天津、广东、香港也有电影学校,但数量较少。上海的电影学校多在《申报》等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以上海生源为主,外省生源为辅,即使外省学生或其它国家学生此时也大多汇聚于上海。除上海外,学员来源较多的地区为广州。洪深1946年在上海《文选》第2期发表的《胡蝶迷》一文列举了广州地区出现电影演员较多的原因。因为广州距离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较远,这里的人们敢于尝试新事物,女性也较为开通,且20世纪20年代的影片均为默片,虽然广东女子讲粤语但并不影响影片效果,只要漂亮就可以。从阶层而言,这一时期各电影学校学习表演的学生大多为城市中下阶层,农村学员较少。这与农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和封建的社会风气有关。而城市中一些出身卑微,为生活所迫的青年,由于有些影戏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拍片还付给报酬,一旦成名演员的收入又很丰厚,所以选择报考。少数家境较富裕的学员则大多出于对电影或演员这一摩登职业的热爱。
四、师资构成及其知识背景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电影表演教师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知识分子或由舞台转入电影行业的业内人士,如郑正秋、郑鹧鸪、任矜苹,另一种是外籍教师或有留美、留法、留日背景的电影精英,如贝兰电影传习所——美亚电影传习所——美华电影传习所和中西影戏学校的外籍教师及汪煦昌、徐琥、洪深、侯曜、沈诰。当时的师资队伍呈现以下特点:(一)兼职教师多,专职教师少。那时中国电影表演教育行业的主要教师如郑正秋、郑鹧鸪、周剑云、洪深、任矜苹、汪煦昌、程步高、徐琥、侯曜都在影片公司担任导演、编剧、制片,在影戏学校教学纯属兼职。如此多的“分身”使他们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必然顾此失彼影响教学。(二)师资构成复杂,流动性强。20年代的教师虽然有专攻摄影、戏剧、化妆的汪煦昌、洪深、沈诰,但“专职表演并具有长期演出经验的教师乏善可陈”[21],有表演教育背景的只有关文清。很多老师“同时担任多所学校的教员乃至负责人”[22],且在各制片公司供职,强流动性必然导致教学团队不稳定,影响教学质量。(三)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储备匮乏。这些教师多为业界从业人员,已经有了初步的电影实践经验。但作为中国电影表演教育的第一批教师,他们大多没有受过电影表演专业教育,也没有前人的经验积累和谆谆教诲,理论储备基本空白,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边做边学,都是无师传授,只靠自学求通。”[23]
五、课程设置、学制安排与教材建设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教育学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电影公司创办的电影学校,如明星影戏学校(明星影片公司)、大中华影戏学校(大中华影片公司)、大陆影戏学校(大陆影片公司)、菩萨电影学校(菩萨电影公司)、坤范女子电影学校(上海乾坤电影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南洋电影学校(上海南洋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民新演员养成所(民新影片公司)、新月电影学校(新月影片公司)、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洋洋影片公司与南洋华侨影片公司)、昆仑电影学会(昆仑影片公司)、美亚电影传习所(中美电影公司)。另一类是私人电影学校,如中华电影学校、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光华电影专修学校、中西影戏学校。从数量而言,以附属于影片公司的学校为主,这种附属性质决定了它们要以制片公司的需求为导向,为公司培养人才。
这些电影学校大部分以表演教育为主,程步高在《影坛忆旧》中说“早期许多男女明星,电影学校出身者不少,不过要学其他部门的学问,此路不通。”[24]这里所指的“其他部门的学问”主要指电影摄影、照明、洗印、剪辑等技术门类。电影公司制片过程中演员的需求量较其它技术门类更大,尤其是女性演员更为缺乏。当时银幕上演员表演存在生硬、夸张、过火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影片在观众中的接受度,演员表演备受诟病,因而对演员的需求更迫切。演员的培养相较于编导等技艺更容易上手,成本较低。编导需要相当的文化基础,而初期中国大部分电影教育学校并不具备培养技术门类所需要的设施设备、师资力量和经验基础,所以不得不抛弃种种不急需的课程,而以演员的培育为主。但也有学校设置技术类课程,有些学校甚至专门设置摄影科,如光华电影专修学校。这些课程的设置要么是为了培养技术人才,要么是为了普及电影常识,以使学生对电影制作有基本的了解。而像远东电影学校、贝兰电影传习所——美亚电影传习所——美华电影传习所、中西影戏学校则更偏重于音乐、舞蹈培训。
经过分析,可以将20年代各电影表演教育学校的课程分为以下几类:(一)表演类,如明星影戏学校的《表演术》《实地训练》《分幕练习》《演剧理论》,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的《表演学》,中华电影学校的《影剧表演之艺术》,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的《表演》,远东电影学校的《电影表演》,中西影戏学校的《演艺》,以电影表演教学为主。(二)编剧类,如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的《编剧学》、中华电影学校的《影剧之取材及其结构》《编制电影之艺术》《西洋近代戏剧史》《影剧概论》《编剧常识》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的《编剧》。(三)摄影类,如明星影戏学校的《摄影术》,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的《摄影学》,中华电影学校的《摄取影剧之艺术》《电影摄影术》《摄影场常识》,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的《摄影》,以电影摄影理论与实践教学为主。(四)导演类,如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的《导演学》、中华电影学校的《导演术》,以导演工作及如何指导演员为教学内容。(五)輔助课程,如明星影戏学校、昌明电影函授学校、中华电影学校、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远东电影学校、中西影戏学校均的《化妆术》《电影化妆》,中华电影学校的《电影行政》《电影原理》,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的《制片》《配景》《美术》,中西影戏学校的《布景服饰》《装璜》。(六)才艺拓展类,如中华电影学校的《舞蹈及歌唱训练》,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的《跳舞》《技击》,远东电影学校的《舞蹈》《音乐》,美亚电影传习所的《跳舞》,中西影戏学校的《梵哑铃》(Violin)、《钢琴》,以唱歌、舞蹈、乐器训练为主。这些影戏学校大多将理论教学与片场实践相结合。有些是在授课过程中实习训练,如明星影戏学校设置了《实地训练》与《分幕练习》。有些是将课程讲授与实习训练分开,如中华电影学校设置3个月学习期,3个月练习期,南洋电影学校在6个月学习毕业后有3个月实习期。有些则在上课过程中让学生参与影片摄制,如中华电影学校“在练习期内,如加入演员之列,本公司亦一律酌给薪水”。[25]
程步高概括了这一时期各影戏学校课程安排方面的特点“缺乏专人主持,粗枝大叶,教些表演方法,讲些拍戏情况,练习电影化妆,了解初步常识。训练三月,即告结业。”[26]凸显了这一时期电影表演教育的强功利性、针对性、商业性、实用性。虽然为了适应电影制片的专业化要求,有些学校在课程设置和培训要求上愈趋周密严肃,如中华电影学校“督促很严,如无故缺席达三次,学校随时可以勒令退学。”[27]总体而言这时期的课程大部分需要迁就拍片需要和师资队伍,并没有教学大纲,更谈不上完善的教学体系,只能有什么教什么,会什么教什么。属于短期职业培训,并非学历教育,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学员毕业后虽然能够对口就业,但进入电影行业后淘汰率较高,成名的较少。
从各学校的修学年限来看普遍较短,大部分学校修业年限在半年以下。如光华电影专修学校原定1年毕业,实际只开办了3个月;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学制3个月,只办了一届便停办;中华电影学校学制6个月,也只办了一届便停办;新月电影学校学制3个月;南洋电影学校学制6个月……除了学制短暂,各学校并不是全天上课,大部分学校每天授课2-3小时,明星影戏学校、中华电影学校、中华影片戏剧研究社每次课都是2小时,光华影戏专修学校每次课3小时。这样计算下来,每期学生实际的上课时长是很少的,对于一门艺术或技术而言,这样的学时学制安排无疑无法保证教学质量,也无法使学生建立系统完整的知识结构,只能学一些电影表演、化妆、制作的基本知识。
教材方面,这一时期专门的电影表演教材非常少。中国电影表演教育初期,教师的讲稿经常被编成讲义发送给学生,他们的讲稿便是初期中国电影教育的教材。这些学校中教材建设最完备的要数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和明星影戏学校。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编写了系统的教材——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其中包含《影戏概论》《编剧学》《摄影学》《导演学》四部分,并不含“表演学”。相反明星影戏学校在表演教材的建设方面较为突出。1924-1925年间明星影片公司的周剑云与凤昔醉将Inez和Helen Klumph合著的好莱坞电影表演教材Screen Acting翻译过来,先后分别以《影戏学》和《银幕上的动作》为题连载于《电影杂志》和《明星特刊》。该书曾在明星影戏学校大力推行,是这一时期少数的专门以表演为内容的教材。明星影戏学校在谷剑尘主持教务后曾以《戏剧的表演术》为讲义,具体内容作者并未找到。但1927年曾有一篇原载于中华第一公司《花国大总统》特刊的《演剧须知》被认为是明星影戏学校的讲义。“作者是谷剑尘。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呼吸和语调声音能帮助随意筋’。”[28]所谓的随意筋指面部肌肉神经组织,认为即使默片演员也应该说台词刺激内心体验,帮助控制面部表情。文章中关于气、动作、语调、声音、肺、腹、呼吸、声带、音调高低的论述与1935年洪深的《电影戏剧表演术》相通。《戏剧的表演术》与《演剧须知》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演剧须知》是《戏剧的表演术》中的一部分,二是两篇均为独立文章,这一点待考。其它电影学校如民新影戏专门学校、新月电影学校、昆仑电影学会虽然有发放讲义的记载,但讲义的具体内容却寻而不得。以上几本教材和文章即是初兴期电影表演教材的基础建设。
六、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表演教育的得失
这些电影表演教育学校并不是有规划的成立的,而是一哄而起的,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功利性、短视性,采用的是“速成”式的职业教育培训。由于没有经验,亦没有前车之鉴,很多学校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很快昙花一现集体消失了。这种集体出现、集体消失的纷乱现象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是商业的混乱和无序,中国电影表演教育并没有上升到专业建设层次,也没有被纳入国家教育规划,而是任由民间办学自生自灭。但民营电影公司或私人资本又不愿意冒险大规模投资,很多学校办学简陋,只是照着其它已有学校的样子照猫画虎,没有进行多元教学模式的探索,只以电影表演教育为主。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也停留在浅显的电影知识普及和电影表演技巧传授方面,上升不到理论层次。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电影企业奋发图强,为了实现民族电影的繁荣,在企业内部进行的这种教育培训和探索,不只“打通了普通人与电影事业的隔阂”[29],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影业发轫时期演员极度匮乏的窘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第一批专业演员。20世纪20年代经历过电影表演教育学校或歌舞团培养的一批学员如王献斋、张织云、胡蝶、徐琴芳、高梨痕、萧英、黎明晖、徐来、王人美、黎莉莉、周璇、薛玲仙、胡笳、马陋芬、白虹、严斐、英茵经过5-6年的银幕实践都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影坛明星。这批明星为后学者树立了榜样,1941年金星影片公司开办金星戏剧电影训练班,曾在《金星特刊》开辟《金星戏剧电影训练班学员文辑》专栏刊登学员的文章。裘萍在《完成我的愿望》中曾坦陈受前辈明星影响。“有时我会学着胡蝶咬着嘴唇微笑,学着阮玲玉一种内心苦怨的激露,学着王人美、黎莉莉她们唱歌跳舞,高兴时我还会替自己化妆成一个女侠,拿着两根木棍学夏佩珍舞剑……”[30]可见,裘萍进入金星戏剧电影训练班学习表演完全是受前辈明星的激励。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表演教育使得中国的电影表演事业向着职业化、专门化、规范化方向发展。这些学员大多没有文明戏表演经验,经过培训后在电影镜头前较少程式化动作和夸张、过火的表演,而偏向于日常化、生活化、真实、自然的表演。各影片公司在电影学校中挖掘有潜力的新人,开始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波“造星”运动。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表演教育的最大突破是电影表演教育观念的诞生和训练机制的转变。徐公美在《演剧术概论》中说“从前他们以为要造就一个演剧人,只消保养他本人的感情就可以成功了。学校中的教育反而要伤及他本能的感情,倒不如不入学校,许可以收成功的期望——这种主张,起初听来似乎很有理由的;其实仔细思考一下,则不但碍于富有经验的演剧人的进步,并且对于初学的人,更足以造成绝大的危险。”[31]借用洪深的话说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表演教育“使得一般人稍为感觉,电影需要学习,也是严肃而不太容易的工作”[32]。这一时期中国的电影教育家们意识到了戏剧表演与电影表演的不同,突破了中国古代“师徒制”的艺术传授方式,开始了近现代专业化、职业化的艺术培训。就规模而言要比以前的戏班子大很多,属于批量式人才培养,实现了电影教育的大众化。他们也注意到了电影表演教育的强实践性,将教学与实习训练结合并使实践与就业紧密勾连。这种强目的性、针对性、商业性是值得借鉴的。这一时期电影表演教育教学与实习训练的设计、对演员培养机制和人才补充机制的初步探索也为中国以后电影表演教育的发展确立了初步规范。
【作者简介】 孙 玥,女,内蒙古赤峰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博士,主要从事电影表演导演艺术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民新影校积极进行[N].申报,1926-05-22.
[2]周剑云.影戏杂谈[N].申报,1922-03-09.
[3]明星影戏学校招生[N].申报,1922-02-19.
[4][16]上海民新影戏专门学校续招女生广告[N].申报,1926-06-04.
[5]大陆影戏学校招收男女学员[N].申报,1924-06-07.
[6]民新影戏学校之发起[N].申报,1926-05-10.
[7]张其琛.风雨之夕——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开学记[ J ].民新特刊:“和平之神”号,1926(2):30.
[8][21][22]刘琨.摩登使命·逐利主义·致命惯习——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戏学校的‘表演’政治[ J ].当代电影,
2017(2):111-116.
[9]申报,1924-07-26.
[10][23][24][26]程步高.影坛忆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133.
[11]明星影片公司设立演员养成所广告[N].申报,1927-02-14.
[12]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M].广角镜出版社,1976:114.
[13][25]马森.记:“临时演员”之家“联合社”:“明星”·“上海”到“联合”,“五角”·“一元”到“二元”[ J ].青青电影,1948(23):2.
[14]演员训练自己的方法[N].申报,1932-11-07.
[15]剑虹.电影学校的教材问题[N].民国日报,1924-12-06.
[17][27]胡蝶,刘惠琴.蝴蝶回忆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4,15.
[18]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69.
[19]民新影戏学校考试新生[N].申报,1926-06-01.
[20]舒平.中国電影之最.见:上海电影史料(2-3合辑)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1993:264.
[28]陈亮.中国本土电影表演观念研究(1905-1937)[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60.
[29]王海洲,周强.中国电影教育发展回顾[ J ].影博·影响,2015(7).
[30]裘萍.金星戏剧电影训练班学员文辑:完成我的愿望[ J ].金星特刊,1941(4):20.
[31]徐公美.演剧术概论[ J ].国闻周报,1924(5).
[32]洪深.胡蝶迷[ J ].文选(上海),1946(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