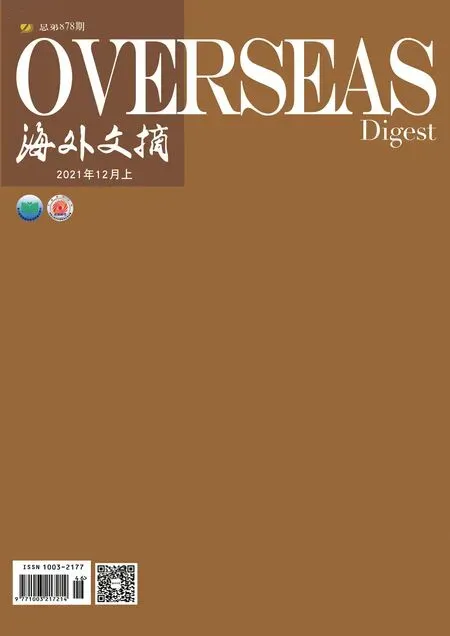中日之“诚”的异同
何姝婧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美国著名日本学家唐纳德·基恩在比较中日文学差异时提到,尽管古代中国有很多日本没有的事物,但日本人还是找到了一个只属于日本而中国没有的东西,这就是“诚”(まこと)。实际上,无论从伦理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美学角度看,中国古典文化中“诚”的概念早已有之,只不过在具体讨论时由于文化背景和发展轨迹的不同,中日之“诚”在相似中又产生了诸多差异。
1 伦理之诚:君子之道与武士之道
现代汉语中的“诚”多与“诚信”“忠诚”等词语相联系。追根溯源,诚、忠、信三个字来源各不相同。信和忠二字出现较早,均最早见于金文,诚字则较这二字出现时间晚,始见于战国文字。在《论语》中多用“信”“谅”表今义中的“诚信”,如“友直,友谅,友多闻”“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在《论语》尚没有提到“诚”这一哲学概念,到《中庸》时,子思将“诚”作为重要的哲学伦理理念提出。《中庸》的“诚”既在本体上被视作是世界的本源:“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同时又在形而下的层面被视为一种道德规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圣人是掌握了“天之道”的至诚之人,普通人则要努力使自己“诚之”,不断努力使自己接近圣人,方能掌握“人之道”。总之,在“诚”提出的早期,“诚”字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即追求真诚的情感与体悟真实的本体”。
孟子继承发展了《中庸》的“诚”的概念即“反身而诚”,通过内心的反省追求诚信的自觉,做到不自欺、不欺人,“诚”也特别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一种道德和伦理准则。宋代程朱理学进一步拔高了“诚”的地位,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达到诚的方法也类似孟子的反身而诚,认为思诚是“自修之首”。可以看出,“诚”发展到程朱理学的时期,“诚”从一个抽象的本体概念向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转变,从强调天之道落实到以诚为标的人之道上,这和唐宋以来的社会变更密不可分,这种对“人之道”的重视呼应了新的社会现状下维持社会和谐的要求。
相较于落实于君子之道的中国之“诚”,日本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诚”更多体现在武士道精神之中。在镰仓幕府时代,程朱理学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到日本,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混乱,为了加强中央权力、维护统治秩序,江户时期的日本统治阶级开始大力推广朱子学。程朱理学本身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为了适应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这种作用在江户时代维护天皇正统地位的要求下也发挥了巨大的功效。原本武士效忠对象仅仅是自己直属的君主,早期的武士道简单的主从道德关系的规定,在朱子学影响下变成以家臣方面忠、义为主的一整套武士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天皇成为了武士的效忠对象,同时武士道从道德行为准则发展成为思想信仰,并广泛地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逐渐成为日本全民道德规范。
尽管发展自朱子学,由于武士道之诚立足于武士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它和“忠义勇武”的武士精神密不可分。1899 年,新渡户稻造出版《武士道》一书,向西方世界传递武士道精神,其中就提到了对于日本人至关重要的“诚”:“没有诚实和信实,礼仪便是一场闹剧和演戏。”在他看来,“诚”是与言语真实分不开的,“诚”就意味着言行合一,武士要信守“武士一言”,说一不二,充分保证自己说话的真实性。菅原道真的和歌中也谈及了诚之道:“心だに誠の道にかなひなば祈らずとても神や守らん(只要从心底遵从“诚之道”,即使不向神灵祈祷,也会获得神灵的保佑)。”可见“诚”为武士的行为提供了合理化的保证。另外,武士道的“诚”与“忠”密不可分。武士对主君绝对忠诚,以正直之心侍奉主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化死亡的死亡观念,这种死亡观在近代以来日本多次侵略战争中都有充分的展示:为了效忠天皇不惜己身“玉碎”。这种对“诚”的变异正是日本民族性的集中体现,也对日本民族精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 美学之诚:“华实之辨”与“修辞立诚”
从美学角度看,中日之“诚”在发展源头上便有各自的不同。正如上文提到的《武士道》之“诚”,新渡户稻造将其解释为言行合一,这与“诚”的日本发源密切相关。在日语原本是没有“诚”这个字的,汉字初传入日本在公元3 世纪至5 世纪左右,这时的日本人借用汉字为本土语言注音,此时的“诚”读作まこと;完全按照中国读音的音读“せい”属于汉音,按推算应该是从唐朝时才传入的。因而讨论日语语境下的“诚”应该跳出字形的限制,回到まこと之上。まこと一词可分为两个部分:ま意即“真”,こと有两个含义,分别是“事”和“言”,因而まこと可视作一种事物和言语的一种主客观真实性的统一。
上古日本没有文字,文化、信仰、历史都是通过口头的传递,这种文化传递方式一直持续到公元3 至5 世纪,这就使得日本民族甚至对语言产生了“言灵信仰”,原本是源于对神的敬畏,随后演化成对语言使用的慎重。“以《万叶集》为代表的的上代文学的特点用一个词概括就是まこと,这个诚其实就是相信语言的力量,不敢有任何欺骗地把真实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言灵信仰体现在文学中,便是作者对文字的重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文学性的自觉追求也在不断深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学虚构与真实之辨。在日语中,まこと除了可以写为“诚”,又可写作“真”和“実(实)”。在《源氏物语》第二十五回《萤》一章中,作者借角色之口对物语创作中的“诚”进行了讨论。如表1 所示,对比原文(古代)、近代、现代三种版本,我们也能看出对“诚”内涵的阐释:

表1 《源氏物语》第二十五回《萤》不同版本对比
其中的まこと(真)即现实生活中的客观真实,而与之相对的“偽り”(伪)被解释为虚构、谎言(嘘う),是一种包含了主体成分在内的文学虚构。源氏先是笑话了玉蔓阅读虚构作品“甘愿受骗”,随后对文学虚构表达了肯定:“这些伪造的故事之中,亦颇有富于情味,描写得委婉曲折的地方,仿佛真有其事。所以虽然明知其为无稽之谈,看了却不由你不动心。”正是因为文学需要主体参与,通过虚构的方式表现主体的情感、意志、追求,才使得文学作品具有高度的审美性,也正是这种审美性才是打动读者之处。另外,文学虚构并不是空中楼阁,总是基于现实创造出来的,“因此欲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则又专选稀世少见的恶事,使两者互相对比。这些都是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文学虚构是一种艺术真实,不同于文学真实,它追求的是一种刻画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真实,于个别中揭示一般性,是一种真实与虚构的统一。因此,诚在这一意义上进一步深化,不再简单的表示言语(文字)与真实的完全呼应,而是一种艺术真实,展现的是“真”与“伪”的统一。
这种艺术真实的讨论在和歌上体现为“华实之辨”。在《日本物哀》中,本居宣长提到,“花(华)”是华美辞藻,“实”是心之诚实,他认为和歌创作应该以“花”或者说“词”为先,追求言语上的审美性。同时,他所谓的心之诚实并不是抒发今人浅陋之思,而是要努力学习古人之端丽文雅之“心”。他所说的古人之心并不是以古为尊,而是强调一种在内容和意蕴上的对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升华;在他看来,今人文学创作的问题在于抒发个人情感时过于直接浅显,缺少一种幽曲的意蕴。努力靠近古人之心,或者说对现实的艺术升华,是一种艺术上的“伪饰”,但这种“伪”并非对客观现实的错误反映,而是对直抒胸臆的华饰。有了语言形式的审美和文学内蕴的审美的结合,和歌的神韵才能体现出来,唯有这样才能走上“诚之道”。
中国古代文论之“诚”源自《中庸》,但这一“诚”更多的是与宇宙本体与主体价值观的形成有关。《周易·乾》中提出“修辞以立诚,所以居业也”,从语言的修饰达到社会实践的效果。东汉文论家王充提出“疾虚妄,务实诚”的观念,反对文辞的夸饰,追求文学作品的内容真实可靠。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觉醒使得文人们在关注文学反应客观真实的同时开始注重对内心真实的反映,正所谓“诗缘情而绮靡”“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此时的“诚”除了忠实与反映客观现实,也是文学创作的起点,正是主体情感的产生使得文学作品得以创作,而这种遵循情感的创作是“诚”于主体内心的。之后中国古典文论之“诚”也和“华实之辨”类似,无论是唐代对儒家伦理之“诚”的强调还是明清之际对“绝假存真”的内心之“诚”的强调,中国之“诚”在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在客观真理和个体经验中保持着平衡。
3“阳刚”与“阴柔”:中日“诚”的不同体现
在涉及日本古典艺术时,唐纳德·基恩往往将中日文化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他认为,从风格上看,中国文学是一种富有阳刚之气(益荒男振り)的文学,作品内容多为抒发家国情怀;日本文学富有阴柔之气(手弱女振り),主题多为恋情、四季风物。他赞同“中国文学富有阳刚之气,不适合表达感情”的观点,以此为对比,他以纪贯之《土佐日记》为例,试图证明日本文学更适合抒发个人情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女性口吻,用平假名记载日常琐事,抒发了对小女儿的思念。在此之前,平假名通常被认为是女性使用的不上台面的文字,日本文人主流都是使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基恩将这部作品作为日本文学阴柔气质的代表,认为如果是汉文写成,就不可能表达丰富的情感意蕴。尽管这一说法有些以偏概全,但是也有一定可取之处。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之“诚”在于展现内心之经验性真实或宇宙、人间的普遍真理,因而中国之诚更带有理性的思辨色彩。日本之“诚”从哲学论理角度来看并不如中国之“诚”有上升到宇宙本体和人生真理的高度,更多是从艺术真实论的角度对创作主体和客观实在的互动关系中进行归纳总结。反映在文学创作的倾向中,中国古典文学尽管有很多抒情性的内容,但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倾向于文以载道,通过文字来阐明真理、传达道义。正如王夫之所说:“诚与道,异名而同实。”这也是大一统封建国家中文人们通过文学来宣扬主流话语的客观要求。而日本文论的“华实兼备”要求以华美辞藻为载体,以审美之心为内容,因而日本文学更注重审美抒情性。这种倾向在近现代中日文学的风格差异中也有所体现。同样是遭遇了西方列强殖民入侵的危机,中国文人选择以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刀枪,唤醒国民,救亡图存;而日本近代文学中,抒发个人情感的私小说、唯美主义、新感觉派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中国的现实主义倾向便是基恩所谓的“阳刚”,而日本的抒情倾向的文学便是所谓“阴柔”,这也正体现了中日之“诚”在发展脉络上的差异。
总而言之,中国之“诚”的美学观脱胎于哲学观,从追求宇宙真理出发,强调天与人的整体关系,具体到个人身上便是对内心真善的反求,这种追求体现在文学中便是“修辞以立诚”。而日本之“诚”缺乏哲学之义,伦理观和美学观对“诚”的阐释有一定割裂:从伦理上看,日本之“诚”和忠君爱国和向死而生的武士精神密不可分;从审美角度看,诚则体现出对“华实兼备”的艺术真实的追求。回到文章开头,从源头和发展上看,要说“日本的‘诚’(まこと)是中国所没有的”无可厚非,但实际上中日文论中对诚的表述都涉及客观现实和主观感受的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