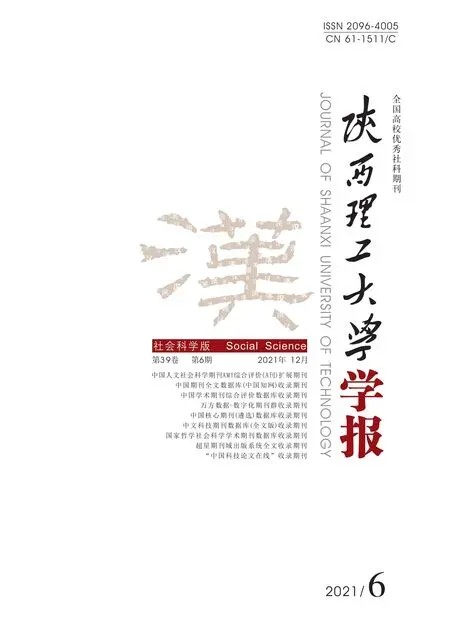人类学与古典新释:萧兵《楚辞》研究回眸
苏 永 前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对今天许多学人来说,萧兵或许是一个略显生疏的名字。毕竟在一个新理论、新成果不断涌现的时代,前辈学人很容易被湮没在众声喧哗之中。不过,如果我们对相关学术史略加留意,就会发现萧兵独特的学术个性与意义。这不仅因为他颇为曲折的学术历程,还因为他在《楚辞》等学术领域的辛勤开拓,以及与叶舒宪等学人一道开创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本文的写作,即源自笔者近年来所从事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史研究,拟通过对前辈成果的重新考察,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为后来者提供某种借鉴。
一、萧兵《楚辞》研究历程
在中国当代学界,萧兵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与丰硕的学术成果曾引起学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有“萧兵现象”之称。(1)有关“萧兵”现象,参见周建忠,等《对萧兵现象的思索——兼评〈楚辞的文化破译〉等书》,《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梅琼林《萧兵现象:反思一种文化研究方法——论楚辞学专家萧兵的研究》,《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萧兵早年考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福建分校,曾在海军厦门基地司令部和机炮连任见习文化教员,后在华东军区师范部中文系受训后,到海军上海预备学校任教员。1957年后在农村和工厂劳动,其间曾在淮阴市文联、剧团任编剧。1980年调入淮阴师专(今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2)参见《淮阴师专中文系教授——萧兵》,《淮阴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封二”。萧兵虽然在军队院校接受过中文训练,但毕竟十分有限,早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部队、农村和工厂度过,因而主要凭借自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据周建忠对1979年至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的统计,这一时段被转载最多的“楚辞学”论文,作者即是萧兵,高达34篇;排名第二的作者转载量仅有6篇。[1]虽然上引数字很难呈现一个学者的真实成就,但起码说明,萧兵的研究在当时确曾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论起自己的学术之路,前辈学者中,萧兵最为推崇的是闻一多。在《三十年自觉生涯》一文中,萧兵回顾道:“我年轻时候,开始只能学着在报刊上写点读诗学文的小心得,更注意在紧张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挤时间读书。闻一多先生的《神话与诗》《古典新义》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2]在《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个微宏观互渗的研究》(以下简称《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书前言部分,萧兵再次说:“我在二十岁左右,受了闻一多等先生大著的启发,发愿写一部大书《玄鸟》。”[3]5与闻一多一样,萧兵的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坚持师承乾嘉诸老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3]5,有着中国传统学术的烙印;另一方面,萧兵又深受弗雷泽等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者的影响,广泛运用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资料,“用世界各古族和后进群团的文化为参照”[3]5。
萧兵的学术成果中,影响最大的是有关《楚辞》的研究。按其多年前的设想,计划写一部由系列论著构成的大作《玄鸟》,“系统地研究我国上古东夷、西夏、南苗、北狄四大部落集群的民俗神话和文化交流”[2]。或许因设想过于宏大,《玄鸟》最终未能完成。后来所发表的有关《楚辞》神话与民俗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该书系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第一部,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诞生于南方“蛮夷”之地的《楚辞》,向来以深奥难解著称。当代学人毛庆在《〈天问〉研究四百年》开篇即说:“楚辞研究,从来称难。”[4]按照萧兵的观点,其原因就在于《楚辞》(尤其是其中的《屈赋》)里面隐藏着许多“文化密码”。近世学者如姜亮夫、汤炳正、朱季海、刘尧汉、童恩正,等,已从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乃至天文学、地理学等领域出发对之进行索解,但仍有许多“密码”有待破译。萧兵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楚辞》中的许多谜题作进一步解答。其所倡导的“微宏观互渗”的研究方法,即是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与文化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有机融合。一方面,运用音韵学、训诂学知识对《屈赋》进行细密精深的考订与微观分析;另一方面,结合地下考古证据及田野调查、文化人类学资料,把以屈赋为主体的《楚辞》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放在有关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等背景下加以研究,进而探讨其与世界各大文化区的古老文明以及我国上古周边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
在《楚辞的文化破译》之前,萧兵已出版多部与《楚辞》相关的著作:《楚辞新探》重点考释《楚辞》在民俗神话方面的疑难,系考证性质,属于所谓“微观”研究的范围;《楚辞文化》是把《楚辞》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跟广义的楚文化一起,放在广阔的“环太平洋文化”与“中国上古四大集群文化”之前,考释其神秘的意义、结构与关联;《楚辞与神话》考释、讨论与《楚辞》有关,或由《楚辞》引起的中国上古神话传说问题,跟《楚辞》本身的关系较为疏远;《楚辞与美学》讨论作为一种“潜美学”系统的楚辞文学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楚辞的文化破译》则是集中检讨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兼民俗文化现象的《楚辞》本身的结构、特质及其谜底,既有理论性的探索,又有实证性的考述,宏观、微观研究兼而有之。由于这部著作在萧兵的全部《楚辞》研究中,带有总结的性质,因而下文的讨论,主要围绕这部著作展开。
二、《离骚》主人公原型考证
《楚辞的文化破译》全书分四部分,分别围绕《离骚》《九歌》《天问》《招魂》展开论述,各部分自成一个单元。第一部分“《离骚》:关键的破解”,主要在于破译抒情主人公的身份问题。引起萧兵注意的首先是主人公的诞生日期:“惟庚寅吾以降”。“降”字作何解释?萧兵引姜亮夫、董楚平等学者的观点,认为表示“天降”,也即神的诞生而非人的出生。萧兵由此得出结论:“作者是把歌主当作一位神气十足的伟人来看待,这个伟人起码也是天神的‘精神’后裔。”[3]24-25如此一来,《离骚》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便具有了神的背景。关于主人公的“降生”日期,据宋代钱杲之、清代顾炎武,以及近人游国恩、浦江清、郭沫若,等的观点,认为是在“寅年寅月寅日”。尽管郭元兴、周文康、汤炳正,等对此提出质疑,但都承认该年、月、日是比较特殊的“吉期”。关于“庚寅”,萧兵又引《史记·楚世家》,以说明这一日期是“吉日”或楚国的纪念日。《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5]609萧兵援引詹姆斯·弗雷泽《金枝》所载“杀王”习俗予以解释:
庚寅是商、秦、楚在一定历史时期里的纪念日或吉日,例如被视作“火日”等等。重黎渎职,故在庆典时杀之,以示其辜负“佳节”,并用其血来点染、加强这个纪念日——多少有点后代在重大典礼里杀人祭旗的意思。……旧王死去,新王即位,是所谓“复活”或“回归”的庆典。这,翻一翻J.Frazer的《金枝》12卷本的第一卷或郑振铎先生的《汤祷篇》所介绍的杀髦君、立新王的喜庆,也许能扩大一下思路。[3]36
在此前出版的《楚辞与神话》一书中,萧兵考证,先秦时期楚人、秦人许多习俗相同,都跟崇拜“太阳神鸟”的东夷集群有“文化血缘”关系。他们都以太阳神巫“巫咸”为大神。萧兵由此推论:《离骚》的抒情主人公既然同样生于“庚寅”,那么,他的身上也便同样承袭着“高阳氏—重黎(祝融)—吴回(祝融)—伯庸(祝融)”一系的太阳神性或火神属性。简言之,在萧兵看来,《离骚》抒情主人公的原型即为太阳神。此外,萧兵在《楚辞与神话》里面的“颛顼考”一章中,已论证“帝高阳”为太阳神,联系《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为抒情主人公的太阳神属性又提供了一条证据。
由上述结论出发,萧兵进一步对《离骚》的结构问题进行了“破译”。大体来说,《离骚》前半部分主要写抒情主人公自剖心迹,后半部分则写抒情主人公愤懑之下的周游求索(即“四次神游”)。对于前一部分,后人的争议多集中于具体名物和词句的训释;对于后一部分,则多集中于神游的方位、路线及原因。因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对《离骚》的结构问题提出了批评。晚清廖平曾说:“《远游》有条理,《骚》则杂沓不堪。”[6]1261英国学者霍克斯也说:“《离骚》所游历的宇宙轮廓不清,连所经路线也不确定。”[3]124不过在萧兵看来,《离骚》的结构虽然貌似纷纭杂沓,有些地方甚至可能存在“错简”,但整体而言却是严整的。通过对“女媭”“重华”“悬圃”“西极”等的跨文化考释,萧兵提出:《离骚》抒情主人公的几次“飞行”,均循着太阳西行的路线,因而在《离骚》深层潜藏着一个太阳或“光明崇拜”的“秘密系统”。
从抒情主人公的“太阳神”属性出发,萧兵还对《离骚》的题意做出新的解释。关于“骚”,萧兵援引刘自齐、韦庆稳、吴荣臻,等学者对于苗族、壮族语言、歌谣的研究,认为该词很可能源于苗语,其本意为“歌”。关于“离”,萧兵在《马王堆帛画与楚辞》一文中考证,“阳离”为太阳神鸟,《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书中又引龚维英的说法,将“阳离”与《离骚》之“离”贯穿起来,认为“离”的本意亦即太阳神鸟。如此一来,所谓“离骚”,可能指“太阳神鸟的悲歌”。
三、《九歌》与“求雨祈丰”仪式
《楚辞的文化破译》第二部分为“《九歌》:诸层的探掘”,这部分内容同样天马行空,读者犹如走进一座纵横交错的迷宫。不过作者的主要意图,以及书中最具原创性的地方,是借助文献资料和人类学知识,探究《九歌》的原始形貌。
虽然《楚辞》中完整地收录了《九歌》,但在萧兵看来,这些诗篇并不能反映其最初形貌;所谓“人神恋爱”,完全是《九歌》的后起形态,并非其本来面目。倒是《天问》中的几句零星记载,更能体现《九歌》的原始形貌。换句话说,《九歌》的“密码”隐藏在《天问》里面。这几句记载是:“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萧兵先从其中的“勤”字入手,通过对楚帛书《老子》与今本《老子》的对读并结合金文资料,得出“勤”“堇”上古相通的结论,因而“勤子屠母”即“堇子屠母”。又因“堇”字训为旱馑,则“堇子”即“旱子”,用萧兵的话说:“这就是关键的关键,秘密的秘密。”[3]199萧兵又结合文献资料与人类学中对于祈雨仪式的大量描述,证实夏启不仅是“旱子”“晴神”,而且“在形势的要求下也会对立转化为祈雨的大巫”[3]201。于是,《天问》中关于《九歌》的记载,被解释为“祈雨求丰的巫术”仪式。对于“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一句,萧兵的推论是:“夏启之所以名‘晴’而号‘堇’者又反映起源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夏族习惯于低雨量生活,而早夏时期夏启东据黄河下游、南下豫鲁之际又遭遇了一场苦旱。到最后关头,他甚至用屠杀他的母亲(女酋长、女族长)并且将她的尸体砍碎分埋四境各地的手段来抑旱求雨。”[3]203其依据,便是文化人类学中有关“模拟巫术”的记述。据弗雷泽《金枝》、简·赫丽生《古代艺术与仪式》等的记载,古代许多民族为了求神降雨并赐予丰收,往往在播种季节将某一象征神灵的女性杀死,将其碎尸埋入土壤,以此保证风调雨顺、庄稼丰饶。萧兵由此得出结论:“启母因为发现了禹的图腾秘密,触犯了‘塔布’(taboo)而化石,粉身碎骨而死,但是她的生命却在启的身上得到了新的回归。但是启又遇到新的劫难——洪水的对立面‘干旱’,启的母亲又必须再次牺牲自己(碎尸分埋)来挽救新的生命,以使大地和庄稼以及人类的生命在大雨之中复苏。”[3]210
由上述出发,萧兵进而推论“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的“本相”。自清代朱骏声、王闿运以降,都认为“商”乃“帝”之误。不过在萧兵看来,此处“商”字可能无误,“商”也可指商人祖先神或商之天帝(即部落最高神)。如此一来,上述两句引文便被解读为:“夏启用怀柔绥靖策略向暴怒的商神祈请商族祈雨招风的巫术乐舞,即与舜乐《九韶》同类的《九辨》《九歌》。”[3]226经过层层的发掘,萧兵最终“还原”出《九歌》的原始面目:商族祈雨招风的巫术乐舞。萧兵进一步推断,原始《九歌》最初可能比较简单,后来其功能不断扩展,所招神祇逐渐增多,乐章也逐渐变得复杂。随着文化的演进继续往后发展,又逐渐凝固、正规,其乐章、变奏及所祭神灵最终确定为九个,于是才有《九歌》以及《九辨》《九招》等名称。
四、《天问》的文体源流
《楚辞的文化破译》第三部分为“《天问》:根脉的寻觅”,主要探讨《天问》的文体源流及其性质。在《楚辞》各篇章中,形态最为奇异、争议最为激烈的当推《天问》,全诗由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构成,诗人未给出一个答案。各个问题之间跳跃性极大,很难捕捉其间的逻辑关联,以至自清初学者屈复始,不断有人提出《天问》“错简”说并试图对之加以整理。近代张希之、胡适、郑振铎,等学者,进而否定《天问》的文学与思想价值。比如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鄙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7]75更有甚者,郭沫若、潘啸龙等认为《天问》系屈原在精神迷乱时所作,这才导致文义不畅,结构混乱,内容艰涩。此外,还有学者对东汉王逸的“题画说”提出质疑,认为楚先王庙宇祠堂中的壁画之说纯属杜撰,因而与《天问》无任何关联。面对上述种种争议,萧兵试图从《天问》与古代绘画及其题铭的关系;《天问》与古今中外“问答体”“问句体”文学的异同;《天问》与“后进民族”的赛歌、盘诗及“入社考试”制度的关联等方面入手,对其文体源流及性质做一探讨,并对《天问》与壁画关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解答。
《天问》与古代绘画及题铭的关系。最早谈到《天问》与楚先王先公庙宇祠堂中壁画之间关联的是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章句》中,王逸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伌,及古贤圣恠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8]67不过对此观点,清代王夫之、廖平,近代郭沫若、陆侃如、苏雪林,法国马伯乐(Maspero)、德国卫德明(H.Wilhelm)等学者均提出质疑。在萧兵看来,“追寻《天问》与壁画关系的途径,首先是必须证明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楚国存在着画壁的传统,然后才能谈得到壁画对《天问》的诱发刺激和制约作用。”[3]788此问题并不难解答。萧兵援引《韩非子》《国语》《说苑》《文选》等早期典籍以及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先秦时代的祠庙是有壁画的,有关宗教神话历史的绘画相当发达,尤其是在南方。”[3]820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壁画,生发出《天问》式的问题极有可能。以马王堆出土帛画为例,这幅画卷虽然仅有三平方米左右,但是内容和主题异常丰富。帛画共分天空、人间、地界、海洋四大部分。天空包括太阳、月亮、女娲、守天门者四个主题,每个主题又分几个单位,每个单位还可分出几个文化因子。按照萧兵的统计,整幅帛画大约有16个主题,近40个单位,以及成倍于此的“因子”。一幅帛画的内容尚且如此丰富,比帛画大好多倍的祠庙壁画更不用说。萧兵据此发问:“难道一座(或几座)祠庙的壁画还激发不出一篇不过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的《天问》吗?”[3]821
《天问》与古今中外“问答体”“问句体”文学的异同。据萧兵考察,在韵文或散文中模仿问答的形式(或只问不答),即所谓“问答体”(“问句体”),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庄子》《论衡》等先秦典籍及敦煌变文中,均可看到这种文体。汉民族之外,诸如《苗族古歌》、纳西族史诗《创世纪》、印度古代经典《吠陀》《奥义书》、古波斯祆教赞美诗、《旧约·约伯记》中,均可看到这种文体,且与《天问》在形式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者,仅仅在于《天问》体现出屈原自身的遭遇、情思和宇宙观,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萧兵由此提出第三个问题:这种奇特的文体究竟从何而来?是诗人的独创还是渊源有自?
《天问》与“后进民族”的赛歌、盘诗和“入社考试”制度的关联。在萧兵之前,钟敬文、顾颉刚、王慧琴等学者,已经注意到《天问》与西南民族“对歌”“盘歌”习俗之间的关联。在《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书中,萧兵进一步对国内少数民族的“问答体”“问句体”诗歌进行了考察,比如《苗族古歌》中的“开天辟地篇”,不仅与《天问》形式类似,而且两部诗中均“传道”古事、盘问与宇宙相关的大事,诸如“天柱”“射日”等内容更是趋同。因而在萧兵看来,《天问》的文体与西南民族的“对歌”“盘诗”有着一定的关联。虽然萧兵未明说,但从文意判断,萧兵同意钟敬文等学者的观点,即西南民族的“问答体”诗歌很可能是《天问》的形式渊源。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上述“问答体”诗歌便是《天问》的终极来源。在萧兵看来,无论《天问》还是西南民族的“问答体”诗歌,二者还有更深一层的根源,即原始先民的“成丁礼”。如此一来,对于《天问》渊源的考察,便由民族学领域进一步拓展到人类学领域。萧兵引用人类学家的考察:在原始部落中,成员达到规定年龄时往往要举行“成丁礼”,其仪规十分复杂,“一般除了可怕的肉体伤残和‘死亡—再生’之类的考验外,还有部落秘史、制度、风习和知识的传授”[3]968。所谓“知识”,通常是部落的神话、传说。这种习俗在澳大利亚、大洋洲、南美洲的土著部落和我国境内的基诺族中间均可以看到。结合《天问》的形式与内容可以推断,《天问》的终极“根脉”,便是各民族早期流行的“成丁礼”及“入社考试”制度。
五、《招魂》的文化解读
《楚辞的文化破译》第四部分为“《招魂》:奥秘的阐发”。萧兵注意到,《楚辞》一书中,与“魂游”“神游”相关的篇目很多,除《招魂》《大招》外,《离骚》《国殇》《远游》《礼魂》等诗篇中,均有上述主题的书写。与前面三个部分重在发掘深层源头的“文化破译”取向不同,这一部分中,萧兵主要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把“招魂”作为一种广泛分布的民俗文化现象,从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究其心理上的依据与根源。萧兵首先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揭示“招魂”仪式的心理基础。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等的研究,面对做梦、疾病、死亡等社会现象,早期人类萌生出一种观念:在人的肉身之外,还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此即灵魂。每当做梦时,人们以为灵魂暂时离开了躯体外出漫游,梦醒时灵魂又回到身体;生病时,是灵魂因迷途而长时间淹留在外,因而需要借助仪式行为招引其返回;死亡时,则是灵魂永远离开了躯体,即便如此,也需运用特定的招魂术,使灵魂重返人间、轮回再生。比如北几内亚的黑人们认为,发生癫狂是由于病人过早地被灵魂抛弃了,同时灵魂只是在睡眠时暂时离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各个地方,招回失去了的灵魂就成了巫师和祭司们的专门技能。[9]424与上述梦境、生病、死亡相对应,前两种灵魂可称为“生魂”,后一种灵魂为“死魂”。这种观念不但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体现,在我国云南地区的独龙族、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以及古埃及人的观念中,亦牢固地存在。由上述出发反观《楚辞》,其中可以发现对不同灵魂的描述,比如《九章·抽思》中“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惜颂》中“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之无杭”,在萧兵看来,正是对“生魂”暂时离开躯体而飞行的描写。此外,萧兵还根据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志资料,对《楚辞》中《招魂》《大招》等篇章的来源进行了推断:“我国南方文化系统(尤其是傣族、彝族和苗瑶族系)相当普遍地流传招魂的风习,有大量的叫魂词、招魂咒语和指引亡魂升天避害或归籍返家的《魂路历程》之类巫术经典,其中有的无论在意构还是手段、目的上都很像《楚辞》的《二招》。楚文化具有强大的土著性和‘西南夷’文化的因子。屈原们很可能就是在古代南方土著或者说楚国民间流传的叫魂词的基础上再创造《招魂》和《大招》的。”[3]1053
总体来看,萧兵的《楚辞》研究旁征博引、新见迭出。作者一方面从文献资料入手,对相关名物、习俗进行微观考证;一方面又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知识,对相关文化现象进行宏观比较。举凡文学人类学“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在此书中亦有明显体现。此外,作为“宏观研究”的一部分,萧兵对楚辞文化的考察,往往联系人类学者凌纯声提出的“环太平洋文化区”来立论,强调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类同及关联。比如在对楚先公先王庙宇祠堂壁画的考察中,萧兵注意到,这种现象在太平洋文化区的一些民族中同样存在[3]803。对于夏启“屠刳其母”的文化意涵,萧兵从太平洋文化区的“祈雨巫术”进行考释[3]229。当然,书中有些论述,也有主观臆测的嫌疑。比如第二部分第一章“‘宾帝’或‘宾商’”一节中,根据人类学理论与萧兵的论证逻辑,《天问》所载“启棘宾商”之“商”,须指商人的祖先神或商人的天帝,即部落最高神。而自清代朱骏声、王闿运以降,都认为“商”乃帝之误。银雀山出土汉简《孙膑兵法》,也从侧面证明上述学者的观点能够成立。不过,如果“商”作“帝”解,则与商之部落神有抵牾。因而萧兵才强调“启棘宾商”一句无误。萧兵又说:“即令‘商’是‘帝’之讹,此‘帝’也可能指的商人的最高自然神、祖先神(如帝舜)。”[3]226这一对“帝”的解释显然比较牵强。胡适曾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像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10]不过如何在“大胆想象”的同时,又能“小心求证”,无疑是包括《楚辞》在内的中国古典学研究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