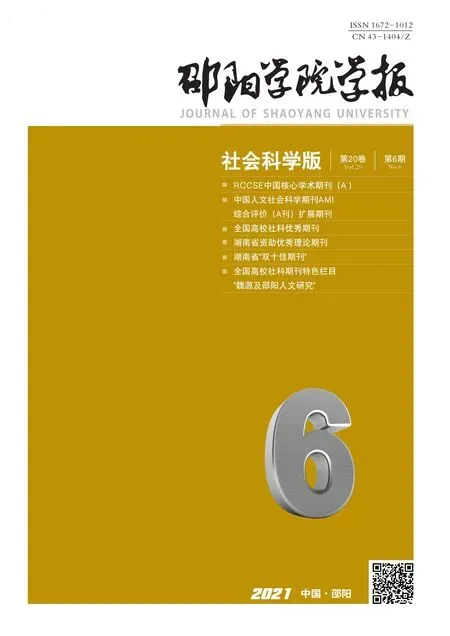五缘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构形态
施炎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062)
一、重构: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重要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中国人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努力,往往伴随着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问题的探讨展开。这是因为从文化层面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及其思想资源的传承、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现在,我们确实需要有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精神特质的把握以及体系框架的学理性建构,以便全面、准确、有效地选择吸收中华文化历史演进中积累的内涵特质、基本精神、独特创造、价值理念、思想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已有前辈学者为此做过不懈努力,如梁漱溟以中西印文化“三路向”为背景,据“伦理本位”说阐述中国文化之要义;费孝通以“差序格局”论为题,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来探讨中华文化的思想特色,建构其体系框架。近年来,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或做课题、或著书、或撰论文,着力于从整体上系统性梳理和把握中华文化发展进程、精神价值和资源意义,给出诸多体系框架的构想,以呈现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风貌。
但比较来看,林其锬创导并阐述的五缘文化学说,在前辈和时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人际缘分的凸显和五缘网络的建构,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认知、精神特质的理解和丰富内容的框架性把握,都有所深入并具体化了。当然,这种理解和把握,不一定很正确,也远非完善。但相对而言,在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重构其思想体系框架方面,应该是比较合理,有独到见解的。
就此而言,笔者认为五缘文化学说的特质亮点和价值功能,更多体现在它为我们在文化整体性、精神价值层面和思想特色上理解、把握中华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念、思路和体系重构的框架。尤其是,五缘文化学说着力于采用中国特色的话语系统和术语概念,力图重构一个中华文化传统,确立的前提条件是认可五缘文化研究的对象,与中华文化的内涵、外延有相当的契合,甚至互相包容。
我们知道,五缘文化研究强调制度行为文化同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彼此相连不能截然分开,主张基于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互动关系,着重在制度行为层面探讨和考察中华民族人际结构网络,断定“人的社会性和民族性是五缘文化的基础”[1]5。同时,又确认并探讨了人的社会性与民族性,实出于人之本性、情感的趋同性和稳定性,由此论证这种依据于人性、人情作立论,从而形成的“缘分”(或称“缘”),是具有客观性、实存性和必然性的文化特征。这样,五缘文化学说试图通过建构一个人际关系的五缘网络框架,以实现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观照和体系性把握,就有了一定的根据,变得更合理,给人以可信感。
值得重视的是,五缘文化确认的研究对象、所构建的五缘网络,其涵盖的内容,触及了我们真正需要认同的中华文化大传统、真系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广度和生命活力。其含义至少有三:一是突破过度学科化、学派性思维导致的对中华文化体系的切割和知识化、碎片化处理,确立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理解和把握中华文化的态度、理念、智慧和方法;二是根据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思考,梳理并整合中华文化体系各层面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关联;三是给出了一个建构思路和体系框架,合理呈现中华文化大传统的精神品格和形态面貌。
从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讲,所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构”,其学理指向并不局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梳理和呈现,而是要进一步促进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和思想资源的传承发展及其现代转化。其进程至少包括三个层次:首要是对文化传承载体的经典文献做认真、扎实、深入的考察、梳理和解读,弄清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和原初风貌;二是对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精神要义、独特创建进行理论研究和学理考察,即在古今沿革的历史进展中,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的内涵特质和根源性;三是对传统的思想文化做现代诠释,揭示并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和现代意义,并转化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说五缘文化学说的创建,意味着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重构”形态的出现,是因为五缘文化的网络建构标志了中华文化传统由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一个转变。
区分文化形态上的自在与自为两种状态,来自于黑格尔关于哲学史研究构想的启发。黑格尔曾把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区分为自在和自为两种形态。在黑格尔看来,自在即潜在的活动,自为则是实现(或呈现)的活动。前者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哲学史,属原生态的;后者是人们经过研究、梳理、总结、整理出来的哲学史。由此就有了客观的哲学史和主观的哲学史的区分,或称在的哲学史及写的哲学史。以此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来理解中华历史上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形态,这首先是一种潜在的、客观的过程,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当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自在”传统。要使中华传统文化能得到实现和呈现,为现代中国人所看到、理解以致把握,那我们需要有文献的整理,思想的考察、剖析,文化体系的建构和表述,并通过现代诠释作出评价和选择,由此呈现的中华文化传统才成为一个自为的文化体系。而唯有成为一个自为的体系,中华文化的整体演变进程、精神特质及其根源性因素、资源性价值才有可能得到揭示和呈现,否则就只能是图书馆收录的文献和博物馆的展品而已。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五缘文化学说的提出,是通过将自在的中华文化传统转化为自为的中华文化思想体系,来实现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重构”。这样的五缘文化,很大程度上既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梳理和总结,也是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形态的“再建”。
二、缘文化:透视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价值
五缘文化学说能以特定的话语系统和网络框架来表达中华文化的整体建构及其精神价值,一个重要根据就在于它论证了中华文化传统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缘文化”,并揭示出此“缘文化”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文化大传统的精神基因和价值归结。
按五缘文化的观念,传统中华文化关注的重点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机制及其网络建构,其核心问题源于一种“缘分”的内在联结和制约,而非西方式的契约束缚和宗教裁制。所以,缘或缘分,自然就成为观察和思考中华文化关于人际关系问题的核心处和关节点。
“缘”一词,本指关系之间的自然连接,犹如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贯穿似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在中华文化历史上,这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主要是就人际关系而言,而它的产生和形成,却是在中华元文化的发生期。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中华元典中用的“缘”字,原指衣服的边沿,常用为“缘饰”,如汉许慎《说文解字》指出“缘,衣纯也”。但缘饰并不局限于“衣边”“镶边”的解释,还有“围绕”“凭借”的意思,此如荀子所说:“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其所讲“缘”,则又包含事物关系连接中有所依靠、有所根据的因素。
用“有所依靠、有所根据”来解释“缘”,与其意思相似的,还有一个“因”。孔子就很重视“因”的观念,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在关于“礼”的理解上,孔子对应“损益”来讲“因”,侧重于殷周礼乐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沿革变迁,认为“礼”所依靠、所根据的是对前代积累的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因革”。这说明,孔子提出“因”的概念,有一个变与不变关系的考虑,意图是要寻求后代文化发展和前代创获之间连接的“一个神圣链条”(黑格尔语)。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寻找和把握一个民族前后代之间的文化“缘分”和演变线索。所以,因、缘两字连用是十分自然的。
到了汉代,“因缘”联用词的使用更为广泛,尤其应用于表达人际交往活动的一些关系因素,其涉及的含义有二:一是讲机缘关系,一是讲依靠(凭借)关系。人与人之间“缘”的存在,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缘分关系”的连接。“缘分”一词,不仅表示人与人之间外在的关系连接,更表示在精神心理、价值认同的层面上有互相的沟通理解甚至默契。所以,缘分是人际关系中相对稳定、能长久起作用的因素。这种作用因素往往是内在的、隐性的,却通过交往行为、沟通礼仪、形象、语言等载体得到呈现。在人际沟通交往中,双方对“缘分”认知和理解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双方关系的亲疏、深浅。就此而言,缘或缘分的考量,往往是中国人的人文论和人际关系论上的题中应有之义。
按五缘文化学说的理念和思路,把中华文化传统归结为一种“缘文化”,实际上涉及对“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人化或人文化”的理解和认知。诚如《五缘文化论》一书所断言,中华民族以伦理为中心、以‘五缘’为形式的文化,其突出的功能便是起协调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又指出,中国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以家为中心,强调的是家、族、宗、国,人际关系重伦理,所以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2]2-3。
以伦理为中心,以群体为本位,是中华文化的又一项基本特质。事实上,这个基本特质的发现和概括,和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性、人情、人文等因素的考察密切相关。《管子·心术》就提到:“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喻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3]221以“因人之情、缘义之理”的因缘观念,解释“礼”的本质在出乎人的情义,而义出乎理,理因乎宜。宜,强调要适宜。适宜什么?理要与人情、情义相宜适应。可见,人际交往中讲的理义、缘分,所依据的还是人文情性的因素。同样的意思,司马迁也有明确的论述。《史记·礼书》引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4]398很明显,司马迁已意识到:以礼乐文化的制度性建构去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不是主观人力所能为的,而是要善于总结夏、商、周三代的经验教训,知道文化创制还有一个“缘人情”“依人性”而发生的客观过程。
在我们切入中华文化的发生机制时,可以发现:文化之“元(源)”与人文之“缘”是相依互补的。根据人情、人性的内在根因,展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活动,才有助于形成接缘、续缘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使中华缘文化的形成由可能变为现实。正是这种缘文化,才属于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
三、五缘网络:中华文化传统重构的体系框架
引入五缘文化网络的建构模式,来探索和梳理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重建中华文化的体系框架为什么可行?这是我们根据对五缘文化的思考来探索和把握中华文化精神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否则,人们会有疑问:中国人的人际缘分关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那何以要用“五缘”来概括,而不以三缘、七缘、八缘或九缘做界定?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秉性智慧中,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崇五”思维。
从中华文化发生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基本观念中,五缘之“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字之“五”,而已经发展成一个哲学的概念。因为,以“五”开启文化创制的建构框架,在中华文化源头处已显端倪,并在中华文化早期发展(先秦时期)中形成一种思维模式。但“崇五思维”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和建构框架,当出于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律。
中国人思想律之源起,离不开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原”的《周易》。《周易》对中国思维、中国智慧的一大贡献,在于奠基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并首创以“五”为天地之数模拟天地自然之变化,由此建构其言、象、意组合的思想体系。这个天地之数“五”,是圣人观察总结天文地理、自然万物、社会人文变化之道的结果。此“结果”,司马迁《史记》概括为“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之说,内含有“五”观念的确认[4]436。
与《周易》相呼应,《尚书·洪范》有关于“五行”一说的具体诠释。它不仅是指木、金、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而且和地理环境、空间方位的表达相关,引申出五方、五位等说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人更注重用五方、五位来表述,以凸显自然地理环境的空间性、立体性。在东西南北、上下前后的结构次序中一定要挺立“中”。这个“中”,就是宇宙(自然地理)环境结构次序的汇聚点和支撑点。“五”在其中就不是一般的数字的表达,而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文化创制模式的一个立论点和核心观念。《尚书·皋陶谟》还由五行派生出五礼、五典、五服、五刑等用语,标志着被赋予社会人文、政治、伦理内涵的五行思想更丰富、更系统了。
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学派性的(如儒家)还是时代性的(如宋明理学)思想体系,也不管是国家层面上的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以“五”为概括和表达的思想观念、文化样式,应用广泛,十分普遍。例如,许多经典文献常有五典、五经、五行、五方、五族、五位、五爵、五礼、五政、五伦、五德、五教、五达道、五事、五服、五刑、五智、五才、五色、五音等用词术语,在不同的层面,或从不同的方面,来表达中华文化的展开和思想体系的建构。至于在人际缘分关系和社会结构上的呈现,也经常有“五”作为缘分类型划分的标志,形成层层叠套的五缘关系网络。这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演变发展及其体系建构中的一大特色。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阴阳五行论始终是贯通其间的一条主线,也是文化体系结构的一个骨架。诚如庞朴先生所说:“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5]黑格尔也认为:“《书经》里阐述了五项义务,作为尊崇不变的基本关系:⑴君臣,⑵父子,⑶兄弟,⑷夫妇,⑸朋友。……他们有五种自然元素:空气(火)、水、土、金和木;他们设想有四个方位和一个中心;凡是建有祭坛的圣地,都是由四个土丘和中间一个土丘组成的。”[6]118犹如西方人看重“三”,中国人把“五”这个数字当作固定数字。所以,五缘文化学说引入“五”的概念解释中国人的人际缘分网络,首先是延续了“中国人思想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智慧、中国话语的表达。其次,“五缘”的概括,给中国人人际缘分涉及的广泛内容和分层结构,也提供了一个简明、合理的建构框架。从实际效果来看,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五种“缘分”作为联系环节和沟通纽带,含有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诸多内容和精神价值因素,还是颇为恰当的。
就“五缘缘分”的内涵而言,亲缘是指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为纽带的人际联系和结构网络。中华民族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缘分系统,包括属亲(血缘亲属)、族亲、宗亲、姻亲、假亲(领养、过继)关系等。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亲缘是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中的基础性、基因性“缘分”,确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关键性特征;血缘亲情关系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最普遍、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关系;而亲缘文化虽纠结于血缘亲情,但往往突破血缘亲情,纳入“尊贤”“尚能”的考虑,扩大了血缘亲情的范围,呈现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连接网络,更有持久维系家庭、家族及社会结构秩序稳定的功能。
地缘,可理解为一种按乡土、地域、区域关系作为纽带建构起来的人际沟通系统。在具体内容上,地缘讲的是邻里乡党关系,其所承载的是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影响、制约下形成的地域性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包括人际交往中的乡土情结和籍贯认同。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土地的眷恋和归属,是人们很强烈、很普遍的心理情感,在同一地域、同一方水土的人们中激起互相认同的共鸣效应,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地缘文化长久持续的重要原因。
神缘,从广义上讲,是指中国人基于自身的信仰系统而发展形成的缘分关系,不局限于宗教神学信仰支配下的缘分。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文化中的信仰系统,总有两个基本的路向和建构体系:一是宗教的信仰系统,如本土的道教,印度传入并中国化的佛教,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民间流传的宗教派别。其信仰是多元的,并有宗派性差异,但同时也有在宗教神学的网络框架内发展形成的价值共享和信仰趋同。二是追求理想境界的、出于理性思考的信仰,往往和人们的信念相通。不过,在汉语言系统和中华文化背景中,宗教性的神学信仰却并不突出。而且,“神”作为专用术语,虽然也表达为“神仙”“神人”“神性”,有宗教神学的意味,但更多还是从理性的、思维智慧的含义上讲的,以呈现“神妙”“神化”“神圣”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容。这是中华文化中信仰系统的特点,也是中华神缘文化的特色所在。
业缘,是在学业、事业、产业等社会活动中形成、发展的缘分关系,一般表现为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同行同业关系等。业缘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形成,又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业缘的根本特点是它的职业性、专业性和分业性。形成这种特点的前提是人们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类的日益发展。业缘的形态广泛而复杂,丰富又多彩。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开展的种种有关学业、行业、职业、专业以及科学技术的活动及其组织形式,都是业缘形态的呈现。
物缘,则是通过物质的载体,或以物质化的制度、组织系统为媒介而建立起来的人际联结纽带。在人类社会的人际交往中,物缘关系也是个包容性极广的综合性系统,既有人们在与自然环境的交往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有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组织结构及行为规范下结成的关系;还有人们通过各种创设或制造的产品、技术、工具为媒介而建立的沟通联络关系。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历史积累中创设、发展起来的组织制度系统和物质技术系统,更多表现为人们结成一定的物缘关系来拓展人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五缘网络形式上可以分列,实际存在的是一个互相联结、渗透、联动的结构系统,其涵盖的内容,和一般文化形态学上区分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层,或区分深层结构的意识精神文化、中层结构的制度行为文化以及表层结构的器物技术文化三项,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在文化形态的“重构”上存在思路、方式、框架、内容侧重等方面的差别。
四、跨文化沟通:五缘文化的全球性结缘
林其锬提出的五缘文化学说,旨在建构一个人际关系中的五缘网络,采取的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进路,主要对象是中华民族古今延续的人际交往行为及关系网络结构,体现的是一个中华文化形态的概括和话语表达。
二十多年来,五缘文化研究的学理深化和应用推广不断发展,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上也引起许多关注。事实足以说明:据于五缘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不仅可用于对世界范围内华人华侨交流、沟通网络的理解把握,同样可以推广应用于对国际关系格局新变化的认知、理解。因为“国之交在民,民之交在心”,这个民之交、心相通,在五缘文化的视野和框架下,也可以把文明沟通、国家交往的基础归置于人际缘分内涵的人性趋同和民心相通的文化基因。这个似乎由“缘文化”引出的国家观、天下观、世界观,在不同的文明体和不同民族国家内,都有各自的存在和传扬。其实,当我们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性观念和人文思想,很容易发现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人性观念等都有其相似处和会通点。
中国的儒家、墨家、道家及佛家,都有关于人文、人性、人道问题的论述和表达,提出过许多立足于“心通”“性近”“类同”观念的人论言说,涉及人际缘分关系存在的认知和理解。例如,墨家有著名的“类同”一说,以为有类同关系的不同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在本质和属性上相似或相同,这可以视为对墨子讲“兼爱”、倡导人际普遍之爱的一种逻辑证明。荀子则认为,“类同”从逻辑上讲是一个“大共名”,他将其用于解释儒家关于人之“类”属性的思想,提出了人际关系考量上的“分群、合类”说辞。荀子一方面讲“人以群分”“明分使群”,主张人际关系先要分群;另一方面,又指出人与禽兽之间的“别”“异”,强调“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人生而具有“情性”,又有知、有思、有辩、有礼义,据此肯定人与人之间皆是一种“类同”的存在,“故最为天下贵”(参见《荀子·王制》)。而孟子则以“心之所同然”观念立论,断言人与人皆有“人同此心”“人同此情”的人心、人情,并将之归结为仁、义、礼、智“四端”,即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故人性本善。显然,孟子从“人性善”出发,肯定了人际关系上内在有“类同”的基因,是进一步强化了人际缘分间内涵普遍人性的。
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背景下,我们已经认知和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交集和会通。五缘文化所凸显的人际交往沟通中的“缘分”,因其立论于人性、人情等人所共有的本质和属性,与马克思多次强调并深刻阐述的人之“类本质”,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大有相似和趋同,就是个典型。
类,英语中一般以species作表述,意指同一类的或共同的。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用“类”概念作为其人论的说辞,但费尔巴哈在单个的、抽象的人的意义上,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宗教的本质,定义为理性、爱、意志力等要素。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改造。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揭示人的本质在于“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个著名的人论命题,是扬弃费尔巴哈的旧唯物论观念,依据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思想论证人的“类”本质和“共同性”。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性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所以,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马克思特别批评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强调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又引入社会存在、社会实践观念,重新解释费尔巴哈的“类意识”概念,明确把人的类意识归结为“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以此界定人的“类”本质[7]54-57。深刻领会马克思的这个观念,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关于人际缘分之人性论基础的问题,提升对此问题的思考力和说服力。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为更多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所接受。在事关全人类切身利益的经济、贸易、安全等领域,需要多边机制、多元发展、多赢共利的呼声更为强烈。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各国、各民族、各人类群体之间,总是存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甚至对峙,很容易导致国家、族群关系处置上的分歧和冲突。这就需要人们在联系、交往、沟通方面有更广泛深入的发展,更自觉持久地推进、发现和开拓更多便捷有效的纽带和通道。在此背景下,五缘文化善用人际缘分网络来加强跨文化沟通,必然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举例来说,亲缘文化是五缘文化网络的基础建构,也是核心性因素。而在中华文化的框架内,亲缘并不局限于血缘亲情关系,而是有扩展化(泛亲化)、普遍化的发展趋向,不断衍生出各种亲缘情谊结构,实实在在经历了一个由亲缘文化向泛亲缘文化延伸发展的过程,完全可以突破宗、族、国的界限,发展成全球性的广结善缘、联谊交友、和谐共处的人际缘分交往活动。一方面,以家庭、家族、宗族为单位的血缘关系,通过姻亲、拟亲等族外亲属关系不断发展、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血缘亲情关系也成为一个可以扩大的、开放的系统。另一方面,血缘亲情关系又和五缘文化的其他缘分关系互动、连接,尤其是亲缘因素向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关系领域的渗透和扩展,再加上文化思想层面“仁爱”“泛爱众”“兼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等观念的传播和推广,亲情关系不断发展为更具普适性的情谊关系。
以情谊亲缘作为缘分联结、构建起来的人际群体关系,其发展和扩大着重的就是“推(广、扩)”。孔子讲“推己及人”,可以逐步扩大到“泛爱众”;孟子则倡导“推恩”,以“泽被天下”的胸次和气度,把“仁爱”和“仁政”推及他人,恩泽众生。其中,就凝聚了亲缘情谊的价值资源,因其具有贯穿古今的“共理”,又体现着普遍人性的基本内涵。
在中华文化精神演变发展的背景中,梳理亲缘文化的历史沿革,可以清晰看到:由重宗亲到“泛爱众”;由主张“别爱”到创导“兼爱”;由仁义亲爱发展到“周知周爱”“民胞物与”,其思维指向和价值意涵,旨在传扬天地人间大爱,都和追求“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一致。对此,我们断不能以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为借口而否定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