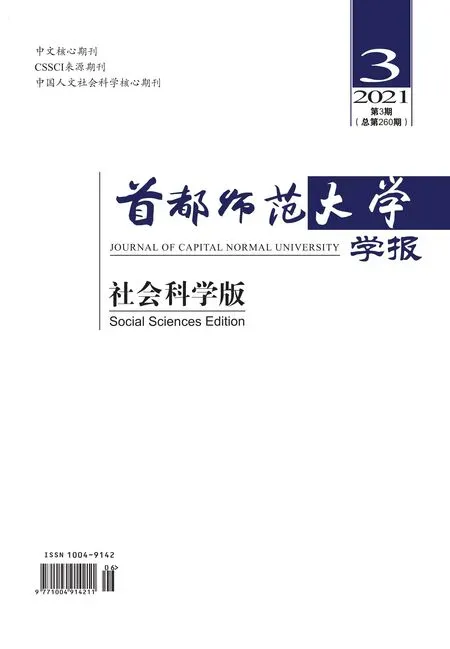《文心雕龙》创作理论生成的基础
詹福瑞
近些年来,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已经不再拘守文学理论的旧说,许多文章认为《文心雕龙》是文章学,即使是文学理论,它所讨论的范围也是大文学或曰杂文学,而非纯文学。此说是颇有道理的。今天的文学概念来自西学,是指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文体在内的纯文学。而中国古代所说的文学,实则是经史子集四部之中以集部为基础、以诗文为主体的文章。《文心雕龙》所论之文,就是如此。而从其“论文叙笔”的文体论看,其文章范围甚至包括了史传与诸子。从表象看,《文心雕龙》所涉及的文章范围更加宽泛,即使是在齐梁时期,其文学观也是比较趋旧的。既然如此,刘勰《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讨论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文章,其写作理论性质如何,就不能不辨。
考察一部著作、一个理论的性质,无非是看其立论基础,即理论产生的直接条件。就文章理论而言,不外是据以形成理论的文体及其作品。所以,此文即具体考察《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理论所据以生成的作家作品。
一、《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引文统计
关于《文心雕龙》所引作家和作品,罗宗强先生曾将其作为刘勰的素养和知识结构给予考察,统计出引及作者322人,其中提到扬雄26次,曹植25次,司马相如24次,陆机22次,班固、张衡18次。引及作品436部、篇,引用原文223处。①罗宗强:《〈文心雕龙〉的成书与刘勰的知识积累——读〈文心雕龙〉续记》,《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罗宗强先生统计的是《文心雕龙》全书,为了考察刘勰的创作论,受罗宗强先生启发,可对《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所引作家、作品再做统计,以便进一步分析。
《神思》论及的作家有刘安、张衡、王充、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王粲、曹植、阮瑀、祢衡、左思,作品有张衡《两京赋》、左思《三都赋》、刘安《离骚传》。
《体性》论及的作家有贾谊、司马相如、刘向、班固、扬雄、张衡、王粲、刘桢、阮籍、嵇康、陆机、潘岳。
《风骨》论及五位作家:司马相如、孔融、徐幹、刘桢、潘勖,作品为司马相如《大人赋》、潘勖《策魏公九锡文》。
《通变》涉及作品有:黄帝时《弹歌》、尧时《在昔》、舜时《卿云》、夏时《五子之歌》、周朝《诗经》、楚国的骚体、汉代的赋颂、魏之篇制、晋之辞章、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赋》、马融《广成赋》、扬雄《羽猎赋》、张衡《西京赋》。
《定势》谈到的文体有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连珠七辞,而作家只有桓谭、曹植、刘桢和“近代辞人”。
《情采》论及的作品有《孝经》《老子》《庄子》《韩非子》《诗经》,并论及辞人。
《熔裁》讨论了谢艾、王济、陆机、陆云等作家。
《声律》论及的作家有曹植、潘岳、陆机、左思、张华,波及的作品只有楚辞。
《章句》篇论诗之体,二言引了黄帝时代的《竹弹》,三言引了虞舜时代的《元首》之诗,四言引了夏代的《洛汭之歌》,五言引了《诗经·召南·行露》,六七言引了《诗经》和《离骚》,作家则为贾谊、枚乘、刘歆、桓谭、曹操、陆云。
《丽辞》论及的作家有张衡、扬雄、蔡邕,作品有《易传》中的《文言》《系辞》、宋玉《神女赋》、司马相如《上林赋》、王粲《登楼赋》、张载《七哀诗》、张华《杂诗》、刘琨《重赠卢谌》。
《比兴》篇论及《诗经》里的《鹊巢》《淇奥》《板》《小宛》《荡》《柏舟》《蜉蝣》《大叔于田》,宋玉《高唐赋》,枚乘《菟园赋》,贾谊《鸟赋》,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张衡《南都赋》,潘岳《萤赋》,张翰《杂诗》,另外论及扬雄、班固、曹植、刘桢等作家。
《夸饰》论及经书中的《书》《诗》,作品有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西京赋》、张衡《羽猎赋》,另外还有宋玉、景差等作家。
《练字》讨论的作品有司马相如《凡将篇》《上林赋》,扬雄《训纂篇》,班固《两都赋》,傅毅《靖王兴诔》,曹摅诗,王融序,另外谈到京都苑囿、貌状山川,显然指的是辞赋,常文指应用文体。作家只有曹植。
《指瑕》论及的作品有曹植《武帝诔》《明帝颂》,左思《七讽》,潘岳悲内兄、伤弱子的哀文,崔瑗的诔,向秀《思旧赋》,张衡《西京赋》。
《养气》涉及作家有王充、曹褒、曹操、陆云。
《附会》论及张汤的奏、虞松的表、倪宽改奏、钟会改表。
《总术》论及陆机《文论》、曹丕《典论·论文》。
《时序》几乎是刘勰的文学史,谈到的历代作家作品有:《南风》《卿云》,《诗经》之《周南》《邠风》《板》《荡》《黍离》,《大风歌》《鸿鹄》,柏梁联句,杜笃诔,班彪奏,班固史,贾逵《神雀颂》,刘苍礼文,刘辅《五经论》,庾亮之书记诰令策问及辞赋等。涉及的作家有孟子、荀子、邹衍、邹奭、宋玉、屈原,贾谊、邹阳、枚乘、主父偃、公孙弘、倪宽、朱买臣、司马相如、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安、终军、枚皋、王褒、扬雄、刘向、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逸、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路粹、繁钦、邯郸淳、杨修、何晏、刘劭、嵇康、阮籍、应璩、缪袭、张华、左思、潘岳、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刘隗、刁协、郭璞、温峤、简文帝、袁宏、殷仲文、孙盛、干宝、王僧达、袁淑、颜延之、谢灵运、何逊、范云、张邵、沈约。
《物色》篇主要讨论的作家是《诗经》作者和屈原,作品为《诗经》之《周南·桃夭》《小雅·采薇》《卫风·伯兮》《小雅·角弓》《周南·葛覃》《召南·草虫》《王风·大车》《召南·小星》《周南·关雎》《卫风·氓》《小雅·裳裳者华》,楚辞《招隐》《七谏》《九歌·少司命》。
《才略》论述的作家作品在诸篇中也是较多的,论经书:“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义固为经,文亦师矣。”重在辞采可为文章典范。以下有诸子、屈原、苏秦、班固、宋玉、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刘歆、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逸、张衡、蔡邕、刘桢、应玚、嵇康、阮籍、陆机、陆云、成公绥、夏侯湛、曹摅、张翰、张载、张协、孙盛、干宝,作品有楚辞、乐毅《报燕惠王书》,范雎《上秦昭王书》,李斯《谏逐客书》,荀况的赋,陆贾《孟春赋》,贾谊的议及其赋,枚乘《七发》,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王褒《圣王得贤臣颂》,扬雄的辞,桓谭《仙赋》,冯衍《显志赋》,班彪《王命论》,杜笃《论都赋》,贾逵《神雀赋》,李尤《函谷关赋》《函谷关铭》,马融《广成颂》,王延寿《鲁光殿赋》,赵壹的辞赋,孔融的章奏,祢衡的《鹦鹉赋》,潘勖《策魏公九锡文》,王朗的序铭,曹丕的乐府和《典论》,曹植的诗和表,王粲的诗赋,陈琳和阮瑀的符檄,徐幹的《玄猿赋》《中论》,路粹和杨修的笔记,丁仪和邯郸淳的论,刘劭《赵都赋》,何晏《景福殿赋》,应璩《百壹诗》,应贞《临丹赋》,张华《鹪鹩赋》,左思《三都赋》《咏史诗》,潘岳《西征赋》以及哀诔,孙楚的诗,挚虞的述怀和《文章流别志论》,傅玄的笔奏,刘琨的诗,卢谌的表,郭璞《南都赋》和游仙诗,庾亮的表奏,温峤的笔记,袁宏《天台山赋》,殷仲文《咏孤云》,谢混写闲情之作。
《知音》论及的作家是韩非、司马相如、班固、傅毅、曹植、陈琳、丁廙、曹丕、桓谭、刘修,作品是《子虚赋》。
《程器》主要讨论的是作家,有屈原、贾谊、邹阳、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马融、冯衍、杜笃、孔融、祢衡、王粲、陈琳、丁仪、路粹、潘岳、陆机、陆云、孙楚、黄香、徐幹、庾亮、郤縠、孙武等。
二、《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引文分析
《文心雕龙》提倡宗经,经书是刘勰所树立的文章典范,而非研究的重点,所以创作论中所征引的经书,不能算作他所考察的文章对象。如果不算经书,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刘勰后二十五篇所涉及的文体虽然有诗、赋、颂、箴、铭、诔、碑、书、章、表、奏、议、论、序、符、檄、移、策、史、连珠、七辞等二十余种文体,但主体是赋和诗。尤其是赋在所引一百五十余篇作品中,竟然有近五十三篇之多(包括重复引用的)。除屈原《离骚》、楚辞《七谏》《招隐》《九歌·少司命》之外,具体有宋玉《神女赋》《高唐赋》,司马相如《上林赋》(引及四次)、《大人赋》(引及二次)、《子虚赋》,贾谊《鸟赋》(引及二次),枚乘《七发》(二次)、《菟园赋》,班固《两都赋》《西京赋》,王褒《洞箫赋》,刘歆《遂初赋》,张衡《西京赋》(引及二次)、《两京赋》《南都赋》《羽猎赋》,扬雄《羽猎赋》(引及二次),贾逵《神雀赋》,陆贾《孟春赋》,桓谭《仙赋》,冯衍《显志赋》,王延寿《鲁光殿赋》,杜笃《论都赋》,李尤《函谷关赋》,马融《广成赋》《长笛赋》,刘劭《赵都赋》,祢衡《鹦鹉赋》,徐幹《玄猿赋》,王粲《登楼赋》,何晏《景福殿赋》,向秀《思旧赋》,应贞《临丹赋》,张华《鹪鹩赋》,潘岳《西征赋》《萤赋》,左思《三都赋》(引及二次)、《七讽》,郭璞《南都赋》,袁宏《天台山赋》。
其次是诗,有汉初《大风歌》《鸿鹄》,左思《咏史诗》,张载《七哀诗》,刘琨《重赠卢谌》,张翰《杂诗》,陆机《园葵诗》,应璩《百壹诗》,郭璞《游仙诗》,殷仲文《咏孤云》。
再次是颂、诔和铭文,有马融《广成颂》(引及二次),王褒《圣王得贤臣颂》,贾逵《神雀颂》(引及二次),傅毅《靖王兴诔》,曹植《明帝颂》《武帝诔》,李尤《函谷关铭》。
征引较多的文体还有书:乐毅《报燕惠王书》、范雎《上秦昭王书》、李斯《谏逐客书》、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曹植《报孔璋书》、陈琳代笔的《与曹丕书》。
由此可见,刘勰征引的作品是以赋为主体的韵文,刘勰的文体论,首列诗、乐府、赋与颂赞,亦可印证刘勰考察文章的重点。
再看《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所论作家,频繁论及的有屈原、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傅毅、桓谭等辞赋家,再有就是曹植、建安七子、嵇康、阮籍、陆机、陆云、潘岳、左思、张华等诗人。征引次数如下:司马相如、扬雄各十一次,张衡、曹植各九次,班固、陆机各八次,王粲、潘岳各七次,贾谊、枚乘、刘桢、陆云各六次,屈原、宋玉、桓谭、马融各五次,傅毅、蔡邕、陈琳、左思各四次,邹阳、刘向、刘歆、杜笃、崔骃、刘劭、孔融、曹操、曹丕、祢衡、路粹、张华、张协、孙楚、庾亮各三次,征引二次的有司马迁、王充、崔瑗、王逸、王褒、王延寿、贾逵、嵇康、阮籍、郭璞、张翰、傅玄、张载、挚虞等三十人。
以上征引作家情况可与征引的作品相印证,主要还是辞赋家和诗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的“割情析采”理论,是建立在以辞赋和诗歌为主要考察对象之上的创作论。诗赋这样的文学作品,在汉魏六朝及其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是以审美作为主要创作目的的文学作品,因此而与其他说理达意的应用文体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分为二途。
三、基本问题之一:心与物
作为以审美为写作目的的作品,无论是创作,还是总结创作经验的理论,都面临一些基本的问题,这也是刘勰在其“割情析采”理论部分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心与物的问题。讨论的篇章主要为《神思》和《物色》。
应用文体的言说对象主要是义理,所以从《史传》到《书记》,会言及心,却基本不及物。诗赋则不然。赋是汉代兴起的主要文体,此后对古代文人有深远影响,是衡量文士学识与才华的重要文体。汉代的大赋以体物大赋为主流。“汉初词人,循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①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诠赋》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以下《文心雕龙》引文皆出此书,随文注出篇名,不另出注。。《文心雕龙》所引的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扬雄《羽猎赋》以及左思《三都赋》都是体物大赋,其特点就是“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齐梁之前的诗,其类型主要还是抒情之作。但是,如《文心雕龙》所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物色》)。刘宋之后,山水诗兴起,同体物赋相似,山水之作也以体物为要旨,所以文贵形似,与体物之赋殊途同归。写作这样的作品,面临的首要之点就是如何对待外物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如何“挫万物于笔端”,而加以表现。而这个问题只是赋和诗所要解决的,其他文体则较少涉及。
关于心与物的关系,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创作中主客体的关系。其实,刘勰所关注的心与物的关系,集中在作品的构思中。在《文心雕龙》中,刘勰首设《神思》篇,明显受了陆机《文赋》的启发,但其“言为文之用心”的开创性还是不容忽视的。而刘勰之所以要讨论神思问题,就是因为他在总结体物大赋的创作经验时,深感构思在赋的写作之中的重要。这就如同《文选》选文的标准侧重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一样,重视文之构思,是面对体物大赋这样比较复杂的文章样态时形成的。创作京都赋,作家必然要涉及地理环境,如司马相如《上林赋》的“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①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班固《西都赋》的“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②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③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313页。,都要描写地理环境。所以此类赋中,多描述东西南北地理方位;京都赋还要描写宫殿园林,这里也有一个方位问题。《神思》云:“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里所说的“规矩虚位,刻镂无形”,虽然揭示了构思的一般想象特征,但是其抽象出一般理论的直接创作实际,则是辞赋的构思。过去,我们的研究多把“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概括为艺术现象中情感的注入,此种因素不能说没有,但非刘勰主要表达的思想。这里的情与意,实则就是指作家进行作品构思时的想象。衡量作家创作才华之多少,就是要看他能否按照表现之物的需要而展开想象。
京都辞赋的创作,不仅要描写山川地理、宫室园林,自然也要描写历史人文和物产风情,汉大赋的特点就是把世上同类东西集于一赋。大赋作家的想象,虽然不需要人物故事的虚构,却必须有跨越时空的联想,这也正是《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理论产生的直接基础。
诗赋的写作,在其艺术构思中,如何具体描写和表现物象,也是重要问题。这正是《物色》篇所讨论的中心。既往的研究关注的是诗人感物之说,而实际上,刘勰此篇论述的是诗赋家如何准确描写物象,即诗赋的艺术表现问题:“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 ‘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诗是如此,赋亦然:“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诠赋》)“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物色》)。这些理论现在已经被抽象为文学创作形象思维的一般特征了,而从具体语境看,刘勰此处论述的就是诗与赋中外物的具体描写,在艺术构思中如何恰当地表现物的特征。
大赋的写作,内容宏阔,天文星象、地理知识、历史典故、物产风俗,都要涉及,所以作家的两个积累至关重要:一是读书所获得的学识,一是阅历所获得的人生经验与事理。正因为如此,刘勰提出了使作家神思畅通的四个基本训练:“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神思》)“积学”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相比于其他文体而言,学识对于辞赋的创作至关重要。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班固、左思写作辞赋,主要依凭的就是他们的书本知识。“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事类》)。从《事类》篇所举作品实例看,刘勰设此篇,主要是为了诗赋写作的需要。当然后来左思于书本之外,也开始注意实地考察。在书本知识中,也包括了文字的功夫。汉赋作家,多通小学:“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练字》)有的就是文字学家,如司马相如著《凡将篇》、扬雄撰《训纂篇》,正如此,“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练字》)。这就不仅仅是积学的功夫,也包括了“驯致以怿辞”的训练。因为构思中如何恰切地表现物象,语言表现是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神思》)《文心雕龙》专设《章句》《丽辞》《练字》篇,解决的就是此类问题。所以这四句话,也是刘勰总结赋家的经验而得出的。
所以,把刘勰关于心与物的理论,放到产生作品的具体环境下,应该说,他是在诗赋创作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总结抽象出“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具有普遍意义的“神与物游”的文学创作一般理论的。
四、基本问题之二:情与采
情与采的问题亦包含了意与辞的关系,此为《文心雕龙》“割情析采”部分的重点。而此一部分的理论,明显是建立在对诗赋创作经验考察的基础之上的。
《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即今之文体论。六朝始有文笔之分,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刘勰即按此而分文体。自《明诗》至《谐》为“文”,《史传》至《书记》为“笔”。而“笔”的部分都是应用文体。刘勰在讨论这一部分问题时,极少涉及情,主要论文章的理、事、辞。《史传》:“析理居正”“务信弃奇”;《诸子》:“理懿而辞雅”“事核言练”;《论说》:“叙理成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心与理合”“辞共心密”;《诏策》:“腾义飞辞”尚“理得而辞中”;《檄移》:“辞切事明”“事昭而理辨”“言约而事显”;《封禅》:“事核理举”“义吐光芒,辞成廉锷”;《章表》:“言必贞明,义必弘伟”;《奏启》:“理既切至,辞亦通辨”;《议对》:“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断理必刚,摛辞无懦”。总之,不出理、事、义、辞,基本不谈情。这是因为此类文体主要的功能就是说理议事。说理尚圆通切要,议事讲审核明辨,若掺杂以情,会影响理正事核。如《诏策》批评汉光武帝刘秀“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若斯之类,实乖宪章”。就是因为他的诏书深受感情左右,影响了公文的平允。
而诗赋以及由此衍生的文体则不然,无论是表现之内容,还是决定艺术表现之“势”,情都是问题之核心。诗不必多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而且其作用读者之手段亦是情感,故刘勰训诗为“持也,持人情性”。衡量一个作品的标准自然也是情,在《明诗》篇,刘勰之所以给与《古诗》以很高评价,称其为“五言之冠冕”,就是它“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赋由诗出,因此班固说赋为“古诗之流也”。它与诗的分野,在“极声貌以穷文”(《诠赋》),即体物的“铺采摛文”“穷变于声貌”。然赋之体物不离“写志”。在刘勰看来,情依旧是赋所要表现的主体,与物一体,都是赋的“质”。《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赋之写作的触发,是辞人见到物兴发了情感,而在赋的写作中,辞人观物以情,亦要写物以情,这样才会使作品达到“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刘勰认为这才是赋之写作的正途。
诗赋写作,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情与采的关系,《文心雕龙》专立《情采》篇,即与此密切相关。文采问题的出现,不能不与诗赋地位的提高有关。尤其是辞赋,自汉而至齐梁,已经成为深受文士重视的文体。萧统编《文选》,以赋为首,刘勰论述文体,继诗与东府之后就是赋,而《文心雕龙》本身就是以骈体写成,都充分说明辞赋在文坛的突出地位。而在诸体之中,诗赋无疑最重文采,“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藻饰文辞是其显著特征,尤以辞赋为著。
当齐梁之时,刘勰必须面对关于文采的两种态度、两种倾向。一种是推尚文饰,变本加厉。对此文风,刘勰多有评论。《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通变》:“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夸饰》:“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亦注意到历代文风之变中,重辞藻的现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①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第六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78页。另外一种则是对文采的否定态度,如裴子野。据《梁书·裴子野传》:“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①姚思廉:《梁书·裴子野传》第二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3页。他的《雕虫论》即批评了东晋以来重文采的文风:“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②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七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页。如何看待文章的文采,需要怎样的文采,是刘勰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在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作品由内容与形式构成,因此二者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当然也是核心范畴。就此而言,中西、古今文学理论是相通的,刘勰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也把情与采作为其理论的核心范畴。因此诸多《文心雕龙》注本或研究文章,径直把情采翻译为内容与形式。不过《文心雕龙》考察的对象以诗赋为主体,因此情和采涵盖的范围与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论述情与采的关系,其揭示的基本原则,与内容决定形式相近,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文心雕龙》所说的“情”,主要指情感,在具体表述中,刘勰多用“情性”二字,如“文质附乎性情”,“辩丽本于情性”,“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有时也用“志”,如“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无论是“情”“情性”或“志”,其内涵基本一致。就此来看,的确如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所言,情的内涵只是内容的一部分,小于内容。而刘勰所说的“文”,更简单,就是文辞的藻饰文采,涵盖的范围更小于形式。③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20页。
研究《文心雕龙》情感与文采关系的文章甚多,然对其既特色鲜明又极富有创造性的文采自然说,鲜有揭示。在《情采》篇,刘勰肯定了辞采在文章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创造了文采自然说。同《原道》篇研究“文”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一样,刘勰讨论文采,也用自然来解释文章之所以需要文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认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圣贤的著述之所以命名为“文章”,就是因为它有文采。由此可见,文采虽然属于形式,却决定着文章的性质和属性。没有文采,就不会有文章,文章因为有文采才得以“立文”。文采为何如此重要和必要?这是因为人类抒写感情的需要,“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既然抒发感情是人性之自然,那么组织文辞以修饰之,使其表达得明确充分,就是自然的。神理之数,就是自然而成之意。因情而生文,文又需要文采把情充分表现出来,这一理论很显然是从诗赋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正是因为刘勰认识到文采之于文章的重要,所以探讨文章如何似雕刻龙纹一样写得美丽,就成为他撰写《文心雕龙》的主要任务。詹锳先生《刘勰与文心雕龙》论述《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提出修辞学,把《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都列入修辞学,而修辞学主要解决的就是文章如何修辞,即如何运用文采使其成为美文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没有诗赋的创作,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讨论以上修辞之事。尤其是《声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就带有更大的专属性,非诗赋莫可。
刘勰把文采的必然性抽象为自然,提升到决定文章属性的高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极有意义的理论事件,是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中国古代文学与欧洲文学有很大不同,欧洲文学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学为主,因此以人物、事件为主的形象是文学的主要特征。而中国古代文学是以诗文等言志抒情文学为主,即六朝时期所说的“文笔”。志与情不似人物、事件那么生动具体,因此文学的审美性特征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于作品所描写的事象、物象,决定于语言文辞的表现,因此刘勰所创造的文采自然说,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这一时期文人追求文章之美的努力。
文采自然说,立足于诗赋作品分析,不仅确立了文采在文章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规定了文采“本于情性”“附乎性情”,即从属于情性,为抒写情性而服务的属性。围绕这一问题,刘勰重点论述了情感和文采的关系:“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在文章中情感是表现的对象,位于文章的主体,文采次之。所以文章优劣,首先要看情感是否真实、深厚,此为一篇文章成功与否的关键。而文采存在的意义在于表现情感,衡量文采优劣的标准是其是否准确而又充分地表达了情感。关于情感与文采的关系,刘勰总结出两种类型:一种是《诗经》为情而造文的类型。诗人心中郁结着不得不发的情感,发而为诗。诗的文采是吟咏性情而自然形成的,故语言极为精炼,情感亦真实。另外一种类型是辞赋为文而造情的类型。作者本没有情感,却为了写文章而虚拟情感,结果造成文章的浮华艳丽。可见文章中文采是否得当,关键还是在作品的情感,即内容。“繁采”原因在于“寡情”,“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情感真实,内容充实,文采就不会浮滥。刘勰论述情感与文采的关系,并非割裂、孤立地讨论文采,始终是从情感及其表现出发加以考察和论述,这是《文心雕龙》的高明之处。
情与采的主从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因此必然涉及情感的艺术表现理论,为此刘勰又设有《风骨》篇。刘勰创造的“风骨”概念,究竟是何性质,学界分歧很大,有代表性的意见可归纳为“理想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要求”。二者皆接近这一概念的内涵,但似乎失之过泛。具体而言,“风骨”论述的核心是文章的艺术表现问题。所以,刘勰把创造“风骨”定性为“文术”和“文用”。
风骨一词,六朝已经流行,主要用于描写人物。《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晋安帝纪》:“羲之风骨清举也。”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5页。《宋书·武帝本纪》:“风骨奇特。”②沈约:《宋书·武帝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王韶之和沈约以“风骨”标举人物,这与魏晋南北朝盛行人物品评有关。但也正因为如此,“风骨”的内涵并不清晰,是带有明显的印象式描绘的语词,而且很少见到用于诗赋评论。刘勰使用“风骨”讨论文章,其功不仅在于把品评人物和绘画的语词转移到诗文理论上来,更在于他使这样一个印象式的语词变成了内涵清晰而又丰富的理论概念,并以此建构了系统而又独特的风骨理论,最具中国传统批评的特色。
在《风骨》篇,刘勰赋予“风”和“骨”以明确的理论内涵。
“风”对应的是“述情”,即情感表现。什么样的情感表现才形成“风”?就情本身而言,文章所表现的情感要“意气骏爽”,它不应是低沉阴郁的,而应是昂扬清朗的,这是其情感基调。而就情感表现来说,首先,有“风”的文章“述情必显”,一定是表达鲜明的,意气骏爽不仅是指所要表达的情感的基调,同时亦指情感表现的明快性;其次是思维周密,富有条理,具有逻辑的力量;其三,是文章要才气充沛,生气勃勃,富有感染力;最后是音韵流畅,因为这也直接关系到情感表现是否具有感化读者的力量。刘勰讨论问题,多有例证,所及作品,除了作为典范的经书,主体是汉魏以来的文章,“割情析采”部分所引文章集中在诗赋,而且多具有代表性。但此篇所举二例却颇遭诟病。不过,刘勰称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风力遒劲,显然是强调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汉武帝读《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可证辞赋有了风力,对读者的影响有多大。就此可以看出,刘勰论“风”,重在阐述情感表现,而非情感本身。
“骨”对应的是“铺辞”,即辞藻的运用。如何使文章备“骨”?“结言端直”是其一。这里既涉及到措辞要使用正确语言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使用语言的态度必须端正。六朝文风之中,有一种现象引起刘勰的高度关注,即追求使用奇字,认为奇字怪字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刘勰认为,出奇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能够准确表现情感变化,非此就是写作时使用语言的态度有了偏差。对此,刘勰批评说:“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不是为文的常态。练“骨”其二是“析辞必精”,选择文辞要精当,这就需要反复推敲锤炼,使文字坚实到一字不移。文字的精准,自然是针对文义的表达而言的。刘勰用以描述“骨”的特征,就是“刚健”。刚健就是文辞表达思想情感简练有力,没有游离的多余的辞藻,即所谓的“丰藻”“肥辞”,“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文义贫乏,徒然堆砌辞藻增饰,那就使文章变成了拖着肥肉、举翅无力的野鸡。刘勰赞许潘勖《策魏公九锡文》,也是因为此文在文字上取法经书,呈现出文字“昭灼”的特点。
《文心雕龙》设立的话题,既来自文学史现象,也生发自现实中文章写作的具体实践。“风骨”这一概念的提出亦然,它的出现并非偶然。齐梁整体文风是追求新奇,文章盛藻饰,文体讹滥。文士追逐这种文风,无非是为了提高文章的表现力,这恐怕是比较普遍的认识。刘勰拈出“风骨”概念,就是表明,文章的表现力量产生于情感的鲜明表达和文辞的精准确实。花样翻新、辞藻泛滥,非但不能增加文章的艺术表现力,反而会淹没文意、买椟还珠,损害了文章的表现力,丧失其感染力量。正是出自这种考虑,《风骨》篇用了很大篇幅讨论“风骨”与文采藻饰的关系:“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文章有风骨而缺藻饰,固然还有强大的表现力,如鹰隼之高翔,但是色彩不鲜艳;而文章虽有文采,却缺乏风骨,则似野鸡在地上乱窜,基本没有什么表现力。由此可见,比较风骨与藻饰,风骨对于艺术表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文章具备了风骨,再加以文饰,那就会更增加其艺术表现力,就应该是文苑的鸣凤,属于文章精品了。
总之,刘勰借“风骨”所确立的为文“正式”,就是鲜明而又刚健的艺术表现力量,有了这一表现力量,文章会传播得更广,影响力更大,刘勰形象地把其比喻为“征鸟之使翼”、鹰隼之“翰飞戾天”。
从文采自然观点出发,刘勰还提出了文采的最高境界,或曰理想的文采,是“贲象穷白,贵乎反本”,最好的修饰是返回本色。而文章的本采是来自情感本身的魅力:“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这样的观念,与孔子“辞达而已矣”的思想是相接的。文采不在多,而在适当。文采之美决定于情感,而不在辞采的自身。在六朝重文采辞藻的风气下,刘勰提出这样的情采理论,自有其纠正讹滥文风的意义。
五、基本问题之三:体与性
学者对于体与性的内涵有多种解释,一般倾向于认为指文章风格与文士的个性。①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185页。与心物、情采这两个话题相比,体性不似前二者明显指向诗赋,其理论更具有普遍性,似乎适用于所有的文体。风格和作家个性是所有文章都具有的问题。无论是诗赋为主体的韵文,还是以公文为主体的散体,只要是成功之作,一定有其个人风格;成熟的作家,在写作中也一定会把其个性发挥到极致,并贯注到其作品中去。
然而从《体性》篇所举例子来看,刘勰研究体与性的文体,仍主要依据于诗人、辞赋家及其作品:“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这里是刘勰举例讨论体与性的关系,所举之十二个文人:贾谊、司马相如、刘向、班固、扬雄、张衡、王粲、刘桢、阮籍、嵇康、陆机、潘岳,多是以诗赋为主的作家。自然这些作家多数是诗文兼擅的,不过,但凡《文心雕龙》所论及的,主要是他们的诗赋。此处论贾谊,说其“文洁而体清”。《才略》云:“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哀吊》云:“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周而事核,辞清而理哀。”洁而清的风格,由其辞赋显示出来,还有主情且为韵文的哀吊。司马相如文章“理侈而辞溢”。《诠赋》:“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才略》:“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物色》:“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显然指其辞赋。扬雄既是辞赋家,又立志子学,著《法言》《太玄》,其文晦涩艰深,所谓“志隐而味深”者,是否指此类文章?证之以《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似乎不是如此。《诠赋》:“子云《甘泉》,构深伟之风。”《练字》:“扬、马之作,趣幽旨深。”可见亦来自辞赋。文中言班固“裁密而思靡”。《封禅》:“《典引》所叙,雅有懿采。”雅丽似与裁密思靡不符。《诠赋》:“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赡者,丰富也,正与“思靡”相合,可见“裁密而思靡”说的是班固的赋作。平子即张衡,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辞赋家,《文心雕龙》中多有论及,仅下篇就谈到九次,仅次于司马相如和扬雄。淹通,即《才略》篇说的“通赡”,乃言张衡的才性。而“虑周而藻密”,即《杂文》“结采绵靡”,是对其《七辨》的评价。“七”体皆被刘勰列入杂文系列,如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萧统《文选》亦分类为“杂文”,说明六朝时期,“七”与“赋”别为一体。但今人研究辞赋,认为“七”体是赋的分支,故费振刚编《全汉赋》收入“七”体文章。说明“七”的文体特征与赋相近,泛称为辞赋应该没有问题。《诠赋》:“张衡《二京》,迅发而宏富。”“宏富”与“虑周”相关。在以上辞赋家中,唯刘向“趣昭而事博”无法证明所指是哪一类的文章。此人既是著名经学家、学者,又是辞赋家。然《文心雕龙》论之甚少。《时序》云:“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未及体性。《才略》云:“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旨切”或即“趣昭”。果然如此的话,汉代的作家,只有刘向的风格,未以辞赋为例。
至于汉末及魏晋作家,所论风格主要是诗赋,此更明确。《才略》:“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此正言“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虽然各体都擅长,但以辞赋最好,其风格个性也体现得更为突出。关于刘桢的个性和文章风格,《才略》篇有“刘桢情高以会采”之评价,未明什么文体。然刘勰同时代评论家钟嵘《诗品》评价刘桢之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可证“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总结的就是刘桢诗的风格。正始名士阮籍、嵇康,《明诗》分别评价为“阮旨遥深”和“嵇志清峻”与此篇所论之“响逸而调远”“兴高而采烈”接近。又《书记》说“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亦切合此篇关于嵇康风格的描述。说明,阮籍和嵇康的风格,主要总结自诗,亦兼顾到了文。潘岳和陆机亦如是。《才略》:“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熔裁》:“士衡才优,而缀词尤繁。”此即“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但未言何体。虽然以上篇章未明文体,但《明诗》篇对西晋诗人有一总体评价:“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流靡”切合“韵流”,与潘岳相合;“采缛”而“辞隐”,适用于陆机。由此可知,《体性》对潘、陆风格特色的描述,主要来自诗。然《哀吊》曰:“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说明“文繁”是陆机诗文的总体特征。
刘勰以诗人和辞赋家为例讨论体与性,应该是充分考虑了风格形成的各种因素。文章风格,虽然由作家个性所决定,却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体的影响。文章既有作家的个性风格,还要受文体风格的制约。曹丕《典论·论文》论四科八体,就是文体风格,陆机《文赋》演变为十体,即十种文体的风格。文体风格是文体规格要求的总体呈现。比较而言,应用为主的公文,受其使用范围、使用功能的决定,文体风格会直接制约作者个性的发挥,因而也最不容易形成文章的个性风格特征。如章表奏议,目的在于明事说理,张扬个性,辞胜于理,反而会影响到论理说事的平正,效果适得其反。因此,应用文体如果说也有风格的话,其文章所呈现出的也应该是文体的风格特征。而诗赋这一类以审美为特性的文体,最需要也最容易发挥文士的个性,因而个性之于风格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和明显,其所呈现出来的文章风格才是作家风格。所以,讨论风格与个性,诗赋最为典型。
《体性》创造了中国最有系统的风格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之一,就在于认识到了“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文章风格的存在。而文章风貌之不同,乃来自于文人的情性和陶染,具体说决定于文人的才华、气质、学识和习染:“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此段话深入阐发了文人的个性之于文章风貌的决定性影响。其二,总结出八种风格类型,并概括出每一种风格的风貌特征:“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 ∶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为文人自觉追求风格指出了途径,同时也为读者把握风格特征提供了样板。自然,文章风格丰富多彩,不限于以上八种,刘勰的概括似乎比较刻板。但能够在众多的文章中总结出八种风格,并描写出其基本风貌特征,仍是一件艰难而值得肯定的工作。其三,对文人的个性做了更为深入的辨析,将其分为先天的才、气与后天的学、习:“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此四个因素中,才、气为左右文人风格的主要因素,是“盟主”;学、习则为次要因素,是“辅佐”①《事类》:“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由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刘勰尝试探讨个性的四个因素分别对文人写作的作用:才情气质决定着文章风格的刚柔和文辞义理的平庸与杰出与否,学识和习染则影响着用典的深浅和体式的雅与俗;前者偏重于文章的内容,后者偏于文章的形式。从影响的不同看,的确是才情气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总之,《文心雕龙》研究的虽为文章之学,其“割情析采”之创作论,赖以建立的基础则是以审美为特征的诗赋,其基本理论亦多围绕诗赋写作问题而展开。任何理论的形成皆非空穴来风,都离不开时代风气,《文心雕龙》亦然。魏晋以来,即逐渐兴起重辞采之风,所以才有齐梁时期文笔之辨,欲把以审美为特征的文章独立出来,而诗赋就是“文”体中的核心。就此而言,《文心雕龙》自然是体现了此一时期文风倾向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