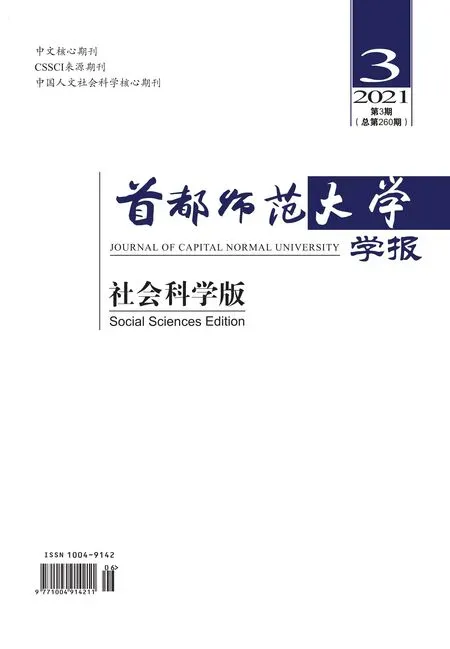《捉拿康梁二逆演义》考
——时事小说与戊戌政变史再解读
陆 胤
康有为、梁启超为清季政坛风云人物,各种笔记、小说颇载录其逸事。通俗小说方面,较知名者如黄世仲(小配)撰《大马扁》十六回,刊于宣统元年(1909),从革命党人立场出发,叙述康有为及其门徒的“行骗”史。《大马扁》的叙事时段,始自康氏剽窃缪寄萍(廖平)的《新学伪经辨〔考〕》,讫于政变后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多处采取了黄世仲自撰的其他小说和当时革命派报刊上嘲讽康、梁的材料。此外,《孽海花》等小说中也有大段影射康梁的文字。然而,诸书所述康梁行实,止于戊戌政变前后,距离成书已有多年,更应划入“近史小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时事小说”。①时事小说强调题材的时效性,其所记载事件的年限,应根据不同时代信息传播的效率来界定。陈大康曾将晚明时事小说问世与所描述事件结束之间时间差的最大范围定在“十年左右”。清末报刊、电报、邮政等新媒介涌现,对时事小说时效性的要求,至少应高于晚明。因此,与戊戌前后史事相隔十年以上的《大马扁》,自不应再视为时事小说。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31页。
本篇将考论另一部康梁题材的通俗小说《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因其成书于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对考察当时舆论环境或不无意义。而作为一部基于反维新立场的时事小说,《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上承明季以来时事小说传统,不仅采录见于京报或报刊的上谕、摺奏等官书文献,又利用当时各种时事报道乃至士大夫口耳相传的逸闻,部分记载颇具史料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归在杨深秀、林旭名下的“狱中诗”,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等主流历史叙述所载通行版本颇有出入。比勘之下,小说本可能更接近原初面貌。历史叙事与小说构思并非截然划界,即便是主观立场浓厚的时事小说,也有可能比史撰更近“真实”,或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对历史叙事进行“再解读”的入口。
一、版本形态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著录《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四卷四十回,题古润野道人著,有光绪己亥(1899)石印本四册,又翻印大本四册;①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此书还有《中国近代小说目录》著录的光绪戊申(1908)上海书局石印本,②王继权、夏生元编:《中国近代小说目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以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录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③此本内封题“维新小说康有为”,目录与卷端均题“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无序跋,不题撰人;有绣像六幅,正文半叶20行每行45字。参见《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823页。郑振铎《西谛书目》著录有石印本《绣像康梁演义》(四卷四十回)一种;④郑振铎:《西谛书目》,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64a页。孙楷第亦著录“坊间石印本”《康梁演义》(四卷四十回)一种。⑤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此外尚有“伏魔使者撰、却邪居士评”《康圣人显圣记》四十回,有北京文盛堂光绪己亥刊本。⑥阳世骥:《文苑谈往》第一集,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111—113页。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13版)将上述《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三版本及《康梁演义》、《康圣人显圣记》分别著录为五个条目。⑦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13版)K0047、K0053、Z1578-Z1580条,清末小说研究会2021年版,第2555页、第2556页、第6605—6606页。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及《绣像康梁演义》二种。
《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四卷四十回,石印巾箱小本,四册。不题撰人。白口,单黑尾,无界栏,四周单框,版心中署卷数、回数、叶数,正文半叶13行行30字。有目录。书前有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初)古润埜道人撰序:
自古佥壬邪佞挟阴险诡谲之计,以济其贪婪诬罔之私,辩言乱政,蠹国害民,上与下交受其祸,至今读史及之,犹令人眦裂发指,废书三叹焉。而当其时,里党相揄扬,僚友争推荐,君若相亦深信不疑,鲜有能发其奸者,何也?采虚声而不察实行故耳。世有君子而不敢自信为君子之人,断无小人而自居于小人之人。且微特不肯自己小人己也,阳与君子附,阴与君子仇,甚至援君子于小人,而以小人冒君子,植党羽,结奥援,互相标榜,为之游扬言名誉,致令正人志士误入牢笼中而不悟,迨变乱成章,排击善类,天下骚然不靖,然后知其前之误也,不已晚乎?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即此之谓欤?是为序。时在光绪己亥嘉平月古润埜道人撰并书。
题署“古润”,则作序者当为镇江人,大抵以康、梁为阴险小人而能攀附君子,既叹息君子为小人所误,又痛恨小人依草附木、混淆是非、变乱清议。所谓为小人所误之君子,当指引荐康、梁的翁同龢、张荫桓、李端棻等人。
此外,该本正文前有绣像六幅,每幅二人,分别为:(一)至圣先师、如来佛;(二)外国教主、元始天尊;(三)康有为、梁启超;(四)杨深秀、康广仁;(五)刘光第、杨锐;(六)谭嗣同、林旭。
《绣像康梁演义》四卷四十回,石印巾箱本,但其开本仍比《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略大。合订一册。北大藏本为潘景郑旧藏(内封有“潘景郑所藏说部秘籍”印)。有内封,署“绣像康梁演义”,下题“子明氏署”。不题撰人。花口,单黑尾,无界栏,四周双框,鱼尾上署“绣像康梁演义”,版心中署卷数、回数、叶数,正文半页17行行32字。有目录,无序跋。查其目录与内文,知与《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实为一书,但并非翻印。《康梁演义》纠正或修改了《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若干错误。如第十五回述保国会事,《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云:“当时如宋伯鲁、杨深秀,以及康之门生谭嗣同、杨、林旭,还有不知名姓的多人,在会馆聚议其会曰保国”,不仅脱落杨锐之名,且杨锐实为张之洞门生,与康氏并无师生之谊。《康梁演义》此句作“当时如宋伯鲁、杨深秀,以及康之门生谭嗣同、林旭……”,删去“杨”字,应为后出的改正。可知《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当较《康梁演义》更接近小说文本的原初状态。
《康梁演义》书前亦有绣像,共四幅,每幅三人:(一)至圣先师、元始天尊、如来佛;(二)外国教主、康有为、梁启超;(三)杨深秀、林旭、康广仁;(四)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绣像所绘与《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完全相同,唯杨锐与谭嗣同二人形象被互换。《康梁演义》三人一组的绣像也许更符合小说内容。因为小说末尾讲述儒、释、道三教教主联合捉拿康、梁“二逆”,而康、梁则受外国教主保护,最终掀起中国三教与西方各教的战争。作者竟把“英吉利的耶稣、法兰西的天主、美利坚的基督”看作是三位西方教主,且捏造出所谓“噜国”教主首先向子路、韦驮、赵元帅组成的三教联军发难。三教教主属于一个阵营,外国教主和康梁属于另一个阵营,颇能表现戊戌、庚子间朝野的反教排外思想。
小说第四十回末云:“你道这一道檄文赍去,那西国等教,不但不能奉行,而且更加袒护,所以后来儒、释、道三教,成了骑虎之势,于是兴师问罪。西国各教,亦兴兵抗敌,在英国大败迷云阵,儒、释、道三教议破‘迷魂阵’(据《捉拿》本,《康梁演义》作“迷云阵”),康有为逃往美利坚,儒释道三教议设十面埋伏阵,捉拿康有为等事,奇奇怪怪,颇有可观,俱于续集详载。”可知此书尚有续集的计划。
二、多元材源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时事材源,既有京报或报刊转载的摺奏、上谕等官书,也有当时报章的新闻报道;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很可能是士大夫口耳之间流播的传闻,见于同时代书信、笔记等私家材料。
小说开头套用章回小说常见的神话框架,叙述康、梁本为星宿托生,分别是心月狐与虚日鼠,“妖狐之性,最善感人;鼠耗之精,怪能钻洞”(第一回,以下引文均据北大图书馆藏光绪己亥序刊本《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以表现二人魅惑、钻营的本性。此类怪谈当然出于虚构,但也并非毫无凭据。康有为为狐之说,目前尚不知何出;而目梁启超为耗子精,则是当时士大夫间流行的议论。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沈曾植在给王彦威的信中提到:
恭读十一月十六日诏书,慈恩浩荡,海内人士,同声感泣。康逆平生伎俩,专藉名流名字,上欺显宦,下罔生徒。如朱蓉生(一新)、文仲躬(悌),皆其徒所称为康逆讲学至交者。文幸身为台官,得以上书自白;蓉生身后著述大行,彼党不得以一手掩天下人之目。自此以外,有辨奸之志之言而闇汶不彰者,固屈指难数矣。闻有人物表一册,多载海内名流,贱名亦遭窜入其中,加以诋之语,未知确否?有所闻,幸望示知。天祸人国,生此妖物。(原注:芍翁[李文田]常目为耗子精。)当春间出都之时,曾告诸公此人未可轻视,能令出洋最好,无如人之不信何也?(原注:彼不得君,固不能肆其猖撅,出洋而少给经费,困之有余矣。)①沈曾植:《与王彦威书》,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书信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43页。
沈曾植此信论“康逆平生伎俩,专藉名流名字,上欺显宦,下罔生徒”云云,正与小说书前“古润埜道人”序中指责康、梁“援君子于小人,而以小人冒君子,植党羽,结奥援,互相标榜”诸语相合。沈曾植最初名列保国会,提倡变法甚早,与康有为亦颇有往还,但戊戌前后转而批评康党。这固然有划清界限以自保的用意,更重要的还在于不满康氏的冒进政见与虚妄学说。沈氏不仅泛称康有为一党为“妖物”,更记下李文田曾确指其人为“耗子精”。李详《药裹慵谈》有“沈乙庵述李若农善相”一条,述此事更详:
李若农先生文田以善相名,乙庵(沈曾植)其门生也。一日集沈所,门者以梁启超刺入,沈亟白李曰:“老夫子曾言:吾乡新出梁生,足为粤人生色。今其人来,可以一谈。”及梁入,李骤色变,翅须咏齿,若无所见。梁窘甚,辞出。沈云:“往者老夫子于梁闻声相慕,今何蓄怒以待?”李云:“耗子精,扰乱天下必此人也。”②李详:《药裹慵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按此条材料已经许全胜引出与前信互证,参见氏著《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0页。
此条笔记将“耗子精”指为梁启超,似与沈氏信中所述有所出入。实则此类士大夫风传奇闻本在疑信之间,但小说却将之坐实为人物的出处。
小说作者对康、梁二人的情况似乎相当隔膜。如第二回以康、梁为同县人,康有为原名“康直”,且以康、梁二人为朋友而非师徒,叙述康有为在童生覆试时即与梁启超相遇等;又如第十回述戊戌以前康有为赴外洋游历四载,凡此俱与史实相差甚远。而虚构康有为的出游经历,恐怕还是为了解释康氏这样的“小人”何以能够欺骗众多朝中“君子”(第十二回),并把政变责任最终推到洋人和“西学”身上。(第七回)
尽管如此,在叙述有关康梁变法的内容时,小说作者还是搜集了一定数量的史料,其中大部分是“百日维新”期间各种奏摺等公文。作者很可能从当时报刊转载的京报或宫门抄上获得这些材料。小说第十六回至第二十五回几乎就是新旧各派诸人奏折的缀连,兹考得所引折奏、上谕、章程的部分材源,排列如下表: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页。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80—482页。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30—432页。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32—434页。⑤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9页。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82—489页。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0—255页。⑧ 载《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卷二,此本当时并未公布。该摺修改本题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载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知新报》。小说作者看到的当为《知新报》本,知作者对当时各派报章有广泛的采取。
小说引用奏摺等官书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这些章奏、上谕为叙述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旧纷争提供了框架。作者全引或节录这些文书时,并未完全依照时序排列,而是按情节进展的要求穿插文中,自然难免简化或扭曲某些材料的原意。如第十九回述孙家鼐奏改《时务报》为官报,其实改官报之议本就出自康有为:当初《时务报》馆中代表张之洞势力的汪康年与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多有龃龉,康有为等遂草摺交御史宋伯鲁出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并进呈御览。此举本意在于驱逐汪康年,进而以“官报”之名掌控全国舆论。⑨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32—434页。上谕交孙家鼐议复,孰料孙氏竟顺水推舟,奏请以督办官报为名,调康有为出京。⑩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49—556页、第567—572页。如此云谲波诡的政治角力,在小说中被叙述为“孙中堂因《时【务】报》恐多关碍,即奏请以《时【务】报》改为官报,并批章程三条……”,不仅孙家鼐成了《时务报》改官报的发动者,奏摺背后的立言动机也一概略去,改官报之议只是旧派主动狙击康、梁的一项举措而已。
其次,奏折内容亦可直接转化为小说情节,如小说第十四回述康有为拜访阎迺竹(阎敬铭子)事,第十五回所述许应骙阻止康有为立保国会,第二十二回述林缵统请托文悌事,以及同回述文悌误入康有为内室得闻密谋事,都来自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文悌《严参康有为摺稿》。其中文悌误入康有为内室一节,尤富于情节性,文悌原折云:
……(奴才)遂于(四月)初八日至康有为寓所,其家人因奴才问病,引奴才至其卧室。案有洋字股信多件,不暇收拾,康有为形色张皇,忽坐忽立,欲延奴才出坐别室。奴才随仆,又闻其弟怨其家人,不应将奴才引至其内室。奴才乃匆匆起立,惟告以《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不可分门别户,致成党祸,置国事于不问。
而小说第二十二回则将此数句敷衍成半回篇幅的情节:
这日文御史出城,至广东会馆答拜康有为……康有为的家人,将名帖接去,知是文御史到此,以为自家主人,与文御史向有来往,并不先去通报,随请文御史进入里面,引到内院屋中内书房坐下……这内书房原是康有为私自办事之地,许多机密,非同党之人,不能进内。那家人以为文御史亦系同党中人,遂将文御史引入里间。文御史坐下,但见案上有洋文信件不少。御史平日也通知洋文,便走至案旁,随便看了两件,见上面写着许多暗语,不甚了了。正欲再取一两件细看。但见康有为仓皇匆迫,从外而来,望着文御史,勉强作了揖,那两只眼光,直射在案上,望了两眼,忙与文御史道:“蒙荷眷顾,有失迎迓,此地狭窄得很,请在外厅坐罢。”说罢便邀出来。……文御史一面与康有为说话,一面留心听那外间,唧唧喳喳,像似有人说话。再一细听,但闻说道:“这内书房,是个机密之地,许多紧要事件,何能使外人进来。你们但见宋(伯鲁)大人他们一起,时常进内,他是我们圈里人,故不妨碍。这文大人你老爷虽常去他那里,十次到有六次会不见,就使见着,稍一劝他入会,他便拒绝不从。可见与我们不类。今日将他请在那里去坐,案上许多要件,万一给他瞧出来,泄漏出去,误了大事,那时如何说法?况且他又是满人,尔等如何这样粗心,毫不检点?”底下还有许多话,却越发低了,听不出来。……你道那外间说话的是谁呢?原来是康广仁,在那里抱怨家人,不提防被文御史听了明白。
此外,这些折奏还为这位对康、梁了解甚少的作者提供了想象康、梁早年生涯的材料。如许应骙折中有“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语,小说第三回、第六回即描述康有为居家时“揽词讼作事荒唐”“恃功名甘心作刀笔”的劣迹。又康有为有改乡邑淫祠为小学堂的上奏,小说第三回至第五回便有康有为先后敲诈“宝珠寺和尚”“洞坤宫道士”,最终引起公愤,被革去生员的情节,以说明康有为与僧、道结仇的渊源。
然而对这部“近代时事小说”而言,最直接的资料来源可能还是报章。小说在描述康有为早年生涯以及变法事迹时,不仅多想象虚构,较为符合史实部分也往往采用粗线条的勾勒法。但在第二十七回以下叙述政变发生后康有为逃亡的历程时,却相当详尽。第三十一回述“布罗网逆贼幸逃亡”,直接点出系取材自“英国报馆新闻”,与《中外日报》《字林西报》等对康有为外逃的报道相当接近。①《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日报道康有为改乘重庆太古轮南下,并最终在西人帮助下逃脱;而英领事则因为上海道此前之骚扰禁止华官上船搜查等事,与小说所述甚为接近。而第三十二回叙述康有为在香港答记者问,亦有《字林西报》的报道。此外,小说也采取了见于报章的部分捉拿康、梁传闻,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国闻报》有报道:
昨日上午八点钟忽有探马报到,说康有为在新河小船上蒙被而卧,有日本人数人为之保护,请速派兵往捕。中堂正在入都启节时,即与袁慰帅密商,饬传天津县并招商局黄花农观察带同捕役兵丁数十人前赴新河、塘沽等处会拿,并闻提督聂军门亦带兵一队前往。及至新河,下船查询,知船上均系日人,某疑为康有为者,乃一年约二十左右之中国人。于是大众始知探报者误传,而日本驻泊塘沽之兵船,闻有中国官兵欲至日本船搜查之说,即传令列队准备,以防不测。嗣赴沽者陆续回津,始知此事之真同捕风捉影也。
此事即小说第三十回“以讹传讹捉拿逆贼”所本:
初十日,荣中堂(禄)正奉到电谕入都,一时忙碌异常。忽有人来报说,本日上午八点钟,康有为在新河小船上蒙被而卧,时有日本人数人为之保护,请速派兵前去捉拿。荣中堂闻报,即飞报之袁慰帅、聂军门、黄观察、吕大令,各带兵丁干役,驰至新河,各乘快船,追赶前去。直追至塘沽,果然见上流头有只小船,在前面扯满风帆,直驰前去。袁慰帅一见那小船,乘作风如飞而去,亦喝令各船上水手,齐将风帆扯起,迅速赶来。将至塘沽口外,离那小船不远,各兵齐声喝道:“前面小船听着,我等奉荣中堂之命,闻说康有为在尔等船上安住,特地前来提他。尔这船只,可速速停泊,以便我等搜拿。”那小船上隐约间听不清楚,仍往口外驶去,这边见那船不睬,仍自驾驶如飞,更加信以为实,因即驾上双桨,加力飞划,追赶前去。看看逼近,相离约有一箭多路,袁慰帅坐船上有一个当差官,踊身一纵,登时跳过那船,赶将那船上风帆落下,随后袁慰帅等人,纷纷齐至,逐一搜检。见船上皆系日本商人,内中只有年约二十以外之中国人一名,系因抱病,蒙被而卧。于是众人方知探者误报,只得仍上本船,驶回而去。
对得报与派兵的描写,小说与《国闻报》大同小异;塘沽口追赶一节,则为添加的成分。然而,小说对报纸报道也有所别择。比如,当时中西各报颇记载康有为进药饵谋害光绪帝的传闻①如《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报道:“据北京西友来函云:本月初六日皇上未理朝政,皇太后询问原由,经内廷大臣奏称皇上圣体欠安,因服康有为所呈进药饵所致。皇太后闻之大怒,……”,从《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作者的立场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材料,却未被采纳。小说作者宁可采用官方的“谋围颐和园”说。
三、杨深秀、林旭狱中诗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第三十五回,述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康广仁等人将被处决,“杨深秀在刑部监内,自知不免一死,于(八月)十三日晚间,吟诗数首”;第二天将赴刑前,林旭又吟诗两首。②按“六君子”就义当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捉拿康梁二逆演义》误为十四日。小说将二人的五首诗全部转录,与后来各种通行版本不尽相同。其文字出入之处,如下表所示:小说第三十五回回目为“逆党株连市曹伏法”,在杨、林等人赴刑时,着力描写其懊悔被康有为牵连的苦状。故小说作者征引二人狱中诗的立场,与梁启超表彰“六君子”的用意截然不同。

杨深秀三首

林旭二首
杨深秀狱中作诗,可证以当时刑部司员唐烜所作《留庵日钞》:“八月廿四日……在署见有狱卒由狱内抄出杨侍御深秀诗三首,均七律。杨素工诗,其稿已刊。被逮在初九日,至十一日送部入狱后得诗一首,次日又成一首,十三日午刻后即奉即行正法之旨。临刑已日夕矣,盖此日清晨,尚用香火划壁成诗也。观诗中词意,皆以直言敢谏、御侮破敌为言,非本事诗也。”③此日钞由孔祥吉发现,转引自氏撰:《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及其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版的《清议报》第三册载有此三首诗,并在三首诗下分注“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与《留庵日钞》所记相同。但《清议报》本缺第三首首句,小说所载则为足本。所缺“自许清操不受污”一句,正可用来表现杨深秀入狱时不愿被康党牵连的意愿,符合小说立意,却显非梁启超等所能容认。第二首小说本“有意筹边”“臣狐”等语,《清议报》本作“安耻□(汉)边”“孤臣”,很可能是为了跟对句“当思殷武”“酷吏”对仗而作的改动,但也使诗意有所变化:“臣狐”(《左传·宣公二年》董狐记赵盾弑君事)指史官直笔,称史笔化为“隍中鹿”(《列子》蕉下覆鹿事),似有不传心事的遗憾;《清议报》本作“孤臣”,则仍为康党中人自高身份之语。下句“殿下鹰”用《史记》《汉书》酷吏传郅都号为“苍鹰”的典故,小说本“差”字略有期待之意,《清议报》本“羞”字则显为谴责。
小说归为林旭所作的“吟诗二首”版本差别较大。第一首放在林旭名下大概较少异议。④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七:“戊戌六士之难,暾谷(林旭)在狱中,有一绝句:……当时疾暾谷者谓暾谷实与谋,袒暾谷者谓此诗他人所为,嫁名于暾谷。余谓此无庸为暾谷讳也。”可知最初亦有不同意见,但与林旭为同乡且颇有交往的陈衍则论定此首必出自林旭。参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其本事是政变之际,谭嗣同等主张鼓动袁世凯,林旭则主用董福祥,卒从谭议而致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林旭传》称:“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推〔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⑤任公:《戊戌政变记·林旭传》,《清议报》第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照梁说,则此诗当作于政变以前,非如小说所云作于赴刑前。⑥陈衍亦认为此首作于政变后,用的是“倒戟而出之法”:“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乃追溯未败之前,吾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参见《民国诗话丛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林旭此诗又见《晚翠轩集》,题为《狱中示复生》,除首句“无补”作“何补”、第三句“欲为”作“愿为”外,与《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所载全部相同。⑦林旭:《晚翠轩集》,民国二十五年序墨巢丛刻铅印本,第42a页。《林旭传》本经梁启超改窜,“难酬国士恩”变为“何曾报主恩”,大概是为了强调保皇思想,以适应己亥、庚子之际的政治形势。
小说所称林旭诗第二首,即为通行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另一版本。但小说本与通行谭诗非但设定作者有别,字句也还有所出入。首句小说本作“怜张俭”,通行谭诗本作“思张俭”,一“怜”一“思”,二者态度之不同立见。史载张俭“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结果却导致“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惨剧。以之指代当时亡命在外的康、梁诸人,或将祸连无辜,表达林旭懊恨之意,正与小说宗旨相合。①若指为谭嗣同所作,则此“张俭”可理解为自指。如李肖聃《星庐笔记》:“时康有为已出亡,复生不知其能脱险与否,故以张俭相况。”参见《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09页。第二句小说本作“直谏陈书愧杜根”,不仅切合林旭谏官身份,更影射了当时帝后对峙的形势:杜根直谏汉安帝亲政而几为邓太后所杀,最终遇赦隐居;小说本安在林旭名下的诗句,显然是欲以杜根自比,正可说明林旭对于免死尚有所希冀。通行谭诗此句作“忍死须臾待杜根”②关于归于谭嗣同名下的此诗,史学界颇多讨论。黄彰健《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指出此诗表现的应为八月初六日政变后,初七、初八日谭嗣同被捕以前的心情。同时,黄彰健早就发现《绣像康梁演义》载有此诗(但将此书误为光绪三十四年初版),认为小说本当为谭嗣同入狱后修改的版本,为真正的谭嗣同狱中诗,“狱中改本”(即小说本)最终被梁启超隐晦而未能刊布。但黄氏亦未能注意到此前《国闻报》已披露此诗的“狱中改本”,并将其系在林旭名下(详下文)。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第808—538页。孔祥吉《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及其传抄本的发现及其意义》转引当时刑部司员唐烜《留庵日钞》,据说载有此诗的“最早版本”:“(八月)廿五日……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杜〕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孔氏认为此材料正可证明梁启超《谭嗣同传》对谭嗣同诗的第四句确未改易。参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200页。,“杜根”指他人,一般认为此句表现了谭嗣同对“行者”的期待。③前引《星庐笔记》:“其称杜根,以拟大刀王五耳。”左舜生《万竹楼随笔·我眼中的梁启超》附录四《释谭嗣同狱中题壁诗》:“谭盖以邓后拟贪位恋权之慈禧,安帝拟光绪,而己则不望为倖免之杜根也。”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2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41—14742页。小说本与通行本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间最大不同还在于末句:一作“留将公罪后人论”,一作“去留肝胆两昆仑”。学者早已注意到“公罪”一词可能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以谋反为“公罪”(即后来所说的“国事罪”)的论述有关,进而推论此句暗指谋围颐和园。④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第538页。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初版时间,在梁启超等刊布杨深秀、林旭、谭嗣同等人诗之后。或者小说本据《清议报》改动、补充,或者小说本另有所本,二者都有可能。因此更重要的在于,小说征引此五首诗的来源为何?其原本时间和可靠性又如何?检《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得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条下有云:
昨《国闻报》有杨深秀三律,中阙数句,记下一律云:“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安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絏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⑤《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12页。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所载有阙文数句,与小说本及《清议报》本都不尽相同。英敛之日记所录第一首中,颔联出句“自晓龙逢”与《清议报》本同而异于小说本,对句“何尝虎会”与小说本同而异于《清议报》本。又查英敛之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条下:
灯下阅《国闻报》,有林旭狱中诗二绝云:“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殴〔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罢〔罪〕后人论。”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11页。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国闻报》载有林旭《狱中诗》二首,将后来流传为谭嗣同所作的《狱中题壁》归入林旭名下,其文字亦与小说本几乎完全相同(唯第八句“功罪”小说本作“公罪”),却跟梁启超《谭嗣同传》所载之通行本大异。《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作于光绪二十五年末之前,所录林旭、杨深秀狱中诗,有可能取材自当年三月间《国闻报》的载录。而前引小说第三十回“以讹传讹捉拿逆贼”取自《国闻报》报道,亦可证明小说作者对《国闻报》的利用。唯杨深秀诗阙文在小说中被补足,是另有所本,还是小说作者的虚构,则有待于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