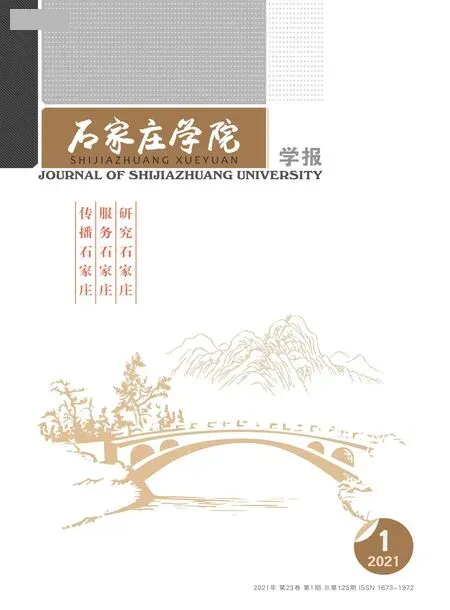晚唐流寓文学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汪 钰,陈煜菲
(1.仰恩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2.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以学术界新兴流寓文学视角,关照晚唐这一文学史研究的热门时代的具体研究,虽为数不多,但也不乏先行者。为更好地梳理研究历程、把握研究现状、确证研究意义,并指导该领域内的进一步研究,有必要对已开展的有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作出展望。而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流寓文学文化本身的理论探讨与构建,其二是具体的晚唐时期流寓文学研究。由于自觉的流寓文学研究开始较晚,故而将与此相关的贬谪文学、地域文学等研究成果亦包括在内。兹从上述两点展开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趋势作一展望。
一、“回归文人本位的理论探索”——流寓文学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流寓文学实践肇基很早,《诗经》中的《黄鸟》等篇目、《楚辞》中屈原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典型的流寓文学作品。相应的,《诗小序》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也可以视为最早有关流寓文学的论述。太史公虽已述及“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但当时先贤显然没有形成自觉而系统的流寓文学视角与运用此视角开展研究的意识。在古代,“流寓”一语原本广泛使用于历史书写中,尤其是地方志中常有以“寓贤”“流寓”为名的专传。而迟至清乾隆朝,才有云南保山人袁文揆纂辑《国朝滇南流寓诗略》,以蔡平教授的说法,这便是“文学最早的‘流寓’观照”[1]。
近代学术方法与学术规范建立以来,虽有以日本学者今关天彭1928年出版的《日本流寓的明末诸士》、陈寅恪先生1941年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读〈哀江南赋〉》等作品问世;新时期以来,复有以“武汉大学尚永亮、黑龙江省社科院李兴盛、新疆大学周轩主导的湖湘贬谪文学、东北流人文学、新疆流人文学研究三个流寓文学研究重镇”[1]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为数不少的流寓文学具体个案研究。然而,从实践到理论、从特殊到一般毕竟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流寓文学、文化本身的理论构建不仅开始较晚,而且首出于历史学者的有关研究。李兴盛先生在《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中,基于对流人史的研究,提出了“流寓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流寓史是历史学中属于专史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研究与阐述一个地区流寓者产生、发展的历史与其历史作用的学科”[2]11,而流寓文化是“流寓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流寓者这一社会群体在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中所创造与传播的一切知识体系的总和”[2]11。
流寓文学概念的提出,包蕴和发展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当中。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文人的流向问题,将之分为向心型、离心型和交互型。跟随文人的流向,文学地理进行着从三秦区域到中原区系再到吴越区系的迁移转换。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聚焦于流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影响,其中的游民多为知识分子。这些研究均涉及流寓文学理论的领域,虽然并不是将流寓文学作为主要对象,但非常具有启迪作用。
流寓文学本身的理论构建肇始于2012年的“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文人研究学术研讨会”。该会论文结集为《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一书。蒋寅在《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刍论》一文中指出“流寓文学是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3],关注近十年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将文学视为发生在一定空间场域中的现象,成为考察文学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不过,在地域文学研究中潜藏着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定义人与地域的关系。该文试图从流寓的角度考察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以古典文学所表现的人与地域的隔阔感、融合感及地域对流寓文学的接受与认同为例,揭示流寓作为人与地域更真实的关系以及流寓文学对于地域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并兼及中国古代地方文化研究中流寓意识的形成。蔡平的《中心与边缘——中国古代文学流寓现象透视》则从主体的空间流转与主客认同、主体空间转徙的主客选择、主体空间转徒的向心与离心三个方面,对流寓现象的内涵、发生、表现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刊载了若干文章探讨流寓文学的有关理论。理论的探讨离不开对既往研究的全面回顾。蔡平教授在2015年以《文学史脉络的生成与地域分布的清晰化呈现》为题,对既往的流寓文学研究进行了综述。该文从“流寓视角的古代文学研究概貌及价值”“流寓经历中的古代文人研究”“流寓状态下的古代文人作品研究”“古代流寓文学的接受研究”四个方面对当时既有的流寓文学研究予以综述。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流寓文学不同于既往的文学通论、分体文学论与“诸如山水文学、宫廷文学、宗教文学等以文学书写对象为研究视角的学术推衍”[1],而是一种以文人生存状态为本位的研究。他进而认为,“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研究便是着眼于古代文人转徙流寓经历中所生成的文学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全面考察”,并指出“流寓文学的研究将启发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实现学科构成意义上的现代转换和新变重组;奠定以流寓的视角进行中国文学历史书写的基础,打破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的认知模式,建立文学经典阐释新的话语系统,使长期缺席于古代文学个案研究和文学史书写的文人及其作品确立起他们应有的位置”。[1]李永杰的《“流寓”概念探源》则在历史溯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流寓的概念,指明“流寓”一词最早出于《后汉书·范廉传》,并就“流寓”概念的界定采访了蒋寅、张学松等较早关注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蒋寅认为,流寓是个中性词,包含了贬谪的迁徙在内,“所谓流寓文学,也就是侨居异乡者所创造的文学”[4]。相比之下,张学松则将是否出于无奈或者不得已作为界定“流寓”的关键。“流寓,‘不得已’离开本土而移居他乡”[4]是其给出的定义。而蔡平教授《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研究视阈》一文则在张学松教授的基础上作了补充。他认为:“一个人并非为生活所迫、被逼无奈,也并非因罪被流贬,而完全是一种流寓者的自主选择,为的是离开家乡和亲人去开拓一片新天地,从而改变现有的生存处境。这种情况流出时或许是满心欢喜的,但到寓居地后的处境却更为艰难,因而孤独感、无助感更加强烈,心中升起一种羁留他乡、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漂泊之感。”[5]平心而论,在具体的流寓文学文化研究中,蒋寅教授的定义虽然更为全面,可以作为广义的流寓文学的定义,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过于宽泛,难以凸显流寓文学的核心特质;而张学松教授的定义则显得过于狭隘,照此研究,不免有所遗漏。依照蒋寅教授的定义,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流寓文学”,除了居乡之作,几乎无所不包。若照此将非京籍文人在京的应制、奉和甚至是馆阁创作,杜甫早年壮游齐鲁和晚年飘零巴蜀湖湘时的作品,白居易早年循例出任京畿县尉、晚年主动分司东都时的创作与被贬江州时的创作一并被视为流寓文学,那么涵盖太广,严重缺乏特异性,实际的研究指导意义不强。而张学松教授给出的定义则无法涵括其本人流寓文学研究的实际,他将客寓京城备考学子的创作也视为流寓文学,这便与其“不得已”的定义核心相矛盾。他在《论中国古代流寓经典之产生机制——以杜甫、苏轼为中心》一文中,由于定义的局限,不得已将苏轼的《和子游渑池怀旧》作为定义外的特例纳入,有失严谨。蔡平教授的补充,则无疑弥补了张学松教授的不足,又避免了失之宽泛,在流寓文学文化的研究实践中更具备可操作性。
其实学者们对于流寓文学定义的分歧,实质上是自身对流寓文学本质理解的差异。蒋寅教授仍将流寓文学置于传统的地域文学领域内,将之与以籍贯为依据的传统地域文学研究相比较,认定其“为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3]。而蔡平显然更关注客寓心理这一内心体验,诚如其所谓“流寓现象一旦发生,必涉及因何而流寓、离开流出地、自流出地至流寓地、到达并寓居流寓地的全过程。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存在流寓者主体情感与心态的变化,也关涉到与流寓者的流寓行为发生关系的所有因素,只不过在整个流寓过程中有时偏重于客体因素对流寓者的改变,有时则偏重于流寓者对客体因素的影响”[5]。而其本人强调流寓文学应向文人本位的回归,而非地域本位,显然就更偏重于作家的主体性因素。他提出:“为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换,研究视角的转变、由作品本位转向文人本位的研究,将创作行为视为古代文人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将作品视为文人生存状态的艺术再现,从而在关注人的真实境遇上使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实现古今人平等对话与心灵共振的媒介。”[5]实则,回归文人本位,这也更贴合文学生成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是作家独特的精神创造,审美活动更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家的外部生存状态唯有通过内心感受这一媒介才能间接作用于作品,外部生态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以此观之,蔡平教授的定义与理解才真正更合乎文学创生规律的本质,真正体现了古代文学学科的现代转换。
2019年,张学松复在《清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论中国古代流寓经典之产生机制——以杜甫、苏轼为中心》一文,进一步以具体例证申述流寓文学经典的产生机制。该文认为,“流寓经典产生的根本因素是作家的流寓遭际”[6]80,包括精神孤独在内的生存困境是流寓经典产生的内因,流寓导致客观上的闲暇与心情的闲适,加上流寓地山水风物的“江山之助”,从时空两个维度揭示了流寓经典产生的外部客观因素。这三者的交互作用正是流寓文学经典的产生机制。另外,刘刚在《中国古代文人流寓心态的多样呈现》一文中,以苗君稷流寓辽东这一个案作为切入点,还原了其内心世界。该文指出苗君稷的内心一方面挣扎于“主客认同”问题,另一方面又深受孤独与乡思之苦的折磨。除此之外,他还必须直面自身对时间与价值的焦虑。同时,作者亦发现苗君稷身上具备一些积极向上的心理力量——能充分利用流寓地的文化资源,消解了相当部分的负面情绪。该文虽立足于明末清初的个案,却极具典型性与代表性,对今后探讨其他作家的流寓心态富有启发性。上述两文均从具体的研究实例出发,进一步验证了作为内因的文人流寓心理与作为外因的外部生态,尤其是地缘生态二者在流寓文学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就流寓文学的研究内容而言,蒋寅教授将“侨居异乡者所创造的文学”[4]全部纳入,在操作实践中过于宽泛。而且,并非所有侨居异乡的外部生态都必然导致主体的客寓心理。张学松教授的另一篇文章《“人生到处应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将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如下三端,即“‘流寓者的书写、书写流寓者、流寓者书写流寓者’”[7]。从逻辑角度而言,第三端不过是第一、二端的特殊情况。其主要特征又可分为“凸显乡国之思与漂泊之感”“流寓者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自然风物、民情民俗之地域色彩的展示”。从中不难看出,只有第三点与传统地域文学研究关联紧密。张学松早已不是简单地将流寓文学放置在地域文学的理论框架内,将之视为某地流寓者的创作,而是将流寓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重在内心感受与客观的存在状态,地域因素只是作为存在的外部环境之一端。蔡平的《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研究视阈》一文则提出,流寓文学研究应“体现文人本位的回归”[4],以文人群体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该文进一步明确了流寓文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在人而不在地,关照文人在流寓这一存在状态下的创作。他认为:“从以往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看,除了以‘流寓’立意之外,尚有立意于‘侨寓’、‘流贬’、‘贬谪’、‘谪居’、‘迁谪’、‘谪宦’、‘寓居’、‘流徙’、‘流人’、‘流放’、‘逐臣’、‘徙居’者,这些无疑都可以归于流寓问题。其实,还有几种情况也是应被纳入流寓文学研究范围之内的。第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并非为生活所迫、被逼无奈,也并非因罪被流贬,而完全是一种流寓者的自主选择,为的是离开家乡和亲人去开拓一片新天地,从而改变现有的生存处境。这种情况流出时或许是满心欢喜的,但到寓居地后的处境却更为艰难,因而孤独感、无助感更加强烈,心中升起一种羁留他乡、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漂泊之感。对文人来说,则会将这种感受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出来。第二种情况是:他人流寓,我等作诗文为之怨,如历代咏昭君的诗文。第三种情况是:王朝更迭之际,前朝人被迫用事于新朝者,他们虽然身仕新朝,内心却充满了对家国败亡的惋惜与思念以及用事于新朝的无奈。也许生存的地理空间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但主客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前朝的主人心理变而为新朝的客寓者心境。此类文人及其作品往往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被称为‘遗民’文学,但从流寓视角看,依然可以纳入流寓文学研究的视阈。”[5]蔡平教授所认定的流寓文学的研究领域,总体而言,与其对流寓文学的定义一脉相承,无疑较张学松教授所言更为全面,唯是所补充的三种特殊情况,细究之下,不宜全盘采用。第一种情况,作家虽然主动离乡,但其感受到的以漂泊感、孤独感、无助感为核心的客寓心态是一致的,理应被纳入;第二种情况,作家虽然身未流寓,但代人书写时,已通过审美想象与共情,实现了创作主体与作为客体对象的主客浑融,同样体验到了作为客体的流寓者的内心感受,亦应被纳入研究范围;第三种情况则应区别对待,盖因被迫用事于新朝,却未“流寓”的遗民,虽然在归属感缺乏等方面与流寓者有相似之处,但毕竟未有流寓之实,内心体验终究与流寓者有所不同。遗民心理与流寓心理并不能简单等同,比如:其或有易代之悲,却绝少有不平之鸣;或有无力回天之恨,却并不常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同时,对于未曾流寓的遗民,异域文化的熏染与江山之助等作用于流寓文学的外因亦不存在。其实,将未曾流寓的遗民及其创作纳入,这也与蔡平教授本人关于流寓文学研究的定义相左。正如前述,他认为,“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研究便是着眼于古代文人转徙流寓经历中所生成的文学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全面考察”[1],而转徙流寓经历作为其定义的核心要件,恰恰是未曾流寓的遗民所不具备的。虽然并不能将未曾流寓却被迫出仕的遗民创作等同于流寓文学,却必须注意到,王朝更迭会使流寓者成为遗民,具有于新朝的客寓心态与漂泊异乡的流寓心理、亡国的易代之悲与个体的身世之悲、无力回天的遗恨与壮志难酬的遗憾,虽分别因国家与个体而生,却在心理结构上具备同构性,交叠强化后必然使得个体作家的内心体验更为丰富且深刻,作品的意涵的深度与广度必然得以大为增进。这是包括晚唐五代在内的异代之际的流寓文学研究中,必须予以着重关注的。
二、凸显地域与时代因素的具体研究——晚唐地域、贬谪、流寓文学研究综述
地域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唐代地域文化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戴伟华教授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一书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著作,该书对地域文学进行了分地区的论述。其创新之处在于: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研究;在编制《唐文人籍贯数据库》和《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基础上,分别讨论了唐诗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创作的历史传统与诗人生存的地域空间在诗歌中的表现和差异,并对弱势文化和域外诗给予了关注。值得重视的是,该书与蒋寅教授将流寓视为比籍贯更真实的人地关系的主张一致,重在诗歌的创作地域。戴伟华教授在该书中同时提出“地域诗学”这一理论范畴,认为“它旨在说明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对文化的选择与地域性的关联”[8]14。同时,戴伟华教授编写的《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更是为流寓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检索工具。李定广教授的《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虽非专门性质的地域文学或流寓文学专著,却切实地论及了唐末文人集中流寓形式,即因蹭蹬科举,流寓长安;因传食诸侯,入幕他乡;或因辗转避乱,客寓终老。其指出,晚唐时期存在着“普遍苦吟现象”。这一现象一方面既因文人“蹭蹬科举,流寓京城”而形成,复又影响到诗人处于其他流寓状态时的创作。此外,该书将唐末五代文学创作与作家心理悲剧的抒泻与消解紧密联系,而无论是心理悲剧的生成还是消解,俱与流寓直接相关。孙振涛的博士学位论文《唐末五代西蜀文人群体及文学思想研究》虽然仍立足于地域文学视角,却已经在首章大量涉及如韦庄、郑谷、李洞等唐末流寓此地文人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探讨了蜀中文人以流寓此地为主的生成态势以及与流寓高度相关的人格心态。郝红霞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晚唐文学的南方化》虽然亦是立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和考察,但最后一章——幕府与南方文学,主要阐论了李商隐与杜牧的幕府创作,属于晚唐流寓文学的范畴。总体而言,该文对闽南、荆楚、江南、岭南等地本土作家与文学着笔更多,于流寓作家群体与流寓诗歌关照尚显不足。同时,自1985年竺岳兵先生在《经济生活报》上发表《浙东唐诗之路》、1995年肖瑞峰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以来,唐诗之路研究亦成为近年学界的一大热点,并在浙东唐诗之路的基础上,延伸出浙西唐诗之路、两京驿道唐诗之路、大庾岭唐诗之路等多条唐诗之路研究,涉及李商隐、许浑、顾非熊、张祜、徐夤、方干、李群玉等一众晚唐作家。其关注重点也从早期“天光水色的自然景观和回响着历史足音的人文景观”[9]37,转向山关水隘背后的“一种特有情节”[10]13。
入幕是唐代文人常见的一种流寓形式。戴伟华教授早期的著作《唐代幕府与文学》,在考证幕府制度源流之后,列举骆宾王、陈子昂、高适、杜甫、岑参、李益、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作为“初盛中晚”唐的代表,主要从诗歌、散文、传奇三种体裁分析唐代文人如何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幕府产生关联并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和人生轨迹。同样,也是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试图去阐释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因素。所惜作者虽注意到“中唐以后入幕人数更多”[11]23,且在小李杜之后的唐末时期韩偓等在幕之作,成就亦高,但由于当时学界对该段文学的一贯轻忽,该书虽有涉及,终未能如前述“初盛中晚”时段各代表作家一样,专辟章节,予以论述。
贬谪属于流寓的一种形式,贬谪文学自然也是流寓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永亮先生对唐代贬谪文学的研究深受学界推重,其研究专著主要有《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和《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前者以韩愈、元稹、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元和贬谪诗人为代表,探索了流寓文化与流寓文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唐元和贬谪文学的发展轨迹,悲剧精神和时代特征”[12];后者则以唐五代的逐臣及其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到了唐五代,贬谪之频繁,人数之众多,均远迈前代”[13]2,并将唐五代的逐臣按时空分布划分为四类:初唐神龙逐臣、盛唐荆湘逐臣、中唐元和逐臣、晚唐乱离逐臣,分别探讨各逐臣群体形成的历史政治背景、文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的创作特征等相关问题。此外,还对唐五代逐臣的别诗加以研究,分析了逐臣别诗的“回归情结”、艺术表现及传播方式。尚永亮先生的研究从元和五大诗人拓展到整个唐五代,全面构建了唐五代贬谪文学的立体框架,而且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较为新颖,文化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交叉运用,尤其是计量分析法的引入和采用令人耳目一新,使得论述更有说服力。尚永亮先生显然是将贬谪作为人的一种存在状态,以文人而非具体的贬谪地域为本位展开研究,其具体研究范式与手段具备很高的方法论价值,值得在整个流寓文学的研究中加以推广。另外,吴在庆“在《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黄山书社,2006年版)一书第四编‘贬谪的生活心态与文学’中,对贬谪者在贬谪途中、贬谪地的生活、心态、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阐述”[14]12。
直接以“流寓”为名的创作,近年来亦有不少。以群体作家为对象的流寓文学研究,有周建军先生的著作《唐代荆楚本土诗歌与流寓诗歌研究》。该书以漫游、宦游以及流贬而来的人士为主,“对其产生的现实背景做了一番考察,更主要的则在于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分析”[14]12。在第二部分也即第四、五、六章,论述了唐代荆楚地区的流寓文学。首先,对唐代荆楚地区的流寓文人进行考述,揭示了文人流寓现象产生的现实背景即唐代的流贬制度以及漫游风尚;其次,分析唐代荆楚流寓诗歌哀怨、山水、民俗三大主题;再次,以杜甫的夔州诗、元稹的江陵诗、柳宗元的永州诗为例,利用个案研究对唐代荆楚诗歌进行微观剖析,其中,亦有部分篇幅关涉晚唐时期流寓此地的作家。杨丁宇硕士学位论文《中晚唐五代江西地区流寓文人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以江州为例》,主要论及上至中唐,下迄五代时期流寓江州的文人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其着重点在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诗人,仅在第三章对晚唐时期流寓该地的贯休、齐己、方干、杜荀鹤、许棠等人略作描述,认为他们承袭了中唐姚贾一派的苦吟习惯与幽僻诗风。单篇期刊论文方面,黎爱群的《生态隐喻下的唐宋北部湾流寓诗研究》与本课题研究范围存在交集,作者将流寓视为一种生存状态,从生态隐喻视阈研究唐宋北部湾流寓诗,“旨在探析自然生态、心灵生态与文学生态对流寓者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审美结构等所造成的影响”[15]183。较有启发意义的是该文所谓的文学生态,并不局限于唐宋北部湾这一具体的时空,而是将唐宋以前历代流寓文学皆囊括在内。诚然,身处流寓状态的作家,除了就近取材之外,在文学史中与前代流寓文学经典产生共鸣,是更为普遍的情况。郭素华的《晚唐诗人周朴在福州的流寓生活及其创作》一文则从周朴这一晚唐作家着手,探讨了其流寓生活与创作,对个体流寓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具体范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中央大学学者李宜学的《论李商隐流寓桂林时期诗作的空间书写》一文。该文乃以李商隐流寓桂林时期诗作为研究对象,企图透过文本分析,探赜诗人此一阶段的心灵世界。其运用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空间诗学》中所揭示的空间理论,探讨了李商隐如何选择性地描绘桂林当地的山水风物与民俗,以承载其流寓困境所致的负面情绪,并通过营构高阁中一方笼罩幸福辉光的私密空间抚慰敏感的心灵、寄寓还乡的希望。该文借鉴西方理论,又紧密贴合文本,分析细密而独到,是对李商隐桂幕生涯较好的阐释。
三、理论与时代的共同召唤——流寓文学新视角下的晚唐文学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无论是流寓文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具体的流寓文学研究实践,都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仍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在理论层面,关于流寓与流寓文学的定义和内涵的争议尚未解决。表象背后其实是关于流寓文学立足点的根本争论,是将流寓视为“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3]20,将流寓文学纳入传统地域文学的理论框架之内,作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抑或是认同流寓文学应立足并回归文人本位,将其视为一种文人的存在状态加以研讨。上述争论急需更多具体的研究实践作为支撑,并加以解决。其次,就具体的流寓文学研究而言,亦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研究仍未能完全摆脱旧有的地域文学研究的框架,仍将流寓作家群体与创作视为某一地域作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多仅能凸显流寓作家与该地域之联系,对流寓者的内心世界开掘不够,而这恰恰是决定流寓文学所呈现的艺术风貌、所能达到的艺术成就的决定性因素。传统流寓地的山水风物与地域文化仅能作为外因,起到辅助性作用。另一方面,流寓文学研究对时代性因素凸显不足,与时代文学风貌勾连尚欠紧密。因此,能够凸显时代因素,并以文人为本位,深入探索流寓心态,兼及异域风物、异质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具体流寓文学研究在当下显得十分必要。
既有的晚唐文学研究已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各角度与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已不可谓不丰硕,但流寓作为一个晚唐作家普遍的经历与长期的存在状态,对该时期的作家作品与文学活动均有重大影响。相较既往的贬谪文学、文学地理学等研究视角,流寓文学或更为全面,或与文学的关联更为紧密、更具本质性。而且,晚唐时代的文人因为蹭蹬科举、传食诸侯甚至避乱他乡,流寓便成为一种较之前代更为普遍的存在状态。同时,由于文坛的支离破碎,藩镇割据导致的地域间相对隔离,使得作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格外强烈;又因为身处末世,对政治的不满、易代之悲与自己的身世之慨相叠合,互相交织、强化,在流寓文学史上又富于典型性。晚唐流寓文学研究虽兼备了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与典型性于一身,但由于这一视角的提出与自觉使用的年限尚少,所以参与的学者与有关论著并不多,既有的成果也仅仅是有关个别作家与少数地域的蜻蜓点水式的涉及,并无涵盖整个时代的专论问世。目前流寓文学领域内仅有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游子·寓贤——元末明初流寓江南的江西文人研究》《明初中原流寓作家研究》均聚焦于元末明初这一时代,而艺术成就更高、影响更为深远的晚唐时代却鲜有问津者。
总之,一方面,流寓文学理论框架已初步成型,其意义与价值已渐为学术共同体所公认;晚唐文学方面,史实、文献考辩、作家作品研探乃至数据库的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已臻成熟,贬谪文学、文学地理学研究业已开展有年。同时,流寓文学领域呼唤能够凸显时代因素的具体研究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晚唐文学领域亟待流寓这一新兴研究视角的统摄。故而,在研究理论与文献基础业已夯实的情况下,晚唐流寓文学研究同时兼备了可行性、必要性与典型性的特点,理应水到渠成,成为学术界重点聚焦的新趋势与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