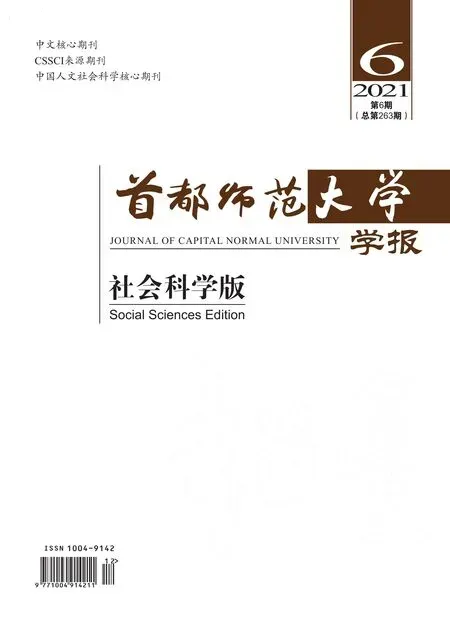城里人下乡:叙事空间的打开与控制
——沈从文小说《三三》解读
罗宗宇
小说被巴赫金称为“艺术时空体”,空间是小说叙事之维。美国约瑟夫·弗兰克认为20世纪以来的现代小说更强调空间形式,叙事学的空间转向强化了对小说叙事空间的理论研究。社会现代性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使城乡区隔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现象,它导致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差异,也激活了城乡之间的互动,“城里人下乡”或“乡下人进城”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一直以来与乡土中国社会保持现实互动,“城里人下乡”或“乡下人进城”是小说叙事的内容,并已成为一种叙事传统。①从“城里人下乡”叙事来看,它在不同时期小说中以不同形式存在。如五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回乡,鲁迅小说《故乡》和《祝福》就有一个“走出—归来”的乡土知识分子“我”;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和“十七年”乡土小说中多有干部下乡书写,如赵树理《老杨同志》中下乡检查的老杨同志和周立波《山乡巨变》中指导“合作化”工作的邓秀梅;此后有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下乡,新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工返乡和扶贫题材小说中的大学生村官以及扶贫干部下乡等。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其湘西小说中不乏“城里人下乡”或“乡下人进城”叙事。②据笔者粗略统计,“城里人下乡”叙事文本有《三三》《夫妇》《贵生》《凤子》《菜园》等小说,“乡下人进城”叙事文本有《虎雏》《丈夫》《边城》《贵生》等小说。本文解读沈从文小说《三三》,以其中的“城里人下乡”叙事为核心分析小说叙事空间的打开与控制问题。①在我看来,《三三》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文本。小说写于1931年,此时正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成熟期。小说中的“城里人下乡”的叙事较早打开了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封闭叙事空间,是具有空间形式的文本。另外,从小说叙事笔法和主人公形象塑造来看,它与代表作《边城》存在某种相似的情形,或者可以说它是《边城》创作的一次叙事演练和最初生产。此外,小说主人公三三与沈从文在书信中对张兆和的昵称一致,从而推测这可能是作者喜爱的文本。
一、“城里人下乡”与小说叙事空间的建构
在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民国初年的湘西尽管偏居一隅并且相对滞后,但还是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社会现代性标志的工商业得到了大力发展。20世纪20年代,湘西王陈渠珍主政后,办教育,设师范,办报纸,兴实业,现代文明的输入进一步加快,湘西的社会现代性进程加速。②具体论述参见罗宗宇:《沈从文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6页。虽然沈从文称自己为最后一个“浪漫派”,但其大多数湘西小说如《长河》等仍是现实性很强的小说,即便多数人认为的浪漫牧歌作品《边城》,也反映了一定的湘西社会现实。③关于《边城》是现实的还是浪漫的存在争论,如刘一友在《评一曲弹了五十年的老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一文中就认为《边城》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世外桃源论”的解读是失误的。因此,沈从文小说中“城里人下乡”或“乡下人进城”叙事是对古老湘西社会现代转型的反映。
受制于社会现代性的发展程度,民国初年湘西社会的“城”无法也不可能是现代性的都市,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它只是居民相对集中,交通比较方便,可以作有无交易,物资集散转口的山区小镇”④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所谓“城里人”也多属于此种城镇人,与此相应,小说中的“城里人下乡”也多指生活在湘西城镇里的人来到了乡村。⑤有一个例外,小说《凤子》中那个到湘西来的工程师是来自现代都市青岛。
“城里人下乡”与小说叙事空间的建构必然关联。叙事空间是对叙事作品空间存在方式、故事内容结构及叙事技巧的空间性设置的整体表现。⑥陈晓辉:《叙事空间抑或空间叙事》,《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将叙事空间区分为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或存在物存在的场景或地点,而话语空间则是指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⑦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城里人下乡”叙事既是故事空间行动者的地理空间流动,也是话语空间的叙事策略和技巧问题。地理空间位移涉及小说故事空间的场景或地点,如小说《三三》中行动者由城里到杨家堡及在杨家堡这一空间内的地点穿梭。与此同时,“城里人下乡”作为一个话语空间的叙事问题,“谁下乡”“下到哪里”“在乡下如何行动”以及城里人的行动采用何种视角来呈现,该行动是否构成小说叙事的核心情节等都与叙事控制相关。⑧依据“城里人下乡”叙事在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功能地位和结构样式,它可分为“平行型”、“镶嵌型”和“点缀型”三种类型:平行型“城里人下乡”叙事指的是下乡来的“城里人”与本地乡下人共同成为主要行动者,基本上居于同等重要的叙事地位,其行动共同组成并推动小说核心情节发展;镶嵌型“城里人下乡”叙事指的是下乡来的“城里人”并非小说叙事的主要行动者,其叙事地位和功能次于本地乡下人,但其行动仍居于小说情节序列之中并推动其发展;点缀型“城里人下乡”叙事指的是下乡的“城里人”在小说中不是主要行动者,其行动也不在小说情节序列的链条上,在叙事中只起一种催化情节的点缀性作用。从分类逻辑上来讲,还应当有一种“主导型”,即下乡的“城里人”在小说中成为唯一主要行动者,叙事行动以其为中心展开,但在笔者对沈从文小说的考察中暂未见到此类型。如《三三》中下乡的是年轻的白脸病人,他来杨家堡乡下养病,其叙事行动主要表现为钓鱼、追求三三和吃鸡蛋,直到最后死去,他的行动未构成小说叙事的核心情节,属于镶嵌型“城里人下乡”叙事。更进一步而言,“城里人下乡”叙事还涉及话语空间运用何种叙事技巧来强化空间性,进而促使小说空间形式的生成,以及选择采用什么叙事视角来呈现叙事空间,如《三三》中如何对“城镇空间”进行呈现等。
二、空间并置:叙事空间的打开之一
从叙事空间角度来分析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可以发现其苗族传奇系列小说叙事多设置在某一地点进行,并且这个地点还相对封闭,如《月下小景》中的黄罗寨就是一个自足封闭的空间。①黄罗寨这一地名为湘西实有,它既指向具体的自然地理地点,也是一种社会空间,同时还是历史和文化空间,其中蕴含了地方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如果结合湘西历史来看,这种地方为苗民聚居地,是一个被边墙封闭的生苗聚居空间。②边墙以外者为生苗,边墙以内者有民村错居,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为熟苗。通过一道边墙,将生苗与熟苗分割开来。参见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其他非苗族传奇系列的湘西小说也多设置在单一空间地点,如《阿黑小史》中的“油坊”、《旅店》中的“旅店”和《雨后》中的山野等。小说《三三》则有所不同,由于“城里人下乡”叙事的出现,它打开了叙事空间,出现了杨家碾坊三三家与总爷家两个空间的并置。③“并置”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创作批评概念,它指的是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参见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指两个地点的并列存在,当然二者都从属于杨家堡这个更大的地方。
地方景观是文学地理空间的一个要素④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3页。,在分析小说叙事空间时,地方景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小说开始的两段就采用“场景化”方式来呈现杨家堡地方景观⑤“场景化”作为一种叙事空间建构方式,指的是通过叙述者的聚焦,对现实生活中的特定空间作还原式呈现的叙事建构方式。:
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湾处忽然转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
从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里比屋连墙,嘉树成荫,正是十分兴旺的样子。往下看,夹溪有无数山田,如堆积蒸糕,因此种田人借用水力,用大竹扎了无数水车,用椿木做成横轴同撑柱,圆圆的如一面锣,大小不等竖立在水边。这一群水车,就同一群游手好闲人一样,成日成夜不知疲倦的咿咿呀呀唱着意义含糊的歌。⑥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在杨家堡的地方景观“场景化”呈现之后,小说用“凡是到杨家碾坊碾过谷子的,皆知道杨家三三”⑦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一句过渡,引出主人公三三出场,这种先景物后人物的小说笔法显现了小说叙事的空间意识,与后来《边城》开头的写法非常相似。
在杨家堡空间“场景化”的基础上,小说叙事开始了杨家碾坊和总爷家两个叙事空间的并置交替,其情形大体如下:
1.第一天:三三与来钓鱼的城里白脸年轻男子相遇(杨家碾坊)——三三跟随城里年轻男子和总爷家管事,听二人谈话(杨家碾坊)——三三到宋家婶子家(宋家婶子家)。
2.第二天:三三妈妈到总爷家(总爷家)——三三妈妈回到杨家碾坊(杨家碾坊)。
3.第三天:三三妈妈应城里白脸年轻男子要求送鸡蛋到总爷家(总爷家)——三三妈妈回到家(杨家碾坊)——三三梦见城里白脸年轻男子和总爷家管事来钓鱼和买鸡蛋(杨家碾坊)。
4.某天下午:三三和妈妈第二次送鸡蛋到总爷家(总爷家)——三三和妈妈黄昏回家(杨家碾坊)。
5.过几天:女看护同总爷家小女孩来杨家碾坊玩,三三陪同(杨家碾坊)。
6.再过几天:白脸年轻男子和总爷家管事又来钓鱼(杨家碾坊)。
7.一个月后:三三和妈妈再送鸡蛋到总爷家,白脸年轻男子死去(总爷家)——三三和妈妈回家(杨家碾坊)。
由上述情节序列可知,随着白脸“城里人”、总爷家管事女看护到杨家碾坊来钓鱼游玩,以及三三和她妈妈“送鸡蛋”到总爷家去,小说叙事空间实现杨家碾坊和总爷家交替并置。
在两个空间并置时,展现了杨家碾坊具有湘西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
这磨坊外屋上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树林里,常常有三三葱绿衣裳的飘忽。因为一个人在屋里玩厌了,就出来坐在废石槽上洒米头子给鸡吃。在这时,什么鸡欺侮了另一只鸡,三三就得赶逐那横蛮无理的鸡,……这磨坊上游有一潭,四面有大树覆荫,六月里阳光照不到水面。碾坊主人在这潭中养得有白鸭子,水里的鱼也比上下溪里特别多。①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后来,当三三陪城里女看护游玩杨家碾坊时,小说再次重塑这一自然空间:“三三则把客人带到溪下游一点有水车的地方去,玩了好一阵,在水边摘了许多金针花,回来时又取了钓竿,搬了凳子,到溪边去陪白帽子女人钓鱼。”②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小说同时还利用“城里人下乡”叙事揭示杨家堡的社会空间。三三与城里白脸男子首次相遇,总爷家管事先生向白脸“城里人”介绍三三,却没有向三三介绍白脸“城里人”,三三在没有获知白脸“城里人”任何信息的情况下,竟然直接判定他为城里人,“你城里人只怕狗”③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三三的认定一是基于熟人社会突然出现陌生人所作出的经验判断,二是男子“白裤白鞋”的服饰穿着与本地乡下人穿着不一样,“那个好像从城里来的人白裤白鞋”④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由此可以看出,杨家堡是富于地方性的熟人社会,如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⑤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小说对于总爷家空间的叙述也是如此,先有自然景观的呈现,如“不到一会儿,就望到大寨那门楼了,门前有许多大榆树和梧桐”等⑥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更有社会空间的呈现。社会空间是一种关系系统,下乡的“城里人”住在总爷家,说明了城与乡之间的联系,也说明了乡下总爷的社会地位,如三三妈妈所言:“总爷是一堡子的主人。”⑦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其中恰恰体现了乡土中国社会的长老统治⑧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三、空间叠加:叙事空间的打开之二
空间并置之外,《三三》中叙事空间的打开还体现在想象性城镇空间与乡村空间的叠加。所谓想象性城镇空间,指的是城镇在小说中借助于乡下人物的想象而存在,是一种纯粹虚构的叙事空间。由于城镇空间是借助于人物的想象而呈现,因此城乡空间在小说中并不是同一平面空间的并置,而是一实一虚两个空间的立体叠加,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的许多社会空间往往充满矛盾性地相互重叠,彼此渗透。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确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⑨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页。
白脸“城里人”及女看护的空间闯入,激活了三三母女等杨家堡乡下人的城镇空间想象,以三三为例,小说中曾多次写到她的城镇想象,比较典型的一处如下:
自从这两个客人到碾坊这次以后,碾坊里有点不同过去的样子,母女两人说话,提到“城里”的事情就渐渐多了。城里是什么样子,城里有些什么好处,两人本来全不知道。两人用总爷家的派头,同那个白脸男子白袍女人的神气,以及平常从乡下人听来的种种,作为想象的根据,摹拟到城里的一切景况,都以为城里是那么一种样子:一座极大的用石头垒就的城,这城里就有许多好房子,每一栋好房子里面住了一个老爷同一群少爷,每一个人家都有许多成天穿了花绸衣服的女人,装扮得同新娘子一样,坐在家中房里,什么事也不必作。每一个人家,房子里一定都有许多跟班同丫头,跟班的坐在大门前接客人的名片,丫头便为老爷剥莲心去燕窝的毛。城里一定有很多条大街,街上全是车马。城里有洋人,脚干直直的,就在这类大街上走来走去。城里还有大衙门,许多官如包龙图一样,威风凛凛,一天审案到夜,夜了还得点了灯审案。城里还有好些铺子,卖的是各样希奇古怪的东西。城里一定还有许多庙,庙里成天有人唱戏,成天也有人看戏,看戏的全是坐在一条板凳上,一面看戏一面剥黑瓜子。①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在此,三三的城镇空间想象是湘西特色的城镇想象,具有鲜明的沈从文个人经验和认知,如作者紧接着所发的议论:“自然这些情形都是实在的。”当然,撇开生活的真实不论,这种实在是以想象方式出场并且叠加在杨家堡空间之上的,小说叙事空间因此成为真实与想象的交织、乡土与城镇的重叠。这种重叠,有时还在三三的心理活动中进行:
走到外边站到溪岸旁,望着清清的溪水,记起从前有人告诉她的话,说这水流下去,一直从山里流一百里,就流到城里了。她这时忖想……什么时候我一定也不让谁知道,就要流到城里去,一到城里就不回来了。但若果当真要流去时,她愿意那碾坊,那些鱼,那些鸭子,以及那一匹花猫,同她在一处流去。②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内心独白是一种特殊的虚拟空间想象,三三在这一心理活动中,借助联想律,把城镇想象与乡土空间紧紧关联,城镇想象连接着“真实”空间,也连接着想象空间,在城乡的“想象—真实”叠加中,小说叙事空间得以延展,溢出了杨家堡,实现了城镇与乡土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统一。《三三》的这一城镇空间想象后来在《边城》中也有显现,如翠翠得知傩送走出“边城”后,就有“船过青浪滩”和“下洞庭”的空间想象,《边城》的空间叙事也用想象方式溢出了“边城”,这可能是《三三》在叙事上埋下的“草蛇灰线”。
小说中还写到了杨家堡其他人的城镇想象,不过她们集中在对城里人的认知上,与三三因爱而生的城镇空间想象有所不同,如宋家妇人说:“谁清楚城里人那些病名字。依我想,城里人欢喜害病,所以病的名字特别多,我们不能因害病耽搁事情,所以除打摆子就只发烧肚泻,别的名字的病,也就从不到乡下来了。”③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四、重复叙事与乡下人视角:“城里人下乡”的叙事空间控制
叙事空间控制是小说叙事的一种空间机制和普遍现象,论文讨论的《三三》中“城里人下乡”叙事空间的控制不是指叙事空间的收缩,而是指对叙事空间建构行为的调控。由于故事发生地点和场景属于故事空间,其叙事选择主要取决于作者早期的湘西生活经历和经验,因此在此只讨论叙事话语空间进行的叙事空间控制。
如前所述,杨家堡空间是一种“场景化”叙事建构,杨家碾坊与总爷家两个空间实现了并置,城乡空间因乡下人的想象而叠加,促使了小说空间形式的生成。从叙事话语空间的技巧来看,小说《三三》空间形式的生成还与重复叙事和叙事视角等有关。①约瑟夫·弗兰克认为影响小说空间形式生成的叙事技巧还有主题重复、章节交替、多重故事和夸大的反讽等(参见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限于篇幅,本文只选择这两个因素进行分析。重复叙事是指多次讲述同一事件行动,它是重新架构叙事的特殊形式。《三三》中的重复叙事首先体现在四次叙述白脸“城里人”、总爷家管事和女看护来杨家碾坊边的水潭中钓鱼,个别时候叙述节奏很快,如“再过几天那白脸人同总爷家管事先生,也来钓了一次鱼”②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其他三处叙述的节奏都较慢,如开头第一次写钓鱼:
三三就一个人赶忙跑回碾坊来,快到屋边时,黄昏里望到溪边有两个人影子,有一个人到树下,拿着一枝杆子,好像要下钓的神气,三三心想这一定是来偷鱼的,照规矩喊着:“不许钓鱼,这鱼是有主人的!”一面想走上前去看是什么人。
就听到一个人说:“谁说溪里的鱼也有主人,难道溪里活水也可养鱼吗?”③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在此,叙述由于写对话而相对停顿,其空间感反而更强。由于人物的钓鱼行动在重复叙述,所以钓鱼地点杨家碾坊旁边的水潭也被反复叙述,而地点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存在,如米克·巴尔所言:“地点可以标示出来,就像城市和河流的地理位置可以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一样。地点概念关系到物理和数学上可以测量的空间形态。”④米克·巴尔:《叙述学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因此,重复叙事使小说叙事不断空间化。与此同时,三三母女去总爷家“送鸡蛋”的行动也被三次重复叙述,其效果同样是强化了小说的空间形式。
《三三》中的另一种重复叙事是意象的重复,如果说杨家碾坊与总爷家属于小说叙事的大空间,那么具体的意象则属于小空间。“空间形式小说是由许多分散的而又互相关联的象征、意象和参照等意义单位所构成的一个艺术整体”⑤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如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通过竹林意象的重复让小说获得了空间形式感⑥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创作受到了废名的影响,笔者推断《三三》或许受到了《竹林的故事》的影响,理由在于: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同名,均为纯真美丽善良的形象,家庭成员结构都是母女二人,再加上南方的竹林意象等空间形式因素,两篇小说确有诸多相似之处。。《三三》中的核心小说意象也重复出现,如“鱼”“溪(潭)水”“碾坊”“水车”等,这些意象不管自身是否为空间意象,其重复属于“人们所说的作品中的符号、词句和话语的与时间无关并且有可逆性的布局”⑦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它们在小说中的分散和不断出现,构建了小说文本在言语—文体层面的空间形式。
叙事视角是指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在文本中体现为通过谁的感知来进行叙述,叙事视角的选择是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创作来看,《三三》中的“城里人下乡”叙事具有多种可能性叙事视角,以“城镇空间”的叙述为例,其一是通过白脸“城里人”或女看护的视角来正面展开叙述,让“城里人”成为叙述城镇空间的主体,如同当代知青小说中利用知青视角来展开城市空间叙事一样。其二是让“乡下人”三三进城,把她心理层面的城镇想象变为物理层面的城镇空间感知,这种叙事处理,沈从文在小说《贵生》曾短暂运用,小说写乡下杂货铺老板的女儿金凤本来打算嫁给乡下人贵生,贵生担心她“克夫”在犹豫中,这时“城里人”五爷下乡看上了金凤,贵生于是进城找舅舅商量,小说用不多的笔墨叙述了贵生在城镇空间的见闻。但《三三》没有采用以上两种叙事视角来写城镇空间,而是采用了三三等待在乡下的“乡下人”视角。白脸“城里人”下乡引发了乡下人的城镇认知和想象,再借助乡下人视角来认知和想象城镇空间,如前面第三节所显示的那样,三三母女、宋家妇人等成为了城镇空间认知和想象的主体。这一乡下人叙事视角的选择,使小说中的城镇空间呈现由实转虚,确保了叙事空间建构的重心在杨家堡,有利于湘西地理与社会空间的表现,但也存在叙事风险,那就是“乡下人”对城镇空间认知与想象的偏差,如小说叙述者所议论的那样:“一个乡下人,对于城中人隔膜的程度,在那些描写里是分明易见的。”宋家妇人在解释另一妇人害病时也说:“你文雅得像城里人,所以才生疡子!”①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那么,小说为何要选择乡下人视角来进行“城里人下乡”叙事中的“城镇空间”建构呢?应当说,这一叙事控制与小说叙事空间的隐喻性意义生产相关。如前所述,“城里人下乡”叙事与社会现代性的发展相关,20世纪30年代初的湘西,虽然“城”不发达,社会现代性也有待大力发展,但现代文明的症候已露端倪,白脸“城里人”的痨病成为了城市文明病的象征性表达,这与沈从文在小说《夫妇》中用城里人“璜”患有“神经衰弱症”来隐喻城市文明病如出一辙。②参见王润华:《从沈从文的“都市文明”到林耀德的“终端机文化”》一文的相关观点,原文参见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3页。《三三》以“乡下人”的视角来窥见和想象城镇,为城市文明病的批判提供了一面借镜,“城里人下乡”竟然是为了从乡村获得对病的“治疗”,虽然《三三》中的白脸“城里人”和《夫妇》中的“璜”最终都没有达到治病的目的,但小说中作为文化寓言的“城里人下乡”叙事还是表达了对于城市文明的反思和乡土文明的自信。当然,这种视角选择也与作者的“乡下人”自我认同相关。20世纪30年代初的沈从文已开始在文坛崛起,他早期的“乡下人”自我认同也已启程。③有关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形成过程的具体论述,参见罗宗宇:《沈从文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0页。沈从文的“乡下人”自我认同让他在《三三》中对“城里人下乡”的叙事价值追求不在于思想启蒙或政治革命,而是以乡下人之眼观城里人和城镇,进而发现现代文明病,这在一个方面表明了沈从文叙事意识与文化意识的超前性。
总之,《三三》中的“城里人下乡”叙事打开了小说叙事空间,选择了相应叙事手段和技巧实现了文本空间形式的生成,其中也蕴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乡土文明的自信这一文化隐喻,由此构建了“城里人下乡”叙事的意识形态,这一叙事意识形态在后来贾平凹等人的“城里人下乡”叙事中得到了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