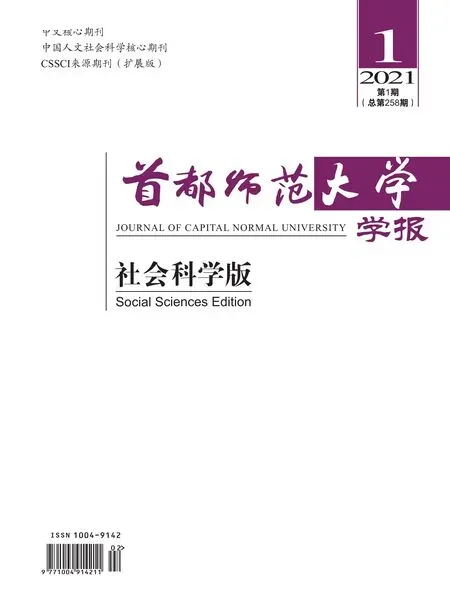美学语法、科学哲学语法的差异及其与时间性之关系
——从美学来阐发胡塞尔《逻辑研究》之一
刘彦顺
美学语法,自然之道也。
使思想得以显现的未必都是语言,但绝大部分思想要经语言进行陈述。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哲学来说,其就只有依靠语言来陈述,如此则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语言的语法。这种语法是哲学陈述中的概念、语词、句子所遵循的法则、规则。但规则、法则并不来自于思想或哲学,而是来自于思想或哲学所思、所学的对象。合乎对象本貌、保全对象完整性的陈述既是正确的思想,同时也是合理的语法。思想正确与语法正确是一回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们认为某个人的思想错了,往往会说——你“说”错了。因此,哲学语法就是“说法”——“说话”的“法度”“法则”。但哲学语法绝不只是狭义语言学意义上的“词句语法”,而是一种“对象语法”,亦即由所思、所学之对象的性质、状态、构成方式所自然滋生出的概念、语词、句子及其特殊的陈述方式。人生的根本在于为“意义”而活着,因此哲学的对象与基本问题就是人活着的“意义”,而“对象语法”就具体呈现为“意义语法”。就分领域的对象来看,人们所创造、追求的“意义”主要有四种:从自然求得知识的科学生活,从神祇求得信仰的宗教生活,从感官求得欢愉的审美生活,从人际求得良行的道德生活。以此四种意义及其所体现的四种生活为研究对象所产生的哲学,可以分为科学哲学、神学哲学、审美哲学、道德哲学。凡是能够合理地分别陈述科学、宗教、道德、审美之意义的语言,便是“意义语法”。
从整体与细节来看,胡塞尔的《逻辑研究》都不是美学著作,而是一部科学哲学与基础现象学著作。但他在进行科学哲学构建与基础现象学奠基时,却在“偶尔”提及审美现象以及“时常”以审美现象为科学哲学之“反例”的陈述过程中,提供了可供阐发的、卓越的美学思想。本文所论美学语法与科学哲学语法的差异及其与时间性之关系便是如此。
一、科学哲学的陈述语法及其与美学语法的差异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对语言陈述活动的研究,凸显了现象学哲学“走向实事本身”之“实事”的特质。具体而言,不仅突出了“实事”的直观或者被充实状态,而且更加突出了直观化、充实化了的“实事”本身在当下的、现时的、独一无二的构成性,这些特性对于语言来说尤其如此。在这里隐含着作为一位美学家的胡塞尔。他集中关注的是科学文体或科学著作文体的根本特性,这些基本特性只能由科学知识、纯粹逻辑规律的含义所决定。在《逻辑研究》时期,胡塞尔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是为塑造科学文体服务的,他并不关注科学文体之外的语言文体,或者为了突出科学文体的属性,才附带性地列举来自于包括文学文体在内的其他文体的属性。
为了建树起现象学哲学体系,胡塞尔认为必须利用分析的现象学来做准备工作并为之奠基,也就是科学哲学的陈述方式与表达的“表象”问题。“这种分析的现象学首先涉及‘表象’,更确切地说,它首先涉及表达的表象。但在这些复合行为中,逻辑学家的原初兴趣应当在于那些连同‘单纯表达’一同出现并行使着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之功能的体验。同时,他也不能忽视这些复合行为的感性语言方面(‘单纯’表达在其中所构成的东西)以及它与那些赋予活力的意指之间的联结方式。”①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既然科学知识、纯粹逻辑规律就其根本特征而言超离时间性,那么表述、表征它们的语言或者语言所表达的表象也应该是如此。因此,要对语言及陈述中所包含的概念、术语及语法进行“含义分析”。他所设定的最佳状态就是——“我们都知道,语词是有所指的,并且一般地说,不同的语词影响着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一种完善的、先天就有的相应关系,尤其是看作一种为本质性的含义范畴造就出其语法范畴中的完善的对应面的相应关系,那么,一门语言形式的现象学本身同时也就包括了含义体验的现象学,含义分析也就可以说是等同于语法分析了。”②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3页。一种精确的、谨严的、可用于广泛交往的语言对于胡塞尔这一时期所倡言的科学哲学现象学或纯粹逻辑现象学,就是至关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胡塞尔才提出了与科学语言或者科学陈述语法相对立的、在审美领域之中存在的现象。他说:“我们知道,表达的差异并不仅仅由含义的区别来决定。我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修辞的区别以及话语所具有的美学趋向:它避免在表达式上的空乏单调以及在语音上和韵律上的不和谐,并因此而要求有一批可供选择的同义表达。”③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14页。胡塞尔在此表达了极为有趣的关于文学作品语言功能的美学观点,虽然在整体上并不是专门就文学而论。他表达的意思是:第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形象的、生动的、令人愉悦的,而不是空乏单调的。第二,不同的文学作品虽然可以传达相同的含义,但是其选择的表达方式或者语言却是不同的,而且完全可以把这一思想转述为——不能因为不同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含义相同或者相通就取消或无视其形式的差异,这意味着不同的文学作品能否带给人愉悦或者带来什么样的愉悦感是完全不同的。
胡塞尔花费了极多笔墨来描述纯粹逻辑学语言表达的构成状况。他认为,符号在呈现方式上的差异不足以造成含义表达的本质差异,比如同一个科学规律可以用不同的概念、符号、语言及其组织表达出来,虽然在概念、符号、语言的组织上有所变化,但是这并不影响科学规律的含义本身,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传达的含义是等值的。以上是就科学活动的对象或者客体而言的,对于科学活动的主体来说同样如此,不管其主体如何变化、心理状态如何,这些因素都不会影响到科学规律自身,比如,不存在8岁儿童、30岁成人与70岁老人不同的“1+1=2”这一数学规律。
但是对于审美生活而言,如果改变了审美对象的构成,那就完全改变了审美生活的性质,让其变成令人不快的、平庸的、面目全非的感受,胡塞尔所言的诗作就是如此。就一首诗歌而言,比如《将进酒》,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一方面,从其作为审美客体或者审美对象的角度来看,任何对于《将进酒》的改动、增删、替换都会引发审美生活的被破坏。甚至以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嗓音、不同的诵读方式来进行诵读,这首诗给我们的感受都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以上诵读方式不同,而作品相同、文字与语言结构相同,就说作品的内涵、含义不同,并且仅限于此。当然,同一首诗在不同的诵读中保持了相同的含义、内涵,但是这些含义、内涵只是作为统一性感受或者完整的审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绝对不可能从统一的直观活动之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否则就破坏了审美生活,破坏了审美价值存在的鲜活状态。那么,审美生活及其审美价值一旦被破坏,艺术作品的内涵、含义就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审美主体本身也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其价值观、心理状态、审美能力要么处于提高之中,要么处在变化之中,其对《将进酒》的体验与感受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不可能像对“1+1=2”一样的完全不变。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研究对象是纯粹逻辑学或者科学哲学,其直接涉及美学的论述实在是屈指可数,但是在这些屈指可数且是顺带性的论述中,却包含了极为重要、深刻的美学思想,尤其是在涉及科学活动与审美生活相比较的话题中。
在论及科学陈述的方式时,胡塞尔就涉及了这一比较,他说:“实际上,从逻辑上看,六个多面体是六个对象,六首曲子也同样是六个对象;力的平行四边形定理是一个对象,巴黎城也同样是一个对象。”①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13-114页。很显然,如果不考虑价值与意义所属领域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往往是根本性的,那就会把“六个多面体”与“六首曲子”同样归为抽象的数字“6”,把“力的平行四边形定理”与“巴黎城”归为“1个”对象,似乎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上述数字“6”与“1”显然适用于对以上这些对象的计算,但是把这些归属于完全不同的价值领域、把具有不同意义的对象归并在一起,其意义又在何处呢?“六首曲子”与“一个巴黎城”属于具体而微的对象,且“六首曲子”显然毋庸置疑地属于“审美对象”,尤其是“六首曲子”还隐含有这样一个被陈述的前提——只有在听过、欣赏过之后,而且这六首曲子都给某一审美主体带去完全不同的美妙感受之后,才会在事后被如此称谓、陈述为“六首曲子”;而“巴黎城”也同样能够给人带来诸如诗意的建筑、浪漫的情调等感受。
与这两个对象相对应的另外一组对象——“六个多面体”“力的平行四边形定理”则是科学知识或数学、几何、物理知识。这些知识或逻辑规律正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一再倡言的无时间性的存在者,其根本特性是一般性、恒定性、普遍有效性、确然性。虽然这些知识在具体科学活动尤其是科研主体的心理体验中得以直观呈现,但却绝不能拿心理体验自身的特性,尤其是拿这些心理体验所带有具体且变动的时间性特征来决定知识自身。
这就是胡塞尔所要建立的科学陈述方式或者纯粹现象学的陈述方式——一种法则,也就是一种广义的语法,以此法则、语法来统辖、约束形形色色的具体陈述。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超时间性、无时间性、非时间性的语法。胡塞尔说:“含义与各个意指行为的关系就与种类的‘红’与这里放着的都‘具有’同一种‘红’的纸条的关系一样。每一张纸条除了其他构造因素之外(广延、形式等)都具有它的个体的‘红’,即这个颜色种类的个别情况,而‘红’本身则既不实在地存在于这张纸条之中,也不实在地存在于任何世界之中,而且也更不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因为这个思维也一同属于实在存在的领域,一同属于时间性的领域。”①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13页。在这段话里,胡塞尔明明白白地要把“时间性”排除在外,只保有观念性的、抽象的、一般性的“红”。当然,胡塞尔在这里所列举的“红”的例证,只是为了阐述科学知识体现为科学陈述及其概念、术语在“含义”上的绝对客观性与一般性这一目的,并没有穷尽“红”所存在的对象或领域的丰富性,他的立意根本不在这里。
那么,上述“六首曲子”这一陈述所包含的“6”在需要进行计算的场合中,所充当的当然是纯粹数学上的“含义”,事实上,审美的意义与价值在前、在先,而且在这里所说的“审美价值”“审美意义”显然是指业已发生了的具体的审美生活,还有,这些具体的审美生活原发性的、原生的呈现状态一定是正在兴发着的域状的时间意识,我们只是享用这个愉悦的域状过程而已。因此,胡塞尔所说的科学语言的陈述语法就是这样的——“种类的观念性则是实在性和个体性的惟一对立面;种类不是可能的追求目标,它的观念性是‘在杂多中的统一’的观念性;有可能成为一个实践理想的不是种类本身,而只是它所包含的一个个别之物”。②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14-115页。胡塞尔研究的对象还是科学哲学或者纯粹的逻辑学,因此他所说的意指内容只是指向无时间性的、抽象的、客观的科学真理或者规律自身,自然不包括所有体验内容,否则就会沾染上心理主义。
二、种类之物与个别之物——科学与审美的差异
说起艺术与科学的区别,最为常见的回答可能莫过于具体、形象与一般性、抽象的区别。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极有创造性。当然,他思考的重点是科学。
在他看来,科学或者纯粹逻辑学追求的是种类的观念统一。虽然在具体的事物中包蕴着观念,但是科学陈述的目标却在于传达含义的观念统一。他说:“当我们在意指红的种类时,一个红的对象对我们显现出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观看这个对象(我们尚未意指这个对象)。同时,在它身上显现出红的因素,因此我们在这里又可以说,我们朝此观看。但我们也并不意指这个因素、这个在此对象上的个体确定的个别特征,就像我们陈述一个现象学说明:显现对象的分离表面部分的红的因素同样也是分离的,在做此陈述时,我们并不意指那些红的因素。”③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21页。这段话的意思是,科学陈述或者科学文体中虽然也会出现具体事物,但是其行为特征却在于在这些具体事物之上构建起来的种类观念。因此,比如康德才会把审美判断称为单称判断,当然,这种说法看似强调与突出了审美或者艺术的特性,其实还是局限于以科学审视审美,以科学语言套用于审美事物、审美现象,像这样的语法错误在美学中是必须加以消除的。
就上述胡塞尔所说的“红”而言,这个“红”就不是我们在审美或者感官愉悦中所看到的一朵玫瑰花的“红”,其出发点是科学研究。他说:“红的对象和在它身上被突出的红的因素是显现出来的,而我们所意指的却毋宁说是这同一个红,并且我们是以一种新的意识方式在意指这个红,这种新的意识方式使种类取代于个体而成为我们的对象。因此,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含义与表达和对表达之意指的关系,无论表达是否与相应性直观有联系。”④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21-122页。这就突出地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朵玫瑰花虽然可以成为科学与审美的共同对象,但是当一个主体在全神贯注地对玫瑰花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却不可能“同时进行”会带来感官愉悦的欣赏。这也就是说,抽象活动与形象活动或审美生活作为时间意识活动,只能是“前后”相续的关系,绝不可能同时出现。
胡塞尔所说的“抽象”当然不是逻辑学或者科学哲学上的心理主义所说的“判断”“推理”等心理活动,这样会把这些心理活动与逻辑规律或知识相混同。在他看来,心理主义在此抽象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只是一种非本真意义上的抽象。他说:“作为种类的含义是通过抽象而在被标明的底层上形成的;但这里所说的抽象显然不是那种在非本真意义上的抽象,这种非本真的意义一直主导着经验主义的心理学和认识论,它根本无法把握种类之物;而且,它未去从事对种类之物的把握,对后人实在可以说是一件幸事。”①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22页。之所以说心理主义不可能把握“种类之物”,原因就在于“种类之物”是观念性的,也是无时间性的、超时间性的,而心理活动自身则是具体的,也是变动不居的、时间性的。可见,在胡塞尔论及“抽象”之时,必然会走向对科学活动作为一种全神贯注的“注意力”的研究。只要人们把注意力指向“种类之物”,而不是仅仅关注“个别之物”,那就是“抽象活动”。
胡塞尔对“种类之物”进行论述的目的当然只是为了建树纯粹逻辑学或科学哲学,虽然也涉及“种类之物”与“个别之物”的对比,但他所说的“个别之物”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审美色彩。因此,在科学与审美之间进行比较,必须同时直接突出两者在本质特征、构成方式、呈显状态上的差异、对照,而不能侧重论述某一方,然后从这种论述倒推出另外一方。因此,要在胡塞尔此处的论述中添加美学之思,就只能从审美生活的意义与根本特征说起。科学活动的价值在于寻求绝对客观的、一般性的、恒定性的、观念性的知识,而审美生活的价值则在于寻求感官所能直接感受到的丰富的、独特的、个别的、新鲜且流畅无间的快感。就此而言,胡塞尔对于“种类之物”的论述的确给科学与审美的比较奠定了“科学一方”的坚实基础,而他所说的“个别之物”一旦添加上“快感”“美感”作为前提,“审美一方”的根本特征及其呈现方式就被奠立,那么,“两方”之间的比较因而就获得了合理性、合法性的奠基。
胡塞尔对“种类之物”论述的特别之处在于把“种类之物”完全置于科学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在确立科学活动是一种意向性活动的前提下,才能把“种类”作为“观念”或者“观念统一”在“直观”中显现出来,才有可能对“种类对象”与“个体对象”之间进行有效的划分。他说:“我们只须回到个体表象或种类表象在其中得到直观充实的情况上去,我们就可以在这些问题上获得最清楚的明晰性:这些表象所意指的究竟是什么,并且,在这些表象的意义中什么东西必须被视为根本不同的,什么东西必须被视为根本相同的。”②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23页。可见,在抽象的科学活动中,主体的注意力自然是一般性的知识本身,而一般性的知识并不是虚幻地存在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立义行为”,也就是不仅把具有感性特质的个别之物“立义”为一般性的“科学知识”,而且还把主体自身心理活动的特殊性、变化性驱离出去——这正是胡塞尔反对、反驳心理主义的伟大成果。
在此,针对主体面对同一个具体之物,胡塞尔设想了两种不同的立义方式,他说:“同一个具体之物在两方面都显现出来,并且由于它的显现,同一种感性内容在同一个立义方式中被给予;这就是说,现时被给予的感觉内容和想象内容的同一总体都受到同一个‘立义’或‘释义’,在这种‘立义’或‘释义’中,对象的现象连同那些通过这些内容而被体现出来的属性对我们构造出自身。但是,这一个相同的现象却承载着两种不同的行为。”③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24页。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在胡塞尔看来就是——“这一次,这现象是一个个体意指行为的表象基础,这个个体的意指行为是指我们在素朴的朝向中意指显现者本身,意指这个事物或这个特征,意指事物中的这个部分。另一次,这现象是一个种类化的立义和意指行为的表象基础;这就是说,当这个事物,或毋宁说,当事物的这个特征显现时,我们所意指的并不是这个对象性的特征,不是这个此时此地,而是它的内容,它的‘观念’;我们所意指的不是在这所房屋上的这个红的因素,而是这个红。”①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24页。上文已经多次提到,胡塞尔的现象学自始至终都不是专为美学而设,在这里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志趣仅仅在于建树纯粹的逻辑学或者科学哲学,而且他也没有把自己的视野立足于把科学与审美、宗教、道德进行对比,或是把以上所提及的四种价值进行统整性的宏观思考,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价值的缺席或者混乱,基础现象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基础”的,这都是需要存疑且要具体分析的。当然,在此并不是要对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划时代贡献进行质疑,而是主张对不同价值或意义领域中的不同现象进行研究。胡塞尔为了凸显“种类之物”的一般性、观念性,才与“具体之物”进行比较,这当然是出于价值比较的立场与需要。他关于抽象理论的贡献,就在于从具体价值——科学价值及其具体呈现状态出发,使一般对象、一般性在意向性的科学活动尤其是在此活动中的对象——个别之物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科学价值的驱动,科学活动才把“注意力”置于“具体之物”的“内容”或“观念”之上,也就是“具体之物”向上所属的“种类”之上。
在面对同一个“种类”在不同情况中的呈现时,胡塞尔所关注的正是“同一个”特质,他说:“从种类上看,这个红与那个红是同一个红,即它们是同一个颜色,而从个体上看,这个红与那个红又不是同一个红,即它们是不同的对象性特征。就像所有基本逻辑学区别一样,这个区别也是一个范畴区别。它隶属于可能的意识对象性本身的纯粹形式。”②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24-125页。一个苹果加上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既是其个别性的自身,甚至于这两个苹果中的任何一个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内在地寓有“1+1=2”这一逻辑联系与逻辑规律。显然,这一逻辑联系是大于个别性对象的一般关系。
以抽象消除形象、具体与丰富性,所保存的是一般、共性与单一性,而且这个一般、共性与单一性是观念性的,而不是一个实体。这就是科学的价值。而审美的价值则体现于特定的审美快感奠基于特定的审美对象之上。“特定的审美快感”意味着审美生活是一个随机缘、时机而发,且具有时间、境界上被提高、上升或超越——也就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实际生活经验;“特定的审美对象”则意味着任何审美对象的空间性构成都是独一无二的,构成审美对象的部分或者因素都处在特定的位置之上,一旦审美对象被改变、改换,要么是审美主体指向了不同的审美对象,要么是同一审美对象的构成被改变,审美生活的质量、状态就会大相径庭、面目全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审美对象的空间构成的完整性绝不是一个先验的、可以预先做出判断的结论,而是在一个审美生活正在进行或者已经结束之后,审美主体只有基于自身审美感受作为时间意识持存、前牵后挂的流畅性,才有可能对审美对象中诸因素或部分空间构成的完整性做出陈述。所以,科学是基于“种类之物”“一般之物”的“判断”,而审美则是基于“个别之物”的“愉悦感受”“快感”或“美感”。
在汉语陈述上,一定要对是使用“判断”还是“感受”(如“愉悦感受”“美感”等)进行清晰界定,以至于这种界定能自明地、直接地反映出科学与审美生活之间的本质区别。“判断”隶属于“科学”,是“反思性”的、“回忆性”的;而“感受”“美感”或“愉悦感受”等相应词语则隶属于“感官”“审美”,是直接的、直观的。我在买东西需要计算的时候,可以去“回忆”一个无时间性的数学公式;但是,一段好听的旋律却只能通过“耳朵”这一感官才能原发性地欣赏到,且任何事后对此旋律的“回忆”都只能是“拟—相似”的。“判断”倾向于“求同”,而“美感”则孜孜于“求异”。对于求同所获得的科学知识、逻辑规律而言,按照胡塞尔反对心理主义所取得的硕果,科学活动既要确保科学知识自身的一般性、恒定性、普遍有效性,不能以科研主体的心理活动的时间性影响科学知识的无时间性,又要让科学知识在意向活动中自明地被意指且直观显现。
胡塞尔还基于科学哲学论述把判断分为两种:“与个体的和种类的个别性之间区别相符合的是同样本质性的个体的与种类的一般性(普遍性)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完全也可以适用于判断领域并且贯穿在整个逻辑学的始终:单个的判断分化为个体单个的判断和种类单个的判断,前者例如有:‘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后者例如有:‘2是一个偶数’,‘圆的四方形是一个悖谬的概念’;普遍判断分化为个体—普遍的判断和种类—普遍的判断,前者例如有:‘凡人都会死’,后者例如有:‘所有解析函项都是可分的’,‘所有纯粹逻辑学的命题都是先天的’。”①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26页。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单个的判断”或“单称判断”还是“判断”,而非“感受”,更不是“美感”“快感”或“愉悦感”,因此,绝不能沿用“判断”一词为审美进行陈述,也就自然不能运用于美学自身的语言、概念及其陈述上。简而言之,“感受”尤其是“快感”“美感”“愉悦感”作为价值寻求,仅仅体现在作为时间意识持续、绵延的流畅性、绵长性上,而“判断”作为价值寻求仅体现在科学知识、逻辑规律的一般性、恒定性、普遍有效性上。这正是审美与科学体现在时间性与非时间性、超时间性、无时间性之间的根本区别。
三、抽象活动的时间性、无时间性与审美生活的时间性
当胡塞尔继续就“种类之物”“一般之物”与“个别之物”“具体之物”进行深入探究之时,他不仅论及抽象活动自身作为实际生活经验或行为的时间性及其作为注意力所指向或意指含义的无时间性,还明确指出了审美生活只流连于个别之物、具体之物或具体形象而不进行“一般表象”的根本特性。虽然他没有对审美生活的时间性或审美生活作为时间意识的兴发、绵延、持存进行直接论述,但只要与他对“个别之物”的时间性论述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他对审美生活时间性或审美生活呈显为时间意识的思想是显著的、突出的,而不是潜隐的。
在《逻辑研究》第2卷第1部分第2研究第8节名为“一个迷惑人的思路”中,胡塞尔提到了一个极妙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谈论某种甚至不存在于我们思维之中的东西呢?”②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40页。并继而说道:“因此,不言而喻,观念之物的存在是意识中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说:意识内容。与此相反,实在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中的存在或内容—存在,而是自在存在、超越的存在、意识之外的存在。个体连同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实在的;它是一个此地和此时。对我们来说,时间性就足以是实在性的特征标志。虽然实在的存在和时间性的存在不是同一概念,但却是范围相同的概念。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心理学的体验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事物。然而,如果老的形而上学信念在这一点上是合理的,即所有时间性的存在都必然是一个事物,或者一同构造着事物,那么心理学的体验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事物也就同属于一个事物性的统一。而如果所有形而上学的东西都应当始终被完全排斥在外的话,那么人们便只能用时间性来定义实在性了。”③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40页。更为重要的是,他直接点出了这里所涉及的唯一一个问题:“观念之物的非时间性‘存在’的对立面。”④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40页。在这里,胡塞尔所传达的还是一贯的思想——虽然抽象活动自身是具有时间性的,但在抽象活动中被给出的“观念之物”却是非时间性的,它不仅真实地存在着,而且能够被我们自明地、明见无疑地意指着、谈论着,更能在不同的具体之物、个别情境中作为标准进行运用并保持其恒定性。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观念对象则真实地存在着。我们不仅可以明见无疑地谈论这些对象(例如,谈论2这个数,谈论红这个质,谈论矛盾律以及其他等等)并且附加谓词来对它们进行表象,而且我们还可以明晰地把握到与这些对象有关的某些范畴真理。如果这些真理有效,那么所有那些作为这种有效性之客观前提的东西也都必然有效。”⑤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41页。
一切思想都必然被陈述为语言或以语言陈述并呈显,上述“观念之物”与“个别之物”同样如此。胡塞尔列举了两组不同的名称,一组是苏格拉底与雅典,一组是4、作为音序成分的c调与作为颜色名称的红,很显然,前一组是用来指示个别之物的专名,而后一组则是用来指示种类之物或者观念之物的。他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描述:“与这些名称相符的是某些含义,借助于这些含义,我们可以与对象发生关系。人们会想,关于这些被指称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引起争议的。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这个人,雅典这个城市或其他一个个体对象;另一方面是4这个数,c这个音调,红这种颜色或一个其他的观念对象。”①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60页。一方面,胡塞尔对个别之物及其用来表述的专名与种类之物及其相应的名称进行了有效区分,他所说的“个别之物”尤其适用于对审美生活的分析,因为任何审美对象都无可替代、变动,否则审美生活作为意向活动就会变质或剧变;另一方面,胡塞尔在这里说“c调”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c调”只能作为一个质料、构成因子出现在独一无二的音序或音乐作品之中,世间绝无可以独立存在的、好听的“c调”,“可以独立存在的”其实就意味着“好听”,或者说只有“好听”才值得存在,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存在;世间只存在好听的“音序”或者“旋律”,当然,好听的“旋律”“音序”只能是或者必然是一个兴发着的时间意识。也就是说,在某一个好听的、动听的旋律之中,“c调”位居其中——它只是前牵后挂的时间视域中的一个“相位”而已,如果缺少了“前牵”与“后挂”,“c调”就只可能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音”,不过,这个“音”也太孤苦伶仃了,大概只有钢琴的调音师才会凝神于一个琴键所弹出的“c调”吧。因此,“4”“红色”与“c调”是不能并列在一起的,这意味着胡塞尔没有领会科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及其相应的不同呈现状态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胡塞尔旗帜鲜明、苦心孤诣地捍卫科学知识、逻辑规律的无时间性的时候,却在这里把时间性、审美生活的时间性嵌入非时间性之中了,或者是把审美生活的时间性当作科学活动或科学知识、逻辑规律的无时间性来处置了。像这样的混淆,在《逻辑研究》中还是第一次,是一种偶然的错失,还是一种惯性的熟思,这是需要关切的。
虽然“种类之物”“一般之物”寓居于“个别之物”,但却不能为“个别之物”的时间、地点、变化所牵绊、牵制。相反,“种类之物”“一般之物”作为无时间性的存在是观念性的,“那些对于个别情况来说具有意义和真理的陈述,对于种类来说则是错误的并且简直就是悖谬的。色彩具有其地点和时间,它展开自身并且具有自己的强度,它产生并且消失。如果将这些谓语运用在作为种类的颜色上,那么它们只会产生纯粹的悖谬。如果房屋被烧毁,所有的部分也就化为灰烬;个体的形式和质性、所有构造性部分和因素也都不复存在。现在,例如有关的几何学的、质性的和其他的种类已经被烧毁了吗,或者,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纯粹的荒谬?”②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74页。事实上,对于审美生活而言,以上这种变化或状态是注定要发生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纯粹的艺术作品而言更是如此。在科学活动中,其所追求的是抽象的、客观的、规律性的观念,且这一观念绝不仅仅限于某一具体事物或仅为某一具体事物而设。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这些具体事物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存在的,其可能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但那些科学原理、逻辑规律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而审美生活的对象,尤其是艺术作品却是一个具体且整体性的构成,任何一个因素、部分都在整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功能。这些所有因素、部分之间是一种不同却亲密到极致的关系,绝不可以像科学活动那样对这些艺术作品中的因素、部分进行化约、归类,而后再抽象出像科学规律一般的美学原理。科学活动对构成艺术作品之因素的任何努力都是枉然的,其所具备的所有机制、目的、手段都无法穿透艺术作品及其构成要素。当然,这里所说的艺术作品是指那些经典的艺术作品,其实也就是带给某个审美主体以完满、高质量和理想的审美愉悦的作品。而上述一切关于科学与审美、科学与艺术的比较,最后都要归结于两者的最底层构成——时间性或时间意识的构成。
因此,胡塞尔所说的“抽象”并不是注意的一种思维功能,也不是对位于某一具体之物且不可分离的部分属性——“种类之物”的关注,而是在直观基础上直接把握到的“一般性”。在这里,胡塞尔就提出了一个直接与审美、美学相关的问题,这就是“对被直观对象的一个不独立的因素之关注与对相应的种类属性之关注之间的区别”。③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77页。胡塞尔认为,如果把“种类之物”“一般之物”视为对隶属于“个别之物”这一整体中的某个一般属性的意指,尤其是视为在“注意”中显现的“属性因素”,那就无法把“一般之物”“种类之物”的无时间性、恒定性、普遍有效性显现出来。
接下来,他对科学活动与审美生活进行了直接对比。“我们现在要问,当我们的目光明确指向个体因素时,情况会是怎样的呢?这两者的区别何在?如果对象上的某个个体特征,它的特殊的色彩,它的高雅的形式等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么我们便特别地关注这个特征,但我们却并不进行一般表象。同一个物体也涉及完整的具体之物。一方面是对个体显现的形态的惟独注意,另一方面是对那个可以在无数实在形态中实现的相应观念的直观把握,它们两者的区别何在?”①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177页。当我们凝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时,如果仅仅把视线或焦点投向某一个点,仅仅指向某一处色彩,那就意味着对整个作品欣赏的终结、中断或从未激发、兴发起审美生活。尽管这个点或色彩的确在此时此地属于《蒙娜丽莎》,是这幅画作的一个点或色彩,但在上述观看行为中,它们只是如同大千世界中事物的任何一个点或色彩一样,毫无二致。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先行欣赏了这幅画作后,却对其中一个点或某一处色彩进行孤立的处置,把它们视为独立自足的存在、将其总结为一般之物,如一般性的创作手法、创作规律乃至艺术理论的知识体系。以上两种情况可谓殊途同归,因为前者对作品所采取的完全是纯粹客观、纯粹科学的态度,认为此画作上的色彩不过是可供科学研究的光谱等,而没有把这些个别因素、个别属性看作坚实的有机整体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且个别因素、个别属性之间是一种互为是否值得存在的前提的关系。每一个构成因素、属性都是不可缺少的,且在整体中承担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后者而言,这一态度或操作虽然看似强调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但其根本缺陷在于:没有把当下即席的、主客不分的、意向性的且涌现着的、兴发着的愉悦过程——观赏过程本身当作此画作价值的唯一呈现本身,正是在这个观赏过程中,画作的所有构成因素、那些个别性的属性或部分才成其为一个整体。
在这种以绝对客观为对象的科学知识中,虽然其只能体现于个别之物,且其呈显的载体、符号等也都具有感性特质,但这些感性特质只是伴随性的、伴生的、寄生性的,在科学活动只能呈现出的理性直观中,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在理性直观作为一种抽象注意力的活动中,感性特质完全服务于、臣服于、消匿于纯粹逻辑规律之中。因此,胡塞尔指责休谟不去观察在含义意指与含义充实中的“含义特征”,而“迷失在那些发生性的联系之中”。②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2卷第1部分,第212页。这些“发生性的联系”正是带有时间特性的那些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胡塞尔认为这种发生性的联系会赋予名称以“联想”关系,即把名称和与其相对等的这一等级的对象相联系。按照胡塞尔的思路进行推导,这一“联想”不仅会破坏和中止正在进行抽象思考的“注意力”,而且在根本上,纯粹的逻辑规律或科学知识与这些具体感性的事物是完全不相容的,至少从时间性角度来看,前者是无时间性的,而后者则洋溢着充盈的诸如随机而发、变动不居等时间特性。
正是在对科学活动与审美生活、科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差异的有意识对比中,胡塞尔才提出,审美生活所指向对象之内任何因素、部分或个别属性都不会触发抽象之思。虽然《逻辑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通常字数不多,且重点也不在美学上,仅在论及科学、纯粹逻辑之内在本质属性时,尤其在论及科学、纯粹逻辑所面对的对立面以及错误思想时,才不得不顺便提及审美价值及其呈现状态,以此凸显科学哲学的正面建树。但字数之寡、分量之轻都并不妨碍胡塞尔美学思想的重要建树及其贡献。其实,这也是胡塞尔审美时间哲学,尤其是审美时间意识现象学创构的开端。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