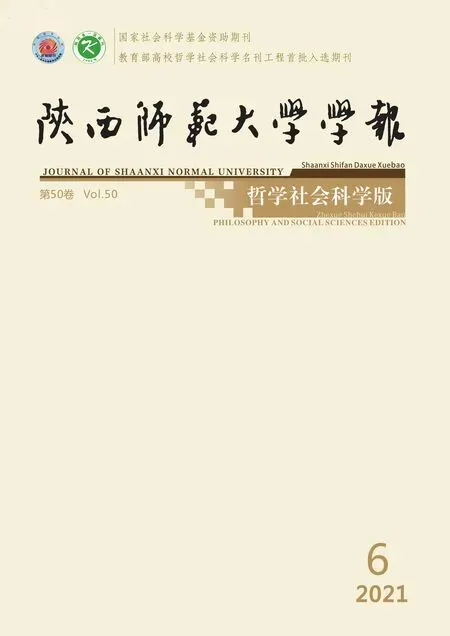疫情之下对例外状态理论的再思考
张 铮, 于天洋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例外状态)。”[1]5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的这一论断在2020年显得尤为振聋发聩。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正在被拖入“非常状态”之中。对于很多国家而言,能否清晰认识到当前已然处于非常状态,并及时采取果断而有效的应对措施,已经成为考验各国政府国家能力的必答题。显而易见的是,世界各国的抗疫表现已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初就果断采取了“封城”“封路”“隔离疑似病例”以及“要求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等有效措施,并因此成为最早战胜疫情的国家之一,如今中国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些本应该展现出良好防疫水平的西方发达国家,却陷入了一种自由主义话语的困境——在“人权”和“自由”的争吵声中踯躅不前,坐视疫情扩散而难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很显然,疫情迫使社会触发了例外状态的运行模式,这是客观事实。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何以一些国家如此抵触诸如“封城”“停工”“隔离”“戴口罩”等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呢?何以例外状态之下的一些不得已且必要的非常之举竟被视为自由的对立面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必要回顾和反思一下西方学术界对“例外状态”的思考。
一、 西方思想界对“例外状态”的思考
“例外状态”亦作“非常状态”或“紧急状态”。所谓“例外状态”指的是国家通过中止正常的法律秩序以应对某种危机的政治现象。作为一种法学理论的“例外状态”,最初是由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系统提出来的。他认为,例外状态产生于政治危机,由主权者来决断其是否开启以及何时终止。当国家遭遇到紧急的危机,且依靠现有的法律制度资源和常规的政治规则秩序无力解决这些危机时,主权者就会宣布进入例外状态,通过结束日常秩序,悬置部分法律乃至中止宪制,使社会以非常规的方式运行,从而应对这些危机。
根据施米特的表述,我们可以把例外状态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法律层面的例外状态,即国家通过政令宣布戒严、宵禁、军事管制以及进入紧急状态。这是一种法理意义上的例外状态,它区别于日常的法律秩序,也是西方思想界所关注的“例外状态”。二是现实层面的例外状态,即真实存在于世界的重大危机,如自然灾害、饥荒、暴乱、革命、外敌入侵等,它颠覆了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迫使社会以一种“例外”的方式来运行。
施米特提出例外状态理论是意在阐发其主权决断论。第一,例外状态是一种依赖主权者进行决断的法律状态。他反复强调例外状态具有不容否认的法学意义。“非常状态真正适合主权的法理学定义,这种主张具有系统的法理学基础。”[1]5第二,例外状态证明了国家或主权者是高于法律秩序的存在,在例外状态中主权者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国家的存在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国家高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决断不受任何规范的束缚,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东西。”[1]9第三,常规秩序是通过例外状态产生的,例外状态比常规有更强的解释力,更能反映主权者的本质。“规范证明不了什么,而非常状态就能证明一切:它不仅确认规范,而且确认规范的存在,因为规范只能来自非常状态。”[1]11第四,主权者不仅有权通过宣布进入例外状态来中止法律秩序,也有权决定何时恢复法律秩序,甚至有权创制新的法律和秩序。
从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例外状态与主权者处于一种互相论证、彼此纠缠的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主权者创造了例外状态,另一方面例外状态也定义了主权者。“主权的定义必须结合于际缘状态(Grenzfall),而非常规。”[1]5主权者既凌驾于法律体系之上,其权限又在法律规定之中。透过例外状态这个孔隙,人们可以窥见主权者的真实面目。究竟是谁能够超脱于法律秩序之外,去宣布法律的中止与秩序的恢复?这样的决断,无疑出自真正主权者,因为“对非常状态做出决断乃是真正意义上的决断。因为常规所代表的一般规范永远无法包含一种彻底的非常状态”[1]5。从这一点来说,例外状态是最接近于主权者本相的状态。
在施米特的理论中,例外状态是对一种客观政治现象的观察和描述,这种政治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政治危机都是真实存在的,例外状态中进行决断的主权者也是真实存在的。施米特只是将其描摹出来,然而他的主权理论倾向于赋予主权者以几乎无限的权力,并将其正当化,这引起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广泛担忧,也是他思想中广为诟病的一点。但若考虑到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这种理论主张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强权政治的时代,越是政治孱弱的国家,越需求并且渴望一个强势有力的政治领导,以带领国家摆脱危机。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的崛起,似乎也历史性地印证了这一点。然而,鉴于德国纳粹政府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惨痛记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难免因为涉及纳粹意识形态而遭受批判,其例外状态理论也在其中。自此开始,西方思想界对例外状态的基本态度转向了怀疑、警惕乃至戒惧。
在施米特之后,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采用生命政治学的视角对例外状态及其主权决断论展开了冷峻的观察和批判性的评述。
其一,阿甘本重新定位了例外状态与法的关系。首先,阿甘本指出,施米特着意将“例外状态”纳入“法的脉络”之中,然而例外状态本质上却不是一个法的状态,而是一个没有法的空间。“如果例外状态的特性是法秩序(全部或部分)的悬置,那么这样的悬置如何能依然被包含其中?一个无法状态如何能被铭刻在法秩序之中?”[2]32其次,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的特殊作用是实现了法律效力与法律的分离,从而使政令及其背后的权力获得了法律的地位和效果。“(例外状态)定义了一个‘法律状态’,其中一方面规范有效(vige)但未被适用(它没有‘效力’[forza]);另一方面,没有法律之价值的法令却获得了它的‘效力’。也就是说,在极端情势中,‘法律效力’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元素流动着,得以同时被国家权威(其作为委任独裁而行动)与革命组织(其作为主权独裁而行动)所宣称。”[2]57最后,阿甘本通过梳理本雅明与施米特的隐秘对话指出,例外状态正在谋求常态化,成为日常治理的手段,而这对民主和法治构成了威胁。
其二,阿甘本引用“神圣人”和“赤裸生命”这两个概念来揭示“例外状态”的本质。[2]所谓“神圣人”(Homo sacer)(1)Homo sacer译为“神圣人”。实际上,sacer这个词还有“被诅咒”的含义。见阿甘本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 。是古罗马的一种特殊的刑罚。“神圣人”不受法律和宗教的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杀死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神圣人”是被剥夺了人类社会资格的人,他们只是单纯的生命体,不享有法律的保障。阿甘本把这种境况称之为“赤裸生命”(Bare Life)。阿甘本用“神圣人”和“赤裸生命”来讽喻“例外状态”,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在例外状态之下,所有人都是处于“赤裸生命”的境遇之中,他们直面权力的威胁乃至迫害,却得不到法律和制度上的援助。在权力面前,他们形同赤裸,只是一些任凭权力拿捏的活物或肉体罢了。阿甘本以被美国关押的塔利班战俘为例指出,他们“不仅未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地位,他们甚至无法享有根据美国法律被控犯罪者的地位。他们既非战俘亦非被告,而仅仅是被拘留者”[2]7。在阿甘本的这一视角下,国家及主权者的形象成为面目狰狞的利维坦,例外状态之下的人们(赤裸生命)则是利维坦的饵料,而例外状态则成为这个利维坦吞噬个体的方式。
其实,施米特与阿甘本的理论旨归有着明显的不同。施米特对于例外状态的关注点在于政治危机的紧急性以及悬置法律秩序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人们无法预知一种紧急状态的确切细节,也无法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在遇到极端紧急的情况并寻求如何消除这种情况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权的前提和内容必然不受限制”[1]6。此外,例外状态中所表现出来的主权决断,使人们能一窥主权者真实面目,而在日常秩序中,主权者是被常规的法律秩序所遮蔽住的。阿甘本则把法律的悬置可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作为其核心的学术关怀。鉴于施米特的纳粹背景,阿甘本以魏玛共和国宪法和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设譬,其对施米特的批判之意是不言自明的。“在魏玛共和国(2)本处“国”为笔者所加,中文译文原文为“魏玛共和”,但据笔者查到的意大利语和德语方面的资料,译作“魏玛共和国”更妥。中(其宪法第48条规定了帝国总统面临‘公共安全与秩序’受到威胁时的权力),例外状态显然发挥了比在意大利或法国更为重要的作用。”[2]15阿甘本这是在提醒读者,施米特的例外状态理论及其主权决断论,可能会成为孕育纳粹的温床。
阿甘本之后,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为了防止例外状态导致极权,提出了“紧急状态宪法”概念,[4]用以规范例外状态的法律程序。阿克曼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紧急状态,其一是对国家存亡构成威胁的紧急状态,其二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构成威胁的紧急状态。阿克曼指出,很多国家宪法中的例外状态条款都是以威胁国家存在为理据而设计的,然而本·拉登及基地组织所实施的恐怖袭击,并不能对国家的存在构成威胁,而是对国民生命和国家治理能力造成威胁和挑战。当恐怖袭击对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害之后,政府能否及时为国民提供安全感,就构成了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阿克曼将此称为政府的“安慰功能”(Ressurance Function)。阿克曼认为,恐怖袭击并不足以对国家存在造成威胁,然而国家通过例外状态滥用“安慰功能”来安抚社会恐慌,则会对公民权利和自由造成损害。
为此,阿克曼提出应该反思法律中关于例外状态的条款,要基于“安慰功能”重新设计例外状态。为此,阿克曼精心发明了一种“绝对多数自动扶梯”(Supermajoriarian Escalator)式的制度设计,即每次想要延长例外状态必须在议会中获得更高的绝对多数支持。第一,阿克曼限制了例外状态的触发条件,即只有遭遇恐怖袭击之后才会触发例外状态。第二,阿克曼限制了例外状态的时间长度,每次例外状态的持续时间为2—3个月,到期自动终止。第三,阿克曼提出,如果要延长例外状态,必须获得议会的绝对支持,首次延长两个月需要60%的赞成票,再次延长则需70%,第三次需要80%……以此类推,直至例外状态自然终止。同时,阿克曼还提出对在例外状态中被抓捕的无辜者进行赔偿,在审讯过程中尊重被羁押者等原则性的建议。
二、 对例外状态理论的反思
平心而论,无论施米特、阿甘本,还是阿克曼,他们对于例外状态都有独特的思考,然而也有各自的不足。施米特关注的是主权的本质,在例外状态中,主权不仅能中止秩序,还能创制新秩序,因此他肯定例外状态在非常时期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说,施米特对于例外状态是认可和赞许的,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在他所主张的例外状态中,当主权者获得了不受限制的权力之后,所展现出的究竟是创造力还是破坏力,它给国家带来的究竟是福音还是悲剧。纳粹造成的悲剧殷鉴不远,这使得人们面对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和例外状态理论时,总是不自觉地与之保持距离。
阿甘本关注的是在例外状态中,主权对普通人的危害。公允地说,阿甘本对例外状态的批判,戳破了西方社会民主、法治与人权的神话,他揭示出这些美好幻象的底色不过是例外状态的常态化,是主权者的专断主宰。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美国以反恐战争的名义,使例外状态常态化。然而也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阿甘本通过例外状态揭露了西方法治与人权的虚伪,但施米特发现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施米特所倡导的例外状态和主权决断,是为了解决政治危机而出现的。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仅仅批判例外状态可能引发的人权危机,却不消除例外状态之所以产生的现实根源——政治危机,那么这种批判只能是无力的。阿甘本反复引用那句古老的谚语“必要性无法可循”,其实也说明了例外状态之所以存在,正是因其必要,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阿甘本对例外状态也并非全然拒斥的。他曾设想一种近乎神学的“弥赛亚例外状态”,然而这种天马行空般的激进思想几乎没有实践的指导性,不具有现实意义。
相比阿甘本,阿克曼没有从理论上否定例外状态。阿克曼认识到例外状态的存在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例外状态以及如何驯服权力,因此他尝试把例外状态纳入法治秩序中,为此还设计出了一套看似精妙的紧急状态宪法。应该指出,如果仅从理论上来看,阿克曼的这一设计是充满想象力的。然而,如果立足现实政治来审视阿克曼的制度设计,则未免感觉阿克曼有些纸上谈兵。首先,在西方现实政治中,由于反对党的存在,国会经常成为执政党与反对党进行党争的场域,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十分明显地出现政治极化的趋势,公正客观地讨论政治议题已经变得日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阿克曼寄望于国会对例外状态做出明智的决断,可能是不现实的。其次,执政团队出于自身利益的不同、政治立场的差别以及认知水平的差距,往往很难统一认识。当国家遭遇危机时,执政团队中的很多人甚至多数人可能尚未认清危机的严峻性,因而也难以做出正确的决断。所谓“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处理危机,尤其需要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断力,然而这却是多数从政者所不具备的能力。最后,例外状态应以解决政治危机为最终目的,而不仅仅是以安抚社会情绪为旨归。阿克曼为例外状态设定倒计时,可能并不利于危机的解决,因为危机未必就是短期的。其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国家的扩散已经充分暴露出其政治生态存在的上述问题,西方国家的政客们既没有认识到疫情的严峻性,也没有认识到抗疫工作的长期性,他们把疫情当成攻讦政治对手的武器,然后用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去期待病毒自行消失。可想而知,在这种政治现实之下,如果把阿克曼的制度设计付诸实践,大概率会导致政客之间相互牵制和倾轧,最后演变成一事无成的困局。
综合来看,西方思想界对于例外状态的认知还相对片面。尽管他们从自身的学术立场出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然而却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状态。
其一,西方思想家关于例外状态的观察带有片面性。他们过度的关注例外状态对公民权利的压迫性,而没有看到例外状态在非常时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没有指出例外状态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手段,而是政治与社会运作的客观需要。实质上,在非常时期,主权者之所以悬置常规秩序,正是因为常规的法律秩序无力解决现实危机。从这一角度来说,悬置法律并不是主权者主观意愿选择的结果,而是不得已而为之。阿甘本反复吟咏的谚语“必要性无法可循”,其实恰恰说明一方面例外状态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有些危机却无法通过遵循常法来解决。
其二,西方思想家对例外状态的讨论与批判,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例外状态本质上是一个权力运作的问题,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正是权力直接加之于身体的状态。然而,权力不仅有破坏性的一面,还有建设性的一面;它不仅有压迫性的权力,还有解放性的权力。有学者通过分析权力的性质指出,权力可以区分为“支配性的权力”“反支配的权力”和“无支配的权力”。[5-6]阿甘本等学者所批判的例外状态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力支配的场域,可以归因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的支配性和压迫性属性。然而,作为反支配性的权力和解放性的权力同样可以创造出例外状态。比如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就是一种“必要”且“不拘常法”的例外状态。在这种例外状态之中,革命者塑造的权力主要呈现出反支配与反压迫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实质上就是要求革命者积极地发动革命,主动创造例外状态,不仅不能被现存的资本主义法律秩序与常规束手束脚,还要勇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一方面热情讴歌了巴黎公社,但另一方面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一是没有没收国家银行的资产,反而致使这些资产流向了敌人; 二是没有趁敌人虚弱的时候抓住机会消灭反动军队,反而给了敌人休养生息和组织反扑的时间。实际上,革命在本质上正是一种例外状态,这就意味着革命不能遵循常法。巴黎公社没有没收银行资产,反而主动维护资产阶级的金融秩序;没有及时消灭反动军队,反而把大量的时间用以组织民主选举。这些行为恰恰都是遵循常规秩序的体现,也恰恰证明了革命者对于当时处于例外状态的事实没有清晰的认识。例外状态的首要任务是解除政治危机,而不是恢复常规秩序。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常规秩序的不屑,“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7]118。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与常规是带有压迫性的,而革命创造的例外状态反而是一种解放。
三、 不决断: 无例外的例外状态
疫情之于常规而言,显然已经构成了一种例外,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的大流行已然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拖入这种例外状态之中。面对疫情,世界各国应对的措施不尽相同,不过,根据其态度和政策效果却可以大体区分为3种类型。其一,有些国家能够及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取得了较好的抗疫成果。其二,有些国家在疫情严重之时能够采取一定的紧急措施,但是却不够坚决果断,不能将政策贯彻到底,在局势稍有好转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解除禁令,这往往造成疫情几度反弹,令抗疫成果得而复失。其三,有些国家以保护公民权利之名拒斥例外状态这种做法,拒绝宣布超出常规的应对措施。总体而言,中国、韩国基本属于第1种类型,能够采取果决的措施,也取得了很好的抗疫效果。而西方很多国家则呈现出第2种、第3种类型,他们或在例外与常规之间左右摇摆,或干脆拒绝承认已身处例外状态。似乎只要不承认,疫情就不会对国家构成风险与危害。这种消极应对,正在使更多人的生命成为疫情下的赤裸生命,由此也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例外状态样本:以不决断为决断,以常规为例外的例外状态。
第一,无论是否做出决断,例外状态同样存在。例外状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状态,也是一种社会状态。从表面上来看,例外状态似乎是来自国家的布告,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国家何以能够宣布进入例外状态?社会又为何能够接受这样的例外状态呢?显然,例外状态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即社会已经出现了某种危机。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已经重塑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迫使社会以非常规状态运行。对于正常运转的社会而言,这已然是一种例外,无论国家是否欢迎例外状态,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从政治上宣布例外状态,不过是对此状态的确认和应对。而国家拒绝承认这种例外,也不会消弭它对正常社会造成的损害和风险。
第二,决断或不决断,都体现了权力的意志。以往的西方思想家关于例外状态的思考与批判,大多关注权力在例外状态中做了什么,以及对公民造成了哪些危害,对自由民主政治构成了何种威胁。如施米特提出的“主权者就是决断非常状态”,并据此提出其主权决定论。阿甘本与阿克曼关注和主张限制的也都是可见的权力运用现象。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不决断”这种隐蔽、消极的权力行为。在非常时期,权力的不决断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一种权力的意志,不做决断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决断。巴卡拉克(Peter Bachrach)与巴拉兹(Morton S. Baratz)的研究指出,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精英为了防止不符合他们利益的议题进入讨论,完全可以控制议程的方式,令相关议题被摒除在外,使这些议题被免于讨论,以此来压制冲突。[8]因此,决策与不决策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分别代表了权力的两重面向。不做决策也反映权力的态度和意志,尽管权力保持缄默,但权力仍然在场。
第三,不决断,同样制造“赤裸生命”。从福柯开始,生命政治学揭示出了这样一种政治现象,即人的自然生命被纳入政治的考量之中。阿甘本运用生命政治学思想,创造性地使用“赤裸生命”和“神圣人”等概念对例外状态进行了批判。应该认识到,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背后,是例外状态中权力的积极行动和扩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疫情之下,我们正在见证另一种“赤裸生命”,以及一种例外的例外状态。在这种例外状态中,权力并不直接危害人的身体,也不直接对人构成压迫,甚至以公民权利和民主政体的保护者自居。然而吊诡的是,人的生命却仍在政治的算计之中——隔离、封城、停产等措施是否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要求公民出门戴口罩是否会降低自身的支持率?疫情造成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打击政敌的武器?医疗、保险行业的资本利益和患者的生命哪个更重要?穷人和富人,老人和年轻人,哪个更有资格获得医疗资源?……执政者把国民的生命和诸多利益置于天平之上,然而天平却并没有向生命倾斜。在诸多考量之下,如果国家权力无所作为,举国民众就会化为“赤裸生命”——他们被国家权力所抛弃,任由他们无所遮蔽的暴露在病毒面前,漠视他们的生命为疫情所吞噬。如果说,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是人在社会暴力与政治权力下的赤裸,那么当前的“赤裸生命”就是被政治权力弃之不顾直面威胁的赤裸。在最需要公共权力有所作为的非常时期,如果他们却得不到来自公共权力的救助,对于执政者而言,病亡人数和感染人数都不过是一串冰冷的数字。
综上所述,真正应该批判的并非例外状态,而应该是例外状态中权力的不当运用,是权力的非公共属性。真正应该消除的也不该是例外状态,而是导致例外状态发生的社会根源,是正在酝酿的社会矛盾和风险。例外状态不该成为极权专制与政治迫害的代名词,相反,在一些例外状态中(如革命和防控疫情),权力塑造的例外反而是民众获得救济、免于遭受更大损害的途径。所以,评价例外状态的关键,应该聚焦于例外状态中权力,分析其权力的性质。而例外状态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权力的孔隙,通过例外状态,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权力的真实面目。如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中国采取了隔离、封城等限制措施,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而一些国家虽然以尊重自由权利来粉饰其无所作为,但其国家权力的阶级性、私有性却也暴露无遗。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例外状态,已经撕扯出了一条观察权力的裂隙,无论是否承认这个例外状态,都能呈现出权力的立场与意志。
四、 结 语
2020年初以来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证明,例外状态自有其存在的社会根源。一味地批判例外状态,想要永久地消除例外状态,或是对权力盲目的限制都是不合时宜的。真正需要追问的应该是权力的性质,是谁之权力?维护谁的利益?体现了谁的意志?如果是已经异化了的公共权力,那么无论是否启动例外状态,它都将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司法与行政的实践中滥用例外状态,并且谋求例外状态的长期化、例行化,然而另一方面,当国家真正需要启动例外状态应对危机时,国家权力却迟迟不做决断,无所作为。实质上,这种看似矛盾的吊诡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即公共权力的异化,它属于政治精英,属于资本财团,却不属于广大民众。在这种异化权力的统治之下,人人都是赤裸生命,时时都是例外状态。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进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地要求我们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去构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以抵御各种未知风险。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需要国家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实现从“危”到“机”的转化。这也必然要求中国学术界依据中国自身政治实践去完成例外状态以及国家紧急权的理论建构。应该认识到,例外状态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政治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会面临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风险,甚至在很多时候,这种风险还是未知的,毫无预兆的。不过,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本质上决定了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够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抗风险。国家与社会的利益与认识高度一致,因此在例外状态中,国家的一些非常之举能够得到民众的充分谅解。只有权力真正属于人民,例外状态才不至成为公民权利的对立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