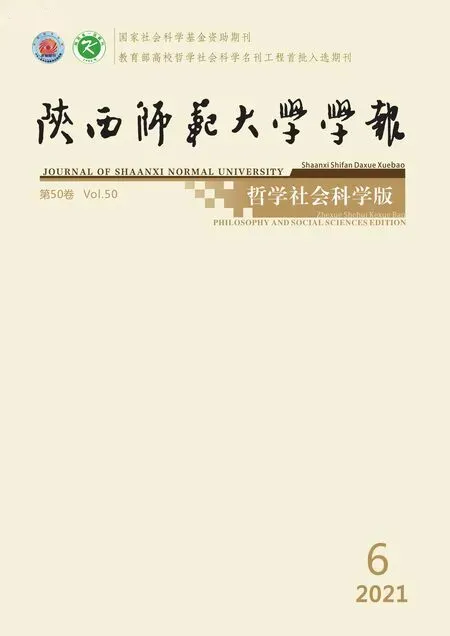学科建构视角下的语言治理研究
王 春 辉
(首都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语言治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一、 引 言
“2015年国家语委全体委员会议”于当年1月在北京召开,“强调要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从落实依法治国要求的高度,推进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参见教育部网站: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07/201501/183145.html。。2020年10月13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要“构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语言发展规划,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0/13/c_1126602191.htm。,这也应该是“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新目标的思维主轴”[1]和枢纽工作。“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后者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构成。
语言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2]它至少涵盖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语言文字本身的治理、语言文字生活的治理、语言文字工作的治理、语言治理助力国家治理。
语言治理研究就是针对上述几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当前中国的语言治理研究主要聚焦以下论题:语言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国家语言能力、领域语言治理研究(网络语言治理、语言扶贫、应急语言、国际中文教育等)、全球语言治理、语言治理与国家安全、法治社会的语言治理、智慧城市与语言治理等。本文的目的是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梳理语言治理研究的源流并对其未来予以展望。
二、 语言治理研究的源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治理观”“语言治理研究”“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等新提法是中国语言生活派经过近20年发展之后的一个新提升,是一个新系统和新范式,是中国学者在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自觉探索适合东方传统、本国国情的理论体系的最新尝试。[3]语言治理研究的异军突起是时代背景、历史积淀、现实需求、学科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国内和国际学界的互动融合、顺势而为。
(一) 语言治理研究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个学科或者研究方向的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底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个学科建立起来,其时代背景就是二战以后诸多新独立国家诞生,它们面临着一系列的语言问题,从语言文字地位的确立到语言文字规范的设定再到语言习得和教育的诸多方面。[4]
语言治理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勃兴亦有其时代背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世界环境与中国社会都正在经历巨大变革,许多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挑战由此产生,进而对语言文字事业以及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的确立为语言治理研究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和时代机遇。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构成[3],国家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类语言文字问题,都是语言治理应当关注和予以解答或解决的。[5]
(二) 语言治理研究的学术沿革
时代背景提供了历史契机,而已有的学术研究则为语言治理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给养和基础。语言治理研究的学术承袭可以从学科外和学科内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学科外是国际和国内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研究的勃兴,学科内则是国内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历史沿袭。下文聚焦于学科内这一层面,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 国内学术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政策与规划以及对于语言生活的描写和解释一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最核心的研究领域。[6]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3)这里的分期采用了李宇明教授的建议。: (1) 1949—1985年,以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为界,基本完成了汉字简化和规范化、普通话推广、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民族语文工作、扫盲运动等五大任务,建构起了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底盘; (2) 1986—1999年,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为界,以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法制化”为特征,为语言文字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3) 2000—2019年,以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国家和公民语言能力为特征,提出语言资源的理念、语言生活的理念,提出大语言观、大语言工作观等构想; (4) 2020年以来,以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为界,是中国语言治理阶段的开启,开始致力于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依据上述事业的4期划分,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也可以分为4个时期:五大任务研究为主的时期、“四化”研究为主的时期、语言生活研究为主的时期、语言治理研究为主的时期。这一研究重心的演变趋势可以表示为下图1。总体来看,语言治理研究是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新时期的新发展,前3个时期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来语言生活派的研究[7-8],为语言治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1 新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重心演变
2. 国外学术沿革(4)由于笔者语言背景原因,这里的“国外研究”仅限于英语文献。
“治理”具有很强的地域和国别性,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语言治理研究兴起的影响是间接的。这种间接性一方面体现在将语言与治理联系在一起的个别的、非系统的研究中,另一方面体现在术语的翻译中。
英语学界直接聚焦语言治理这一主题的学者不多,文献也有限。威廉姆斯(Williams)的论文集是较早将“语言”与“治理”链接起来的文献,但地域限于欧洲和加拿大,论题聚焦官方语言的推广以及小族语言的相关问题[9];沃尔什(Walsh)则明确提出了现有的“语言政策”概念框架应该扩展到包括“语言治理”这一新兴领域的观点,因为后者关注机构和组织寻求制定语言政策的多方面内部和外部环境[10];普帕瓦茨(Pupavac)聚焦语言权利,认为国际语言权利正在从言论自由转向语言治理[11];斯贝罗(Sberro)认为语言可以作为边界,并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语言治理方面的经验和前景[12]51-72;威廉姆斯(Williams)和沃尔什(Walsh)分析了少数族裔语言治理和监管的问题[13]101-129。
术语翻译,指的是有的学者将language management这一术语译为语言治理。国际上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流派,比如以伯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吉瑞·内克瓦虎尔(Jiri Nekvapil)等为代表的“语言管理”学派(language management),以托马斯·李圣托(Thomas Ricento)、詹姆斯·托勒夫森(James Tollefson)、斯蒂芬·梅(Stephen May)为代表的“语言政治”学派(language politics)、以南希·霍恩伯格(Nancy Hornberger)、特丽莎·麦克卡蒂(Teresa McCarty)等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志”学派(linguistic ethnography)等。(5)周庆生曾提到了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四大流派(见周庆生《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和思想》,《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与本文的分类不同。随着近20年中国语言生活派研究的提升,这些学派的主要成果、理论方法等都已被翻译或引介到了国内,他们与语言生活派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这其中,“语言管理”学派对语言治理的兴起起到了间接推动,(6)国内在指称“语言管理”学派时其实有两个分支,即伯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为代表的分支(Bernard Spolsky.Language Manage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和以(吉瑞·诺伊施图普尼)、(比约恩·颜诺)、(吉瑞·内克瓦皮尔)为代表的分支(何山华、戴曼纯《“语言管理理论”:源流与发展》,《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年第1期),本文这里说的是第二个分支。即有些学者在引介“语言管理”理论时,也会翻译成“语言治理”,比如周庆生[14]、郭龙生[15]等。(7)个别学者则是在国家治理框架下来分析语言管理理论的功用,如王世凯《新时代呼唤中国特色语言管理理论》(《语言文字周报》,2020年1月1日第2 版)。应该说,语言治理不仅是国内语言生活研究的新发展,也是对语言管理等国际研究范式的新超越[16]。
(三) 语言治理研究的历史节点
王春辉指出,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网络和现实中的语言文字治理问题,但这一时期治理视角的研究基本上是微观地或零星地就事论事,对于“治理”的认知还未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对于语言治理及其在国家和全球治理中作用的研究还是不自觉、非系统的。学界真正自觉地从国家和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系统性探究语言问题和对策是近几年才出现,准确地说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开始的。[2]
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应该还不是太精准。2013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命题提出之后,学界有了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解读和考察“语言治理”的自觉性,但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非“系统性”研究,仍未从“学科建构”的层面进行探讨。这种状况一直到2020年才有了质变,实现了“系统性”考察、“学科建构”视角的突破。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或许2020年是中国语言治理研究开始系统性构建的元年。这一年有好几个标志性事件,正符合复杂系统论所谓的“涌现”[17]52-64。
一是术语界定。以往以“语言治理”为主题的研究尽管使用了这一术语,但是并没有进行界定和系统阐释(8)郭龙生《双语教育与中国语言治理现代化》(《双语教育研究》2015年第2期)和妥洪岩、田兵《社会学视角下的美国语言治理解读》(《前沿》2015年第1期)两文中曾论述到“语言治理”,但是前者说的是欧洲的“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后者说的是福柯意义上的“语言治理术”(language governmentality),与本文所说的不是一回事。与本文的界定更为接近的是刘华夏、袁青欢《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一文使用的语言治理,但是其视角仅聚焦于“边疆语言治理”。,比如张日培[18]、任颖[19]、文秋芳[20]等。2020年伊始,王春辉连续刊发4篇文章,对“语言治理”进行了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初步探讨了“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2][21-23]。随后李宇明[24-25]、王玲和陈新仁[5]等分别从路径和观念的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是研究蜂起。以“语言治理”为主题搜索“中国知网”,去除干扰项,从1985到2020年一共有108篇文献。从年度发表来看,2015年首次超过10篇,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2019年的16篇,到了2020年则倏然达到了35篇,这一突起的趋势如下图2所示。

图2 “语言治理”主题年度发文趋势
三是专题探讨。首先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2020年5月第3期刊发了全国首个“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研究专题;9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发了第二个语言治理专题。(9)2021年两个杂志延续这一趋势,又各自推出了两期语言治理研究专题。“语言治理”作为核心板块之一,也首次被列入《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21)》。
四是论坛荟聚。2020年1月和12月,首都师范大学语言治理研究中心相继举办了两届“语言与国家治理论坛”[26-27];2020年11月,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全球语言治理论坛”。
五是会议指引。2020年10月13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的“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新目标的思维主轴”[1]10,这也为未来中国的语言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
任何一个学科或者研究方向的发展,都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即一开始的研究是零散的、非系统的,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成为聚合的、系统的。本文着眼于语言治理研究的学科发展脉络,强调“系统性建构”就是着眼于“质变”这一临界点,这是学术研究的规律。正如李宇明所言:“一般情况是,先有学者对某社会语言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发表论文。接着,兴趣研究扩展为专题,有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和科研项目,再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最后发展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28]
三、 语言治理研究的未来
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中国的新发展阶段,语言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前景广阔。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的中国语言治理研究有必要在以下一些论题上重点着墨:
(一) 厘清术语关系
目前来看,围绕着语言与治理二者有机体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有不同的称述,如语言治理[2][5][16][18][24],语言文字治理[3],语言生活治理[24][29-31],语言文字工作治理[1]等。术语使用上的多样,也正反映了其处于初始阶段的特征。
综合来看,可能“语言治理”是一个更具有概括性和包容性的术语:一方面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文字的基础,谈“语言”往往就蕴含着“语言文字”;另一方面“语言治理”既可以包括治理对象的“语言生活”,也可以包括治理工作的“工作治理”;最后一点,比起其他说法来,“语言治理”更简洁明了,也更方便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
(二) 明晰研究取向
一般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基本上有3种研究取向[31]: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语言作为资源。上文图1中提到的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的4个阶段与这3种取向也有一定对应关系:前两个时期主要是语言问题观和语言权利观,第3个时期主要是语言资源观[32]。当前进入语言治理研究阶段,其在研究取向上应该说是一种综合观,即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语言作为资源3种取向的互补融合。在这一取向下的语言治理理论和语言治理实践宜采用的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
(三) 分步骤的语言治理研究
语言治理是一个分步骤的实践过程,大致说来包含以下几个主要环节:问题识别(收集数据)——目标详述(治理措施撰写)——成本和收益分析(理性演示可选择方案,投资回报率)——治理措施执行(措施付诸实施)——评估(将预期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十多年前托马斯·李圣托就提醒人们要注意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两大困境: 一是有关语言规划的实践问题还没有深入的探讨,即具体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二是研究者们对语言规划的机制缺乏兴趣[33]17。时至今日,这两个困境依然存在。未来的语言治理研究有必要在各步骤的精细描写和深入解释上提升力度。
(四) 分主体的语言治理研究
语言治理的主体(agents)是多元的[18],至少涉及以下一些主体:执政党,政府部门(比如外交部、民政部、工信部、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国务院侨办等),司法机关(检察院、法院等),社群团体(语言团体及与语言文字相关的社会团体),企业(出版企业、人工智能企业、语言产业相关企业等),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等),个体公民(知名人士、权威学者、普通大众等)。[2]与此相对应,后续的语言治理研究需要针对不同的治理主体进行细化考察,比如国家语言治理、部门语言治理、司法语言治理、社团语言治理、企业语言治理、媒体语言治理、公民语言治理等,探究它们的内涵和外延,考察不同主体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现代化的路径措施。
(五) 分领域的语言治理研究
语言治理不是空中楼阁、空悬的理论,而是脚踏大地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具体实践探索。未来的语言治理研究,更多地需要精准的、细化的领域性研究,比如国家安全领域、乡村振兴领域、外交领域、国际关系领域、新媒体领域、人工智能领域、数字社会领域、航空领域、人名地名领域、边疆治理领域、法治领域、教育领域、健康领域、老年社会领域、机器人领域、国防和军事领域、医学领域、消费领域、艺术领域、科技领域、经济领域、服务领域、政治领域、道德伦理领域等。领域语言治理的基本运作机制可以是:行业主管部门“主管”,国家职能部门指导,专家队伍学术支撑,多主体合力治理[34]。
(六) 语言治理研究的学科建构
除了上述5点,语言治理研究的学科建构还需要在理论、方法、队伍、人才建设,以及学科层级、刊物、课题等诸多方面努力。
在理论方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启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学术体系的内化,汪晖一语中的地指出:“由于与西方思想的碰撞,在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期,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都被重组了。我曾经将这个重组概括为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公理世界观对于以儒学及其价值为基础的天理世界观的替换。”[35]217经过180多年的民族奋斗,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转型,即“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向“以中国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变。[36]中国学界亟须王汎森所提到的第二个自觉,即“自觉到从本土的经验与学术研究可能提出独特而有意义的理论建构”[37]。这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的语言治理研究,即基于中国国情、中国实践和中国研究可能提出独特而有意义的理论建构。比如在语言助力人类减贫治理方面[38-39]、语言应急治理方面[40]、语言国情调查[41]、学前学习国家通用语言[42]等领域,中国学者就进行了一些前沿性探索,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创见。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核心,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实践给人类未来发展带来各种影响,未来的中国语言治理研究也应抓住时代机遇、为人类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理论探索贡献更多力量。
在方法方面,也是语言治理研究需要着重强化建构的方面。从整体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语言本身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语言治理更是一个复杂系统,在研究方法上更加需要的是与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相协调的方法论,即系统论[43]。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传统似乎比西方近代哲学更有优势。正如普里戈金和斯唐热为《从混沌到有序》写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44]1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鉴于语言治理研究是一个跨学科、交叉的领域,除了对语言学领域方法的应用之外[45-46],也需要借鉴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物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治理研究是当下中国新文科和交叉学科发展的天然试验田。
其他方面,还涉及学科地位问题(比如语言学成为一级学科,语言治理是否有可能划到交叉学科等)、课程体系问题(即语言治理方向应该开设哪些课程,如何完善知识体系等)、人才培养问题(本硕博的连续性,招生和就业等)、队伍建设问题(构建语言治理研究共同体)、研究成果发表问题(发表的语种选择、出版社和刊物范围、新刊创设等)、课题的设立和申请(10)2020年和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连续两年有关于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课题立项;2021年的国家语委科研项目则将“我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现状及创新研究”列为重大项目之首。等。
四、 结 语
人类学科发展的历史证明,综合实力是决定一国学术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提升,站在时代更前沿的中国在一些领域正在从跟随者向领跑者转变,一些人类社会引领性的发展趋势正第一时间在中国出现,比如数字货币、网络支付、电子银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等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中国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处于同等甚至领先水平的。从跟随到引领,这就意味着许多相伴随的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话题也会同时甚至第一时间在中国出现。这就给中国的语言治理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来源和施展空间,也就可能在理论和实践的传导中被他国所借鉴。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新的社会形式——数字社会,它对语言治理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语言治理研究有必要对人类社会这一新形式予以重点关注。[47]
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该纲要的出台为中国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也为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语言治理描绘了蓝图、列述了指南。
在上述背景下的语言治理研究,需把握机遇、顺势而为,放眼人类历史进程、脚踏中国大地河山,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国情怀,“注意发现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发现这些问题的着眼点和入手处”,“将所发现的问题‘学术化’”,以解决学科发展和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48]。
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在中国的新发展阶段,语言治理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的演变,更是一系列研究理念(国家治理观、语言治理观、整体观和系统论等)、研究行为(分步骤的、分主体的、分领域的等)和研究规范(研究方法、写作范式、交叉学科等)的变革。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专业或学科或研究方向在其初始期,最好采用分子遗传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提出的“有限的草率原则”,即一门科学在它的最初阶段如果不能在某些关于定义、概念和测量的问题上放宽一些,它就不能迅速进步。[49]2对于语言治理研究这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来说,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