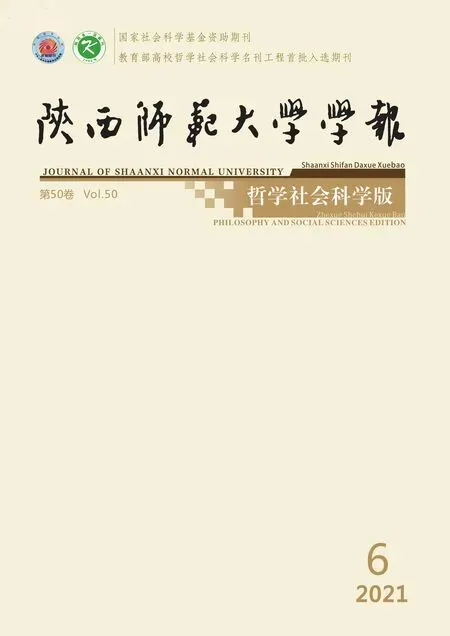中国古代早期庶人的“名”与“姓名”
鲁 西 奇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4)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1]1-2在《通志总序》中,郑樵引左氏之论,以为“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1]5,其所举32类氏姓,亦皆源于国、邑、族、部、官、爵及事、技,故其所说之“贵者”即有土有民或有官爵、身份及因技能而得尊显者,“贱者”则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即“庶人”(1)“庶人”的本义即“众人”。在先秦至秦汉文献中,“庶人”一般与诸侯、卿大夫、士以及工商、隶臣并列,用以指称无特权身份、人数众多的平民百姓。本文所讨论的“庶人”,即在此意义上的“庶人”,主要指西周春秋时期不具有贵族身份的“国人”和“野人”,以及战国秦汉时期的编户齐民。在战国秦汉时期,部分平民(编户齐民)因军功而获得官爵,或因罪而被罚没为徒隶,然其出身身份仍是普通平民,也包括在本文所讨论的“庶人”范畴之内。关于先秦时期“庶人”的内涵与指称范围,请参阅斯维至《论庶人》,《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张玉勤《也论庶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应永深《说庶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何兹全《众人和庶民》,《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关于秦、西汉时期的“庶人”,请参阅曹旅宁《秦汉法律简牍中的“庶人”身份及法律地位问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王彦辉《论秦及汉初身份秩序中的“庶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此论为后人所沿袭并不断充实、发挥,遂基本成为定论:贵者有氏有名,庶人有名无氏。顾炎武概括说:“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2]1 279李学勤说:“在古代社会中,并不是人人都有姓氏。姓是只有具备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有的……至于氏,得自世功官邑,身份低贱的人自然也无从具有。”[3-4][5]116-136李学勤还引述考古发现所见甲骨文、金文文献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证。(2)关于中国古代姓名的一般性认识与相关研究,请参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侯旭东主持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219页。张淑一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先秦的庶人与贵族二者虽然存在贵贱、贫富的差别,但其毕竟都生活在同一社会发展模式当中,有着类似的血缘组织形态,因此在血缘组织的标志符号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差异,庶人也应当有姓、氏”[6]92-106。张氏之驳议虽然并非十分有力,然却说明:庶人(平民)既然均属于特定的血缘组织(或集团),自当“有”其姓氏;而文献所见,庶人却多无姓氏,盖“有姓氏”与“称姓氏”并非一事:庶人有姓氏,却未必“称姓氏”,故文献所见庶人“称名不称氏”,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庶人”即“无氏”。故此一认识的正确表述当是:上古时代,庶人或亦有其姓、氏,却并不称其姓氏,而只称其名。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论者遂得进一步讨论上古时代(商和西周)的姓氏制度与称名方式(贵者用“氏+名”,庶人但称名)如何向秦汉及其以后的姓名制度演变的问题。一般认为,自春秋战国以迄于秦并六国,随着同姓不婚制度的逐渐破坏和家族组织的一步步解体,姓氏“别婚姻,明贵贱”的功能逐步丧失,“姓氏混而为一”,姓即氏,氏即姓。(3)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制度的变革及姓氏合一,请参阅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1—458页;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146页。同时,不同社会阶层的称名方式也渐趋统一,无论贵贱,皆得使用“姓(氏)+名”的称名方式,以姓名为称。战国以至秦汉时期,乃是庶人姓氏形成并逐步普遍化的阶段;秦汉以后,庶人及其以下阶层均得普遍使用姓氏。(4)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庶人逐步拥有姓氏、庶人称名由单称名到使用姓(氏)名的演变,请参阅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特别是其第一章,《古代姓氏制的展开和“家”的建立》,第63—94页;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88—196页。杜正胜曾概括性地指出:自春秋战国以迄于秦汉,随着古代贵族社会的解体,以及编户齐民制度的实行,普通民众乃模仿或抄袭上层贵族社会,给自己的名字冠以姓氏,从而使人人得以有姓。可是,杜正胜并未对此展开细致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并未举出证据,以说明普通民众的姓氏,乃模仿或抄袭上层贵族社会而来,以及何以要模仿或抄袭上层社会的称名方式,请参阅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特别是第11—12页。因此,对于庶人称名方式的变化,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在殷商和西周时代,庶人称名不称氏(无论其是否有氏),春秋战国庶人渐有称氏者,至秦汉时期,庶人逐步普遍地使用“姓名”。
总的说来,关于中国古代姓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姓氏制度的形成、变化及其政治、社会内涵与意义方面,特别是社会上层(贵族与官僚士大夫阶层)采用或获取怎样的姓氏、姓氏在政治与社会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对于庶人(平民百姓)的称名方式及其变化,仅在讨论称名方式的阶层差别及其所反映的尊卑贵贱的政治与社会差别时,有所涉及,并未予充分展开。(5)侯旭东在讨论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时,曾分析户籍制度的建立对于平民百姓“策名委质”的意义,请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5期。然庶人的称名方式及其变化,实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盖庶人唯有其名,方得与他人交往,通婚、交易,处理矛盾、解决纠纷,结成社会关系与组织,形成社会关系网络。而庶人之名,本起于口语称谓,口语所称之名主要用于特定的人群范围及其社会体(主要是其所在的血缘或地缘人群与组织)内,以音表达并传递其意涵,故在一般情况下,并无须指称其所属之血缘或地缘人群、组织或集团(族、氏),亦无可能得到书写,并被文献记录下来(文献所记,主要是血缘或地缘人群组织、集团的首领与上层,即贵者,故贵者称氏)。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古代血缘或地缘性人群组织或集团渐趋解体,建立在地域与人民控制之上的新型政治体逐步“越过”贵族阶层,直接掌握、控制普通平民(庶人),列名籍,别乡里,庶人之名遂被书写成文字(而不仅仅限于口语发音),列入籍簿,以征发赋役。在这一过程中,庶人名的功用、内涵均超越了其原有的血缘、地缘组织(家族或村落)的范畴,并被应用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故其所属之血缘或地缘组织乃成为界定其属性(特别是来源属性)的组成部分,氏遂被冠于其名之上,形成姓名。不仅如此。由于庶人多不识字,不能自书其名,庶人之名得到书写,多是书写者根据庶人所报告其名之发音,选取适当的文字书写成特定汉字,并在其名之上冠以氏称。所以,庶人名之书写及其姓名之成立,虽然有庶人自身之报告与其所属血缘、地缘组织为基础,但在根本上,仍主要是国家权力(书写者、文字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家权力的代表)从外部进行干预甚至直接执行的结果。因此,庶人的称名方式,包括3个层次的问题: 一是庶人如何称名(即口语表达的人名),二是庶人之名如何被书写为特定的文字(即书写成文字的人名),三是庶人之名如何被使用(即实际使用的人名)。
就逻辑层次而言,庶人自然是先有其名,后被书写,然后方得被使用。可是,历史上的庶人之名,唯有被书写下来,方能得见。故吾人所讨论之庶人名,乃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庶人名,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得到记录的书写人名。本文之研究,即从中国古代早期(周秦至汉初)不同文献对于庶人名的记载出发,考察古代早期庶人名使用的不同类型与方式,分析书写性庶人名的结构,进而探究庶人“名”与“姓名”的本源与实质。
一、 庶人的称名方式及其变化
“九年卫鼎”铭文记载周共王九年(前914)裘卫用车和各种皮革同矩伯交换土地的经过,其中说到交换的土地位于颜林里,由颜氏具体占有并管理,故裘卫在向“矩”和“矩姜”支付眚车、、贲鞃、帛等物之外,另外“舍颜陈大马两,舍颜姒,舍颜有寿商裘盠(幎)”。协议达成后,“矩”与“”乃指挥“寿商”具体办理交接事宜,“乃成夆四夆,颜小子具叀夆”。交接完成后,裘卫通过“卫小子家”“卫臣”,“舍盠冒□羝皮二,皮二,业舃俑皮二,朏帛金一反,厥吴鼓皮二。舍虎、□贲□鞃,东臣羔裘,颜下皮二”。[7-8][9]194-204;[10-11]铭文中的“矩姜”当是矩伯之妻,“颜陈”与“颜姒”当是颜氏的夫人,其称名方式,皆属于贵族阶级的称名方式,即“夫方的氏+父方的姓”。“裘卫”之名,则为“氏+名”,是贵族阶级男子最为普遍的称名方式。“”可能是矩伯的“有司”或“臣”,“寿商”是颜氏的“有司”,“家”是裘卫的“小子”,“”是裘卫的“臣”;“盠”“业”(或“业舃”)、“朏”“吴”“东臣”都是参与此次土地交割的“小子”,铭文所记,皆当为其名,其称名方式,符合“庶人不称氏,称名”的规则。
著名的“散氏盘”铭文,记载“散”与“夨”双方划定眉、井2邑土地疆界的过程及其结果。据铭文所记,参与勘界的“夨”方代表有15夫,即“眉田鲜、且、微、武父、西宫、襄,豆人虞丂、录贞,师氏右眚,小门人繇,原人虞艿,淮工虎孝、丰父,人有司、丂”;“散”方代表有10夫,即“土□□、马兽,人司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段父、父,之有司橐,州,焂从”。[12]345-346豆人“虞丂”与原人“虞艿”称名中的“虞”,当为姓。其余诸人,鲜(“田”为职名)、且、微、武(“父”为尊称)、西宫、襄、贞(“录”为职名)、眚(“师氏右”当为职名)、繇(“小门人”为其身份)、虎孝(淮人,“〔司〕工”为职名)、丰(“”为职名,“父”为尊称)、、丂(人的有司)、兽、(“君”亦当为尊称)、德(“宰”为职名)、戎、段、、橐(“州”当为职名)、(“焂”当为地名,“从”当为职名,或“焂从”即为职名),则皆有“名”而无“氏”。“豆”“原”“小门”“淮”“”“”“”等皆当是眉、井2邑所统辖聚落的“有司”,即各聚落的管理者,故铭文只称其名;“虞丂”“虞艿”则当为豆人、原人之首领,故得有姓(“豆”“原”或为其氏)。
山东临淄等地出土战国陶文中,述“立事”之官长,多称其氏与名,如“平陵陈立事岁”[13]46-54的“陈”,“内郭陈齎叁立事左里敀[亭](亳)豆”[14]91的“陈齎”,“王孙陈棱立事岁左里敀[亭](亳)区”的“陈棱”,等[14]96,99;而署制陶之陶工名,则多为单字名,如“高闾里曰潮”“高闾豆里人匋者曰兴”,[14]500“左南郭[乡](巷)辛[](匋)里臧(井圈,临淄出土)”[15]1 178。《新出齐陶文图录》0349:
“陈固”是昌櫅(又作“昌齐”,齐都临淄的区域名)的“立事”,由他主持制作此件置于昌櫅南左里敀亭的“区”;右敀□[乡](巷)尚毕里的“”(“季”为其排行)是制作此件陶区的陶工。“立事”者称名用“氏+名”,陶工单用“名”,符合“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的称名规则。
包山楚简85是一支疋狱(狱讼记录)简。简文曰:
包山楚简120、121、122、123所记是关于一宗刑事诉讼案的详细记录。其大意谓:周客监“”楚之岁享月乙卯,下蔡荨里人“舍(余)猥”向下蔡的“执事人”(负责治安司法事务)、昜(阳)城公“(瞿)睪”报告说:“”(据下文,为下蔡山阳里人)窃马于下蔡而卖之于阳城,又杀下蔡人“余睪”。阳城公瞿睪命令“倞”拘捕了。丁巳日,向阳成公瞿睪、大尹“屈”、郫昜(阳)莫嚣“臧献”“舍(余)”供称:自己并不曾盗马,但确实与下蔡关里人“雇女返”、东邗里人“场贾”、荑里人“竞不割(害)”共同杀害余睪于“竞不割之官”,但竞不割并未亲手杀人(“不至兵焉”)。行文相关各里,命令抓捕场贾、雇女返与竞不割以及的家小(“孥”),(东邗里)里公“”、士尹“缜”、加公“臧申”、(关里)里公“利臤”、(荑里)里公“吴”、亚大夫“(宛)乘”以及加公“范戌”、(山阳里)里公“余□”都回复说:诸人已于此前逃跑。后来,未及判决,即死于狱中。[16]25;[17]53在这件文书中,“周客”(当是周天子的使者)、“监”(官称)被称为“”,是单名,未及其姓、氏,然前已指明其为“周客”。昜(阳)城公“瞿睪”、大尹“屈”、郫昜(阳)莫嚣“臧献”、“舍(余)”以及里公“”、士尹“缜”、加公“臧申”、里公“利臤”、里公“吴”、亚大夫“(宛)乘”、加公“范戌”、里公“余□”是不同级别的官员,其称名大抵皆可确定为“氏+名”。“余猥”是下蔡荨里人,“”是下蔡山阳里人,“雇女返”是下蔡关里人,“场贾”是东邗里人,“竞不割(害)”是荑里人,他们都当属于楚国的庶人,也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
包山楚简151、152载:
左驭“番戌”有食田,属于贵族阶层,故“番戌”“番疐”“番”“番”之称名,用“氏+名”的方式,“番”乃为其氏。然番戌之食田,在国噬邑,“番”之氏称并非得自于食地。番戌死后,番家地位似渐次降低,至番乃卖掉食田以偿债,其地位盖已降为庶人,然仍得称为“番”氏。
据包山楚简2、3、4、5、6记载: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楚怀王九年,前320)冬之月,令“彭围”(下文称为“围”)受命检查人的户口籍帐,有一位名叫“”的书吏具体登记了两个人(“凡君子二夫,是其箸之”),都属于“之少僮,族”,一个叫“”,另一个叫“”,居于路区湶邑。[16]17;[17]3“”与“”都属于“族”,族即氏,则2人的正式称名当分别为“”“”。他们被登记在的“玉府之典”中,又被称为“君子”,其地位可能较高,或者并非庶人。而在包山楚简11中,的上连嚣“之还集瘳(廖)族衍一夫,(处)于(国)之少桃邑,才(在)陈豫之典”。这里的“衍”属于“瘳(廖)族”,被登记在“陈豫之典”中。所谓“陈豫之典”,当即简7、8、9中齐客陈豫贺王之岁(楚怀王十二年,前317)八月乙酉日大莫嚣“屈昜(阳)”命邦人上内(纳)的“溺典”。在简7、8、9中,“臧王之墨”(官署名,可能负责供应王宫的用墨)上纳了“其臣之溺典”,中有“喜之子庚一夫,(处)郢里,司马徒箸(书)之;庚之子一夫、之子一夫,未在典”。[16]17;[17]3居于郢里的“庚”被登记在“臧王之墨”管领的“溺典”中,其身份似乎是“臣”。“喜”“庚”“”“”,一家4代人,均以名称,未及其氏或族。列入陈豫之典的“衍”,地位当与“庚”一家相似(或者都属于“臣”),却有明确的“族属”。而在简32中,邸昜(阳)君之州里公“登(邓)缨”于八月戊寅“受期”,然到辛巳之日,却因“不以所死于其州者之居处名族至(致)命”而使“阩门有(又)败”。[16]19;[17]16死于邸阳君之州者不知何人,然里公“登(邓)缨”按规定应当报告其“居处名族”,说明其时无论身份若何(即使是“臣”),皆有其“名”与“族”。前引包山楚简120、121、122、123中,述及“”“雇女返”“场贾”“竞不割(害)”等人,都言明其居处名族,即符合法律的规定。

而秦人的称名方式又有所不同。“秦封宗邑瓦书”铭文记载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分封宗邑的情况。在铭文中,受周天子之命“来致文武之酢(胙)”的卿大夫书作“辰”,传命分封的秦大良造、庶长名“游”,受封的右庶长名“歜”,具体负责确立封地的司御、不更(秦军功爵第四级)“顝”,参与划分封地界线的大田佐“未”、史“初”与“羁”、卜“蛰”、司御“心”,无论其地位高低,均只称名,而未著其姓氏(无论其有无氏),其中,顝、未、初、羁、蛰、心等低级官吏,地位大抵近于庶人。[18][19]177-196;[20]
里耶秦简中所见曾担任洞庭郡“守”或“假守”的人有:“高”[21]374(简9-1 861)(假守,秦始皇二十六年二月在任)、“昌”[21]35(简9-23)(假守,秦始皇二十七年十一月在任)、“礼”[21]447-448(简9-2 283);[22]46(简8-61+8-293+8-2 012),193(简8-657),217(简8-759)(守,秦始皇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年二月、三十四年六月在任)、“齮”[21]186-187(简9-713)(假守,秦始皇三十一年六月在任)、“铺”[21]376(简9-1 864)(假守,秦始皇三十四年十月在任)、“绎”[22]217(简8-759),348(简8-1 523)(假守,秦始皇三十四年六月在任)、 “冣”[21]325(简9-1547+9-2041+9-2049)(假守,秦二世二年十月在任);担任南郡“守”的有:“恒”[22]119(简8-228);[21]414-415(简9-2076),内史“守”有:“衷”[22]119(简8-228),南阳郡“守”有:“衍”[21]414-415(简9-2076)。这些郡守一级的官员,在正式的官方文书中,也只是用单名。


里耶秦简8-145所记是迁陵县接受并分配、移交官徒的记录,其中所见徒隶之名,有圂、叚、却、剧、复、卯、枼、痤、带、阮、道、遏、、豤、款、、林、娆、粲、鲜、夜、丧、刻、婢、娃、变、齐、姱、、兹、缘、婢、般、橐、南、儋、青、夕、强、姊等,全部是单字名。[22]84-86简9-2289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迁陵县司空守“圂”上报的“徒作簿”,所记徒隶之名,见有平、臣、益、惊、亥、央、闲、赫、宵、金、、椑、鲤、厩、强、童、刚、聚、移、昭、操、宽、未、衷、丁、圂、辰、卻、剧、复、卯、枼、痤、蔡、阮、道、遏、、类、款、林、娆、粲、鲜、夜、吴、刻、嫭、卑、鬻、娃、变、齐、姱、梜、兹、缘、般、槖、南、儋、青、夕、强、姊、谈等;接收其中3名徒隶的县仓假守名“信”,书写并致送此件“徒作簿”的司空佐名“痤”。[21]455-458在这份文书中,从司空守、县仓假守、佐,到徒隶,全部是单字名。
在里耶秦简中,也有一些“户人”使用“氏(或姓)+名”的称名方式,如“杜衡”[21]50(简9-43)(高里户人,大女子)、“己夏”[21]108(简9-328)(东成里户人,不更,有隶大女子“瓦”)。“受令”简中,“受令”者有安成里不更“唐頪”[21]81(简9-170)、东成里不更“朱发”[21]266(简9-1130)、武安里不更“周柳”[21]274(简9-1186)、南里不更“公孙黚”[21]337(简9-1623)、南里不更“屈埜”[21]342(简9-1644+9-3389)、东成里不更“相赫”[21]343(简9-1650)、安成里不更“屈杨”[21]345(简9-1668)、安成里不更“远禾”[21]442(简9-2273)、安成里不更“蛮孔”[21]567(简9-3292)。在《里耶发掘报告》所公布的户籍简中,见有“蛮强”(K27,南阳户人,荆,不更,伍长,妻曰“嗛”,有子小上造“□”,子小女子“驼”,臣曰“聚”)、“黄得”(简K1/25/50,南阳户人,荆,不更,伍长,妻曰“嗛”、有子小上造“台”“□”“定”,子小女“虖”“移”“平”)、“大□”(简K43,南阳户人,荆,不更,有弟不更“庆”,妻曰“”,庆妻“规”,子小上造“视”和“□”)、李獾(K31/37,南阳户人,荆,不更,妻与2子之名均为单字,漫漶不识)、“黄□”(简K17,南阳户人,荆,不更,妻曰“不实”,有子不更“昌”,子小上造“悍”“□”,子小女“规”)、“彭奄”(简K30/45,南阳户人,荆,不更,有弟不更“说”,母曰“错”,妾曰“□”,子小上造“状”)、“蛮喜”(简K4,不更,有子不更“衍”,妻大女子“媅”,隶大女子“华”,子小上造“章”,子小上造“□”,子小女子“赵”,子小女子“见”)、“宋午”(简K2/23,南阳户人,荆,不更,有弟不更“熊”,弟不更“卫”,熊妻曰“□□”,卫妻曰“□”,子小上造“传”与“逐”,熊子小上造2人,并失名;卫子小女子“□”,臣曰“”)。[23]203-208;[24]144;[25]249-355他们全部是南阳里的户人,爵级亦均为不更,各自的弟、子也多有不更、上造、小上造的爵位,更全部是荆人。这些人的称名方式,很可能沿用上揭包山楚简所见战国中期楚人的称名方式(“氏+名”),而其弟、子、妻、妾、臣则因系于“户人”名之下,故仅称其单名。“受令简”中的“唐頪”等人,身份也都是不更,其地位与南阳里不更“蛮强”等人相似,故也很可能是荆人。
有5支简述及其所记之人时,特别指明其所属之“族”。如简9-885:
简9-757的行文格式与此相同:
更戍卒士五(伍)城父成里产,长七尺四寸,黑色,年卅一岁,族
“产”与“贺”都是来自城父县的更戍卒,同一天在戍地迁陵县廷受“探”(检查),监督“探”的迁陵县守丞“昌”“衔”与具体负责检查的令佐“章”均只署有单名,却特别指出“贺”与“产”的族属(“产”的族恰残缺)。(7)简9-1029所记的一个人,卅八岁,“族”字下也恰残;简9-1257所记的一位,名字也缺,卅一岁,“族黄氏”,分别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4页、第282页。城父,《汉书·地理志》属沛郡,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城父集,属楚东国故地。简8-1555:
冗佐上造临汉都里曰援,库佐冗佐。为无阳众阳乡佐三月十二日。凡为官佐三月十二日。年丗七岁。族王氏。为县买工用,端月行。库六人。[22]357

更为重要的是,据里耶秦简8-461,在秦统一后公布的正用字中,“曰产曰族”,即改“产”为“族”。换言之,秦言之“族”,乃是指六国言之“产”。[22]156而在前引简9-885、8-1555等简文中所说的“族”,显非“产”意,故其所谓“族”某氏,只能是在楚言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里耶秦简中所见“氏+名”的称名方式,很可能沿自战国中期以来楚人的称名方式,而其时秦人(无论地位高低)仍然多以单名为称。
秦据有楚地及统一全国后,盖推行秦的称名方式,故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与岳麓秦简所见人名,乃以单名为主,即使是荆(楚)人,也多单称其名,而较少使用“氏+名”的楚人称名方式。在岳麓书院藏秦简《狱状》“癸、琐相移谋购案”与“尸等捕盗疑购案”(均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五年)中,南郡假守“贾”,州陵守“绾”、丞“越”,沙羡守“驩”,校长“癸”,狱史“驩”,史“获”,监御史“康”,求盗上造“柳”,士伍“轿”“沃”“琐”“得”“潘”“沛”,走马“达”“好”,求盗“尸”,以及逃亡在荆地的秦男子“治”等固然是单名,荆男子“阆”等,也都是单名。[26]1-18,95-117“芮盗卖公列地案”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二年,是一起经济纠纷案件,涉案诸人大抵均为江陵本地人,其中有公卒“芮”、大夫“朵”、士伍“方”(“朵”子)、隶臣“更”、亭佐“驾”、“材”、走马“喜”,都是单名。[26]22-26,129-140
至西汉初年,情形又有所不同,普通编户齐民(庶人,庶民)盖已普遍采用“姓(氏)+名”的称名方式。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所出衣物疏称:
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伥(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葬),具器物名,令会,以律令从事。[27]91
“四年”,即汉景帝四年(前153)。张偃即墓主,他生前曾任过江陵西乡的有秩或啬夫,是乡里小吏。衣物疏是正式的丧葬文书,具有向地下主陈告亡人身份的功能。同墓所出另一块木牍上,记载了致送奠仪的人名(奠仪名单),有载翁仲、庄伯、应小伯、阎翁仲、陶仲、王它、王翁季、胡兄、袁兄、氾氏、姚季、张母、张苍、杨公子、靳悍、伥(张)父等16人;在木牍的背后,又特别记载了“不予者”2人:陈黑、宋则齐。翁仲、伯、小伯、仲、翁、翁季、兄、母、公子、氏、季、父等称谓,显然不是正式的名,但这些人的称名,却均当如张偃、张苍、靳悍一样,是“姓氏+名”的方式。
江陵凤凰山十号墓所出A类竹简(郑里廩籍),是汉景帝初年官府向郑里25户发放贷种、食的记录,其中所记“户人”之名,有圣、、擊牛、野、、、立、越人、不章、胜、虏、、小奴、佗、定民、青肩、人奴、楚奴、射□、田(公士)、骈、朱市人、奴、□、市人(公士)。[27]106-113这些在廩籍上登记且有其具结的户人名,应当是正式的称名方式,大多未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然在B类竹简关于“计算应役”的记录中,又以“氏+名”的方式称名,如简35:
邓得二、任甲二、宋则二、野人四·凡十算遣一男一女·男野人,女惠。[27]113
据A类竹简13,“户人野,能田四人,口八人,田十五亩”。简35中的“野人四”很可能就是指简13中“户人野”家中能田的4人。在A类竹简15中,“户人,能田二人,口三人,田廿亩”,“”很可能就是B类竹简35中的“宋则”。若然,则A类竹简所记“户人”,至少有一些本当是有姓、氏的,只是在廩籍中未予记载而已。在同墓所出记录算钱的木牍上,张偃也只被记作“偃”[27]100,说明即使在正式的官文书中,也可能只写其名,而省略其姓氏。
D类竹简中,每一支简只记一个人名,应当是乡里的名籍。简63、64、65、66这4支简,人名上都加了一个圆点,分别作“·杨人”“·郭贞”“·王则”“·杨暤”,应当是“户人”(户主),均使用“氏(姓)+名”的方式。其余简所记人名,既有用“氏(姓)+名”者,如“大女杨凡”“杨阆,小”“杨毋智”“杨累”“王终古”“王圣”“郭修”“伥(张)奴”“伥时”“伥□”“徐来”“杜留”“朱旦”“黄嬅”;也有仅记其名而未及其姓氏者,如“女迣”“泽之”“毋佗”“欧”“婧”“喜”“昴”“田”“益”“送”“缇”等,一般认为当属于家庭成员,因为系于“户人”之下,故省略其姓或氏。[27]120-129
综上考述,可以认知:西周之世,姓、氏盖为贵族阶级所独用,庶人不称氏,仅得称名。此种规则,至春秋时期,盖大多得到遵行。至于战国,齐国仍秉持旧规,贵族官吏多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庶人徒隶则但称其名(多用单字);楚国则较为普遍地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无论贵族平民,大抵皆有其名、族(氏);秦人则较少称氏(族),贵族官民,大抵皆以名为称。到西汉前期,姓、氏既合而为一,称名亦不再有贵族官僚与庶人(编户齐民)之别,故庶人称名,多用“姓氏+名”的方式。
二、 庶人名的书写
包山楚简“集箸言”“受期”“疋狱”及“案卷”等文书中,在每件文书的末尾,一般会标明由某人“(识)之”,某人“受李”(受理),所记当是本件文书的记录者和归档者,其身份应当是书吏。(8)关于“之”与“受李”,诸家有不同解释,请参阅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注18;第21—22页,注6。结合比较诸家之说,“”仍当释作“识”,解为“志”“记”;“受李”,当即“受理”。
简46:
简52:
简55:
简64:
对这4支简进行比较,可知其所记实为同一案件之多次提交审理,越异之司败、大帀(师)及“疋”()前后皆当同为一人。可是,在简文中,越异司败之名的写法,也有“”“豫”“”(“番”当为其氏)3种(其在原简中的写法也确实不同)。如果排除释读导致的差异,那么,这种现象只能是同一人名的不同写法。简46中的“碨”、简55中的“”、简64中“疋”也显然是同一人,其名却分别写作“碨”与“”。
在包山楚简中,此种现象相当普遍。简22、24、30所记,显然也是同一案件。在简22中,“受期”的司马之州加公作“李端”,里公作“随得”,受伤者作“陈”;而在简24中,则作“司马豫之州加公李逗,里公随得”,伤者作“陈”;在简30中,受期者作“司马之州加公李偳、里公随得”,伤者作“陈”。3支简的记录者均为“罗”。[16]18-19;[17]15-16“端”“逗”“偳”是司马之州加公之名的不同写法(“李”为其氏),“”“”“”是该案中伤者之名的3种不同写法。同样,邸昜(阳)君之州里公,在简27中写作“登(邓)婴”,而在简32中则被写作“登(邓)缨”(“登”为其氏);前一支简的记录者作“塙”,后一支简的记录者作“旦塙”,显然也是同一人。[16]18-19;[17]16
在里耶秦简中,“狐”是一个常见的名字,至少见有8位“狐”。(9)至少有8位“狐”: (1) “尉守”(简8-132+8-334); (2) 启陵“乡守“(简8-769); (3) “少内守”(简8-806,秦始皇三十四年九月); (4) 启陵“乡佐“(简8-1783+8-1852); (5) “库佐”(简9-89); (6) “仓守”(简9-356); (7) “史”(简9-482); (8) “田佐”(简9-1486),分别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第222页、第230页、第390页;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第113页、第141页、第317页。简9-356是一支残简,仅留有一行文字:
其时迁陵县的仓守与尉守均名“狐”。据简8-769,秦始皇三十五年八月三日(己未),启陵乡守“狐”向县廷户曹提交了一份报告,回复县廷要求取鲛鱼献之的命令,并亲自书写了这份文书(“狐手”)。[22]222据简9-202+9-3238载,“癸巳,仓守适、佐、稟人中出稟启陵乡狐正月、二月十三日食。”[21]87由于简8-58+8-770+8-1797见有“恬”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五月时见任启陵乡守,[22]42,223,392所以,“狐”任启陵乡守的时间,必包含秦始皇三十五年八月三日到三十六年二月这几个月之内。而在简8-205背,则见有“九月戊子,启陵乡守觚敢言”[22]113。九月在八月至次年二月之间(秦以十月为岁首),故简8-205背的“启陵乡守觚”,很可能就是简8-769与9-202+9-3238所见的“启陵乡守狐”。因为简8-1101中又见有“守觚出以稟发弩绎”[22]277,所以简8-205背的“觚”不会是一时的误写。“狐”与“觚”,很可能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八月至三十六年二月间担任启陵乡守的一个人名字的不同写法。
同一个人的名,可以写成不同的汉字,说明一个人的名字,被写成怎样的汉字,可能是由书写者在书写时决定的,被书写者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应当使用怎样的汉字,而只知其发音。包山楚简162、163、164、165是左尹“所(嘱)告于正娄”的诸种诉讼案件,其中简163见有“楚斨族伥动”。[16]29;[17]78“动”既属于“斨族”,则“斨”即为其氏;然简文又称其名为“伥动”,是以“伥”为其氏,故“伥”“斨”当为同一发音的不同写法。里耶秦简8-550:

浮,晳色,长六尺六寸。年卅岁。典和占。[22]178
丗二年六月乙巳朔壬申,都乡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产。典私占。[22]326
高里士伍“武”向里典“私”报告(“言”)自己的财产分割情况,“私”将之登记下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之名,都可能是“私”书写为特定的汉字的。在简8-1554中,秦始皇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己酉),“高里士伍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嚋、饶,大婢阑、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齿。典弘占”[22]356-357。“良”“完”“嚋”“饶”“阑”“愿”“多”等可能是“广”家奴婢之名,也可能是由里典“弘”写定的。而在里耶秦简9-2037+9-2059所记东成里户人士伍“夫”一家的名籍中,子小男子名“嘉”,妻(大女子)名“沙”,下妻曰“泥”,两个女儿(子,小女子)分别名“泽若”“伤”。[21]408使用特定的汉字以表明具体人的性别特征,应当也出自负责占籍的里典。前引里耶秦简8-550、9-757分别记录了“”“浮”与“产”的肤色(“晳”,“黑”),说明肤色乃是户籍登记时记录的内容。而“黑”也是常见的名字,某人之名被写成“黑”,或者亦因为其肤色较黑之故。(10)在里耶秦简中,至少有3位叫作“黑”的人: 一是□城县宗里人;二是襄县完里人簪褭,在迁陵县屯戍;三是迁陵县贰春乡的乡佐(秦始皇二十八年正月在任),四是迁陵县库的佐(秦始皇二十七年十二月在任)。因为前两位“黑”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故曰至少有3位叫作“黑”的人。分别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简8-871;第363页,简8-1574+8-1787;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34页,简9-22背;第36页,简9-23背。里耶秦简9-2552见有一位女子名“黑容”,显然是因其面黑而得名。[21]504睡虎地四号墓所出11号与6号木牍中所见的“黑夫”,肤色也应当比较黑。[28]629,637
除了里典,其他小吏也可能是庶人名的书写者。里耶秦简8-988:
迁陵狱佐士五(伍)朐忍成都谢,长七尺二寸,年廿八岁,白晳色。舍人令佐冣占。[22]257
“冣”是“谢”的舍人,他报告并登记了“谢”的身高、年龄与肤色,虽未必当着“谢”的面,但对“谢”是有充分了解的,“谢”的名也是由“冣”书写的。简8-217是迁陵县仓发放稟食的记录:

令史悍平。 六月食。感手。[22]116
产子□=子女婴曰女巳。令史华监。瘳手。[21]116
女婴“女巳”应当刚出生,需要向官府申报以领取稟食。令史“华”与“瘳”受理此事,“女巳”(以地支“巳”命名)之名,或者就是记录者“瘳”命名并书写的。
里耶秦简8-533是一份刑徒名册,其中见有“瘳”“齰”“欬”3人,均被罚作城旦。[22]1753人名所用的汉字,都与具体的身体特征有关联。“瘳”的本义是指病愈,“齰”的本义是咬舌,“欬”即咳。以这样的汉字书写人名,除了记录其发音之外,还应当与所记录者的身体状况有关系。
具有书写能力的人,当然自己书写己名。里耶秦简6-10:
简文中“自占”者名“黄亥”,应当是他自己申报并书写的。在简9-947中,“自占”人之名恰残缺,而他声明是“昭王卌二年产”。[21]228前引里耶秦简8-1555所记“援”的宦历,也当出自其自述;作为官佐,“援”当然会写自己的名字。睡虎地十一号墓地的主人名叫“喜”,他的两个弟弟分别叫“敢”和“遬”,3个子女分别叫“获”“恢”和“穿耳”,均见于“喜”编写的《编年记》(《叶书》)中,其所使用的汉字应当是“喜”确定并书写的。[29]13在喜墓所出的漆器的外底等处,见有针刻的“士五军”[30]27-28(M11∶19,M11∶9,M11∶18)、“安里皇”[30]30-31(M11∶1)、“大女子妴”[30]34(M11∶51,M11∶28,M11∶11)、“大女子臧”[30]122-132(M11∶29,M11∶35)等字样,很可能是这些器具的使用者或与其亲近的人刻下的,“军”“皇”“妴”“臧”应当是其使用者或其亲近者选择的文字。因此,秦简中所见的许多庶人名,应当是书手(里典、佐或史等)或当事人及其亲近者在登记户籍、制作籍帐、记录稟食发放情况时,根据其发音,并结合在现场所见当事人的身体特征,用自己认为适当的字写下来的;具有书写能力的当事人,当然会自己选择适当的字。
在大多数情况下,书吏或当事人应当会使用较为简单的一个字,记录一个人名字的发音。从书写简易的角度来说,无论一个人的名字在口语中发音如何,最好能用一个常见的汉字加以表达,所以,在人名书写系统中,单字名应当是一种原初的倾向。在同音字较多的情况下,采用哪一个汉字,则大抵取决于书写者的书写能力、情景判断或情感偏好和意义选择。前文所见人名用的汉字,大多比较常见,所用文字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意义,但也有些人名所用的汉字,可能具有特定的意义。(11)刘钊曾讨论人名音、义的问题,请参阅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在包山楚简中,地位较高的人名使用的汉字明显较为复杂,而且可能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如“集箸”所见的令“围”(彭氏),仹大令“悆”,新官帀(师)“瑗”,新官令“越”,大莫嚣“昜(阳)”(屈氏),漾陵大邑“”,大馹尹“帀”(师)、公“丁”,士帀(师)“墨”,可能是当事人自己或其家人选用的字;而地位较低的庶人,人名用字则较为随意,或者不具有特定意义,如同样见于“集箸简”的少僮“”“”(属于族),“衍”(瘳族),以及“喜”“庚”“”“”等,其人名用字则可能是负责登记(“箸”)的书吏(如司马“徒”)在登记时写定的。[16]17;[17]3(简2-13)但这种区分,并不是很明显,也难以确证。里耶秦简所见的人名,则很难辨析出存在类似的差别。
有的名字发音较为复杂,就写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从而形成双字名或多字名。包山楚简与里耶秦简中,皆见有一些庶人(包括地位较低的基层官吏)的名字,被写成双字(不包括姓、氏)。这些双字名的构成,有两种类型:
(一) 由单纯词构成的双字名
里耶秦简8-1069+8-1434+8-1520是秦始皇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迁陵库守“武”报告的“作徒簿”,有奖、庆、忌、、船、何、冣、交、颉、徐、娃、聚、窜、亥、罗等城旦、鬼薪、舂、隶臣,共15人。其中,只有“”是双字名。(12)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272—273页。简牍上的“”字二见,编校者认为其中的一个“”可能是衍文,或者是两个人同名“”。编校者将“”释为两个同名“”的人,而将“庆忌”释为一个人。今按:若以“庆忌”为人名,则“庆”当为氏称。在里耶秦简所记作徒簿中,除此例外,并无以“氏+名”指称徒隶者,故“庆”“忌”当是两个人的名。“庆”“忌”既为二人,则“”当为一个人的名。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常见以叠字称呼人名,然在简文中,却甚少见到,盖以书写简省之故。
在里耶秦简中,见有迁陵守丞“膻之”。据简8-75+8-166+8-485,秦始皇二十八年十二月癸末,迁陵守丞“膻之”为了涉及某些金钱的事情,致函本县少内;[22]55-56而在简8-60+8-656+8-665+8-748中,又见有秦始皇二十八年十二月戊寅,“迁陵丞膻”就冗佐、原籍在僰道西里的“亭”欠赀问题的报告,其中的“丞”当为“守丞”。(13)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同一件文书中另见有“迁陵丞昌”。据上引材料,知当时担任迁陵县丞的,确是“昌”,那么,“膻”的职务当是“守丞”。显然,“膻”和“膻之”就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在口语中,或者更近于“膻之”,但书写时,也可以只用“膻”一个字。所以,“膻之”与“膻”一样,都是单纯词。
里耶秦简8-823+8-1997是校长(低级军官)“予言”写给他的一位长辈“柏”的信,在信中,他自称“校长予言”。[22]233前引简8-149+8-489所见的“校长予言”,与这位写信的“校长予言”可能是同一人。里耶秦简中见有另几位名叫“言”的人:一位是迁陵“仓守”(14)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简8-898+8-972;第303页,简8-1268,秦始皇三十五年七月。,另一位是高里士伍“武”家里的大婢[22]326(简8-1443+8-1455),还有一位是迁陵县的令史(15)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页,简8-1560,秦始皇三十一年后九月。。显然,“言”也是一个常用名,“予言”的“予”字应当是语气词,这位校长名字的核心还是“言”,所以,“予言”也是单纯词。
前引里耶秦简8-138背+8-174背+8-522背+8-523背所载迁陵县负责“行庙”的令史中,见有一位“莫邪”。简8-647中另见有一位“莫邪”,是酉阳县的令佐;[22]189简9-23背又见有一位“莫邪”,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十一月迁陵县库中负责收发文件的小吏。[21]35-36他与简9-1408背和9-2288背中所见的“莫邪”当是同一个人。[21]301“莫邪”也当是一个双音节的单纯词。
里耶秦简中所见的“缭可”[22]149(简8-439+8-519+8-537)(右里人,士伍,秦始皇二十五年九月逃亡)、“免将”[22]219(简8-764)(巫县中陵里人,士伍,在迁陵县从役,秦始皇三十一年正月)、“渠良”[22]228(简8-793+8-1547)(巫县司空守,秦始皇三十一年四月在任)、“郀般”[22]316(简8-1364)(郫县小莫里人、士伍,在迁陵县从役,为尉史)、“可思”[22]327(简8-1444)(江陵慎里大女子)、“华”[22]335(简8-1470)(使治狱)、“良朱”[22]343(简8-1515背)(隶臣)、“玺余”[21]236(简9-986)(高里士伍“顺”的小妾)等双字人名,大抵都是由双音节的单纯词构成的。
以“不”“毋”“如”字为称的人名,如“不疑”[22]46(简8-61,8-293,8-2012)(书吏)、“不耆”[22]351(简8-1531)(隶徒)、 “不”[21]9-10(简9-2)(阳陵县仁阳里人,士伍,戍洞庭郡)、 “不识”[21]11-12(简9-3)(阳陵县下里人,士伍,戍洞庭郡)、“不仆”[21]26(简9-19)“不唯”[21]157(简9-567)(小女子,东成户人大夫寡“晏”之子)、“不害”[21]380(简9-1872)(迁陵少内守,秦始皇二十六年六月在任)、“不市”[21]400(简9-1969)(居债),“毋害”[22]114(简8-209)(男子)、“毋死”[21]1(简9-1)(阳陵县宜居里人,士伍,戍洞庭郡)、“毋择”[21]204(简9-778),“如意”(一位是迁陵县的书吏[22]362(简8-1565背),另一位是□阳县益里人,士伍[22]432(简8-2113)),也都是双音节的单纯词。值得注意的是,里耶秦简中见有两位“彼死”(一是酉阳县书吏[22]189(简8-647背),二是迁陵县令史[22]338(简8-1490+8-1518))。 “彼死”,或当作“不死”“弗死”解。同样,“去死”(涪陵县戏里士伍,在迁陵县作戍卒)也当看作为一个单纯词(而不当理解为动宾结构的复合词)。[22]276(简8-1094)简8-201见有酉阳县守丞“扶如”[22]112(简8-201),简8-2299+9-1882见有发弩守“相如”[21]384。“相如”意为“相同”;“扶如”之意,或当即“弗如”(不如)。凡此,都说明这些人名应当是根据其发音记录下来的。
(二) 由复合词构成的双字名
根据用作人名的复合词的构成方式,又可分为3种类型:
1. 偏正型,即由一个修饰或说明、限定性的词与一个主体词构成的人名,如 “敦狐”[21]260(简9-1112);[22]341(简8-1510背)(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间担任迁陵守丞)(16)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2018年版,第260页,简9-1112,秦始皇二十六年二月;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2012年版,第341页,简8-1510背,秦始皇二十七年三月。、“小欬”[21]23(简9-18)(阳陵县褆阳里士伍,在洞庭郡戍守)(17)简文又将他的名字简写作“欬”,显然,“小”是用于修饰“欬”的,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页,简9-7。、“央刍”[22]301(简8-1259)(官徒,分别受派负徒、徒养,一次病)、 “般刍”[22]385(简8-1743,8-2015)(官徒,私自为人佣),以及“皇楗”[22]144(简8-406)(男子,涉及刑狱)、“敝臣”[22]354-355(简8-1545)(孱陵县咸阴里士伍,在迁陵县屯戍)、“久铁”[21]201(简9-762)(巫县狼旁里人,士伍,在迁陵县屯戍)等人名中的“敦”“小”“央”“盘”“皇”“敝”“久”,是分别用来修饰“狐”“欬”“刍”“楗”“臣”与“铁”的。
2. 联合型,即由两个平等并列的词构成的人名。如戎夫、氐夫、夷吾、囚吾、越人、吴骚等(详见下文)。有些复合词构成的人名,是在特定语境下使用的。里耶秦简9-2344所记是迁陵田官守“武”上报县廷的爰书: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田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吾武自言:谒豤(垦)草田六亩武门外,能恒藉以为田。典缦占。
六月丁巳,田守武敢言之,上黔首豤(垦)草一牒。敢言之。衔手。
六月丁已日水十一刻刻下四,佐衔以来。□发。[21]477
高里士伍“武”又见于简8-1443+8-1455(已见前引)、8-1537,只是称其为“武”。在本件文书中,田守“武”、佐“衔”、里典“缦”等皆仅书单字名,唯有高里士伍“武”书为“吾武”,当是为与田守“武”相区分之故。
里耶秦简8-138背+8-174背+8-522背+8-523背所记“行庙”日程中,见有“史戎夫”(当为“令史戎夫”);在同一件文书中,另见有“令史夫”。(18)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第356页,简8-1551,见有“令史戎夫”,当与简8-138背+8-174背+8-522背+8-523背中所见的“史戎夫”是同一人。参与“行庙”的众吏,除“莫邪”“戎夫”2人外,均为单字名。“莫邪”乃双音节的单纯词,已见前;然则,“戎夫”之称,很可能是为与令史“夫”相区别,根据其身份特征而加上“戎”字的。“氐夫”是迁陵县贰春乡守(秦始皇三十一年前后)。(19)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简8-816,秦始皇三十一年三月;第312页,简8-1335,秦始皇三十一年四月;第358页,简8-1557,秦始皇三十一年四月;第364页,简8-1576,秦始皇三十一年三月;第366页,简8-1595;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页,简9-761。在此前后,启陵乡(迁陵县的另一个乡)的守也叫“夫”(“夫”是很常见的人名)。(20)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简8-157,秦始皇三十二年正月;第327页,简8-1445,秦始皇三十二年。贰春乡守“氐夫”,可能也是为了与启陵乡的乡守“夫”相区别,特别加上“氐”字。因此,“戎”与“氐”,当是在同时存在同名“夫”之人的情况下,为表示区别,而加上的。
里耶秦简中又见有3位“囚吾”:一是田佐[22]368(简8-1610),二是校长[22]101(简8-167+8-194+8-472+8-1011),三是发弩[22]390(简8-1783+8-1852)(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在任)。简8-136背+8-144背则见有一位小史,名叫“夷吾”,负责传送文书。[22]76“吾”也是常见人名。在里耶秦简中,至少见有3位“吾”(一是贰春乡守[22]291(简8-1207+8-1255+8-1323),二是贰春乡佐[22]312(简8-1335),三是书手[21]108(简9-328))。因此,“囚”与“夷”很可能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吾”而加上的,用以表示其身份。
“乾人”“它人”“越人”“程人”“滑人”作为人名,构词方式与“戎夫”“氐夫”“囚吾”“夷吾”的构词方式,应当是一致的,“乾”“它”“越”“程”“滑”都是用于说明“人”的来源或属性的,只是其使用语境有所不同。“乾人”在里耶秦简中两见: 一次是官徒,被分配去“负土”[22]225(简8-780);另一次是小城旦,被分配到贰春乡捕鸟及羽[22]343(简8-1515)。称为“它人”的,也有两位:一位是“隶徒”,被分配从事一种编织工作(“级”);另一位是“佐”,与3个隶徒一起运输粟。(21)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1页,简8-1531;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简9-53。两处所见的“它人”应当不是同一个人。“越人”虽两见,但大约为同一个人,是阳陵县逆都里的士伍,在洞庭郡戍守。[21]16(简9-8),246(简9-1044)“程人”见于简9-31背,身份是士伍。[21]44“滑人”见于简8-48与简9-33,身份是隶臣。[22]40;[21]46这几个以“人”为称的人,除“越人”外,身份都比较低,基本上是官徒,很可能并非其原名,只是在登记作徒簿时,根据其来源地,将其登记为“某人”——“乾”“它”“程”“滑”,应当都是地名。“越人”来自阳陵,盖在阳陵,来自越地的人甚少,故以“越人”称呼这位士伍,其意亦为“来自越地的人”。
3. 补充型,即由一个主词和一个补充性的词构成的人名,如“李季”[22]113(简8-206)、“毛季”[22]126(简8-272)、“兰叔”[21]262-263(简9-1117+9-1194)、“孟妪”[21]203(简9-768)等,其中“季”“叔”“妪”乃是对“毛”“李”“兰”“孟”的补充。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木牍“奠仪名单”所见的“载翁仲”“庄伯”“王翁季”“胡兄”“姚季”“张母”等人名(已见前文),其构词方式也均为补充说明型。里耶秦简8-659+8-2088是“赣”致“芒季”的信:
简8-1817见有“私进令史芒季自发”,[22]395说明“芒季”当是正式人名。而简8-477见有“臞季”[22]162,简8-1065又见有“忘季”[22]272,以及前文已及之“毛季”“李季”等,说明“季”非特定人名。在“赣”的信中,“季”与“柏(伯)”并列,显系行第,当是以行第之称为名,则“季”是对“芒”的补充性说明(意为“芒”家之“季”)。
无论是偏正型、联合型,还是补充型,复合词构成的双字(或多字)人名一般由限定或说明性语素和主体语素构成,具有特定的内涵与意义。在偏正型复合词构成的人名中,限定或说明性语素多为形容词(如“敦”“小”“央”),用于描述、说明主体语素的特征;在补充型复合词构成的人名中,说明性语素多置于主体语素之后,用于说明主体语素的地位属性;而在联合型复合词构成的人名中,限定性或说明性语素多为名词,与主体语素之间是平等、并列的关系,用于说明主体语素的身份、居地、来源、族属等,当说明性语素固定下来,成为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人群共同的说明性语素,实际上就成为“姓(氏)。
三、 庶人称氏及庶人“姓名”之成立
“氏(姓)+名”的称名方式,属于联合型复合词汇,前一个语素“氏(姓)”与后一个语素“名”在结构上是并列平等的关系,但又有某些限定或说明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盖源于单称其名不足以确切指明特定的人,故以其所属之氏(族)或“姓”加以“名”之前, “氏(姓)”具有说明、限定“名”的作用。在前引里耶秦简9-2344中,因为田守与高里士伍均名为“武”,故田守“武”在其报告中特别将高里士伍“武”称为“吾武”,即是典型的例证。而前文所举的“戎夫”“氐夫”“囚吾”“夷吾”的称名,则并不局限于特定的语境,只是“戎”“氐”“囚”“夷”之称,尚未被“夫”“吾”的后人却继承。而在前引南阳里户籍简中,户人“蛮强”“蛮喜”的子女,均可得称为“蛮某”,故“蛮”实已成为氏(姓)称。需要指出的是,“戎”“氐”“蛮”“夷”“囚”,应当主要是“他者”(特别是官吏)从外部给予当事人的指称和身份界定,并非当事人的自称;其成为氏(姓)称,也是由外部给予的,所以,很可能因为得不到当事者后人的认可,而不能稳固地沿用。
以其职业、身份(包括族群身份)指称庶人,并将之作为庶人的氏(姓),在包山楚简中即颇有所见。前引包山楚简46、52、55、64所见的“越异之大帀(师)”“儥”被称为“越儥”,其“越”字(当为其氏)当来自“越异”。越异之司败与大师并非庶人,然其氏称仍或是来自外部的他称。包山楚简80:

以来源地作为庶人的属性并进而成为其氏称,在战国时或即颇为盛行。前引包山楚简85中所见诸人之氏称,有沈、黄、陈、登(邓)、番、郑、宋、周等,多为楚国境内或相邻区域的古国名。在“集箸言”中,五帀(师)宵倌之司败“若”报告视日说:邵行之大夫“盘”今无故而“执仆之倌登、登期、登仆、登臧”。在另一个案子里,“蔡遗受铸剑之官宋强,宋强法(废)其官事,命受正以出之”[16]17-18(简14,15,16,17,18);[17]11。“五帀(师)宵倌”与“铸剑之官”皆当是官营的手工业作坊。五师宵倌的“倌人”均以“登(邓)”为氏,很可能本是邓人,或来自古邓国(在今襄阳北邓城遗址);而铸剑之官“宋强”则或出自宋国,“蔡遗”则可能出自蔡国。“案卷”简中有一个复杂的案子,诉讼的一方是秦竞夫人之人“舒”氏一家(“庆”,庆父“”,庆兄“”“”,以及舒”“舒”),另一方是阴人“苛冒”“(桓)卯”“(桓)”,相关的证人则有陈、陈旦、陈越、陈、陈宠(陈龙)、陈无正、陈、连利等,都是阴人。[16]26-27(简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7]54-55此案显然发生在阴地。舒氏当是外来移民,简文特别指明其“坦凥阴侯之东之里”,很可能来自“群舒”(原居于淮水中游两岸,为楚所灭);(桓)氏则可能是阴地土著;诸陈被认为是阴人,当已久居阴地,也可能本来自陈国(原在淮水流域,为楚所灭)。在简82中,“舒快讼郘坚、郘、郘怿、郘寿、郘卒、郘,以其不分田之古(故)”[16]22;[17]37。诸郘(吕)可能是当地土著,而舒快或为后者之移民,故要求诸郘分田。“郘(吕)”氏或源自吕国(在南阳盆地,春秋时其故地入楚,东迁淮水流域,复入于楚)。包山楚简145载:
“绅朝”等入楚为“客”,地位并不低,其中,登(邓)余善、陈慎在其居郾(燕)、秦时即各以“登(邓)”“陈”为氏(“绅朝”之氏,或即“申”),而“魏奋”的氏“魏”,则很可能是在入楚之后方因身为魏客而以“魏”为氏。公孙哀、鼙喿虽同为魏客,各以其身份(“公孙”“鼙”)为氏;越客前、左尹也各以其身份冠于名前(“前”“左尹”皆当是官位身份),说明魏奋在魏国时或者并无特别身份,故入楚后不得不以“魏”为其氏称。据此推论,当楚国灭亡邓、吕、陈、蔡、黄、舒诸国之后,诸国之民(非诸国公族,庶人)渐散处于楚境各地,乃以其故国之名为氏,以与当地固有之楚人相区分。楚地庶人之称氏,或即源于此。
郑樵论姓氏之起源,谓“有封土者,以封土命氏;无封土者,以地居命氏。盖不得受氏之人,或有善恶显著,族类繁盛,故因其所居之所而呼之,则为命氏焉”[1]3。实际上,其所举“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也都是“以地为氏”。而在“以族为氏”下则说:“姓之为氏,与地之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赐者为姓,不得赐者为地。”[1]4因此,“以地为氏”,乃是最重要的姓氏来源,大部分姓氏均可能来源于居地或与居地有关。问题在于,何以要“以地为氏”?郑樵在《通志二十略》卷1《氏族略·氏族序》中曾谈道:“居傅岩者为傅氏,徙嵇山者为嵇氏,主东蒙之祀则为蒙氏,守桥山之冢则为桥氏”[1]3;而“隐逸之人,高傲林薮,居于禄里者,呼之为禄里氏,居于绮里者,呼之为绮里氏,所以为美也。优倡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为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为社北氏,所以为贱也。又如介之推、烛之武未必亡氏,由国人所取信也,故特标其地以异于众”[1]3-4。可见,“以地为氏”,无论是自命,还是他称,都是为了“标其地以异于众”,即以其居地或来源地作为自身人群的标识,以区别于周围的其他人群。战国时期楚国境内本属于其他古国古族,其故国为楚所灭,自身被强制迁移到新地的庶人,或者来源于楚国周边地区、因不同原因进入楚国的庶人,为表示其非楚国本地之人,乃以其故国或来源地为氏,以区别于新居地的其他人(特别是楚人)。
在前引里耶秦简中,“乾人”“它人”“越人”“程人”“滑人”“巍(魏)婴姽”“吴骚”等,基本上均可判定其已离开故土,故特别以其故土之地为称,以明其来源或地域属性。里耶户籍中所见的“蛮强”“蛮喜”,“受令简”中所见的“蛮孔”,已入籍成为户人,显然早已脱离“蛮”区,盖离开蛮区之后,方被称为“蛮”,并以“蛮”命氏。同理,里耶户籍简中所见的“黄得”“黄□”“彭奄”“宋午”,“受令简”中所见的“吕柏”“唐頪”“朱发”“周柳”“相赫”“远禾”等(均已见前),也很可能是以其故属之国或故土之地作为其氏。
在里耶“受令简”中,大都使用“氏+名”的方式指称受令之人,其所受之令,当是从事转输之类徭役。里耶秦简9-1667:
大女二人。
不更舆里□豕。
□大女三人。
小女二人
……繇(徭)□七日……[21]350
“豕”前所缺之字,也当是氏称。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律令》(一)录“徭律”规定:“岁兴(徭)徒,人为三尺券一,书其厚焉。节(即)发(徭),乡啬夫必身与典以券行之。田时先行富有贤人,以闲时行贫者。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而署其都发及县请。其当行而病及不存,署于券,后有(徭)而聂(蹑)行之。”(22)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150页,简1241、简1242、简1363、简1386。“书其厚焉”之“厚”,整理者引《韩非子·有度》“毁国之厚以利其家”,释为“财物”,似不妥恰。此处的“厚”当解作“重”,乃是指主要的事项。“署其都发及县请”,整理者将“都”释为“都官”,或可从;“县请”之“请”,认为是通“情”,则难以信从。盖“县请”相当于睡虎地秦简所见的“邑中之功”,就是县中征发的徭役;而“都发”就相当于“御中之征”,也就是朝廷征发的徭役。前引里耶秦简9-1667、9-1707或者就是此类征发徭役的券。然则,征发徭役的券中,是要写明应征人的氏(姓)与名的。换言之,一个人如果离开家乡外出从役,即需使用“氏+名”的称名方式。在前引里耶秦简8-1555中,“援”受命带领县库的6名吏员,“为县买工用,端月行”,故简文特别写明其“族王氏”。前文所见更戍卒“贺”“产”,或者亦因为从城父县来到迁陵县更戍,才特别写明其族属(即氏称)。
然而,里耶秦简所见的大部分更戍卒,虽然来自外地,却并未写明其氏(姓)称,即使在正式的官方文书中,也仍然使用单名。盖更戍、转输,仍多以所在县为单位(23)秦军的编制,按照《商君书·境内》的说法,是以五人为一伍(或“屯”),百人置一将。百人之将(百人队)乃是秦军最基本的编制单位。一个百人队的士卒,基本上来自同一个地方。里耶秦简9-1114所记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十一月鄢将奔命尉“沮”与迁陵县贰春乡乡守“后”交涉的文书。“沮”是鄢县的尉,他率领一支由本县壮丁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将奔命”)经过迁陵县,有部分士兵因伤病,不得不留在迁陵县治疗,“沮”将他们的情况登记在“牒”上,移交给迁陵县贰春乡,请给予口粮,病愈后即让他们归队,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页。简9-452所记应当与此相同时。另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丹阳将奔命”,在丹阳县尉“虞”的率领下,经过迁陵县,要求迁陵县供应“丹阳将奔命吏卒”的稟食。这份文书由丹阳县□里的士伍“向”送达迁陵县,显然,这一支部队是由丹阳县的子弟兵编成的。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故士卒、役徒仍大都在“熟人社会”里活动并得到界定,并无须特别指明其来源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所出C类竹简所记,应当是市阳里受征前往“仓”从役的记录:
市阳,两户遣一人繇仓,书。/郭、乙二户,儋行,少一日。/寇、都二户,兼行,少一日。/好、昆论二户,善行,少一日。/越人、□二户,唐行,少一日。/上官巴人、圣二户,□,养餑,少一日。/□、贞二户……/安国、晨二户,赤行。/终(?)古、斯二户,□己行。/臣、□二户,□行。/首(?)、右车二户,士子行。/□徒、宫二户, 如行。/任、但二户,造行。/莫、□□二户,泽。/儋、宇(?)二户,庳。/状(?)、小奴,□树行。成。/平,中章。见。/[27]116-120
据简文首行,市阳里每两户要遣一人到“仓”中服徭(繇)役,则第二至第十五行“二户”之前所记,即分别为户名,“郭”“乙”“寇”“都”等,大抵皆为姓氏之称(有的也可能是名);而“儋”“兼”“善”“唐”等人,则当是受遣前往“仓”服役之人。在这份文书中,虽然“儋”“兼”等人是到“仓”中服役,然仍以“市阳里”为其服役单位,故简文但书其名,而不著其姓氏(“儋”“兼”等人当有其姓氏)。同样,在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所出B类简中,计“算”的户人多以姓名相称,如邓得、任甲、宋则,而受遣的男女则仅称其名,如“男野人、女惠”(简35,已见前文)。同墓所出A类竹简(郑里廩籍)虽然是发放廩、种的官方文书(同墓所出C类竹简也是官方文书),但所记限于同里(郑里)户人,故也无须指明各户人的姓氏。而同墓所出的“中服共侍约”,则写明“中服”(参加“服”)诸人的姓氏,却未著其名,但以“张伯”“□兄”“□仲”“陈伯”为称。[27]94-96服长张伯,即十号墓的墓主张偃。张偃等人所“中”之“服”,无论其功能若何,都是一种民间共同体性质的组织,“中服”者相互熟悉,彼此尊重,故“服约”但以其“姓氏+行辈”为称,而不称其名,以示尊敬。显然,采用怎样的称名方式,与不同的语境有着密切关联。
四、 庶人“名”与“姓名”的文字书写及其意义
“人之有名,以相纪别。”[32]1 160在较小的家庭范围内,人们用亲属关系区分不同的个体,所以,亲属称谓可能是最基本的人名来源;当家庭规模扩大、家族亲属关系较为复杂,特别是同辈同性别人数较多时,人们就需要使用特定的称谓,以指称个体的人,这就是“名”;当人们走出家庭或家族、在家庭或家族之间交往时,就可能需要分别同一“名”的个体所来自的不同家庭或家族,会在其“名”前冠以其母亲或父亲的“名”,或者其家庭、家族所在的地点或标志。人们逐步确立了某些规则,用同一原则指称来自不同家庭或家族的同名和相同行第的个体,并将之固定下来,这就是口头传统中的“姓”,亦即“姓(氏)”的本源。简言之,在口语系统中,是先有“名”,后有“姓(氏)”。
可是,在文字表述系统中,“姓(氏)”与“名”的使用先后,可能正与此相反。文字表述系统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标识系统,其标识规则在于首先区分人群,然后再区分个体的人。一个血缘或地缘性的人群是“族”,用于标识“族”的文字符号便是“姓”或“氏”。郑玄谓:“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代,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24)《史记》卷1《五帝本纪》“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句下“索隐”引郑玄《驳许慎五经异义》,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所谓“赐姓命氏”,本质上就是以包括文字形式在内的符号标识不同的人群及其组织。在姓、氏相同的情况下,则需要标识其首领(酋长、祭司)的“名”(也可能发展为“氏”)。因此,在文字表述系统中,是先著明“姓”(或“氏”),然后才会标明其首领之名。在古代社会中,无论是血缘人群、组织,还是地缘人群、组织,其普通成员,在文字表述系统里并不需要“名”,也不会书写其名。在这种以血缘、地缘人群组织为基本单位的古代社会解体之后,原来属于血缘、地缘人群组织的个体(个人与家庭)才成为新型“国家”的“庶民”和“编户”,由于需要“直接”面对“国家”,而不能再通过血缘、地缘人群组织人群作为中介,他才需要一个用文字表达的自己的“名”。用文字书写的人名是用于标识、分别不同个体的人的符号,庶人平民拥有这样的文字符号,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是可以直接面对“国家”的、相对自主的个体。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只有在春秋战国以后,庶人在文字表述系统中才逐步拥有书写成文的“名”,而且在“名”不足以标识具体之人的情形下,复在“名”之前冠以姓、氏,使用“姓名”的方式,指称个体及其家户。
普通民众如何得到用文字书写的自己的名字?在由两个或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情况下,其名字用怎样的文字表示以及表现为怎样的结构?不仅关涉以汉字书写为中心的华夏文化传统如何进入广大乡村地区的问题(即所谓“文字下乡”问题),还关涉“华夏文化”如何向新拓展区域扩散、渗透并扎根的问题(即所谓“华夏化”问题)。杜正胜率先将庶人姓氏之使用及其普遍化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编户化进程联系起来,认为姓本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是统治者特殊身份的表征,平民本无姓氏可言,姓“是随着编户齐民的出现才逐渐普遍化的”。[33]188-196魏斌曾主要利用长沙走马楼所出三国吴简材料,讨论其所见吏民姓氏的构成、汉姓与蛮姓的辨别、编户化进程与汉式姓名的推广,关注点在于姓氏所反映的族群类别、蛮民所用汉名姓氏的来源、编户蛮民与汉人移民的关系以及地方豪族的成长等问题。[34]23-45在《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一文中,魏斌进一步讨论走马楼吴简所见吏民的名字均为整齐的单名(指“姓”以外的“名”)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认为这一现象应是东汉时期长沙等郡大规模编户化过程中新附人口户籍登录整齐化的结果,而其背后则是华夏文化对南方社会的持续影响。[35]魏斌的研究抓住了“编户化”与“华夏化”两条主线索,认为南方地区土著人群使用汉字姓名乃是秦、汉、吴等政权推行编户制度的结果,而其使用怎样的汉字姓名,则主要反映了其“华夏化”的进程。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讨论庶人之名的文字书写、庶人使用姓氏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和意义。本文的研究更有力地表明,著籍(编户化)乃是庶人(平民)称名书面化最重要的途径。前引包山楚简所见的“玉府之典”“溺典”“陈豫之典”皆为特殊功用的户口籍帐,居于路区湶邑、属于“族”的“”“”,居于郢里的“喜”之子“庚”,(处)于(国)之少桃邑的瘳(廖)族“衍”,分别被登记在人的“玉府之典”、的“陈豫之典”与“臧王之墨”的“溺典”上,、、衍、庚等人之名是在著籍时被写成特定的文字而成为文字名的。同样,前引里耶秦简8-550所见的“浮”与“”,9-2295所见的贰春乡东成里户人、士伍“夫”一家(妻“沙”、下妻“泥”,子“泽若”“伤”“嘉”),简6-10所见的“黄亥”等,都是在著籍时拥有其文字书写之名的。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所出D类竹简则可能就是造籍时用于登记个人的名籍简(已见前文),其上登录的人名,很可能就是其当事人名原初的书写方式。
徒簿、作徒簿(或徒作簿)是记录刑徒、隶臣妾劳作的文书,也可以看作为一种籍帐。前引简9-2289背称:“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圂敢言之:写上,敢言之。痤手。”[21]458里耶秦简所见的大部分类似的徒簿、作徒簿,均注明为“写上”(誊录如上),说明其籍簿是抄录而来。盖县司空在接收隶臣妾时,即有一种徒簿,司空守“圂”所上的徒作簿即是“痤”据已有的徒簿抄录整理而成。简8-533可能就是一份移交到迁陵县来的刑徒名单。简牍分上下两栏,上栏五行,下栏两行:
戌,有罪,为鬼薪。/齰,城旦。/赢,城旦。/欬,城旦。/瘳,城旦。/滕,司寇。/懀,司寇。[22]175
如上所述,“齰”“欬”“瘳”3人之名皆暗示其身体特征,应当是在3人被罚为刑徒之后,才被书写为“齰”“欬”“瘳”3字的。换言之,徒、隶之名,可能在编制徒簿时写定或改写的。而徒、隶本身自亦有其籍。里耶秦简8-18是一支断简,仅写有“隶臣赤”3字;8-119仅见有“城旦修”。[22]32,66;[36]16,28这两支简,很可能就是隶臣“赤”、城旦“修”的名籍简。简8-48右上方写有“隶臣滑人”4字,左下方署“感手”;简8-261右上方写有“妾宛”,左下方署“感手”。[16]40,124;[36]19,53这两支简,则应当是隶臣“滑人”、隶妾“宛”被送到迁陵县后,由迁陵司空官的史“感”另外签发的。在这一过程中,徒隶人名的具体用字也可能发生改变。
显然,在编户著籍之外,庶人还有诸多方式,获得其文字化的人名。徒隶之名在被“写”入徒簿(作徒簿、徒作簿)之前,很可能出现在不同类型的司法文书中。包山楚简的“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案卷”等,都是司法文书,其中所见的诸多庶人名,很可能是首次被写成文字出现在官方文书中。在前引包山楚简80中,少臧之州人冶士“石佢”控告其同州、同为冶士的“石”杀伤了其弟“石耴”,3人之姓名因此而被写成文字,记录在文书中。在包山楚简83中,罗之壦里人“湘”讼罗之庑(国)之者、邑人“郥女”,谓“郥女”杀嗌昜(阳)公“会”之妾“叴与”。[16]22;[17]37“湘”是壦里人,“郥女”庑(国)之者、邑人,在此前当已著籍,或列名于某“典”中,然“会”妾“叴与”似并不在典中。前引包山楚简7、8、9说“喜”之子“庚”已由司马“徒”登记在籍(“箸之”),而“庚”之子“”与“”之子“”本不在“典”上,因为此次“集箸”,方被检查出来;然后,当庭记录下来,列入“典”中(“廷等〔志〕),所以内〔纳〕”)。那么,“”“”是先在司法文书中得到书写,然后才被登录到户口籍帐中的。

齐国的陶工将名字印、刻在自己制作的区、豆等标准量器上,以示负责,也具有法律意义。《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孙希旦解释说:“勒,刻也。器之功致与否,一时未能遽辨,必用之而后见,故刻工名于物,于其既用而考之,则其诚伪莫能逃矣”。[37]489-490是在器物上铭刻工匠之名,意在表明其对于器物之质量、标准负有责任。侯旭东说:“人‘名’出现在器物上主要意味着‘责任’,而不是‘拥有’。”[38]所论颇为中的。据此反推,“九年卫鼎”“散氏盘”铭文与“秦封宗邑瓦书”中特别写明相关众“小子”“臣”及“众人”之名,也是为了表明其对于土地疆界之划分与标识负有责任。
因此,庶人(“贱者”)人名之被书写为文字,较早应当是由于其参与“贵者”或“国家”的有关事务并被要求负有责任,故一般在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中被记录下来。法律文书对于庶人名的记载虽然并不普遍,却早于编户化进程中户口赋役籍帐文书对于庶人名的记载。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律文书的适用与有效范围一般均超越当事人所生活、活动的人群或地缘单位,故而需要标识其所属的人群或地缘单位,亦即其氏(族,或姓)。换言之,庶人文字化的人名使用“氏(姓)+名”的方式,盖源于在诉讼事务与法律文书中需要指明当事人之所属、居地与来源。
在前引里耶户籍简以及凤凰山所出“郑里廩籍”等户口赋役文书中,很多户人并未使用“姓氏+名”的称名方式,而是直称其名,并不标明其姓氏。在凤凰山十号汉墓所出C类竹简所记市阳里行徭册中,行徭户名或用姓氏称,而受遣前往“仓”中行徭的人则只称其名(已见前文)。显然,参与行徭的家户及记录者皆明知受遣行徭人的姓氏,故简文略而不书。“郑里廩籍”所记34位户人,多无姓氏。杜正胜说:“有姓无姓并存,应当是姓氏普及化前期的自然现象”;而“因为户籍系于县里行政系统,汉代的籍贯绝不能省略里,里贯既明,政府对于有名无姓的庶民仍能有效地控制”。[33]194所以,著籍并不必然要写明其姓氏,编户化也并不必然带来姓氏的普遍化。

然则,盖楚法要求明确当事人之“居处名族”,故楚人多言其名与族(姓、氏);而秦律要求“定名事里”,故秦人多只称名。秦并楚地,以秦律为主,然仍得杂用楚人惯习,称楚地之人,或仍用楚法,兼称其名族(姓+名),抑或以秦律,单称其名。入汉以后,则渐用楚俗,姓名之称,乃渐次普遍。故从本源而论,庶人使用姓名,当来自楚国、楚地与楚人。
可是,如前所述,楚法之所以要求载明涉事人之“居处名族”,正是因为其境内人民来源多样,“族”属复杂,且迁民既已离其故乡、与楚地土著及来自他处之人共居,故以其来源地冠于“名”之前,亦易于标识。前引里耶秦简9-1667、9-1707及“受令简”等材料也表明,人们在离开其原居地、前往外地“更戍”“转输”时,更需要标明其居地名族。因此,离开故乡,脱离其固有的血缘或地缘人群组织,很可能才是庶人称名普遍使用姓氏的主要原因。居延汉简所见的士卒名籍,皆普遍记录士卒的姓名,盖正是因为他们均离乡远戍之故。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有机会与日本东京大学窪添庆文、佐川英治、小寺敦,以及中央大学阿部幸信、学习院大学庄卓麟等先生讨论,得到诸多帮助和建议。匿名评审专家也给予了很好的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