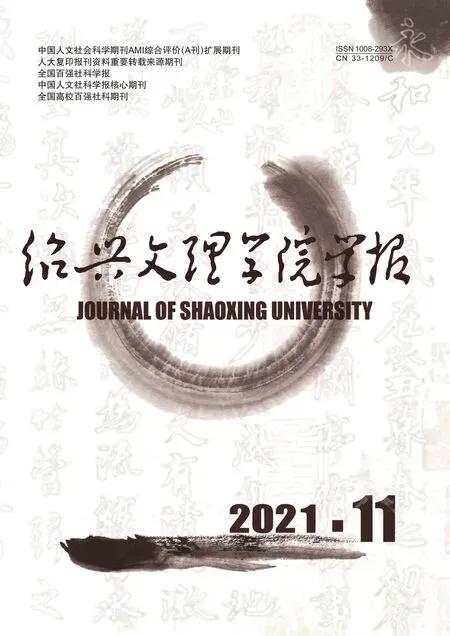苏轼望湖楼前忠君儒礼的隐性书写
何湘君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梧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入选教育部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在一些教学活动中,教师通常会带领学生围绕诗人笔下的景物描写、意象组合开展审美与鉴赏。从忠实于自然形象的描写着手解读,关注夏雨前后历历如画的奇特景象,这种聚焦于古诗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开发小学生的直觉思维、形象思维和培养想象力。不过,这种失去外部文化关联的文本分析仅仅针对写景诗才有效,但该诗并非纯粹的写景诗。按照叶燮“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1]的主张,联系苏轼在京城参与社会实践改革的经历,从“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艺术包蕴中,景语之外还应包含象外情、情中理的成分。
一、寄寓醉书的感慨抒怀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组诗一共五首。苏轼题名“醉书”,但组诗绝非在饮酒过量、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写成。恰恰相反,此时苏轼非常清醒,在酒入愁肠之后,借题发挥来回应不久前经历的人生第一场政治风波。
宋英宗三年(1066),苏轼的父亲苏洵病逝。前一年,苏轼年仅二十六岁的妻子病故。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辞去官职,将父亲的灵柩运回四川眉州,在老家祖茔埋葬。居丧服满后,苏轼兄弟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重返汴京,准备接受朝廷任命。
苏轼兄弟返京之年,宋王朝正经历一场浩大的社会变革。宋神宗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开创的新法就此开始实施。新法希望通过更易法制,来摆脱财政上入不敷出、军事上被动挨打的局面,最终达到富国强兵、国泰民康的目的。新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针对财政方面的改革,包括青苗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二是针对国防方面的改革,包括保马法、保甲法、将兵法、减兵并营等改革措施。新法推行的出发点是护国安邦扶社稷,不过,由于政见不同,朝廷内部出现分化,新政推出不久即遭遇很大阻力,很快形成势不两立的新旧两党。主张改革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相互对峙,一场始于志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实思考最终变成尖锐的政治斗争。一时间两派异议,朝野喧嚣。
当权派与反对派各自为阵。当权派以王安石为首,背后有宋神宗支持,另外还包括曾布、吕惠卿、李定、邓绾、舒亶、王雱、谢景温、蔡卞、章惇、吕嘉问等人。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还有韩琦、欧阳修、富弼、吕晦、曾公亮、赵抃、张方平、范镇、文彦博等人。苏轼站在反对新法的一方,直接原因来自王安石的排挤。
王安石对苏轼的排挤从苏氏兄弟还朝之时便出现了。案苏辙写给亡兄的墓志铭“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2],《宋史·苏轼传》“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3]。在官告院任职是一个闲差,这是王安石在执政期间,不满苏轼议论异己的行为,特意给苏轼安排的岗位。
宋神宗惜才。尽管他赏识苏轼,想要起用苏轼修中书条例,但被王安石拒绝。《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4]69。神宗识才爱才,后来干脆拿着苏轼的对策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也不认同,说“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4]117-118。
苏轼天性耿介正直,刚直不屈,逢人不会阿谀谄媚,“多士方哗,而我独南”[5]1956。为官不久位势未显之时,面对压力却敢于抗击,对于王安石的排挤,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从正面予以直接回击。
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新学。新学史称三经新义,在王安石领导下,由经义局对《诗》《书》《礼》进行重新阐释,以此作为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和科举考试的答案。在苏轼看来,学派、理论、观点之间既有差异,也有联系,相反相成、互相吸收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因此,对王安石树一家之说的做法非常不满。“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唯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5]1427
苏轼不认同王安石潜心研究的字源学。字源学应强调科学分析,分析应有充分的文献证据。清儒朴学在这方面钻研很深,采用无证不信的治学方法,追溯汉字从甲骨文到当下的演变,总结出汉字的一般性规律。王安石醉心于独创的字源学,他的字源分析却只依据汉字结构,分析时掺入主观猜测,字源分析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穿凿附会和纵情发挥的想象。研究方法一旦错了,移其心力地苦研解字只会导致错误增多。苏轼不认同这样的做法,据传苏轼曾戏谑王安石的解字,王安石认为“波”字是“水之皮”,苏轼回应,“‘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6]84。
对于新法,苏轼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直陈反对意见。苏轼认为变法要讲究理据,不能随意而为,“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5]303。对于变法的核心内容,苏轼批评变法者没有经过严格论证就草率实施,“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5]304。变法初期最坚实的支持力量来自宋神宗,尽管针对皇上,苏轼也毫不含糊,直言不隐,说神宗义利不分。“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5]303对于两党在朝廷引起不和,苏轼认为不能采取压制策略,“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5]305。
御史是代表新旧两派发言的重要人物,对新法能否顺利实施的影响很大。御史们有支持变革者,也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命运各不相同。察纳忠言者谓之谗慝,他们或遭贬谪或受到降职或选择罢官、隐居,如孙觉、吕公著、程颢等人;谄附者谓之忠良,他们则大都继续留在京城或得到提拔,如李定、谢景温等人。对此,苏轼在给神宗皇帝的奏言中也表现出深情隐忧,提醒神宗不能“有心者怒,有口者谤”。
其实,苏轼并非完全反对变革。曾在宋仁宗时期,他就提出改革主张,有拯救“骎骎乎将入深渊”的北宋王朝的决心。神宗变法,他也表示支持,但提醒要把握改革时机,“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5]304。遗憾的是,他将“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变成了大胆批驳,言辞非常激烈,甚至责难。“新党小生”“怀诈挟术”“小人招权”这些用词都是苏轼针对当权派人事自由放达的斥责。苏轼个性正直,常常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5]363。面对复杂的变法斗争,初入仕途的苏轼显然经验欠缺,准备不足,引来政敌对他的迫害。
熙宁三年(1070)八月,新党御史谢景温控告苏轼曾违法贩卖私盐,低买高卖,从中牟利;并且还假称朝廷差遣,向沿途地方借用兵卒。宋神宗下诏沿路展开调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所历州县”[4]67。虽然最终结果查无所获,但神宗对苏轼的印象已不如以前。“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4]67在此情况下,苏轼只好主动请求外任。次年六月,被任命为杭州通判。
熙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1072),苏轼登上杭州望湖楼,看到雨前、雨中和雨后的不同景色,联想到家庭的悲欢离合、官场的冷暖沉浮、国家的荣辱兴衰,惝恍失意的苏轼饮酒浇愁,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二、反常合道的心象融合
卷入政治风波的苏轼生发惝恍之情,他借用文学创作来进行心理调适。
苏轼精通画理,作诗如同泼墨作画。初读组诗(其一),第一印象感觉作者是一名技法高超的风景画家,在俯仰天地、登临远眺之际,就将黑云压城的紧迫、横风吹雨的急促、雨过潮平的宁静等诸多形象,在作者随景移步之时一一勾勒出来。苏轼曾经评论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能以这种发现的眼光评论前人的作品,在创作中,遇到同类题材不免也会走入“诗中有画”的意境。“黑”“白”“乌”“青”“绿”不正是苏轼在给云、雨、菱、芡、菰等日常物象随类敷彩、勾皴点染而成的吗?其一中的黑云不言自明,小学生的生活经验都能涵盖。白雨是什么呢?白雨是指在白天下的暴雨。案李白《宿鰕湖》“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将白雨比喻成银竹,说明雨大势疾。诗中前一句“暝投鰕湖宿”中已经交代时间为日落时分,可知“白雨”即为白天的暴雨。此外,再结合白居易《游悟真寺》“赤日间白雨”和陆游《大雨中作》的题目和内中诗句“贪看白雨掠地风,飘洒不知衣尽湿”便可印证白雨即白天的暴雨。
针对寻常之物仅仅采取泼墨着色,这不足以产生鲜活的艺术形象,苏轼反常合道的诗趣创造才能使人充满想象。
语言洗练却不乏奇警。苏轼一贯讲究辞贵达意,出语自然,因此苏诗具有简古、淡泊的美学特征,不过,法度之中的用字常出新意。组诗(其一)通过巧妙用字来强调大雨的急促和势大。“翻”字的本义指鸟飞,强调动作的“变化”。“翻墨”合用,不仅形象地描绘出乌云涌动、变化的气势,同时在黑与墨之间也显示出颜色的层次性,画面感强。第二句中的“入”字,包含四两拨千斤之技法,力量十足。同样描写珠子,比较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盘”,“落”与“盘”组合,大珠小珠落入盘内产生时间差,读者从听觉上感知到“落”的参差,珠子落盘之后给人留下“叮叮咚咚”的错杂之声。而苏轼将“跳”与“入”组合,突出的是动作,水珠自下而上、纷纷攘攘溅入船内,说明量大、势急,读者从视觉空间上很容易捕捉到大雨的颜色、形状和动感,形神兼备。因此,“跳”与“落”相比,气势上就大了很多。第三句用虚词“忽”入句,散文笔调,简练朴素。更重要的是,将阴平放在七律第五字的位置,便于重读和发长音,句眼处便可读得十分响亮,增加了不少气势。纵然黑云挟有如虹压城般的气势和白雨如注的磅礴之势,都不及卷地风的力量,卷地风“忽”地瞬间出现,黑云和白雨便即刻消亡,望湖楼前水面顿时变得平静如常。一个“忽”字,在全诗意境由细密到疏阔的切换中贡献最大。
虚实结合,清雄互渗。全诗由实起笔,中间两度由实向虚,以虚终篇,虚实交替,跌宕有致。组诗先从实景起笔,黑云、山、白雨、船、卷地风、望湖楼都是雨景一部分。鱼鳖、荷花、月亮、乌菱、白芡、青菰、游女、翠翘等为雨后诗人眼中的自然景象。对于雨景,作者通过突出变化来展现不同景物。如其一前两句密集使用动词,“翻”“遮”“跳”“入”等词气势不凡,节奏感强。第三句力大势沉,当如撞钟,为第四句戛然而止的收束提供转承,一气呵成。其一前三句雄放,结句清净平和,清音有余。文笔上的简淡与疏阔、节奏上的密集与舒缓、风格上的刚劲与柔和全部融合在一起。对于雨后的自然景象,苏轼用平淡的笔端指向雨后人们祥和恬适的生活,自然景物反倒成了陪衬。组诗其三其四结构相同,前两句写实,没有难字僻句,作者在朴实平静中描写自己雨后的感性体验。后两句触景生情、由实而虚,从个人生活的快乐场景到官场政治的寂寞失意、从作者自身到诗人屈原、从会灵观到楚辞,由感性体验到理性升华,为组诗最后一首“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直接抒怀做好铺垫。这样,作者将雨前、雨中、雨后景色,以俯瞰、仰视、平视的观察视角,加上自己的想象与情感,融触景与感事、生情、议论于一体。全诗雄浑与清雅并存、骞腾与清远互渗,波澜起伏。
在意象选择方面求奇尚怪。组诗中尤以第一首的物象融入了作者较为丰富的主观情思。在日常生活中,黑云、白雨这类自然现象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给人带来不便甚至造成威胁。所以,艺术作品中这类物象往往指向现实世界的破坏势力。在中国古典诗学中,黑云意指敌对、黑暗,如“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雁门太守行》)、“战处黑云霾瀚海,愁中明月度阳关”(钱起《送张将军征西》)。暴雨和黑云类似,具有破坏力,传达畏惧和担心。“人心失去就,贼势腾风雨”(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冷落闲门,凄迷古道,烟雨正愁人”(高观国《少年游·草》)。苏轼选择这些丑象入诗,一方面是宋代同时期文人求奇尚丑的风气使然,非雅致意象频繁见于诗作中,苏轼难免随顺俗流而为之;另一方面则是诗人在艺术形象塑造中的刻意铺垫,用黑云、白雨这类丑象的黑暗反衬出卷地风的威力与光明。
苏轼深谙比兴象征传统,“卷地风”是诗中最具开拓性的艺术形象。将传统意象翻新,扩充其内涵是本诗反常合道创作的精彩之处。就自然现象来说,卷地风在本质上和黑云、白雨一样,都有来势迅猛、让人避之不及之意,容易唤起人的抵触情绪。但在本诗内,苏轼却给“卷地风”增加了新的意象。“望湖楼下水如天”是结果,“卷地风来忽吹散”是原因。吹散的对象作者没有明确指出来,但联系前两句,可知是卷地风吹散了黑云和白雨。“黑云”和“白雨”为破坏势力,已被作者赋予了“恶、丑”的品质形象。“卷地风”与“黑云、白雨”成对立鼎峙之势,对应为“善、崇高”品质,是一种重建力量。这种对卷地风意象赋新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开创性地给卷地风增添了新的象征意义。如同雪莱《西风颂》中“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的西风,是权威力量的象征,在与其他自然力量较量中,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卷地风与组诗(其四)中的传统香草杜若并列,分章互见,是已被情感化和人格化的形象,作为主体人格的象征。作者寄意深远,希望借卷地风超自然威力形象获得精神鼓舞,在暴风骤雨的政治斗争中,卷地风所象征的正直贤明之人会及时出现,外抚四夷,内亲百姓,最终给人们带来稳定、和平的曙光,因此,卷地风扫除黑云白雨是苏轼追求美政理想的一种隐喻。
从传统审美角度看,一味以追求奇特为趣味,显然会给一贯重视雅正的古诗接受带来不利影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苏轼对此自然是明白的。显然,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原因有二:一方面是诗人自由个性所然,要满足自己在创作中一贯尚奇求怪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将客观物象和主观心象进行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诗人的情感世界。根据吴乔“情乐则景乐”这一观点[7],便可推出,景不乐则情不乐。所以,此时望湖楼上的苏轼一定是心有郁结。
三、忠君待举的理性投射
心有郁结的苏轼离开党争的漩涡,登上望湖楼,此刻并没有心情赏景,写诗是以理性的超然姿态回应政治纷争。
在北宋中后期,文艺的本体精神是理性。宋代士人好发议论,无论是在朝堂上发表政见,还是在学府中商讨学术;无论是干预政治,还是描写民瘼,都倾向于把议论当作阐发感悟的途径。宋儒朱熹总结为“道者,文之根本”[8]。理性精神的崛起常常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弘扬,所以该时期的诗词或多或少包含理性成分。
从外请任职到熙宁五年六月这段时间,可以看出苏轼的创作都从现实出发,以艺术的笔墨投射到内心。“几乎没有哪一时的内心世界的波动不曾表现在诗里,故读苏诗等于听他一生的诉说。”[9]444例如,在赴杭州途中的几首诗。“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这几首诗中无一例外都有“我”,这一阶段往往渗透创作主体的情感旨趣。《泗州僧伽塔》中更是多次以自我身份抒发情感,“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这些都是苏轼留下情感痕迹的印证,是在官场受到挫折后情感的直接投射。这不难理解,因为“诗和艺术是人的心灵对生活的投射”[10]。
苏轼的情感倾向是要通过诗歌创作表达政治上的失意,至少《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这首诗如此。不然,一次登临、一场雨,如何让一个人记得那么清晰?当时间过去十几年后,作者对过去的事情依旧记得很清楚。“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即可说明这一点。纯粹一场雨,没有情感主导,是很容易被人忘记的。时间已经过去十五年,且在饮酒的状态下,作者还记得当时下雨的情形,说明这种外部感知和内在情致是互有关联的。换言之,这次雨中登临是情感触发所致,绝不是疾风骤雨本身让作者陶醉其中。
苏轼在组诗内留下的思想感情痕迹是明显的。组诗五首尽管内容各异,但其内部主题统一,每首诗在情感上都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因此对本诗的解析不能独立开来,应该放到组诗整体的构思当中,才能透彻、全面把握作者的情感。顺着组诗的意脉顺藤摸瓜,从其五“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和其四“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招”即可窥见作者理性的言意观:理性、忠君。
北宋士人具有传统儒学忠君思想的典型性。《礼记·儒行》中对士人的告诫是“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11]1399-1400,“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11]1401。宋代士人在开明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儒学“忠信、忠君”思想代代相传。“事君必忠”就是苏氏家训一直所强调的一个方面,以致有学者认为,“‘三苏’的忠君爱国思想是贯穿人生始终的”[12]。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也十分重视君臣关系,“堂不可以卑而乱制,君不可以黩而不尊”透出“欧阳修自我的忠君思想”(《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13]。如此,苏轼继承了儒学、先祖和老师的遗训,忠君思想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组诗内表达出来。“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招”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否则,纯粹的写景诗内不会出现“吴儿”“楚辞”“杜若”等含蓄深远的字眼。这也说明,作者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表达忠君之节。
苏轼的忠君之节隐含在组诗其四,其中对“吴儿”的理解是关键。对于该词的解释历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围绕“吴儿”是实指还是虚指展开。实指派认为“吴儿”指吴地的人,虚指派则认为苏轼在这里采用借代手法。从苏轼其他诗作来看,“吴儿”在诗中既有特指,也有虚指。特指吴地的人有:“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案注解“水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14]485。这里的“吴儿”即“民”,特指两浙地区的人。“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将之湖州戏赠莘老》)案注解“吴儿”指唐吴昭德,吴兴人,善造鲈脍[14]396。“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一》)案注解“七年,楚杀巫臣之族,巫臣乃通吴于晋,教之射御战陈,吴始伐楚”[14]564。“吴儿”指吴地的人。虚指的有“空使吴儿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闽路”(《送张职方吉甫赴闽漕六和寺中作》)。依注解:吴儿,木人石心也[14]335。可以看出,苏轼用“吴儿”入诗,依据情境,虚实皆有所指。
外部分析缺乏足够支持,只能转向文本内部去寻找作者的原意。首先,从句法关系角度,“吴儿不识楚辞招”支配关系中的核心词为招,招即《楚辞》中的名篇《招魂》,《招魂》的主题是“召唤、回来”。其次,联系上下文语境,前面一句是“无限芳洲生杜若”,前后两句构成转折关系,既然“杜若”象征忠君,那么“楚辞招”和“杜若”就成了同一类指。再者,从情景语境分析,主观上,作者在失意中表现出无奈,“聊中隐”就是一种无奈选择,是紧承“吴儿不识楚辞招”发出的无奈。因此,“吴儿”是苏轼在本诗中的陈述对象,即北宋朝廷或者宋神宗。正因为朝廷对苏轼的不理解,被召回朝廷工作一时无望,诗末最后作者才表达出失落之情。
再来看杜若,它原本是一种林下地被植物,被屈原用在文学作品中。不过,杜若在屈原笔下并无香泽之态,它被塑造成为香草美人,目的在于用杜若表达忠君之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15]苏轼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传统。因此,杜若在组诗中作为苏轼主体人格的写照,具有明显的伦理特征。通过效仿屈原的离骚之文,苏轼引类譬喻,延续了杜若为忠君文化的象征。
如果说组诗其四是忠君思想的表达,那其五就是苏轼在行动上的呼应。外任期间,在等待云销雨霁、彩彻区明的这段日子,苏轼该怎么做呢?组诗内“未成小隐聊中隐”与“卷地风来忽吹散”遥相呼应,苏轼以超尘脱俗的气质,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儒学士人,在他深层文化意识中,当身处逆境时应该“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11]1409,“聊中隐”就是对儒者“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的自觉践履。正如他自己所说“君子循理而动,理穷而止,应物而作,物去而复”[5]399-400,静以观物中等待“卷地风来忽吹散”那一刻。这不难理解,对于出仕不久的人来说,政治思想一般都处于上升时期。因此,远离京城之后,苏轼之前优游浸渍的处世哲学必须调整,“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11]1400,是处于人生低潮的备豫者苏轼德行的恰当诠释。
综合以上所述,光从诗的语言角度看,解读苏轼的这篇组诗就非常复杂。作品中一部分笔墨用于纯粹写景,如其二、其三。如果单独将组诗其一独立成篇,也属于写景范畴,但如果放在组诗整体中,那些自然现象就已经上升为哲理。组诗末尾借景抒怀的痕迹比较明显,“未成小隐聊中隐”是诗人壮志难酬、退避无奈的选择。此外,政治上的纷争又是作者抒发情感的起点。如果我们遵循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告诫,则可以从写景文辞的蒙蔽中跳出来,将作者主体意识及全篇旨意置于首位,在“七二一”式精妙结构中感受作者笔下的景物与情致,即组诗按照“七分写景、二分抒怀、一分政治”来理解。
将诗置于历史语境来看,苏轼动人之处是“以超尘脱俗的气质, 寓意于各种形式的文化创造活动, 从而展示其文化性格内涵的丰富性”[9]575。站在望湖楼上,苏轼俯瞰大自然洗礼的各色景物,骤雨疾风之后,眼前留下的是一湖静水,清景无限,大音希声。作为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备豫者,苏轼在政治漩涡中拒绝俯仰随俗,在望湖楼上,在水平天阔的映衬下,珍以待聘,怀忠信以待举,在平静、规矩中守候一份儒者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