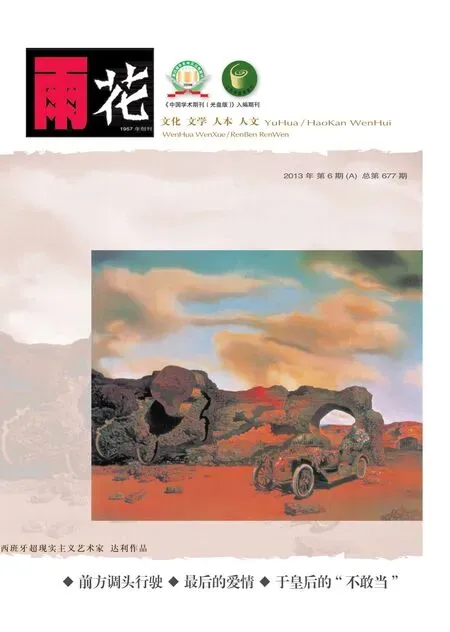最后的爱情
游利华
林奔走过来,心照不宣地冲白雨笑笑。仿佛一道光射进黑屋子,白雨突然都明白了,她早就听说林奔跟方总不和,上一次去美国,就是因为一桩订单,跟方总闹了矛盾愤而辞职。
白雨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林奔的情景。当时她跟林芳在卧室聊天,步入客厅时,一个戴着眼镜相貌儒雅俊秀的男人冲林芳挥了挥手,手里还拿着一块芝士炸薯饼,姐,你什么时候也玩起厨艺来了?手艺还真不赖。林芳指了指身后的白雨,我玩什么厨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辈子最怕进厨房了,这都是白雨做的,人家送下来给我尝尝。
热爱生活的女人才是最可爱的女人。林奔把眼睛转向白雨,微微点了点头,认真地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眼。
这一眼,像一束光,一束温暖刺目的光,金灿无比。
现在也是光,深圳夏季的阳光。千根万根银针刺得白雨忍不住眯缝着眼,她拉下办公桌左边的细竹条窗帘,一阵急切的电话铃响把她从回忆里拽回来。
是茗佳猎头公司的小刘,喜洋洋地在电话那头报告一个好消息,白小姐吗?你们要的人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回,包你和林总都满意。
初荷走进办公室时,仿佛一阵习习的清风顺着她的白纱裙溜了进来,她迈着小碎步,踩着清风,裙子一扬一飘,清秀瘦弱白皙得像《聊斋》里狐狸化作的女子。你好,我是初荷,是这儿需要招聘总经理秘书吗?她的声音也弱不禁风,细得像风里的歌声。
其实初荷并不算漂亮,起码在前来应聘的十几个女孩中,她的外貌还排不进前五,茗佳猎头的小刘却一口咬定她和林奔都会一眼就喜欢上初荷。白雨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她带到林奔办公室,林奔礼貌地泡上茶,问了几句,初荷就递过来几本杂志,翻开其中一页,点了点,这是我写的诗,十六岁起我就喜欢写诗,大学里还参加过诗社。林奔微笑着点点头,接过来仔细看着,嘴角的弧度变弯了些,又忍不住更深地点了点头,不一会儿,他抬起头,弯起两根指头在桌面敲着,挺好的,我看这样,你回去准备准备吧,下周一,就到白小姐那儿做入职报到。
早在两个月前,方总和副总林奔的秘书因为一个过失,被林奔毫不留情地辞了,寻找新秘书的工作,自然落在了刚到公司没多久的人力专员白雨的身上。深圳女孩多,漂亮又有学历的年轻女孩也不比牛毛少,她们像相亲一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辗转于各种人才市场。林奔一再强调,漂亮当然是前提,但不能光漂亮和有工作经验,方总常常在办公室里看诗集,你就给我们找个也喜欢诗歌的来吧。
晚上是公司月末聚餐,也是白雨试用期满正式转正的日子。方头大耳的方总拍了拍她的背,白雨,你的面子可真大啊,林总亲自把你要到公司来不算,还要给你开庆祝会。
林奔嘿嘿地望着白雨笑,脸上浮着与他的儒雅不相符的心照不宣。公司里的人都说,林奔和白雨关系不正常,至少不会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可只有白雨知道,他们的关系从那一眼后,就不正常了。
那一眼是绝好的醍醐,冷不防地自她头顶倾盆而下,她不单是头脑清醒了过来,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清醒了过来,明白了一种叫爱情的东西。
只是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他们,依然各自生活,风平浪静,其间,有雨雪霏霏的凄凉,也有杨柳依依的风光。凄凉的,是白雨,自那次与林奔初见后不久,她和丈夫冷战了半年的婚姻终于用一张大红的离婚证画上了醒目的句号;风光的,自然是林奔,他辞职去了美国,听楼下的林芳说,是去某大学做访问学者,顺便还带了他娇小可人的妻,林芳边说边叹了一口气,奔奔也该去外国转一转了,他工作太忙了,连休息日都没有,陪家人吃个饭都奢侈得很,我还劝他干脆留在美国算了,做大学老师多好,搞搞学问看看书,比在公司做那个窝气的副总强多了。
林芳在说这些话时显然没注意到白雨的神情,白雨怔怔地望着她的嘴唇,它们像两片发动机,嗒嗒嗒,嗒嗒嗒地发出频率相同大小相仿的声音,她努力想要听清她后面说的什么,耳朵却不争气地嗡嗡嗡一片,只能强忍着泪水与头昏,扶着门框不让自己瘫倒。林奔走了,也许再不回来了,他们俩不过在林芳家一起打了几次麻将,他或许还没记住她的模样。想到这儿,白雨赶紧冲进厕所,黄豆大的泪滴打在手臂上,生疼。
厕所墙上大方镜子里,印着一张黯黄瘦削的脸,左边鼻翼下的法令纹不笑也挺明显,幸好一双顾盼有神的眼睛挽救了这一切,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三十五岁稍微年轻一点点,也不过是比芝麻粒还小的一点点。疯了,真是疯了。白雨使劲揉了一把脸自言自语,人家三十五岁相夫教子,炒股开店,她的三十五岁,邂逅了一场爱情。
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有人开了舞灯,放了卡拉OK,包间里立即有了气氛。
白雨握着一瓶啤酒,跟一位男同事聊天。男同事说白雨你这个女人很奇怪,公司里别的女孩都有个女孩样,你没有,瞧你穿的这身衣服,地摊货似的,哪个男人会看上你。白雨大大咧咧地给了他一巴掌,人家是做投资,我这把年纪还做什么投资。男同事又恍然大悟地看她一眼,凑过去小声说,那当然,你还投资什么,你和林总都确定关系了吧。白雨呸了他一口,站起来混进人群跟着扭动,让他们去乱说吧,她白雨才不会在乎呢。
昏暗的灯光里,林奔和几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桌,有说有笑。林奔站起来,端起一杯红酒,跟几个人逐一碰了杯,然后坐下,轻轻摇晃着手里的高脚玻璃杯,俯下头吸了一口气,一定是在闻酒香,这一招,是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学来的。林奔说,红酒闻着其实比喝进嘴里感觉好多了,他喝多了红酒还容易醉,一醉就容易控制不住。白雨问他美国好不好,林奔说好,白雨又问他既然好,怎么只待了半年就回来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深圳也好,有时觉得美国也挺像深圳的,所以,还是回来吧。白雨有些失望,他没提那些她发给他的邮件,一个字也没提,也许,她自我安慰,隔着一片无边无际的海,它们字字句句碎进了气流里,他没收到吧,又或许,是林芳给她的电子邮箱地址不对。
这一次回来,是转了一个圈,应上海总部的请求,又回到了原来的公司原来的职位,惟有一样不同,林奔带来了白雨。他在电话里温柔地说,小雨,别一个人闷着啦,到我这儿来吧,跟我一起干,有我饭吃就有你饭吃。平时嘴快牙利的白雨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眼泪又泉水般咕咚咕咚地冒出来了,他一定都知道了,她离了婚。
林总,来一个嘛,来一个嘛。有人大声提议。
白雨还没反应过来,后背被人猛地推了一把,忍不住打了个趔趄。
林总,亲一个嘛,人家白雨都主动上来了。人群开始起哄。
什么亲一个,你们搞什么。白雨有些生气,他们还真把他俩当情人关系了。几百人的公司里,确实有几对情人关系的同事,公然喊老公老婆的也有,可白雨不是那种人,她绝对不是。
但是她动弹不得,已经被人包围起来,她想叫,两只手下意识地推搡,右脸上意外被人吻了一下,她愣了一下,右脸上又被人吻了一下,这回更重了,她扭过头,跟林奔四目相对。
灯光已经全部打成暗光,褐黄得像琥珀色的酒液,他们在酒里,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但白雨还是感觉到林奔在笑,那种时常挂在脸上,心照不宣的笑,她拍了拍他的肩,像往常俩人聊天聊到兴头处,林奔,坐回去休息会儿吧,你有点喝多了。说完她仰着脖子狠狠地喝了一口啤酒,挤到旁边,继续与人扭臀送肩地对跳恰恰。
初荷是个极其安静的女孩,这种安静,跟办公室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方总果然对初荷也很满意,第一天晚上,就带着她去跟客户吃饭,还郑重其事地介绍给别人,这是他的新秘书初小姐,中文系毕业的才女。
一到下午,办公室里便弥漫着一股近乎凝固的沉闷与烦躁,让人无比压抑,往往这时,林奔会借着休息的机会找白雨聊几句,大部分时候,是林奔说,白雨听,他的话不多,跟白雨在一起却变成了话痨,江水般滔滔不绝。
许多时候,白雨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迷恋林奔,他其实并不是她心目中完美的形象,甚至相去甚远,他不挺拔,也算不上才华横溢,甚至不太阳刚。她是中了某种蛊,那么,放蛊的人是谁呢?白雨不去想,没什么好想的,爱情这东西最说不清楚,何况还是当局者本人。
今天下午,林奔依然找她聊天,先问她租屋里的空调买上了没,天这么热,要是没钱,他可以先垫上,接着又聊了些工作上的事,末了,他望望窗外说,近来天气这么好,也可以搞搞旅游活动,让公司的人出去放松放松嘛。白雨正要走,他冷不防地又抬起头,支吾着压低了声音,小雨,上次晚上那事,真的发生过吗?
白雨也怔了怔,随即却莞尔一笑,林奔,你一定忘了,你那天喝醉了。林奔还要说什么,她头也不回地出了办公室。回到座位上,照了照妆镜,才发现眼圈红红的。
她还能怎样呢?听说林奔的妻子近来怀了孕,他们一直想要个孩子,那个小鸟依人般的女人,有一张极漂亮的脸,声音娇嗲,是林奔一个朋友公司的文员。林奔曾经说过她有许多想法都很奇怪,他无法理解,她也时常听不懂他的笑话。但他们依然在一起平静地生活了四年。
晚上白雨例外地没有加班,在夜幕中走出了办公大楼,汇入了人流与车流。
深圳的夜迷乱而繁华。提着公文包坤包的男人女人面无表情地等待公交车,面对面却视而不见地挤地铁。食馆百货大楼灯火通明,夜夜笙歌、朝秦楼暮楚馆,不过如此。白雨从公交车上艰难地挤下来,穿过小马路,打量着对面的几家快餐店,一个长得绿豆芽似的小女孩丢开一对情侣横过来拦住她,缠着要她买一朵玫瑰花。白雨扑哧笑出了声,小女孩一定是饿昏了,她需要什么玫瑰花,她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碗香辣的牛肉米粉。小女孩的花不好卖,没有人光顾,再怎样也不该向她推销啊。但白雨却意外地买了一朵,小女孩说了声谢谢飞也似地跑开了,玫瑰花在夜色里,黑糊糊一团,看不出模样也辨不出颜色,淡淡的香味却固执地直往人鼻孔里钻,有倔强和不甘。
回出租屋路上,白雨又去了趟麦德龙,明天是周末,早在前两天,她就已经计划好了,利用周末的时间做一个提拉米苏蛋糕,她已经有一年没做过这种点心了,以前跟前夫在一起时,她做过两次,前夫不爱吃甜点,她哄了他几次,他敷衍地咬一口,好吃。他说,脸上却木木的。鲜奶油、马斯卡彭、郎姆酒、巧克力粉……白雨念叨着,一一从货架上拿下。她想起她的前夫,那个看似老实得像一块老木头的男人。他比她小两岁,喜欢看各式各样的财经节目,还喜欢悄悄塞给她一件情趣内衣。她把他当小弟弟,记不起来她怎么与这个小弟弟上了床,事后才发现,他还是第一次,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来,像伦勃郎的油画那样明亮厚重,一块一块堆积在她和他身上。她竟然哭了,哭得差点昏厥过去,头一回动了结婚的念头。
但是白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正是这个老实人背叛了她,五年后,他出了轨,刚刚搬进他们一起供上的新房第二年,他就出轨了,趁她出差,明目张胆地将女朋友接到家里同居,他们睡的床,一定是他和她睡过的那张,家里惟有一张像样的床。白雨从此就只在沙发上睡觉,一看见主卧里那张标准双人床,就要犯恶心。
周末的晚上,她总是睡得迟,电视里在播一部侦探片,单身女人被人莫名谋杀,两个男人抬出来,单架上,一块巨大的白布遮盖着她,露出两只光光的脚。白雨本能地往后一退,打了个冷颤。
她闭了闭眼睛,努力回想林奔的模样,又打开冰箱清点晚上购买的材料,手指饼、鸡蛋、咖啡粉,一切也都好,如果愿意,她现在就可以动手做一块香甜的提拉米苏,作为明天一大早的早餐,太阳新鲜又温暖,照着她的小木桌也照着漂亮的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太大太腻,最好能一家人分食。
她的小屋,此刻与世隔绝,惟有玫瑰的清香是触手可及的。
方总嗜好诗歌这一点,是初荷来了以后,白雨才认识到的。不单嗜好,白雨还看过他写的诗,初荷忙完手头的工作,帮方总整理办公室时翻出来一个笔记本,拿来给白雨看,嘻嘻念道,《渡》,我与佛一起坐在渡口上,回忆三月的江南。
什么嘛。初荷皱着眉,佛怎么会回忆三月的江南呢,那可是草长莺飞的人间呢,胡扯。
她又来借彩色打印机用,说要帮方总打印诗歌专辑。有时他们也关进办公室大半天才出来,白雨想,除了谈工作,方总大概还跟初荷研究诗歌吧,公司里,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方总谈过诗歌,难怪方总气色越来越好,看不出,平时严肃、做事干练利索的他还有这个嗜好。
阳光灿烂的周末,公司去了一个附近的小城市做短途旅游。备选的地点有几个,最后由林奔做了决定,去一个有连绵荔枝园的地方,听说宋朝的苏东坡以前也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还写下了被人背烂了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正是荔枝成熟时节,他们一人向果农交了五十块钱,冲进荔枝林。成串的累累红果实,吊得树枝都垂折了,方总跟初荷守着一棵树,方总拉树枝,初荷踮起脚摘最大最红的。白雨看着他们,无端想起杨贵妃和唐玄宗,这个小城的荔枝,听说许多年前已被列为朝廷的贡品。然而它的鲜美又异常短暂脆弱,离了枝在人间只短短两天,便香消玉殒,憔悴干瘪了。
吃过晚饭,林奔建议去游泳,白雨换了泳衣,游了一会儿,躺在沙滩上看星星,等林奔上来也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就在月光下信步。
我已经去关外看过了,有个厂房位置价钱都不错。林奔说。
什么时候出来单干?白雨侧过头看着他,这样的话,他已经说了不下十次了。
你愿意跟着我吗?林奔没有直接回答。
当然,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白雨坚定地点点头。
傻小雨。林奔不好意思地笑笑。
白雨心头一惊。她惊奇的是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话,她跟着他做什么呢?只为天天能看见他吗?二十岁时她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三十岁时也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现在,经历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她反而这样一根筋地爱上了一个人。
林荫道里很安静,林奔边走边说着自己办公司的打算与计划,他是个办事周全的人,包括将来财务如何管理,也想到了。
白雨渐渐落在了后面,隔了几步,她看着他,他的背影挺直匀称,月光像一个多情的文艺女青年,把他的背影渲染成一个好看的剪影,像她多次想像过的背影,但又不像。
不知不觉,他们竟已经走到宾馆,看看夜色已晚,不如休息。林奔住房在一楼,他边掏门卡边笑着问白雨,你不进来坐坐吗?
进去干嘛?白雨抹下他的手,责问似地说。
干嘛?林奔装愣地摸摸后脑勺,聊天,我们聊一个通宵。
无聊。白雨拍了拍他的脸,转身离去。
林奔还在后面叫她,她没有回头,他还是把她当小妹,她加快了脚步,鼻子猛地一酸。
站在门口的林奔摇了摇头,准备关门的一瞬间,一个白影飘了过去,前面是方总的房间,那个白影有些像初荷。他的脸上又挂上那种心照不宣的笑。
进入八月份,天越发热了,办公室里数百台电脑同时发出嗡嗡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闷闷的热气,电话铃声、说话声、传真、文件、客户……开着低温度的空调,也让人心烦意躁。
有人悄悄告诉白雨,上次吃饭看见林总的老婆,肚子大得快要走不动了,林总扶着她,像扶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瓷。接着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白雨,白雨被看得不自在,甩了甩头,瞪我干嘛,关我什么事,你说的这些统统都与我无关。
确实,她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上班、回租屋、睡觉,周末有时去红树林公园看鸟,有时去超市采购几包吃的,回来按书上的步骤做点心、做一道复杂的菜,也给林奔留一点,去公司时带给他。她心平气和,像红灿灿开在山里的映山红。
林奔去了上海总部出差,要一个星期,临走时,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一套白雨,让她没事去家里陪陪妻子小蓓,她一个人害怕。
俩人还害怕。白雨咕噜了一句,她指的是小蓓肚里的孩子。没想到小蓓也这么说,她在电话里告诉白雨,林奔根本没必要担心,家里请了一个白天过来做家务的钟点工,吃饭的事根本不用发愁,晚上有她和宝宝,睡得比什么时候都香。
这天白雨因为陪客户吃饭很晚才回到家。喝了点酒,头有些昏沉沉的,正打算睡觉,小蓓打来电话,说她不知怎么突然便了点血,一个人害怕极了。
你别急,会不会是搞错了。白雨安慰她,她又累又头晕,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就只想躺着。
不会搞错,下午还没事,你快来吧,小雨姐。听得出小蓓快要哭了。
白雨只好强忍着头晕疲倦站起来,打了的士,直奔林奔家。
刚出电梯,小蓓已经收拾好站在门口了,哭着要马上上医院,刚才又便血了,调理了一年好不容易怀上孕,万一宝宝有个三长两短,林奔和她都受不了打击。
尽管已是夜里九点多,医院里看病的人依然排着长龙,白雨帮小蓓挂了号,医生开出几张检查单,说要化验,白雨又是付款,又是拿器具,还要帮着小蓓交标本等结果,一边坐着的小蓓不好意思起来,小雨姐,你先歇歇吧。白雨白了她一眼,有什么好歇的,一口气做完了事。
原来不过一场虚惊,小蓓得了尿路感染,药无法吃,却要打吊针,护士推过来大大小小四五个装满药水的玻璃瓶。小蓓一看就吓住了,问她要打几个小时。
大约五个小时吧,你有身孕,还不能滴快了。护士抬起下巴望了一眼墙上的钟说。
小蓓啊了一声,白雨的头晕转成了头痛。她后悔晚上喝了那么多酒,现在脑袋里像长出一只手,一下一下地用力揪着她的大脑神经,每揪一下,她都要痛得禁不住浑身打个哆嗦。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白雨现在才明白,古人们守着更漏是什么滋味。
小雨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也没事。小蓓嗫嚅着说了一句,今晚的事,她实在有些抱歉。
我回去了,你换药水上厕所怎么办。白雨又白了她一眼,她不喜欢这个小鸟依人的小女人,从第一眼就不喜欢,那只手又在大脑里揪了一把,她痛苦地皱着眉头。
小蓓不再说什么,转过头装做看电视,白雨也不理她,她跟她每次见面,都没什么话说。
天气一天天转凉时,初荷和方总的事终于败露。
这天公司里一如往常地忙碌沉闷。一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不管不顾地闯了进来,大声嚷嚷着要找初荷。前台小张眼尖,认出是方总夫人王姐,偷偷溜进方总办公室,给初荷方总报信。
等王姐冲进方总办公室,初荷已经闪出了办公室,方总一个人坐在老板椅上,抬头一脸迷惑地看着她。
有事吗?这么急匆匆的。方总站起来,准备倒茶。
你做的好事,那个叫初荷的呢,躲起来就逃得掉了?王姐踢了一脚红木办公桌,气势汹汹地吼道。
找她做什么,她是我的秘书。方总把茶递给王姐,却被王姐一把打飞,茶水溅了一地一桌,也溅湿了桌上一叠写了字的纸张。
海子诗选。王姐尖叫起来,像被烙铁烫了一下。海子诗选,这一定是你写给那个姓初的情书。她一把操起来纸张,阴阳怪气地念起来,惹得围在门口的人一阵哄笑。
看看你们做的好事,你们做的好事。王姐疯了似地撕扯着纸张,撕完纸张,她从包里掏出一沓相片,“啪”地扔在桌上,有几张顺着桌面滑出去,方总的肿泡眼立即直了,竟然是他和初荷在办公室勾头互视微笑,还有一张是荔枝林里的,他拥着初荷,几颗鲜红的荔枝挡住了俩人相对的脸。
方总什么也没说,咚一声,重重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椅子吱地尖叫一声,无力地颠了几下。
林奔走过来,心照不宣地冲白雨笑笑。仿佛一道光射进黑屋子,白雨突然都明白了,她早就听说林奔跟方总不和,上一次去美国,就是因为一桩订单,跟方总闹了矛盾愤而辞职。
她很快也走出了办公室,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这个沉闷压抑的地方,可是,能往哪儿去呢,楼上楼下,依然是办公室,出了大楼,前后左右,依然是办公室,这城市里处处皆是办公室,她不过是一只蠕动在办公室里的小生物。
无处可去。白雨来到洗手间,想要洗把脸,却意外发现,初荷也在这里,正缩在角落,靠着黑色大理石墙面小声啜泣,单薄的肩膀一耸一耸,像暴风雨下摇晃的荷蕾。
是你害了初荷,白雨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是你把她找来的。你也是不纯洁的。
年底时,林奔携家去了上海,公司在总部给他安排了一个更高待遇更好的职位,小蓓生了个大胖儿子,高兴得像个孩子。
方总到底与初荷在一起了,他们像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夫妻,存钱买房,上街买菜购物,追着大吐黑气的公交车狂跑。还是方总坚持离婚的,当初他是公司的业务经理,怀着四个月身孕的集团总裁侄女王姐看上了他,于是,才认识半个月就直接升为总经理,现在,自然该还的还,他们离了婚,方总又成了净户出身。
也挺好的。白雨轻轻吐一口气,嘭地锁上门,她今天要搬家,林奔和小蓓把以前住的房子空了出来,林奔说她是他的小妹,小蓓说她帮了自己和小胖大忙,都热情地要让她搬过去,本来林奔让她也跟着去上海,在那边,有比这边要好的工作,但她固执地留了下来,也依然做她的人力专员。
房子还是老样子,四室两厅,白雨嗅到了淡淡的烟味,是她熟悉的中华烟,林奔喜欢的牌子,这房子里,充塞着林奔的气息与体味,像一层厚厚的壳,把她包裹在其中,其实,这城市里也到处是林奔的气息,他走过的路,吃过的餐馆,望过的楼房,那么,这座城市也是一座巨大的房子,把她包裹在其内,充塞满了那种钝痛里掺一丝蜜的感觉。
立冬的前一天,白雨开始在别人的介绍下与人相亲。内心里她还是爱着林奔的,那一次她差点就要恨他了,事后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她为什么要恨他呢,爱与恨,其实都是她一个人的选择。还要爱多少年,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正如她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要继续多少年。